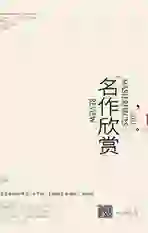乔叶小说中的女性群像
2021-01-25高会敏
高会敏
关键词:女性群像 生命样态 生存与困惑
“五四”以来,长期湮没于历史黑洞中的女性终于在欧风美雨的碰撞中“浮出历史地表”,庐隐、冯沅君、萧红、张爱玲……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以独有的性别体验把女性活着的不同姿态及其命运诉诸文字。百年时间倏忽而过,当代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建构也日益丰富和多元,而河南作家乔叶以其细腻、灵动的笔触把当代女性群体的不同生命样态和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切、立体地还原出来。这一女性群体包括在黄土地挣命的祖母辈,至今依然在乡间生活的母亲辈、姐姐辈,更包括由乡下走向城市的少妇辈、少女辈。她们或扎根于乡土,或漂泊在城市,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得她们呈现出不同的生存面相。但一代代女性群体所面临生存的艰辛和对生命的真切体验与困惑却是一以贯之的。
一
乔叶中短篇小说里的女性群像如一幅幅画卷绵延成穿越百年、横跨城乡的风景画廊,她们年龄不同,有老人、中年人,也有少妇、少女;职业不一,有大字不识的农民、辍学就业的打工者、创业者,更有通过求学进入城市机关的文艺青年、基层领导……在近百年的时间长河里,三代女性群体连接起乡土与城镇、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世界。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女性谱系包括一生都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祖母辈、大半生在困顿中度过的母亲辈、以“我”为代表生长于农村工作于城市的少妇辈和更年轻的少女辈。虽然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真实的自我呈现,女性自身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对异性的情感、生理欲望的真切感受常常被遮蔽,但乔叶执着地沿着女性主义作家的路径,以女性的视角大胆地表露女性的自我诉求与欲望,在呈现出不同女性自身生存体验的同时,也消解着男性作家对女性群体认知的话语霸权。
小说中对祖母辈女性及其生活的乡土世界的描述,在展示乡村女性遭遇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彰显出她们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祖母辈们多生于20 世纪初,几乎一生都在贫瘠的黄土地里摸爬滚打,艰难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大小苦难。面对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她们用裹着小脚的弱小身躯,依靠自己的心灵手巧、精打细算,坚韧地从土里刨食,艰难地养育着子孙后代,为整个家庭撑起一片天。《最慢的是活着》中“我”的祖母生于1920 年,虽然不识一字,但做过村妇女主任,好强能干,勤俭持家,一如刘震云笔下的“我姥姥”。祖母在丈夫参加解放战争牺牲后,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不仅拉扯大自己的孩子,还替代了忙于工作的儿子儿媳,把四个孙辈抚养成人,用柔弱的肩膀扛住一切不幸和打击,以顽强、乐观的心态面对孩子的夭折,丈夫以及儿子、儿媳的早逝。诚然,坚强、能干的祖母并非完美,虽然她的成长时间几乎与提倡女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同步,但生于乡村的她并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乡间的传统文化仍是她认知的唯一源泉。她固执地迷信在阴历二十出生的孙女“命硬”“克人”,为此还请风水先生寻求破解的办法。儿子、儿媳的早逝更让祖母坚信“命硬”的她和孙女能把人“克死”。与几乎所有的农村老太太一样,祖母“重男轻女”,认为闺女不算人,男孩子犯错无须责罚,但打骂女孩子却无关紧要。有了孙子辈,祖母会拿出她金贵的嫁妆做礼物,生男孩就赠银锁,如果是女孩则不送……这一切使得作为孙女的“我”与奶奶的关系一度紧张。祖母勤劳简朴、坚强乐观又因循守旧、盲从迷信,几乎是20 世纪乡村女性群体的化身。
作为祖母辈的延续,仍坚守在乡土世界里的母亲辈,虽然中晚年的生活有所改观,但她们仍像祖母辈一样勤恳、节俭。为了庄稼有个好收成,她们可以大热天去田里喷洒农药,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只要自己能干动的活,她们就舍不得雇机器收,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在田间劳作。诚然,她们身上也保留着农耕时代的乡土气息,安分、保守、闭塞,几乎没有现代科学常识,极度穷困的前半生使得她们在生活条件改善后更喜欢吃香甜够味的食物,喜欢穿大红大绿的喜庆衣服。她们不大愿接受新事物,女儿在省城给她们买的衣食不如在小城镇买的受欢迎。而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姐姐辈,比起前辈虽有了新变,她们可以借助农用机械,把自己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像前辈那样勤恳,如《月牙泉》中的“我”姐姐,闲暇时搓麻将成了她最好的娱乐方式;但是她仍像前辈们一样重男轻女、保守粗俗:“为了生个儿子,连生了六胎”,说话高声大气,碰到偶尔可以吃自助餐,猛如饕餮,连吃带拿。农村依然贫穷的现实让她们顾不上太多体面,而相对闭塞的乡村也让她们怯于尝试接受新生事物,不敢乘坐电梯。这一姐姐辈形象在当下的农村依然有很大基数,成为很少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乡村女性代表。而与她们同时代的姐妹们进入城市工作以后,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新面相。
二
改革开放尤其是21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由乡入城的打工一族成为庞大的社会新群体。乔叶小说真实地再现了青年女性在这一历史潮流的裹挟下由乡入城的奋斗历程。小说中以“我”为代表的少妇辈及更为年轻的少女辈多是在农村长大,通过升学或打工来到城市。视野更为开阔的她们不愿再把青春与激情留给贫瘠、落后、闭塞的乡土世界,而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入城镇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与前辈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塑造现代城市的同时,她们也在塑造新的自我。这一女性群体大多精明能干,又受过中高等教育,爱好读书、写作或曲艺、旅游等,不再像奶奶辈、母亲辈那样迷信、守旧,而是更为开放、时尚和精致。在求学、工作的磨砺中,她们学会了察言观色,审时度势,无论身处官场还是商场,都能凭借自己的机敏处理好各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她们仍继承了前辈们勤奋、上进的品格;另一方面,她们拥有更独立的自我意识。而精神上的自立与其经济上的独立密不可分,经济独立是她们进行一切自主选择的基础。
为了实现在都市经济自立的理想,凭着自己的机敏能干,她们在繁华的城市里开辟出全新的生活,走出了一条“没有锦衣,就自己给自己造一件锦衣”(《最慢的是活着》)的艰辛之路。《玛丽嘉年华》中的肖玛丽,中专毕业后即来到城市打工,很快就适应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乐于享受都市生活的奢华。而她的这一想法已与身在农村的父母辈格格不入,她特别想扎根城市,欣赏敢冲敢闯的男朋友,鄙视农村的破败以及农村男人的吹牛和俗气炫富、女人的爱嚼舌根。这一少女形象基本成为由乡入城的大多数年轻女性的代表。为了能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她们勤奋、节俭,如《月牙泉》中的“我”在城市的生活已經相当富足,但节俭的习惯俨然成了“我”的本能。每次住宾馆,“我”就会把一次性的洗漱用品装回家,以备家里来客使用。一次,“我”因开会地点离还在农村的姐姐家很近,跟姐姐见了一面,就把酒店里的洗漱用品连卫生纸一起送给姐姐。因为姐夫赌博成性,姐姐家已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因此“我”对姐姐的帮助也要精打细算。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在城市打拼的“我”们已没有祖母辈的质朴而更显精明: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还要琢磨如何应对领导和同事的各种小心思;既要坚持底线,不被牵着鼻子走,又不能得罪领导和同事,以至于后来在各种场合都可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诚然,繁华的城市带给她们的并非都是美好,当女性独自一人在城市中挣扎时,常常会伤痕累累。为了能脱离乡村,她们会选择出卖自己的青春之躯来获取物质回报,如《紫蔷薇影楼》中的小丫用出卖肉体来养活自己和爹娘,并完成将来发展的原始积累。表面上看,这是女性主动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事实上,这样的选择仍受男权社会的支配、控制,尤其是当官员嫖客利用权力继续逼迫她进行肉体交易,并与她合谋欺骗、愚弄其妻子时,年轻女性仍是男性利用钱权进行消费的工具这一事实就非常明了。而选择在城市打拼,有时还会付出高昂甚至生命的代价。《四十三年简史》中的“她”来自农村,中专毕业后被调到镇政府办公室。因为一心想要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她”拒绝在乡镇找对象,经营关系并很快被调进县城,工作之余她还兼职开起打印社,靠自己的勤恳能干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在成功调入省城后,她依然努力赚钱、投资,同时,她大把花钱,买各种奢侈品,供女儿到国外读书;另一方面又节俭成癖,“一块毛巾,洗脸用旧了,用来擦脚,擦脚太硬了,用来当厨房的抹布”。矛盾的她最终承认:自己骨子里、精神上仍是穷人。后来因为升职,她来钱更快,却在筹备女儿移民时得病去世。一直铆着劲在城市里辛苦打拼的她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快节奏的现代城市仿佛是一个巨型饕餮,用丰厚的物质作为诱饵,一步步掏空了那些用力过猛的女性们的青春、灵魂和肉体。
在由乡入城的时代大潮中,太多的乡村女性完成了农民到城市人的“华丽”转型,但其生活依然无法轻松,这几乎是现实生活里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乔叶在谈起她的小说主人公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小说中的‘她,没有名字,所以可以姓张也可以姓李,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是的,她们的经历何尝不是当下城市女性群体的代表?而她们用的小心思和小伎俩,作为读者的我们又何尝不用?我甚至常常疑惑,到底是如此驳杂的城市文明塑造了驳杂的我们,还是灰色的我们和另一半的他们铸就了灰色的生存空间?以至于在更具温情的两性之爱上,小说中的她们也能在欲望的不断升级中不得不保持冷静、拿捏分寸和精于权衡。
三
乔叶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群像虽然年龄、职业跨度大,在不同的生活境遇里有不同的面相,但作为女性,尤其是走入婚姻家庭的少妇们,却面临同样的问题和压力。虽然小说中的她们通常面貌模糊,甚至没有具体姓名,但她们在对庸常婚姻的疲倦,對婚外两性关系的渴望、尝试与失望上,则惊人的一致。乔叶通过一系列少妇形象的塑造,展示出她们隐秘、真实、缜密、复杂的内心世界。
在女性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工具的今天,婚姻并非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水到渠成。即便男女双方的结合源于两情相悦,琐碎的日子也会把婚姻磨成鸡肋。已婚男女在精神或身体层面的出轨也就屡见不鲜。因为男性在出轨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包袱,“成功者”甚至可以“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但出轨之于女性,则另当别论。当女性为婚姻牺牲太多却没有得到抚慰或回报时,对庸俗婚姻的质疑催生出渴望新鲜、刺激的精神及生理之爱的冲动,如《失语症》中的尤优、《打火机》中的余真,这与其说是源于耳鬓厮磨的审美疲劳,不如说是她们对俗世伦理、平庸道德的抗拒。但她们在抗拒中表现出来的瞻前顾后,也表明了几千年来横在女性心头的贞洁意识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长期作为历史叙事的盲点,女性自身的欲求被父系社会的秩序牢牢控制,性爱方面的欲求更被禁锢。这些有形无形的束缚一直延续到今天,让即使已经身处现代社会的她们也无法做到如男性般无所顾忌,彻底藐视社会舆论对男性出轨的宽容和对女性苛责的双重标准。因此,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即使有出轨的念头,也只把相恋严格控制在精神层面或上半身肌肤之亲,不轻易突破“贞洁”底线。于是,背负着更多的道德包袱与社会压力的她们,常在婚外情的边缘徘徊,既渴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欢爱,又不想在背离婚姻束缚的路上走得太远。如《走到开封去》中的“我”渴望从常规的生活中逃离出来,来一次彻底的自我放飞,便和一位不太熟悉的男性,由郑州徒步穿越小路走到开封去。《他一定很爱你》中小雅与昔日情人旧情复燃后,依然坚守着所谓“贞洁”底线。
女性对身体出轨的谨慎,也折射出她们对婚外情抱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一旦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出现后,她们会小心翼翼、反复掂量,异常冷静地在性与爱的边缘挣扎,把女性的敏感与算计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真的爱她?爱到什么程度?或者只是逢场作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在任何情况下,通奸、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渴望两性之间有灵肉的完美结合,并不停追问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旦发现男性只是逢场作戏,会让她们心灰意冷,而这一关系也会随之无疾而终。如《月牙泉》中,“我”的婚外情人用稀少、乏味的短信维护二人一年因开会亲密一次的两性关系,当“我”对这种方式感到彻底索然无味后,就中断了这场似有若无的婚外情。《妊娠纹》中,“她”与苏的关系最终止于肉体出轨,而她拒绝的原因由起初对身上妊娠纹的自卑转变为对情人薄情寡义的失望,并发出感慨:“她已经不会爱,只会算了。她曾经以为的爱,不是爱。只是……以爱情的名义在婚姻之外生发了出来,在他和她不谋而合的共同算计中,这种貌似的野性和棱角生发得很安全,安全得如同动物园里的动物。而她的算,却是货真价实的算,算得细,算得深,算得透,算得脏。”因为在婚外情中患得患失,她们常常琢磨对方是假意还是真心,盘算着彼此的付出比例,最终导致这些婚外恋常常以刺激开始,以无聊终结。乔叶小说中看似大胆又极为谨慎的婚外情叙事,不仅以女性的视角展示了乏味的婚姻生活,同时揭示出婚外情多半无聊的事实,在解构婚姻的同时也解构了婚外的两性关系。而这一切,似乎在指向一个事实: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导致她们渴望的理想性爱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乔叶以不疾不徐的耐心和细腻、举重若轻的灵动笔触,描绘出女性对两性关系的真实态度和精神诉求,将女性内心真实的苦恼、渴望、挣扎、失落写得细腻周到又惊心动魄,建构出当代女性群体的性爱感受史。无论她们身处闭塞的乡村,还是相对开放的城市,都能为了生存,以机智敏捷、勤劳能干为铠甲,在各种环境里所向披靡。但透过婚内婚外的两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她们真实的困惑与疑问:哪里才是可以自我放飞、实现灵肉完美结合的两性关系的地方?这是女性自我诉求的真实呈现,同时也是对庸俗双标道德的挑战。乔叶小说对女性内心世界的自我开掘和拷问,也预示着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真正能够放飞自我,实现对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突围,挣脱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义、塑造和制约,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