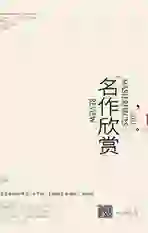与中文系学生谈唐诗的专业读法
2021-01-25蒋寅
蒋寅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要把自己读唐诗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分享,供你们参考。
首先我要说,艺术欣赏是非常主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欣赏方式。很多人说古典音乐听不懂,其实听音乐根本不需要知道音乐里面讲了什么主题和情感内容,只要听着觉得好听就行。这样音乐对你来说就没有门槛,读唐诗也是这样,要求不要太高,一首诗里有一个字或一句让你很喜欢或受到感动就行。一首五律,能挑出十个字来大家都认为好,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在前人已经写了无数遍的情况下,还能写出十个有新意的字,让别人看了佩服,这就是作者的成功。而作为读者,能感觉有十个字很好,也可以满足了,不要期望一首诗从头到尾每个字都让你精彩叫绝,那是很少见的。
但上面的话只是针对普通读者来说的,我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专业需要一种专业的阅读能力,一套专业的阅读方法或者说一种专业技巧。一个学文学的人看完一部电视剧,被它打动,就应该用一套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即艺术批评。批评不是天生具有的才能,感受力才是天生具有的,但是感受力并不等于批评能力。看戏,读诗,听音乐,虽然你有一肚子的感动,但只有用一套专业的术语把你的感动及其缘由说清楚,才能说是一个专业的读者。一个专业的读者需要掌握一套解读作品的方式。这个方式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从唐诗诞生以来,每个朝代的人都有各自的解读方式。作为专业读者,我们需要了解。
一个专业的读者,对作品的判断应该超越自我。如果个人意味太浓,那就叫趣味。所谓趣味,就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判断力,但又不等同于判断力。一个趣味好的人,我们说他有判断力。比如你听某人评论电影,他说的让你服气,你就会认为这个人判断力好;也有一些人,他很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虽然他也能说出一番理由,但我们可能不会认同他,觉得他太偏执、太主观了。从趣味上说他可以持个人看法,但从判断力的角度,我们会认为他的判断力和大家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说,我们心目中对判断力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那个标准就是基于专业阅读的一套规矩。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专业阅读的一套规矩,是传统的解读唐诗的方法,现代的专业阅读则有现代的一套规则。
体制
读诗的第一要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掌握“体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术语比较模糊,往往一个概念有不同的表述法。有些人就把“体裁”跟“体制”等同起来,把五律、七律的结构、修辞等要求叫作“体制”,这是不符合古人习惯的。“体制”主要与“类型”有关,而“类型”是文学乃至艺术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它和“主题”有关联但又有差别。比如说母爱是一个主题,但爱情就是一个类型。母爱是很明确的,就是讲母亲对孩子的爱;爱情则包括热恋、单相思、失恋等。所以爱情诗就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个类型。同样的,唱和诗、送别诗、都邑诗、游览诗,都是一个类型。有人会说田园是诗的一个主题,而我认为田园诗是一个类型。因为田园诗里有讽刺朝廷的,也有悯农伤时的,还有像陶渊明那样因脱离官场回归田园而感到身心愉快的。我们读诗首先要看它是什么类型,类型直接决定了它的体制。类型是诗的外在形式,体制是类型的内涵,读诗不把握它的体制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它。
举一个例子,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现在大概没人会否定它是一首杰作。但是明代最杰出的诗论家许学夷、清代学者也是诗论家王夫之都认为这首诗不好。王夫之说它“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认为这首诗前后兩截,意思不搭,有点牵强。我起先还以为的王夫之看到的诗题不对,因为宋本作《岳阳楼》,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作《洞庭湖作》,《唐诗纪事》作《湖上作》,只有《文苑英华》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后来看到他的《唐诗评选》,正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那么他的差评就是判断力问题了。这首诗应该是献给张九龄的,“上张丞相”可能原为小字题注,后或转写脱落,或乱入题中变成《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总之,这首诗不是游洞庭湖的即兴之作,而是一首干谒诗。干谒诗的体制要求是,首先你要证明自己是有才能的人,应该受到赏识,这是干谒诗最基本的要素;其次还要把你的目的说出来,请求别人提拔。我们来看孟浩然这首诗是怎么写的,有没有达到体制的要求。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首联两句总写湖水的广阔浩渺。下面两句是这首诗最精彩的部分,写洞庭湖的气势。“气蒸云梦泽”,写湖水的水汽蒸腾到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说波浪拍打着岳阳城,好像都能把它撼动。这四句把孟浩然的诗家之能事展现无遗,自我表现的任务已完成,接下去就要表明干谒之意了。“欲济无舟楫”是暗示自己想有所作为却无人提携,一般人这么说倒也无所谓,但是像孟浩然这样的高士,明白表达热衷功名之意,会让人感觉很俗气。于是下句马上补充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端居耻圣明”,说正逢盛世,不出来做官岂不辜负了圣明君主,有愧于太平盛世?《论语》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样孟浩然就为自己热衷于功名找到了古老而正当的理据。结联“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正像俗语所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把张丞相比作姜子牙,希望自己能像鱼一样被钓上去。希求汲引之意再清楚不过了吧?如此说来,诗是先总写湖,由湖自然地引出舟楫,由舟楫又自然地联想到钓鱼,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水到渠成,不露痕迹。作为一首干谒诗,至少从写作技法上说是非常成功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
王夫之认为这首诗不好,应该与他诗歌观念的偏颇有关。王夫之虽然有哲学家的头脑,讲诗歌理论每有过人的深刻之处,但他对诗的感觉并不太好。我在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理论的巨人,批评的矮子》,专讲王夫之诗学的缺陷。王夫之论学还留有明人的习气,好作大言,常有刚愎自用的议论。王夫之做理学而不做考据,在知识上就难免不够深厚。他的诗话议论也很精彩,但稍不留神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围,就捉襟见肘。他论诗不懂体制,经常抓不住要害,也很难对诗作给出准确的评价。
古人论诗一向是非常重视体制的。大概到宋代,作诗文评者已经意识到文学批评要先讲体制,所以王安石有一句名言叫“先体制而后工拙”。我们读诗或写诗也应该首先把握体制,然后再论工拙。文学批评并不纯粹是主观的,它需要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我们可以先了解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再判断他做到了没有。孟浩然献给张九龄的这首诗,是出于干谒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干谒诗的体制来确立批评的标准,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这是我们读诗要注意的第一点。
结构
第二点讲结构。掌握了体制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作品,这就进入结构分析的阶段。有了“体制”,我们便可考察作者是如何实现体制的要求,如何构思作品的。孟浩然这首诗的构思就是用湖的直接描写,引出一个比喻,也就是借咏物搭建起一个平台,然后在上面做文章,把表意的部分牵引出来。这首诗后半段整体是一个比喻,即古人说的“比兴”。
下面我们再通过咏史这一诗歌类型来看唐代诗人是怎么设计结构来完成体制的,这就是构思。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举三首七绝,李白的《越中览古》和《苏台览古》,以及窦巩的《南游感兴》,让大家对照着看看同样的主题诗人们是如何变换出多种写法、多种结构的。如果我們把怀古当作一个主题的话,它可以有很多表现的内容。像杜牧借怀古来讽刺当朝;像王昌龄借怀古来抨击现实,他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来感叹朝中无人;纯粹哀悼古代历史的消亡,哀悼文明的毁灭,通常也是怀古诗的内容。这些诗的立意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说怀古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个类型。它最基本的结构就是“今昔对比”,任何怀古诗都离不开今昔对比的结构。
为什么要举七绝来说明今昔对比的结构呢?因为七绝是一种典型的诗体,每句都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元人讲起承转合,就对应于七绝的四句。关于七绝,建议大家都读一读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很多我们以前读过的诗,看了沈先生的讲析之后,会发觉自己根本就没读懂。我这里讲的三首七绝,也是取自沈先生的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三首诗: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李白:《越中览古》)
前两句写吴越两国交战,吴王夫差攻破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用美人计又打败了吴国。第三句“宫女如花满春殿”,是说越国把吴国的宫女都掳到越国去了,后宫好不热闹。这一句平仄不合格律,合律应该写作“宫女如花春满殿”,但不知为什么,好像没有这样的版本。前面三句都写古,末句笔锋一转,以“只今惟有鹧鸪飞”写今,构成今昔对比的关键全在于末句的转折。转折是七绝常用的手法,唐人怀古类的七绝一定有一个转折,先铺垫,最后突然转出一个意外的结局,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这首诗的笔法,四句都用实笔,旨在说明当年那么威武、那么繁华的一个国家,如今也消亡了。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李白惯有的历史虚无感,但也不排除有一层讽刺的意思在里面:曾经破了吴国的越王勾践虽风光一时,但最终也逃不过女色亡国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首: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苏台览古》)
这也是一首怀古诗,抒发今古兴亡之感,但与前一首不同的是,这里用的是暗中转折的笔法。诗的前三句都是讲现在,直到最后一句“曾照吴王宫里人”才讲过去。西江月是现在的月亮,但末句既用“今月曾经照古人”之意,就暗中转到了古代。诗人想到过去的苏台是那么繁华,吴国的宫女是那么妷丽,而今人去楼空,只剩下旧苑荒台供人凭吊。前诗的“只今”提示了第三句转折,本诗的“只今”却因三四两句上下相贯,直到第四句才揭示今昔对比,而且字面上也没有直接点明今昔的不同,只是用“曾照吴王宫里人”引导读者去想象昔日的繁华。这是暗示性的虚写,言外说不出的感慨,将怀古的惆怅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来看窦巩一诗:
伤心欲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
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
(窦巩:《南游感兴》)
这首诗也是由越王的遗迹而生发的感兴。首句刚要追溯历史,次句马上就转写眼前的江水,暗示前朝遗事再不可追寻。因此这是欲转而未转,未转而已转,“前朝事”仍旧与后面的越王台遗迹构成古今对照,只不过是笼统的虚写而已,于是感觉更虚无渺茫。
以上三首怀古诗虽然主题相同,即抒发古今兴亡之感,但表现手法却很不一样。就类型而言,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咏史可以由书本知识生发感慨、议论,而怀古诗却一定是面临特定的场景产生相应的感触,因此怀古诗通常都包含一个今昔对照的转折结构。上面三首绝句无不如此,只因转折的方式不同,或明转或暗转,再加上回溯往古的虚实笔法不同,就产生了异样的效果。第一首最具有戏剧性的冲击力,第二首意味隽永而引人遐思,第三首情调最落寞怅惘而有浓重的历史虚无感。你们看,如此简短的四句诗,就有这么多的结构变化,营造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结构对于诗作的意义还不重要吗?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风格,读者对结构的不同分析,会对诗的意趣产生不同的理解。
风格
第三点讲风格。关于风格,文学理论书籍有不同的解释。对风格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作家在艺术表达中遵循的一些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使用的一些手法或一些程式的总和,也就是创作整体上呈现出的一种统一性。一般来说,只有成熟的作家,作品才具有风格(不成熟的作家就谈不上风格了),像唐朝的一些名诗人,他们留下来的诗作都有一定的风格。不过,风格是不是很明显,是否能让读者一下子感受到,就千差万别了。通常大作家的风格都很明显,给人鲜明的印象,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的独特面貌。但要注意的是,风格是由作者的许多作品共同构成的,如果你没有读过足够多的作品,就很难真正把握一个作家的风格。下面我们通过杜甫的《登高》来说明如何把握作家的风格: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这首诗被明代胡应麟推为唐人七律第一,引起后人一直不断的争论,也有推许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的。但不管怎么说,杜甫《登高》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后人谈到杜甫诗作的风格,一定会提到“沉郁顿挫”,用这四个字来概括杜甫的风格似乎也最为恰当。关于“沉郁顿挫”,古来论者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的理解是,“沉郁”指内涵的深沉浓郁,直白地说就是意义容量大,信息量大,纳入的内容多;“顿挫”按古人的讲法,是声情浏亮,节奏感强。但到清代,诗论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指诗句之间非平顺惯常的衔接。
诗的首联写登高眺望,第一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是往天上看,第二句“渚清沙白鸟飞回”是往地上看,都是写近景,十四个字写了六个事物,没有一个多余的闲字。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推开视野写远景,上句是空间轴的展开,“落木”点明秋季,又暗比衰老的自己;下句是时间轴的展开,江水不尽意味着宇宙的永恒。大家读过杜詩就知道,杜甫经常将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广阔相对举,以反衬人世的无常和渺小。这一联同样如此,暗示了在自然的广袤和永恒面前,人生是多么短暂而有限。诗写到这里,主人公还没现身,直到第五句才有这样的自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盛赞这一联,说十四个字里包含了八层意思:作客,常作客,悲秋作客,万里作客;登台,独登台,扶病登台,百年多病。如此密集的意义叠加,大大强化了诗的意义密度,使作品所抒写的事理格外丰富,情味格外浓厚,给人以深沉厚重的感觉,这就是“沉郁”之义。“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意思是:衰老多病已经让我不堪忍受了,现在竟又穷得连酒也没得喝!诗人在前六句中已经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写得很到位,第七句又把这种感情加以总结提炼,把读者的情绪推到顶峰,第八句不顺着写下去,却突然来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通常写到这种痛苦的身世之感,都以“举杯消愁”之类的意思结束,但是杜甫却反其道而行之,说痛苦而偏偏“潦倒新停浊酒杯”,这就形成一个急剧的转折,使前七句诗不断地铺垫、升腾到顶峰的情感戛然而止,跌落到更不堪的境地,从而构成一种落差(古人也叫“反跌”),造成一个出乎意料、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也就造成了读者阅读时情绪上巨大的起伏感,从意义脉络的角度说便是“顿挫”。
再从声韵上说,七律的中间两联要求对仗,一般作者能对得工稳已不容易,而杜甫以他过人的才力,不仅应付自如,还常常通篇使用对仗,这首《登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结句要求有回旋不尽之意,而对仗的两句一般是并列关系,不像一般句法的线性模式更便于推动诗意的发展,所以不宜用作收结。为此,《登高》结联采用了“流水对”的形式,上下两句的意义脉络为逆接,而非顺接,这就造成了读者情绪的波澜起伏,给人一种顿挫之感。大家仔细品玩一下《登高》,我想就能体会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了。
唐代近体诗格律定型后,人们写古体诗也常不知不觉地合乎近体声律。初、盛唐诗人对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还没什么意识,诗作中律句较多。从杜甫开始,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意识明显加强,写古体诗时往往有意回避律体。到中唐时期,诗人们对体制的意识愈加清晰,写古体诗时经常有意识地回避律调。这种现象在韩愈诗中显得很突出,我曾做过分析。有时一首古体诗长达几十句,从头到尾竟没有一句合律。后来我指导一个访问学者又对杜甫的古体诗做了分析,发现避律调的现象明显存在,其顿挫的诗风或许也与这种意识有关。这正是构成风格的要素,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首诗去剖析一个诗人的创作风格。
韵律
第四点讲韵律。这里说的韵律不是格律,格律是近体诗规定的平仄格式,而韵律则是诗歌语言的一种音乐性,包括字音的清浊、开合及仄声上去入三声的搭配。盛唐时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序言说:“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这里的“词与调合”就是指诗句有着和谐的韵律,即今天说的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那就绝不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那么简单的事了。清代诗论家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有这么一段话:
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浅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又如龙标绝句“不斩楼兰更不还”,俗本作“终不还”,便属钝句,此平仄一定法也。又如杜五言“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怨惜”换作“怨恨”,不稳叶,此仄声中分辨法也。
齐梁以来到初唐的诗人一直都在苦心探索和谐的韵律。所谓“四声”“八病”的总结,多半出于避免恶声的意图。但音乐性是很微妙的,很难总结出什么清楚的规律,只能靠自己体会。所以清代诗论家方贞观《辍锻录》说:“音韵之说,消息甚微,虽千言万语,不能道破,惟熟读唐人诗,久而自得。”例如张潮《江南曲》云:
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人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
这首诗的韵律非常谐畅,很关键的一句是“妾梦不离江上水”。有的版本如《唐音》《唐诗镜》作“妾梦不离江水上”。你们自己念一下,看哪个好听。是“江上水”更和谐吧?“江上”是叠韵,好听;“江水上”是隔字叠韵,在唐人看来是一种病,即“八病”中的“小韵”。再加上“江水上”平声+ 上声+ 去声的结构,和“凤凰山”三个字相对,“上”和“山”只差一个后鼻音,声音过于接近,也不好听。所以“江水上”无论如何也不如“江上水”来得顺口悦耳。填词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李白《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两句,词谱规定“汉”字必须用去声。词中的很多领字也是这样,如“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的“对”字,一定要用去声,表达一种急促而有力的情状,不能用上声。这就是韵律。当你们诗读得多了,能够体会到诗歌的字音配合之妙时,就能领略唐诗的韵律之美了。唐诗在这个方面做得是最好的,宋以后的诗歌望尘莫及。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载自己《送黄宫保巡边》诗有“秋色玉门凉”一句,蒋士铨看到说:“‘门字不响,应改‘关字。”你们体会一下,蒋士铨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又比如蒋学坚《怀亭诗话》卷三载:
昔人诗云:“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或谓藕花盛于六月,何不曰“六月”而曰“五月”?不知改“五”为“六”,便不佳。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谓“藕”字亦妙,若说“荷花”,便不成诗矣。
道理很简单,“五”和“藕”都是上声字,上声字念起来最能咬得住,换作入声字“六”、平声字“荷”,或急促或平缓,都咬不住,读起来就缺少起伏,不如“五月”“藕花”抑扬有致。
再举正反两个例子来体会一下。正面的例子是吴锡麒“酒人好似枫林叶,一日斜阳醉一回”一联,“斜阳”如果换作“夕阳”就不好听,太急促,出不来悠闲的味道。反面的例子是黄景仁《绮怀》其十六“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一联,“丝竹”若换作“丝管”会更合调,竹、入两个入声相连太急促,用个上声字“管”略见摇曳,方显得骨重神寒。
自然高妙
以上讲了欣赏唐诗的基本路径,大多数唐诗都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解读、分析。但有时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读到一首诗,只觉得它好,却说不清楚好在哪里,似乎也难以从上面这些角度判断高下。比如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古代有人说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它是好诗,但却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遇到这种情况,不妨用姜夔的说法来自我宽慰。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里曾说: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这不是姜夔在故弄玄虚,诗写到想落天外、妙手偶得的境界,确实就达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自然高妙之境。“自然”一向是中国古代美学的至高境界,也是艺术家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有的诗论家称之为天趣。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载:
吾弟超然善论诗,其为人纯至有风味。尝曰:“陈叔宝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维摩诘《山中》诗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舒王百家衣体曰:‘相爱不忍发,惨澹暮潮平。欲别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问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识其天趣?”超然曰:“能知萧何所以识韩信,则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诘,叹曰:“溟滓然弟之哉!”
对那些只觉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作品,我们只能称之为自然高妙,或天趣。
比较
最后再讲一点比较的问题。鲁迅说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于是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诗歌只写到唐为止。唐以后果真就没好诗了吗?要知道,唐诗现存不过四万多首,有名的、被收入各种诗选的就更少了,这是历史淘汰的结果。时代越往后,经历淘汰过程的就越少。离今天最近的清诗,基本上还没经过历史的淘汰,仅诗别集就存有四万多种,这就显得良莠杂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绝不意味着清代就没有好诗。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清代诗人——黄景仁。近代以来,自鲁迅、郁达夫、徐悲鸿、瞿秋白以降,很多文学家都喜欢这个人,我也很欣赏他,还为他编了一部选本。我觉得他的诗作把封建社会末期文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十分透彻,十分深刻。
黄景仁在创作上受李白和李商隐的影响很深,这里我只谈一下他和李商隐的关系。李商隐《无题》中有“昨夜星辰昨夜风,小楼西畔画堂东”两句,黄景仁反过来写作“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诗人怀念自己少年时代的恋情,异常动人。再如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达了相思之苦和绝望之情,黄景仁脱化成这样两句:“缠绵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二人都是用的比喻手法,李商隐的比喻更多的是强调结果,而黄景仁的比喻则是着重强调过程——相思像丝被抽尽的蚕茧,伤心如被剥剩的芭蕉,那惨烈的情景给人更直观的视觉刺激,把情感的缠绵和内心的伤痛表现得更为强烈,给人的印象也更加深刻。黄景仁写愁,道是:“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古往今来,多少诗人感叹时光的飞逝,希望时间慢一点流走,黄景仁却因对人生绝望而期盼时光快点逝去,以此表达人生愁苦之不堪忍受,构思多么奇特。再如写生活贫寒之状,说:“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直截而又淋漓尽致地写出对贫困的家境、多舛的命运以及孤苦无依的生存状态的复杂感受,在艺术表现上可以说是化复杂为简单,而正是这种“简单”给读者带来十足的震撼力。《癸巳除夕》是他在除夕之夜所作的一首绝句: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除夕之夜,别人都在家里乐融融地团圆度岁,黄景仁却孤身一人伫立于市桥,莫名地感受到一种忧患之情。此时正是乾隆盛世,这种忧患之感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因此他感到分外孤独。“一星如月看多时”,是说只能从一颗星星那里找到一丝慰藉。这种心情有点接近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但其中表达出的是一种与世界完全隔绝的孤独凄寂之情,是唐诗里不曾出现过的。唐诗整体上洋溢着一种健康的美感,而宋诗则更倾向于病态的美感。我曾形容这种现象,说唐人欣赏的是“肉感”,而宋人则对“骨感”情有独钟。黄景仁的诗歌把中国文人特有的漠视社会、与世隔绝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极为深刻,把读者能感受到的和不能感受到的东西都表达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对民国时期乃至以后的旧体诗写作影响极大。
最后讲一点我个人读诗的感悟。艺术欣赏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趣味和判断,至于如何养成,我认为广泛的阅读很有必要。要多读名家的经典之作,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杰作,杰作的好处在哪里。但一味地追逐好的作品,而把相对较差的作品抛之脑后,也很难真正體会到那些传世之作究竟好在哪里。读诗也不应该仅限于读唐诗,要放宽眼界,读一些宋元明清各代的诗,这样才能通过对比,看到唐诗的局限性,更好地欣赏唐诗。先师程千帆先生曾说,从唐诗入手的人往往会觉得宋诗佶屈聱牙,声韵不扬;而从宋诗入手的人则又会觉得唐诗写得很笨拙,不如宋诗那么灵巧。前人有唐人尚情、尚韵,宋诗尚意、尚理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唐诗都不是无可挑剔、绝对完美的。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高峰,但后代人绝不是没有超过唐人的地方。近代以来,像钱锺书先生那一辈学人,对晚清同光体诗家都很熟悉,多少会受到他们的熏陶,对清诗有一定的了解,1949年以后就很少有人关注清诗了。其实清诗中也不乏好的作品,一些成就最高的诗人水准也不亚于唐诗。与唐朝不同的是,清朝夷夏、满汉、官匪以及朝野清浊流等诸多复杂关系使清代士人内心的情感体验都要复杂、丰富得多,因此清诗思想的深刻性有时也是前人所达不到的。这是题外话了。
以上是我关于“如何欣赏唐诗”的一些个人见解,谨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多批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