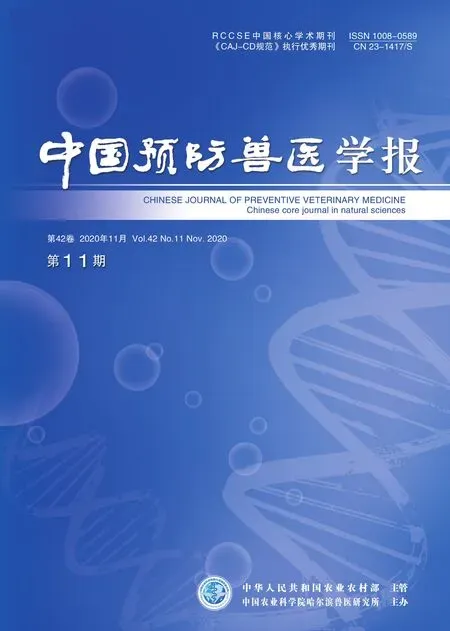基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官方报告的全球西尼罗河热疫情回顾与分析
2021-01-22卢亦杰程昌勇卫芳芳宋厚辉
卢亦杰,何 展,程昌勇,卫芳芳,蔡 畅,孙 静*,宋厚辉*
(1. 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中澳动物健康大数据分析联合实验室/浙江省畜禽绿色生态健康养殖应用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动物健康互联网检测技术浙江省工程实验室,浙江 杭州 311300;2.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fice, Murdoch University, Murdoch,Australia)
西尼罗河热(West nile fever,WNF)是由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WNV)引起,并由节肢动物作为传播媒介的一种人兽共患病,可感染蚊子、鸟类、人、马和猪等多种动物。在自然界中主要在蚊子和脊椎动物宿主之间循环,其中人和其他哺乳动物被认为是终端宿主,原因是它们不能产生足够高和长时间的病毒血症[1-2]。WNV 作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虫媒病毒[3],目前在非洲、欧洲、中东、北美洲和西南亚均有相关疾病的报道。WNV 属于黄病毒科(Flaviviridae),黄病毒属(Flavivirus)[4],在血清学上是脑炎病毒复合体中的蚊媒黄病毒,该复合体包括:日本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墨累谷脑炎病毒(Murray valley encephalitis virus,MVEV)、阿尔弗病毒(Alfuy virus)、乌苏图病毒(Usu⁃tu virus)、圣·路易斯脑炎病毒(St. Louis encephali⁃tis virus,SLEV)、库坦戈病毒(Koutango virus)、雅温德病毒(Yaounde virus)和卡西帕科利病毒(Cacipa⁃core virus)[5-6]。临床症状上,WNV 除了引起以亚临床症状为主的WNF 之外,还会引起以神经症状为主的西尼罗河脑炎以及马的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7]。所以,WNF 是我国重点防范的外来人兽共患病。
1 病原学及临床表现
WNV 最初于1937 年从乌干达分离,后来在亚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爆发疫情,并于1999 年传入美国[8]。WNV 粒子呈球形,有囊膜,直径约50 nm,属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 病毒,基因组长度大约为11 kb,其结构包含一个开放阅读框(ORF),编码一种独特的多蛋白,由3433 个氨基酸组成,通过细胞和病毒蛋白酶将其裂解为核衣壳蛋白(C)、包膜蛋白(E)和膜蛋白(prM/M)等3 种结构蛋白和7 种非结构蛋白(NS1、NS2A、NS2B、NS3、NS4A、NS4B 和NS5),其中包膜蛋白和膜蛋白镶嵌在包膜中,是主要的病毒抗原型结构,可能与病毒的毒力以及亲嗜性相关[9-10]。
根据系统发育分类,WNV 有7 个主要谱系,其中两个主要谱系的差异在于25%~30%的核苷酸同源性。人类疾病仅归因于谱系1 和谱系2[11]。谱系1 通常分布在非洲、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北美和中美洲以及中东。谱系1 进一步细分为1a、1b 和1c。谱系1a 在美国的传播最为广泛(NY99 株),非洲,欧洲和中东,并主要在这些地区爆发。谱系1 菌株通常被认为是新出现的,并与脑炎和脑膜炎的暴发有关[6]。通常谱系2 菌株的致病性较低,并且在地理上局限于南非和马达加斯加,但最近在欧洲出现了导致严重人类疾病的变种[12-14]。
症状范围从轻度WNF 到严重或致命的神经侵袭性疾病,包括急性弛缓性麻痹、脑膜脑炎、脑炎、脑膜炎或这些疾病的某些组合。由于其E 蛋白具有神经侵染性,当病毒在中枢神经系统(CNS)种扩散时,该蛋白结构域会形成相关的受体结构域,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机制可能包括直接穿过血脑屏障、被动通过内皮转运、感染的巨噬细胞穿过血脑屏障或直接轴突逆行转运[15-17]。一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病毒引发炎症,并随后导致脊髓和脑干灰质神经元的丢失。在大约15%的病例中,脑功能障碍发展为昏迷。伴随的异常可包括抑郁的深腱反射,弥漫性肌肉无力(通常伴有深度近端肌肉无力),弛缓性麻痹和呼吸衰竭[18-19]。
2 流行病学
自1999 年引进以来,WNV 已在北美各地引起季节性流行病和流行病。随着气温升高和降水模式的变化WNV 蚊媒的地理范围继续扩大,广泛分布于非洲、中东、南欧、俄罗斯西部、西南亚和澳大利亚(WNV 的昆金亚型)等地,其流行病学因地理位置和流行季节而异[20-22]。
在自然界中,WNV 通常在鸟-蚊子-鸟之间呈现传播循环,偶尔通过蚊子对其它动物尤其是人类的叮咬造成循环外溢[23-24]。在美国,已在65 种不同种类的蚊子中检测到该病毒[23]。然而,据报道,只有少数种类的库蚊能推动流行病向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传播,而且这些主要媒介种类因地理区域而异[25-26]。
蚊子叮咬几乎是所有人类感染的原因。蚊子在感染的10 d~14 d 后就可将病毒传播给其它鸟类、人和其它动物。此外,病毒可通过其他罕见的传播途径包括受感染的供体血液、器官、母乳或经胎盘感染进行传播[27-29]。幸运的是,由宫内感染引起的胎儿畸形并不常见:71名怀孕期间感染的妇女所生的72个活婴儿中,无一个畸形与WNV感染有关[30]。
3 2004 至2017 年间WNF 疫情三间分布分析
通 过GenBank 的 序 列 检 索,对2004 年~2017 年间,OIE 成员国确诊并汇报的WNF 疫情进行筛选和整理,截止2018 年2 月30 日,GenBank 中有清晰宿主描述的且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已知的WNV 株,共有1 119 株。其中47.3%来源于鸟类,45.1%来源于蚊子,其它序列则来源于人类(6.9%)、马属动物(0.5%)和松鼠(0.2%)。随机抽取部分序列进行分析发现,人源WNV 株与鸟类,库蚊及马属动物来源的WNV 亲缘关系非常接近。而鸟类并不能直接传染人类,所以库蚊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病毒载体。同时,马属动物也是用来监测WNF 疫情的最常用哨兵动物(图1)。

图1 1119 株WNV 全基因序列分析及种间分布
通过对OIE 公开发布的WNF 疫情政府报告的检索,2004 至2017 年间,OIE 成员国共提交WNF 疾病疫情432 起,其中11%未有说明疫情细节所涉及的物种。其中,78%的疫情汇报了马属动物感染,5%汇报了鸟类感染,哺乳动物疫情有23 份占6%。382份有详细受感染物种的疫情中,共涉及动物病例1 899 例,其中鸟类的病例数达到924 只,马属动物947 只(包括驴病例5 例),牛2 例,其他注释为哺乳动物但未指出具体物种的有26 例(图1B)。此外,大部分的疫情所呈报的病例数不会超过20 例,然而,在2009 年呈报的5 起疫情中涉及的病例都超过了20 例,最高的病例数将近140 例。这些病例数超过20 个的疫情,都是针对鸟类的大规模监测和检测所发现的鸟类阳性病例数量(图2)。从疫情发生月份上分析,83%的疫情集中在8 月份(67 起),9 月份(181 起)和10 月份(112 起)的北半球,可见WNF的暴发有着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2006 年2月份发生的3 起疫情为阿根廷呈报的马属动物疫情,而阿根廷作为南半球国家,其2 月份的气候与北半球的8 至10 月份相似,所以这3 起疫情也发生在与北半球相同的季节。

图2 2004 年~2017 年间呈报疫情的发生年份月份分布
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显示,WNV 之所以能够在多个大陆爆发一个重要因素在于WNV 可以利用多样性的宿主进行无障碍的大范围传播[24]。数量丰富的雀形目鸟类(如画眉和麻雀)和库蚊(如芋头库蚊和琵琶库蚊)使得美洲地区数次暴发大规模疫情[31-32]。鸟类迁徙的飞行路线也解释了WNV 传播路径变化,然而也有可能是其他机制导致了病毒的快速传播和频繁混合[33-35]。例如,人类行为对WNV 传播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北美洲密集的卡车运输业无意中运输受WNV 感染的鸟类或蚊子[35-36]。迄今为止,在搜集到的OIE 官方报告中,还没有来自中国呈报的疫情报告,但是2011 年,我国新疆地区首次报道了WNV 的人间阳性病例并提出了此种病毒可能已经在中国广泛流行。2018 年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广泛分布的蚊种主要是库蚊、中华按蚊和白纹伊蚊等,提示我国WNF、乙脑、疟疾、登革热等疾病在国内暴发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建议开展大规模的WNF 监测项目。从疫情发生的空间分析,动物感染WNV 病例分布在21 个国家和地区,结合WNV 重要载体鸟类的迁徙路线分析,我国处于多条鸟类迁徙路线的途经之地(http://www.waderquest.org/2014/05/world-mi⁃gratory-bird-day.html),所以中国也存在很大的潜在的流行风险。
此外,WNV 持续多样化,虽然目前很难看出WNV 进化所起的直接作用。WNV 和其他蚊媒病毒的进化是复杂的,因为它们需要在交替和完全不同的蚊媒和脊椎动物宿主中保持适宜性[37]。因此,WNV 的进化速度(大约4×10-4变化/区域/年)慢于许多其他单宿主RNA 病毒[38-39]。WNV 在美洲出现以来,在病毒种群中几乎没有发现阳性选择的证据。然而,最初的WNV 基因型(称为NY99)被局部衍生的基因型(WN02 和SW03)取代,表明该病毒可能在美国经历了适应性进化[29,40]。这样的可能性在中国也同样可能发生。目前尚不清楚病毒在国内的动态聚集是否会导致新的适应性基因型的出现,以及局部适应性病毒是否更有可能导致疫情爆发。了解各地区之间和区域内WNV 株的流行病学和生物学的这些基本问题对于有效打击这种根深蒂固的病毒可能很重要。
4 全球对于WNF 的监测
本研究参照和借鉴了美国和欧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发布的关于WNV 等虫媒病原的监测、实验室诊断与检验以及预防和控制等技术性指南,并结合已公布的WNV 基因组序列的分子进化分析以及全球WNF 疫情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回顾性论述,期望能够为该病传入我国的风险预测和预警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预防和控制WNV 和其他人畜共患病的虫媒病毒病,最有效地是通过综合媒介管理(IVM)计划。IVM 是基于底层的理解生物学的虫媒病毒传输系统,利用向量蚊子种群的定期监测和WNV 活动水平来确定,其成虫控制部分的目标是通过减少一个地区成虫的数量来补充幼虫管理计划,从而减少在繁殖地产卵的数量。控制成年蚊子的另一个目的是减少蚊虫叮咬和受感染的成虫数量,以防止它们将WNV 传播给人类,并打破蚊鸟传播循环。此外,IVM 计划的幼虫蚊子控制部分的目标是在蚊子成年之前控制它们的数量,在暴发情况下,幼虫控制补充了成年蚊子控制措施,防止产生新的媒介蚊子。然而,一旦病毒扩增达到引起人类感染的水平,仅靠幼虫控制无法阻止WNV 的暴发。
WNV 的暴发与地区水平和多种参数有关,WNV的监测可以用于确定该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多发季节、地理位置和人口模式等,还有助于确定临床疾病表现和疾病结局,以及确定WNV 疾病相关的高危人群和影响因素[41-42]。尽管这些与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有文献记载的联系,并认识到某些地区经历更频繁的暴发和更高水平的人类疾病风险,但还没有建立模型结合进行长期有效的预测。由于WNV 暴发的不可预测性应建立和维护监测系统,以此来发现更多的WNV 传播活动,并能够对监测数据作出有效的、减少疾病的干预反应。
美国对WNV 的监测一直较为严谨,自2003 年以来美国的血液供应一直定期进行WNV RNA 筛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建议,采血机构应全年对所有血液捐献进行WNV 核酸扩增试验(NAAT),器官和组织捐献者不定期接受WNV 感染筛查[27,43]。大多数疾病病例是由公共卫生或商业实验室向公共卫生当局报告的,卫生保健提供者也提交疑似病例的报告。关于WNF 的研究,美国也列出许多需要优先进行的研究课题,例如鸟类迁徙作为病毒散播机制的研究、蚊子的生物学和行为学、抗病毒疗法的研究等。
接触病媒传播疾病取决于工作类型、地理区域、季节和工人在外工作的时间长短。雇主一定要意识到这种风险,并评估这种类型的生物危害,这种生物危害可能对许多类别的工人都是危险的,比如农民、林务员、园艺师、园艺师、油漆工、屋顶工人、铺路工、建筑工人等[27,44-45]。因此,像WNF和其他蚊子传播的疾病不仅应被视为对一般人口的一种危害和公共卫生问题,而且还应被视为一种具体的职业风险,并应在职业和卫生安全立法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在我国的一些特定区域,公共卫生监测系统要进行预先指派和定期体检,以便及早发现接触这种生物危害的工作人员的健康受到的影响。职业健康监测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一项二级预防措施,是当工人容易暴露于初级措施无法消除的职业风险时所采取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应放在老年、孕妇或免疫缺陷工人的潜在个人限制,特别是当他们受到共病影响时。职业健康监测可评估和提供整个评估过程的流行病学信息,有助于预防风险。
综上,目前中国尚无WNV 感染的疫情报告,但是通过对2004 至2017 年间WNF 疫情三间分布分析,我国存在很大的潜在的流行风险,而且介于其作为虫媒病毒,WNV 的活动起起落落,但从来没有真正消失。结合WNV 流行形势、借鉴美国等国家先进的防控经验及应急预案,我国应该针对WNV和其他重要虫媒疫病展开综合性的虫媒疫病监测和病媒控制计划。结合大数据技术和地理信息分析等关键技术建立气候,鸟类,蚊子等的综合风险预警平台,做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提升虫媒病害的公众认知,可以利用现阶段非常活跃的手机端社交平台(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来配合对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教育民众如何避免或减少被蚊虫咬伤,例如,个人应该避免在蚊子经常出没的区域活动,在蚊子活跃的地方活动应穿长袖衫裤,并使用驱蚊剂;为门窗上安装纱帘;定期清理屋外的积水(如排水沟、花盆和水桶等)。避免蚊虫叮咬是避免被WNV 等虫媒病毒感染的最直接方式。最重要的是,对WNV 等人兽共患外来病防控,首先应在国家层面提高重视,加强国际间的联系与合作,建设外来病监测网络,以确保反应及时、判断准确,防控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