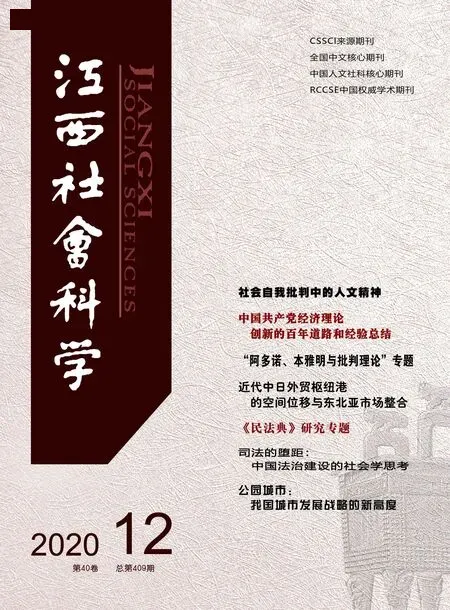上海海产品市场的近代发展
2021-01-19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水产品消费市场和集散地。近代上海市场上的海产品有冰鲜鱼、咸鱼和海味三类。整体看来,冰鲜鱼输入的数量最多,咸鱼次之,海味最少。其中,国产海产品中冰鲜鱼输入最多,咸鱼次之,海味最少,而舶来海产品中则海味输入最多,咸鱼次之,鲜鱼最少。输入上海的海产品除一部分用于本市消费外,剩余部分一般转运至外埠销售,另有少量海产品出销或复出口至海外。上海海产品市场在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渔轮的出现和新式运输方式的引入,对于促进上海海产品市场发展及对外经济交流均有重要意义。
肉类是人类生存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常见可食用肉类主要包括猪肉、鸡肉、鸭肉、牛肉、羊肉、鱼肉等,其中尤以鱼肉为最佳,有“畜肉不如禽肉,禽肉不如鱼肉”的说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近代以前内陆地区仅近水居民可食用部分新鲜淡水鱼,海鱼的产销也往往局限在沿海地区。近代随着渔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水产品保鲜和加工技术的进步,水产品的销售范围不断扩大,其中在海产品方面,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产品销售和集散市场。
对于海产品的市场和销售问题,学界已有不少关注,如邱仲麟曾对明代至民国江浙地区的冰鲜渔业和海鲜消费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讨论[1],众多渔业史及其相关研究对此也多有涉及①。而就本文所重点讨论的上海水产品市场而言,伍振华曾从上海的鱼行和零售点出发,复原了鱼行在空间分布上“集中—分散—集中”的演变过程和不同零售点的分布态势,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做了详细分析。[2]丁留宝曾对上海鱼市场与统制经济、渔业救济的关系做了全面探讨。[3]姜明辉则单独讨论了近代上海冰鲜鱼的消费和渔业用冰问题。[4]以上研究都将考察重点放在了上海本地水产市场的运作、分布和发展状况上,对上海水产品的来源及转销范围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另外,以研究精度而言,既有研究也未能区分水产品市场中淡水产物和海洋产物具体差异,而将两者混在一起讨论。因此,本文拟单独从海产品出发,讨论近代上海海产品的主要来源、在上海本埠的销售状况及转销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上海海产品市场中出现的新要素和新变化做初步探究。
一、上海海产品的主要来源
近代上海市场上的海产品有冰鲜鱼、咸鱼和海味三类。冰鲜鱼实为海洋冰鲜鱼,“因其一离海水,即难生息,故需以冰冰之,藉免腐烂,遂名冰鲜”[5],虽然亦有河鲜用冰保鲜,但因其数量较少,故“冰鲜鱼”一般专指海洋冰鲜鱼。咸鱼是用盐腌渍过的海鱼。海味则包括鲍鱼、虾米、海带等多种海产加工品。
(一)冰鲜鱼的主要来源
上海市场上的冰鲜鱼主要有三个来源,“一由本市渔轮直接采捕而来,二由冰鲜鱼船收买贩运而来,三为由各冰鲜装桶以商轮运载而来。除此之外尚有日本渔轮在我领海侵捕运入本市,或由大连、青岛以商船运入者”[6]。
先来看上海渔轮直接采捕而来的冰鲜鱼。近代上海渔轮分拖网渔轮和手操网渔轮两种,最早的渔轮是1904年张謇创办的江浙渔业公司所购买的“福海号”渔轮,此后上海渔轮业不断发展,至1935年共有拖网渔轮8艘,手操网渔轮9对。[7]渔轮的捕捞渔场主要在舟山群岛外海,其中以花鸟山东北、佘山东北以及海礁附近等处最为重要。[8](P31)
渔轮的渔获物种类非常丰富,根据《二十二年份(1933年)上海市各渔轮渔获类别产量统计表》[9],除各类杂鱼外,渔轮共计有31种渔获物,其中以黄华鱼(小黄鱼)、大黄鱼、鮸鱼、鲳鱼、鞋底鱼、鳗鱼、鱏鱼、梭子蟹的数量最多。但产量方面,渔轮渔获物在上海全部进口冰鲜鱼中所占的比重却不是很大。根据表1,1934年渔轮渔获量仅占上海全部进口冰鲜鱼的10.12%[10],1935年渔轮渔获量占比也仅为15.09%。

表1 1934—1935年上海冰鲜鱼进口统计表
再来看传统冰鲜船。“冰鲜船为大型帆船,渔汛时装载多量之冰,往渔场收鲜,以冰保藏。”[6]与上海本市渔轮相比,冰鲜船才是上海冰鲜鱼进口的主要力量,“沪市海鲜大都仰给于冰鲜船,其次为渔轮”[11]。根据表1,1934年冰鲜鱼船运至上海的冰鲜鱼占上海全部进口冰鲜鱼的72.34%,1935年的占比则为70.76%,可见通过冰鲜鱼船输入的冰鲜鱼占了上海全部进口冰鲜鱼的一大半。
在来源方面,根据《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1932年11月到1937年2月共50期的统计,冰鲜船运入上海市的海产品主要来自舟山渔场,并以当时属上海崇明县管辖的嵊泗渔场(位于舟山渔场北部)为核心渔场,冰鲜鱼种类以所谓四大经济海产,即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带鱼为主。
进入上海市的冰鲜船主要自上海港上岸,只有少部分自吴淞镇上岸。据统计,1933年自吴淞镇上岸的冰鲜船共计运来冰鲜鱼21856.24担,仅占全部冰鲜船输入冰鲜鱼数量的4.4%[12];1934年自吴淞镇上岸的冰鲜船共计运来冰鲜鱼32284.67担,仅占全部冰鲜船输入冰鲜鱼数量的5.7%[1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吴淞镇上岸的冰鲜船运来的冰鲜鱼数量与上海港相比很少,但其来源除舟山渔场各岛屿外,还有北方烟台、威海卫等地,范围较广。
最后来看冰鲜桶头。根据表1的统计,虽然使用冰鲜桶头输入上海的冰鲜鱼数量,在上海全部进口冰鲜鱼数量中的占比并不是很大,但地位却十分重要。冰鲜桶头是用一种松杉类木材特制而成椭圆柱形木桶,能保持鱼类新鲜的时间大约是四五日。[14]其出现主要是为了调剂上海冰鲜鱼市场的盈虚平衡,“此类桶头之输入,大都为适应本市(上海市)之需要,而为外埠之过剩,或上海鱼价较别埠为高时,使得输入”[6]。在运输方式上,各地冰鲜桶头多由商轮运入上海市场[15],火车出现后部分也采用火车运输。
由于使用冰鲜桶头保存鲜鱼的时间较渔轮和冰鲜船略长,因此冰鲜桶头的输入地也更为广泛,“有所谓北洋冰鲜和南洋冰鲜之别,北洋冰鲜指长江以北各口岸运来者,而南洋冰鲜亦即明示为长江口各地以南各地输入者”[6]。运入上海的冰鲜桶头中,南洋鲜和北洋鲜的数量平分秋色,没有明显的南、北方来源差异,其中北洋冰鲜桶头产地有烟台、青岛、天津、威海卫、大连等,以烟台、青岛为最多;南洋冰鲜桶头产地有舟山、宁波、坎门、石浦、芜湖、温州、瑞安、平阳、延平等,以舟山、宁波为最多,如表2所示。[16][17][18]

表2 1933—1935年上海市冰鲜桶头输入统计表 单位:担
除国内冰鲜鱼外,上海市场上还有部分鲜鱼来自国外,并以日本为最多。但日本输入上海的鲜鱼并非来自日本渔场,而大都由日本渔轮在我国沿海渔场捕捞所获。截至1930年“12月止,在苏省沿海捕鱼之日本手操网渔轮,共有9对,计18只……知已运至上海销售之鲜鱼,曾经报关手续者,已有五万余担,事实上因漏税而少报之数,当在两倍以上”[19](P67-68)。除此之外,另有日本鲜鱼使用大连、青岛的商船冒充国货运进上海[20],以及冒名运货船等走私进入上海市场[21]。1930年以后由于上海的各类抵制日货活动,日本鲜鱼输入数量下降,俄国鲜鱼输入数量渐占优势。[22]
(二)咸鱼的主要来源
上海水产品市场上的咸鱼分国产和舶来两种。国产咸鱼夏季有黄鱼、鳓鱼(俗称鲞鱼)、小干(小黄鱼干)、金鱼(大黄鱼干)、潮鲞、白鲞、油同、马鲛鱼等,冬季有带鱼、白古、条鱼等。[23]舶来咸鱼主要有萨门鱼、大青川鱼、小青川鱼、人面鱼、大口鱼、小口鱼、白鳞鱼干、黑鱼鳞干八种。[24]
输入上海的国产咸鱼可从上海港和吴淞镇两个港口上岸。1933—1934年,上海港进口的国产咸鱼几乎全部自长江以北而来,长江以南极少,其中长江以北主要来自青岛、烟台、威海卫、大连、牛庄五地,长江以南主要来自宁波和温州两地。[25][26]究其原因,长江以南海产品大多出自舟山渔场,以冰鲜运入上海更为便捷,加工制成咸鱼,反而麻烦;而长江以北海产品大多出自黄海北部渔场,距离上海较远,咸鱼能保存更长的时间而不腐坏,便于长途运输。
自吴淞镇上岸的国产咸鱼来源则与上海港不同。据统计,1933年7—12月自舟山群岛输入吴淞镇的国产咸鱼共计30684.9担,自长江以北各地输入吴淞镇的国产咸鱼共计19827.82担[27];1934年自舟山群岛输入吴淞镇的国产咸鱼共计134094.18担,自长江以北各地输入吴淞镇的国产咸鱼共计93932.97担[28]。通过比较发现,自吴淞镇上岸的国产咸鱼,长江以南各地输入的数量多于长江以北各地输入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吴淞镇地处长江口,靠近嵊泗渔场,所以自吴淞镇上岸的咸鱼以舟山渔场北部的嵊泗列岛为最多,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咸鱼来自舟山渔场的海产品加工中心岱山岛和衢山岛。
上海最早进口的舶来咸鱼为咸青鳞鱼及萨门鱼。1907年美商天祥洋行将美洲所产咸青鳞鱼及萨门鱼20000箱运至上海试销,成绩颇佳,1910年日本又将俄属沿海滨省一带所产之萨门鱼及北海道、朝鲜一带所产之鳘鱼,运至上海试销,结果亦甚为满意。于是自1911年起,咸鱼开始源源不断输入上海。[24]
近代上海水产品市场上舶来咸鱼的种类众多,并以咸青鳞鱼、咸鲑鱼、咸鳟鱼、咸鳘鱼的数量为最多。咸青鳞鱼即上海所称咸青川鱼,分大青川和小青川两种,大青川来自日本、朝鲜、海参崴,进口数量较少,小青川进口数量较多,主要来自美洲及日本,其中日本的小青川并非产自日本,而是转口自加拿大。咸鲑鱼和咸鳟鱼即上海所称咸萨门鱼,原产于美洲、日本、俄国等地,多由日本转口输入,以俄国堪察加货尤多。咸鳘鱼即上海所称水口鱼,分大口鱼和小口鱼两种,皆主要来自日本北海道。[29]
虽然输入上海的舶来咸鱼种类丰富,但在输入数量上,舶来咸鱼却无法与国产咸鱼相较。以表3所统计1933—1935年上海进口咸鱼数量[30]来看,1933年舶来咸鱼数量只有国产咸鱼数量的七成不到,1934年和1935年舶来咸鱼数量更是只有国产咸鱼数量的一半不到。但在1937年淞沪会战前,无论是国产咸鱼还是舶来咸鱼,输入上海的数量均不断增加。

表3 1933—1935年上海进口咸鱼数量表
(三)海味的主要来源
近代上海市场上海味种类众多,最有名的是“鲍、翅、肚、参”四大海味。1909年上海市场上已有海带、海菜、鲍鱼、海参、虾米、干贝等海味[31],1931年输入上海的海味种类更为丰富,除上述几种外,还有鱼翅、鱼皮、鱼肚、淡菜、螟蜅、紫菜、鱿鱼、蜇皮等[32]。当然,实际海味的种类远不止这些,以海参一项举例,即可分为黑刺参、黑光参、白海参3大类,黑刺参下又有十番参、八甲参等6种,黑光参下又有鸟元参、香条参等11种,白海参下又有玉参、虫参等11种。[33]海味种类的繁复性可见一斑。
根据来源地不同,海味分为国货、东洋货、西洋货三种。国货有南洋货和北洋货,南洋货自福建、浙江等地而来,北洋货为浙江岱山以北所产海味。东洋货即日本货,其中高丽、海参崴来货亦被归入东洋货之类。西洋货除美国外主要产自南洋群岛,来货以吕宋、直腊、暹罗各地者居多,也有自香港地区转口而来者。[34]
输入上海的国产海味主要来自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的沿海地区。其中,鱼翅、鱼头和鱼皮在浙江、福建、江苏以及北方烟台等处均有出产,并以浙江沈家门所出尤多;鱼肚由江苏和浙江各海岸所产;虾干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均有出产,且以福建沿海、浙江台州和山东烟台为最多;虾米在沿海各口均有出产,以江苏江北和山东烟台为最多;螟蜅鲞和紫菜由江苏、浙江、山东所产,以浙江的嵊山与宁波出口最多;鲍鱼和鱿鱼在福建和广东两省有产,但出产量极少;海咸由浙江与威海卫所产;洋菜由宁波、烟台所产;干贝在烟台有出产,但运至上海的数量不多;蜇皮由江浙两省所产,且从宁波运至上海销售为最多。[32]
虽然国产海味种类不少,但其输入上海的数量仅占上海市场上全部海味数量的一小部分,舶来海味才是上海市场海味输入的大宗。据上海渔业指导所统计[35],1933和1934年输入上海的舶来海味是国产海味的近4倍,1935年舶来海味数量甚至达国产海味数量的10倍以上,如表4所示。

表4 1933—1935年上海市海味输入量比较表
输入上海的舶来海味主要有三大来源:“一由南洋群岛、新嘉坡、锡兰、望加锡、香港、吕宋来者,其数最多,民国十八年份由上列各地输入上海者,价值二百万两以上,至其种类则以鱼翅、鱼皮、海参等为大宗。二由日本输入者,民国十八年份计所输入之海味价值五十万两。三由美国输入者,计民国十八年份输入上海者,价值八十万两,中以鲍鱼、鱿鱼、虾米为大宗。”[36]
1934年日本输入上海的海味增至最多,且数量惊人,其次输入较多的是南洋各地和美国,另外印度、非洲、澳大利亚等地亦有海味输入。[37]自日本输入的海味虽在上海舶来海味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但由于近代中日政治局势的影响,海味输入的数量波动很大。1931年6月上海海味业同业公会通知各会员抵制日货[38],随即日本海味输入数量急剧减少。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战前“日本货总是占半数,自从抗战以后,几片行号都自动停售日本货”[39]。
二、上海海产品的销售市场
输入上海的海产品除一部分用于本市消费外,剩余部分一般转运至外埠销售。其中“鲜货以本市为消费之大宗,间有少数行销京沪线、沪杭一带,咸货销行较广,尤以海味为甚”[22]。另有少量海产品出销或复出口至海外,限于数量较少,本文不予详细讨论。
上海市场上的海产品均由鱼行代售,鱼行是渔业运销的中间环节,为“代客买卖,从中收取佣金,以营水产物之交易机关”[40]。鱼行分冰鲜鱼行、咸鱼行和海味行三种,但三者经营范围划分并不十分明确,有兼售咸鱼的冰鲜鱼行和兼售冰鲜鱼的咸鱼行,亦有兼售咸鱼的海味行和兼售海味的咸鱼行,还有部分咸鱼行兼售咸肉。1936年上海“冰鲜鱼行一十余家,淡水鱼行五六家,兼营者尚不与焉。此外尚有咸鱼行三十余家,海味行(连兼者在内)五十余家”[41]。鱼行大部分集中在法租界十六铺一带②,“南自东门路铁栅栏起,北至舟山路东至招商码头,西至民国路交界处止”[42]。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代上海鱼行的经营资本都较小,所以国外的咸鱼和海味并不由鱼行直接进口。舶来咸鱼的进口由洋商所经营,大大小小的咸鱼行组成无限责任公司性质的组织,以公司名义统一向洋商购买,到货后再分派于各鱼行。此种组织上海有两处,一为信孚公司,俗名南公司,在十六铺内培德里,由24家咸鱼行共同组成;一为仁孚公司,俗名北公司,在十六铺内大达里,由20家咸鱼行共同组成。[29]海味业则由专门的海味号从事海味进口,习惯上海味号输入后,再批售于海味行,亦有少数海味行直接从外国进口海味,但逢海味号开盘,仍可到场交易。[24]
冰鲜鱼行的销售分早午二场,早场从凌晨四、五点起至九、十点为止,多为本地鱼贩[14],拿货后即迅速将冰鲜鱼运送到菜场的鱼摊进行销售,1935年上海市的菜场“在公共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南市、闸北、浦东计七十处,鱼摊数约三千五百余个”[43]。其中,英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菜场鱼摊共计2333个,肩挑叫卖之小贩约五六百人,专在各里弄兜售,所贩之鱼大都不甚新鲜;南市、闸北、沪西华界内菜场的鲜鱼鱼摊共计822个,以杨树浦之八仙桥,西藏路之东,十六铺附近,售海鲜鱼为多。[44]冰鲜鱼行销售午场从下午四点起至六点为止,拿货者多为内地水客和各近镇鱼贩[14],一般于第二天上午将冰鲜鱼送至当地各菜场和鱼摊出售。另有冰鲜鱼以冰鲜桶头的形式,或通过轮船运往宁波,或通过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运往沿线各站。
咸鱼销售有如冰鲜鱼在鱼摊销售者,如南市、闸北、沪西华界内菜场的咸鱼鱼摊即有188个[44],但其主要销售渠道还是由鱼行派人向市内南货店和客帮商号驻沪之庄号实行兜售。[22]在销路方面,除在本市鱼摊和南货店销售外,“吴淞上岸的国产咸鱼,运销嘉定、罗店及附近一带”[45]。上海港上岸的“咸干鱼鲞,运销长江一带,远达苏北及汉口”[46]。舶来咸鱼由于种类繁多,无法明确其具体运销范围,但以进口数量最多的萨门鱼来看,“到沪时期为每年秋初起至翌年初春止,其散销地为浙之宁波、杭州、嘉兴,苏之无锡、常等州处为大宗;秋冬之交,内地因刈稻而销场特畅;广东、汕头、福州等处,在初冬时间,亦有大批来沪购办”[47]。由此可见,咸鱼销售范围之广。
虽然上海舶来海味由海味号负责进口,但海味号不得直接与客商交易,客商只能向海味行办货,1928年上海经营海味行业者,大小凡40余家。海味行出售海味与咸鱼行派人外出兜售的方式大有不同,其销售主要靠茶会接洽。茶会每日举办,由海味行同业组织专门负责组织,各路客商和各行经理、跑街等人聚于茶会,凡海味市场消息,均可于品茗闲谈中得之,但茶会中只能谈市况,不能做交易,买卖双方在茶会接洽之后,客商到行看货,然后才能成立买卖。此种茶会地点有三,一在小东门外点春堂公会,聚会时期为每日下午一时至四时,客商除广帮以外,皆到此会;二在新北门口杂粮公会,每日聚会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十时半,客商到此会者,多为广帮和汉帮;三在新北门外蕙芳楼,到会者多为兜售本街买卖之跑街,客商鲜到此会。[24]
至于海味的销路,可以通过海味市场上的客商帮号来反映。近代在上海批发海味的客商帮号众多,有“本街帮、内路帮(沪杭甬沿线谓之内路帮)、温台帮、江西帮、湖南帮、徐州帮、江北帮、四川帮、建帮、汉帮、烟台帮、沙宜帮、天津帮、大连帮、牛庄帮、广帮、潮州帮、汕头帮、山西帮、陕西帮、河南帮、芜湖帮、安庆帮、九江帮、南京帮、苏帮、扬帮等,其中以四川、天津、汉口及广、建、汕等帮销路为最大”[24]。由此可见,海味的销售市场除上海本市外,不仅覆盖各沿海地区,亦深入北方及西南内陆,尤其是四川、天津、汉口和广东的销路最广。
其中,各帮客商因销售市场的不同,所经营的海味种类亦有不同,上海本地销售以鱼翅、海参、虾米、干贝为大宗,广东客商以鱿鱼为大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西南内陆省份的客商以海带、带丝、海参为大宗,鱼翅、鱼肚除上海外,天津和汉口销售最旺。
综上所述,上海输入的海产品中,冰鲜鱼由于保鲜时间短,多在本地市场销售,少部分销往周边集镇及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等周边城市。咸鱼和海味由于保存时间较长,其销售范围不仅覆盖周边各城镇,更远及东部沿海各省和长江沿线省份,海味市场甚至还覆盖北方、西南内陆地区。
三、近代上海海产品市场中的新变化
近代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地和集散地,在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渔轮的出现和新式运输方式的引入。
渔轮出现以前,上海冰鲜鱼进口全靠冰鲜鱼船,但“冰鲜鱼船到沪之多寡,全视外海渔汛旺盛与否而定”[6]。从表5可知,渔汛期通过冰鲜船输入上海市场的冰鲜鱼数量达几万甚至十几万担,非渔汛期仅几千担,一年之内输入上海市场的冰鲜鱼数量变动巨大。反观渔轮输入上海市场的冰鲜鱼,虽然数量大多只有几千担,但渔汛期与非渔汛期间差距并不明显,且捕获能力呈一年高过一年之势。在1、2、3、10、11月的非渔汛期内,渔轮捕获的渔获物数量持平甚至可能高于冰鲜船输入上海市场的冰鲜鱼数量。对比之下,足见近代渔轮的出现对非渔汛期上海市场冰鲜鱼供应的重要补充作用,以及在平衡上海冰鲜鱼市场方面具有的重要地位。
近代上海海产品市场上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轮船、火车等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扩大了海产品输入和销售的范围。

表5 1933—1935年上海市各月份冰鲜渔船与渔轮输入冰鲜鱼数量表
原本上海水产品市场上的冰鲜鱼皆靠冰鲜鱼船运输,且来源不外乎长江口附近的舟山渔场和吕泗渔场,近代渔轮的捕捞活动也是在上述渔场范围之内。近代新式轮船出现以后,远至北方天津、山东等地,南及浙江南部沿海地区的冰鲜鱼皆可使用冰鲜桶头通过轮船运入上海,根据笔者在上文中的统计,近代通过冰鲜桶头输入上海的冰鲜鱼占上海全部输入冰鲜鱼的近20%,由此可见,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作用不可小觑。
火车对海产品销售的影响,是新式交通运输方式意义的另一个例证,它主要起到调剂上海冰鲜鱼市场的作用。具体说来,当外洋渔汛捕获的大量冰鲜鱼涌入上海时,即将冰鲜鱼装成冰鲜桶头,再通过京沪线和沪杭线将冰鲜鱼运送至沿线各站。1933年“一年中由京沪路输出之鲜鱼,合计三十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公斤,由沪杭路输出之鲜鱼,合计二百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六公斤,总计输出二百四十万公斤以上,足见铁道在鲜鱼运输上之重要”[48]。除了运输冰鲜桶头外,火车亦可运送咸鱼和海味。据记载,1935年上海北站运镇江、南京二埠,运送海产品大部分为海产冰鲜鱼,次为海味咸鱼,其他为蚶子、梭子蟹、青蟹等;上海麦根路车站经营京沪线海产品运输,输出种类以冰鲜黄华鱼、带鱼为数最多,咸鱼次之,海味则极少;上海南站经营沪杭路海产品运输,输出种类以咸鱼为最多,鲜鱼次之,海味最少。[49]
虽然经火车运输的海产品数量众多,但就整个上海海产品市场来说,其运送规模还是有限的。为了发挥火车运输量大、速度快的优势,1926年吴淞铁路工厂曾建造一种新式车辆,可置冰以存放冰鲜鱼,投放至上海北站。[50]当时铁道部亦曾筹建全国铁道冷藏库,并选定上海为起点,在麦根路货站内空场,建设我国第一铁路冷藏库。[51]但这些措施最终都未能推广,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在海产品运输中没有能够发挥其本应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结语
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水产品消费市场和集散地,其原因有三。一是“清嘉道年间,万商云集的上海县城已是冰鲜业的最大市场”[52](P58)。二是上海地处长江口,不仅南靠近代中国最大的近海渔场——舟山渔场,北临的吕泗渔场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三是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众多、消费庞大;同时上海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交通发达、运输便利,其腹地不仅仅是长江流域,还包括北方地区甚至面及全国。
就整个近代上海海产品市场来看,冰鲜鱼输入的数量最多,咸鱼次之,海味最少。其中,国产海产品中冰鲜鱼输入最多,咸鱼次之,海味最少,而舶来海产品中则海味输入最多,咸鱼次之,鲜鱼最少。国产与舶来海产品来源的差异,固然是由海产品的保质期长短导致的,保质期较短的冰鲜鱼多由我国沿海地区运来,保质期较长的海味多由国外进口而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代水产工业的落后,国产海产品业多集中于鱼类的捕捞、保鲜和简单加工,加工方式更为复杂的海味则主要靠海外进口。
但也要从中看到,近代上海海产品市场上出现的新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渔轮的出现,对上海冰鲜鱼市场尤其在非渔汛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渔轮使用机械动力,其捕捞范围并不局限于近海渔场,而是迈向传统渔业未曾涉及的远洋,并因此发现了嵊山外海丰富的小黄鱼资源,引导传统渔民前往捕捞,开启了近代嵊泗渔场开发的黄金时代,从而为上海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海产品。其次,虽然近代新式交通工具轮船、火车的出现,并没有根本变革传统水产品运销方式,但这不是由轮船、火车这类新式交通工具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而是因新式交通工具发展的规模不足所导致的。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规模未能满足水产品运输的需求,这也恰恰说明了新式交通工具对于水产品运输的重要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南洋一带而来的海味运至上海后,大多采办中国土产运回,如望加锡之华商来海味去黄豆、绿豆,新加坡之华商则来海味去丝绸,吕宋之华商来海味去土布及各种杂货。[24]可见直至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沿着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依旧繁盛不息,只不过随着近代轮船交通业的不断发展,贸易种类已不仅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贵重物品,还拓展到海味、土布、黄豆、绿豆等普通商品,经济交流愈加频繁,规模愈来愈大。
注释:
①渔业史及其他相关研究中涉及海产品销售市场的主要有(包括但不限于):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江浙渔业公司1911年版),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股份公司1937年版),侯朝海《中国水产事业简史》(上海水产学院1958年蜡印版,未出版,后由上海海洋大学档案馆整理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丛子明、李挺任《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②虽然1936年5月12日上海鱼市场在定海岛开业,鱼行大部分移入鱼市场经营,但上海鱼市场开业仅一年多,即因淞沪会战的爆发而停业,之后鱼行经营受战争影响极不稳定,故本文讨论以1936年前鱼行经营状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