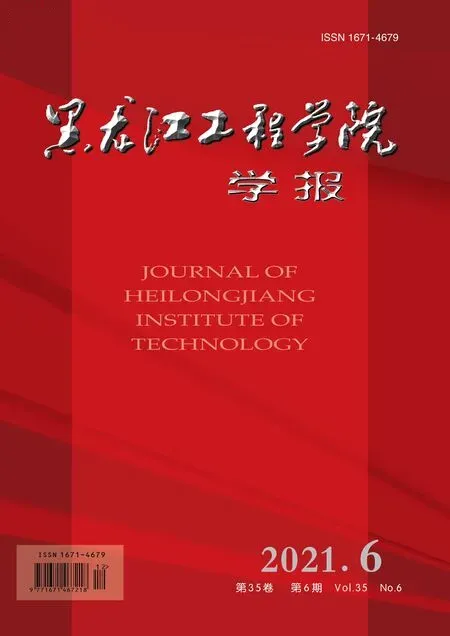中介语与超语视角下二语习得观的异同
2021-01-17李驰
李 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二语习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兴起,研究内容主要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并解释其特征,构建理论体系[1]。迄今为止,二语习得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内容涉及中介语研究与学习者内、外部因素研究等方面[2]。近几年来,超语行为也成为外语教育界和应用语言学界的热点话题[3]。不同的语言系统理论(如中介语系统、超语行为)均认为二语习得过程主要是学习者通过输入一定的语言知识学习目的语言,从而流畅地使用目的语完成交流、写作、翻译等输出任务的过程。
以往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学习者的语言使用,而不是语言习得;研究的是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4];研究也大多局限于考察情境因素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对输出的影响,而非探究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交互过程,调整过的输出是否促进二语学习,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帮助[2]。中介语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聚焦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独立的、与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系统并列的语言系统,涉及整个二语习得过程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以及中间状态。而超语立足于双语、多语现象,认为学习者可以利用输入的语言资源去获取知识、产生意义、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最终输出目的语,用该语言进行交际[5]。两种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均对研究二语习得过程有重要作用,但尚未有研究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鉴于此,文中将从中介语和超语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入手,以期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新视野和新思路。
1 文献综述
中介语是二语习得者利用母语中存在的语法、语音、词汇知识等学习目的语所形成的有别于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学习过程的某个特定时期认知目的语的结果与方式的特征系统;二是指在二语习得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学习者的二语能力发生与发展的特征性系统[6]。前者强调学习者自身所拥有的独特中介语语言系统,后者则更多表示所有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拥有的普遍和抽象语言体系—中介语系统,又叫“中介语连续体”。有关研究发现母语知识在中介语形成时有明显的负迁移, 使得学习者在嵌入句、词序和并列结构等方向受到干扰[7],母语与目的语的相似之处可促进第二语言的习得,例如母语为法语的学习者学习汉语时比学英语更困难,这就是由于学习者已有的母语知识为其所利用形成中介语系统,更易促进目的语的习得。
超语是指多语者将来自不同语言实践的多层次、多模态的语言符号资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建构意义、获得知识、理解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复杂话语实践[8],它超越语言层面构建知识,涉及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的动态和功能整合使用[9]。母语和目的语以一种动态的功能整合方式促进学习者的听、说、读、写等任务[10]。目前,有研究将超语系统引入课堂观察与研究,结果发现双语或多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策略,调动自身所有的“语言和交际资源”来进行创新的、批判的或者自我独立的认知活动[11]。也有研究发现英籍华人小学生在中文语言学习班里会表现出一定的超语行为,这些学生会将自己已具备的中、英文和跨文化知识结合起来去灵活地使用语言资源并习得新知识[12]。同时,有研究将语码转换与超语行为相联系,认为语码转换和超语行为都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的双语和多语现象的研究[13],二者都是对源语和目的语进行整合和加工。超语理念也可以应用于非学术、教育等领域,如双语电影、杂糅词、网络流行语[14]等领域,从而更好地帮助习得者理解文化。
已有研究大多各自从中介语系统和超语系统进行研究,探索二者各自的核心理论和实际运用;也有研究利用中介语系统和超语系统进行课堂观察,发现习得者在各自语言系统指导下语言习得表现和效果不同,希望可以激发学生在双语课堂里开展具有认知深度及协作精神的学习活动[15]。但尚未有研究将两者进行对比,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对比分析方法探索异同,以期丰富二语习得理论,为二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 中介语和超语视角下二语习得观对比
中介语和超语理论视角下对二语习得的探究均离不开母语的输入和目的语的输出。两个系统均认为母语的词汇、句法、结构等对目的语的习得有重要影响,存在一定的母语迁移现象;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会形成一种不同于母语和目的语系统的中介语语言系统或超语语言系统,该系统是不同学习者利用各种资源形成的,具有学习者个人独特性。然而,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母语知识影响、资源整合方式与语言输出三个方面仍具有一定差异。
2.1 母语知识影响
母语是二语习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二语习得理论和教学方法的丰富离不开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对比分析[16]。中介语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它区别于学习者的母语,也不同于学习者的目的语,其思绪流动过程源于母语,以中介语为过渡语,最后到达目的语。母语对中介语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迁移现象,正迁移可以促进目的语习得,反之则是负迁移[17]。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鼓励学生尽量使用目的语去完成理解、写作、交流等任务,但学生并不能习得完美的目的语,会采用自己独有的中介语。母语知识会帮助学习者构建大脑思维和想法之间的联系,继而利用中介语产出,这种产出受母语影响较大,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错误。例如,汉语中没有第三人称单数的语法和概念,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如‘She want to see a doctor.’(正确为‘She wants to see a doctor.’)这样的错误。一些日语习得者也会因为对日语词类划分或者词汇的固定用法掌握不足,就将母语的思维方式、语法范畴、观念带入日语理解中,用母语知识进行类推,造成日语习得过程中的错误[18]。
不同于中介语作为母语和目的语中间的过渡语,超语理念下的语言习得并不是独立或分散的,他们是一种无规则的连续体,二语习得并非线性过程[19],而是处于一个不断进行的、创造的阶段。在二语教学实践中,学习者可用母语或者目的语来完成对话、理解、翻译等任务,不一定完全采用目的语或摒弃母语,这是由于母语不仅可以从句法、语法等方面为二语习得提供语言层面的参考,还可利用母语包含的文化、社会资源促进学习者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认知层面的提升。教师构建超语情境,鼓励学习者借助母语使用目的语,激发学习者兴趣,促进同伴交流,完成写作和交流[19]。汉语母语者在习得英语时,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可以帮助其创造一些符合英语规则但却蕴含中文意义和屈折的表达[20],如smilence(smile + silence,笑而不语,指的是面对某些现象只是笑笑不说话)、chinsumer(Chinese consumer,疯狂购物的中国人)、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你行就上,不行就别叨叨)。
2.2 资源整合
中介语的资源整合主要是对母语和目的语的整合,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假设对这个过程进行了阐释。对比分析假设首先对母语和目的语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对比和分析处理。相关研究表明,母语语言体系中存在的结构、内容、知识可能会对目的语的习得产生正迁移或负迁移。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按照自身体会、察觉到的异同之处, 把各种具体或抽象的句型划入不同的范畴。但是,这一理论对于学习者可能出现的语言错误无法预测。鉴于此,提出偏误分析假设,旨在帮助学习者了解学习中产生的共同困难,助其不断纠错,从而更好地整合资源,找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在此基础上,学习者不断对已有资源进行加工和整合,持续发展中介语系统,使其向正确形式的目的语靠拢[21]。
超语的资源整合主要是对学习者所有的语言资源、认知资源及社会资源等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学习者特定的语言、符号系统。一些亚洲国家在语言习得中,通常将语言之间的关系割裂来防止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19]。学习者需要对各种语言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加工、学习,最终实现语言习得的目的。在这样的整合加工方式下,超越两种独立语言系统的多种话语实践[19]的超语概念就应运而生。来自不同文化的习得者拥有不同的传统与历史,他们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模式也会影响超语过程中的资源整合,这对理解隐喻等修辞有重要影响[22]。KAUFHOLD对多语言背景下学生整合资源开展学术写作进行探讨,发现学生会形成“超语空间”对自己的各种语言资源、社会符号进行整合来完成学术写作[23]。
2.3 语言输出
每个人的母语系统可以设定是“完美的”,但二语初学者和熟练者的中介语系统始终无法达到母语系统的“完美”。外语高水平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语言直觉和能力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异[23]。BENT等[24]发现英语母语者在进行英语听力时,更易识别英语母语者产出的句中单词,说明即便是高水平学习者,产出的单词依然弱于母语者的产出,从而对听者造成影响。相比之下,汉语和韩语母语者在识别非英语母语但具有高水平英语者产出的句中的单词时,其准确度比识别英语母语者的产出更高,体现出学习者更容易识别来自相同语言系统的二语产出。中介语在母语和目的语间搭构了“互通有无”的桥梁,但却无法达到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语言能力水平;目的语系统始终处于中介语系统之上,造成学习者的习得结果无法达到高度理想,甚至输出的中介语系统也是僵化的。
超语系统中,语言输出是基于目的语符号体系,新语言实践和现有语言实践进行互动融合,之后融入和组建新的语言技能库[25]。不同于中介语系统可能导致语言输出“僵化”,超语系统下输出的语言是有意义并可为他人理解的,它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各种认知加工的协商中,既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和解决问题,也可以使学习者通过语言创造意义和塑造知识、经验[5],这种输出超越了语言本身而到达认知、经验、文化等层面[12]。Li(2014)对英国一所移民小学中以粤语方言为母语的中国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观察,发现教学过程中老师用英语提出问题或者布置任务,学生用英语、粤语交叉进行说、写、读等任务输出,这些“超语行为”的出现不仅帮助学生理解并完成任务,也促进了课堂的顺利展开。这是学习者利用不同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个人历史和社会文化经验、态度和意义等各方面知识和资源进行语言输出的结果。
综上所述,从输入和输出方面来看,中介语在内部组织上拥有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系统,学习者可以利用这些规则系统生成其从未接触到的话语;从其功能说,中介语可以服务于人际交往。然而中介语输出的系统可能是僵化的,中介语的可变性也存在一定争议[7]。不同于中介语,超语是一个利用全部语言资源来习得知识、促成理解、表达思想以及交流观念的过程[8]。语言学习者利用包括母语、二语甚至多语的语言结构、语法、社会资源等在内的所有语言资源,由此产出的语言是流动的、可变的。
从应用层面来看,中介语和超语都可以应用于语言习得实践,探索语言习得的影响因素,来提高学习者语言系统的输出水平。中介语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倡导学习者和教师在课堂上利用各自发展形成的特有中介语系统来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超语允许课堂上使用母语、目的语、其他语言,这有利于学习者接受语言知识,理解文化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习得目的语言。不同之处在于:二语习得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中介语,学习者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介语,从而构建“完美”的中介语体系。但是超语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则认为在二语习得初级阶段,学习者尚未完全习得目的语知识,对其掌握不足,因此,无法用目的语更好地表达思想或者流利地进行对话、完成任务。
3 结束语
二语习得涉及母语和目的语的影响和作用、资源整合、语言输入和输出等不同过程,这些都在中介语和超语系统中起到重要作用。中介语和超语系统均是语言习得中的重要理念,对语言习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本研究将两个语言系统核心理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有一定的联系,都强调母语的影响和作用,也都强调独立系统的个人独特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在母语方面,中介语摒弃母语在习得过程中的使用,而超语系统则将母语作为习得者已有的语言资源加以利用;在资源整合方面,中介语主要利用偏误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梳理并作为语言习得资源,而超语系统是将所有的语言资源、社会资源、认知资源等动态整合为习得者所用;在语言输出方面,不同于中介语存在语言僵化的可能性,超语输出的意义是动态的、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二语习得理论,为厘清不同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观做出贡献,也可以更好地指导教师开展二语教学,促进学生二语的掌握和提升。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以上发现进行真实二语课堂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中介语和超语系统在二语课堂上的长处和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