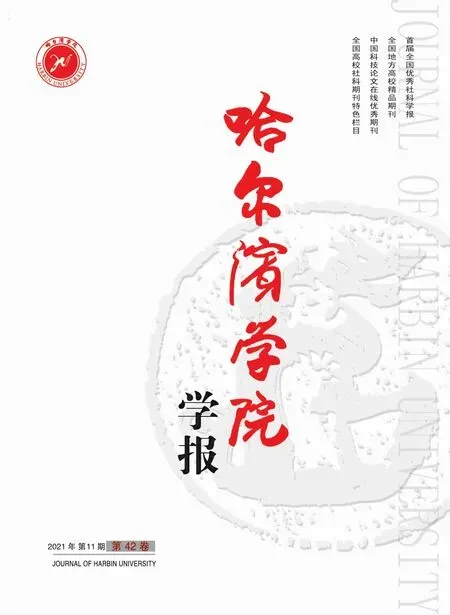清代江浙闺秀诗社之变迁
2021-01-17王细芝
王细芝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0)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源远流长,明清以来,女性文学创作更表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其中,不仅创作人数众多,而且就人事而言,更呈现出家族化、地域化的群体特征。才媛们既于闺中唱和酬答,更与闺外知音结社联吟,将一代闺阁文学推向了繁荣兴盛。
关于结社,明清之际风气尤为浓厚,正如谢国祯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所言:“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数百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1](P7)江浙闺秀们受此风浸染,纷纷走出闺阁,效仿文士结社吟诗。这当中,尤以“午梦堂”作家群、山阴祁商作家群、蕉园诗社、随园女弟子群、清溪吟社、碧城女弟子群、秋红吟社、秋社等闺秀作家群影响最大,她们代代相继,在有清一代经历了萌芽、壮大、成熟阶段,由家族性创作走向跨区越省,最终引领了整个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与昌盛。
一、家族式闺秀诗社的萌芽发展
在明末吴江的众多名门望族中,“午梦堂”作家群最是文采风流,济济一堂,其中,女性创作更是“午梦堂”文学的主体。这个群体的中心是沈宜修和她的三个女儿及表妹兼弟媳张倩倩,成员包括沈家主要房支的亲戚一共约有十五人。她们以家庭亲缘关系为纽带,聚集在一起雅集吟赋、授管分笺,引领了家族式女性诗社的萌芽。
入清以后,浙江山阴的祈、商两族联姻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创作群,其中心人物为商景兰、商景徽姐妹二人。商景兰不仅帮助两个儿子继承家学,还向三个女儿及两个儿媳全心教授诗书,并与诸女时常聚赏吟咏,“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盛事;而门墙院落,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2](P29)
如果说祈商家族创作群体的聚集吟咏由于成员之间本身的亲戚关系显得相对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她们与当时行走尘世以卖字画为生的江南才女黄媛介和王端淑的交游唱和就尤显难能可贵了。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她们的社集活动,但她们诗作中出现的“诸社姊”“社集”等说明她们的确曾有结社吟咏。尽管她们没有给自己结社确切的称谓,但其已具备了超越闺阁的标志性意义,当可视为正式的闺秀诗社的登台。而伴随着当时男性结社炽盛的学术风气,闺阁诗人结社之风亦紧步相随。
梁乙真曾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中云:“自来闺秀之结社联吟,提倡风雅者,当推‘蕉园’诸子为盛。”[3](P24)说的就是清代著名的“蕉园诗社”成员。“蕉园诗社”的延续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清顺治年间,由钱塘顾之琼(字玉蕊)发起,邀诸女结“蕉园诗社”,其中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凤纶五人因合刊诗集,史称“蕉园五子”;后期则由林以宁发起,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云仪、顾姒、冯娴、毛媞、张昊在内,史称“蕉园七子”。“蕉园诗社”自成立之初延续了四十余年,前后均以“蕉园”命名,在“五子”与“七子”的变换中也完成了新老成员的交替,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家族姻亲和地域的局限,并以其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当时江浙一带乃至全国各地闺阁诗人结社的发展壮大,于整个清代女性诗社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酬酢式闺秀诗社的繁荣壮大
女性诗社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闺阁才女的创作热情。乾嘉时期,受文人奖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女子读书结集俨然成风,女性文学交流也不再局限于家族姻亲之中,江浙闺秀结社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发展势头,如“随园女弟子”“碧城女弟子”“清溪吟社”和常州女词人群等女性文学群落的出现。这时期的江浙女性文学社团基本上突破了以往的家族姻亲关系,甚至不同地域闺秀之间也互有交集,社内成员属地几乎涵盖了整个江浙辖区。她们打破世俗偏见,结社拜师,交往酬酢,在诗艺切磋之间开拓了自己的眼界胸襟,也激发了自己朦胧女性意识的觉醒。期间最为名噪一时的女诗人群即为“随园女弟子”群。“随园女弟子”群可谓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文学创作群体,不仅因其师为名噪一时的大家——袁枚,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济济一堂,作品之丰富与影响之深远难有出其右者。
《随园女弟子诗选》中共录有女弟子二十八人,后据王英志考证,“随园女弟子”人数实已超过五十余人,[4]加上袁氏家族的女诗人袁机、袁杼、袁棠,以及袁枚招收而人名不详的女弟子,则师从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体数量是空前的。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曾提到袁枚“影响所及,南至闽粤,北极燕鲁。钱塘为其桑梓之乡,金陵乃所久居之地,故两地妇女被其声教者尤广。读《湖楼请业》之图,知一时红粉,俱拜门墙,盖自古以来,提倡妇学之力,未有如袁枚者也”。[5](P404)
以袁枚为核心的“随园女弟子”群在当时盛传天下,名动一时,女弟子们跟随袁枚学诗填词,直承性灵诗学观,与“性灵派”作家互为呼应,对当时注重考据和拟古的诗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她们的作品普遍饱含真情实感,风格清新自然,向世人展示了女性诗歌独有的清丽细腻。
与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约略同时的还有松陵任兆麟结成的“清溪吟社”,“清溪吟社”从规模和影响上虽不及“随园女弟子”群,但在吴中(江苏吴县)地区也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在任兆麟、张允滋夫妇的带领之下,诗社中众多极具才华的闺秀常与闺阁外诗人书检往来,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清溪吟社”成员以吴中十媛为领袖,时称“吴中十子”。她们各有诗集问世,且有合集《吴中十子诗钞》,一时可以“媲美西泠、颉颃蕉园矣”。[3](P155-163)不同于“随园女弟子”的是,“清溪吟社”成员除了吟习诗词外,还兼习各种技艺。因此,论文学与竞技艺,正是“清溪吟社”的特色所在。
“随园女弟子”与“清溪吟社”繁华过后,另一为世人所关注的闺阁群体——“碧城女弟子”群应时而起,为清代的女性诗社的振兴推波助澜于后。“碧城女弟子”的授业恩师是嘉道年间浙江钱塘的陈文述。与袁枚一样,陈文述亦对女弟子满怀提携热情,其在很多文作中均不遗余力地介绍各闺秀才媛的生平事迹。门下女弟子群体成员约为四十四人,以吴藻以及陈文述的儿媳汪端为首,他们的组织与活动形式与“随园女弟子”群体颇为相似,当时的许多闺秀亦以身列碧城之门墙为荣。
袁随园与陈碧城两位文士对女弟子不遗余力的奖掖和提携,不仅从侧面加深了女弟子学习与创作的兴趣,更促使了整个清代闺秀诗社的发展。道光以后,江浙地区闺阁女子结社成风,并由此绵延了整个有清一代繁盛的女性文学创作。而她们的创作亦平衡了文坛上男性文学一家独大的状态,让文学的空间因此更加完整和丰富多彩。
三、开放式闺秀诗社的成熟圆满
历史进入晚清至近代以后,女性文人的地位发生了更多的改变,大规模的结社吟咏不再受到封建保守主义者诸如章学诚之流的抨击。此期的女子结社有以沈善宝、顾太清为中心的“秋红吟社”,以徐自华、徐蕴华为代表的“秋社”,以沈祖棻为核心的“梅社”等。而这时期的女性诗社相比清前期、中期的诗社,成员结构已由以亲眷闺友为基础的本地闺秀组合发展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异地结合,这无疑是明清以来女性诗社发展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浙江籍女子为主在京城结社的“秋红吟社”,就是由钱塘才女沈善宝发起,组合来自全国不同区域的在京上层贵妇及官员女眷而成。据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己亥(1839)秋日,余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6](P651)诗社以沈善宝为首,顾春(太清)、许云林、项屏山、钱继芬(伯芳)、楝鄂武庄等才女为成员。“秋红吟社”的成员大多远离了自己成长的故土,凭着对文学的真挚热爱与倾心向往,不再拘于家族内亲眷间的唱和酬答,而是选择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友人为知己结社联吟。她们不曾借助父兄、丈夫与师长等外力扶持,纯以闺阁女子之力相约结社,为当时的女性结社提供了又一个全新的典范。
“秋红吟社”的发起者沈善宝曾著有《名媛诗话》,这是一部纯粹的女性诗歌论著,其目的旨在传扬闺阁之才华,不使之淹没于后世,实乃研究清代女性文学的宝贵历史文献。沈善宝与吴藻、许云林、顾太清、汪端等才媛结成“秋红吟社”后,常常在诗词唱和中取长补短,竞相赶超。她们相约集会,结伴游赏,诗社生活极其丰富多彩。
值得一提的是,“秋红吟社”的重要支柱顾太清,还积极引荐了一些满族成员加入诗社,如富察蕊仙等人。如果从诗社成员籍贯结构来看,“秋红吟社”在当时无疑带有了全国性的特点。而以满族诗人顾太清为主的群体不仅突破了以往诗社成员的地域同一性,也突破了长久以来女性创作中的群体同族性。从这一点来看,“秋红吟社”对于女性文学创作的交流、传播,较之以前的地方女性诗社前进了一大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社中成员多为眷属,随着家人的出任异乡而交通不便,才媛们的联系不免日渐稀少,再加上沈善宝的谢世更使“秋红吟社”遭受了致命打击,所以不过三四年,活跃一时的“秋红吟社”便星流云散、各归东西了。
随着女性诗社的日渐成熟和时代的风云变化,女性意识在闺秀才女中也日渐觉醒,近代著名才女徐自华于1908年发起成立了“秋社”,诗社成员在创作上更多地关注于广阔的社会空间、国事动态。她们秉持自由思想和心怀民族解放的火种,诗文往来之间少了许多以往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更多地是表现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浓厚的时代感。相比以前纯粹的闺阁文学,她们的作品又有了进一步的情感升华。
此期闺秀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闺阁诗社活动,她们当中很多人开始勇敢地加入以男性为主的诗社,共同追求事业的成功,比如当时极富盛名的“南社”,江苏籍女性成员就有二十多人。随着两性诗社成员的相互渗透,闺秀诗社从早期的单一纯粹最终发展到了与男性诗社合流为男女共同参与的团体,绵延有清一代的女性结社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综上,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清代江浙才女诗社的涌现,乃是历史与江浙文化交汇的一种体现,凸显了江南钟灵毓秀之地的人文风雅。而其中之才媛以女子特有的柔韧坚忍以及对艺术的执著,引领了清代女性文学步履蹒姗的发展,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闺秀诗社由闺阁而至社会,由江浙而至大江南北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