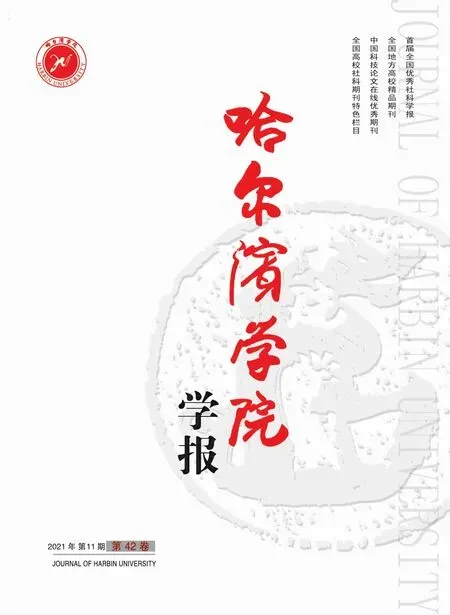沈括诗学观之“造微”说探赜
2021-01-17蒋思翔
蒋思翔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北宋时期的学问大家沈括,可以称之为历史上罕见的“通才”,《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1]并非言过其实。沈括早年进士出身,先后助力王安石变法、提举司天监掌管浑天仪、出使辽国、改革盐钞役法,政绩斐然,其还主持修撰了《奉元历》,编订《九军阵法》《使辽图抄》,天文地理无所不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所建树。近知命之年,沈括因永乐城失陷所累被贬至随州,后经周转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筑梦溪园一座,度过余生。在被贬黜的十几年间,沈括醉心于学术著作的记述和编撰,并自嘲道:“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者言,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2](P257)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梦溪笔谈》就写于这一时期。
《梦溪笔谈》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笔记小说,除却记述沈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见闻之外,还收录了相当的人文学科内容,涵盖了历史学、音韵学、书画学等诸多方面。其中,《艺文》卷较为集中的整合了沈括的诗歌理论,在卷十四《艺文一》的《论小律诗》一节中,沈括提出了诗歌写作要“造微”的观点: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暇可指,语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为难医也。[3](P481)
“造微”最早出现在五代齐己的《酬微上人》诗中:“古律皆深妙,新吟复造微”,是指“达到精妙的程度”。这一观点在以往讨论沈括诗学观时虽被屡次归为要点提出,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细致分析。下文拟从“造微”的前期准备、“造微”的实现与“造微”的接受等对沈括诗学观之“造微”作出探析。
一、“造微”的前期准备:求工亦求真
文人墨客对遣词造句的重视自古有之,《论语·卫灵公》曰:“辞达而已矣。”[4](P569)汉代刘向的“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4](P569)更是将谨饰文辞的用处拔高到安身立命的高度。通读《梦溪笔谈》之《艺文》篇发现,沈括对位于“造微”之前进行诗歌写作的基本功要求亦在于遣词造句的工致。
《艺文一》开篇即记载了欧阳修对林逋诗歌的评价:“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3](P471)这里的“语新”和“属对亲切”即是指诗歌语言的清新脱俗和上下句对仗的贴切,此句虽是欧阳修所感,却也侧面体现了沈括对在遣词用语及对仗方面表现诗文的认同。沈括对诗句修辞美的追求更直观地体现在《艺文一》篇二《论对句》中,他举韩愈文集中的《罗池神碑铭》一诗,诗句“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与彼时铭文的石刻本对照,却是“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沈括由此追溯古人好将诗歌字词错落“倒装”的历史:“如《楚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3](P472)词序经过倒置,上下两语互相交错,语句的气势反而变得强健有力,这正是语句精工的艺术所在。沈括认为,于遣词造句处求工,当是诗歌通往“造微”的必要条件。
沈括生活在欧阳修执掌文坛的时代,他本人对欧阳修有着极高的评价,于《上欧阳参政书》中誉其“为天下之师三十年余矣,其养育贤才,风动天下,未有不如其意。”[5](P51)所以,沈括的诗学观念多少会受到欧阳修诗文写作理论的影响。欧阳修在当时对史、传文的写作提出了以“事信言文”为基础的理论观点,并于《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中明确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要求对人物的事迹、经历记载要正确,评价要客观,论断要恰当,不能文过饰非、徇情溢美,要实事求是、内容真实,才能取信于人。[6](P151)这种求真求实的作文要求与沈括身为科学家细致严谨的作学之风不谋而合。
沈括认为,诗人在写作诗歌时,对所写内容要力尽“求真”,不能不切实际、过分夸大,以致诗文读起来荒诞不经。《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篇中,沈括直接以《文章之病》为题对司马相如、白居易和杜甫天马行空的荒谬行文作出讥讽: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馅耳。此亦文章之病也。[3](P712)
《上林赋》中,司马相如将上林的八条河流形容为各自分流、方向相背而姿态各异,水势浩瀚无边,最终向东汇聚注入太湖。沈括于此处生疑,八条河流明明都汇入黄河,何来东流进入太湖一说?《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其间却突兀一句“峨嵋山下少人行”,峨嵋山地处嘉州,与唐玄宗巡幸四川路线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杜甫写柏木粗四十围、高两千尺,可四十围不过直径七尺,只是一个男子的身高而已,实在显得细长了些,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身材简直就是一张馅饼。
沈括将上述几种情形统归为“文章之病”,表示出强烈的否定态度。卷十四《艺文一》《唐人富贵诗》中也有一例,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3](P474)事实上十幅红绡做成的蚊帐内里只有四五尺宽,根本无法伸脚,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描写,皆因韦楚老“不曾近富儿家”,并未亲眼见过实景实情罢了。从上可知,在沈括的诗学观念中,作文写诗,当以写真实发生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事为佳,如果强以不知以为知,在脑海中胡乱勾画,则容易使诗文经不起推敲,落人口实。
求工与求真,在先人文论中已不鲜见,沈括引这两点为诗歌写作的基础,体现了他趋于传统的诗学观点。在他看来,“造微”固然艰难,“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但在“造微”之前,通过清丽工整的诗歌语言和考据扎实的诗歌内容,使诗首先成为诗,实乃“造微”之基本。
二、“造微”的实现:精炼到传神
《论小律诗》中,沈括直言“造微”之难,难就难在“字字皆炼”。何为“字字皆炼”?结合沈括在《诗主人物》一节所云“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3](P481)可知,此处的“炼”指的是炼字锤句,在已具雏形的诗文之上进行长时间的推敲、琢磨,使文辞简明畅达,文不害意,达到语句精炼的效果。
《诗主人物》中记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创作经过:“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3](P475)
古有《文心雕龙·练字》语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7](P470)即是强调诗句讳忌“同字相犯”。可崔护炼诗,为护意全语工,哪怕一句有两个“今”也全然顾不得了,这正是“唐人工诗”的功夫所在。在炼字的基础上,沈括又提出了“求简”,这不仅与当时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相呼应,也契合了沈括深受晚唐体影响而形成的“平易清丽”之诗风。
《拙涩与文风》一篇中记载了一则“黄犬奔马”的故事: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3](P488)
通过这则记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沈括对于诗文繁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宋初,受“西昆体”影响,华靡之风流于文坛,对偶句成为文人崇尚的写作方式,并盛行一时,但穆修、张景给出的另类行文则反叛了这一规约,虽然在古文革新运动之初显得较为呆板,但仍值得肯定,所以才能“传之至今”。沈括在二者行文基础之上以“有奔马,践死一犬”记之,比起前二者的“拙涩”,显得简明有力,后世鲁迅、陈望道等也撰文奉沈括此句为佳,认为还是沈括的写法最为明了。由此观之,炼字苦吟,去冗求简,即是沈括胸中“字字皆炼”之道。
然而,“字字皆炼”只是“造微”的第一步,沈括旋即指出:“若字字皆是无暇可指,语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字字无暇虽难得,但仔细推敲起来没有好处可言,写景达意纵然完备,但仍缺少可以讽诵玩味的地方,仍难以实现“造微”。这并非诗文语言层面上的缺失,为了进一步阐明“功”与“可讽味”之处,沈括举“三馆楷书”为例,称其“不可谓不精不丽”但“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这种在历史上通行于昭文馆、集贤殿和史馆中的标准楷书,类似于明清“馆阁体”,字形上追求整饬匀称,但风格僵化,无法展示书法运笔灵活多变的“神韵”。可见“造微”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到“传神”。
“神”最初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后经“天人合一”思想的转化,逐渐影响到后世诗学。南朝刘义庆“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唐代张九龄“意得神传,笔精形似”、白居易“文之神妙,莫先于诗”皆是从其发展而来。[4](P395-396)到了宋代,又有邵雍的“艺虽小道,事亦系人,苟不造微,焉能入神”、刘道醇的“命笔造微,事物皆备,……故列神品”,[8]都指向“造微”与“传神”的内在联系。
作为书画学大家,从沈括的书画学观点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其文学观点的投射,在卷十六《书画之妙在画意》中,沈括着意探讨了存在于书画中的“意”到“神”明,指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3](P528)这里的“奥理”,指的就是艺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寓意。之后,沈括又云“予家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3](P528)更直接点明了艺术作品至臻至妙之时,神韵的自然到位。沈括认为,“传神”必须依托于作品的深层寓意来传递,诗人在创作诗文时要特别着重雕琢诗歌的意蕴,不能使诗歌空有其表,降低品格成为像《折杨》《黄华》一般的滥调俗曲。诗文写作,要通过精炼的文辞和内蕴的积蓄完成“造微”,由“造微”达至“传神”,使诗歌拥有点睛妙笔,读来回味无穷。
三、“造微”的接受:理想读者的在场
在追求诗歌“造微”的同时,沈括还特别注重能够品鉴“造微”的读者。在现代接受美学中,一部作品完成之后,在读者接受之先,便已隐含着读者,[9](P329)隐含读者即是创作者为作品所预先设定的能够完全接受其主旨内涵的理想读者。白居易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0](P15)传达了身为创作者对理想读者的期待。贾岛《送无可上人》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11](P81)刘勰于《文心雕龙·知音》中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7](P578)则足见优秀文学作品在文学接受环节的境遇不容乐观。
正如:“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论小律诗》云:“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沈括明确指出,在诗歌接受环节,形成接受障碍与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读者欣赏作品时不经思考,未曾“冥造”,对诗歌敷衍读之。在他看来,世上欣赏作品的人,大多数都指认浅显易见的部分,对于艺术家寄托于作品中的深刻寓意,能够进行潜心思索并最终得见的接受者凤毛麟角;诗歌作品即便“造微”,如果阅读者草草了事,也难以体会其精妙何在,所以写诗难,读诗亦难,如果诗歌的文学接受中缺少了懂诗的读者,就算诗是好诗,也很难得到正确的鉴赏和传诵。
“造微”作为沈括《梦溪笔谈》所构诗学体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观点,涉及遣词造句、用事、炼字求简及文学接受等各方面,以之为镜,可以通观沈括诗学观念之整体。沈括提倡诗歌写作先要“造微”,进而“传神”,呼吁理想读者归位,不仅蕴含着其对诗歌创作过程之初、之中所持的独到认知,还对位于再创作环节的接受者的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做出了进一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