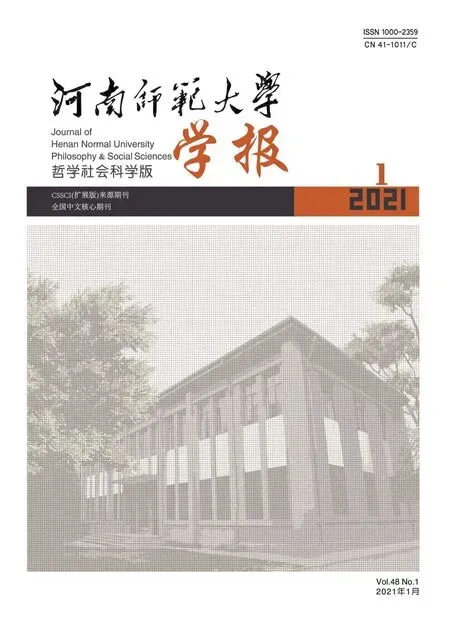治水国家:公共性建构的主体转换与政治发展进程
2021-01-16万婷婷郝亚光
万婷婷,郝亚光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无论是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社会公共空间,均蕴含着“一种公共性”(1)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符佳佳译,《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只有依赖一定的公共性方式,如共同生活和互相交换,才能进行生产。对于长期面对水威胁的中国而言,治水离不开公共性活动。从传统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再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基层治水先后孕育出民间河长、队长河长和主官河长。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治水的公共性如何转变?现代社会治水的公共性因何产生,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治理优势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借用公共性建构的分析框架,历时性剖析传统社会时期、改革开放前以及新时代治水的公共性流变过程,挖掘现代社会公共性的治理优势,补充“共在—共有—共识—公意”的公共性建构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
公共性一直是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就公共性的实现而言,西方学术界大致有三类观点:一是以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为代表的“社会行动交往论”,即在一个不同于私人领域的社会公众领域中形成的公共意识,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准则,以保证公共性的实现。二是以韦伯、卢曼等为代表的“法律制度正当论”,即按照正确程序制定的法律制度,其拥有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共识性,自然成为社会个体的行为规范,确保了公共性不受个体行为的影响。三是以马克思、罗尔斯等为代表的“价值信念认同论”,即以重叠共识、公共理性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表现的公共性,共同核心是正义。基于正义的政治认同,便能共同建构公共性的属性。
一般而言,公共性主要包括共在性、共有性、共识性和公意性四个维度(3)郭湛,王维国:《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在基层治水社会过程中,公共性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治水空间的共在性、治水问题的共有性、治水方法的共识性以及治水当事人的公意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由于基层治水的共在性、共有性、共识性以及公意性不同,基层治水的主体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如在传统社会时期,囿于中央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在双层治水体系(4)郝亚光:《“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下内生出类型多样的民间河长(5)“垸首”“堤长”“坝长”“堰长”“块首”“圩长”“河长”“沟长”“沟老”“渠长”等。参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家户调查数据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渗透到民众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蜂窝状结构”(6)“蜂窝状结构”,指在中国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虽然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稀缺资源,并且为了执行国家的意志而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系统,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相反,各个地方反而形成了一整套的自给自足的自治体系。这一概念是由唐尼索恩提出的,许慧文借它来概括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详见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By Shue Vivienn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75.内部的水利建设由生产队长带领完成。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基层治水则由地方主官负责(7)地方河长指省、市、县、乡(镇)各层级的主要党政负责人。。为解释这一变迁,本文拟从公共性建构的视角,从共在性、共有性、共识性和公意性四个维度,探讨中国基层治水的主体变迁及其历时流变进程。
二、民间河长:传统社会时期水利共同体的内生需求
在传统社会时期,不同村落的祖先无论是为了躲避战争,抵御野兽的侵扰,还是被迫逃荒寻生、开荒插标,都会选择适宜居住的地点。在选择居住点时,除考虑外部社会因素,还要考虑居住点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特别是村落与水源及农田与耕地的关系。为确保生存,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村民们,一直围绕着“如何满足生活与生产用水的需要”开展自愿联合;在半湿润、湿润地区的村民们,围绕着“如何保证生产用水的稳定”开展多样合作。在共同用水、治水的过程中,内生出多种类型的“民间河长”。
(一)临水而居的共在
农村的居住形式,一般由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农业经济共同决定。时间越往前追溯,自然条件越起到决定性作用。起源于四大河畔的世界古文明,便是例证。
法国近代知名地理学家德芒戎指出:“干燥而坚实,或多沼泽而又松软的地表,可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完全不同的居住形式。不论危险来自河流或海洋,防止被淹的需要常导致人们集居在一起。”(8)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4页。华北地区和地中海区域的干燥地区一样,“水对农村的居住形式肯定有专制的影响……几乎所有人口全住在村庄里,每个村庄都位于泉水附近”(9)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5-156页。,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井域社会”(10)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的概念。在湿润地区(华南、江南等区域),村民分别聚集在江、河、湖、泊、堰、塘、坝、沟、渠等水源附近,以保证水稻生长过程的用水。
由于受地形、地貌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南北区域村落内部的空间结构形式有较大差异。北方的村落,不但形成以单个或多个水井为中心的集聚结构,而且形成以水井为中心的村落公共空间。在长江流域以南,“房屋在经过农耕整治的坡地上分散成小群,稀疏分布在一些园圃和农田中间”(11)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0页。,不但形成散居的村落结构形式,而且形成以湖、泊、堰、塘、坝等为中心的生产公共空间。
(二)治水困境的共有
气候的季节性、水源的便利性、土地的肥沃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着村落的规模、存续、分布及其生产活动(12)R.M.基辛:《文化·社会·个人》,甘华鸣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在传统社会时期,囿于气候规律和土壤条件,改善用水条件一直是村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如何实现“水源使用的便利性”,是所有用水当事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作为生命之源的意义尤为凸显。该区域干旱少雨的客观气候条件,致使地表径流较少、钻探水井的难度较大,远远“超出个体能力和范围的生存条件,村民便需要与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13)胡群英:《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建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在山西、陕西、宁夏、新疆等地,村民除积极组织邻居对有限的地表径流开展治水、用水外(14)在传统社会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斯坦村的村民共同推选出“米拉普”(管水员),专门负责管理渠道的维护与水源的分配。,还积极联合其他村民共同凿井,即北方乡村常见的“官井”(15)在传统社会时期,山西省运城市席村以及河北多地农村都有“官井”之说。。
在半湿润地区,特别是居住在黄河边的村民,有着和尼罗河流域相似的“肥沃的土地与有利的气候条件”(16)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6页。,先民们既不需要用犁犁地,也不需要用锄掘地,甚至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取得大地的果实(17)《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5页。。但是,村民必须对水进行较为合理的综合控制,或共同开凿沟渠,或共同修筑堤坝,以使低洼之地免遭洪灾(18)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48页。。所以,视沟渠、农田为“命根”(19)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第一卷 东方的遗产》,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96页。的村民,共同面对着如何避免河水泛滥失控的难题。
在湿润地区,充沛的雨水孕育出纵横的江河与遍布的圩田。如何利用既有的地形、地势进行引水、排水,保证水稻生长所需的水分,是所有稻农共同面对的难题。不论是散居还是“集居的村庄,都在那些耕地连成一片、能够进行同样经营的地区。在共同需要的支配之下,形成了集体的组合。井、水塘、池沼的挖掘和维护”(20)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1页。成为共同生产的基本要求。
(三)生存伦理的共识
传统社会时期,基层用水当事人“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1)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为“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22)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1页。,用水当事人在共同治水的议题下,形成了以生存伦理为导向的“相邻为好”“权责对等”“同干同湿”等重叠的共识。虽然重叠的共识不是“严格的共识”(2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10-411页。,但经过用水当事人的共同商定,便具有较强的公共性(24)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首先,相邻为好,是生存伦理下的基本共识。由于受地形、地貌的影响,连片的田地很少,“插花田”“插花地”非常普遍。无论是旱地还是水田以及插花田(地)的排灌离开邻田(地)均无法实现。水经过别人的田地,必定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影响。为尽量减少对“淌田”(25)淌田是指被水流经过的田地。带来的减产,各地用水当事人在“相邻为好”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过水不带水”“下肥不过水”“缺水带水”等过水共识。倘若有人违反这些“规则”,将面临用水共同体的制裁。正如美国教士明恩溥看到的:“如果什么时候某个人在他的乡村里特别不受欢迎了,那么第一个威胁就是切断他的水源。”(26)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
其次,权责对等,是生存伦理下的共识原则。在生存伦理的治水共识下,尽管保证了每个家庭的生存用水,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享有。无论是将“自然雨水”转变为“可灌溉用水”还是除去“水患”,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政府无法提供此类公共服务时,只能依靠基层社会自我完成。为此,各地在兴修和维护水利工程时,基本按照“按亩出夫、照夫派土”的标准,在所有用水户中分派挑土和出工任务,即田地多者需多挑多工多费;田少者可少挑少工少费,确保每位用水受益人为治水付出等量劳动或货币。
最后,同干同湿,是生存伦理下的共识理想。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一直秉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理念。在同一个用水共同体里,用水当事人有着同进退的本质意识(27)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6页。。为实现这一共识理想,不少地方成立了塘委会、堤委会、垸委会、水会等相对稳定的自组织机构,甚至有的地方设立了固定的办公场所,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水。
(四)自我实施的公意
为保证治水共识的长期有效,“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28)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即治水当事人需依赖公意,因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页。。
首先,民间河长是治水公意的代表者。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为实现共同治水的公意,各个基层水利共同体成员选出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以及治水经验丰富的民间河长,如“堤长”“坝长”“堰长”“垸首”“圩长”“河长”“沟长”“会长”等,并将“同意权力”(3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6页。让渡给“民间河长”,委托其负责基层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维护,统筹水源的分配与利用,协调用水的矛盾与争端。
其次,自治组织是治水公意的执行者。为更好地执行公意,在治水难度较高或用水规模较大的地方,出现了诸如堤委会、垸委会、坝委会、塘会、水利会等水利自组织。这些自组织不但有独立的组织架构,而且有行之有效的组织章程。如在湖南泉塘村(31)郝亚光:《“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塘会由社员(用水户)大会、股东塘委会(从用水户中选出4名股东代表)、15名股东以及职业看水人共同组成。即使在塘长更替的情况下,相对固定的自主治水组织,也能维持治水的正常秩序。
最后,民间惯习是治水公意的保障。法律作为公意的表达(3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1页。,不但承载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而且保障公意的执行。在传统时期的基层社会,用水当事人为实现共同治水的共识,经过累世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共同遵守的民间惯习,长期寄居在当事人的身体之中,成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3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确保治水公意的持续实现。
三、队长河长:改革开放之前水利共同体的国家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的开展,传统的生产关系得到重塑。特别是“计划经济代替了自然的小农经济,以及伴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政权结构上的转化——由皇权国家机构转为控制着每家每户经济抉择的党政机构”(3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93页。,国家权力深度介入村庄及村民生活。随着传统的治水共同体瓦解,水利政治共同体逐步形成,并在中央政府细致入微的指导下,动员“天下一家”的社员对农田水利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35)在地方主官的带领下,通过合作化、集体化的形式,全国先后修筑了八万余座大中型水库,实现灌溉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50%以上,较1949年前的灌溉面积提高了3.5倍。参见郝亚光:《公共责任制:河长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一)“细胞化”乡村的共在
一般而言,“一个群体的形成包含着整合纽带的发展,这种纽带将个体们团结在一个集体单位中”(36)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7页。。在传统社会时期,基层水利共同体在血缘、地缘、文化等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以共同治水为纽带的多层次自愿联合共同体。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传统的交往模式被中断。以血缘、文化为主要联系纽带的“熟人社会”(3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被新的政治关系取代。乡村社会不但逐渐被“细胞化”,而且“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整体中,成为其有机体的细胞组成部分”(38)姜振华,萧凤霞:《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载刘东:《中国学术》(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50-351页。。
特别是经过合作化运动,进入人民公社之后,中央政府完成了对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重构,建立了新的权力结构。村民也因此完全被限制在由乡村干部所控制的行政单元(人民公社)。在萧凤霞看来,当时的乡村干部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借助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大工具,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的意志。村民的农业生产行为不再由个体决策,而听命于组织的统一安排与指挥(39)参见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基层治水方面,“过去很大程度上归于地方和乡村上层人士的偶然的倡导和协调。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改进的关键在于系统的组织,从跨省区规划直到村内的沟渠”(4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234页。。正是在这样的系统组织下,“细胞村落”治水从传统社会时期分散的自愿联合变为统一的集中组织。
(二)追求旱涝保收的共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传统时期的大水利工程均归国家所有。私人投资的小型水利设施,仍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恰如土地改革给无地或少地村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过于“均分”导致普遍出现一户分得1/4头驴、1/4辆大车以及十几户共有一张犁的窘境(41)弗里德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相互独立的用水农户内生出合作治水的需求,多地出现季节性、常年性的灌溉组织,如“浇地队”“打井队”“巡渠组”“包浇组”等。各级政府因势利导,推动各类互助组的建立和运行,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鉴于此,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将农业合作化提上议程,并于1951年9月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成为全国范围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端。经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以及“跑步”进入人民公社后,一方面,“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的塘、井等水利建设,随着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07-408页。,实现了对大小水利工程的公有化改造。另一方面,村民全部纳入“社员”。当然也有不少村民为了避免出现“不入社,以后社里不借你东西使,叫你自己打井”(43)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的尴尬,不得不加入“社员”组织。如何实现集体农业生产的旱涝保收,治水问题成为全体社员的共有难题。
(三)“改天换地”的共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4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兴修水利是中共中央对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基本判断。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一方面在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因地制宜地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和台田系统,开展小河治理等;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开展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以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45)史敬棠,张凛,周清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79页。。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松江县,20世纪50年代集中修筑了海塘、湖堤、河坝以及开凿和疏浚大的河渠,20世纪50年代几乎在“每个公社建立了电灌站”。1960年代末,全县上下将“大规模水利工程和田块用水连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4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234页。。
水利作为一项特殊事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弱、技术相对落后,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中央政府通过“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三主方针”等措施完成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提升和改善。以工代赈作为经常用的灾民救助措施,不但可以解决公共性问题,而且可以使民众受益。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明确指出,“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民众“修堤治河不但可解决灾民目前吃粮,而且是解决水患的基本办法”(4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6页。。民办公助是以“统一规划、尊重民意为前提,以财政补助为引导”,将投资与投劳并举,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又妥善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难题”(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基于河南省治理漭河的经验,《人民日报》于1958年3月21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49)《人民日报社论选辑 1958》(第2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年,第54-58页。的“三主方针”,迅速成为全国群众性治水运动和水利建设“大跃进”的基本方针。因此,在河南仅水渠一项,“大跃进”运动中便修建了“红旗渠”“共产主义渠”“东风渠”“人民跃进渠”等重要灌溉渠道。
(四)“政治主导”下的公意
在“改天换地”的共识下,全国各地社员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以至省界,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到外地参加水库、渠道和运河的兴建甚至挑水抗旱(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为确保集体治水公意的实现,各地通过“军事化”“工分制”“国家化”等手段,组织动员社员积极参与。
其一,军事化。步入人民公社后,不愿意在革命发展中停顿下来的劳动人民,希望得到更多利益,提出了“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51)人民出版社:《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页。。之所以要将组织军事化,主要是为了保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率。众多跨社、跨县甚至跨省的社员,只有在“军事化”纪律的要求下,才能在较大范围内自由调动。虽然党中央也明确要求注意把握劳动节奏,“苦战”结合“必要的休整”(52)人民出版社:《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页。,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出现工作超时和“开夜车”(53)胡伟:《貌合神离:正当性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集体化后期水利个案研究》,《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卷。等现象。
其二,工分制。基于军事化的组织动员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一批水利工程设施。但过于“硬性”的要求,使不少社员产生负面情绪。由此,将社员个体与人民公社命运紧密连接的“工分制”应运而生,并成为社员普遍接受的劳动计量与报酬分配的基本制度。为体现每位社员在集体工作中的公平性、效率性,激发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各地因地制宜地制订出较为详细的工分标准。如河北邢台白岸公社规定,“男劳力每月26个,单身汉25个,妇女、民兵26个,有2个妇女小孩不吃奶20个,小孩大的15个,小点的身体不好的10个,年老体弱的6个,脱一个工罚1个,超过奖1个,到地迟5分钟去5厘,10分钟去1分,20分钟去2分”(54)邓群刚:《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07页。。
其三,国家化。国家主导完成的各项水利设施,与传统社会时期基层水利共同体修建的水利工程相比,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维护,与习惯法截然不同。所有建成的水利设施,均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什么时候可以用、谁来统筹安排、谁负责操作以及具体责任和义务,均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具体负责人作为国家在乡村的代理者,严格履行国家意志,塑造着国家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即使有着“传统底色”的社员,也会按照“国家化”的规则治水、用水,形成新的“整体意识”和“生活感觉”(55)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35-336页。。
四、主官河长:新时代生态共同体的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打破了“蜂窝结构”的界限,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改变了农村共同体的结构。随着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推进,农业现代化经营既要借助于农村水利基层服务体系,又要依赖于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5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7页。。
(一)“流动社会”的共在
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就地转移到异地,从“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单栖人口变为“离土又离乡”的城乡两栖人口(57)钱文荣,朱嘉晔:《农民工的发展与转型:回顾、评述与前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9期。。在2018年农民工的总量中,近六成是乡外就业,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占44%,省内流动人口占56%。从年龄结构看,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其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58)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村工作通讯》,2019年第11期。。相对于年轻力壮的外出务工人员而言,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是老人和妇女。原有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彻底改变,原有的生产用水共同体成员发生重构,原有共同用水的机制发生了变化。随着土地承包与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进,以家庭为主的生产用水需求日益凸显。生活在同一地域下的老人与妇女,成为“流动社会”背景下新的共在组合。
(二)“公地悲剧”的共有
小农户的生产活力虽然随着政社合一体制的调整而得到激活,但因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安排的调整尚未跟上,致使小农经营再度陷入“汪洋大海”。一个个独立、理性的农户,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行为,形成多重层次的“公地悲剧”。如集体化时期较为有效的自流灌溉系统,因无人维修而废弃。原本属于村集体灌溉渠道的占地,常常被沿渠农户填埋种地(59)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24-625页。。公共沟渠被破坏,导致某些旱涝保收的地方重陷“晴旱雨涝”的困境。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竞相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导致了水体污染、水土流失以及生态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无序开采、农业地膜滥用、生活垃圾随意处理、农村养殖场布局不当等,不但造成河道的生态环境破坏,而且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乱象,甚至影响到饮水安全。2018年,全国10168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27.86%的浅层地下水监测井水质总体较差,Ⅰ至Ⅲ类、Ⅳ类和Ⅴ类的水质监测井分别占了23.9%、29.2%和46.9%(6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mee.gov.cn/home/jrtt_1/201905/t20190529_704841.shtml.。
(三)“生命共同体”的共识
鉴于农村生产用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央政府专门在21世纪初发出《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从管理机构、基础设施、人才队伍、资金投入等层面改善和提升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积极尝试引入市场机制,如山东等地开展了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的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不但有效地吸引了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而且破解了水利设施供给的不足。还有不少地方产生了用水者协会,既解决了上下游的供水失衡,又避免了“搭车”收费,还大大节省了管水劳动力。
然而,市场机制对于较大范围“公地悲剧”的破解难以奏效,必须依靠国家解决。虽然各级政府深谙“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的道理,但是“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治水行动大大降低了治水效用。国土单位只关注地下水、水利单位只关注地表水、环保部门只关注水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导致治水“碎片化”。对于跨地域的河流,涉及不同层级、不同主体的地方政府,因缺乏协同形成上下游、左右岸的治水局部化,严重制约了治水成效。因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6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7页。,水的治理须在“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水思维指导下,才能实现整体治水的最佳效果。
(四)“生态文明”的公意
面对日益严峻的治水形势,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时有发生,政府作为民众的代理人,是“主权者的执行人”,理应按照“公意”诉求行事,最大限度回应公意,将水治好(62)郝亚光:《公共责任制:河长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区域内的所有河流进行系统性治理,地方主官(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治水第一责任人,不但要实现纵向职责的有效配置(如主体承包责任、分级承包责任、分段承包责任),而且要实现横向联动的协同责任(如部门间横向协作责任、地方间横向联动责任),切实履行好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专业责任,保证治水公意的如期执行(63)郝亚光:《“河长制”设立背景下地方主官水治理的责任定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在框架分析理论看来,河长制作为河湖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不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治水领域的具体体现(64)郝亚光,万婷婷:《共识动员:河长制激公众责任的框架分析逻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而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地方主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下,在“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要求下,不但积极组织领导辖区内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如行政区内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以及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长进行督导、考核,而且主动对跨行政区域河湖的上下游、左右岸进行协调,形成联防联控,促成生态文明建设公意的实现。
五、结论与讨论
借助公共性建构的分析框架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基层治水主体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每一类治水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共在性、共有性、共识性以及公意性逻辑。公共性建构的不同条件,内生出相应的治水主体和负责人呈现出共同认可的约束机制,确保了公意的落实和治水国家的政治发展。
(一)从封闭到流动:共在空间的拓展
传统社会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不高,较低的交通水平大大增加了“距离的摩擦力”(65)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使治水共同体成员累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落世界。或因抵御水患,或因发展水利,治水当事人形成的共同体所涉及地域往往限于某个村落、几个村落或某个水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传统时期的治水共同体相继被改造。特别是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诞生之后,集体经济组织为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联合形成不同规模的治水共同体,跨村、跨乡、跨县甚至跨区、跨省兴建各种水利工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渗透,参与社会大分工。在“流动的社会”,原本同质的村民分布在不同的行业、领域,虽然看起来“劳动越加分化”,但这种“有机团结”使“个人贴近社会”(66)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1-92页。。水利共同体成员所共在的空间,不断得到拓展,共同关注的问题也不再限于生产用水。
(二)从一元到多元:共有困境的演变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时期治水共同体有着相对集中的难题。处在黄河流域的用水当事人,共同面对的困境是如何避免黄河的泛滥;处在沿江湖等多水地区的不少村落,共同面对的困境是如何抵挡洪水的肆虐;处在西南部高原山地的云贵村落,共同面对的困境是如何实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保证梯田用水。进入集体化时期后,原本不多见的水利工程变得“司空见惯”,原本缺水的农田变为高产稳产,原本缺田少地的山区被开山垦田,甚至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等)。为兴建这些水利工程,不同层次的水利共同体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原本在集体化时期妥善解决的用水难题,因为经营制度的变化而重新显现。与此同时,原本有助于农业生产、渔业生产的方式,外部负效应日益显现,并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从生存到发展:共识框架的扩展
为破解治水难题,不同阶段的治水共同体形成不同的共识。传统社会时期,各地用水户共同推选出来不同的民间河长,以实现共同体的治水目标。如“堤长”“坝长”“堰长”“塘长(塘会头)”“垸首”“块首”“圩长”“河长”“沟长”“沟老”“渠长”“水佬”“会长”“看水人”“管水员”“放水员”“看河人”“看堤人”“守堰人”“水利统头”(67)调查者:佀传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家户调查数据库。等。在集体化时期,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结构塑造了“队长河长”,不但赋予了队长带领治水的权力,而且规定了队长河长的具体职责。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虽利用市场机制,有效地破解了基层水利服务建设中的“公地悲剧”,却无法依靠市场解决较大水域治理的“囚徒困境”。为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的共识框架下,重新明确地方主官的治水责任。
(四)从惯习到法治:保障公意的实现
“着眼于公共的利益”(6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页。的公意,要求每一位河长及用水当事人遵照共识治水,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在传统社会时期,法律虽未健全,但各地长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治水惯习。在集体化时期,旧的治水惯习逐渐失效,各地在国家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建立起各种治水规则,有效约束了队长与社员的用水行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速推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与水相关的法律陆续出台,不但可以确保地方主官积极履行治水责任,而且可以促进民众自觉履行生态文明建设所规定的自然义务”(70)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3页。,上下合力共同促成国家治水公意的实现。
由此可见,中国基层治水的主体从“民间河长”到“地方河长”的转变,不仅是因为国家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是治水这一公共性事务的机理发生了变迁。《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于2016年11月28日正式推行后,19个月内便在全国全面建立了河长制,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究其原因,不只是地方主官治水公共责任的积极履行,而且有众多“乡贤河长”“企业家河长”“巾帼河长”“养殖户河长”“红领巾河长”甚至“洋河长”等社会公众的踊跃参与。从治水的公共性看,生活在同一时空下的社会公众,面临着相同的治水难题,达成了治水的共识,实现了“地方主官”执行国家治水的公意。然而,社会公众并非将“同意性权力”让渡给国家后消极等待,而是在治水共在性、共有性、共识性和公意性的内在需求驱动下,依托生态保护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治水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