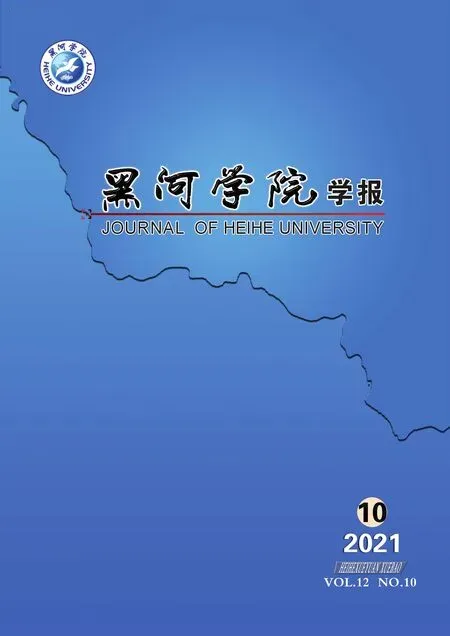《万历十五年》中皇帝的多维立体形象分析
2021-01-16崔芳芳
崔芳芳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1572年,10岁的朱翊钧继皇帝位,次年改元万历,被称为万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谥号神宗。万历在位48年,没离开过帝都巡视他统治下的万里河山,后面30多年除了视察定陵一次外,再没离开过紫禁城一步,在最后的28年里几乎不早朝。传统史学认为,万历在早期和中期勤于国政,配合首辅大臣张居正等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改革经济,开创了短暂的“万历中兴”,但后期却成为“沉迷女色”、不事国事、横征暴敛的昏君。
黄仁宇于1981年出版《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给世人呈现了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帝却二三十年不早朝,不管是在600多年前儒学当道的明朝,还是在600年后的今天,都应是一个被历史诟病的皇帝。《万》从多方面分析了万历为何从一个有志成为明君却最终成为竖起“无为而治”大旗而“不谋其政”的皇帝,使世人看到作为皇权象征的皇帝万历与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万历之间的内心挣扎与苦闷,看到作为皇权符号的万历与绅权的士大夫阶层的苦苦斗争及抵抗。
一、皇权符号“万历皇帝”与“凡人”朱翊钧的矛盾
在《万》中,黄仁宇明确指出万历的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因为作为全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享有一切尊荣,却“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在实际上,她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有权利……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照办不误……”[1]30。同理,作为皇权象征的皇帝万历,也是一个制度的附件,是一个象征符号,“有义务”“按部就班”地做好“传统习惯”要求他作为皇帝应尽的一切义务。
大臣们和皇帝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千头万绪的国家政事“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1]3,所以,在大臣们的心中,10岁登基的少年天子只需要扮演好他应扮演的皇帝形象,和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维护国家体制就行了。《万》中提道,八岁皇太子朱翊钧就已经“按照各种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被引导行礼……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后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1]4。从6岁被封为皇太子之后,朱翊钧定期参加这种繁杂且长时间的仪式,庄重不能出错。《万》中还单独举出在万历10岁继承皇位时,按照传统进行的“劝进”程式。群臣三次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但前两次皇太子必须拒绝,到第三次才能接受,就是“三推让”。拒绝的理由是固定的——“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个人名位呢?”[1]4自然,接受的理由也是固定的——以江山社稷为重,而“勉如所请”即皇帝位。“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犹如经过预习”[1]4。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就算再早熟,也许会有疑问,为什么对于失去父亲的真实哀恸却变成了官方“程序”呢?
除了处理政务和出席各种仪式,他的业余排满了经书、书法和历史的学习,为了成为自己、群臣和百姓心中的明君而坚持不懈努力着。定期举行的每月三次“经筵”不仅是学习,还是一场场枯燥而复杂的仪式。从10岁的男孩天性来说,确实有些难以忍受。“如果当今天子偶尔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绝无宽待……”直到他改正[1]53。按着这样既定的路线,万历应该就这么和百官合作,作为全国的榜样而终其一生。
作为皇权符号的皇帝必须是庄重的,能够庄重地完成各种场合需要的仪式,能够庄重地上早朝处理政事,之后能够庄重地参加经筵,坐几个小时听各个讲官讲授四书和历史。这些繁重的仪式会让一个成年皇帝疲惫不堪,何况一个10岁男童?10岁的少年有自己的喜好和情感,万历的天性和情感却被过度压抑。在学习上,偏爱书法并且进步神速。然而当时的首辅大臣张居正认为书法这种末节小枝与圣贤君主以德治天下的理念没有益处,就停止了他的书法学习。笔者无法猜测,被告知拥有至上皇权却连自己喜欢的科目都无法进行的万历,是以什么心情结束了书法学习。
史料记载万历宠爱郑贵妃,闹到不顾立长的传统而要立郑氏之子为太子的地步,导致长达十几年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国本之争。后世史书自然唾骂郑氏,把她写成祸国殃民且差点导致国本动摇的妃子,并指责万历沉迷女色而误国。黄仁宇却在《万》中分析了万历为什么宠爱郑贵妃——因为郑氏让他朱翊钧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需求的人。从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就必须在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检阅军队、接受战俘等场合,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让他深深受伤的是,甚至他的母亲都“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1]34。黄任宇指出郑氏得宠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符合皇帝情感上的需要”[1]33。“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1]34。所以,虽然拥有众多妃子,也被大臣们指责沉迷女色,甚至有八个不同的妃子为他生育皇子,但他一生偏爱郑氏及其所生子女,最后不惜与文官集团对抗十多年而不立太子。
在文官眼里,皇帝是一个机构,但万历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是既会冲动也会感伤的人。黄任宇点评万历,认为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而且欣然接受精神上的活埋”[1]149,所以,他没有魄力像太祖或者武宗那样把传统踩在脚下,而只是做到不顾群臣反对宠爱郑氏,以各种理由延缓立太子的时间,用自己不上朝、不经筵、不接见百官等各种消极怠工的方式表达有限的反抗。可以说正是这些去符号化的反抗,让万历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这符号与人性之争更体现在皇权与绅权的争斗中。
二、皇帝君权与士大夫绅权的矛盾
吴晗在《论皇权》中指出,皇权可以理解为治权,在秦以前是贵族专政,在秦以后是皇帝独裁[2]30。皇权具有独占性和片面性,不能与家人共治天下,不与将领共治天下,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理论上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利。现实却是皇帝一切行为需要按章办事,遵循祖制礼法。章是什么?礼法是什么?就是费孝通在《论师儒》中所说的“道统”——由士大夫阶层维护的那些“被认为维持政治规范的系列”[2]20。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被修改成为维持皇权的体系,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道统。士大夫阶层没有治权,不是通过政权来保障阶级利益的,而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驾驭或者影响皇权以保障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士大夫们秉持“事归政统,理归道统”的思想,一代又一代地与皇权共治天下。
在《万》中,黄仁宇指出当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之际,时年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就担起了皇帝这个身份的所有责任。不仅成为皇权的符号,还要努力成为明君圣王的形象。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的严厉管教之下,万历毫不懈怠,上早朝处理政事,参加经筵,各种典礼和仪式,每天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万历也能知“错”就改,庄重而且高贵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士大夫的代表张居正以理想的君主形象培养着这位少年天子直到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
这十年里(1572—1582年),年弱势弱的皇帝惟张首辅是从。这十年是张居正作为帝师兼首辅大臣的十年;这十年是张居正作为文官被皇权所能赋予最大权利的十年;这十年是张居正借用皇权的权威改革的十年;这十年是万历朝欣欣向荣的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是皇权与绅权合作的十年。费孝通曾指出:“师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说是政统加道统”[2]23。如果道统的出现就是为了影响或者限制政统,那么张居正非常成功地实现了道统的最高理想——不占有政权,也可以保障士大夫的阶级利益。但万历朝的前10年,是以皇权放弃诸多权力,而绅权获得极大扩张的不对等合作。因此,张居正死后被清算,除了压抑的个性和情感反弹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万历在争取皇权的斗争。
因为绅权需要皇帝成为一个社会机构,成为一个符号,而皇帝作为皇权的代表需要权力。文官们需要一个听凭他们摆布的皇帝,而皇帝又通过各种方式夺回属于他的权力。如黄仁宇在书中指出,与开国皇帝的职责和权限不同,万历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作绝对的抑制……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1]102。“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的要求恰相符合”[1]102。
皇权与绅权的争夺在张居正死后的万历朝处处可见。张居正去世那年,万历已经20岁,已经结婚生子,是正值精力旺盛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年纪。可是,万历突然发现自己最信任的老师居然是“欺骗”他多年的“道德伪善”之人,并且假借皇权赋予的权力反而压抑了他10年之久,甚至享有无上权力,于是开始了对张居正及其张党全国性的清算。从万历的角度看,后来众多指责和证据显示提倡节俭的张首辅居然私下生活奢侈,出行逾矩使用轿夫的数量,根据首辅自己利益安排官员等,这些权力的运用比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权力还要大,因为他很难升迁自己喜欢的官员,没有办法制定法律,不能统帅兵马,不能整顿军备,不能离开京城巡视个省,虽然表面上他被称为天子,被认为拥有至高的权力。
吴晗曾经指出,“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都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2]35。万历也在争取自己的皇权。但在万历朝的皇权和绅权的争斗,可以看出在士大夫们圣贤经典教育下长大的万历,不像他的先辈们,而对文官们还是忍让了许多。《万》这本书中着重描写了万历消极怠工的无奈。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万历会采取报复行动,但由于性格的缺陷,其“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1]120。在与绅权冲突的过程中,由于性格的懦弱与犹豫不决,万历没有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不合意的文官们,而是竖起了“无为而治”大旗来抗争。让首辅申时行苦恼不已的就是万历不参加经筵,不早朝,不见百官,平均一年才召大学士商议国事。
文官们为了道统,为了限制皇权,可以死谏。清流和死谏被文官视为为国效忠,应当流芳百世。于是,万历年间,也有很多文官为了清流的名声而批评皇帝的所作所为。万历不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以各种理由推迟立太子,各首辅却以各种道统的理由催促,实在劝谏无路就引咎辞职,用挂冠而去来“威胁”作为皇帝的万历。在中朝史料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本国史料记载多为大臣直言劝谏万历戒除酒色,朝鲜史料也有多处关于当时文官们劝谏万历的记载,其中礼部尚书冯绮临终前曾给万历呈有言辞恳切,但也颇为严厉的遗疏[3]。万历虽然不早朝、不接见大臣、不出宫门,不补充官吏,并不等于放弃治权。在其之后当政的二三十年里依然通过书面沟通的方式行使着皇帝享有的权力和履行着皇帝的职责,例如,万历三大征、梃击案的处理、及晚年横征暴敛并增加赋税以对金用兵等。
在绅权和皇权的博弈中,万历皇帝继续维持着明朝用道德代替法治来治理国家的传统,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来运作全国经济,没有抓住全球地理大发现的机遇来发展海防和海外贸易,与世界同步。在黄仁宇看来,当时的明朝,一个社会组织薄弱但官僚机构却因“乡谊”“年谊”“姻谊”捆绑在一起而异常强大的社会,对张居正死后的清算可以说是由于文官内部分裂而与争取皇权的皇帝部分合作的结果。张居正的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效率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得文官们处于被监控的心理恐惧状态之下,最后只能借着皇权取消了张居正的政策和清算了其支持者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皇权与绅权再一次的成功合作没有让万历获得更多的权力,只能在之后的30多年里以他自己的方式继续表达不满和争取皇权。
三、结语
10多年来,对万历皇帝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史料,通过对比研究韩国和朝鲜史料,万历皇帝不再是明清史料记载的消极怠政、横征暴敛的好色昏庸的一维肖像,而是一位“恩同君父,被士庶歌功颂德、建坛立祠的大德皇帝 ”[3],但也从一位“积极勤政”的皇帝变成“贪婪奢侈”的皇帝,并且手握权柄直至去世前一刻[4]。这也印证了黄仁宇从各方面对万历的描述,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过早失去童年,以及被亲人(母亲李太后)和师友(张居正和冯保等)当作权力符号对待并利用,而形成了懦弱却又不甘的性格。性格发展导致他虽不甘被道统控制,却最终又甘愿被精神活埋似地活在紫荆城,然终其一生都在采取挑衅传统儒家圣王形象的方式践行着、争取着皇权。虽然李亚平谈到《万》这本书的时候,提到黄仁宇写历史是客客气气的,点到即止[5],但万历的立体形象却因为这本书而广为人知。历史的研究方式和书写方式也因此而更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