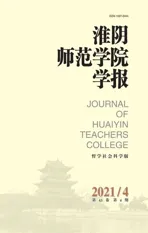保护利用运河宗教遗存弘扬淮安开放包容文化
2021-01-16仲波
仲 波
(淮安市政协 文化文史委, 江苏 淮安 223000)
淮安因水而生,依运(河)而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所开凿邗沟的北端至淮河南岸末口,从此淮安处于控扼江淮的交汇点而成为南北交通干线的重镇。2 500多年来,大运河多次变迁,历经朝代更迭,淮安因处于黄淮运交汇之地,“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成为漕运要津、交通枢纽、军事要塞。明初至清中叶,“天下九督,淮居其二”,出现了“河、漕、盐、榷、驿、仓(船)”萃处一郡的独特局面,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先后开府于此,淮北盐政分司专职驻节,淮安成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黄淮运河治理中心、淮北盐集散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船制造中心等五大中心,与杭州、苏州、扬州并称大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是名副其实的“壮丽东南第一州”、中国“运河之都”。南船北马人流大量涌入,“五方之民杂居淮上”,带来了异质文化的输入,催生了多元开放包容文化,提升了文化的张力和竞争力,为多种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和融合提供了便捷路径和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围。
一、淮安多教融合,遗存丰富,呈现纷繁兴盛的宗教发展格局
在淮安大运河两岸,各类宗教遗迹星罗棋布,蔚为壮观。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淮安境内的庵、观、寺、院就有124座。在清江浦大闸口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的清江文庙,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的佛教慈云寺,建于明代的道教都天庙、伊斯兰教古清真寺,以及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基督教堂福音堂等。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教”汇聚一处,呈现出宗教文化兴盛繁荣的独特图景。
淮安道教文化源远流长。传说在今洪泽湖南岸淮河入湖处的老子山,春秋时道祖老子曾在此修道炼丹。炉火烘烤而使山石褐红,故名“丹山”,坐骑青牛踩踏而留下圆坑蹄印“青牛印”。其地负山临湖,有湖山之美,现存仙人洞、凤凰墩和炼丹台。今清江浦钵池山,昔日岗阜盘旋,外高中凹,周环以水,形如钵盂。唐代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将钵池山列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相传“周灵王”太子王子乔曾于此炼丹、得道升仙。市域内最古老的道观有淮安区晋初所建的紫霄宫、大清观,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东岳庙,则是市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活动场所。清江浦建于明代的都天庙,每年农历四月初十的庙会热闹非凡,远近闻名。始建于明正德三年(1508)的清口惠济祠(今淮阴区马头镇北1公里处)因与治黄淮保漕运关系密切而备受明清两代朝廷的重视,现清口惠济祠遗址、天妃坝遗址、御制重修惠济祠碑等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佛教约在东汉年间传入淮安。建于西晋永嘉年间的正法华院为淮安龙兴寺之始,寺内文通塔建于东晋大兴二年(319)。此塔原名敦煌塔,因“晋时有敦煌和尚在寺释法华经,即以名此塔”。明清时期,淮安佛教呈现繁荣景象,寺庙庵堂随处可见,有“九庵十八庙”“三步两庙”之说。从河下古镇到清江浦有“八大寺”“小八寺”,尽显淮安庙宇云集之盛况。清江浦有名冠江淮的“六大寺”,其中慈云寺因顺治皇帝国师玉林通琇在此趺坐圆寂而名满江淮。淮安区历史上寺庙之多堪称苏北之首,当地谚语道:“鼓楼在正当中,三界寺在更楼东,青龙桥挨着文昌宫,东岳庙靠着紫霄宫。”
伊斯兰教在淮安的传播。自唐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穆斯林商人沿着大运河、盐河往来楚州、泗州、淮阴、涟水等地定居经商。元代至顺年间,初有马姓、沙姓等穆斯林从甘肃灵州辗转山东、镇江来到淮阴古淮河北岸大清口、王家坡(今王营镇)落户。明代清江浦开埠后,走南闯北的樊氏、杨氏等穆斯林与先居回民相聚相处、传道讲经,有的经营骡马厂站。《王家营志》记载:“其自清真寺南趋,抵黄河(黄河故道)大堤,皆轿车厂,凡百余家……又有骡厂七八家,则专给骑乘,计程取直。”[1]还有的从事餐饮、皮货生意和宰牛杀羊。清真寺也随之而建。在大闸口清真寺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石碑记载“袁浦礼拜寺建自前明”。内有清真寺禁谕碑、重修清真寺大殿碑记、明成祖御制《百字赞》等珍贵文物。建于清雍正年间的王家营清真寺珍藏阿拉伯手抄本《古兰经》一部共30卷,分上、中、下三册,为明朝末年传承之物。明清以来,淮安回族聚居地主要沿里运河自东南而西北分布在河下古镇、清江浦、王家营、马头镇等地。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淮安。同治年间,天主教在淮城镇小羔皮巷北建立教堂,并附设一所达义小学。1869年7月,英国传教士童根福首先来到清江浦设立教会,随后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也来到清江浦传教。[2]对淮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188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赛兆祥(美国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之父)来到清江浦定居传教。随后,陆续有美国传教士林亨利、家雅各、林嘉善、林嘉美等传教士、医生先后来淮。他们在赛兆祥牧师领导下在清江浦、淮安区传教。1888年,在慈云寺开设第一个西医门诊,并命名为“仁慈医院”,开创了淮安市西医的历史治病的先河。1906年,淮安发生大瘟疫,在本地绅士的帮助下,仁慈医院在铁心坝(即铁水牛)设隔离医院,制止了瘟疫蔓延。此后,仁慈医院得到了中国居民的认同,业务逐渐发展起来。据记载,1929年苏北农村流行黑热病,仁慈医院经研究发现黑热病是由寄生虫白蛉虫传播的。仁慈医院医治的患者从1932年的3 283人上升到1940年的4 717人,病床增至380张[3]。此事在当地及周边百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教会还开办了袁江小学、妇女学道院及基隆小学、敬业(袁江)中学。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以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为主要手段推动了基督教在苏北的传播,同时在客观上推动了苏北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开阔了当地人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和卫生习惯。
二、大运河宗教遗存体现了淮安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
淮安儒、释、道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学互促,以及对中国未曾断绝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包容和吸纳,是历史上不同信仰间可以对话、共处、互融的极好例证,也是中华文化具有极大包容性的证明。淮安大运河两岸的宗教遗存大多因时间久远、岁月变迁而自然消失了,但其相关的信仰文化、祭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在淮安民间仍有不少保存和传承,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突出地呈现着淮安文化传统开放与包容的典型特征,较好地体现和印证了淮安“包容天下,崛起江淮”的城市精神。
以兼容并蓄的胸怀,追求内涵的丰富与完美。淮安民间的水神崇拜体现了兼容并包、不断演进的特点。大运河中的“水神信仰”文化种类众多且分布广泛,大运河上逐水而行的商家船民和沿岸枕水而居的居民,除了信仰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水神外,还特别信奉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泰山奶奶、齐太太)。随着海上漕运向运河漕运的转变,原来流行于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妈祖娘娘(又称“天妃”“天后”)也从海运之神转变为运河之神而在淮安大运河沿岸落地生根,以满足人们祈求淮水安澜、水运平安、生意兴隆的愿望。惠济祠地处古清口,历史上这里处于黄、淮、运、湖交汇之地,这段河道上建有惠济、通济、福兴三闸,由于清口地势高,水位亦高,漕船过闸完全靠人力拉纤,三闸水位落差一丈有余,水流湍急,断缆沉舟的事时有发生。人们为保平安,过闸前皆舍舟上岸到惠济祠烧香祷告。清初惠济祠由原来只供奉碧霞元君,而改为后殿仍供奉碧霞元君,前殿供奉妈祖娘娘,共保一方平安。清代河务、漕运皆系于清口,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必到清口巡视河工,多次临幸祠下虔诚奉祀。其后的雍正、乾隆、嘉庆皇帝也都崇奉惠济祠神主。
“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等古语名言阐述了一个浅显但深刻的道理——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它也成为各大宗教修行的重要内容,作为特定的饮食文化对地方百姓的饮食习性产生深刻的影响。宗教普遍讲究适量饮食、节制饮食的节食观念,佛教、道教素食养生的习性,戒食、“辟谷”的修炼功法,道教药食同源、讲究食补的传统,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基督教通过禁食祷告来忏悔罪业的宗教习性,佛教平均分配、公开进食、“不别众食”的戒律等饮食方面的理念、风习,对淮安本土饮食文化、百姓生活理念、饮食行为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节俭爱物、取之有度、敬畏天地、吃斋念佛、注重养生等理念成为淮安人的一种风尚。
抱从容自信的心态,不断吸纳互补借鉴。特定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当与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生产等条件下形成的异质文化相遇时,当地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就会产生出“内固”“外阻”等自我保护机制,两种文化由砰然撞击而渐进磨合,由悄然吸纳而变通融汇。清江浦仁慈医院西医门诊开设初期,由于当地人对西医不了解,加上语言不通阻碍正常交流,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就诊者门可罗雀。林嘉善、林嘉美兄弟主动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学习当地方言,留辫子、着中式便服,主动上门免费送医送药。接受治疗的患者不断痊愈,西医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1906年,清河县周边发生大水灾,60多万灾民困滞清江浦,瘟疫流行,基督教会配合当地乡绅筹措资金和物资,积极赈济灾民,仁慈医院积极施治,控制了疫情。这样,仁慈医院的西医疗法逐渐得到认可,业务逐渐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外来异质文化欲被接受和吸收,必须适应当地民情和习惯,融入百姓生活。一旦被认识,成为社会共识,当地民众就会主动接受和吸收而为我所用。回顾当初西医传入淮安的历史过程,虽有排斥的一面,从中仍可以看到淮安地方文化从容自信、来者不拒、为我所用的特质,最终达成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
从清真饮食文化融入淮安社会也可以看到淮安文化传统这一特质。俗话说:“回族人两把刀,一把宰牛,一把切糕。”意思是回族人善于经营餐饮行业。清真饮食文化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而融入淮安人日常生活,在选料和烹饪技法上与汉族淮扬菜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提高,对清代淮扬菜系的形成、南方清真菜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淮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稗类钞·饮食类》录有天下五大名筵,淮安独具其二:一为全鳝席,以鳝鱼为主,配以“牛羊豕鸡鸭”,“号称有一百有八品”;一为全羊席,“以羊之全体为之,多至七八十品,品各异味”。其他三种分别为满汉全席、燕翅席和豚蹄席。其中全羊席就是清道光年间清江浦回民饭店大厨的杰作。清真全羊席在继承伊斯兰教传统烹饪技艺的基础上,借鉴融合了鹿尾、熊掌、驼峰以及豹胎的炮制方法,整只羊从喉舌耳眼脑、头尾蹄内脏分别作主料,无不著手成味,迎合食客喜好,不断推出新菜品。当时,里运河两岸回民饭店的清真全羊席与文楼汤包、新半斋的“大烧马鞍桥”并列为淮扬菜系三大名菜肴之一。淮安清真菜特色是长于牛羊肉的炮制兼治家禽熏烧和腌制,制作比北方精工,口味比北方清淡,其高超的烹饪技艺常为当地淮扬菜厨师吸收演化。收入《淮扬谱》里的扒烧牛筋、红烧牛皮等深受当时文人墨客、盐商官宦等喜爱。而“马头汤羊肉”则是吸收了淮扬菜的烹饪制作手法而形成的一道风味独特的“招牌菜”。
在民间,清真饮食文化中不食体形丑陋、性情凶暴的动物,不食自死的动物、不食有病的动物、不食不反刍的动物、戒酒等禁忌,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的饮食习惯,对当地百姓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胡萝卜、菠菜、石榴、无花果、芝麻、胡椒、香菜、荞麦等穆斯林常用食材早已成为汉族百姓生活必需,清真菜肴食品对当地百姓的口味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秉持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维护不同宗教和谐共处。淮安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对宗教持宽容开放的态度,老百姓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论的存在,既支持本地宗教发展、也允许外来宗教的传播,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的存在。这就促使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能在淮安扎根并得到发展。佛道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轮回转世、摆脱苦难、善恶相报的思想与传统民间鬼神信仰、日常禁忌等相结合,与民间祭祀、门神、庙会等民俗文化相融合,已经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元素,满足着百姓各种美好的愿望,表达了对平安幸福生活的祈盼,丰富和规范着百姓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
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其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习俗也处处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在饮食方面,回民饭馆在遵守清真饮食禁忌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淮扬菜烹饪技法,形成了独特的清真餐饮文化和特色菜肴、面食点心。在衣着方面趋于大众化、平常化,除宗教节日男人戴白(黑)帽、女人戴头巾外,大部分人平常着装与当地百姓已没有明显区别。婚嫁方面,伊斯兰教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双方自愿结合,讲求信仰相同,但必须求得双方父母同意认可等,这与汉族青年男女婚姻有许多相同之处。丧葬方面,除了伊斯兰教丧葬文化的个性化要求外,要举行“头七”“二七”“百日”等祭祀仪式,这些都深受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而且有典型的地域特色。
基督教在淮安的传播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文化讲究“百善孝为先”,基督教宣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基督教教义中则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中国文化提倡“仁爱”,基督教提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等等。这些向善的教义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有共通之处,这使得基督教逐渐被百姓接受而得以传播[4]。
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交流、吸纳、借鉴是双向的动态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综观淮安的宗教传播史,不同宗教始终多元发展、和谐相处。有关淮安的历史文献中,还未发现地域范围内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即使在19世纪末基督教强势进入中国,与中国原有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过短暂的激烈冲突,全国各地时常发生“教案”的时候,淮安不同宗教之间、信徒与民众之间也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三、加大对淮安大运河宗教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文化对淮安文化传统形成、发展、创新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5]中国大运河成就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地位,造就了淮安融南汇北、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和取法自然、“水韵天成”的营城智慧,为各种宗教文化的传播、碰撞和融合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水文化与宗教文化呼应融合,大运河、城市、宗教三者生演相系,造就了具有大运河特征的城市风貌,赋予了淮安这座古城迷人的魅力。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的加快,我们应当加强对大运河淮安段宗教文化遗存和传统的研究、利用和开发,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大运河区域标识和文化特色,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寻找宗教建筑与运河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管控城市风貌的原则、方法和要素,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标志性城市,讲好中国大运河“淮安故事”。
以敬畏历史之心,推进历史文化保护和古城风貌品质新提升。明代吕坤《呻吟语》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要本着对淮安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系统梳理、准确凝练、深入分析淮安历史文化名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淮安古城(含河下古镇)、清江浦至清口枢纽一线城镇整体以里运河为主轴,傍漕盐两运、治河保运而带来市井繁华、经济繁荣,特殊的人文环境导致这一线成为宗教建筑荟萃之地,所谓“城镇所在必有大型庙观,码头要津无不名刹云集”,构成了区域宗教传播及宗教建筑分布的独特景观,诠释了运河、城市、宗教建筑三者共生、相互塑造的关系,彰显了淮安城市的独特个性。要全面保护古城的风貌,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因素,重视宗教建筑在塑造城市风貌和个性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城市历史文脉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肌理,从而以悠久的历史文脉作笔、运河风情风光为墨,描绘出一幅新时代的淮安“清明上河图”。
延续各类宗教建筑特色,营造亲切宜人的空间尺度和人文环境。保护文化景观遗产是保护传统的人地关系,一个重要原则是使这种景观和居民的相互关系能够维持发展下去。历史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形态的物质层面,其承载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也是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沿里运河两岸的都天庙历史地段、大闸口历史地段、清江浦风情街区等里运河文化长廊各项保护更新工程,要高度重视历史地段历史价值的再现,要高度重视以“五教融合”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丰济仓等为代表的漕运文化,以江淮民居、民间建筑、宗教建筑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大闸口商贸街为代表的商贾文化,根据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划分“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风貌保护区”“建设开发区”等类型,循序渐进地保护与利用,以主题鲜明、独具特色、多元聚合的系列文化成果,为古清江浦的保护和利用奠定“文化之魂”。马头古镇惠济祠、天妃坝等道教遗存,是明清时期运河沿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妈祖道场,备受清朝康雍乾嘉四朝皇帝推崇,形成了完整庞大的宫庙建筑、碑刻等遗存。随着当今淮安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地位的提升,重建惠济祠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吸收借鉴宗教建筑元素,为古城保护更新增添魅力和韵味。淮安宗教建筑和民间传统建筑在整体格局和细节装饰上相互影响和融合。以清江浦清真寺、王家营清真寺为代表,在建筑的整体布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建筑表征。这两个清真寺为中国传统的殿宇式砖木混合结构,具有浓厚生活情调的庭院风格,采用阿拉伯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融合的装饰手法,借用匾额、楹联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表现伊斯兰教文化的内容。淮安民居建筑深受徽派建筑的影响,形成具有淮安特点的青砖灰瓦、清水砖墙的风貌,在建筑装饰上也常见宗教建筑元素,如很多民居院墙上筑立供龛,“万字”“寿字”“莲花”“如意”等纹样在民居装饰中很常见。深入挖掘这些大运河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建筑文化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挖掘、借鉴,以实现显山水、亮文化、增活力的目标追求,更好地保护与更新城市风貌。
弘扬开放包容文化,重视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行动指南》中指出,中国大运河遗存“代表了人类的迁徙活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由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交流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形态,在当代仍然散发着独特的光彩和魅力,是传承文化、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当今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一些宗教习俗和文化艺术种类面临消亡的危险,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部分绝活绝技的传承后继乏人。要结合淮安文化中的包容特点,重视对淮扬菜文化和清真菜肴食品内涵与传承的挖掘和研发,不断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特别要注重抢救和保护那些陷入困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通过普查摸底,全面掌握大运河淮安段民族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建立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筛选确定代表性传承人,制定相关保护措施,同时要培养一支包括有宗教界人士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队伍,促进淮安大运河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繁荣发展。
提高保护意识,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强化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更新的合力。当前部分基层人员保护意识淡漠,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文物保护工作的具体要求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导致一些城市、镇村悠久的传统风貌遭到破坏,失去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淮安市的牛行街、都天庙、林默予故居、赛珍珠故居、左宝贵楼、普应寺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宗教建筑、百年老店等因城市改造、道路扩建而被毁拆。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宣传推广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包括宗教建筑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提高社会公众、青少年特别是基层各级干部的历史文化素养,加强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保护,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落实保护措施和责任。同时要充分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更新,形成政府、专家、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