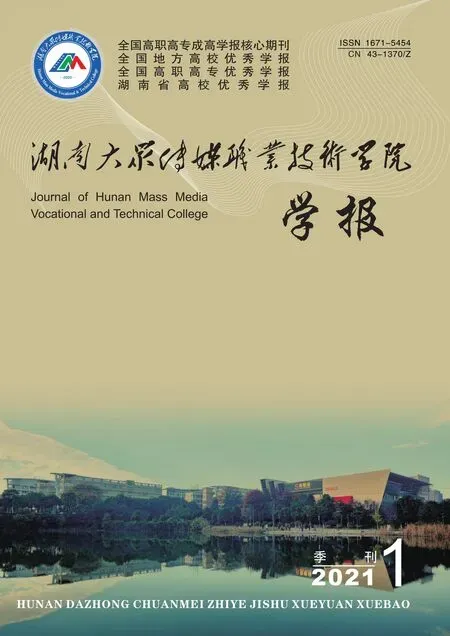试析民俗资源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应用
2021-01-16谢秀琼
谢秀琼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浙江 宁波 315100)
国产动画电影与民俗资源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过去将民俗范围局限于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信仰的框定较为狭隘,故转而扩大为生活文化。“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虽然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是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民俗随着时代、地域而不断演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它不仅呈现了民间审美范式,也以意象原型的形式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是在传统民俗资源的滋养下,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为国产动画电影内容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民间技艺、绘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形式创新,营造出奇幻瑰丽、独树一帜的中国气派。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探索民俗资源在动画电影中应用的新思路,形成蕴含中国文化特质的动画电影,显得尤为必要。
一、故事新编,注重对民间文学的重述、改写与再创造
在民俗资源中,民间文学的动画电影改编大体有3种形式。一是忠实于原著的重述。199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改编自民间传说《劈山救母》,其故事结构大致为:二郎神夺取宝莲灯,三圣母被压华山——沉香得知身世真相,历尽磨难铸成神斧——灯人合一打败二郎神,劈山救出母亲。《宝莲灯》既保留了民间传说《劈山救母》立志救母的情感力量,又加入了沉香历尽艰险的自我成长主题,冒险救母与个人成长两条线索交织并进,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推动着故事发展走向。《铁扇公主》《大闹天宫》《金猴降妖》等动画电影则是截取原著中的经典片段加以改编。
二是对原著进行现代性改写,使之更具时代感。“好的叙事在高潮迭起的故事中置入一个能触及每个人的个人经验的概念,借此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进而达到营销目标。”[2]取材于《封神演义》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成功塑造了勇敢机警、爱憎分明的少年哪吒形象,他因闹海怒杀敖丙而得罪东海龙王,为了不连累父母和无辜百姓而选择剔骨剜肉而亡。20年后,《哪吒闹海》中那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悲剧英雄似乎难再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于是201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将当下普遍存在的自我认同焦虑嵌入哪吒屡遭世人排斥与不认命的矛盾冲突中,观众得以跟随哪吒成长的心路历程,完成相似个人经验的激活与虚拟体验。再如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另辟蹊径,述说白娘子与许仙的前世故事,当电影结束在断桥相会时,耳熟能详的《白蛇传》故事被重新唤起。
三是选取一个母题进行再创造,抛开原著框架束缚。母题可以是一个主题、人物、情节或意象,因具有某种不寻常的特性而反复出现。例如,不畏强权、奋力抗争的孙悟空形象在民间早已深入人心,《铁扇公主》《大闹天空》《金猴降妖》《西游记》《宝莲灯》等多部动画电影中都出现其身影。而在2015年上映的《大圣归来》中,孙悟空呈现出桀骜不驯却法力不再、匡扶正义却带有一丝邪气的浪子形象。另外,以年俗为母题创作的动画电影《年兽大作战》,叙事完全脱离了人们熟知的年俗传说,但年俗文化的精神底色得以保留并强化。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将传说、故事等民俗资源原封不动地改编为动画剧本,容易获得较为广泛、稳定的观众市场。而基于母题的动画电影再创作,如果流于形式上的文化符号叠加,忽视精神内核的深入挖掘,必将失去观众。如《大鱼海棠》,一开始以浓郁的民族风格构建了混沌初开的宏大叙事背景,但随后故事却走向三角恋叙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最初的创世哲学铺设。所以,无论是对原著进行重述,还是融入时代精神的改写或母题再创造,关键在于发挥动画突破真人电影和物理世界局限的优势,在与传统民俗资源的对话中,注入坚实的故事内核,让观众跟随虚拟人物一起冒险、共同成长,从而摆脱国产动画长期存在的低龄化、同质化问题,最大限度地激活民俗资源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性和价值认同。
二、以形传神,注重对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
民间工艺、绘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在审美意蕴表现、美学观念上追求得“意”而忘“形”,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象性,适合动画电影的空间想象呈现。事实上,早期的国产动画电影利用传统戏曲、音乐、绘画、民间剪纸、皮影戏等的二度转译,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与实践。
一是在场景设计上讲究神韵。早期国产动画电影利用水墨画等传统绘画形式,以层次丰富的墨韵创作出虚实相间、美轮美奂的奇幻意境,观众观其“形”便可得其“意”。在这方面,全片以水墨画呈现的有《小蝌蚪找妈妈》,作为一种意境、风格、风骨运用的有《大闹天宫》《天书奇谭》《崂山道士》等动画电影。二是造型艺术上讲究革新。利用民间工艺简单中有变化、统一中求差异的艺术特色,产生了一批经典动画电影,如剪纸动画《渔童》、皮影动画《猪八戒吃西瓜》、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折纸动画《聪明的鸭子》、木雕动画《神笔》等。三是在人物设计上讲究以形传神。如《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双眸乌黑、两道剑眉,透露着那股割骨剔肉的狠劲。《大闹天宫》中长着桃心脸、腰束虎皮裙的孙悟空形象堪称经典,以至于后来的动画电影《人参果》《金猴降妖》《宝莲灯》等直接沿用这个形象。在《大闹天宫》中,人物的举手投足及武打的一招一式采用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语言。行云流水的打斗场面在锣鼓点的配合下,形成强烈、明快的视听效果,尤其是孙悟空与二郎神的变形斗法,两人多次幻化成珍禽猛兽等形象,闪转腾挪又扣人心弦。
动画电影中民俗资源的应用,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传递出所要表达的风格、境界及精神内涵。“何谓‘民族特色’?民族特色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符号,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积淀,是一个民族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境界、一种风骨、一种处世哲理和一种自信态度。”[3]动画电影《小门神》利用皮影戏“年的故事”作为叙事开端,既是对传统的致敬,又将故事引向纵深。历史上,门神的造型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据《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曲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4]相传,神荼、郁垒每日在树荫如盖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发现有危害人间的恶鬼便将其投喂老虎。后来,人们立桃符于门,画神荼、郁垒之形以驱灾纳祥。《小门神》参考古代有关门神的想象叙述,结合剧情需要,塑造了全新的神荼、郁垒形象。神荼矮胖,为人敦厚,手持烧火棍能驱邪避鬼;郁垒修长消瘦,心气甚高,为证明门神的存在价值而不惜放出年兽。可以说,两位门神的形象设计与他们各自的性格发展、行为动机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此外,该片在场景营造上,如江南水乡的静谧、四季不动声色的切换,以及一点水滴的晶莹、一片花瓣的悠然飘落,都尽显东方美学神韵,也较好地呼应了守护传统这一电影主题。
三、与时俱进,注重为民俗文化内涵注入时代性
民俗作为“一种经久传承的民间文化”,[5]成为早期国产动画电影的核心价值输出。这其中,既有《哪吒闹海》《金猴降妖》《神笔马良》中对勇敢正直、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等精神的歌颂,也不乏《崂山道士》《九色鹿》《骄傲的将军》中对虚荣贪婪、忘恩负义、骄傲放纵等人性弱点的揭露。《金色的海螺》《梁山伯与祝英台》《宝莲灯》表达了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憧憬,《雪孩子》讲述了关于亲情、友情的感人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可视作个人在不断受挫与迷茫中寻找亲情的成长之旅。
在近年来的国产动画电影中,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佼佼者,皆在坚守传统文化根源的同时融入了时代精神。《大圣归来》从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讲起,小男孩江流儿无意中帮助孙悟空逃出五行山,从此两人一起踏上冒险之旅。最终让孙悟空解除封印的不是佛祖的咒语,而是江流儿的善良激活了潜藏于孙悟空内心的正义。《年兽大作战》反复提及的“什么是幸福”“开心是否等同于幸福”等哲学命题,可溯源至中国人在传统年俗中寄予的除旧迎新、团圆和睦、兴旺发达等价值观念。该片通过毁钥匙、找钥匙、还钥匙这一典型结构展开叙事,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幸福”语义指向了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意义,女孩沙果体悟到亲人团聚的可贵,年兽收获了友情带来的欢乐,而观众在年俗中追求团圆、幸福的文化心理也被唤醒。相比之下,加入大量中国元素的《大鱼海棠》,从故事创意到建筑、服饰等细节都极具民族审美特质,但美轮美奂的画面不足以弥补其故事叙事的明显弱点。如主人公椿为救鲲而不顾洪水泛滥殃及族人,这样的价值取向是有待商榷的。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小门神》的故事讲述中,心气甚高的郁垒为证明门神的价值而不惜放出年兽,其行为本身就违背了贴门神以祈福纳祥、驱灾避害的民俗文化内涵。
要维持国产动画电影的魅力,归根结底,需要以时代精神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根植于生活文化的民俗资源,以民间文学的重述、改写与再创造,为动画电影注入坚实的故事内核;利用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特色,丰富动画电影的形式创新;与时俱进,注重为民俗文化内涵注入时代性,通过动画人物的形象刻画发掘人性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