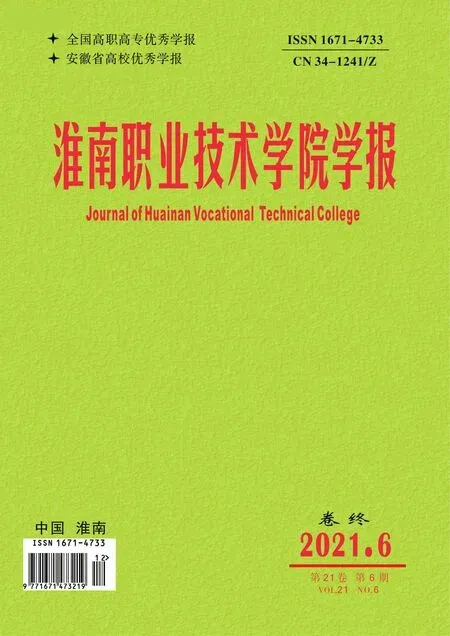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2021-01-15徐健
徐 健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大连116026)
《史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学著作,历代的研究者从历史学和文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创作这部史学著作的作者司马迁,有着非常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在国家治理等方面也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研究者要进一步研究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需要对《史记》这部著作中涉及到司马迁个人观点的部分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司马迁个人人生轨迹,进一步体会和理解司马迁在国家治理方面所提出来的科学观点。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样表达自己著作《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表明了司马迁透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对于历朝历代的君主以及王侯将相等进行评论,这些观点也是在司马迁之前很少有史学家能做到的。如《春秋》这一类的史学著作,大多数是“春秋刀笔”,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观点,在后人的理解中则不易进行体会,因此衍生出大量的注释作品[1]。这也与史官本身的身份地位有关系,不能直接抨击时弊,以更加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治国理政思想的评判。司马迁则不同,其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大多以比较辛辣且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因此鲁迅才评价司马迁的著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是对司马迁的史学作品和思想的较高评价。
一、司马迁国家治理思想中的名实思想
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思想也就是名实思想。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论语》中也有多次记载了孔子对于名实的思考。比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以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这两个对话场景中,孔子表达了自己对君臣父子、纲常秩序的观念,而且孔子也在应对子路的问答中表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等相关的名实思想。在此孔子提出了证明的观念,即是以名正实,以名分、位分等来确定每一个阶层人的实际行为,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作出符合社会礼俗规定的行为。就是《论语》中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基础。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继承和发扬,并且运用这种思想表达自己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比如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这一篇,表达了《春秋》这类儒家的史书中“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主要倡导的就是孔子的这种名实思想在儒家诗书中的体现。司马迁认同这种名正言顺的行为,因为只有每个社会阶层都按照国家所界定的各种礼俗行事,才能够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当然这也是一种有一定保守成分的思想[2]。
司马迁在《史记》这部著作中,对人物或事件进行描述,往往涵盖了之前各个朝代不同人物与不同地位的情况,司马迁充分吸收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却有别于孔子。孔子更多强调的是“以名正实”,司马迁强调的是“以实正名”,在司马迁的笔下更多是侧重于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所作出的社会影响以及实际的功绩,即便是出身卑微的人物却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会按照其所创造出来的历史影响力排序,并为这些人物谱写相关的文章。比如在司马迁的“本纪”中,即便是没有拥有帝王名号的历史人物,也被司马迁列入这一范围内,同样甚至是一些具有帝王名号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纳入到这类篇章中。比如项羽或者吕太后,这类人物虽然并没有真正统一天下或者成帝,但是却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创造了巨大的功绩,在秦汉时期的历史格局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因此司马迁也把他们纳入到“十二本纪”,反而像汉惠帝等没有为国家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因而也没有纳入到这一范畴中。
司马迁把项羽纳入到本纪,受到一些后代学者的批评,比如历史学家刘知几就评论“项羽僭位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在这类历史学家的观点内,项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配列入到本纪的范畴。项羽虽然只是称霸,没有帝王的名号,但是司马迁却尊重历史的实际地位为其确定名分纳入到本纪中,其实也更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之中,像项羽这种接过项梁的反秦大业,在巨鹿之战中大败秦军,随后又入关咸阳成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路诸侯等,都对秦汉时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又对于汉朝的建立形成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甚至在司马迁的著作思想中,项羽的楚国是继秦国之后的一个重要政权。又如吕太后与汉惠帝,虽然汉惠帝所在任的时代,天下十分稳定,维持了汉高祖刘邦所打下的国家基业,但是在当时实际对国家的运行和实现影响的则是吕太后,而并非汉惠帝。因此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影响又进行了评判,更多重视吕太后的执政与影响,而对于汉惠帝则仅仅是列入记载。
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更多是强调了对于名实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只有以国家的发展为基础,把实现国家的推动与变化作为己任,才能够成为对国家和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因此即便拥有相当重要的权位乃至于称帝于天下,但是未对国家和黎民苍生做出重大影响,没有举全国之力实现国家的进步,那么这样的人物也无法真正被历史所肯定。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名实思想虽然脱胎于儒家以及孔子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对这种思想的再创造,对于后世治国理政者的思想也形成了很大影响[3]。
二、司马迁国家治理思想中的选贤用能思想
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选贤用能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变化与国家动荡中人才的重要性十分突出,要实现国家治理或者富国强兵,必须要选用能人或贤才。司马迁对于历史的风云变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选贤用人的思想也渗透在自己所创作的《史记》中,认为选贤用人将影响到国家和政权的兴亡,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比如在“楚元王世家”中,司马迁就表达“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这一类的思想,其表达的就是楚国的兴衰成败,乃至于其他政权的兴衰成败,都与选贤用能密切相关。具有贤能的人能够辅佐国家的兴亡,司马迁也举出了非常多的例子,比如,楚国的国王戊如果能够对申公的观点进行采纳,也不至于有被篡位谋刺的风险。
对于没有选贤举能的政权,司马迁也深表痛惜,认为功业无法建立或者国家的正统无法形成,其关键也与贤能之人密切相关,只有选举优秀的人到国家重要位置上,才能够对国家的兴旺起到促进作用。比如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表达“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认为负责军事力量的将以及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相,各自对于国家的兴旺和正统的兴盛有着积极的影响,只有选举具有能力的人担任政权的将相,才能够为政权的延续与发展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力量[4]。此外,司马迁认为作为政权中的大臣,也应该积极为国家举荐贤人之人,这样才能够有人才辈出的状况,从而为国家的兴旺发展奠定基础。国家的领导者或君主未必能洞察一切,包括对于人才的选用也未必能够事必躬亲,这时候作为国家的臣子就应该为君主分忧,为君主举荐具有能力的人担任重要职位,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比如“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为了以免引来杀身之祸而不向汉武帝举荐具有才能的人这类行为予了一定的批判。卫青与霍去病担心自己举荐的人无法满足君主的要求,害怕受到所举荐人的牵连,引来各种灾祸,因而在君主面前从来并不言及于举贤用能。奉法遵职是作为人臣必须做到的,但是也应该为君主分忧,举荐贤能的人,通过引入更多优秀人才参与到政权的治理中,这样才能够推动国家治理的发展。
在这种机制里,司马迁认为虽然举用贤能有才的人,可以通过大臣的推荐,但也需要君主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也就是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识人之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圣君治国累世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部分的观点就是司马迁对用人体系与国家治理关系的分析。在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即便有贤能的大臣,但是如果君主不够贤明,无法举贤用能,则不可能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即便在过去的时代中以往的君主创立下不朽的功绩,但是往往因为继任的君主缺乏能力,特别是没有知人之明,就不能延续这种国家兴盛大的局面,最终可能引发政权的灭亡。
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了楚怀王的例子。楚怀王由于无法明辨忠奸,从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出现割地求和等现象,最终楚怀王客死他乡。楚怀王的问题是咎由自取的,但是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是领袖缺乏对人的识别能力,以为是忠良的大臣本质上并不忠良,以为是贤能的人却没有办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里,司马迁认为贤能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运用,关键在于国王也就是领袖是否贤明。国家的发展并不有赖于单一方面的发展,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包含了朴素的系统思维,认为领袖与大臣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君主作为领袖缺乏一定的能力,尤其是无法选拔具有能力的人才,那么国家也无法通过一些忠臣的支撑而实现发展。
三、司马迁国家治理思想中的吏治思想
在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吏治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司马迁认为在国家的官僚体系里管理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无法对国家的官吏实行良好的吏治,那么国家也无法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这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3]。这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史记》“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里。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先是引用了孔子的观点来表明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差异,也就是“道之以政”和“道之以德”之间的差别,管理民众的方式有两种与别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道德礼教去约束和引导人民,另外一种则是采取比较严苛的政治手段管理人民。但是司马迁认为“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这个观点与孔子应当有一定的差别。孔子认为以道德礼教束缚人民,能够起到良好的国家治理效果,而在司马迁和其著作《史记》中的观点认为,只有采取一定的法令,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治理提供支持。当然治理国家未必都需要使用酷吏,也未必都要用比较威严的酷刑去压迫管理百姓,但是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必须要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才能够避免国家出现混乱。孔子所在的时代虽然是一逐渐出现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仍然保留着一些西周建立以来的礼教制度。在战国后期特别是秦汉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对礼教的认同并不是十分强烈,社会与阶层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因此在国家治理的方式上与孔子所在的时代也应当有所不同,这也就是司马迁重视法令刑政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在汉代建国的初期,之所以能够维持良好的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吏治。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有赖于国家采取各种行政手段进行良好的控制。但是在汉景帝的后期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情况,大不如汉朝初期,在《史记》中也记述了当时社会秩序出现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是由于国家富裕之后,奢侈豪强之徒逐渐影响了社会的秩序,从而对国家的治理体系造成挑战。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如果采取因循守旧的手段进行管理,则不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当时必须使用严酷的官吏解决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在司马迁的这些表述中,循吏与酷吏都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手段,并没有孰是孰非,只有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国家运行的情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推动国家治理的发展。因此,司马迁的吏治思想,更多是对于具体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分析,而并不是对官僚行为的一概否定或肯定,这也是司马迁对于国家治理提出的更加系统和全面思想的表现。
四、结语
在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包括对官僚行为以及君主领袖的评价,无疑蕴藏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司马迁认为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君主是否具有一定的识人之明,是否能够选用具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司马迁在分析国家的具体社会动态时,主张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情况,选用更加合适的官僚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司马迁在《史记》中,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进行历史的追溯,其主要还是探究了历史上不同政权的国家治理情况,倡导运用王道等思想对国家进行治理。这些宝贵的国家治理思想,不仅仅为汉朝的国家政权治理提供了一些参考,更是为后代国家治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