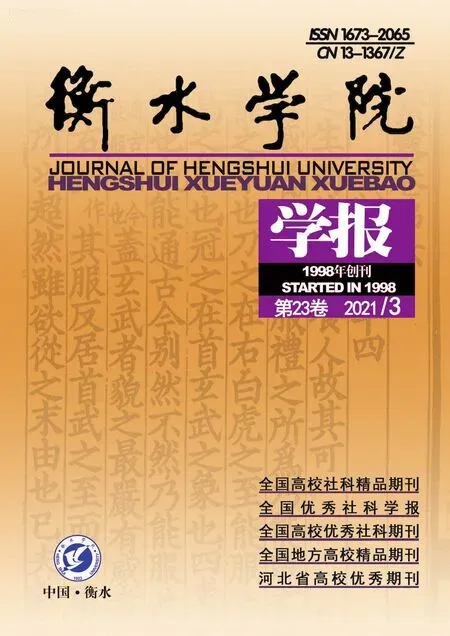《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2021-01-15余治平
以礼义概括《春秋》之主旨,始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谢遐龄教授近年来把学术视野投向董学,创获颇多,精彩纷呈。他从礼学进路阐释董仲舒,新见迭出,别有一番洞天而引人入胜。在他看来,孔子身当乱世,“王路废而邪道兴”,所以才发心拨乱反正。董仲舒则身当太平盛世,天下统一,吏治蒸蒸。从高祖到武帝初期,在整个国家机器任职的主流人才都崇尚武力与刑罚,流行的是黄老之术那种让弱者任强者欺凌、自生自灭的治国思路。这种思路在远古小国或许适用,汉初战乱之后与民休息也还可用,但在社会财富积累之后,权贵渐兴,王室富豪骄横肆虐,在天下一统的郡县制国家则难免导致社会秩序和江山稳固被破坏的灾难性后果。董子要求“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可谓切中时弊,所张大的恰恰是儒家天道为仁的理念,这便“为儒家在中华民族取得永恒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一句应该被看作礼学的基本构架。古人心目中的天人关系,既是思想观念,也是现实结构,因而神人一体、宗教与政治一体。天人、君民在一个结构中,切勿以当代思想解读为分开的两个结构合并成一个,也不能解读为君主的权谋、利用宗教统治民众。天、天子、民众是一个结构中的三环。“屈君而伸天”所教育的对象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及其接班人,目的是让他们敬畏上天,不要滥用权力而胡作非为。这是礼学的深刻用意。而古礼中最重要的则是祭礼,祭礼最重要的是祭祀天地,就是董学特有的“屈君”之术。郊社、禘尝之类的宗教活动是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常有论者曰“董子尊君”,其实仅对了一半,且是一小半,董子更尊天。“祭天、祭祖越隆重,天子越谦卑,不会出现个人迷信现象”。礼制既是政治制度,又是宗教制度,体现了宗教与政治之一体性。祭祀要追溯到最古的帝王,历代帝王须选择杰出的配祀,则是“奉天法古”之落实。由此想表明,“中国社会的国家宗教是从远古连贯下来的”,至少五千年;历代皇室都认为,既然君权天授,“作为受命的天子,自己就是这个国家宗教的教主继任者”,因而怎样祭天,祭祀时配多少先祖、前朝帝王,就成了重大实践问题。这些见解都非常新鲜、深邃而富有启发,值得董学界揣摩和消化。
清华大学丁四新教授长期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丰硕,声名远扬,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董学、支持董学。他挖掘了“三纲”的历史渊源,梳理了其流变脉络。从《论语·颜渊》篇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到郭店简《六德》“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和《成之闻之》篇的“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妻之别”,再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到《彖传·家人》卦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到《逸周书·常训解》的“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直至《韩诗外传·卷三》的“百王之法,若别白黑;应当世之变,若数三纲;行礼要节,若运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时;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圣人也”,“三纲”之名的形成是有过程的,显然出现在董仲舒之前,而不是董子的发明,其具体内容更不可能首先由董子提出。在汉初,“三纲”一名已成为一个公共话语词汇,故若“以董子为‘三纲’一词的发明人而开罪董子,进而谩骂董子,这是不讲事实、不求证据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董子以天道观或阴阳学说为理论武器,将“三纲”上升为天意在伦理世界的具体呈现和落实,而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重要命题。这是迄今把“三纲”观念形成史说得最清楚、最系统的一篇学术论文,为董子辩诬、开罪得力,贡献巨大,值得肯定。
义利关系在儒家一向是热门话题,常说常新。写过《中国正义论》大著的黄玉顺教授站在政治伦理、分工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独特维度而强调,董仲舒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已经把同属于一个权力主体群体的官吏、君王,与民众相对置。“义”是权力的本质特征,即“正其义”是权力主体的政治伦理义务;而“利”则是民众的本质特征,即“谋其利”是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利。“义不谋利”的要求并非针对民众,而只针对权力主体。对于君臣、官吏阶层,“义利之辨”可以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按照董仲舒所揭示的“分予”的“天理”,天子、贵族、官吏等权力主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就是“义不谋利”、不得“与民争利”。当权者为民谋利乃是权力的最高正义,而与民争利则是权力的最大不义。这种疾呼振聋发聩,既是对历史世界正义价值的积极阐发,又是对现实社会的诸多不公现象的有力针砭,值得引起董学界的高度重视。
宋大琦教授以研究儒家礼法学闻名。在他看来,汉儒以天人阴阳之庙栖孔孟仁义之魂。孔孟从人的本初存在的情感、情实入手,延伸及公共政治,最后都要落实回个人感性情实的最初出发点。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学天命政治学却以天命、天道为出发点,把情感、情实纳入天道,而完成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天人关系亦是伦理关系,天定人命,人仿天秩。这一套架构超越了孔孟。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先言天命、构建天道,再从天人同构之原理构建静态的政治制度,从天人感应之原理预言动态的政治行为。孔孟“由仁义行”,董学则先定仁义。仁义在孔孟是原概念、出发点、不证自成,而在董仲舒则被安排进天学知识框架中。这些区分精当准确而又简洁明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哲学理解能力和诠释能力,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但其言汉代经学“规模之宏大远超孔孟,然而其精微根本之处又不如孔孟”,则有待商榷。
在中国,“大一统”不仅是历史存在,还是中国人的信仰。刘丹忱教授指出,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实质上是天、地、人三才贯通之道,不仅涉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更关切文化统一、思想稳定。统一的思想文化必然要求制定国家法律制度,否则老百姓会无所适从。主张文化的“大一统”则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这是董仲舒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理念主张。西汉以后,“大一统”转述为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王权一统”,在此基础上则建立起疆域、民族、文字、服饰等各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庞大国家。富有见地,值得一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羊家的经权学说就颇受学者青睐,涌现出诸多高论佳作。周灏博士以扎实的春秋学知识和文本解读工夫探讨了《春秋繁露》中的权变哲学。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用元伦理学的观点予以分析权变的形成机制,并断定“权变的概念应属目的论而不是义务论”。然而,公羊家的权变需要语境,融入一切背景、理性、情感因素之后的行为选择,遵守经常而不违反礼法,仍在“可以然之域”,因而唯有圣人才可以行权,很难将权归入“目的论”“义务论”任何一个抽象概念。
董仲舒对孟、荀的继承和突破,始终为董学界所议论。在李慧子博士看来,董仲舒在天人思想、人心论、人性论和制度论上整合了孟荀思想,并且以此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完成了儒学体系建构,并为汉帝国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论文对于董仲舒统合孟荀思想工作的学术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孟荀思想的异同与意义,也可以纠正宋明理学重孟抑荀之偏,还能够为建构当代儒学提供学理根基与思想启迪,因而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