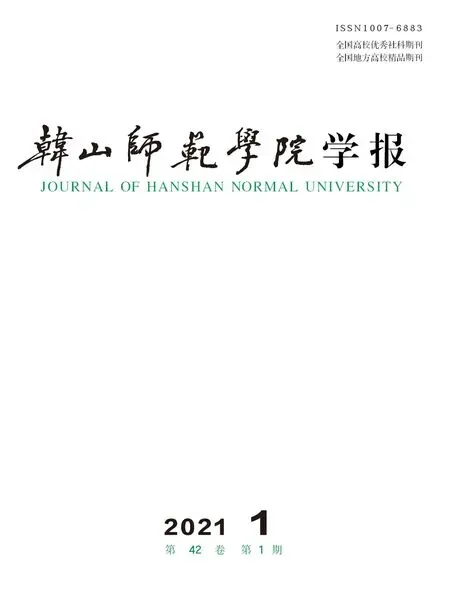乐钧的文学书写与游幕
2021-01-15李金松
李金松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乾嘉时期的游幕士人中,以江浙士人居多。在江浙之外,也有众多士人游幕。在这众多游幕士人中,来自江西临川的乐钧无疑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位。由于家贫,乐钧先后游幕京师、岭南与江淮,晚年寓居扬州。乐钧享年不长,而且后半生基本上是处于游幕的状态,因此,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游幕期间取得的。而对于乐钧,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其有所研究,但没有从游幕的角度。基于对乐钧研究的这一现状,本文主要讨论乐钧的文学书写与游幕之关系,希望藉此拓深对乾嘉时期文学的研究。
一、生平与著述
乐钧(1766-1816)①关于乐钧卒年,袁行云认为“当卒于嘉庆十九年,年不及五十”。见所撰《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1795页。江庆柏从其说,在其《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乐钧名后注“(1766-1814)”,并标明出自《清代诗集叙录》。详所撰《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笔者据乐钧好友陆继辂《崇百药斋文续集》卷二《黄垆续感》之六中“词客生天仍半醉,手攀明月上瑶京”句下小字注提到乐钧:“君嗜酒致疾,以丙子中秋夕殁于邗上。”而断乐钧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616)中秋。详所撰《乐钧卒年辨》,《书品》2014年第1辑。原名宫谱,后易名钧,字元淑,号莲(亦作廉)裳,行三,江西临川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清史列传》卷七十二、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有传。不过,这些文献对乐钧生平行实的叙述相当简略。现根据乐钧的诗文集,并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对乐钧的生平行实作比较具体的叙述,为知人论世提供史实上的依据。
乐钧好友彭兆荪在《青芝山馆集·序》中叙述乐钧行实云:
秀气孤禀,年甫弱冠,即以选拔贡生,举江西乡试,才名溢人口。嗣而之京师,游吴越,所至辄倾其胜流。家贫甚,奉母侨江淮间,江南诸大府虚左争延致,所居大都浩穰赫奕,日周旋于绮襦纨绔之中,而元淑狷狭孤洁,气岸严冷,矜慎片言,而凛取一介,视脂韦淟涊事,嫉之若仇。惟殚精毕虑于诗、古文词,务追古人不传之隐于高遐深夐、幽邃旷远之区,若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不瘁其力不止。
从彭兆荪所述,可得乐钧生平之大概。乐钧十六岁时,其父去世。乐钧在给儿子诗《示少华二首》之一中说:“昔我成童时,汝祖捐馆舍。万事战身心,蹉跎忽老大。”[1]505父亲的去世自然对乐钧是沉重的打击,但“万事战身心”,也砥砺了乐钧的成长。乐钧年少时颇具才华,“乾隆己酉(1789),学使翁方纲奇其才,拔取贡成均”[2]9。受到翁方纲的赏识,他成为拔贡。乾隆五十五年(1790),乐钧第一次离乡游幕,是时年二十四。其诗是依编年编次的,诗集卷二“庚戌(1790)”有诗《将之京师奉别族叔松岩先生》云:“十载孤贫身不死,先生于我犹父子……先生自乐林泉老,劝我远上长安道。”[1]425即交代了自己是因贫而前往京师游幕的。“入都,怡邸延为西席,雅相敬礼。”[2]9自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夏至六十年(1795)初春,乐钧在京师先后客于翁方纲、怡亲王永琅府邸。在京师期间,乐钧与时为刑部郎中的胡克家相识。乾隆六十年(1795)暮春,乐钧南下扬州,入就两淮盐运使曾燠幕府。数月后,离开扬州归里。嘉庆元年(1796)五月,胡克家“迁广东惠潮嘉道”,[3]招乐钧入幕。乐钧有诗《将之潮州别内子三首》(诗集卷六)述其事。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乐钧于十月下旬抵达潮州,其诗《初至潮州,住监司使院西园池上,得诗四首》,其一云:“海国初冬似早秋,晓寒刚称薄棉裘。年时记在燕台住,十月金河冻不流。”[1]486幕游岭南期间,乐钧在多地纵游,在诗歌创作上进入了一个高峰,有组诗《韩江棹歌一百首》。他在岭南胡克家幕府前后四年,其间曾一度返乡数月。在嘉庆五年(1800)夏五月,乐钧离开胡克家幕府,返回故乡。其诗《岁暮往扬州留别胡果泉方伯用张文昌苏州江岸留别乐天韵》“重听严公骏马嘶”句下有小字注:“庚申(1800)五月,仆自潮州归临川,留别方伯诗有‘何时旌节移江左,借看湖山买棹来’之句”。[1]589数月后,他取道鄱阳湖、长江,再次入就两淮盐运使曾燠幕府。其组诗《江行杂时三十二首》即述其事,第三十二首云:“不惜江关路阻长,小寒时节到维扬。坡公生日应开宴,饱看梅花到蜀冈。”[1]525不过,因应江西乡试,乐钧在嘉庆六年(1801)一度离开曾燠幕府,返回江西约大半年。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云:“初名宫谱,字元淑,号莲裳,临川人。嘉庆六年举人,著《青芝山馆诗文集》。”[4]在此年的秋闱中,乐钧举人中试。次年一月,他回到曾燠幕府。而这次回到曾燠幕府逗留时间不长,因应礼部试,而前往京师。在春闱失利三个月后,乐钧再次回到曾燠幕府。自嘉庆七年(1802)至嘉庆十二年(1807),乐钧除了三度返乡,两度入京应试外,基本上是在曾燠幕府中,一直到曾燠升湖南按察使而止。嘉庆十二年(1807)冬,乐钧举家迁居苏州,其诗《移家至吴门,借居杨仁山观察思永葑门别业,得诗五首》中有云,“浮家忽到五湖旁,暂借花溪旧草堂”,“远涉江湖累老亲,如今真作吴乡人”,[1]595叙述全家居于苏州之事。约在是年,乐钧被两江总督铁保聘为扬州安定书院讲习。其《与铁制府笺》云:“何图虞山书币,忽贲吴门;特虚讲帷,以延末学。”[1]650《抚州府志》本传云“江南大吏耳其名,聘主扬州梅花书院讲席”,[2]9即述此事。嘉庆十四年(1809),乐钧又一次赴京师应春闱之试,又再一次落第。次年夏秋之际,乐钧举家由苏州迁往扬州,从此以后,他在扬州定居,于授经课徒之外,与当地以及过往的名流交往,一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秋病逝。[5]从二十四岁幕游北京开始,到五十岁时去世,乐钧大半生是在游幕中度过的,尽管是时断时续,但他的后半生除了在苏州有过约两年的休闲时光外,其馀岁月基本上是在游幕的奔波中。
正如前举彭兆荪《青芝山馆集·序》中所云,乐钧平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因此,他诗、文、词兼善,而且在文坛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其著述,主要是《青芝山馆集》,此集含诗集二十二卷,文(均为骈体文)两卷,词三卷。此外,还有文言小说集《耳食录》。《耳食录》今有两个整理本,分别是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与齐鲁书社2004 年刊行本。而其诗文集《青芝山馆集》,不曾有整理本问世。
二、游幕与文学创作
乐钧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很高,诗、文、词兼善。张维屏说:“国朝诗人善言情者不少,以黄仲则、乐莲裳、郭频伽三家为最。”[6]这是就其诗歌而言的,他颇为推崇乐钧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乐钧同时也是骈体文名家,“诸体之文,靡不奇丽”,[1]634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入选其文达6 篇之多,入选数量在此选中次于洪亮吉、袁枚、吴锡麒、胡天游、彭兆荪、孔广森、陈维崧、刘嗣绾之后,与邵齐焘、孙星衍等,足可见其骈文成就以及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所以,乐钧被论者认为“诗文足以传世,珠光剑气,讵受尘埋?”[7]乐钧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固然与个人的天分、学养有关,但丰富的游幕经历淬炼了其感受现实与表达感受的能力,使其在文学创作上更为杰出。通观乐钧的文学书写,即可发现其文学书写特点与游幕之关系。
(一)重要作品均创作于游幕时
如前所述,乐钧自二十四岁开始幕游。就诗歌而言,其二十四岁之前的诗作,全部收在诗集卷一之中,多为游仙、艳情、咏史、浪游即景之作。而自诗集卷二以至卷二十二,所收之诗,均为其二十四岁幕游之后的作品。这些诗歌除了少数为短暂返乡时所作外,其馀多为其游幕时所作。乐钧游幕时所作的重要诗歌作品有《杂兴十八首》《槛虎行》《笼鸟行》《和绿春词三十首》《刬草行》《潮州杂纪八首》《怪鸟》《韩江棹歌一百首》《岭南新乐府》《南海庙铜鼓》(卷九)、《鹤林寺杜鹃歌》《寒雁篇》《论诗九首和覃溪先生》《扬州灯市词十首》《再和绿春词三十首》等。就文而言,可以确定为其游幕期间所作的篇什,如《闻雁赋》《忆梅赋》《嘉莲赋》《游情赋》《贷园赋》《同胡果泉观察游罗浮华首台序》《金手山三李堂诗集序》《赏雨茅屋诗集序》《郭频伽邗上云苹续集序》《宗室辅国公思元主人诗集序》《宫保百菊溪制府平海投赠集后序》《江郑堂诗序》《香远楼赏雨序》《芳阴别业记》《韩江泛月记》《种榆仙馆记》《江宁清节堂记代》《与铁制府笺》《答王痴山先生书》《与谈观察书》《与刘醇甫书》《重修朝云墓碑》《胜国天潢小裔墓碑》《重修邯郸吕祖庙碑》《江都县学生汪君暨配邹孺人合葬墓志铭》《鲍贞女诔》《汪孝妇诔》《江苏官属公祭浙江提督壮烈伯李忠毅公文代》《书题襟帖后》等。根据统计,乐钧所作文共46篇,而可以确定为游幕期间所作有29 篇,占其文章总数的63%以上。而其馀17 篇,虽然大多不能确定写作时间,但其中的一半当为游幕期间所作。若合此一半之数,则乐钧游幕期间所作文章,占其文章总数的80%以上。就词而言,其词3卷,共165首(含组词),是以编年编次的。其中标乾隆庚戌(1790)之前创作的词23 首,在其游幕之前;其馀的142 首是在乾隆庚戌(1790)之后创作的,即游幕之后。虽然这142首词未必全是在游幕期间创作,但游幕期间创作出来的词作占大多数,这是无可怀疑的。乐钧的小说《耳食录》据其自序,正、续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十九年(1794)。①乐钧:《耳食录·自序》:“仆,鄙人也,羁栖之暇,辄敢操觚,追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己则不信,谓人信乎?脱稿于辛亥,灾梨于壬子(1792)。”《耳食录二编自序》:“余既梓前编,诸君子竞来说鬼,随而记之,复得八卷,犹前志也。……乾隆甲寅(1794)岁十二月乐宫谱元淑自序于京邸芳阴别业。”乐钧著、辛照校点,《耳食录》,齐鲁书社,2004年出版,第2页、第147页。由以上所述,可知乐钧的文学创作的主体完成于其游幕时期。
(二)风物民情的纪事性抒写
士人游幕,其文学书写,不外乎行役感慨、思亲怀乡与纪行述怀,当然也有对异乡山水风物的描写。游幕士人文学书写的这些主题取向,自然也为大半生游幕的乐钧所拥有。但是,相比较于一般游幕士人的文学书写,乐钧更多地将笔触投向幕游之地的风物民情,因而这使得他的文学书写与一般游幕士人的文学书写有别。乐钧平生幕游之地,主要是京师、江淮与岭南这三大地域。嘉庆元年(1796)秋冬之际,乐钧应时官广东惠潮嘉道的胡克家之邀,前往胡氏幕府供职,到嘉庆五年(1800)夏离开胡氏幕府归里,前后近四年。在这近四年的幕游期间里,乐钧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些作品,见于今《青芝山馆集》诗集卷六后半至卷十,文集中卷上的部分篇章,以及词集《断水词》卷一中的《南浦·章门南浦亭作,时往粤东,于此解缆》以下十首词。在这些作品中,乐钧刻画了大量的异于故乡江西的岭南风情民俗,如《潮州迎春词》:
城外千人万人集,不知春自何门入。欲雨不雨天濛濛,东风过处花枝湿。儿童妇女争买花,手中各带春还家。少年喧笑逐春去,乱打春牛石如雨。[1]488
抒写了潮州过春节期间的热闹场面,以及妇女儿童买花回家与少年石打春牛祈祷五谷丰登的迎春习俗。而《韩江棹歌一百首》,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广泛地抒写了幕游地潮州的各种风情民俗。在此组诗前,乐钧撰有一序,云:
……逮朱竹垞《鸳鸯湖棹歌百首》,自比《竹枝》《浪淘沙》之调,不专属鸳鸯湖,亦不专言舟楫,既博既丽,斯为盛矣!辄仿其体,著《韩江棹歌百首》,耳目所及,参以纪载,天时地理、民风物产,拉杂言之,蔓延九邑。巴渝之诮,极知不免。然陈诗太史、博物君子,采览及之,庶以见时平人乐、海滨丰庶之象。风之正变,旨之劝惩,亦或有取焉。至韩江操楫,类皆龙户,故托辞疍女,指事类情,体制则然,亦纪实也。[1]496-497
交代作此大型组诗缘由,即仿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首》而作;抒写内容,乃是“耳目所及,参以纪载,天时地理、民风物产,拉杂言之”;而抒写方式,则是“托辞疍女,指事类情”,藉疍女的口吻,娓娓道来。因此,对于自己创作的这一大型组诗,乐钧认为是属于“纪事”。如其三:
湘子浮桥铁索牵,桥南桥北疍娘船。宜春帖子雄黄纸,“长乐兴宁”小对联。
广济桥,俗呼湘子桥,在城东,横跨韩江。疍舟丛泊,船尾各以红笺,书“长乐兴宁”四字。[1]497
写疍户所居之地及其习俗。如其二十六:
三利溪添水一篙,且郎且大共鱼舠。儿夫少小风波惯,却贩鱼盐上海漕。
三利溪在郡城西,潮人称婿之兄曰“且大”,婿弟曰“且郎”。[1]498
对潮州人普遍以渔业为生计的生活进行抒写。又如其五十一:
君在羊城肯忆侬,寄侬番缎并洋钟。报君土物青铜锁,为锁情关一万重。
潮州铜锁特精,世称潮锁。[1]499
写来自西洋的番缎、洋钟为岭南的时尚物品,据此足可觇知这些物品在当时广东的流行程度。
再如第七十九:
船窗小几供泥孩,土地祠中接取来。莫保生男但生女,为侬承守旧妆台。
妇女多往土地庙迎取土偶,以为怀孕之祥。疍家以生女为乐。[1]500
写潮州疍家的“以生女为乐”的生育好尚,这一民情习俗显然与中原迥异。《韩江棹歌一百首》除最后一首“荷风蕉雨伴闲窗,戏拾蛮笺咏海邦。南国轩如问俗,棹歌声里是韩江”作组诗的归结而无小字注外,其馀99 首均有字数不等的小字注。对于《韩江棹歌一百首》及其小字注,同时期的文学家王芑孙在《书乐莲裳韩江棹歌后》跋语中指出:“乐君莲裳游粤,因为《韩江棹歌》百篇,指事类情,赅引极博,于以达殷勤之心,而颂善丑之德,庶几固所谓微言相感者在焉。其自注,尤精审有法,足为一方职志。异时诗官采言,诵训诏俗,其将于是乎观之。”[8]揭示了其纪事性与其社会史料价值。乐钧对幕游地风物民情的书写,不限于岭南。当游幕扬州时,乐钧亦撰有《扬州灯市词十首》,抒写扬州灯节时的民情习俗。不过,由于沿海与内地的习俗差别,他在诗中呈现出扬州灯节时的民情习俗,不能像其抒写的岭南风物民情那样,给人以深刻的新奇之感。
(三)强烈的现实关怀
与一般游幕士人对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不同,乐钧在幕游期间的文学书写灌注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命运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对社会中的黑暗、病态现实予以严厉谴责、抨击,表现了一个充满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的良知。乐钧对现实的这种强烈关怀,在其组诗《岭南新乐府十章》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该组诗之二《买凶》:
杀人者购一人代为抵罪,名曰买凶,虽茹刑不肯吐实。
富儿杀人走亡命,贫儿受赂顶名姓。甘心性命轻鸿毛,虽有于张讼难听。头颅卖却值几钱?价高不过三百缗。妻孥得此暂温饱,餐刀伏锧无冤言。东市云寒日色薄,临刑犹自念馀橐。北邙山下纸钱飞,何处青蚨贯朽索?富儿生益富,贫儿死终贫。贪夫殉财终杀身,钱能使鬼还通神。[1]506
虽然乐钧在诗中将“贫儿”的抵罪而死称为“贪夫殉财”,但他却揭露了当时社会中“钱能使鬼还通神”的黑暗现实,即富人杀了人可以买凶抵罪。而穷人“甘心性命轻鸿毛”,虽然以自己的抵罪而死使“妻孥得此暂温饱”,但结果仍然是“富儿生益富,贫儿死终贫”。诗人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有力的批判,充满了深切的悲悯之情。该组诗之八《鸦片烟》:
粤人骫法,多食鸦片烟。或曰媚药,或曰非也。久之,且断人道。食至数月,遂不可辍。每日皆有定候,名曰上瘾。必枯槁不寿矣。
鸦片来自西洋船,浓于胶漆毒于鸩,一丸价值千铜钱。得钱不惜买鸦片,但云服之体轻健,彭祖秘术不足羡。床头一灯光荧荧,两人长枕同横陈,竹管制作卜字形。管穴中容烟一粒,一粒一人相递吸,吸烟人如虫蛰蛰。日日吸之时弗失,饭必甘肥饮醲汁。劳力劳心无不可,仿佛丹砂烧伏火。少年那待老见侵,面目枯黧形挛跛。虽有卢扁焉能医,囊橐已空身命危。昼长宵永卧败絮,鼻触烟香涎尚滴。呜呼!杀人之物人争惑,利重民贪禁不得。[1]507-508
抒写了当时民众吸食鸦片的情景,以及吸食鸦片对国人的毒害情形。这大概是最早的揭露、指斥鸦片之害的诗作,与《韩江棹歌一百首》之三十三首“劝君莫食鸦片烟,劝君莫食暝菜鲜。暝菜令人眠不醒,鸦片令人醒不眠”[1]498互为表里。该组诗之十《摸鱼歌》:
按《广东杂记》云:粤俗好歌,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今广州所唱,皆盲词,老妪导盲女夜中沿街唱之,亦娼妓之属。
珠江潮水无清波,盲女夜唱《摸鱼歌》。繁音促节那可听,鬻歌乃比雍门娥。苦无金篦刮眼膜,何曾对镜自梳掠?青春不嫁弄潮儿,身世生涯寄弦索。飞鸟已栖谯鼓鸣,手扶老妪肩背行。街长巷曲是何处?几家灯火门将扃。门外人呼盲女止,一歌再歌歌不已。三弦嘈切檀板急,市人拍手主人喜。可怜《摸鱼歌》,不诉心中悲,不是薄命辞。残花落溷弄馀姿,声声犹说长相思。[1]508
抒写深夜中仍在长街曲巷卖唱的盲女,对其不幸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此外,《诗集》卷八《役夫》描写了在山路中“历艰绳屦断,负重毳褐穿。昼裹豆粥饱,夜假蒲鞯眠”的役夫,控诉了官吏与役长对他们进行的“就中十取五”的剥削。卷十三《麦熟叹》“悲哉翁媪不耐饥与寒,穷冬已入柳木棺”,诗人由今年的麦熟,想到去年因灾荒饥寒而死的灾民;卷十四《秋涨行》抒写了秋日洪灾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黎川一霎连皓旰,孔氏千家无孑遗。浮尸相逐去漫淼,暴物所过俱伤夷……”[1]546卷十五《观音土行》“丰年无钱人食苦,凶年无钱人食土。和糠作饼菜作羹,充肠不及官仓鼠”,[1]552将灾荒年月里的百姓同官仓老鼠作对比,对统治者不恤民生的冷漠、冷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在这些诗里,乐钧怀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抒写普通百姓经历的苦难、灾难,以及对统治者、剥削者的愤怒批判,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所以,袁行云认为乐钧之诗“悯念农家,情尤深挚”。[9]1795乐钧在诗歌中的这些抒写,较之于那些流连光景、交际应酬之作,无疑更具社会意义。
三、游幕对文学成就的影响
如前所述,乐钧享年五十来岁,其后半生基本上是在游幕中度过的,其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在游幕中完成的,因此,其文学成就的取得以及独特的风格,与游幕是密切相关的。近代学者汪辟疆论及乐钧之诗时曾说:“余尝谓江右人诗有江左人气息者,惟兰雪与莲裳,亦以莲裳久客扬州曾宾谷幕中,与吴人习处既久,故肸蚃相通也。”[10]那么,游幕对乐钧的文学成就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一)丰富阅历,拓展了表现现实的广度与深度
如果乐钧不是因为家贫而游幕,而是困守家园,那么,他即使偶尔外出游历,其视野也是有限的,正如他在《答刘醇甫书》所言:“杜迹山樊,涂塞耳目。”[1]652接触不到深广的社会现实。由于自二十四岁时外出幕游,乐钧北至京师,南至岭南,在江淮之间居留最久,所涉地域是相当广阔的。因此,幕游期间的耳闻目睹,以及所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物,极大地扩充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乐钧对社会现实的这种认识,通过文学书写呈现出来,这使得他的诗文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远为拘守于乡曲者所不及。如他前往京师幕游途中写下的《麦秋谣》,叙写了“东邻新妇晨炊罢,腰镰来助阿婿忙”[1]428忙于收割的麦秋情景,自京师南还道中的《童女》诗写到灾荒年岁灾民“树肤剥削尽,搜及枯草根”[1]464的悲惨生活。而幕游岭南,道中作《刬草行》(诗集卷六),藉所逢一刬草老人之口,控诉了“僻壤偏灾官不知,统报收成十分蚤”颟顸昏聩的官府,以及当地百姓“亦无男女堪卖钱,只有乞食白头媪。西家稚子如饥鼠,东邻老父似冻鸟”的惨状;《渔子谣》(卷六)写渔民“罾中得鱼长几尺,网中泼泼鱼纵横”的打鱼生活,《壶卢阁》(卷六)一诗对“纵奸害良善”的官府予以谴责;而《潮州花灯词》《潮州杂纪》《韩江棹歌一百首》《岭南新乐府》等篇什,广泛地抒写了岭南地区的风物民情,以及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如买凶、造饷等予以严厉的抨击,而对不幸命运的普通百姓则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虽然这些作品在《青芝山馆集》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是远逾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对于乐钧的这些作品,当代学者袁行云认为“指事类情,较为警辟”,[9]1795指出了其涵具的特别的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而且,从乐钧的这些作品中,不难体味到其心灵的善良与高贵,以及其敏锐的生活洞察力。
(二)友朋相聚,切磋激发
一般而言,幕府是一个具有各种才艺的人才聚集地。一些才学之士由于功名未遂,出于治生的需求,往往游幕四方,藉幕府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因此,进入幕府,即已意味着与才学之士相聚、往还,并成为朋友。而在幕府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名流,这些为时所称的名流,也是各具才华的。游幕士人不可能将自己孤立起来,封闭在幕府之内,因而与幕府之外的名流自然免不了接触、交往。因此,一个士人游幕,进入到幕府中,就会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而友朋相聚,虽然是流连光景、交际应酬的时候居多,但谈文论艺、进行切磋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乐钧半生游幕,经历了多个幕府,因而结交的朋友颇为不少。他游幕京师期间,幕主有作为师长的翁方纲以及怡亲王永琅,所交之友有乐毓秀、吴嵩梁、周厚辕、罗聘、宋鸣珂、康亮均、舒梦兰、吴俊、李如筠、胡克家、饶敷善、熊方受、法式善等;幕游扬州,所交朋友在幕主曾燠之外,有谢振定、张铭、尤荫、王文治、王嵩高、胡森、陈燮、郭堃等;幕游广东,所交朋友有胡枢、何南钰、吴慈鹤等;再次幕游扬州,所交之友有蒋知节、詹肇堂、汪端光、金学莲、王芑孙、洪亮吉、方正澍、刘嗣绾、陆继辂、郭麐、郭琦、吴锡麒、彭兆荪、沈培、顾广圻、钱坫、董士锡、姚椿等。上述这些人,基本上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文士或学者。同这些人交游,晤谈品题,进行切磋,不但能提升自己的艺文识力与水平,同时能激发创作热情。嘉庆九年(1804)秋冬之际,乐钧与友朋有多次联句,如其诗集卷十六《秋尽日休园小集联句二十四韵》《夜来红联句十六韵》《秋海棠联句二十四韵》等,这种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句活动,其实就是一种彼此之间诗艺的切磋。同卷《冬窗杂诗和芙初四十四首》,是在刘嗣绾原诗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诗前有小序,云:“顷见芙初此作,有触予心。于是感时寓兴,接近怀远,悱然蕴发,拉杂成咏。积累有日,不复诠次。”[1]570对此组诗的创作缘由交代得很清楚。在书函《与谈观察书》中,乐钧述及谈氏对自己艺文的褒奖:
……嗣幕下诸君来过邗上者,多称雅论,特许鄙文。以谓握珠抱璧,实嗣古之才;范水模山,有成章之斐。虽复宁朔盱衡,宣城藉齿,方之于今,何以远过?于是淫淫其汗,惴惴其心……自稔投瓢之具,惟供覆瓿之用。何图偶播爱口,遽渎神矑?遂承光影之褒,不翅声闻之寿。[1]652
谈观察对乐钧文章的褒奖,实际上是对其文章书写艺术的肯定性批评,这就具有切磋的性质了。而在《与姚椿书》中,乐钧述说自己“少失庭训,长而游惰,经籍束阁,尘壒积胸,徒以师友纵臾,胜流渐渍,遂乃操觚襞楮,饰陋缝疏……幸有如足下数君子志侔神合,劘切无隙”,[1]653-654认为自己在艺文上能取得成功,是由于“师友纵臾,胜流渐渍”以及朋友之间“劘切无隙”的结果。书函中所说的“数君子”,指的是姚椿与彭兆荪、郭麐、王芑孙、金学莲等人,他们均是幕游之士;“胜流”与“师友”,很大的一部分系指包括翁方纲在内以及在幕游期间所结交的朋友。也就是说,乐钧在艺文上的进步,创作活动的展开,以及文学成就的取得,与游幕期间所结交的友朋切磋、激发是分不开的。乐钧在此所述的自己的艺文成长经历与幕游的这种密切关系,对游幕士人的文学书写而言,无疑具有典型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乐钧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幕游在外,只是由于省亲或参加乡试,才间或返乡。就诗而言,他幕游之前的诗歌在整部诗集中仅占一卷之多,而其馀的二十一卷诗作,基本上是在幕游期间书写的。其词与文,情形与其诗类似。近代学者汪辟疆认为:“莲裳诗于绮密秾蒨之间,有简质清刚之气,在当时作者刘芙裳、吴兰雪、郭频迦、孙子箫之间,植体为高,但不及黄仲则耳。”[10]然而,游幕赋予了乐钧诗歌深厚的社会内容,使其诗歌同那些流连光景的诗作比较起来,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乐钧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应该在黄景仁之上,而不是像汪辟疆所说的“不及黄仲则”,因为乐钧在诗中不仅抒写了个人的哀愁伤痛,而且还将笔触指向了民生疾苦,而这,正是其迈越流俗之处,应该在清代诗歌史上大书特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