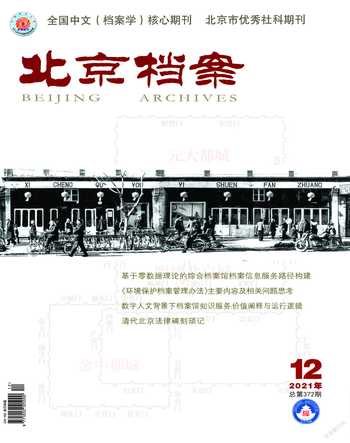中国近现代档案管理机构发展演变研究
2021-01-14丁海斌刘卉芳
丁海斌 刘卉芳
摘要:鸦片战争后,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开始向近代化迈进,直至民国时期专职性已经成为档案管理机构的最大特征,不同体系内的机关档案室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档案馆逐步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管理机构逐步形成了档案室与档案馆两大体系,但在“文革”期间遭受了极大的重创,之后档案管理机构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直到今天,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已经完全进入了信息化的时期,档案数据共享中心等信息化档案管理机构的出现为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档案机构 档案管理机构 近代 现代
Abstract:After the Opium War,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archiv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began to move toward modernization, until the Re? publican period when specialization 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 systems of institutional ar? chives as well as national archives in the modern sense we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fter the found? 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al manage? ment institutions gradually formed two major sys? tems: archives room and archives, but suffered great dam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which archiv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entered a period of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Until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rchiv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has completely entered the period of in? formation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 tion- based archiv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such as archival data sharing centers has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manage? ment institutions.
Keywords:Archival institutions;Archive Manage? ment Agency; Modern; Contemporary
档案管理机构是直接管理档案的业务机构,是档案事业的核心、主体和基础。
此前学界对档案管理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的横向研究方面,针对档案管理机构发展演变的纵向历史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古代档案管理机构的研究方面。对近现代档案管理机构设置的研究,多集中于档案史相关的学术论著中,缺少专门性的研究作品。如周雪恒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裴桐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丁海斌、张洋的《论社会制度与档案事业》[1]等。然而,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档案管理机构变迁的历史背景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对理解档案工作乃至整个档案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关理论研究的缺少是档案学研究的重大缺失。本文尝试对中国近现代档案管理机构的演变做一个整体性的研究,以弥补此前学界研究的缺失。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政体和经济文化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古代档案管理机构体系被打破,此时的档案管理机构逐渐开始呈现社会性的特征,不再仅是国家政权机构的统治工具,设置档案机构的社会实践领域也开始扩展。在中央和地方,机关档案管理机构普遍建立,并形成了一定体系,还出现了第一个近代国家档案馆;在企业当中也开始设立了保管文书和技术档案的专门机构。
(一)近代机关档案管理机构
1.晚清时期。清末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极大地受到了清末政治制度的影响。第一,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意识到外交事务的重要性,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更名为外务部)、总税务司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出现了专门保管档案的部门,比如外务部下设的机要股、总税务司下设的机要科都负责保管各部门的机要档案。第二,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了新政,对原有的档案管理机构进行了裁撤与合并,并成立了新的档案管理机构,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更院(理藩院)为部……隶领办处,以汉档房、俸檔房、督催所改并”[2]。总之,晚清时期原有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被打破,新设的机构开始受到西方档案管理思想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2.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机关档案室在此时也初见端倪。临时政府在总统府下设秘书处,该处下设文牍科,负责整理和保管总统府的档案,此时的文牍科就相当于总统府的机关档案室。除此之外,在临时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都设有政务厅,负责文书与档案工作。总的来说,由于政权草创,临时政府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但在秘书机构中下设了兼管文书、档案工作的机构,这些机构很少承担其他方面的职责,并且都设有专门负责档案工作的人员,相当于专职的档案人员。
3.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档案管理机构,基本沿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做法,但与临时政府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具有近代性质的档案管理机构增多。北洋政府时期实行三权分立,除了在总统府和国务院设立的中央政府文书、档案管理机构,在立法与司法机构中也设有专门的文书、档案管理机构。
在总统府和国务院负责文书、档案工作的主要是秘书厅。1914年总统府颁布了《大总统政事堂组织令》,裁撤了总统府秘书厅,其后主要由机要局和主计局负责文书、档案工作。在立法和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专门的文书、档案管理机构,比如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秘书厅,总检察厅中的书记处等。除了中央,地方的文书、档案工作也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虽然省一级的行政区划时常变化,但其文书、档案工作一直由总务科负责,无论地方行政机构如何变化,文书、档案管理机构是一直存在的。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至1932年,国民政府在中央各部和党务、军务系统中陆续建立了一大批独立的档案管理机构。如中央各部的掌卷室、管卷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属的中央档案整理处,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临时档案室、一般档案室等。
这一时期,随着档案学的产生,许多学者都对档案组织有了自己的认识。因此在当时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有涉及档案组织的内容,其目的主要是研究机关内部应该设立怎样的档案管理机构,机构内部如何分工、管理以及档案管理机构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等。
龙兆佛和黄彝仲都认为档案组织(机构)的职能应当扩大。比如龙兆佛在《档案管理法》一书中就说“欲彻底解决档案问题,管理档案部门的组织必须扩大,工作人员之地位必须提高。档案股应改为档案室,其地位与科平行,然后可以罗致相当人才彻底改革”[3],并指出档案室(处)的内部组织应分作登记、编目、典藏与出纳四股。在谈及文书与档案工作之间的关系时,秦翰才在陈述了当时档案管理机构与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之后说道:“档案工作应脱离一般之文书组织而自有一独立之组织……即在设有文书科股之机构,应另设一档案科股组,两者处于同等地位。”[4]
这些都表明,在国民政府时期,人们对档案机构设置问题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随着人们对文书与档案工作之间分工的认识,独立的档案管理机构已经普遍建立,文书和档案工作开始逐渐分化。
(二)近代国家档案馆的诞生
文献馆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国家档案馆,它不同于近代的机关档案室,是一个专门管理历史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它的诞生与明清档案的整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晚清时期的“八千麻袋事件”等使明清历史档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同时也引起了学者对明清档案的重视。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成立了国史馆和清史馆来保管历史档案,但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负责清理清宫物品及处理善后事宜。经过一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成立,在图书馆之下设文献部,负责明清档案的收集和整理。1927年,文献部更名掌故部,继续从事相关整理工作。1928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正式成立。随着明清档案整理工作的深入,1936年文献馆制定了《文献馆整理档案规程》,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台了《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简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作为一个管理历史档案的机构,其专职性日益突出,它的诞生代表着近代国家档案馆在中国的出现。
(三)近代企业档案管理机构的产生
近代企业档案管理机构产生于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后,一大批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兴起,在这些企业中部分设有专做或兼做档案工作的机构。“有的厂矿设立文案处,专管文书档案。一般厂矿均设有‘画图房’等,既负责绘制技术图纸,也是兼管技术档案的机构。此外,有时技术人员和晒图人员也负责保管技
术档案”[5]。
民国时期,企业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普遍,在许多企业当中都设有文书室(科、股)负责文书、档案的管理。企业中还有科技档案,这部分档案多由专门的技术部门或专人负责保管。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企业档案管理机构等的出现,使得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再局限于国家机关的范畴,而是扩展到经济、文化等领域,并有了一定的社会性特征。
我国现代档案管理机构的建设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档案管理机构认识过程是高度一致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机构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档案管理机构才得以不断地发展完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步建设时期、遭受破坏时期以及恢复和全面发展时期。下文将对主要时期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及档案界的认识进行阐述。
(一)档案管理机构建设初期(1949年—1966年)
档案管理机构初步建设时期的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级档案馆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抢救和接收旧政权档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1951年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处成立。同年5月,文献馆更名为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负责收藏和保管明清的历史档案,这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第二是机关档案室的建设。195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召开中央一级党、政、军三大系统保管文件档案的分工会议,建议各部委建立档案室。同年8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建立与健全党委机关档案工作的意见》发布,在该意见中对档案组织的建立提出了初步的认识,意见提出在华东局、山东分局、各省、大市和区党委的办公厅建立总档案室、分档案室的要求,并要求各个机构都设立相应的档案组织。随后,机关档案工作在中央、省、市级机关初步建立了起来。
1.档案室体系的建立。建国初期我国档案室的建立与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大行政区国家机关改组之前;第二个时期为国家档案局成立之后;第三个时期为集中统一原则确立之后。
在大行政区国家机关改组之前,机关档案室的设置分为总档案室和分档案室,总档案室对分档案室在业务上起到指导作用,同时接受分档案室移交的档案。因此这一时期总档案室兼有档案局与档案馆的职能。曾三先生在1951年11月发表的《关于档案室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我们目前要先讨论的,只是如何建立‘档案室’的工作。”[6]同时指出档案室的建设是档案馆的基础。可见这一时期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档案室是档案管理机构建设的重点,同时,机关档案室工作是档案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它标志着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有领导、有计划的新阶段。它的成立为档案工作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组织保障。曾三同志1955年在《我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一文中曾说:“看趋势,档案工作也要慢慢地成为独立的部门;或者在秘书处设专人或专门的科(室)管理档案工作,因为工作发展了,不分开不行。”[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档案界普遍认为档案管理机构会像其他机构一样逐渐成为独立的机构,而档案室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也是大势所趋。
1956年《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的发布为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法规保障。1959年1月7日《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发布后,我国机关、团体、企业的档案室的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确立后,机关档案室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技术档案在生产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59年,曾三同志曾在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档案是国家全部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8]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室的建设的一个重点放到了科技档案室建设之上,除此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继续建立和健全机关档案室的工作”[9]。1960年,《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经国务院批准试行,1961年新的《机关档案室工作通则》发布,这两个《通则》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机关和科技档案工作机构的建设。截至1962年底,中央一级机关档案室以及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室都逐渐建立了起来,各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建立起了科技档案处(或科)。
2.国家档案馆体系的建立。在建国初期,我国仅有两个中央级历史档案馆,即故宫档案馆和南京史料整理处,但这一时期的档案馆主要负责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的整理。我国国家档案馆体系的建立始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这一领导体制形成之后。
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规定了要建立“各级档案工作机构”,其中就包括档案馆系统的建立,决定中指出“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的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0]。
1959年《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发布后,极大地加强了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也加速了我国国家档案馆体系的建立。1959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成立,并将明清档案馆(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入。1964年,南京史料整理处被命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后地方各级档案馆以及专业系统的档案馆纷纷建立起来。就此,国家档案馆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二)档案管理机构的恢复与全面发展时期(1966年至今)
1.档案馆(室)的全面恢复。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遭到了重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划出档案系统;各级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或被撤销、或被削弱,全国的档案管理机构建设全面停滞。
197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恢复中央档案馆名称和国家档案局的通知》。同年8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任务,档案馆、室的工作开始逐步恢复。此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地方各级档案馆纷纷恢复了工作。截至1980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地区外)都已建立了档案馆。与此同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也逐步恢复。
“文革”以后,技术档案的缺失为生产恢复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档案界也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档案的重要性。因此,科技档案管理机构的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档案机构建设的重点之一。1980年12月《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颁布对科学技术档案工作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截至“一九八二年,在全国冶金系统的225个企业、事業单位中,恢复建立的科技档案室(处、科)的有173个,占76.9%”[11]。
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机关档案室工作条例》,其中规定“中央和地方专业主管机关的档案部门,应根据本专业的管理体制,负责对本系统和直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12]。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机关档案室改为档案处(或科),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教学、地名等类型的专门档案室以及由同系统、同类型机关共同建立的联合档案室。
2.档案馆(室)进入信息化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信息化发展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档案事业也日新月异。在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此期间的最大变化是档案机构的信息化。
2001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中正式提出了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信息化的档案管理机构——数字档案馆也由此发轫。2002年,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在部分中心城市建设示范性数字档案馆。2006年《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颁布,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总体目标的一部分。2014年《数字档案室指南》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数字档案室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数字档案馆(室)。随着数字档案馆如火如荼地建设,“智慧档案馆”概念也逐步进入档案界的视野。2014年2月28日,辽宁省档案学会组织召开了“智慧档案馆研讨会”,同年3月,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学会组织召开了“智慧档案建设研讨会”,档案学界就此提出了“智慧档案馆”的设想。2015年,青岛市智慧档案馆率先投入运行。2020年,苏州市智慧档案馆项目顺利通过第三期的验收。
从古至今,实践的需求一直都是档案机构设置的根本。近年来,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智慧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档案管理机构也走向了自己的智能化、智慧化轉型。2021年11月22日,北京海淀区档案馆智能档案库房一体化管理系统正式落地[13],为档案数据的智能管理夯实了基础,也为城市智慧管理下档案数据的共享与互操作提供了稳固的保障。
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古至今,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从档案库到档案数据共享中心,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中蕴含着“变”与“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管理机构的社会性逐渐增强,职能也不断拓展。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蕴含着“变”,变的是社会对档案机构建设的需要,是人们对档案管理机构的认识,是不同档案管理机构的性质、职能;但档案管理机构的发展也蕴含着“不变”,不变的是档案管理机构设置与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一致性。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国家建立档案管理机构的根本就是实践的推动,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对档案管理机构产生不同的认识,从而对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提出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档案管理机构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档案管理机构之间性质、职能、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不同。
*本文系“新版《档案学概论》理论创新系列论文”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海斌,张洋.论社会制度与档案事业[J].档案学研究,1997(2):21-23.
[2]赵尔巽.清史稿·志·职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6.
[3]傅振伦,龙兆佛.公文档案管理法[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74.
[4]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M].上海:科学书店.1942:7.
[5]丁海斌,陈凡.中国科技档案史[M]//《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5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846.
[6][7]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一集)[M].1980:42,189.
[8][9]国家档案局.曾三档案工作文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02,101.
[10]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集(第1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8.
[11]裴桐.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4.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局.机关档案工作条例[EB/ OL].[2021- 9- 20]. https://www.saac.gov.cn/daj/xzfg/ 198304/48af7a64f8914043a2f778f9865f09d5.shtml.
[13]北京亦庄.“一规一馆一体系”,北京经开区开创档案数据工作“新格局”[EB/OL].(2021-11-21)[2021-11-26].http:// kfqgw.beijing.gov.cn/zwgk/xwzx/yzxw/202111/t20211121_ 2541329.html.
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2.广西数字档案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