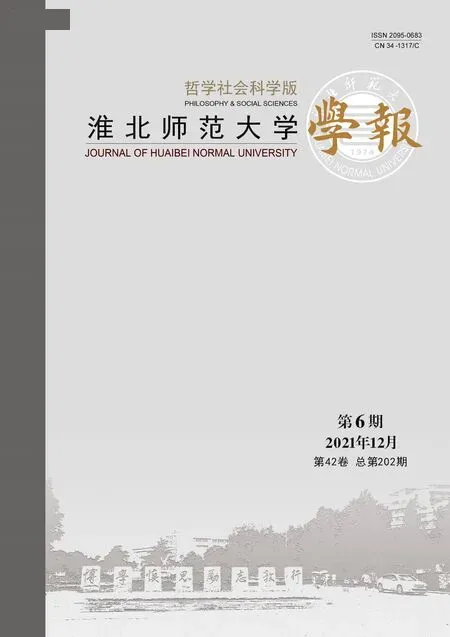继承与开创:“延津叙事”的审美新建构
——论刘震云长篇小说《一日三秋》
2021-01-14陈振华
陈振华
(安徽外国语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合肥 231201)
《一日三秋》甫一问世(《花城》2021年第4期,单行本2021 年7 月版,花城出版社),随即收获了一众评论家、作家、出版人、读者的高度赞誉,被称为作家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的又一当代杰作。来自业界的李敬泽、张旭东、陈晓明、白烨、王干、邱华栋、宋万金、史航等纷纷给予了富有见地的短评。李敬泽认为“《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秋天写作,像秋天一样包容、成熟。”张旭东称小说“据几幅已经灰飞烟灭的画,讲述一部生活世界的演义,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小说实验。”陈晓明评价称“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人生的戏剧性,巧妙勾连,不经意却胜似鬼斧神工。”白烨则以为小说“把戏曲、传说、梦境等都联结和串通起来之后,带有了浓郁的寓言色彩。”[1]1……这些未及展开的评论性文字并不能简单视为出版商的噱头,而是他们在超前阅读中得出的个人性的阐释和判断。确实,这是刘震云又一部极富个人创造性的长篇小说。评判这部小说并非易事,因为阐释评判不能完全就文本而文本,还需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文学史的框架、刘震云自身创作的谱系乃至世界文学场域中去锚定其恰当的坐标。这部作品成功之处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在于刘震云对他自己“延津叙事”的继承与开创。它是刘震云“延津叙事”的新突破,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收获。
一、乡土卑微者“精神肖像”摹画的前史
刘震云的故乡在河南延津,延津既是他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其心灵情感的家园,更是刘震云文学创作上的精神飞地。他的大部分文学创作都指涉或直接表现延津的风土、人物、文化、心理和历史。从早期的《塔铺》《新兵连》开始,刘震云就开启了他“延津叙事”的写作。多数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贾平凹的商州、汪曾祺的高邮、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无不镌刻着作家的精神胎记。刘震云将最真挚的情感、心灵、精神内核放置在故乡延津,但刘震云的故乡叙事是反神话的写作,他关注故乡延津真实的历史情状,尤其对故乡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心灵进行深度打捞,其“延津叙事”既是作家个人独特的文学标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的重要组成。从1980 年代的《塔铺》《新兵连》、1990 年代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到新世纪以来的《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再到刚刚出版的《一日三秋》,它们是“延津叙事”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面相。刘震云在“延津叙事”里构建了乡土卑微者的生活群像,尤其是对既往缺少关注的乡土卑微者的精神肖像有独到的书写。
这里的乡土卑微者或者说是历史细民在刘震云的小说里,主体并不完全是附着于土地的农人,更多是乡土那些带有一定流动性、交易性、手艺性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杀猪的、剃头的、卖豆腐的、修脚的、开染坊的、外出谋生的……他们构成了乡土熟人、伦理、习俗型的社会生态。他们社会地位低微,靠一点手艺、活计维持基本的生存,有的甚至连固定的土地都没有,他们和农人一道构成了乡土卑微者系列。小说由他们的“说话”追溯他们的心理动机、心理活动,形塑中国乡土卑微者的精神肖像则有了艺术的可能。中国小说的发端及其话语多源于“引车卖浆者”的道听途说或街谈巷议,这无疑佐证了乡土卑微者——引车卖浆者之流话语的丰富、随性、粗鄙乃至荒诞不经。构成背反的是,这些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关注的审美对象绝大多数不是引车卖浆者自身的命运或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是“他们”以外的人类。由此,我们古典小说形成了这样的传统:书写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才子佳人、强盗匪寇、青楼戏子的形象与故事,唯独没有历史卑微者自身的面影与心灵。
新文学以降,鲁迅的《呐喊》《彷徨》与之后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人生写实小说、主观抒情小说改变了中国小说既往的关注对象,视点下移,将农民、手工艺者、落魄的文人等历史中失语、被遮蔽或“不在场”的群体纳入了文学视野。在启蒙现代性视野之下,以阿Q、祥林嫂、闰土为代表的乡土卑微者前所未有地进入了现代小说的领地。思想启蒙的前提是国民性批判,因此在启蒙现代性视角下,乡土是晦暗、破败、凋零、闭塞和愚昧的。难能可贵的是,鲁迅触及到了乡土卑微者孱弱的灵魂。阿Q 的精神胜利法和对革命虚妄的幻想,祥林嫂对灵魂的发问以及闰土由“迅哥”到“老爷”称谓的变化都可以看出乡土卑微者痛苦麻木的精神现状。只不过,鲁迅以历史达尔文主义、启蒙现代性“看取”乡土中国的灵魂现实,他站在知识、思想的高度,俯视、揭示乡土卑微者暗昧的心灵和国民文化心理。在鲁迅那里,乡土暗昧的灵魂是作家批判的客体,并由此客体追问国民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缘由及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废名、沈从文则在审美现代性的观照下,以田园牧歌书写乡土、边城人性的健康、人情的美好、道德的淳朴。沈从文的人性、道德乌托邦建基于“去历史化”的乡村,其文本的审美想象建构于现代性历史进程之外的原始和封闭——文明的化外之地。他并没有用过多笔墨去开掘乡土升斗小民的内心世界。解放区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塑造翻身农民形象的时候,对农民心理世界变迁的描绘还没有上升为叙事的主体。建国后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主要侧重于农村新人或英雄、模范人物的塑造。《三里湾》里的“中间人物”在当时受到了批判,今天看来,他们的形象富有历史、文化、心理内涵,其精神肖像似乎比那些先进人物更切近乡土历史的本真。无论是先进人物还是“中间人物”,他们的精神肖像只是在特定历史运动来临时刻才得以阶段性描画,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心理的深度开掘。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也是展示不同历史时期,时代、社会、历史的变化赋予人物的心理征候,陈奂生的心理刻画、精神肖像的描绘是为时代变迁提供心理的佐证。19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叙事,出现了一些新的表征,“乡下人进城”、留守妇女儿童、土地流转、农村的基层治理、城镇化进程、脱贫攻坚等,赋予了乡土叙事新的时代符码。但这些乡土叙事能够写出乡土底层民众真实自我意识的作品并不多见。陈晓明认为:“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并未发现多少自然本真而又深刻描写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的作品。”[2]11从这个层面来看,刘震云凭借“说话”对乡土卑微者“内心的洪流”、个体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所作的细微、全面、深刻的摹写,将乡土卑微者的精神肖像刻画、心理世界的揭橥当作写作的核心追求,不再视乡土卑微者的精神心理为审美客体,而是具有了浓郁的本体论意味。乡土底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第一次上升到叙述主体的地位,成为叙事的重心,这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文学史意义。
这里有必要对刘震云之前的几部创作做简单的阐释性回顾,它们构成了《一日三秋》创作的“前史”。在《故乡面和花朵》创作时,刘震云就自觉意识到精神想象对于创作的意义:“在三千年的汉语写作史上,‘现实’这一话语指令一直处于精神的主导地位而‘精神想象’一直处于受到严格压抑的状态。”[3]118因此,故乡面的“面”还原故乡的现实肌体,而“花朵”则是生长于故乡现实、历史之上的“精神想象”和乡土卑微者的“心灵生活”。藉由文本中“小刘儿”“白石头”“孬舅”等乡村底层民众的话语狂欢和精神想象,刘震云试图深度抵达乡土社会中寻常百姓的精神心理。梁鸿认为这个时候的刘震云:“洞透乐观时代镜像背后的虚无和真相,彻底摆脱‘道德’‘启蒙’之类的词语对中国作家的精神束缚,摆脱了对乌托邦图景情不自禁的幻想,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和人类存在本质状况的描述。”[4]57《一腔废话》将“说话”演绎到极致,在荒诞的情境中,五十街西里(虽是城市街区,但生活其间的民众仍然保留着乡村人的精神底色)底层民众的话语表演、欺骗、疯傻撕碎了“人”的主体性、自我的完整性,以不可言说的饶舌——废话,显影底层民众精神生活的虚妄与贫瘠。当然,刘震云并没有否定“一腔废话”之于芸芸众生精神生活的价值,或者说,正是95%以上的“废话”,构成了乡土生活、乡土卑微者的精神现实。《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是进城的农民工,其命运虽有过于戏剧化之嫌,但他的话语和行为确实凸显了乡土卑微者进入都市后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症候,尤其是小说对刘跃进个体心灵世界的洞幽烛微,切中了国民性的文化基因遗留和精神痛苦。《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以“说话”为叙事动力的特别叙述:“这是一个‘无法复述的文本’,或者说是一个‘语言本体论的叙事’,也就是说,小说如果剥离了其语言本身,叙述和故事都几乎不存在,而不像其他的作品,在经过提炼和浓缩之后仍然有一个故事构架,它的故事可以说无法脱离它的叙述与语言载体。”[5]39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出延津记,牛爱国的回延津记,即是话语编织的叙述,乡土百姓的“说话”呈现了百年乡土卑微者的心灵情状。小说虽然有杨百顺、牛爱国贯穿文本的始终,但刘震云真正想展示的不是单个的“我”的话语,而是乡村众多的“我们”群像及其灵魂的真相。“我们”是文本中卖豆腐的老杨、赶大车的老马、“喷空”的杨百利、杀猪的老曾、被拐卖的巧玲、出轨的吴香香/庞丽娜……源于灵魂的孤独,无论是出延津还是回延津,他们都在寻找“说得着”的另一个灵魂,“说得着”才能够“一句顶一万句”。在中国小说史上,《一句顶一万句》第一次将乡土卑微者的灵魂以“说话”的方式演绎得如此细微而又绵远。这里不惜笔墨回顾《一日三秋》之前的“延津叙事”,意在说明《一日三秋》的创作既是对其“前史”的继承,又在前期创作的基础上有了创造性的开拓。《一日三秋》仍然是刘震云“说话”的延续和新的开创,把人的情、理、欲镶嵌在百姓的话语和行为中,刘震云依然以“说话”敞开故乡延津卑微者的心理和命运,比起《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格局更大,艺术格调更为苍凉和绵远——后文将展开详细的论析。
二、以“笑话”纽结乡土的人伦、人心、情感和命运
《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现,读者普遍以为刘震云的“延津叙事”已然抵达巅峰,后面的故乡叙事将难以为继,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刘震云有他的执拗、韧性或者说有着极为浓烈的故乡情结。有论者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是“百年延宕”,那么《一日三秋》则是“千年求索”。从篇幅上看,《一句顶一万句》36 万字左右,《一日三秋》18 万字上下,体量几乎只有前者的一半;从故事时间来看,《一句顶一万句》从清末民初延续到当下,时间跨度大约百年,而《一日三秋》从冷幽族被屠戮,花二郎和花二娘(柳莺莺)逃亡始至当前,历史横跨三千年。无论是百年还是三千年,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具有非常明确、自觉的“时间意识”,而这种时间意识是作家的权力,因为“小说家应该超越他的主人公的意识,而且这种超越从美学上说是小说创作的组成部分”[6]13。《一日三秋》三千年的故事时间,如何浓缩于一部不到20 万字的文本里,确实考验作家的艺术功力。相较于四卷本近200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话语喧嚣、缠绕、歧义丛生,《一日三秋》采用了极为简洁而又极具穿透力的叙事。从叙事逻辑上而言,这种“立体极简主义”叙事需要一个结构或主题的锚点,锚定人物命运、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刘震云是结构方面的大师,在《一日三秋》的结构图式中,他将锚点选定为:笑话,从而将故乡延津的人伦、人心、情感、命运纽结在了一起。
一方面,“笑话”结构全篇,是文本的结构核心,在其辐射囊括之下,小说成为一个有机的叙述体。小说的前言:六叔的画。其中就有一幅画作——月光之下,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她的身边是一棵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的柿子,她就是误入延津去梦里找笑话的花二娘。另一幅画——饭馆里一人躺在桌下,众人围成一圈,桌上一只盘子里只剩一个鱼头似乎在笑。六叔解释说桌下躺着的人在吃鱼的时候听旁边的人讲笑话,结果被鱼刺卡死了,也是被笑话卡死了。简短的前言,里面的信息量却很大,尤其是里面有关延津笑话的讲述带有很多的暗示、提醒或旁敲侧击。前言是整个文本的总纲,纲举则目张,后面人物的命运、情感、故事则是对六叔画作的展开、阐释、缝合或想象。小说的第一部分:花二娘。花二娘在延津夜间潜入人的睡梦找笑话来抗衡三千年等待的孤独、内心的悲楚。这是一个凄美的传说,文本将花二娘找笑话嵌入延津当下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小说穿越现实叙事的壁垒,于是小说具有了一个魔幻性的框架。小说的第二部分:樱桃。这部分主要讲述樱桃三个阶段的生存状貌:演《白蛇传》中白娘子时的生活;嫁给陈长杰后的婚姻生活;死后的魂灵生活。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将自己活成了笑话,因此,笑话串接了陈长杰、李延生、樱桃以及延津其他人的生活、情感与命运。第三部分:明亮。这部分是小说中最长的部分,写了明亮“当年”“二十年后”“又二十年后”三个时期的生活,三个时期对应着三个不同的空间。明亮当年随着父亲陈长杰颠沛流离到了武汉,后来回到了延津,再后来因为妻子马小萌的事不得不再次出延津到了西安。这部分内容的结尾、落脚点仍然回到了梦里花二娘找笑话和明亮的劈头相遇,笑话作为结构的核心功能再一次显露无疑。第四部分: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该部分以极简主义的笔法,讲述了延津人的一句话笑话、花二郎被笑话卡死的经过以及作为魂灵的樱桃从河里上岸的时间地点。第五部分:《花二娘传》的开头。这部分以极为简短的几十个字,拟写《花二娘传》的开头,以影视剧本的跳宕、省略、极简等笔法回应、概括花二娘传的笑话内涵。它名为《花二娘传》的开头,以下则是空白和省略号,实际上花二娘的命运已经在前此的叙述中已经清晰完整地呈现了。从总体结构上而言,后五个部分就是对小说前言部分的展开,以“笑话”作为主导线索贯穿始终,是“笑话”在不同人、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演绎。
另一方面,“笑话”又是全文的思想核心,“笑话”既是笑书、又是哭书,更是本血书。“笑话”锚定的不仅是花二娘,也是延津百姓的人心、人伦、情感和命运。小说主要有这些人的命运:六叔和六婶、花二郎和花二娘、陈长杰和樱桃、李延生和胡小凤、李明亮和马小萌以及看相的老董、孙二货(作为人的孙二货和一条狗的孙二货)等等。《花二娘传》在司马牛看来是本笑书、哭书和血书,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更是如此,表面看似充满了笑话、风趣和幽默,有些情节、细节和故事还让人忍俊不禁,然读过之后细细品味,则充满了心酸、血泪和痛苦。《白蛇传》中的唱词“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是白娘子、许仙无可奈何、不知所措的生命喟叹和命运忧伤,也是传说中花二娘的命运写照,更是现实囿于各种困境、伤痛的延津人的千年一叹。他们在自己的生命路途上竭力挣扎、闪转腾挪,试图改变自身的命运,结果绝大多数人仍然把自己活成了笑话。延津世代流传的笑话,是多少延津人用生命堆出来的。小说中的六叔,想以自己的画,固定、展示、表现延津的生命笑话,结果自己死于心肌梗死或者说被花二娘的笑话给压死了,六叔死后,他的画作因为“无用”而被六婶付之一炬,化为漫天灰烬随风飘散。演《白蛇传》中白娘子的樱桃,嫁给了当年演法海的陈长杰,陈长杰爱说笑话,起初陈的能说会道让樱桃“滴滴”笑个不停,随后平庸、拮据、暗哑的生活让昔日的诗意荡然无存,因为“一把韭菜”所引起的纠葛,樱桃上吊自杀,陈长杰也因背负道德骂名带着儿子明亮远走武汉成了火车的司炉。李明亮因为和继母秦家英关系不睦离开武汉回到延津,寄养于李延生家里,陈长杰给养的断供不得不让明亮到“天蓬元帅”饭店去炖猪蹄。明亮与马小萌结婚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曾经在北京五年时间里卖身,后被人揭发闹得延津满城闲言碎语。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躲避人言的斫杀,李明亮和马小萌远赴西安,再次出走延津。即便后来在西安炖猪蹄炖出了一点名堂,他和马小萌的人生依然充满了憋闷、屈辱和伤悲,多数时间,李明亮和马小萌也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笑料,连带其儿子李鸿志也无法逃脱他们屈辱生活的阴影。瞎子老董一辈子靠算命看相维持生计,他算准了很多人的前世和今生,却没有算准自己,最终死于替人算命的中途,也是以自己的死构成了延津笑话谱系里的一个章节。当然,在延津,最具有笑话色彩的是穿越三千年等待夫君归来的花二娘,她或许不懂得或许不理会“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的现代爱情观念,把自己活成了望郎山。千年望郎不见,“望”郎山成了“忘”郎山,这也是花二娘津津乐道向延津人讲述的笑话,这个时候,花二娘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的絮絮叨叨,反复叙说,不正表征了自身命运已成千年笑话了吗?由此看来,笑话千百年来笼罩了延津人的生存史、苦难史、心灵史,既笼罩了过去,也覆盖着当下,是否笼罩着未来暂未可知。笑话穿越三千年历史时空,时间似乎凝固了,“笑话”成了“去时间化”的存在,成了延津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宿命。
《一日三秋》以“笑话”结构全篇,以“笑话”纾解生命的憋屈,以“笑话”象喻生命的历史与现实,以“失笑话,找笑话”编织延津人的人伦、人心、情感与命运,以特有的“说话”式的叙述推进故事的进展,“一句话逗一句话,一个事引一个事,好比坂坡走丸,银盘落珠,看着像是一点不费劲似的,就把这世上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个东西就嘟噜到一起了。”[1]1刘震云可谓眼光独具笔力老到,直抵故乡/乡土中国的生存肌理和文化心理岩层,开掘之深,用情之深已然非同凡响。
三、细微、日常又绵远、浩阔的民间叙事诗学
这里的“民间”具有多重意涵。其一是作家所持的民间性思想立场或价值倾向。其二是作品所描绘的民间生活内容。其三是文本所采用的民间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这多重的民间意蕴在《一日三秋》里面呈现为细微、日常而又绵远、浩阔的民间叙事诗学风貌。
陈思和曾将当代文学三分天下:庙堂、广场和民间。1980年代新启蒙/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人文主义逐渐式微,1990 年代多元化/碎片化/消费主义/世俗性/欲望化的来临,文学“民间”的声音逐渐凸显,这种声音迄今仍方兴未艾,具有持久的文学活力。90年代以来,“许多作品都带有了乡村民间社会的文化意蕴,民间文化形态不再在文本中以破碎的形式或者审美的结构性因素存在,而是有着独立的、文化的、精神的美学意义。”[7]76从写作立场而言,刘震云一直秉持着“民间”立场。即便是80 年代他创作的《塔铺》《新兵连》,依然可以看出“民间”的视角和倾向。《塔铺》是那个年代的高考政治经济学,小说以乡土的视角叙述高考恢复后一群复读生的心灵挣扎。《新兵连》也是从民间的视点聚焦一群农村新兵在部队庸俗化的众生相。《单位》《一地鸡毛》《官人》的新写实时期,所谓新写实,呈现的是小林一地鸡毛的生存主义和官场权谋的原生形态,仍然是民间性的审美发现。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或荒诞或反讽,传递的主要是民间的循环论历史观和历史认知。新世纪以来的《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摹写的是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乡土卑微者“拧巴”的生存与精神景观。《一日三秋》在一系列民间性写作的基础上,继续将民间的价值立场贯彻到底,这部长篇小说将时空拉得更远更久,以更为纯粹的“民间性”打量、勘察延津的历史与现实。小说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运动、标志性的历史时间节点是缺席的,或者说是刘震云有意避开的,由此小说呈现出一幅“去历史化”的民间生存图景。历史的内涵被极度压缩、简化甚至抽空,而鸡零狗碎的民间生活细节和场景被刻意放大和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说所营构的民间生活得以全面彻底地敞开,民间生活的意义也在叙事中被敞亮,不再是晦暗不彰的存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民间立场带有非启蒙的价值倾向,民间的生活是自在的自为的自足的,无需外部思想的介入和外部力量的拯救——刘震云向来也对精英启蒙持怀疑的态度。
民间生活场景与细节的细腻刻画,民间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的真实描摹,民间心灵隐秘与精神生活的深度挖掘,夯实了小说民间性的基础。《一日三秋》里面的细节、场景尽管没有《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密集和繁复,但依然是小说叙述的基础性内容。六叔和六婶貌合神离的关系就是在生活细节和行为中展露无遗的。六叔的画因为没有现实的功用而被六婶嫌弃,被认为是“那些破玩意儿”。可以想见,六叔和六婶在精神生活里是两个世界的人,六叔只能在画作里寄托自己的心灵追求。殷桃和陈长杰因唱戏而心生爱意,可惜他们的爱情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和日常生活的磨损,逐渐失去了诗意的激情,在生活的重轭之下,殷桃走向了绝路。陈长杰在武汉重组了家庭,并没有多少幸福可言,只不过延续流水般的日子,明亮和新家庭的隔阂疏离也是后来他离开武汉的重要原因。李延生在现实中也不似许仙的纯情,世俗性的生活不断损毁男人的尊严。他去武汉,也只能通过撒谎和借钱才能勉强完成不得已的心愿。明亮和马小萌在天蓬元帅饭馆的相识及其后续的婚姻生活,充满了多少现实的无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延津人生活的基本状貌,也构成了他们日常的心理现实。令人欣慰的是,延津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垮掉,而是在这般情形中负重前行,体现出民间生存意念的强大和生存意志的坚韧。
《一日三秋》的民间性还体现在文本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地方性、口语化色彩。“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首先是从如下两个方面开始的。1.对来自民间的口语、白话语言的重视。2.与重视民间语言相关的是始于1918年春的民间歌谣的搜集和整理。”[7]18可见,文学的民间性与民间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小说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了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直抵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做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8]366因此,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论上的,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建构生活、建构历史、建构世界,语言也建构人的存在命运。刘震云民间化的语言建构的是民间的生存世界和存在景观。首先是叙述语言的口语化,当然这也是刘震云一直追求的叙述语言风貌。从“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新兵连》的开头)到“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地鸡毛》的开头)再到“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再到《一日三秋》第一部分的开头:“花二娘是个爱听笑话的人。”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奠定了叙述的基本腔调和叙述风貌。之后的叙述,日常的生活、故事、人物和命运都在平实、素朴的语言中一一显现。小说中,延津的方言、俚语、俗语等地方性的话语经由刘震云的转述、化用或直接引用,平添了小说叙述的地域性特色。刘震云特别擅长“饶舌”,对一个细节或场景津津乐道或喋喋不休甚至东拉西扯,总让读者在他富有幽默感的叙述中兴味盎然。他在小说中还经常使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语言,如“一夜无话”“一路无话”“在下”“不在话下”等,这些叙述语言让小说在日常化基础上平添了些许古典白话的意味。小说中还大量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艺术,白描作为一种写景状物、写人叙事的手法,语言是简洁、素朴、传神且富有概括力的。小说对花二娘、樱桃、明亮等人命运的描写时,多处用了白描的手法。叙述语言体现了民间化口语化的特点,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更是带着延津地域性的民间色彩。小说人物的语言涉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别、情境、心绪以及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或者说话是小说基本的叙事动力。比如:《一日三秋》里面明亮和马小萌之间关于马小萌在北京卖身的那段对话;李延生到武汉见到陈长杰之间的对话;明亮和孙二货之间的对话;李延生和算命先生老董之间的对话;李延生与樱桃灵魂之间的对话等等。文本的叙述话语和人物对话潜入延津乡土卑微者的生活、人性、情感的底部,展示他们逾千年而不变的心理根基和人性底色。
刘震云的民间书写聚焦的是家长里短、从日常中打捞芸芸众生的命运故事,在一些生活细微处展开人物的遭际与心灵。这些细微、日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不是肤浅地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是以此为起点,绵延至历史的时空,穿越生死的界限,抵达了绵远、浩阔的审美境界。邱华栋认为:“这部小说正是在最为家常的书写中,呈现了人的生活的丰富生动和无尽的可能。刘震云的小说保持了他一贯的幽默感,在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保持了小说伟大叙事能力的尊严,呈现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价值。《一日三秋》在刘震云的作品系列里,是一部最新的杰作。”[1]1
四、传统性、乡土性与现代性叙事的嫁接与榫合
继《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出现的多处“喷空”场景后,《一日三秋》里面也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明亮和奶奶的“喷空”。“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出一个话头,另一个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1]53“喷空”需要情节故事搭建的逻辑连贯性,更需要高度的艺术想象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喷空”主要由牛国兴和杨百利共同完成,他们似乎像传统剧目二人转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奇思异想脑洞大开。《一日三秋》里面人物的“喷空”主要由明亮的奶奶主导,毕竟明亮年纪尚幼,还不具备完全的“喷空”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日三秋》视为刘震云个人性的叙事“喷空”,文本的叙述声音非常强大,极富艺术想象力,将传统性、乡土性、地域性的日常叙述和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叙事有机地嫁接与榫合,完成叙事的审美创构,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叙事走向世界性的根本路径。
前言中,刘震云的叙事意识非常明确:“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以日常生活为基调,把变形、夸张、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当作铺衬和火锅的底料……”[1]8这部小说具有张旭东所言的方法论上的形式实验意义。前言煞有介事地告诉读者,这部小说的写作是源于六叔画作灰飞烟灭所引发的作者触动和感悟,以小说的形式对六叔的画作进行复刻和还原。画作毕竟已经成了灰烬,因此小说的再次建构就带上了作者个人主观性的回忆,如此就形成了画里和画外的艺术张力。这部小说被称为现实魔幻主义,亦即在写实的日常叙事基础上,揉进大量的魔幻元素。这种写法在当代文学中颇为常见,多数时候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吗?《爸爸爸》《白鹿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里面融入魔幻性因素,《一日三秋》则是一个魔幻的框架,即花二娘在延津找笑话的传说,在传说的框架下推衍延津百姓的冷暖人生。在讨论当代先锋作家的时候,刘震云似乎不在重要先锋作家之列,而实质上刘震云无论在思想题旨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很多时候都是极为先锋的。他的“故乡”系列和《一腔废话》就是非常典型的先锋实验文本。只不过这些先锋文本生不逢时,没有受到前期先锋小说的广泛关注,再加上刘震云深厚的写实功力与成就,导致他的先锋性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
《一日三秋》和既往的“故乡”系列、《一腔废话》叙事狂欢的先锋性有显著区别。小说虽然是一个魔幻性框架,但小说的细部内容仍然是写实的日常。刘震云所谓的变形、夸张、神神鬼鬼、后现代、穿越生死的“超现实主义”都被融入延津人的凡俗生活之中。除了上述画里画外和魔幻性的传说框架之外,小说还将《白蛇传》的戏里人生与陈长杰、殷桃、李延生的现实人生进行互文、对照,彼此镜像。戏里是无可奈何的人生,现实也是憋屈烦闷的生活,还导致了殷桃的上吊自杀。小说将中国传统的戏曲有机地融入小说叙述,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创构,还是主题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小说里面多处将戏文代入现实生活,有关“咋办咋办”“奈何奈何”戏文段落的多次出现,就是以反复来强化小说中人物的现实处境。殷桃的鬼魂附身于李延生,由此产生的命运变化和故事情节可谓小说中极为精彩的神来之笔。李延生身体的不适源于殷桃鬼魂附体,于是李延生带着殷桃的灵魂登上了赴武汉寻找陈长杰的列车。李延生返回延津后,留在武汉的殷桃灵魂因干扰陈长杰后妻的生活而被诅咒并被马道婆针扎,灵魂遭受巨大的痛苦,后来在儿子明亮解救下,投入江水中不知去向。小说后文才接续前文,讲述了殷桃在宋朝的江西九江上了岸。民间一直有鬼魂附体的说法,刘震云巧妙地将民间说法化为叙事的结构性、主题性因素,进一步打通了现实、想象、虚幻之间的叙述壁垒,实现了对生死的穿越。传说中的花二娘是神,《白蛇传》中的白娘子是修道成仙,殷桃的魂灵是鬼,小说由此实现了神(仙)、人、鬼三界命运的交汇与融合。当然,在三界之中,人是小说故事的核心,神、鬼的命运也是因为现实中人的命运而引发的:花二娘是因为在延津漫长等待找不到花二郎而化作望郎山,白娘子是因为爱许仙激怒了法海被压在雷锋塔下,殷桃是因为和陈长杰生活“没劲”而撒手人寰。小说形象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因果循环。
不仅是神仙、人、鬼之间的命运纠葛,小说还叙述了明亮和一条名为“孙二货”的狗之间的关系。在西安的初期,由于孙二货的欺压,明亮和马小萌只能离开大市场另寻生路,到偏远的地方炖猪蹄开饭馆。由于对孙二货的憎恨,明亮把一条不离不弃的狗命名为孙二货。正是这条狗带给饭馆源源不断的客源拯救了明亮,且在之后的几次危险中,也是这条狗的及时预警而避免了饭馆的灭顶之灾。小说写出了明亮对狗由开始的厌恶到最后的深情,在人情淡薄的现实中,狗反而更加忠实于主人,更加诚实守信,狗道主义反证了人世间的世俗虚伪。小说里面的瞎眼老董,在现实中看不见真实世界,反而成就了他对世界的“洞见”,他是算命先生,处在阴阳的临界点上,能够打通阴阳的两隔。小说在很多地方都讲述了老董的算命。算命在乡野民间是常有的事,当现实的困境无法排解的时候,百姓只能把命运寄托给“胡说”“算卦”“占卜”,试图以此洞悉命运的真相,提前规避命途的凶险。《一日三秋》篇幅有限,却给了老董的算命较多笔墨,还写到了化为萤火虫的马道婆,写到了人的六道轮回的转世,这些都是乡野民间文化习俗的本相,这样的叙述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在乡野的生态,给人一种真实感,同时也让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增添了一种宿命的意味。在叙事上,老董的“直播”算命,依靠张天师打通阴阳,也让文本更增添了魔幻的色彩。在结构上,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也具有十足的刘氏风格。前言、附录、某一章或某一部分仅用一两句话构成、二十年以后、又二十年后形成的叙述跳跃和中间的长时段留白等,或许是受到影视创作的影响,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文本特别喜欢采用影视剧本的一些技法。这些结构方面的营构让叙事跳宕不羁充满张力,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平铺直叙,充分体现了文本结构艺术的魅力。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刘震云《一日三秋》在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立足于传统性、乡土性的日常生活叙事,以创作主体“喷空”般的艺术想象力将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梦境、传说和戏曲、神界与鬼界、画里与画外等多重艺术空间糅合在了一起。在文本里,读者既能领略到极为地道的传统、乡土、民间、地域的中国气象、中国味道和中国生活,也能感受魔幻、穿越、变形等现代、后现代的叙事风貌。
综上所述,从《塔铺》起,刘震云就开始了“延津叙事”的文学书写,中间经过《温故1942》和“故乡”系列的持续性发力,之后的《我叫刘跃进》尽管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在北京,但仍然是延津人的思维、性格和文化心理。《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乡村卑微者精神心理空间的勘探展示了文本“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一日三秋》依然是对故乡延津情有独钟的叙事,它比《一句顶一万句》更为简洁灵动亲切,更具有艺术的想象力,于循环的人情世故中体察最根部的人性真相、生命经验和情感心理。王干认为“这部小说也是刘震云多年小说创作的结晶,能读到《塔铺》《新兵连》生活的原生态,也能读到《故乡天下黄花》《温故1942》的苍凉和历史的痛感,还能读到《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峭拔。”[1]1诚然,《一日三秋》是刘震云“延津叙事”合乎逻辑的发展,小说以“说话”为叙事动力,以“笑话”为结构中心,以魔幻为叙事框架,以日常生活为叙述根基,是中国当代新乡土叙事崭新的创造,文本接通了中国古典、民族、乡土与现代、世界的通道,展现了当代中国叙事、中国小说的应有水平。小说以智慧和幽默,改变了人们对当代文学刻板、沉闷的印象,小说以其丰饶与简洁、现实与寓言、荒诞与真实对乡土生活和乡土灵魂作了复杂、透彻、深刻、生动的展示,刘震云已然成为卓越不群的叙事艺术家和叙事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