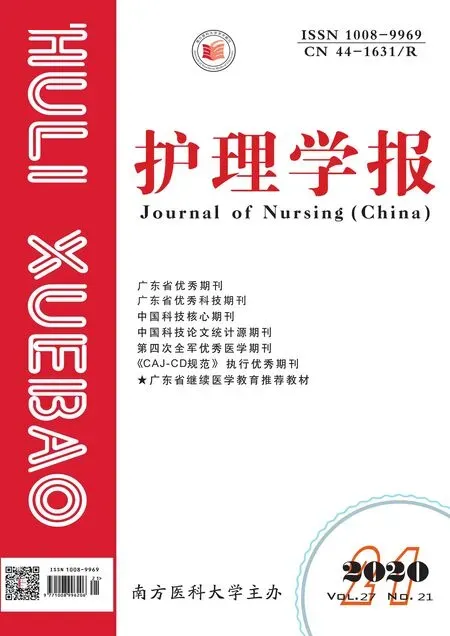儿科ICU 护士肠内营养相关决策行为的现况调查
2021-01-14胡家杰李梅温尊甲严萍曹金金徐邦红徐京任蕾
胡家杰,李梅,温尊甲,严萍,曹金金,徐邦红,徐京,任蕾
(1.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210008;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a.护理部;b.外科重症监护室;c.新生儿外科;d.消化内科;e.心脏重症监护室,江苏 南京210008)
有研究报道, 危重患儿中度至重度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是20%~53%[1]。 营养不良不仅影响生长发育还可延长患儿机械通气和住院时间[2]。 护士作为与患儿接触最为密切的群体, 且是肠内营养的直接执行者, 在营养支持及肠内营养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肠内营养相关知识和决策行为是成功实施肠内营养的关键, 若操作不规范可能造成患儿受伤,甚至导致肠内营养相关并发症、延长患儿住院时间、引发营养不良等不良结局[3-4]。然而国内针对肠内营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提高肠内营养耐受性,对儿科ICU 护士在肠内营养实施过程中的行为调查较少,本研究拟采用自行设计的儿科ICU 护士肠内营养决策行为问卷对儿科ICU 护士展开调查,旨在了解儿科ICU 护士的行为,以期发现儿科ICU 护士在肠内营养实施中的薄弱环节, 为制定肠内营养相关知识的培训、 促进危重患儿肠内营养的管理与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南京市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 儿科重症监护室(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外科重症监护室(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SICU)和心脏重症监护室(cardiac care unit,CCU) 的护士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1)ICU 注册在职护士;(2)正确理解本调查问卷内容含义;(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此项调查。 排除标准:(1)非ICU 护士;(2)在ICU 工作未满1 年;(3)进修、其他普通科室轮转、不在岗护士或实习生。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编制,包括性别、科室、工作年限、职称、学历、是否是专科护士及类别。
1.2.2 儿科ICU 护士肠内营养决策行为问卷 文献检索、 参考国内外危重患儿肠内营养实践指南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5-7],结合临床实践编制问卷条目与供参考选项,随后进行2 轮专家函询(专家遴选标准:从事儿科急危重症临床或儿科护理工作10 年以上,包括:ICU 主任医师2 名,临床资深护理管理者1 名,ICU 护士长2 名,共5 名),经专家审阅后,根据专家意见对问卷条目进行修订、完善,将不合适条目“您检查胃残留的目的和意义是?”“如果不常规监测胃残留,您认为有哪些不妥?”等条目删除,形成最终版调查问卷,共21 个条目。 问卷内容包括肠内营养实施流程的认知及相关护理措施 (7 个条目)、喂养不耐受(feeding intolerance, FI)的监测(7 个条目)与喂养不耐受处理(7 个条目)3 个方面。正式发放问卷前,随机抽取与本研究纳入标准一致的20 名护士进行预调查,测得问卷Cronbach α 系数为0.768,重测信度为0.817,专家函询测得问卷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I-CVI)均高于0.8,问卷总的内容效度(S-CVI)指数为0.933。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将完成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编辑录入,形成电子版问卷,并经网站同意后生成问卷二维码。 由各病房护士长经由微信转发二维码,采用线上填写的方式,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质量, 限制每个IP 地址只能填写1 次,且每份问卷作答时间控制在30 min。 共发放问卷177份,收回142 份有效答卷,有效回收率为80.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 录入及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S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参与调查的142 名儿科ICU 护士,科室分布:NICU48 名(33.8%),PICU32 名(22.5%),SICU26 名(18.3%),CCU36 名(25.4%);男性11 名(7.7%),女性131 名(92.3%);职称分布:护士29 名(20.4%),护师98 名(69.0%),主管护师及以上15 名(10.6%);ICU 工作年限:1~3 年40 名 (28.2%),3~5年35 名(24.6%),6~10 年37 名(26.1%),>10 年30 名(21.1%);文化程度:大专14 名(9.9%),本科及以上128 名(90.1%);专科护士12 名(8.5%),包括10 名危重症专科护士、1 名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和1 名营养专科护士。
2.2 儿科ICU 护士肠内营养实施流程与态度情况142 名儿科ICU 护士,熟知本科室肠内营养实施与护理流程的仅有81 名(57.0%);且仅有10 名(7.0%)护士了解并能说出本科室的肠内营养指导指南;67名(47.2%)护士会对入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评定,其中根据患儿病情动态评估的仅有13 名(19.4%),仅仅入院时评估的有13 名(19.4%),入院和出院时评估的有41 名(61.2%);营养评估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测量体质量(67 名,100%)、测量皮下脂肪(20 名,29.9%)、营养风险筛查量表(13 名,19.4%);胃管留置长度和胃管位置核实方法情况见表1。

表1 儿科ICU 护士胃管留置长度与位置核实方法情况
2.3 儿科ICU 护士对喂养不耐受监测现况 142名儿科ICU 护士,仅有28 名(19.7%)熟知本科室喂养不耐受的判断标准; 护士采取的喂养不耐受判断方法:胃残留(gastric residual volume,GRV)(135 名,95.1%),腹痛、腹胀(130 名,91.5%),恶心、呕吐(106名,74.6%),肠鸣音(46 名,32.4%),腹泻(60 名,42.3%),根据经验判断(16 名,11.3%);130 名(91.5%)护士每次喂养前都会评估患儿的胃残留, 采用最多的评估工具是注射器(140 名,98.6%),其次是胃肠减压装置(77 名,54.2%)、重力引流(17 名,12.0%)、超声(6名,4.2%);评估胃残留时采取的体位护士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最多的是半卧位(97 名,68.3%),其次是仰卧位(48 名,33.8%)、右侧卧位(40 名,28.2%)、左侧卧位(33 名,23.2%)、俯卧位(1 名,0.7%);当被问及不常规监测胃残留的态度时,105 名(73.9%)护士持有反对态度,但有89 名(62.7%)护士认为有必要提高现有胃残留异常阈值。
2.4 儿科ICU 护士针对喂养不耐受相关症状的处理措施现况 142 名儿科ICU 护士,当患儿出现胃残留时,86 名(60.6%)护士选择全部丢弃胃残留,仅有7 名(4.9%)护士选择根据其颜色和量决定相应处理措施;仅有10 名(7.0%)护士总是采取非药物干预方式(减慢喂养速度、非营养性吸吮、腹部按摩、体位管理等)预防或减少喂养不耐受的发生,经常39名(27.5%),有时52 名(36.6%),偶尔22 名(15.5%),从不19 名(13.4%);其他喂养不耐受症状的处理措施情况见表2。

表2 儿科ICU 护士针对患儿喂养不耐受症状处理情况
3 讨论
3.1 儿科ICU 护士对科室肠内营养实施与护理流程掌握程度偏低,对危重患儿营养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科室对相关知识的培训有待加强 本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57.0%、7.0%的护士了解自己所在科室EN 护理流程以及依据的指南。 另外,喂养不耐受是危重患儿常见的胃肠道功能紊乱, 不仅影响EN 的进程与疾病的恢复, 还与危重患儿临床结局与预后密切相关。本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9.7%的护士熟悉本科室喂养不耐受的判断标准。究其原因:(1)83.3%的护士的职称是护师及以下、ICU 工作年限≤3 年,其入职时间短,职称多为初级职称,工作重心过多放在规范操作技术与保证患儿安全上,工作经验及资历尚浅;(2)科室的培训大多集中在常见专科疾病的诊疗与护理,对肠内营养相关知识的培训力度与深度不足,建议针对性加强对低年资护士危重症患儿肠内营养相关知识的培训与考核。 营养风险筛查与评定是及时发现并预防患儿发生营养不良的关键,本调查显示52.8%的护士没有对本科室的患儿进行营养评估与筛查,均匀分布各个科室,分析原因可能是营养风险筛查与评定的方法有多种,实验室指标也是方法之一[8],由于患儿入院后常规进行血生化、蛋白、微量营养素等检查,若无特殊医嘱,护士运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的频次较少,但也有19.4%护士通过测量体质量和使用STRONGkids 营养筛查量表对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这些护士大多是职称较高、工作年限较高的护士,其对危重患儿营养状况更关注。 李菁菁等[8]指出住院患儿营养状况的监测应是动态的,以便及时发现营养不良,但本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9.4%的护士会动态评估患儿的营养状况,究其原因: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以护理人员为主导、多学科团队协作的“营养风险筛查-营养评定-营养干预-营养随访”的临床路径,护士在营养风险筛查中的关键角色和作用未被完全开发[3],建议加强营养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的制度充分发挥营养专科护士以及护理人员在营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3.2 在胃管护理方面,儿科ICU 护士欠缺对新方法的学习与探索 提高留置胃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成功实施肠内营养的前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鼻-耳垂-剑突和前额发际正中-剑突测量方法留置胃管的长度过短,肠内营养液容易通过胃管侧孔流出,刺激食管引起胃食管返流等不良反应,不宜再应用于临床[9]。 因此,国内外针对胃管留置长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研究发现鼻尖-耳垂-剑突与脐中点这一方法比传统的置管长度更长、喂养相关并发症更少[10],并被推荐在临床广泛应用,但本调查显示仅有14.8%的护士选择鼻尖-耳垂-剑突与脐中点这一方法置管与其他改进的方法。 另外,胃管末端处于正确位置也是顺利开展肠内营养的关键,文献[10]报道传统的听诊、水碗检查、回抽胃液的结果并不准确,如:胃管末端的侧孔没有完全开口于胃体部时也能听见气过水声、 检查气泡时也没有气泡逸出;侧孔未在胃液中或患者禁食时间长、胃液分泌量过少时不容易回抽出胃液,此时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X 线是核实胃管位置的金标准[11],但由于医疗设备等的限制加上X 线具有辐射, 因此临床上难以将X 线作为常规监测手段。 现有研究表明,超声是辐射较小、实施更简便的核实方式[12],但仅有2.8%的护士表示将超声运用在胃管核实方面,可见超声虽然已在临床应用,但是受到设备及技术的限制,临床上仍将传统方法作为判断标准,这可能降低肠内营养的效果, 甚至引发因胃管异位导致的误吸、胃食管返流、食管穿孔等严重并发症[10]。 因此,鼓励临床科研工作者探索更简便有效的方法替代传统方法, 从而提高肠内营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3 儿科ICU 护士过度“依赖”胃残留对喂养不耐受的预测作用且监测工具相对滞后 在喂养不耐受的监测方面, 被护士提及最多的监测指标是胃残留(95.1%),这与Parker 等[13]的调查结果相似,高达97.0%的NICU 护士都常规进行胃残留的监测,但是,胃残留受体位、监测工具等因素的影响[14],若测量不准确则影响对喂养不耐受的判断,研究指出:胃残留与胃排空的时间不能作为监测喂养不耐受的敏感指标[6,15],只有当患儿出现胃肠道其他症状或达到最小喂养量时才辅以监测胃残留。 Parker 等[13]的研究还显示不常规监测胃残留患儿的体质量增长更快、 住院时间较短, 有助于减少肠外营养的使用时间、节约医用物资。 尽管如此,本调查中仍有73.9%的护士反对去除胃残留的常规监测, 虽然现无证据证明不常规监测胃残留能产生更大益处, 但在Parker 等[16]的另1 项研究中发现常规监测胃残留的一组患儿表达更高水平的钙结合蛋白S100A12 水平,这是一种炎性反应蛋白,与喂养不耐受与肠道炎症疾病如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生有关, 并且不常规监测组没有引起胃肠道激素分泌的减少和喂养不耐受的增加。 乐观的是,虽然临床护士仍将胃残留作为判断喂养不耐受的主要指标, 但62.7%的护士认为有必要提高现有胃残留的阈值, 只出现少量胃残留则减少喂养量或中断喂养是不正确的,这与Emami 等[17]的看法相似。 规范肠内营养的实施,减少肠内营养中断次数提高肠内营养达标率是改善危重患儿营养状况的关键[18]。 如果必须监测胃残留,Uysal 等[19]指出测量必须精准,因为这会影响对喂养不耐受的判断与处理。 闪烁扫描术是目前监测胃残留的金标准,但是ICU 行间歇喂养的患儿居多且设备要求较高,其实施难度较大[20]。 郑伟等[21]指出超声监测可减少医护人员体液暴露的危险,测量结果也较准确,是实用性较高的方法。 但本研究中仅有4.2%的护士选用超声,高达98.6%的护士选择注射器,由于注射器的型号、奶液的温度、粘稠度均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22],因此注射器监测胃残留的准确性需谨慎对待。
3.4 临床实践中目前还缺乏明确统一的护理决策及流程指导护士应对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症状,且ICU 护士工作主动性有待提高 目前国内外针对胃残留的丢弃还是回输开展大量研究, 吕天婵等[14]认为胃残留中含有消化液以及电解质, 如果丢弃可能加重喂养不耐受的症状,但在1 项Meta 分析[23]中没有发现回输胃残留产生更有益的作用, 因此丢弃还是回输需要根据临床具体情况个性化处理。然而,本研究中60.6%的护士选择全部丢弃, 仅有4.9%的护士选择根据胃残留的量和颜色决定, 可见大部分发生胃残留的患儿的胃内容物被丢弃, 这可能导致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增加患儿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本研究还发现当患儿在24 h 内呕吐次数<2 次、 腹泻次数<4 次时,10.6%~23.2%的护士会遵医嘱给予暂停喂养或胃肠减压,但Eveleens 等[24]通过综合31 项原始研究所提出肠内营养喂养不耐受的诊断标准中,24 h内呕吐次数<2 次、 腹泻次数<4 次不能轻易诊断为喂养不耐受,且呕吐、腹泻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若不是病理因素所导致,轻易中断营养可能降低早期全肠内营养达标率,从而延长达到全肠内营养的时间。另外,腹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常见症状,1项研究设定腹围增大超过原有腹围2 cm 以上视为异常,其结果显示腹围测量代替胃残留监测可缩短达到全肠内营养的时间, 且没有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是较好的监测指标[25]。 但本调查结果显示91.5%的护士表示仅当患儿腹胀时才会测量腹围,且对腹围异常值的认知各有不同,鉴于国内外也暂无统一的阈值,建议临床科研工作者将腹围与喂养不耐受诊断金标准进行大样本的一致性评价以探究合适的腹围截断值,指导临床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腹胀不能作为判断持续正压通气患儿发生喂养不耐受的指标,因为持续正压通气可减少喂养前后肠道的血流量而导致腹胀[6]。 现有研究表明:非药物干预方式(减慢喂养速度、非营养性吸吮、腹部按摩、体位管理等) 可有效减轻及缓解喂养不耐受的发生与发展[26-27],护士可作为主导者,但本研究中仅有7.0%的护士总是采取非药物方式减少喂养不耐受的发生,高达13.4%的护士从不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喂养不耐受的发生, 其中NICU 的护士占有47.4%(9/19),PICU 占26.3%(5/19),SICU 占5.3%(1/19),CCU 占21.0%(4/19)。 NICU 的占比最高,分析原因:(1)本院NICU 收治危重新生儿病情变化快、抢救工作及治疗措施频繁导致护士工作量大,用来预防和减少喂养不耐受的时间较少;(2)ICU 是护士产生职业倦怠的高发科室,是工作积极性降低的根本原因。 建议管理者根据本科室的特点制定合适的培训模式和排班计划、鼓励护士进行碎片化时间管理、优化科室奖惩制度等调动ICU 护士学习和工作主动性,从而加强对喂养不耐受的护理干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致谢]诚挚感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明兄护士长、戎惠护士长、沈飞护士长、吴龙艳护士长、张少华护士长、魏莉护士长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