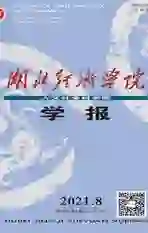从“强攻式传唤”看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2021-01-13谭耿
谭耿
摘要:2020年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要求实施的第五个年头,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和公信力不断得以提升,法治公安建设初显成效,但近年来陆续曝出的几起涉警事件,顿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强攻式传唤”为切入点来分析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自己的思考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全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执法规范化;法治公安;公安传唤
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这表明了我国公安机关全面深化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公共安全服务和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自其实施以来,各地公安机关纷纷结合自身特点出台了丰富多样的举措,执法规范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新时期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在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检验时,各种执法问题暴露无遗,从贵州陆远明事件便可见一斑,民警凌晨“强攻式传唤”被打伤,再审时袭警父子被改判无罪。近些年,诸如此类的事件频发。打铁还需自身硬,说到底还是部分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对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地位和重要性认识不足,运用执法规范化建设基本原理解决具体执法突出问题的能力和本领不够。与此同时,相关的执法规范、执法制度和执法机制还存在一定不完善的地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各种非规范性执法行为也长期存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绝不是一纸空文。新时代公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既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关键性课题,这需要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准绳,推动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公安传唤与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公安传唤及相似法律措施
公安传唤是指公安机关通知违法或者犯罪嫌疑人于指定的时间、地点到案接受调查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根据所涉案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治安传唤、刑事传唤和拘传。刑事传唤针对的是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而拘传通常针对的是经合法传唤拒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采用。治安强制传唤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无正当理由而不接受传唤或逃避传唤的违反了治安管理的相关嫌疑人,其手段主要是采取强制性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治安强制传唤跟拘传不同,它是一种附属于治安传唤的强制措施。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以及《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等法律法规还规定了继续盘问、约束和强行带离等多种法律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其限制人身自由并带离的强制手段和传唤特别是强制传唤非常相似,所以常有实际部门在工作中产生混淆。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内涵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安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它主要是强调公安执法者要按照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总要求,将一切执法行为都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即,将公安执法工作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行使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具体而言,是指公安机关和警務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预先设定的模式、程序和规则,使一切警察权力行使能够遵循法律程序,同时,且警察权力行使也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受到相关监督制约机制的制约和监督,从而达到严格、公正、文明、理性的执法目的。质言之,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就是公安机关执法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体系之内行使自身的权力,从而将公安执法活动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渠道,以实现公正、文明、严格、理性的执法目标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总目标为提升执法能力和公信力,包含执法理念端正、执法主体合格、执法制度健全、执法行为规范、执法监督有效等政策目标体系。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则主要包含五个方面:执法行为规范化、执法保障规范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质量和效率考核规范化以及执法监督规范化等。
二、对“强攻式传唤”的反思
(一)“强攻式传唤”的典型案例
“强攻式传唤”作为一种不规范不科学的传唤形式在公安执法工作中长期存在,其最典型的案例是1998年发生于贵州的陆远明事件。此一事件发生于1998年11月9日凌晨1时的贵州桐梓县,因陆远明涉嫌扰乱机关工作秩序,桐梓县公安机关派民警前往其家中传唤,陆远明以时间太晚为由拒绝开门,并表示天亮再说。传唤民警向上级反映了相关情况,得知情况以后,副局长带领增援民警赶到,并下发了“强攻”命令,民警利用消防车架设云梯的方式强行进入到陆远明家中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在民警“强攻”期间,陆远明父子用木头和砖头作为武器对强攻民警进行了还击。这一袭警案件于1999年2月12日开庭审理,并最终判决陆远明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一审判决后,陆远明父子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同年4月29日,遵义市中院二审宣判维持原判,陆远明父子继续上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最终于2017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院宣判陆远明父子无罪。
(二)“强攻式传唤”与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因而必须要走稳走扎实,切不可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传唤又是众多案件的起点,因而在公安工作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大局,亟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强攻式传唤”是当前公安传唤不规范不科学的突出表现,短期上讲它阻碍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长远来看它会有损法治的权威,破坏和谐的警民关系,是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道路上的绊脚石,而贵州陆远明事件正是公安机关“强攻式传唤”的典型代表,此案虽已告一段落,但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通过对这一案件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检讨,我们发现了当前公安传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可以为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1.传唤理念错位能力欠缺
公安执法理念主要是指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为民理念,这一点在贵州“强攻式传唤”一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后续相关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民警在传唤执法过程中的确存在违法情况,不仅传唤时限上存在漏洞,而且在传唤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必要限度,这些问题背后展现的还是我们部分民警执法理念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模糊甚至淡忘,其结果必然是自食恶果。执法质量是公安机关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传唤执法质量的提高有赖于传唤执法能力的提升,“强攻式传唤”反映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在执法能力和水平上还有很大欠缺,一方面,“在法律真空中走钢丝”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公安机关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外,许多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消极懈怠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许多新时代的先进技术资源在警务工作中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应用,这些都阻碍了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的步伐。
2.法律法规滞后,运行机制不健全
法律是行为的先导。当前“强攻式传唤”等各种执法问题出现的根源还是在于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这就给执法者和执法对象在实践工作中带来了诸多困扰。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法律条文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其必须保证基本的明确性,不能含糊其词。现行法律法规只是对传唤最为基本的问题进行了规定,然而对传唤的法律目的即配合调查,时限,例如对传唤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进行未作规定,对象,如对证人和受害人能否适用,手段即何时何种程度为法律所认可的必要限度,对普通传唤和治安强制传唤与刑事拘传的区分等问题也缺乏明确的规定。另外,当前公安传唤还存在着执法环节不规范、民警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严重违背了“程序正义”之司法理念,因此亟待规范。
3.传唤权缺乏必要保障
“强攻式传唤”这种传唤执法乱象在当前警务工作中仍然有其存在的土壤,其原因就是当前公安执法活动的保障效能明显弱化,这在主体上主要表现为对执法者执法权益的保障特别是对执法相对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相对不足;在内容上尤以法律救济的缺失最为严重,除此之外,在基础建设以及舆论导向等诸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公权力相对于私权利处于强势和支配地位,因而私权利常常受损,司法实践中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贵州陆远明事件折射出来的就是当前公安传唤权力运行机制中对传唤相对人的权利保护的相关内容十分稀缺,被传唤人权利极易受损,且投诉无门。
三、深化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对策
(一)提升公安传唤能力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根本点是提升公安执法能力。张伟珂、李春华等人在其文章《法治公安视域下公安执法规范化实证研究》(2015)中进一步将公安执法能力划分为规范认知能力、规范自觉能力和规范处置能力三大领域,并认为规范认知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环节,因此提出应当完善警察的录用机制并规范培训机制,以此来提升警察的规范认知能力的结论。据此,公安传唤能力提升也可以参照这种思路,在招录机制方面,一是公安机关可以建立以公安院校毕业生招录为主、社会招聘为辅的招录途径,并有针对性地提高传唤相关知识点在招警考试内容中的分值,引起足够重视。在职业培训方面,要着力加强传唤执法专项培训,增强基层民警依法进行传唤的能力,同时针对当前传唤执法的薄弱环节即传唤手段粗暴、时间上的随意性等问题,更要突出执法为民理念在传唤培训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制定公安传唤内在行为规则,营造良好的警营非正式文化氛围,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在每一位民警的心中留下烙印,让公民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此外,身处如今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警务工作水平的高低与其信息化程度日益紧密,这给我们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带来启发,即必须不断提高公安传唤的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促规范化,同时不断拓展科技在公安传唤中的应用空间,多向科技要警力,让公安工作永葆时代活力。
(二)推动公安传唤权责明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政府行政的权力清单。对警务工作而言,这种权力清单尤为重要。推动公安传唤权责明晰化,必须坚持依法进行,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让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在法治的康庄大道上稳步运行。
1.准确定位传唤法律属性,完善传唤运行机制
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首要任务是做到有法可依,即在现行关于传唤的法律框架下,重新定位传唤的法律属性,研究细化相关法律对于公安传唤的目的、对象、时限,手段以及普通传唤和强制传唤与拘传区分的规定。在此,我们还可以借鉴外国警方关于传唤的一些先进经验,“为实现侦查的目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但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不得进行强制处分。”这是日本警方对传唤的经典表述,意即自愿同行,即基于侦查上的必要性在征得被嫌疑人或者参考人的同意的情况下,要求其前往一定场所,这给我们如何在立法中严格把握强制传唤和拘传的启动条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治安强制传唤和拘传二者涉及警察强制力的使用,因而极易对传唤对象的人身权利造成损害,为进一步约束这两种特殊的传唤行为,我们可以考虑将强制传唤纳入行政强制的范围,与拘传一并可以被诉讼,进一步完善警察出庭应诉制度,同时,在当前法律制度框架下,增强公安法制部门在传唤执法复议中的职能作用,这样便实现了规范公安传唤行为严谨和高效的双重价值。与此同时,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还要坚持执法必严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传唤主体责任,健全传唤运行机制,严格依法、依规行使权利、履行责任,从而确保公安传唤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2.加強对传唤过程的监督和制约,形成规范传唤的外在压力
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还要做到违法必究,具体来说一是要对现有传唤监督机制进行系统化的流程再造,发现问题并及时予以完善;二是回归法制部门过程监督本位,探索建立公安法制部门的传唤类型化监督机制,突破既往只注重结果审查这一监督弊端,加强对传唤执法过程的监督检查;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传唤执法行为的监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制约体系。健全的监督机制离不开完善的责任追究和考评机制,否则监督便是纸上谈兵,为此我们应当健全传唤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程序,实行执法质量终身负责和责任倒查问责制,并优化传唤效果考评流程。
(三)强化公安传唤执法保障
落实执法保障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即执法维权、基础建设、舆论导向。首先,对执法者和执法相对人的保障是一体两翼的事,我们应该努力去调节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强弱不平衡、不对等状态,因而执法维权必须使二者尽量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在具体救济时又要兼顾实体救济和程序救济。在实体救济方面,将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和公安内部自我监督结合起来,充分保障被传唤人的权利和警察正当传唤权;在程序救济层面,凡是非法传唤后经过调查获取的言辞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予以排除,并且不得作为后续追责的依据,同时,对于警察的正当传唤行为,应当在制度设计上探索适当可行的自我救济途径,两种救济手段同等重要,切不可偏废。其次,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软硬件设施建设双管齐下。最后舆论导向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公安执法环境,这同和谐社会建设一脉相承,为此我们要加强公安传唤相关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为公安传唤规范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伟珂,李春华.法治公安视域下公安执法规范化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4):114- 124.
[2]姚占军,程华.法律视角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1):91- 96.
[3]易继苍.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述评[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1,(1):22- 27.
[4]赵志新.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改进措施建议[J].公安研究,2010,(2):59- 62.
[5]林水湖,林光辉,洪超明.关于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认识与思考[J].公安研究,2009,(2):51- 54+74.
[6]贺小军,朱建,朱丹妮.法治公安建设:1978- 2018[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4):60- 63.
[7]岳光辉.治安传唤的法律适用[J].河北法学,2002,(1):83- 85.
[8]李小强.治安传唤中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J].江西公安專科学校学报,2003,(6):45- 46.
[9]马方.刑事传唤制度刍议[J].人民检察,2005,(23):40- 41.
[10]黄文忠.正确认识刑事诉讼中的传唤措施[J].中国检察,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