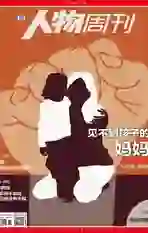张律电影里的人、空间、情感以及白日梦
2021-01-13DLL
DLL

在今年平遥国际影展作为开幕影片首映的《漫长的告白》(2021)是张律自2000年当导演以来第一部商业性质的、有上院线计划的华语电影。如果没有发行方的参与,这部电影本来叫《柳川》。原片名非常张律,此前他90%的电影作品都以故事发生地为片名,比如《重庆》《豆满江》《庆州》《福冈》。
《漫长的告白》主体部分拍摄于柳川,一座日本小城。电影主题提炼起来会很俗套:一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中年男人要去看身在异国的初恋,他叫上自己已婚的哥哥一起出发,哥哥是自己那位初恋的前男友。
三人或多人同游,出游的冲动来自对近二十年前感情的无法释然,这个故事模式张律很喜欢。他曾调侃这就是“陈词滥调的爱情故事”。《庆州》(2014)有两男一女在庆州王陵同游。《咏鹅》(2018)的男主角和前辈的前妻到群山旅游,和一个中年民宿老板又发生故事。《福冈》(2019)里一对师兄弟多年前因为喜欢上同一女生而分道扬镳,人到中年时大学的记忆再度来扰,从首尔到福冈,两男一女展开忆旧。《春梦》(2016)原本的片名就叫《三人行》。张律在采访中说过,他拍着《三人行》想,这是在干嘛,是做梦吗?“后来完全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一步一步往那里去。”这个回答用来解答部分观者对《漫长的告白》逻辑上的疑惑也行得通。立春和立冬(分别由辛柏青和张鲁一饰演)人到中年,往昔回忆造访他们,他们不由得前往柳川。
《春梦》的女主角在韩国水色驿开一家酒铺,日常和三位爱慕她的男人聊天。《漫长的告白》中也有非常类似的场景:三个男人分别俩俩询问、确认过对方是否对女主角(倪妮饰演)有感情。
如上所述,《漫长的告白》在各方面都与张律以往电影一脉相承。
张律出生在吉林延边,祖辈是韩国移民,他读延边大学,后来又到北京生活,到韩国教书。由于个人复杂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他的电影主题常常关乎乡愁、在外游荡,以及追寻身份认同的执着(或展现这种追寻的失败)。他的第一部短片《11岁》(2001)里就表现了初到边境的小男孩如何不见容于当地的同龄人团体;《芒种》(2005)和《豆满江》(2010)的故事都发生在延边的小镇或村庄;《里里》(2007)的背景是中蒙交界处。
《漫长的告白》里,作为女主角的柳川和作为地名、空间的柳川重叠(本来还有作为片名的《柳川》)。几位主角都是中国人,但柳川身上依然有张律以往作品中强烈的不定性。从她与立春、立冬的忆旧中可知,她和家长从外地(听口音是南方)移居北京,父亲出轨后,母亲带她去英国,她在海外二十年,之后一位对她有意的日本柳川男人向她表白——“你的名字是我的家乡”,因为觉得有趣,她任性地来到了柳川,在清吧驻唱。
张律喜欢多角关系,一年前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生活就是暧昧的,一切关系都是多角关系。他不想像好莱坞一样创造一个明晰的东西。柳川与立春、立冬及那位柳川男人的关系也是暧昧的。立春少年时和柳川有过短暂的情侣关系,之后他抛弃她;立冬罹患癌症,对柳川念念不忘,说起二十年前,记忆清晰如昨——片名更改后,本片似乎将视点稍微偏向了立冬。
《漫长的告白》结局抵达的是立冬的死。但这个过程被忽略了。张律的电影里一定会出现不在乎主角死去的人。《春梦》结尾他让一个酒屋的客人问了一句,主人死了啊,很可惜。立冬的死讯是立春的妻子告诉我们的,她在对着立冬的老房子敲敲打打要做装修。立冬死后,故事继续,对至少一个人而言,立冬不重要。
张律说他喜欢到处逛,每到一个新空间,故事便以外来者的视角慢慢流淌。比起立冬,在柳川这个空间里的所有人物和景观加起来才更像是张律的主角。片头在北京的日式酒馆里,厨师和立春说起柳川,是一座“空城”,仿佛只有鬼影。之后柳川确实旷然寂寂。立春、立冬,立春、立冬、柳川,立春、柳川,立冬、柳川,一次次在柳川的河上坐船。台词很少。和以前一样,张律喜欢让镜头和人物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人先于镜头走动,他的镜头再迟钝地跟上,试图再次对准人物。镜头语言腼腆,像他本人性格。
张律在过往作品中常援引诗歌抒发乡愁。《唐诗》(2003)中古诗出现在小偷家的电视里。《芒种》《咏鹅》《福冈》里,电影中人都会念诗。但诗句往往和主人公直接联系不大(如《唐诗》中,小偷发呆,听着《芙蓉楼送辛渐》的朗诵)。《漫长的告白》中柳川几次唱《秋柳》,这是一首李叔同作词的美国民谣,曾出现在音乐家小河的寻谣计划演出中。“君不见/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胜悲。”不知是否有电影这回要面对院线观众的缘故在,柳川对着异国人唱中文歌,吟唱并朗读这样的歌词,情感表露过于直白。
张律在采访中说过他未老先衰,从小被莫名的乡愁困扰。他过去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如下场景:说朝鲜语、韩语、中国话的人无法相互理解,指向的是边缘地边缘人的身份认同之苦,故乡是主角情感的重要归宿。《漫长的告白》也有这种语言的小小迷宫。倪妮与喜欢她的柳川男人说英语,与北京的兄弟俩说普通话;立冬自己学了两年日语,偶尔对立春说日语,立春不懂;柳川和酒馆老板娘互相倾诉,一人用中文,一人讲日语,互相没有听懂,但都哭了。
但《漫长的告白》里没有边缘地作为故乡,女主角柳川就是立春和立冬的乡愁。柳川从南方到北京,再到伦敦到柳川,在立冬去世后又回北京,还在飘零、寻找栖息地。从本片的很多细节看得出张律的精心设计(比如用不同方言对话搭建的场景),仿佛有寓意,但不像他早期的那些电影,人物的际遇背后指向的是对历史和地缘政治暴力的控诉、对边缘人的严肃叙事。这在《庆州》以后就有明显转向,到《咏鹅》《福冈》《漫长的告白》,电影愈发轻盈。多语言的环境、异国文化符号还在,但张律好像只是要讲一个爱情故事。而这爱情是什么,我们看完电影也很难给出简明概括。
《漫长的告白》深夜映后谈上,张律宣布自己已于一年前从韩国的大学辞职,现在学习走上职业导演之路。他说他创作时不会有意识地思考电影的主题、类型,而是着迷于“人、空間、我自己的情感以及自然的白日梦”。就像张律其他的电影一样,《漫长的告白》好像只是列出各种元素,让观众感受。地点、风景、人物交融,呈现某种多义性。
立冬对柳川到最后也没有表白,尽管片名叫“漫长的告白”。张律曾把电影和观众的互动关系说成“你做了爱情的表白,对方接不接受”。他对观众在意吗?他说他在意。但从呈现的结果(电影作品)看,他似乎不在意。就像立冬,心里装着二十年前的柳川,但柳川对他如何,似乎不重要。
在映后谈,一位观众问他片子要解决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在《福冈》之后有媒体问,两个男人的一场漫游能让他们达到自我谅解和救赎吗?我以为张律的回复可以完全挪用给《漫长的告白》——
“这场旅行是跟他们年轻时候的爱情有关。有些问题遗留在记忆里,怎么也得解决一下。就好比说有一件衣服,你穿上的时候觉得某个地方不舒服,总得去解决这个不舒服。但最终有没有解决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