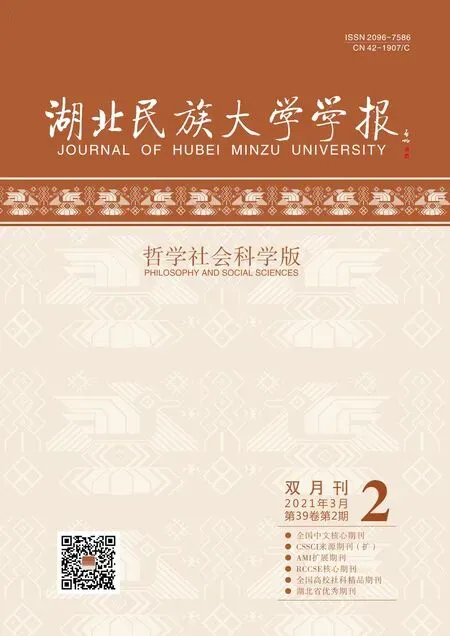从互嵌到认同:移民与清代滇东南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2021-01-13杨宗亮
杨宗亮
“滇东南”的地域范围,一般是指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广南、西畴、麻栗坡、马关、砚山、邱北七县及文山市。清代,滇东南属于广南府、开化府、广西府五嶆州判及师宗州邱北州同辖地。其中师宗州邱北州同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降为邱北县丞,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为县,属广西州。清代,开化府所辖包括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县、河口县的部分地区。所以,本文研究的地域范围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七县一市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上述二县。
先秦时期滇东南地区为骆越民族的活动范围。经过长期的迁徙演变,至明末已经形成以骆越后裔壮侗语系民族为主,包汉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清代,移民的大规模到来对滇东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云南移民问题的研究始于方国瑜先生(1)方国瑜相关论文有《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明代在云南的军屯与汉族移民》等。参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之后还有陆韧(2)陆韧:《交融与变迁——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古永继(3)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苍铭(4)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等学者的研究。这几位学者都从云南全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某一历史时期云南或云南边地(即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沿边沿线地区)的移民方式、来源、民族构成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的研究对本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对滇东南移民的集中研究主要有李和对滇东南区域开发中壮汉民族交融问题的探讨(5)李和:《清代滇东南壮区移民开发与民族交融述论》,《百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杨永福对明清移民与文山地区开发关系的研究(6)杨永福、邱学云:《论明清移民与文山地区的开发(1382-1840)》,《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刘灵坪对滇东南移民垦殖与聚落发展的分析等(7)刘灵坪:《清代滇东南地区移民开发与聚落发展初探》,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滇东南区域整体视角出发,以分析清代滇东南移民产生的背景、移民的民族构成为起始,以移民促进各民族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过程为线索,对清代移民与滇东南区域各民族的互嵌互动进行探讨。
一、滇东南地区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
滇东南地区东接广西,南界越南,西连云南红河州,北邻曲靖市。从自然地理看,这一区域处于云贵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向,境内山脉纵横交错,海拔多在1000~1800m之间,红河水系与珠江水系分流全境的西南与东北地区。境内岩溶地貌发育好,峰林密布,山多平地少,重峦叠嶂,道路崎岖。
滇东南地区瘴气流行,古人多有记载。该地区三国时期属于兴古郡,晋代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兴古郡)“……多僚、濮。特有瘴气”。(8)常璩撰:《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55页。清代的乾隆《开化府志》《广西府志》等对滇东南瘴气均有记载。其中道光《广南府志》记载详细,其文说:广南属于烟瘴之地, ……在皈朝、剥隘、板蚌等地,天气尤其闷热。一年之中,春夏有青草瘴,秋深有黄茅瘴,直至霜降后瘴气才消失。(9)道光《广南府志》卷1《星野气候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1页。万历末年,广南府知府廖铉到临安躲避瘴气,将知府大印寄放在当地土司侬添寿手中。侬添寿死后,印信被家里的下人偷走,发生土官之间争夺印信的事件。(10)张廷玉撰:《明史》卷313《土司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8075-8076页。
滇东南地区与越南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代的开化府属临安府东部地区,史载临安“南邻交趾,北拱会城,……筹边者当先加之意也”。(1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5《云南三·临安府》,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云南史料丛刊》油印本,第29辑,第95页。清代的开化府“接壤交趾,……僻地险区”。(12)康熙《云南通志》卷5《疆域·形势》,民国年间刻本,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第19页。而广南府则“两粤冲途,交彝要障”。⑧
滇东南在秦汉之际属于牂牁郡句町县(治今广南县)。至于其地的僚、濮民族,是“仡佬、壮、布依、侗、水、傣等族的先民”。(13)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三国蜀汉时期属于兴古郡,其民族是鸠僚人。鸠僚“为僮语支族系”。(1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页。唐宋时期,滇东南的部分为唐宋王朝的羁縻州,部分为南诏、大理国所辖;僚人中的西原、广源诸蛮在该区域活动频繁。元代,滇东南地区属于临安路东部、广南西路宣抚司及广西路维摩州辖境。其时,僚人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已出现侬人、沙人、山僚等称呼,他们大多属今壮族先民。明代的滇东南属临安府东部的教化山部、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及直接隶属云南都司的八寨长官司,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辖地。这一带还是以侬人、沙人、土僚为主。此外,还有傣族和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先民。已有瑶族零星迁入,流动性强,文献记载粗略。
清初,地方志对滇东南民族的记载比明代详细。据乾隆《开化府志》记载开化府夷人有37种。(15)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248页。在乾隆开化府所记载的民族种类中属于壮族支系的有:侬人、沙人、花土僚、白土僚、黑土僚、喇鸡;属于彝族支系的是白倮罗、黑倮罗、聂素、黑母鸡、白母鸡、黑仆拉、白仆拉、马喇、花仆拉、阿成、阿戛、阿者、阿系、阿度、普岔、喇乌、孟乌、普剽、昔马、普列、腊欲、腊兔、舍乌、阿倮、腊歌;属于傣族支系的是旱摆夷、水摆夷。僰子是白族,窝泥属哈尼族。对僰人、夷人、山车未做分类。(16)转引自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附录表(十),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据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种人》记载,广南府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壮族支系的侬人、沙人、花土僚、白土僚、黑沙人、白沙人;属于彝族支系的有白倮罗、黑倮罗、黑仆喇、白仆拉、花仆喇;也有称为瑶人的瑶族,称为僰夷、摆夷的傣族。相比之下,广南府的民族成分比开化府略少一些。
二、移民进入的条件与移民的民族构成
滇东南地区,僻处边关,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又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瘴毒流行,令人望而生畏。至明代,广南“知府不至其地”。清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统治较为深入的时期,云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开发达到历史以来的最高程度。就在此时期,滇东南得到深度开发,改土归流、疏通河道、筑路修桥等为各民族人民迁入滇东南创造了交通基础和政治保障。
(一)改土归流为移民进入提供政治保障
清初统一云南后,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度,随着统治的深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广南府因地处瘴疠之区,流官知府难以亲临,由土同知执掌地方。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仍设广南为府,派流官知府常驻,土富州仍为土知州。康熙六年(1667年),以临安府所辖王弄、安南、教化三长官司地设置开化府,并设开化、安南、王弄、永平、东安、乐农、江那、逢春八里。“皆以土司苗裔催征该里钱粮,赴府完纳”(17)乾隆《开化府志》卷2《建置》,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这说明开化府基层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土司苗裔手中。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委任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督事,开始了云南澜沧江以东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宣布“江内地全改流”。清代的改土归流达到高潮。被改流地区土司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广南府土同知侬氏、富州土知州沈氏各愿向朝廷岁增粮二三千石,并自愿捐款建府州城垣。在开化府地区,雍正八年(1730年)设文山县,由流官掌权的县级行政机构来管理征粮事宜,改变了“以土司苗裔催征该里钱粮”的状况。
清初,在与滇东南接壤的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还设有泗城、镇安两个土官府;在南宁、太平、思恩等流官府下,设有数量庞大的土州、土县以及峒、寨等土官。这些土府、土州、土县有的在云南经过广西至内地的必经之地上。雍正时期,需要开采云南铜矿运往各省以缓解国内的“铜荒”。为了运路畅通,对桂西的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在泗城(治今广西凌云县)土府改流之际,清廷将红水河以北原泗城府属地划入贵州省,红水河以南地区仍属广西。泗城府改流及其善后措施使广西、贵州、云南三省边界得到了安宁,为滇铜外运各省提供了安全保障。
总之,与明朝比较,清廷对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深入,特别是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为外省和本省腹地移民进入滇东南消除了政治上的障碍。
(二)滇铜滇钱运输改善了移民进入的交通条件
滇东南地区,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明、清时期,只有联系滇桂的粤西路东西横贯其中,这条路经过今邱北、文山县北部、砚山、广南、富宁而入广西。但山路险峻,路途维艰,且沿途多寇盗,因而“行者以广南为畏途”。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由昆明经呈贡、广南、剥隘入广西百色道上设了25个驿站。还疏通西洋江水道,使船只可达板蚌(广南县板蚌镇)。乾隆十年(1745年)广南知府蒋衡筹资重建西洋江乐安桥。疏通河道,修建大桥后路况得到改善。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以便更好衔接滇铜外运,雍正七年,将田州土州部分地方划出另置百色厅,将原驻武缘县的思恩府理苗同知移驻百色。(18)光绪《百色厅志》卷2《舆地·沿革》,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第1页。百色地处右江流域的中心,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汇处,是三省交通运输的枢纽。清代,广西的驿道网络已渐臻完善,当时桂西有经百色通云南、贵州的大道。百色“为滇、粤门户,水路交汇”。百色厅设置后,对滇钱、滇铜运输的后半路程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清代滇铜外运期间,不仅广西,还有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甚至陕西采买滇铜的运输路线都要经过百色。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1736-1739年),曾在云南广西府(治今泸西县)铸钱运京,每年运抵京师钱文达258万余斤。(19)王德泰:《乾隆初年滇省代京铸钱失败原因探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3 期。乾嘉道三朝100多年时间,广西、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陕西九省采买滇铜量每年平均约为250万斤。(20)马琦:《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各省采买滇铜是为了满足各省局鼓铸,平衡各地钱价。滇钱运京,各省采运滇铜,自云南省城经广南剥隘、广西百色、梧州、湖北汉口、江西九江等地分道,形成一个庞大的运输网络,覆盖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为外省移民进入滇东南创造了条件。
(三)移民的民族构成
明代,广南设府,但流官知府难以到任,仍以土官统治其地。曾设广南卫,不久就将广南卫移至云南府(今昆明)。(21)道光《广南府志》卷1《建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24页。在缺乏官府和卫所支持的情形下,移民进入很困难。除广南府之外的滇东南其他地区,属阿雅长官司(驻今马关八寨)、维摩州(今丘北)、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领地,移民很少到达,文献中更没有关于移民的记载。
滇东南地区,南界安南,与广西、贵州为邻,属边防重镇。清廷于康熙六年(1667年)设置了开化镇;康熙二十一年(1672年)设广南营,隶属广罗镇。分别设有马战兵、步战兵、守兵。开化府和广南府所驻的绿营兵共计3200名,大多是从内地各省招募来的汉族兵丁。他们的到来是滇东南边区移民的开端。
清廷统治的深入及驻军,为移民进入扫清了障碍,外地移民纷纷涌入滇东南的开化府和广南府。根据道光十六年(1836年)云南总督伊里布和巡抚何煊《旨稽查流民酌议章程奏》记载,移民在开化、广南、普洱三府最多,他们来自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和广东、广西各省,有携资经商谋生者,也有开挖荒土或租佃田地谋食者。对进入滇东南的流民数量有粗略统计:“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22)道光《威远厅志》卷3,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云南史料丛刊》(油印本)第44辑,第246-257页。这些数字不够精确,因为“流民忽去忽来,讫无定数”。(23)道光《广南府志》卷2《民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4页。
开化府与安南交界一带储藏金、银、铜等矿产,是滇东南地区的富矿区。清乾嘉时期,有黔、楚、湘、粤的商人前来开采。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办的开化府属麻姑金厂以及嘉道年间开的者囊铜厂、马腊底银厂等兴盛一时,吸引了大量的外省矿业商人和流民,其中大多为汉族移民。根据民国《马关县志》,马关县当时见于记载的各类大小矿厂共有25个。这些矿厂大部分都已经停采,多数矿厂发展成为村寨。在已知其民族种类的18个产矿地中,汉人聚落占了71%。(24)刘灵坪:《清代滇东南地区移民开发与聚落发展初探》,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从民国《马关县志》中对聚落地名记载来看,有如“老厂”“铜厂坡”“硝厂”等代表产矿地的村寨大多数是汉族聚居之地。
汉族移民之外,还有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的民众。《旨稽查流民酌议章程奏》还专门谈到黔粤苗民移居安平厅(今马关县)沿边地区的情况,这说明移民中苗族的人口不少,因没有进行统计,无具体数据。文山州的学者根据史料及调查研究资料,认为“明初,有2000余苗族由贵州迁入文山州境内的丘北县”。清代,朝廷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促使流官和移民涌入苗族地区,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导致雍乾、乾嘉、咸同三次苗民大起义。起义失败后,滇、黔、川三省结合部的苗族大批流入开化府和广南府。从调查的情况看,今文山州苗族大多是清朝时期迁入的。(25)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第74页。
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了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地方性小集体界限被冲破,有部分群体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四处流动,离开了原来的住地,迁到新的地方定居下来。滇东南地区的罗武、鲁兀、聂索等,原为罗婺部人(彝族)中的一部分,分布在今武定、禄劝等地,后来才慢慢散及临安、广西等府,最后进入清代的开化府境内。阿者、阿兀、阿系、葛倮、撒尼等,都是从原广西府等靠内地区渐渐地迁到开化府境内的,他们迁入开化府境后各自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分布于不同的地域范围内,既没有完全融入当地彝族其他部分中,相互间联系不密切,各自都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及经济文化生活特征和原有的名称。(26)万永林:《元明清时期滇东南彝族支系初探》,尤中主编:《西南民族史研究》(1987),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76页。
三、移民与滇东南地区民族社会变迁
根据道光十六年(1836年)云南总督伊里布和巡抚何煊在《旨稽查流民酌议章程奏》记载,开化所属客户流民共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按每户5人计,道光时期开化府和广南府的移民总数约23万。随着人口增长,滇东南地区民族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乃至土著民的社会地位都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各民族间交往频繁,互动性增强。
(一)滇东南地区社会结构变迁
1.民族人口结构改变。随着移民大量迁入,滇东南地区民族人口结构与居住格局发生了变化。清中叶前,滇东南地区主要以壮、彝、瑶、傣等少数民族为主,壮族人口在各地占大多数。至晚清时,部分区域的汉族人口已超过壮族,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
根据《开化府志》的统计,开化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纯汉族居住的村寨有25个,占总村寨数2.1%,汉夷杂居的村寨有110个,占总数的8.8%,其余多为壮、彝、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东安、永平、逢春三里靠近中越边境区,仅有1个汉人村寨和5个汉夷杂居的村寨,可见越往边界地区,汉族的分布越少。至民国年间,在开化里(县),汉族大量迁入并扩散到四面八方,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一半,除集中在文山城和马塘、平坝等主要集镇外,有一部分到有林有水的山区半山区开垦。西部和南部大片在清代以前很少有人烟的地区,这时已布满汉族村寨,汉族在农村聚居的村寨增加到102个,从清代只占聚居村寨3.5%,占总村寨2.1%,上升到31.3%和10.1%。汉族与各民族杂居的达453寨,占全县总村寨58%。全县有汉族居住的达555寨,占总村寨71%。(27)段起鹏、卢金玉:《民国年间文山县民族分布变化情况》,政协文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山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第92-94页,内部资料。汉族人口和居住村寨已跃升到全县第一位。
边境县的汉族人口增长也很突出。民国年间,仅马关县见于记载的595个村寨中,有汉人居住的村寨就有268个,约占总数的45%。(28)民国《马关县志》卷1《地理志》,何廷明等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25页。根据民国时期麻栗坡地志资料记载,全区都有汉人居住,且比例高,在麻栗坡七区中,汉人居住最少的区至少占十分之二,最高的占十分之六。(29)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民族种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苗族村寨也呈快速增加的趋势。民国年间的马关县相当于乾隆时开化府属八里之中的永平里、逢春里的大致范围。民国《马关县志》卷1《地理志》记载的595个村寨中,52个苗人聚居村是乾隆府志中没有记载的。作为地主招来开垦的佃户,文山县苗族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从边远山区逐渐向内地山区迁移。民国时期,文山县纯苗族聚居的村寨增加到110个,占民族聚居村寨37.8%,比清代占23.6%增加了14.2%,属全县聚居村寨最多的民族,但村落小而分散。苗族与其他民族杂居村寨有193个,占杂居村寨39.5%,比清代仅有14寨,占9%增加了30.5%。全县苗族聚居村寨304个,占总村寨38.9%,村寨数居全县第四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开化府,民族的立体分布格局并不突出,总的态势是汉族和苗族已杂居于腹地和边境的其他民族村寨之中。
2.移民的来源地与职业种类。广南府、开化府的移民多与滇铜外运的各省相关,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大多来自滇铜外运的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陕西、贵州各省。对于广南府的移民来源,在《广南府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主要来自今四川、贵州、湖南及广西等地;由于地缘关系,广南府接纳来自贵州、广西籍移民颇多。《开化府志》没有明确记载移民的来源地,但根据公馆、寺庙的建设信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如《开化府志》卷二《建置·寺观》记载了萧公庙、万寿宫、寿佛寺的分布位置、建设情况。据专家研究,湖广籍移民会馆常用的名称是禹王宫;寿佛寺、万寿宫、萧公庙、昭武祠则为江西籍移民最常用的会馆名称。(30)蓝勇:《清代西南的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由此可知,进入开化府的移民相当部分来自湖南、江西、贵州等地。
在移民大规模到来之前,滇东南各民族以从事农业为主。史载“人尽力耕,不治末业”。(31)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47页。随着清朝统治的深入,商业逐渐繁荣,在城镇聚集了成批的商人。随着矿业的开发,矿工成了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矿工数量,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民国《马关县志》卷十有一篇《都竜铜厂记》叙述了都竜铜厂的大致情况:“当有清嘉道时代,厂矿甚旺,矿工达数千人。居民成市,庙宇辉煌。”(32)民国《马关县志》卷10《物产志·矿产》,何廷明等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一个矿厂,矿工就有数千人,加之随矿工而来的家口以及伴随着矿业发展而逐渐兴盛的商业、运输业等部门的从业人员,清代开化府马白关一带因矿业发展而迁入的移民数量有数万人之多。
总之,移民的谋生手段、从事行业复杂多样,如原属开化府的麻栗坡,汉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40%以上,“四川、贵州籍称曰天府人,……以种地为业”“江浙、两湖籍者,……其职业不一,士农工商均有”。(33)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卷中《民族种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滇东南地区各民族的职业呈现多样化趋势。
(二)土著民族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与土客民之间的纷争
随着改土归流的最后完成,在开化府境内,土著民族在当地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逐渐丧失。政治上,土著民族土司的世袭统治,在流官到来之后即已结束。但在广南府,土官势力一直持续到清末。
明及清代前期,广南以流官担任知府,以壮族侬氏贵族为广南府同知,以沈氏为土富州知州,实行流土并存的治理方式,但广南府土同知侬氏及土富州沈氏实际上掌握地方实权。移民中有一部分租种土司土地以谋生计。道光十六年(1836年),广南笼浪寨汉族人徐德成等向侬氏土司租种土地一分,并“每年上纳租钱二千文”。(34)吴晓亮、徐政芸:《云南省博物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此事反映土司势力在广南地区尚且稳固。汉族移民向土司租种土地,每户一年要向土官交租金三钱,当地称“烧山吃水钱”。雍正年间( 1723-1735年)这种土地所有制有所改变,出现土地买卖的情况。道光《广南府志》卷二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云南布政司陈××捐银用来购买土同知侬振裔和土知州沈灿的粮田租给农民耕种,所收粮租用来办义学。此事说明当地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清中后期,在广南府出现了所谓的“田地爬山”的现象,即居住在山区的汉族农民,勤俭持家,积累资金,收买壮族人的水田,山区农民变成了水田的主人。土地占有关系的改变,使当地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亦随之变化。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中卷载:濮喇人,系本地土司,是曾经的地主及地方统治者,自从汉人迁入后,他们的土地被汉人强占,在农村的统治地位也由汉人取而代之。“乃至今日已全为佃农矣。”这里所举的虽是濮喇人(彝族支系),其他民族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后,由坝区进入山区,受地理环境制约,耕地面积开垦有限,时有与同居当地的民族发生冲突的事件。由于不法分子移入,也给淳朴的土民社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道光《广南府志》载:“今数十年来,各省无赖流民窜入其中,……以至欺诈盗伪,……土官土民俱受其蔽,非复向日土府风俗矣。”(35)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2页。
(三)各民族之间商业贸易互动频繁
交通畅通,滇铜外运各省及滇铜粤盐互易,促成沿线的板蚌镇、剥隘镇等商业集镇的形成,也促成了以通道经过的府治为中心、深入乡村的商业体系和市场网络的形成。板蚌,位于广南县城东74km,海拔532m,今为广南县板蚌镇政府所在地,被称为瘴疠之区,有“若要下板蚌,先把灵牌供”之说。随着滇铜粤盐互易的开展,板蚌形成了物资交流和商贾云集的商业集镇。剥隘在今云南富宁县境内,有水陆两路码头,是滇桂通道必经之地。在滇铜外运各省期间,人口不过千余人的小镇却聚居着13个省的人,有大小商店76家,客马栈11家,建有粤东、广西、江西3个会馆。
除了交通道口,在广南府治(今广南县城),开化府治(今文山市),广西府(今泸西县城)也已形成了辐射全府域的商业集镇,在县城同样形成了辐射全县域的商业中心。在广大农村有许多街子,这种街5天或7天赶街一次,是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商品流通环节。 据民国《邱北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全县共有街子24处。就是在中越边境的麻栗坡特别区,民国时期 “其大小街道二十五条”。随着深入乡村的商业体系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商人的足迹深入各民族聚居区,通过不同方式与各民族建立了密切联系。单身者挟带资金进入,与当地人联姻,凭借婚姻关系往来于村寨之间行商。有一部分商人举家迁入民族地区生息繁衍。
商业繁荣,商人势力增强,促成其各种行会和会馆的建立。如设立开化府后,内地汉族人口大量移入。他们来文山经商谋生,从小本经营开始,逐步积累资本,发展到开铺设店,赚了钱就买地置产。为了互相联络聚会,各省的商人都集资建庙立会馆。根据民国《广南县志》卷四之《寺庙坛观会馆附》记载,仅在广南县城内就分布有广西会馆、三楚会馆、川黔会馆、两湖会馆、岭南会馆。这类会馆通过乡土神庙和戏台进行节庆、祭祀、出演地方戏剧等活动来会聚教育众人,因而对移民来源地文化在滇东南各民族中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四、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增强
移民不断增多,外来客民与土著民族之间互动频繁,滇东南地区民族的居住格局发生变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现象普遍,在中越疆界勘划过程中各民族边民的国界意识变得明晰,在抗法的反侵略斗争中国家认同意识增强。
(一)民族杂居村寨剧增与立体分布格局形成
随着移民由交通沿线、集镇逐步向边远山区迁徙,滇东南地区多民族杂居村寨变得普遍。如开化府的开化里,即后来的文山县,1949年,全县单一民族聚居的村寨减少到293寨,由清代占总村寨80.9%下降到只占37.5%,而多民族杂居的增加到488寨,由清代只占19.1%上升到占62.5%。(36)段起鹏、卢金玉:《民国年间文山县民族分布变化情况》,政协文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山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第91页,内部资料。其中多数为两种民族杂居的村寨,最多达到8种民族共同居住在一个村寨。
总体看来,单一民族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民族杂居,但各地各民族的杂居实况各不相同。我们以居住在文山坝子的壮族先民为例予以说明。清代文山县壮族共有侬人、土僚、沙人三大支系。清代壮族的侬人、土僚两支系,已布满于河谷坝区和有水源的半山区。到民国年间,单一民族聚居村寨已占少数,杂居村寨大为增加,尤其是腹心地区的文山坝子更为突出。整个坝子文山县管辖51寨,清代前期土僚居住的41寨,占80.4%,其中聚居的有33寨,占64.7%。民国年间纯属土僚聚居的减少到只有5个寨,汉、倮、侬、摆夷与土僚杂居的增加到36寨。
侬人虽居住河谷,但大都离腹心地区较远,没有居住在腹心地区的土僚变化大,如秉烈地区(今文山市秉烈乡),民国时期侬人仍基本保持原居住地域,汉族、彝族较少。舍舍河谷14寨844户,侬人居住的就有11寨655户,占78.6%,汉、傣、彝族与其杂居的只有3寨,仅占21.4%。而在交通沿线,其他民族与侬人杂居的则急剧增加。如侬人河两岸10寨,清初都是侬人聚居,民国时期侬人聚居的只留下5寨,其余5寨变为侬人与汉族、彝族杂居村寨。壮族的另一支系沙人大部分已融于其他支系,文山全县有沙人杂居的只有6寨,仅占全县总村寨的0.7%。可见,腹心地带和交通沿线多民族杂居状况明显,而离腹心地区较远的地带单一民族聚居村寨多,杂居程度低。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大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入滇东南,与壮族等土著民族错杂而居,打破了壮族大范围聚居的局面,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这种格局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并进一步影响壮族各支系,甚至不同区域同一支系的各小支系之间在语言、服饰、风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因为侬人支系集中居住在滇东南的中、南部汉族杂居率较高区域,所以,侬人支系受汉族的影响较多。土僚支系集中分布在滇东南中、西部,与红河州东部(蒙自、开远等)接壤的地区,与彝族各支系杂居较多,土僚支系自然受彝族各支系的影响较大;因为沙人支系多聚居于滇东南的东部、东北部,更靠近滇、桂、黔壮族(布越、布雅衣)大聚居区的中心,所以,沙人支系保持的越(骆越)文化较深厚。
在汉族、苗族移民大规模迁入以前,广南府地区系侬人、沙人、土僚、摆夷等壮傣民族先民居住在河谷、坝子,他们利用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灌溉条件从事稻作农业。仆喇、倮罗、母鸡等彝族支系主要聚居于山区、半山区,多以种荞及杂粮为生。如倮罗“……种苦甜荞”“白仆喇,多住山坡。种菽麦杂粮火麻。”(37)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0、51、54页。至于“瑶人,……多处深山,喜猎善搏虎豹”。(38)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0、51、54页。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清初广南府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壮傣民族先民住水头,汉族住街头、彝族住山坡、瑶族住深山的立体分布景观。
随着清廷统治深入,乾隆朝及之后,移民纷纷迁入滇东南地区,广南府人口急剧增多。根据清代的户口统计,乾隆四十年(1775年),广南府烟户清册计3555甲,34 997户;道光元年(1821年)4500甲。(39)道光《广南府志》卷2《风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0、51、54页。46年时间增加了近千甲。在明代和清朝初期,汉人至广南者稀少,壮傣民族先民滨河而居,开垦沿河土地为农田。对于山岭间无水之地,抛荒不顾。人口增加后,由于适于农耕的平坝以及河谷地带已被壮傣民族先民所经营,清康、雍以后,外来汉人只能在山岭间开垦新地,并不断由半山区向山区推进。史载“汉人垦山为地,初只选择肥沃之区,日久人口繁滋,由沃以及于瘠,入山愈深,开辟愈广”。(40)民国《广南县志》卷5《农政志·垦殖》,凤凰出版社(南京)、上海书店(上海)、巴蜀书社(成都)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稿本影印,第414、415页。到了嘉道时期,黔省农民大量移入,山区可耕可垦之地多被先来者开垦,故他们只能向“地瘠水枯”的高寒山区挺进,“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直至今日,贵州人占山头,尚为一般人所道”。(41)民国《广南县志》卷5《农政志·垦殖》,凤凰出版社(南京)、上海书店(上海)、巴蜀书社(成都)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稿本影印,第414、415页。清朝末期,广南府境内“侬人占水头,汉人占市头,彝族人占山坡,瑶人占箐头,贵州人占山头”的民族立体分布景观最终形成。
这样的立体分布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居住在不同海拔的民族在资源占有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他们在需求上的互补,这种经济互补关系是民族交往的前提之一。滇东南壮族与苗族、瑶族就有一定的互补关系。壮人住水头,善种水稻,山区瑶人和苗人善于山地种植。壮族向瑶、苗族学习玉米、旱谷的种植技术和经验。苗族、瑶族向壮族学习水稻选种、耕播、管理经验。壮、瑶、苗族际间的商品交易大多是通过街子进行的。广南、开化商业集镇和各地街市兴起繁荣,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前来赶街,众多的人群聚居在街市进行贸易活动。居住箐头、山头的瑶族、苗族等由于所居之处耕地不多,粮食产量少,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必要的生活用品。而壮、汉民族杂居所在的平坝地区发展起来的集镇和街市,为瑶、苗等民族提供了商品交换的场所。
(二)移民促进滇东南地区各民族交融互化的进程
随着移民增加,各民族杂居村落变得十分普遍,加速了滇东南地区各民族交融互化的进程。从总体情况看,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民族杂居村落呈现出汉化程度愈来愈深,范围愈来愈广的趋势。但是,清代的滇东南地区除城镇、交通要道、开化府开化里、安平厅等区域外,壮族在人口数量、政治势力等方面均占主导地位,因而其他民族“壮化”的情况也很普遍。这就是民国《广南县志》所说的“汉少夷多,风俗互化,则夏变夷者多,而变夷者亦不免”。既有壮人汉化,也有汉人及其他民族壮化的情况。较普遍的是汉人壮化。一般来说,改土归流以前进入滇东南的绝大部分汉人已融合于壮族社会中,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一部分壮化。汉人融合于壮人之中首先从交通要道或商业城镇开始。较典型的有广南县的板蚌镇。清末滇桂交通水运冷落,板蚌的商业衰落,外籍人有的迁出,有的在此定居。今板蚌有近80户人家,有黄、陆、李等20个姓氏,绝大部分是外籍人后裔,今均为壮族。(42)杨宗亮:《壮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也有其他民族融入壮族的,如文山市秉烈乡雾露村的马姓、卡左村的那(纳)姓、红甸乡母鲁白村的马姓壮族,3个村子约有400人;分别是一百多年前丙辰(1856年)起义遭清廷镇压后,逃难入赘壮家的开远大庄(马姓)、通海纳家营(纳姓)回族的后裔。这部分人于1990年前后陆续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壮族穆斯林。广南县旧莫乡、董堡乡、那伦乡等地有一些村寨的壮族是被壮族同化了的彝族。(43)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第32页。
(三)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增强
滇东南地区各民族开始接触中原文化是在土司向中央王朝朝贡的过程中开始的。明代,滇东南各土司曾多次至京城朝贡。土司在朝贡往返途中,耳闻目睹所经之地风土人情;土司留京期间,能亲身沐化于国家的礼仪规制中,土司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熏陶,并将其带到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 阿雅(今马关县八寨)土司龙者宁入京师,适逢五月五日皇上巡幸东苑,龙者宁亲自目睹皇帝宴饮群臣的场面。回阿雅后,为感激圣恩,“每年以五月五日端午日令目把等骑射以志不忘之意”。(44)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241、241、246页。阿雅土司龙上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往京承袭世职”。 龙上登在京城拜访了著名学者,回到阿雅兴学校,立孔庙,传播中原文化。
至清代,随着移民增加,普通民众认同并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改土归流后,学宫、书院、义学和私塾等以习儒家文化为内容的教育机构遍及滇东南乡村。因而,各地土著把读书、习字作为时尚。“穷乡僻壤,亦闻弦诵之声。”(45)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241、241、246页。何愚任广南知府时,写过一篇关于兴办义学的文章,文中道:“故今摆子、僰丁多有识字知礼者。”(46)道光《广南府志》卷2《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45页。广南府的白土僚“能习汉语”。开化府侬人刻木为信,不习文字。“设流之后,学校既开,习俗渐改。”(47)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241、241、246页。瑶人“男女皆知书……衣服近汉”。(48)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241、241、246页。居住在坝区、交通要道等地区的部分彝族,也接纳了汉族文化。如邱北境内的“阿兀,……冠服同汉族……多与汉族杂处,喜读书……婚丧概从汉族礼”。(49)民国《邱北县志·建置部》,1926年云南新文石印馆石印本,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第18页。永平里(今马关八寨)属平坝地区,又是交通要道,清以来,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八寨地区,当地彝族中的“聂素”,由于与汉族直接接触、交往,因而能“读书力田,纺织贸易”。(50)乾隆《开化府志》卷9《风俗》,娄自昌等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总之,经过中原文化的熏陶和移民主体的影响,滇东南地区各民族广泛产生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意识。使用汉语作为交流工具,掀起学习汉文化的潮流。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四时节庆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文化。
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改土归流的推进,中原文化的普及,以及大批汉族移民进入当地与各民族混合居住,逐步改变着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的意识而强化了国家观念。在各民族国家意识增强的情况下,在面对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在反侵略的旗帜下各民族团结起来,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19世纪,法国侵占越南南部后向北扩张,进而侵入我滇东南的马关、麻栗坡地区,当地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为捍卫祖国疆域而英勇抗敌。侬茂先是广南侬氏第二十四代土司。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调率部赴越南北方抗法有功;十五年,赏戴花翎加四品衔。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入侵麻栗坡猛硐一带,项崇周(苗族头人)团结苗、壮、瑶、汉民族军,坚持与法军抗战十多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授项崇周为“千总兼南防统带”,赐“边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红缎软匾一面。1884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与之订立《顺化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中法双方就中越边界作了多次踏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法才订立滇越界,并设立界碑。其中,中国猛洞与越南老寨接壤的界碑为11号界碑,此界碑立了不久,就被越南老寨二花官派人悄悄移入我国境内50多米。项崇周闻知,立即前往把界碑移还原位,并严厉斥责法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越南提出无理要求,要以重价购买我国猛洞旁边的一小土山,被项崇周痛骂拒绝。(51)政协马关县文史委员会:《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6年,第92-93页,内部资料。项从周的事迹反映我国边民国土意识、边界意识、国家意识的增强。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议和,清廷内阁学士周德润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及唐景嵩等5人组成勘界大臣,与法国使臣浦理燮、驻越帮办狄隆等会勘中越边界。双方相持40余天。就在中法进行定界谈判期间,“田蓬八寨人民自行改装易服,要求复归中国,迫使法代表同意将田蓬八寨划入滇境”。(52)吕正元、农贤生:《富宁县民族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田蓬八寨(今富宁县田蓬镇一带)的民众心向中国,强烈要求归附中国,就是因为田蓬八寨原是中国领土,当地民众对祖国有强烈的归属感。
五、结语
以往对滇东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多以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为主线,主体多选择壮汉民族关系来研究,研究内容多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以阐述。本文从滇东南区域整体视角出发,以移民促进各民族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过程为线索,以清代移民与滇东南区域内各民族互嵌互动为主要内容展开研究,得出以下认识。
(一)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对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高度重视。2014年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工作会议上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紧接着,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总书记所描述的这一民族关系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此后,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出现在媒体和学术研究视野之中。滇东南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村落层面的杂居为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奠定了地理空间基础,立体的分布状态满足了各民族经济上的互补需求。滇东南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分布格局就是一个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的典型案例。滇东南的历史事实表明,多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能够消除对立的区隔壁垒,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
(二)各民族边民牢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国家边防安全边疆稳定的基石
滇东南地区位于中国的边防前沿,是多民族聚居区。这些民族亲历了中越边界从藩属之界(53)越南自公元10世纪独立后,奉中国为尊,开始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向中国历代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中法战争以后,通过《中法续议界务专条》《滇越界约》等不平等条约,在中越两边立界碑。中越边界不再是藩属之界而成为现代意义的国界。变为现代意义的国界的过程。在清代中越边界的两次划分(54)中越第一次划界在清朝雍正年间。雍正二年(1724年),交趾国王派兵侵占开化府逢春里(今马关县)黑河(大赌咒河)以北一带猛康、都竜等三十多个中国村寨,进逼逢春里城南二里处马白讯小溪(小赌咒河)。清廷于雍正四年(1724年)派云贵总督鄂尔泰与越方交涉议定边界。中越第二次划界在中法战争以后,文中已述及。中边民都表现出积极归顺中国的意向,在后来的抗法斗争中舍身为国保边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的各族人民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始终在发挥作用。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55)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滇东南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清代的两次中越疆界划分使滇东南各族边民的国界意识变得清晰。在反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协同作战,戮力同心,共同对付来犯之敌,国家意识得以升华,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