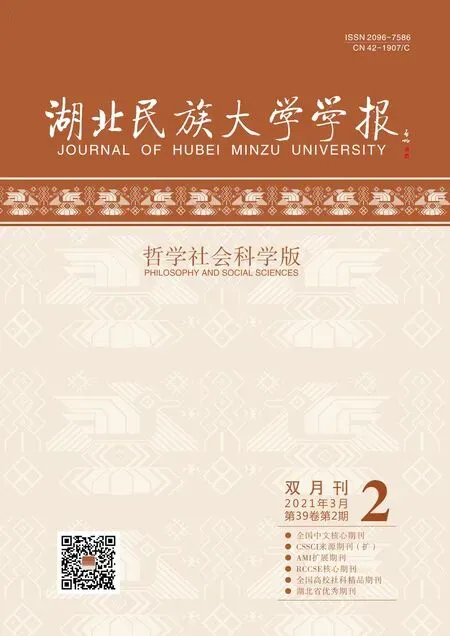生长的“时空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刍议
2021-01-13谢龙新
谢龙新
1949年10月1日,诗人胡风参加了开国大典。数日后,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长诗《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的正中间/ 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的/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屹立着像一尊雕像……”(1)桂兴华:《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1949-201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1页。
这是第一乐章《欢乐颂》的开篇第一小节。不难发现,这是个奇妙的开篇。本节主体是写“空间”,“主席台的正中间”“四面”“正前面”“屹立”等都是空间表达,而整诗却以“时间”领起——“时间开始了”。在这里,时间和空间融合在一起。巴赫金将这种一体化的时空关系称为“时空体”。毫无疑问,胡风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时空体”:新中国的诞生和新时间的开始。
本文将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考查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时空体,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的特征和品格。
本文所论话题有两个重要的学术背景。其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凝聚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使“民族叙事”超越了“汉族—少数民族”框架下的“族别叙事”,使重新思考“民族叙事”的特征和内涵成为必要。其二,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族的地域空间已超越了民族聚集地的原初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空间更多地指向了“世界”,“民族叙事”的他者因此也更多地指向了“世界他者”,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形象”成为“民族叙事”的重要内涵。在此背景下,重新定位“民族叙事”尤显重要。
上述背景也是本文立论的逻辑起点。目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渊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价值意蕴等,然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途经的民族叙事却相对被忽略了,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仅有李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黄伟林的《转型时期民族文学的国家责任》(《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等少数论文正面论及该问题。此外,胡亚敏提出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差异性”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叙事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借助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本文将思考如下问题:民族共同体与“时空体”有何逻辑联系?中华民族“自觉”以来经历了哪些“时空体”,并生成了什么样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应有什么样的特征和品格?
一、民族共同体与“时空体”的逻辑联系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由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有机的、“生长”的“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习近平:《在接见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的谈话(摘)》,中国民族年鉴编辑部:《中国民族年鉴2016》,2016年,第2页。“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生命体”的理论内涵。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自在”和“自觉”的论断在逻辑上也指向民族共同体具有“生命体”的特征。斐迪南·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本质应“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页。吉尔·德拉诺瓦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指出,“民族首先是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之中的。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在这一图解中,前者具有生物特点和自发性,后者由意识形态导向并具计划性。”(4)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6-67页。并且,民族常被“拟人化”(personified),被描述为“集体的个体”(collective individuals)。民族叙事因此会采用“传记”的形式。(5)Loring M. Danforth. Is the “World Game” an “Ethnic Game” or an “Aussie Game”?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Australian Soccer. American Ethnologist, No. 2 (May, 2001), pp. 363-387.就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既是共同体,也是“生命体”。
既然是生命体,就有其生长的时空。时间和空间是生命体存在的“先验结构”,并且,对生命体而言,时间和空间是一体化的。很难想象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也很难想象时空分离的生命体。生命体必在“时空体”之中。因此,作为生命体的民族共同体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尽管巴赫金曾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关于“时空体”的探讨却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用以指称“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6)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在时空体里,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7)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时空体”理论对认识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时空体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和时代性。时空体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生成,并发展变化的,每一种时空体都凝聚着特定的时代文化精神。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命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凝聚着特定的时代内涵。而且,自20世纪初梁启超以“中华”命称“我族”,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深刻反映了“命运共同体”的含义。特定时空体生成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意识,分析这些时空体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而且对重新认识“民族叙事”也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时空体在时间上具有未来优先性,因而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它是受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其中包括未来观念所决定的。要借助未来以丰富现在,尤其是丰富过去。”(8)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时空体指向未来的属性对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未来考量,是基于对当下时空体(“世界舞台”)的科学判断,进而对未来愿景进行的顶层设计。
再次,时空体在空间上具有与他者的“对话性”。每一个个体(“生命体”)都是一个时空体,无时无刻不面对一个具有差异性的“他人世界”,个体只有与“他者”对话才能完成自身。“各种时空体相互渗透,可以共处,可以交错,可以接续,可以相互比照、相互对立,或者处于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些相互关系共有的性质,是对话性。”(9)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空间上的“他者”是生成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与他者的张力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不同的时空体有不同的“对话性”,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西方他者的“独白”,但在当下,与“世界他者”的交流和对话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最后,时空体还是一个价值范畴。“时空体在作品中总是包含着价值的因素。”(10)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时空体是对世界整体图式的把握,是对特定时空中人的存在价值和世界观的总体把握。“每次要进入涵义领域,都只能通过时空体的大门。”(11)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336、446、436、452页。时空体不仅凝缩了个体对世界的体认,而且是个体实现其价值的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毫无疑问具有价值属性。这种价值不仅体现为时间上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跨越不同的“时空体”,而且体现为空间上与他者的“对话关系”——通过他者确认自身。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自在的实体,也是一个自觉的实体。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1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所谓自觉,首先体现为以“中华民族”对“我族”进行命名。命名是一种话语实践,自我意识通过命名得以形成。“我”的整体意识是在“他者”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而言,这个“他者”不是拉康的“镜像”,而是具体实在的“西方列强”。因此,“中华民族”的自觉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他者处于一种空间张力之中。这种张力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生长过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不同的时空体。中华民族与他者的张力关系是本文考察时空体变化和思考民族叙事的重心。
二、民族意识的“生长”:从“门坎”时空体到“广场”时空体
2015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指出“近代以来,我们两国都经历了从任人欺凌走向民族独立、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13)习近平:《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在越南国会的演讲》,《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7页。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15)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1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开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封闭”带来的危害。
“闭”和“开”是生命体的两个简单动作,但正是这两个简单动作决定了生命体对世界的感知视角和体认方式。并且,“闭”和“开”指向了一个重要的时空体——“门”。作为生命体的“中华民族”正是在“国门”的“闭”和“开”中、在与西方他者的空间张力中形成“我族”意识,并在时空体的变化中不断成长、壮大。“门坎”是“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和价值意味的时空体”,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意味着“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16)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次性质不同的“门坎”时空体,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意识。
第一次是历史的“闭”和被动的“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形成的“天下观”,历史地决定了国门的封闭。这种封闭的“天下观”在晚清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被打破。“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的。”(17)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可以说,正是历史的“闭”导致了被动的“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被命名,民族意识被激发。“国家、社会、个人已被民族主义整合进‘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社会、激发民族主义情绪。”(18)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38页。此时与西方他者的关系不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不是“对话”,而是西方主体的一元“独白”。此时的民族意识是救亡图存,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是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危机”使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历史考验,必须跨过这道“门坎”才能实现命运的“转折”。
第二次是主动的“闭”和主动的“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跨越了第一道“门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此时的民族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建构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9)毛泽东:《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此时与反帝反封建时期的民族意识明显不同,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因此是一次主动的“闭”。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次历史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一次主动的“开”。民族发展和民族振兴成为民族意识的核心,发展经济、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的现实追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20)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这场革命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更为重要的是,从深层次上改变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既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视阈看世界,又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看中国,是中国与世界紧密互动的过程。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方世界是以‘敌对’式他者来反衬中华民族建构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世界则是以‘合作’‘伙伴’式他者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建构。”(21)赵刚、李墨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属性》,《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两道“门坎”,两次跨越。“门”作为一个空间实体在这里获得隐喻性含义,“门”的“闭”和“开”指向中国和西方的空间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对西方他者的体认并与之冲突中不断变化(“生长”)的。同时,“时间在门坎这一时空体里,实际上只不过是瞬间”。(22)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3、402、397页。“危机”和“转折”具有时间属性,是“改变生活的决定”的重要“时刻”。中华民族从独立解放到发展振兴,走过的却是艰难的、“漫长的”时间,经过前仆后继的抗战和革命时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间,最后才来到跨越“门坎”的仪式性“时刻”。“门坎”时空体的“转折”意味着它开启了指向未来的时间。
那么,在“改革进入深水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又会经历怎样的时空体变化,形成怎样的民族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新时代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十九大报告无疑是最科学、最权威的文献,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十九大报告在时间上立足历史和当下,指向未来,在空间上立足中国,包容世界。十九大报告本身就体现出时空体的价值内涵。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十九大报告面向“世界”发出的时代强音,不仅勾画出中华民族作为“生命体”的时代肖像和世界责任,而且指明了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时空体——“世界舞台”。
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舞台”被表述为“广场”。广场是“是拉伯雷展现新世界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体现着最具人性的生活,人以及他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一切事件与时间空间形成崭新的关系。”(24)梁佳、刘进:《从巴赫金的“广场”理论看微博空间》,《新闻界》2011年第2期。在广场时空体里,过去“垂直的”等级关系转换为平等的毗邻关系,“这时,毗邻关系中的所有成员(整体的所有成分)都具有同等的价值。”(25)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3、402、397页。“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广场式的交往。”(26)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公开、平等、自由、开放、对话是广场时空体最核心的特征。广场时空体是创造未来、创造新世界的时空体,“把现实生活(历史)同现实地球连接起来”。(27)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3、402、397页。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世界舞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略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定位和民族意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等无不围绕“世界舞台”这一时空体展开。
新时代,新世界,新征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从根本上说来,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8)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站起来”和“富起来”与两次跨越“门坎”形成的独立解放和发展振兴的民族意识相对应,“强起来”则是新时代“世界”成为“舞台”的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反映了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使命,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责任担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在“世界舞台”时空体背景下提出的面向未来的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报告的表述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他者已不是“西方”,而是“世界”。只有通过体验他者,才能体验自我。自我只有在他者的帮助和映照下才能完成自身。新时代的主体是交互主体,新时代的他者是共在的他者。“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论断,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责任和未来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7页。新时代中国的责任担当体现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体现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愿景。
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华民族跨越两道“门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生命体”的中华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自我”意识,并形成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成长故事。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的品格和特征
在民族认同理论,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叙事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被反复调用。“民族叙事,作为一种有效的话语实践,连接着民族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进而塑造了该民族的文化认同。”(30)陶国山:《话语实践与认同建构 论文学话语下的认同建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在《民族与叙述》的导言中,霍米·巴巴使用了“叙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的概念,认为民族关系可以通过界定民族边界的叙事加以建构和识别,并邀请读者“通过研究民族的叙事表达来研究民族”。(31)Homi K.Bhabha.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Homi K. Bhabha, ed. London: Routledge,1990,p.3.民族叙事是一种言语行为,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实践具有“生成”和“生产”的作用。尽管文化认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民族理论的某些观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并不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观点对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正如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导言中所说,“真正理论上的创新和政治上的关键,是需要去思考超越起源的和根本的主体性,进而去关注那些在文化差异的表达中被生产的时刻和过程。”(32)Homi 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p.1.
那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如何理解民族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叙事应充分关注其实践品格。中华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坚实”的路。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叙事不是对民族过去的“想象性”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叙事一方面要反映中华几千年来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尤其要展现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自觉”的过程;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未来,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塑造民族未来形象发挥作用,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责任担当提供话语力量。“奥斯汀的语力概念带来世界的改变,……文学言语行为的语力创造了这种改变。”(33)Lubomír DoleŽel,“Mimesis and Possible Worlds”, Poetics Today,Vol. 9, No. 3, 1988.叙事的“操演性”即这样一种语力(force of the utterance),一种通过话语创造“现实”的力量。因此,民族叙事的实践品格不仅在于能够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更在于能够“生成”民族意识,在具体时空中创造和改变现实。民族叙事的这种“操演性”力量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发展振兴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都发挥过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叙事不应忽视与“他者”的空间关系。关于民族叙事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叙事的“文化定位”,而对“空间定位”有所忽略。民族认同不仅是文化认同,也是空间认同。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一个空间,尽管这个空间不一定是地理上明确的界域。“我族”不仅是文化上具有归属感的认同,同时也是空间上与“他族”的对位,甚至可以说,没有“他族”就没有“我族”。梁启超说,“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如上文所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始终伴随着与“他者”的空间张力关系。从“西方他者”到“世界舞台”,这种关系经历了如巴赫金所说由“垂直的”等级关系走向了平等的毗邻关系。当代全球化视域下,尽管“世界”已变成“舞台”,但“我族”与“他族”这种空间张力关系并不会消失。正如胡亚敏先生指出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要超越民族的界限,融入国际的大循环,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西方文化对区域文化的稀释,警惕全球性话语或西方话语取代了地方话语。”(35)胡亚敏:《开放的民族主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他者”是促进中华民族形成“我族”意识的“他性”因素,并且是中华民族由“封闭”到“开放”、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外在动力。因此,“他者”不仅是民族叙事的重要主题,而且是理解民族叙事的重要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无疑是民族叙事重要的书写对象。但这并不影响民族叙事的时代性。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民族意识。民族叙事不仅是表现时代意识的载体,而且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与“他者”空间张力越大,民族叙事的时代性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叙事都是宏大叙事,都是“主旋律”叙事。抗战叙事、革命叙事、改革叙事等等都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叙事,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振兴贡献了力量。民族叙事的表现不仅是如霍尔所说的传统、神话、民间观念等因素(36)Stuart Hall,David Held,Don Hubert,Kenneth Thompson,eds.,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6,pp. 613-615.,还应呈现时间中的当下和未来。因此,民族叙事的时间性不仅是过去式,而且是进行时和未来时。民族叙事的时代性决定了其具有向未来开放的属性。“世界舞台”是一个对话的“广场”,是具有创造性的时空体,民族叙事必将在这个“广场”上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形象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叙事还必须处理如何呈现传统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是民族叙事的重要面相,也是民族认同理论关注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37)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大会上讲话》,《祖国》2015年第1期。“根和魂”在文学上的表述就是“故乡”。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故乡”,是文学的“故乡”,是中华儿女无论在哪儿都斩不断的“乡愁”。霍尔所说的传统、神话、民间观念等民族叙事因素可以统归为“故乡叙事”。那么,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开放的、发展的时空体。“故乡”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时间和空间:“故”指向时间,“乡”指向空间。“故乡”一词在语义内涵上意味着“走出”,只有“走出”才是“故乡”。因此,“故乡”内在地包含了开放的含义。同时,“故乡”意味着空间“走出”之后时间上的“回望”。一方面,“回望故乡”是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和确认,寻找自己的“根和魂”。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另一方面,“回望故乡”“不是把过去作为古董保存下来,更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历史留存的东西,而是把过去视为对当代的参照,促使我们审视现在的生活。”(38)胡亚敏:《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因此,“故乡”又是一个发展的时空体。民族叙事不是对文化传统的简单复现,而是当代视角下的“反观”,是富有当代情感的未来期许。“只有摒弃那些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才能轻装前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形态的‘民族’所强调的不是过去和传统,而是着眼于当今和未来。”总之,民族叙事对传统的书写既是文化寻根,也是文化反思;既是对民族历史“乡愁式回望”,也是对民族未来“期许性展望”。民族叙事这种特殊的时间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是开放的、发展的书写。
在方法论上,胡亚敏先生提出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差异性”研究对民族叙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民族主义”往往与“自尊”相联系,进而发展成唯我独尊的“自大”,这样就容易形成“封闭”的观念。“开放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被视为关系概念。“‘民族’是一个关系词,用来表示世界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民族的概念往往与另一地域的他者相区别,是在与他者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因此,“开放的民族主义”主张在空间上向“他者”开放,“它一方面坚持民族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渴望立于世界之林。”同时,“开放的民族主义”也主张时间上“历史”的开放,坚持民族和民族性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不断摒弃、吸收、转换的过程”。“开放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坚持民族的差异性和有容乃大”。(39)胡亚敏:《开放的民族主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差异性”研究既是对“趋同性焦虑”的抵制和解决,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研究应该持有的立场和态度。“差异性研究所强调的民族认同并非刻意追求某种独特性,而是追求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此,“差异性研究也是开放性研究。”(40)胡亚敏:《论差异性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差异性研究强调研究的“国际视野”和“主体的反思意识”,并致力于中国学派特色的理论建构。开放性和差异性是一体两面,开放性是差异性的前提,只有开放才能显示差异;差异性是开放的目的,只有显示了“中国特色”才能在“世界舞台”找到自身的位置。坚持开放性和差异性是民族叙事和民族叙事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民族叙事是构建“民族形象”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从“故乡”走来,经过近现代民族“自觉”后的两道决定性“门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空体的变换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长”,民族叙事也随着时空体的变换“生成”不同的“民族形象”。开放是时空体的属性,也是民族叙事应有的属性。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将是民族叙事的重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