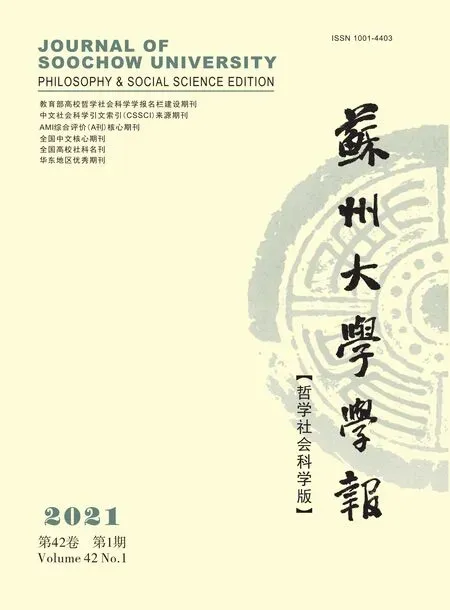共享经济平台用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及其法律应对
2021-01-08张凌寒
张凌寒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共享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网络灵活就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劳动方式。互联网灵活就业以其“灵活性”(Flexibilization)特点获得了就业者青睐,庞大数量的劳动者以“U盘”的方式于平台就业,形成了“即插即用,即拔即走”的工作状态。而雇主不再需要依据固定劳动合同向雇员承诺工资福利等保障,也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等法律替代责任,因而灵活就业受到用工需求方的广泛欢迎。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共享经济2020年参与服务提供人数为7 800万人,且共享服务业态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大幅高于传统服务业态。[1]“兼职就业成为共享经济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就业形势。滴滴平台上兼职司机大约占到九成,78.9%的兼职司机每天在线时间少于5个小时;美团平台上52%的骑手每天工作4个小时以下。”[1]碎片化的、松散的、非正式的、基于任务的劳动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盛行,这种灵活就业的劳动形式被称为“宏观的微观劳动”,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范式转化”。[2]
共享经济带来的劳动形式变化是对未来劳动关系的根本性挑战。这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于平台用工的性质灵活就业所产生的劳动关系应如何认定,劳动者是雇员抑或是独立承揽者等性质争论。尽管近年来学界涌现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仅局限于对用工关系认定、劳动者保护等层面,尚未有学者关注这种劳动带来的性别层面的影响。
共享经济的灵活就业方式对女性有着天然的吸引力。首先,弹性的工作时间方便女性有更多时间育儿与家务。其次,共享经济的灵活就业方式可承接女性退出职场后的收入需求。平台在网络发布任务,将工作变得碎片化,而这种灵活就业的方式使得女性更容易投向零散任务服务。[3]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在劳动市场的整体萧条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相较男性受到更大冲击。
那么,共享经济是以重要的、实质性的方式增加了妇女的机会,还是仅仅复制了“旧”劳动关系的性别不平等?随着各国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人数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上升①(1)①2020年仅美国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人数就占到劳动力总数的10.1%。See Greg Iacurci:The gig economy has ballooned by 6 million people since 2010.Financial worries may follow,https://www.cnbc.com/2020/02/04/gig-economy-grows-15percent-over-past-decade-adp-report.html,2020年10月5日访问。,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对现在灵活就业的女性具有现实意义,也关系到未来社会生产方式中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的重大议题。本文以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中性别平等受到何种影响为切入点,探讨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关系性别平等问题与传统用工性别问题的异同,进而讨论现有法律在灵活就业保护性别平等中的功能缺失,以及应如何调整法律促进共享经济时代的性别平等。
二、共享经济中平台用工的性别平等:赋权有限与歧视延续
共享经济就业被认为可促进劳动市场的性别平等,其匿名性、时间灵活性使得更多女性获得了就业机会。但实证研究发现,平台算法画像突破了匿名性限制,而同等收入条件下,灵活就业比固定劳动合同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长,性别赋权效应有限。与此同时,共享经济的灵活就业延续了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性别歧视与相对较低的工作收入,并且由于性别歧视更具有隐蔽性、损害不宜察觉与证实、劳动性别隔离更严重等特征,女性群体由于缺乏保障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形成了第三代职场性别歧视。
(一)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性别平等假设
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一般指的是非雇佣的全职工作,是以从事短期工作、合同和自由职业为主的劳动力。共享经济的核心是数字劳动平台,如网约车平台Uber、滴滴,美团外卖骑手,TaskRabbit等短期任务在线平台,以及管家、保洁、搬家等提供杂工的家政服务平台。除此之外,国外也有Upwork这样的自由职业网站,它提供从事艺术创意类工作的劳动者与潜在客户的交易洽谈平台,也有诸如亚马逊机械突击队(Amazon Mechanical Turk)这样的临时工作“众包市场”。尽管每个数字劳动平台都有不同的做法和政策,但其共同点是平台利用技术将客户与短期或按任务的服务相连接。伴随着智能手机、无现金支付系统和客户评论网站的使用增加,以及临时和应急就业的日益普遍,这些平台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上升。
一般认为,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方式对促进两性就业平等、赋权女性经济能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就业形式的匿名性。劳动者在网上提供服务时享有更大程度的包容性,例如女性一般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到灵活就业中,而这可以抵消一般劳动市场中女性面临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因在线任务所产生的收入计件而不应受到劳动者性别的影响。[4]除此之外,一般假设认为如果灵活就业的形式并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露面(如在线客服),这种工作关系被认为是横向的而不是科层制的,女性也更加容易实现在与雇佣者谈判中的同工同酬要求。[5]22
第二个原因是这种就业形式的灵活性。共享经济中的灵活就业在工作时间和任务方面具有固定工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为劳动者提供较短的工作时间安排,可能有利于寻求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共享经济中灵活就业的蓬勃发展可能能够增强女性的权能,对促进性别平等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促进性别平等的假设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在共享经济中,个体具有完全的劳动自主性,没有雇佣者告诉他(或她)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承担哪些具体的工作任务,劳动者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劳动市场,劳动者个体具有劳动与否、何时劳动的自主权(或者这种自主权远高于固定就业)[5]8,换句话说,劳动者个体是其工作和生活的“设计师”。因此,基于这样的假设,共享经济就业的灵活性为男性和女性提供了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机会,甚至能够改变正常的社会角色分配。
(二)共享经济就业性别赋权迷思的破解
实证研究发现,平台算法画像突破了匿名性限制,而同等收入条件下,灵活就业比固定劳动合同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长,性别赋权效应有限。
第一,匿名性并不存在,平台通过算法画像对劳动者的条件了解更为详尽。共享平台灵活就业的劳动录取过程一般有雇佣者(在线任务发布者)自行挑选和平台算法匹配劳动者两种形式。劳动者报名需要填写姓名和上传照片。潜在的雇佣者挑选或者算法自动匹配成功后,劳动者接受条款后签订合同。工作任务完成后,雇佣者通过平台托管账户向劳动者提供工作报酬,并以评分的形式将其对劳动的评价反馈给平台,平台按照每笔交易的百分比收取费用。
算法对劳动者和潜在雇佣者的画像在匹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网约车中,一个“可靠的”司机可获得更多的订单,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研究,一个完成2 500次出行的网约车司机比一个在平台上完成不到100次出行的司机每小时多赚14%。[6]原因是平台算法更倾向于随时可以接受任务的网约车司机。男性司机通过更长的每周开车时长积累比女性司机更多的经验,而且更少由于家庭和育儿的原因停止网约车驾驶。作为对更高投入时长的回报,男性网约车司机享有的报酬更多。
第二,虚假的工作灵活性。同等收入下灵活就业反而要求更长的劳动时间。根据研究,非全职雇佣的劳动者如果想在数字平台上获得全部收入,需要的工作时长比起全职工作的员工来,劳动时间相等甚至更长。[7]除此之外,平台通过架构设计来监控劳动者承担了多少工作任务,而未达到平台要求比例的劳动者的账户则可能被停用。如数字劳动平台TaskRabbit的劳动者必须在接到任务的30分钟内做出回应,并至少接受85%的任务,否则就有被停用的风险。这种“随叫随到”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劳动者以更多无偿等待的时间来进行工作。一旦劳动者身兼多职,则不可能做到数字平台随时响应工作任务的要求。根据美国和印度的研究发现,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劳动者们必须每天无偿在线工作数个小时。[7]
此外,由于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工作往往为杂务、送货、司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因此报酬相对较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才能实现财务自给自足。尽管Uber这样的网约车平台在招揽司机时宣称,劳动者能够决定自己的日程安排。但是在深夜或清晨等时段工作,工资远高于正常的工作时间。①(2)①如滴滴代驾超过12点的费用在北京为99元,10点以前的费用为39元。劳务众包平台亚马逊机械突击队的工人表示,他每天花多达17个小时完成任务才能够赚取足够的收入。[6]因此,看似能够照顾家庭的灵活就业,反而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中性别不平等的延续
共享经济就业中的灵活性看似成为女性获得平等报酬和工作机会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延续传统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总体来说共享经济促进了社会就业并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平台用工的录取与报酬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换句话说,共享经济为社会创造了更多劳动和收入机会,但这些收入机会更多地被分配给了男性劳动者。
目前多国的社会调查也显示女性从业者占据了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更大比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广泛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从而增加了女性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参与率。[8]我国学者2016年进行的共享经济从业者小规模(4 762人)调查显示,从受访者的性别构成看,在被访人员中,男性为859人,占比45.72%;女性为1 020人,占比54.28%,略多于男性受访者。[9]同时期美国的一份小规模调查(4 579人)显示,女性占据了55%的共享经济劳动者和44%的在线卖家(女性占同期美国成年人口的52%)。[10]
这样的社会调查结果掩盖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将灵活就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补充来源存在巨大差异,更多的女性将平台用工作为部分补贴收入的来源,而男性更多将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虽然表面上女性从业者总数更多,但依赖其作为全部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中男性比例更高。据2019年美国的调查显示,在所谓的“积极性”(更加正规)的共享经济劳动力中,男性占到了74%。[11]结合将共享经济劳动收入当作主要收入和补充收入的条件,调查中60%的男性从数字平台上寻找工作的原因与收入有关,而所有女性中约有40%。[11]在控制了这一变量后,可以看出获得工作机会和工作报酬上仍延续了传统的性别不平等。
第一,获得劳动机会的差异。劳动力参加共享经济可分为将灵活就业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作为其部分收入来源两种情况。在北美和欧洲,将共享经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要是白人和男性。[12]女性工人的加入条件不利,其在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参与率以及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但目前的调查很难表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环境下这种情况的普遍性。[11]女性在共享经济中定期工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英国,女性在定期工人中仅占16%[13],而另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女性在所谓的定期工人中占26%。[14]
第二,女性在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获得的收入低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从业者,延续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现状。在控制了就业形式(主要还是部分收入来源)、受教育程度、职业分配、反馈变量等因素后可发现,平台用工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4]2016年美国的调查显示,女性的零工工作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低于男性(16%,而男性为23%)。[15]2018年有研究分析了美国Uber平台上100多万名司机的数据,发现男女司机之间有7%的收入差距。[6]2017年在英国的调查显示,75%的女性灵活就业年收入低于11 500英镑,而在所有工人中这一比例为61%;2018年英国的调查则验证了这一结果:49%的女性零工在上一年的收入低于250英镑,而男性为35%。[17]这显示传统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与收入不平等仍在共享经济灵活就业领域延续。
(四)平台用工中性别不平等的升级:职场性别歧视3.0
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为未来劳动关系勾勒出了大致的发展方向,而平台用工情况下的性别差异可以被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歧视3.0”。如果将职场性别歧视的第一阶段描述为“排斥”——禁止女性进入职场,第二阶段描述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职场规范,那么在平台共享经济、灵活用工、数字劳动等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则具有了新的隐蔽性:更隐形的性别歧视、无法衡量的损害结果、更严重的性别隔离,以及女性群体更弱势的劳动地位——女性就业兼职化加剧。
第一,更隐形的性别歧视手段。在线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和既往行为轨迹进行画像,其可能考虑的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从个人资料中提取的经验年限、使用的手机等,这样可以获得本来不在求职中披露的性别信息,并基于此进行工作的匹配。而这样的性别歧视并非直接将性别作为考量要素,并且除非有专业的计算机知识否则极难发现。如亚马逊算法性别歧视事件中,亚马逊的算法模型通过十年来获得的求职简历给求职者评分。由于男性求职者较多,算法模型自动降低包含“女性”这个词简历的评分。例如简历中存在诸如“女子国际象棋比赛冠军”或两所女子大学的名称,亚马逊的算法系统就会自动进行降分评级。这种隐形的性别歧视算法自动将男性与高收入职位挂钩,不仅过滤掉女性求职者、固化性别角色、加剧职业领域的性别隔离,而且极具隐蔽性而难以发现。
第二,难以察觉的歧视损害结果。一直以来劳动市场中的招聘就业性别歧视较为直接,如直接拒绝女性获得某职位,或者直接给女性较男性更低的工作报酬。但是在网络平台的劳动中,性别歧视并不以正式的障碍或公开的排斥形式出现。表面上看,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自由地参与网络任务,且是公平的按件计酬。但是性别的薪酬不平等发生在平台促成的劳动中,或需要大量的数据统计方能获得结论,如之前针对百万Uber司机数据分析得出的薪酬调查结论。又或者必须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如“谷歌职位广告歧视案”中,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名为“广告钓鱼”(AdFisher)的工具[17],以探究谷歌在第三方网站上提供的广告中的性别歧视。研究发现,谷歌对男性求职者网络用户展示的高管职位广告中,薪酬要远高于同等的女性求职者看到的薪酬。[18]
第三,更严重的性别隔离。平台用工中存在比现实劳动中更高的性别职业隔离。绝大多数男性从事外卖、司机等工作,而女性则偏重于清洁、家政、护理或者写作编辑类工作。例如,在英国,在提供清洁服务的Hassle平台上86.5%的工人是女性,而在送餐平台Deliveroo和私人交通平台Uber上,分别有94%和95%的工人是男性。[13]澳大利亚的相关调查也支持男性和女性在共享经济中存在更为广泛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19]本身平台算法在进行职务分配的时候,也会得出女性仅“适合”当行政助理、护士的错误结论,通过算法按类别为不同性别的求职者推送不同求职信息,从而加剧社会劳动的性别隔离。我国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也提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女性兼职化”,即女性更多地从事兼职等灵活性程度较高的职业。①(3)①《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建议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载《中国妇女报》2016年11月28日第4版。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服务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多行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性别隔离问题。②(4)②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第四,女性群体更弱势的劳动地位。性别弱势、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等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随着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研究显示,共享经济中更依赖灵活就业维持生计的人常常来自低收入家庭,往往从事体力的按需工作,如打扫卫生、驾车、洗衣等。虽然灵活就业对这类劳动力群体增加就业及收入有利,但是灵活就业的缺乏福利、过长时间工作、收入不稳定等特点,容易更为加剧其弱势地位,使其更容易与用工平台妥协,甚至放弃应有的安全保障和权利。例如中国的外卖骑手的处境引起了社会关注,其被称为“被困在系统中”,骑行的交通安全由于外卖时长要求过短无法得到保证。③(5)③《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人物》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2020年10月5日访问。国外对印度、肯尼亚、墨西哥和南非平台用工中家政工作的研究发现,“传统”家政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权利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人的剥削和歧视,在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中得到了加强——通过新的、技术化的方式,如通过平台评级和评论系统。[20]美国最近一项关于类似护理工作平台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些发现。[21]
三、现行法律规范应对平台用工性别不平等的三重困难
面对平台用工对女性赋权有限,并且延续职场性别不平等,甚至性别歧视更加隐蔽的问题,现有法律法规可资利用的手段有限,并且面临着三重困难:平台用工关系认定规则不明确,缺乏间接性别歧视法律规定,以及平台责任认定存在障碍。
(一)第一重:平台用工关系认定规则尚属待定
平台用工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究竟属于何种用工关系尚未得到法律确认。平台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将劳动的相关风险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当平台用工的全体劳动者尚缺乏完善法律制度保护时,更无法提供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方面的劳动者保护。
在平台促成的按需劳动的背景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较为复杂。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和远程办公早已存在,但近年来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不断增长的在线服务经济,将合同工模式应用于各个行业。平台共享经济的灵活就业,究竟是雇员身份还是民事合同关系,在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巨大争议。如果劳动者被认定是平台的雇员,则有资格享受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等劳动保护制度。当然这一主张遭到了平台的反对,平台坚持认为这些人是独立的任务承包商。如网约车Uber等公司将司机视为承包商而非雇主,从而避免了加班、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工人保护措施。[5]2019年4月美国劳工部发布意见书,倾向认为网约工不是《公平劳动标准法》意义上的雇员,不受有关工资工时的保护。④(6)④See U.S.Department of Labor,Opinion Letter,http://www.dol.gov/sites/dolgov/files/2019-04-29-06-FLSA.pdf,2020年10月5日访问。2019年6月,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发布《建议备忘录》,认为网约车司机不是《国家劳资关系法》意义上的雇员,不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⑤(7)⑤《建议备忘录》,https://www.nlrb.gov/news-publications/nlrb-memoranda/advice-memos,2020年10月5日访问。
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民事承揽合同,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平台从每一笔交易中获得了佣金,使用算法匹配需求方与劳动者,并对劳动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如行驶路线、客户评分等制度);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何时工作、是否接受工作享有比雇员更多的自主权。德国学界已提出,网约工是“类雇员”,是介于劳动者与独立承包人之间的劳务提供者,有不同于劳动者的自主性,但在一些方面有类似劳动者的社会保护需求。基于类雇员理论和制度,德国形成了“劳动者-类雇员-自雇者”三分法框架,面对平台用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制度弹性。[22]
由此可见,共享经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尚处于争取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阶段,社会对劳动者的权利并未发展至关注性别平等的阶段。网约工在工资、工作时间、职业伤害保障等多方面,有现实的社会保护需求。[22]我国也着手制定政策解决灵活就业中突出的职业伤害保障与社会保障问题。①(8)①国务院于2019年8月8日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避免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区分了“平台企业以劳动关系形式雇佣的劳动者”与“灵活就业的新型平台用工劳务提供者”;并针对当前突出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指出,“鼓励平台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分散风险,更好保障各方权益”;同时“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更多平台从业人员参保”。但是,政策和法律层面尚未关注共享经济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灵活用工的劳动者受到的保护要比被视为雇员的保护少得多,缺乏产假、哺乳假等劳动制度的保护,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严重。
(二)第二重:我国尚无间接性别歧视法律规定
共享经济灵活用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往往以用工结果的方式体现。即往往平台在设定劳动规则时是“中立”的,但是造成了性别不平等的后果,构成了间接的就业性别歧视。然而,我国现在并无相关法律规制间接就业歧视,这为防治共享经济灵活用工中的性别不平等设置了第二重障碍。
首先,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禁止的是直接性别歧视,即“显性”性别歧视,对间接性别歧视重视不足。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的性别歧视属于“间接歧视”。间接歧视是指表面上看似中立的规定、标准或做法实际上对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或群体在机会和待遇方面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23]虽然我国女性就业权保护制度中有一些涉及性别歧视的禁止性规范,但这些禁止性规范并不能涵盖性别歧视的所有内容。直接歧视是指在相同条件下,故意根据人的某种特征(比如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给予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机会和待遇明显低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机会和待遇。如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个部门于2019年2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强调了对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规制以及完善针对招聘阶段遭受歧视的相关救济体制,还停留在仅针对招聘环节的显性性别歧视阶段。
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灵活用工中的性别不平等,由于两性不同的工作投入造成的平台对劳动者算法画像不同,进而加剧了两性获得就业机会与获取报酬的不平等。这是较为典型的由于既往的性别不平等延续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相比我国现阶段仍专注于直接性别歧视,国外尤其是美国法院应对性别不平等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早在1972年的判例中,就确立了禁止间接性别歧视的规则,甚至直接指出“任何表面上中立的,甚至意图上也是中立的做法、程序、测验,如果其运作会冻结以前的歧视做法造成的现状,仍然不能予以支持”②(9)②See Griggs v.Duke Power Co.,401 U.S.424,at 429-430(1971).。
其次,灵活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本身难以证明,而现阶段法院认定性别歧视造成的损害结果标准极为严苛,导致大量职场性别歧视案件以劳动纠纷而非侵权纠纷解决。灵活就业以及在线劳动的歧视本身难以证明,由于网络劳动通常是在所谓“匿名化”政策下进行的,而且没有面对面的交流。2000年至2016年52例职场歧视案件,案由中劳动争议所占比例最大,占据91% ,而平等就业纠纷、侵权类案件、人格权侵害案件仅分别占1.5%、1.5%与5%,反映了我国性别歧视案件特定诉讼理由的缺失。[24]2018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把“平等就业权纠纷”增列在“一般人格权纠纷”(三级案由)下的“四级案由”,对减少女性职场性别歧视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最后,平台用工歧视的故意难以证明。在国外的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中,学者们关注的种族歧视等也存在歧视故意难以证明的情况。[22]平台是商业机构必须不加歧视地对待客户(这里指劳动者)。③(10)③See Noah Zatz,Beyond Misclassification:Gig Economy Discrimination outside Employment Law,ON LABOR,https://onlabor.org/2016/01/19/beyondmisclassification-gig-economy-discrimination-outside-employment-law,2020年10月5日访问。因平台往往通过算法设定规则,而由于规则设定方法的技术性,平台可宣称其应适用技术中立规则。
由此可见,现有法律适用于规范平台用工性别歧视的第二重障碍,既包括我国本就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保护不力,更没有禁止就业中的间接性别歧视的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在反歧视法律相对完善的美国,也面临着平台用工歧视的故意、结果等难以证明的难题。
(三)第三重:平台法律责任认定存在障碍
如果法律要规范平台用工的性别不平等,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谁进行了歧视?应由谁来承担共享经济灵活用工性别不平等的责任?这是平台用工面临的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障碍——平台责任追究的困境。
第一,平台可以主张自己并不具有性别歧视的主观意图,仅仅是由于女性自身的原因产生了性别不平等的后果。根据美国学者对百万Uber司机收入进行的分析,惊讶地发现,在一个工作任务由不分性别的算法决定、薪酬结构直接与产出挂钩而并不需要与资方谈判的环境中,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平均每小时比女性多赚7%。[6]继而,其通过分析将原因划分为并表明这种差距完全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平台上的经验(即司机工作的时长)、对工作地点的偏好(主要由司机的居住地驱动,其次是安全)以及对驾驶速度的偏好。因此得出结论,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妇女无偿工作时间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以及基于性别的偏好和制约因素的差异,也会使性别薪酬差距持续存在。如果将过错作为认定平台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要件,则面临着平台“技术中立”的抗辩。
第二,平台可以主张第三方(任务发布方)的要求造成了参与工作的性别筛选效应,因此作为提供资源与撮合交易的平台不应当为第三方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平台经常以自己是“信息撮合者”而非实际的用工者提出对法律责任的抗辩。如闪送劳动关系认定案中,闪送提出自己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不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公司与李先生“双方间为合作关系,并主张公司也已为李先生等快递员投保商业保险”,李先生是为了承接第三方的工作任务受伤的。最后法院并未接受平台的抗辩,认定闪送平台虽然对李先生无工作量、在线时长、服务区域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但对每单配送时间有具体规定,超时、货物损毁情况下有罚款,因此劳动关系成立。①(11)①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案0108民初533634号民事判决书。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前两重障碍,平台也会以“技术中立”而不具有主观故意、第三方侵权而自己并无责任来推卸推进平台用工的相关法律责任,包括防止歧视促进平等的责任。共享经济灵活用工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现有的法律可以说不具有适用性,无论是从为女性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平等就业保护,还是应对间接的性别歧视,甚至连认定承担推进性别平等法律责任的主体都存在障碍,可谓困难重重。
四、促进平台用工性别平等的制度构建
促进平台用工的性别平等,亟需改变思路,将回答“谁进行了性别歧视”的问题转变为“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应缩小“数字性别鸿沟”,在平台用工入口处减少性别差异;其次应考虑平台在促成在线劳动中的角色与地位,要求平台承担促进性别平等的承诺,将性别平等的理念嵌入平台架构与算法中。最后,应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促进未来劳动关系中的性别平等。
(一)扩张职场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
职场性别歧视3.0表明应重新认识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及时调整应对新类型性别不平等的法律与政策,并重新思考促进劳动性别平等的新机制。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反性别歧视的规定均是针对直接性别歧视的规定。互联网时代的性别歧视3.0发生在平台上,但平台可能并没有性别歧视的主观意图。应通过考察平台用工性别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将性别不平等的结果作为认定性别歧视存在的标准,并以实质影响而非主观故意作为性别不平等的衡量要素。
理论上,性别平等中的经济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要素。机器学习算法虽然是自动运行的,但是机器学习算法是由人来进行编码的。他们可能会将一些固有的偏见编入其中,而这些算法也会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来进一步学习,强化设计者和用户本就已经存在的性别偏见。平台的架构和自动的算法运行可能会在无意中促进性别的不平等。
第一,主观意图不应成为认定职场性别歧视的必要条件。雇佣行为中雇主的故意歧视的主观意图,并非职场性别歧视的必要条件。在1971年的格里戈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像判断差别对待歧视那样去要求雇主须有故意,法官在判决中指出:“意图良好或者缺乏歧视意图并不能使得实施起来对少数族裔地位不利、与衡量工作能力无关的程序和测试免除其责任。”①(12)①See Griggs v.Duke Power Co.,401 U.S.424,at 431(1971).由此可见,法律追责的对象不仅是雇佣中歧视的动机,更包括歧视的结果。这一案件确立了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适用不仅禁止公然的歧视,也禁止那些形式上公平但操作上产生歧视效果的措施。
第二,性别差别影响的判断标准应成为衡量性别不平等的要素。我国未来反就业歧视立法中有必要引入“差别影响”这个概念,因为构成间接歧视的关键,存在事实上的“差别影响”。即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或群体在机会和待遇方面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歧视就成立。[23]当然,这种差别影响的判断标准也一直在美国司法界存在较大争议。1978年,美国发布的《统一雇员选择程序指导意见》提出了判断差别影响的4/5或80%的标准,因其计算标准模糊广受诟病。[23]但现在数字化平台用工的数据获得和统计条件远远优于四十年前,因此这种性别化的差别统计应更为易得。
引入间接歧视的概念,承认性别差别影响作为判断性别歧视的关键要素,可有效扩张职场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方可为共享经济灵活用工中的性别歧视3.0认定扫清障碍。
(二)要求平台算法“设计性别平等”
平台在促进灵活用工在线劳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平台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平台正是通过其架构——基本运行的规则,来通过技术能力和代码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平台的架构与算法,但它们却决定了数据在平台上的流动与运作。[25]34也就是说,平台上人(用工方与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平台的架构与算法决定的。
2019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指出,要致力于开发不带性别偏见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并确保人工智能开发所使用的数据具有性别敏感性。该报告强调了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应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编码者应该认识到算法的高效性、反复性和隐蔽性会导致编码偏见,产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灾难性影响。②(13)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成果文件《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8/t20190828_396185.html,2020年10月5日访问。算法性别歧视的“车轮”会碾压既有的社会性别平等成果。
平台应将“性别平等”理念嵌入平台架构与算法的设计中。现在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开始主张平台“设计隐私”或“设计个人信息保护”,即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从平台架构设计的层面嵌入平台,并贯彻到算法设计、平台内部规约制定、纠纷解决等多个平台运行的层面中。同理,共享经济的平台在促进在线劳动时应将“性别平等”作为设计的基本理念,以避免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设计平台架构,而不仅仅将性别作为收集劳动者个人信息的要素加以模糊或省略,更不能以歧视和偏见的方式对待女性劳动者。
平台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应从平台架构设计、平台研究者和平台用工政策制定者层面推进。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可以让平台向市场通报平均时薪,向任务者提供某些任务的通报平均工资,定期公布平均时薪,或向用工方和劳动者建议合理的报酬。平台可通过算法设计减少某些与性别相关的要素对自动化决策结果的影响③(14)③一些共享经济公司已经开始禁止发布基于性取向禁止用户的资料。Nick Duffy,Accommodation website Airbnb removes listing that banned gay couples,PINKNEWS,http://www.pinknews.co.uk/2014/11/23/accomodation-website-airbnb-removeslisting-that-banned-gay-couples,2020年10月5日访问。,研究现有的架构和算法是如何产生性别不平等的结果的。如果能够从设计部署层面和日常监督层面对平台架构和算法进行治理,并有行之有效的监测制度,则平台能够在避免用工性别歧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平台有能力通过主动的措施来促进性别平等。2015年Uber宣布承诺到2020年让100万女性司机使用其应用,并提出“开车不仅仅是上班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工作”。尽管Uber在现有的研究中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但是其就促进性别平等做出了一定的努力。④(15)④See Blaire Mattson,This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Women Take the Wheel,UBER NEWSROOM,https://newsroom.uber.com/driven-women,2020年10月5日访问。由于平台最容易获得有关其工人时薪和薪酬的大规模信息,以及对会员资格、个人信息类别、反馈分数等数据的控制权,因此平台本身最适合通过其技术能力和代码颁布事先规制的措施,以消除和抵制歧视。[26]促进共享经济灵活就业中的性别平等,将其视为女性的一种解放、平等的工作选择。①
(三)缩小“数字性别鸿沟”
世界范围内,缩小“数字性别鸿沟”是提高平台用工领域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仍然存在着深刻、持久的数字性别鸿沟。研究显示,获得数字技术的机会不平等是女性参与共享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平均而言,妇女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比男子低10%,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性低26%。②以印度为例,根据GSMA《2019年移动性别差距报告》印度只有16%的女性是移动互联网用户。③尽管政府采取了“数字印度”等举措,但数字扫盲仍然是女性数字性别平等中的首要问题。
这种对数字平台的不平等使用有可能将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排除在这些平台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之外,并由此延续进而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现有的不平等。技术嵌入社会的进程不可避免,为保障社会机会平等,需要单独为弱势群体提供摆脱贫困或进入劳动力市场较高质量部分的途径。[27]这就需要国家依据公共利益,采取广泛而积极措施,包括技能培训、软硬基础设施和降低进入壁垒专门政策。例如,2020年1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印发,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让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一些共享经济平台已经采取措施,通过短信等手段与工人沟通,克服数字文盲与缺乏智能手机造成的实际障碍。
(四)发展算法审计与公益诉讼制度
平台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应尽快发展性别歧视公益诉讼,以应对大规模难以察觉的灵活用工性别歧视问题。平台用工的性别歧视具有隐蔽性,依靠个体的经历甚至难以发现。目前已有的算法歧视现象大多并非用户个体发现,而由第三方社会组织通过算法审计发现歧视现象。原因在于:第一,个体难以发现信息权利受侵害之事实,即使发现,也很少提起民事私益诉讼寻求保护。第二,举证困难。用户个体缺乏信息收集、处理数据的技术。因此,应发展第三方算法审计与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受到平台用工性别歧视的个体可以得到相关救济。
第一,应推动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的设立。202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53条确立了事中的算法审计制度。草案条文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定期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采取的保护措施等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审计。”根据第53条,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从外部直接“穿透”至平台内部的算法运行层面。平台应对其算法自动化决策等信息处理活动定期进行审计,必要时监管部门有权启动对平台的第三方外部算法审计。
第二,应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应用于平台用工性别平等保护案件。《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66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法律层面将明确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平台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分散的个体权利损害的救济。公民个人无论是信息遭受侵犯,还是遭遇平台用工性别歧视,往往基于时间或经济成本考量难以实现维权。草案的通过生效将有效缓解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维权的艰难处境。
共享经济灵活就业带来的劳动关系变革刚刚揭开序幕。通过全社会多方努力,在未来的数字经济劳动关系中,规划和创造出真正的性别平等劳动市场。
①关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能力在形成歧视方面的作用,See Ben-David A,Fernández A M.Hate speech and covert discrimination on social media:Monitoring the Facebook pages of extreme-right political parties in Sp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27.(2016).
②See Rowntree,O.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18.GSMA Connected Women Programme.London:GSMA,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18/03/GSMA_The_ Mobile_Gender_Gap_Report_2018_Final_210218.pdf,2020年10月5日访问。
③See GSM Association,ConnectedWomen: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19,https://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19/03/GSMA-Connected-Women-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19.pdf,2020年10月5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