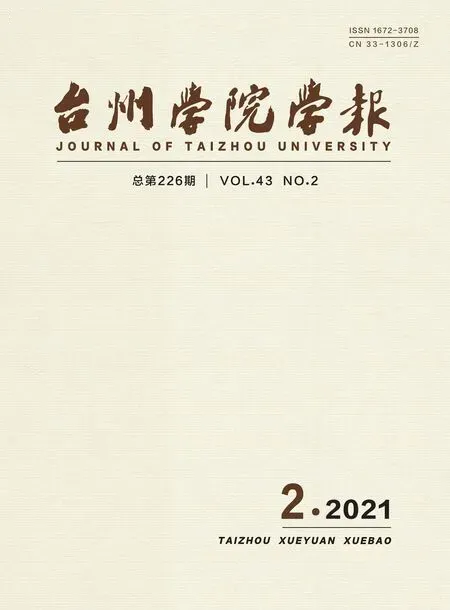浙东渔歌的传承现状与保护对策
2021-01-08陈辉
陈 辉
(台州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浙东渔歌是浙东沿海渔民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和海洋生活中形成的特定歌种。浙江东部濒临东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海洋渔业资源丰富。舟山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等。自古以来,苏浙沪闽一带的渔民汇集于此捕捞作业,由此带来文化的交流。源于海洋渔业生产劳动,起着组织劳动、指挥劳动、鼓舞劳动作用的浙东渔歌也应运而生,散布在浙江东部沿海的定海、普陀、嵊泗、岱山、象山、镇海、宁海、三门、临海、温岭、玉环、乐清、洞头等地。浙东渔歌既是铿锵豪迈的渔工号子,也是渔民劳动之余娱乐消遣的小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浙东渔歌,融海洋渔业生产、生活、民俗、信仰、语言、文化、艺术、娱乐于一体,属于海作文化区特定的民歌歌种。浙东渔歌是在浙东沿海渔区的人文历史、地域环境、社会背景、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民间艺术形式。如果离开了这方文化土壤,这种艺术形式便不可能存活。因此,浙东渔歌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浙东渔歌就是传承浙江海洋文化,保护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一、浙东渔歌的传承现状
浙东渔歌作为浙江民间音乐的瑰宝,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初,周大风先生就曾自发地在舟山民间采录渔民号子80余首,并将部分号子编入《中国民歌选》[1]。后来,随着国家对民歌收集、整理、编纂工作的重视,浙东渔歌分别被收入《中国渔歌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浙江民歌汇集》《东海渔歌选》《舟山渔民号子》等民歌集子中。浙东渔歌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于民间,是本土原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精神性、依赖性、易逝性、传承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浙东渔歌承载着丰富的地域人文历史,是海洋文化的历史见证,是浙东渔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渔歌出现了生存困境。
(一)后继乏人,濒临失传。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依附传承者个人存在的、口传心授的一种非物质形态化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不能脱离民族特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具体的区域历史及其社会环境而存在,它随创造它、使用它、传播它的人群的消失或放弃而消亡,即所谓“艺在人身,艺随人走,人在艺在,人亡艺绝”[2]87。渔歌依附于渔民的生产生活,离开了特定群体和特定场合,渔歌就无法生存。长期以来,渔歌在老一辈渔民中口头传唱,代代相传。目前被音乐工作者采集、记录下来的渔歌只是早期流传于渔民口头渔歌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渔歌有待于人们去发掘。因此,我们要寻找渔歌的传承人,趁那些会唱渔歌的老渔民目前还健在,尽快把渔歌记录、保存下来。
浙东渔歌的传承在从业者同行之间进行,但由于渔船上的人员组合并非长期固定不变,而是具有临时调整的自由性和灵活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改行转业的现象比较普遍,故传承谱系十分复杂[3]。目前,有据可查的舟山渔歌传承人(岱山谱系)主要有:
第一代传人於潮宗,第二代传人於景秀,第三代传人於嘉年,第四代传人於式仁,第五代传人於维裔,第六代传人於岳年、虞阿元、杨德才、何阿昌等,第七代传人林通玙、方正法、叶宽兴、周文利等,第八代传人於文宽、郑应法、洪国强、潘成昌等,第九代传人潘家开、罗市敏、姜继兵、项波等。第一代至第六代传人已经过世,第七代传人年事已高,第八代传人也已60岁以上,不再下海捕鱼,第九代传人基本上已不从事捕捞行业。年轻一代的渔歌传承者基本上是从前辈那里学习模仿来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劳动过程中的本能歌唱。而且,渔民在思想上没有以传承渔歌为己任的自觉意识,会唱渔歌并不代表他们真正喜爱渔歌,自觉传播渔歌。可见,浙东渔歌前景堪忧,濒临失传。
(二)原生环境,不复存在。渔歌是传统海洋渔业木帆船人力捕捞时代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渔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渔歌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渔歌赖以生存的条件改变了,势必日趋式微,逐渐消亡。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渔船上的拔篷、张帆、摇橹、划桨、撑篙、起锚、抛锚、放网、拉网、起网、挑舱等人力劳动方式,如今早已被机械代替,人们再也不需要唱着渔工号子去捕鱼。在所有传统民歌中,号子也许是最早泯灭的体裁。因为它依附于笨重的体力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肩扛手拉的体力劳动逐步为机器生产所代替,劳动号子自然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4]。因为它失去了基本的实用功能,现实生活中已经听不到劳动号子。另外,由于民间渔歌手日趋年老且相继过世,年轻的后继乏人,渔歌的传播者和受众寥寥无几。渔歌的传承一般以从业者为主,主要有船老大、渔工、船工、船匠、搬运工等。以父传子、师传徒和同行相传等途径,在渔业和海运业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近年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当地渔民纷纷转业改行办起了实业,做起了生意,当上了老板,告别了体力劳动。沿海渔区真正下海捕鱼的本土渔民越来越少,船主往往雇用外地民工出海捕捞,并且渔船上人员组合并非长期固定,流动性较大,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也不同。随着渔船上配置现代化的通信设备,无线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都可以接收到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渔民喜欢时尚的流行音乐,对传统的渔歌不屑一顾,兴趣淡化,传承观念淡薄。传承人的缺失导致渔歌的传承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笔者为了研究浙东渔歌,曾多次赴浙东渔区寻访渔民,想获取渔歌原始资料,但大多数渔民不会唱渔歌,甚至没有听过渔歌,并表示唱着渔歌去打鱼是天方夜谭,认为渔歌时代是遥远的过去,会唱渔歌的人是“活化石”,是与时代脱节的“老古董”。随着老一辈渔民的相继去世,在渔民的生活中已经听不到渔歌,渔歌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加大渔歌的抢救、保护力度。否则,渔歌在我们这一代将丧失殆尽,海洋文化的历史记忆将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二、浙东渔歌的保护对策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遵循“公众参与原则,濒危优先原则,真实、系统和全面记录原则,权利与发展原则,物质化原则,保真性原则,生命原则,文化原则,和谐原则”[2]91-98。据此,要鼓励当地民众最大限度地参与,使他们自觉、积极地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保护工作中来。因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人,浙东渔歌是依赖创作、使用、欣赏、传承群体的人的存在为基础的,没有浙东渔民这一创作渔歌、使用渔歌、欣赏渔歌、传播渔歌的特定群体的广泛参与,渔歌就没有群众基础,就像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新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边缘化,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传统民歌正在大量消失。自从渔业生产实现机械化作业后,渔歌便不再是渔业生产的伴随方式,渔民不再唱着渔歌去捕鱼,渔歌成为濒临失传的濒危遗产,如果不予以有效的抢救、保护,将会销声匿迹。
(一)政府扶持,培养新人。近几年,国家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普查、申报、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具有历史、文化、社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抢救、扶持、资助等措施予以保护。周大风、洛地、马骧等老一辈音乐家对浙东渔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做了大量工作,舟山当地的音乐工作者韦俊云、何直升、林通玙等同志,长期坚守本土,为发掘、传承、保护、研究舟山渔歌作出了贡献。正是因为前辈音乐工作者对浙东渔歌的挖掘、采集、记录、整理、抢救、保护,才使这一民间音乐瑰宝至今没有失传。2008年,舟山渔民号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与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岱山县在舟山渔民号子的传承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值得浙东沿海其他各地学习、推广。
岱山县在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以及2003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渔歌挖掘和抢救工作,并提出了打造“中国渔歌之乡”的目标。从2005年开始,岱山县以举办中国海洋文化节为契机,打响舟山渔歌品牌,举行全国沿海省市渔歌邀请赛和以“感恩海洋”为主题的大型歌咏活动,1300余名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渔民、农民群众参与演唱,场面壮观感人,海洋文化气息浓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岱山县文化馆还建立了一支渔民号子辅导队伍,常年下基层进行辅导,并在高亭镇建立了“蓬莱业余文艺演唱队”和“晨练合唱团”,开展经常性的渔歌演唱、教唱活动。当地教育部门在高亭小学、岱山技校等学校开设中小学音乐第二课堂,学唱舟山渔歌。文化馆收集、整理渔歌小调100余首,渔民号子30余首,改编渔歌10余首,创作新渔歌20余首,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岱山渔歌》一书。岱山县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渔歌保护政策,扶持渔歌代表性传承人,对带徒传艺的渔歌传承人进行经济补助。文化馆组织当地群众成立渔歌业余表演团队,在岱山主要渔港和风景区设立渔歌演唱场所,传播渔歌文化,展示地方风情。当地文化部门还举办多种形式、各种级别的渔歌演唱会、邀请赛、研讨会。以此为契机,扩大社会影响,打造海岛文化名片,并利用现有的中国海洋博物馆、岛礁博物馆进行渔业生态环境、渔业生产场景的动态展示,以及渔业生产器具的实物展示,海洋渔业资源的图片展示,渔歌演唱的音像展示,还建立了海洋民俗和渔民号子生态保护区。
(二)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渔歌属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活态传承,也要运用文字、乐谱、图片、音像、数字化技术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因为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劳动中使用渔歌的空间荡然无存;随着传承人的不断减少,现实生活中几乎听不到渔歌。博物馆式保护、数字化记录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记录过程中要尊重原作,保存原貌,不能按照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编、加工。因为这种记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欣赏效果,而是为非遗存档,保存海洋文化的历史记忆。渔歌的传承保护必须建立在维护渔民的人权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基础上,要保护渔歌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其传统观念、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信息化时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可能。就现有科技水平来看,文化遗产保存、传播的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数字化技术可以方便自如地对资料进行录音、录像、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5],通过建立具有互动性与开放性的图、文、声、像文化遗产数据库,并以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这比起过去单一的口传心授、文字记录不知要先进多少,体现了信息化时代的优越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文化形态,对非遗的保护与开发要贯彻保真性原则,就是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都应呈现原生态的自然面貌。对旧时代的渔歌要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再现历史原貌”的宗旨,还原其真实面貌。渔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产生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对生产劳动的体验,对海洋生物的认知和对宗教信仰的敬畏。我们研究渔歌,要探寻它的基因谱系和生命之根,找到它的灵魂和脉搏,即贯穿其中由特定民族精神凝铸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源头和根本上准确认识,精心保护[6]。我们谈保护渔歌,不能漠视外部环境,只顾及渔歌本身,而要分析造成渔歌式微的根源性因素,进而与渔歌生死存亡休戚与共的生态环境一起加以保护。如果竭泽而渔,人对自然的过度攫取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浙东近海无鱼可捕,谈何渔歌?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近海无鱼可捕的地步,渔民不得不远洋捕鱼,国家不得不出台休渔限捕制度。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渔业生产环境、生产条件、生产设备、生产资源、生产方式的改变,渔歌已不再是渔业生产的伴随方式。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人使用的最终结果便是消亡。只有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无可替代的能动主体,因为说到底,无论“生命”也好,“生态”也好,“创新”也好,“发展”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生机活力,实际都存在于生它养它使用它的人群之中。一个特定的社群,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享用和传承主体,绝不会在满足经济物质生活需求的时候,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因为那是他们魂之所系的精神根脉[7]。渔歌作为一个艺术品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仍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哪怕它不再具有实用价值,但仍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仍然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田园牧歌、渔舟唱晚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的景象,但人们依旧向往田园牧歌、渔舟唱晚式的诗意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超越功利、超越物质而代代相传的。虽然农耕渔猎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但其人文精神依然可以遗世独立,其文艺作品照样成为经典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唐诗、宋词、元曲……古琴、昆曲、江南丝竹……号子、山歌、小调……依旧是当下社会最美的人文景观。笔者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漩涡里的歌》,里面有一首激越高亢、震撼人心的插曲《船工号子》,至今记忆犹新。或许,如今川江船夫号子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消失,但据此创作的电影插曲《船工号子》却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这足以说明音乐可以跨越时空,经久不衰,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现实生活中虽然不再需要“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号子,仍然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传承保护浙东渔歌的意义就在于留存一方乡土民歌的基因,保存地域文化的根脉。
(三)多措并举,创新发展。《世界遗产公约》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多种措施进行保护。为此,我们针对浙东渔歌的传承保护提出如下策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收集、记录、整理浙东渔歌,建立浙东渔歌资料库,出版浙东渔歌集,对渔歌实施数字化保护;全面普查浙东渔歌传承人,建立浙东渔歌传承谱系档案库,保护老一辈传承人,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对浙东渔歌进行活态传承;依托地方高校、中小学和文化馆建立浙东渔歌传承、保护、教学、创作、表演、研究基地,发挥文化教育部门服务地方、传播地方文化的作用;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渠道,加强浙东渔歌宣传力度,打响浙东渔歌文化品牌;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海岛渔俗文化区和浙东渔歌示范区,推出渔歌、渔俗文化特色旅游活动,使“走进渔村,品尝海鲜,欣赏渔歌”成为海洋旅游的特色和亮点;在海洋文化博物馆、渔俗文化展览馆设立渔歌音像展示区,专题介绍东海渔俗文化,宣传浙东渔歌文化;浙东沿海地区多地联动,举办渔歌演唱交流、比赛、研讨活动,创造条件定期举办东海渔歌音乐节。
当然,这一切都抵不上渔民在海洋渔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自发演唱,渔民发自内心的自觉创作、演唱、欣赏、传播、使用,是最好的传承保护方式。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传统渔歌不再是渔民生产生活的伴随方式,也许让渔歌传承下去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已,它与其他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艺术和传统工艺一样,最终难逃被历史无情淘汰的命运。与其让它们自生自灭,不如以文字、乐谱、音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以现代数字化技术保存下来,以博物馆的形式收藏起来,以多媒体手段展示出来。这虽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活态传承,但也不失为一种原样保留——保留海洋文化的历史记忆。笔者认为,要使渔歌传承下去,原样保留还不够,传统渔歌也需要创新,也需要发展,旧时代的渔歌显然已经与现实生活脱节,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将原始的渔歌素材进行加工改编,使其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是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艺术作品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审美需求就必须不断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当然,要在传承和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而不是转基因式的变异创新。正如田青所言:“没有传承的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8]
结 语
我们传承保护渔歌这种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何在?无非是想在潮水般涌来的现代文明到来之际,建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将那些已处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为未来新文化的创造保留更多的基因与种源[9]。我们研究浙东渔歌,也无非是想通过家乡鲜活的民歌告诉后人,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唱过的歌,这是深藏在我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在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今天,在许多古老的文化遗产行将消失的时候,我们更要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让它们更好地传承下去,使生活在一方水土的人们找到共同守望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