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技艺理论的本质、内核、分类及艺术学启示*
2021-01-07孙晓霞
孙晓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路径。海德格尔从艺术的视角反思技艺,反对现代知识在理论与实践间的不合理区隔,希望洞悉“在一切艺术之前已然起着支配作用,并且首先赋予艺术以其固有特性”[5]4的希腊艺术的起源。他发现,艺术所能完成的是一些既不能规划控制、也不能计算和制作的内容,它可以解除人类命运的封闭性,原因是技艺与自然“涌现”的共属一体性。[5]4故艺术所代表的技艺产物在此就是一种产出,是从自身涌现出来的,是与认识知识等词语交织在一起的内容;“是以一种知识性的生产指导为方式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开启,这种知识支撑和指导着人类存在者中间的一切‘显突(Aufbruch)’”。[6]5海德格尔从技艺本身,而不是从先定的“艺术反对技艺”这一现代命题出发来理解技艺。
随着近年来科学哲学、艺术学领域对技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技艺概念作为艺术和科学的早期形态和思想共源,在国内日益受到关注①。柏拉图作为早期技艺理论阐说的第一人,其思想中显露出的技艺的本质构成、思想来源、理论内核、分类体系,及其对艺术理论的历史推动力等都需进一步清理。
一、柏拉图技艺论之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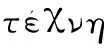

首先,柏拉图的技艺概念强调知识的专业性特征。在柏拉图看来,作为一种与知识相关的专业能力,技艺并不直接等同于知识,而是一种神赐的普遍知识与人生产所需的专业知识之间的统一。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②讨论了多种技艺,其中包含有算术、占卜术、绘画、诗歌、雕刻、驭车、医术、渔猎、弹琴、军务,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话中探讨了不同的技艺所拥有的不同知识范围。绘画、御马皆有各自专门的技艺,因此就涉及到了区分知识的题材。《伊安篇》中有如下对话:
苏格拉底:诵诗的技艺和御车的技艺本来不同,是不是?
伊安:是。
苏格拉底:如果这两种技艺不同,它们的知识题材也就不同。
伊安:不错。[15]14
技艺问题与知识关联在一起,强调的是不同技艺关涉不同知识。柏拉图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区分技艺的标准在于,一门技艺是关于某一类事情的知识,另一门技艺是关于另一类事情的知识。”[16]309(《伊安篇537D》)技艺概念中隐含着分类的先天要求。

其次,柏拉图认为技艺并不等同于普遍性原则。区别在于:系统知识追求一种普遍性原则,而技艺则寻求一种专业性的知识,这构成学科划分的思维前提。在《申辩篇》中,柏拉图记述了苏格拉底拜访的三种类型人群:拥有知识名望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苏格拉底认为,这三类人都是拥有一定专业技艺,是分别属于各自领域的一种特殊的知识,自己所拜访的三类人群皆未达到真正的智慧,均存在着各自的缺陷。其中那些久负知识盛名的政治家总是试图表现出无所不知的样子,而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无知,这让苏格拉底十分失望;[16]7-8而诗人也有此问题,“他们是诗人这一事实使他们认为自己对其他所有行当都具有完善的理解,而对这些行当他们实际上是无知的”。[16]8诗人所掌握的作诗技艺也是一种专业技艺,它并不具有了解其他行业的普遍性。政治家、诗人、工匠等所拥有的知识是低于“神谕”的人的智慧,故都属一种有局限性的知识。
柏拉图承认画家、雕塑家等工匠也“充分地拥有深刻的知识”,[16]8他们懂得哲学家所不懂,但如果工匠们就此误以为自己因为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因此就掌握了一种普遍性知识,可用以理解其他行当或事物,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就是错误的,[16]8因为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真正的智慧是具有神性的普遍性知识,是能够洞悉其他全部专业的知识,而不只是某种专业技艺,技艺并不是最高的知识或曰智慧。技艺具有向系统知识epistēmē趋同的“自觉性”[13]25,技艺与系统知识有衔接关系:技艺一方面是一套法规和原理,需要理论的可塑性,需要以知识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具体的实践操作,[13]221这是纯粹知识进入经验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第三,技艺论强调普遍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之间的内在互动。“在所有的技艺中,相同的技艺使我们知道相同的事情,另一种技艺则不能使我们知道相同的事情,如果的确有另一种技艺,那么它一定会使我们知道其他事情”(《伊安篇》538A)。[16]309这里所说的“不同的知识”倾向于绘画、雕刻、诗歌等具体性技艺内容。驭手、画家、医生们所拥有的技艺不能使人知道相同的事情,[16]310因这类技艺都只是一种独特的专门知识。相应地,“相同的知识”指几何、算术等;这类“自由艺术”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知道相同事物的技艺。它们区隔于具体物的知识,以其普遍性特征侧重于思维方面的理论性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高高在上与现实无涉,因为几何、算术等知识与计量、测度等实用目的相关联时就具有了具体的专门知识之义。休·H.本逊就认为,这类知识或智慧也具有合理性或规则性、可传授性与可习得性、明确性等特征。[20]382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技艺成为达到一般本质性知识的通道,而非本质性知识自身。
二、技艺理论的内核:逻各斯
柏拉图依据了多种原则来构建技艺体系,但仔细甄别,背后均闪现着一个核心内容,即逻各斯(logos)这一哲学范畴。③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对于原理性知识的要求甚为显豁。他认为,烹调根本不是技艺,只是一种程序和技巧,“因为它不能产生原则用以规范它所提供的事物,因此也不能解释它所能提供的本性和原因。”(465A)[16]341柏拉图进一步声明,拒绝把技艺之名赋于任何不合理的事物。休·H·本逊据此认为柏拉图把技艺理解为一种力量或能力,某人拥有知识、智慧或技艺,就会拥有一种力量或能力,这种力量必须与善的活动相联系。但这种善不只是限定在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一种智慧或知识所能确保的正确的判断,是一种终极的完善。因此,“苏格拉底倾向于认为智慧或技艺等同于定义性的知识”,原因在于他认为技艺“拥有其对象的逻各斯(logos)”。[20]382-387不过,律则性的逻各斯尽管重要,但却并不是真理自身,因此柏拉图对技艺的要求并不停留在逻各斯这一原则性知识层面,而是为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引领者:理念。这一点在柏拉图关于知识的名实之辨中有清晰的呈现。
与柏拉图同期的希波克拉底在对医学技艺进行论述时曾提出:“各种艺术(技艺)的名称是由于它们的本体才有的,认为真实的本体与名称分裂是荒谬的,而且这是不可能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真实的本体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自然的产物。”[7]3希波克拉底强调的是技艺名称与本体的整一性,不可分割性,但他没有分析技艺本体的本质性原理。而在《泰阿泰德篇》(147B-D)中,柏拉图以泰阿泰德与苏格拉底两人讨论技艺的名称与知识之关系的对话,区别了知识的对象、知识的种类以及“知识本身是什么”等问题。其中,苏格拉底自认为是掌握了“灵魂的助产术”这么一种技艺,它可以通过各种通道的考查,来弄清楚思想的产物是虚假的怪胎,还是包含生命和真理的直觉。正是在对思想真伪的考察中,苏格拉底反复强调知识不等于“技艺的名称”,[19]658知识也不只是关于某事的知识,更不是泰阿泰德所接受的“知识就是感觉”(《泰阿泰德篇》152A),[19]664或是事物呈现给人的那样。尽管一个人要拥有特定技艺才会正确地知道属于这种技艺的语言和行为,但关于技艺的名称和某种事物所呈现的内容皆非真正的知识,这与把知识作为最高的善、作为通往永恒的唯一,通过定义的方法得出一般本质概念不同。[16]310在此,知识与善及永恒的唯一相关联,知识成为理念性的、高于技艺的一个终极范畴。
技艺受理念的召引,这与其理论的神话起源有关。《普罗泰戈拉篇》(321A-322D)中,柏拉图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那里盗取技艺的故事,来暗示技艺中的神性源头。该篇对话暗示出,人通过技艺与诸神有了“亲属关系”,人与神的沟通之道是技艺。而在《欧绪弗洛篇》(14D-E)中,苏格拉底与欧绪弗洛讨论服侍诸神的问题时,推论出:“虔敬是一门向诸神乞讨和给与的知识”,是一门“诸神与凡人之间相互交易的技艺”。[16]252-253而且,技艺作为智慧的外显,在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所拥有的、能让人维持生命所必需资源的这些技艺之上,还有一种技艺是由众神之王——宙斯所保管的较高水平的政治智慧,指生活的正义、节制和虔诚等美德;每个人都要有美德,这是统治宇宙万物的至高无上主神所要求的,亦是现实中国家存在的前提。④以希腊神话为话语源头,柏拉图将技艺视为一种人类借诸神之力来超越自然界束缚,以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力量,从而将技艺区分于自然的同时又让它与自然共属一体——同属神之产物。技艺由神而出,技艺不只是纯粹人工物品,它同时具备天然性的一面。这是技艺理论联通现实与理念世界,具备理性品质的主要思想起源。
理念是万物的原因,是事物的模型,其构造具有永恒的性质,理念可知不可见,技艺经由逻各斯的中介才能在知识层面不断趋近理念世界。通过逻各斯,人类不但要与属于上天、属于诸神的东西联系起来,也把我们和尘世的、人类共同的东西联系起来,一种唯物主义倾向的“大地之子”试图把属于某种不可见世界的东西拉到地上,而“理念的朋友”则致力于可知的却非物质性的理念成为真正的存在,让·布兰据此认为,“天上的”存在与“地上的”存在成为逻各斯的两个根源,二者缺一不可。[21]75-77从技艺的层面看,这种以逻各斯为基石的知识体系既从“物”指的层面抽象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指向,又涉及生产所需的确定性“知识”,这种知识中需要的是一种为实现目的而必须借助手段的公理性原则,此非技艺莫属。技艺联通“地上的”知识与真理的知识,其路径就是逻各斯所求的规范、原则、秩序、法度以及和谐等。
三、“技艺”的诸分类体系
柏拉图对技艺的分类是基于多个背景的多样表述,形成了多种维度的技艺分类范式。如前所述,技艺概念自身就隐含着分类精神。《智者篇》中,柏拉图提出分类自身就是一种技艺。存在着一种分类的技艺;按种类进行划分,这是辩证法这门学问的事,是所有学问中最重要的,能够涵盖所有的例子,这种技艺叫做“识别的技艺,或者叫做区别的技艺”(《智者篇》226C)。[12]16“在每一种事物分别存在的地方,有一种相到处延伸,贯穿于多种事物;各不相同的多种相被一种外在的相所包含;还有,一种相通过许多整体而使之连成一体;而多种相则完全是分立的。这就意味着知道如何区分种类。”(《智者篇》253D)[12]58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技艺,但同时也要对技艺自身进行分类。由此可洞见柏拉图技艺理论的体系性。
第一种分类法,区分普遍的与具体的知识。在讨论一种技艺的亲缘性关系时,围绕着织布这类技艺,苏格拉底与客人讨论了织布这门技艺不同于具体的纺织亚麻、丝兰以及所有天然植物纤维的纺织工作,也不同于制造毛毯以及制鞋所用的制造毛毡和穿孔缝合的技艺。之后在论及建造房屋的技艺时,又强调要排除防水技艺、木作技艺,制作防盗防爆器具的技艺,制作大门等具体的技艺。[12]120-124这样就在专门知识域内区分了两种技艺概念:制造具体物的技艺和一般概念上的专门技艺。也因此形成了技艺体系中的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区分。于此,柏拉图通过技艺问题初步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层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学科内的一般知识与特殊知识的区分,并强调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故而在后面关于纺织技艺的类比中就有了“普遍技艺的具体再现”[12]125这一论断,在专业知识层面实现了普遍性理论与具体经验的统一。
第二种分类法,区分生产的与“获取的”技艺。《智者篇》中,柏拉图为了探寻到智者的“藏身之所”,在一种普遍与具体统一的结构中不断向下纵深分类。这里,技艺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或创造的技艺,例如农艺、畜牧、制造或塑造器皿的技艺,以及仿制的技艺;其中生产“使先前不存在的事物成为存在的任何力量”(《智者篇》265B);[12]77生产者就是以使原先不存在的事物变成了存在的,而生产的力量就是创造或生产的技艺。另一类是“获取”的技艺,包括认识和学习的技艺以及商贸、争斗、狩猎等技艺。这类技艺主要是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征服,是一种获取(《智者篇》219A-223B)。[12]5-13就在“获取”技艺下的“交换”类别中,柏拉图区别了兜售身体的粮食和灵魂的粮食。他认为作为可以出售的灵魂之粮食,广义的音乐、绘画、木偶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是兜售给灵魂的商品,用于教育或娱乐,他将灵魂的这类商品称为“表演的艺术”。还有一部分指知识生意,包括出售美德的知识和其他种类的知识,兜售这类商品的人被称为“艺术商人”,也就是他所要驳斥的智者们⑤。这里音乐、绘画、木偶戏等艺术是与思想和精神、灵魂的塑造相关联的;而其他制造类的技艺被划为生产性的技艺。
第三种分类法,以言语及身体行动为标线的技艺分类。在《智者篇》中柏拉图提出“获取”性技艺主要是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认识和学习。在《高尔吉亚篇》中,修辞学教师高尔吉亚与学生波卢斯同苏格拉底一起,讨论了修辞这门技艺的范围,进一步围绕言语区分了不同的技艺。高尔吉亚将修辞学的知识范围界定为“话语”,并指出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其他技艺的知识所涉及的只是身体的技艺和相应的活动。修辞学要处理的不会是这类体力活动,而是所有以话语为中介而完成的活动:
我想,在存在着的各种技艺中,有些技艺主要是由行动构成的,而几乎不需要言语;有些技艺实际上并不需要言语,而仅凭行动就可发挥其功能,例如绘画、雕刻,以及其他许多技艺……但也有些技艺确实需要完全通过言语来起作用,实际上不需要或几乎不需要行动。举例来说,算术、计算、几何、跳棋游戏以及其他技艺,其中有些技艺涉及的言语和行动一样多,有些技艺涉及的言语多于行动,它们的整个成就和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归结为言语的作用。我相信,被你确定为与修辞学相关的主要是这类技艺。(《高尔吉亚篇》450B-D)[16]323
最终在关于修辞的定义的对话中,波卢斯认为修辞、医术、算术、绘画、木匠、音乐等属于不同的行业,并对它们进行了反复的比较,以论证修辞学的范围(言语)、定义(说服)等。在此基础上,技艺被区分为行动的、言语的、行动与言语一样多的,共三类。
第四种分类法,区分纯粹性技艺与应用性技艺。从艺术学科角度来看,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的对立是西方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也最为漫长的历史阶段和学科特征,二者在知识层面的分野在古希腊的技艺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明确。苏格拉底曾区分过非自由技艺(illiberal arts)和那些有地位人的自由技艺。非自由技艺将人限定在工坊,并将个人的目光仅聚焦在个人的幸福上,而战争和农事技艺为人带来了更宽广的领域,使人们可致力于他的朋友和城市,农事技艺是其他技艺之母。[22]柏拉图依此发展出纯粹性技艺和应用性技艺的区分。《政治家篇》里,小苏格拉底和客人在讨论政治技艺与其他技艺的区分时,提出了政治的技艺、数学等相关科学皆与实操活动无关,是一种只提供纯粹知识的技艺;但木匠和一般的制作技艺从事实际活动时亦含有知识。这样就出现了“应用性的”和“纯粹性的”的技艺区分。
对话中,在苏格拉底与卡尔米德及克里底亚讨论节制问题时,提到了手艺人的制造和做某些事、工作的不同。他们认为各种技艺全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房屋是建筑的结果,衣服是纺织的结果,但是木工、铜匠等人的知识皆算不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知识的知识或学问的学问,是无法教会人建造的,它是“关于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知识”而不是关于“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事物的知识”。这里强调的知识是“纯粹的知识”(《卡尔米徳篇170A》)。[16]158此外,柏拉图还论述了一类所有知识都要使用的知识——数学。数学区别于具体的如政治的、医学的知识,[16]150-159是每种技艺和学问都一定要做的事;也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学习的知识;数的性质能导向对真理的理解,这是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19]520-525知识本质不涉及具体经验性事物,可感的事物,因“这类事物不包含真正的知识”《国家篇》529C。[19]530事实上,柏拉图眼里,事物可见不可知,理念可知不可见。理念才是知识的真形,是构成纯粹性知识的目标。如果单纯从知识概念来看,这里的论说显然与前述知识与技艺的概念混用形成了矛盾。但其要义在于区分其中的纯粹性知识与应用性知识。
在普遍知识与具象知识、生产的与“获取的”、言语的和身体的、纯粹的与应用性的等多个二元对立的技艺分类体系中,柏拉图把他要追寻的一般本质的实体性真理知识与技艺所要掌握的确定知识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影响到了科学和艺术的学科走向与衍流。与知识通约的科学被引向一种由形而上所主导的定义性知识系统,形成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科学目标:一要纯粹为“自身”而存在,无需功利和实用的目的;二要不借助外部经验,仅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23]49而在科学的对面,这种由形而上所主导的、注重对事物自身原理的探究的认识世界方式由于与技艺问题关联起来,并由此渗入到艺术理论中,对后世艺术理论和学科的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四、柏拉图技艺理论的艺术学启示
分析柏拉图技艺理论的诸多特征后,可发现,虽然其技艺理论在大多数时候是无关艺术的,但其理论的内在特征深层地影响到了艺术的历史进程。这是西方艺术在后世能够实现与科学分化,独占技艺概念领地,并最终走向自身的理论化与学科化发展的决定性动力。
第一,技艺指向专业知识,决定了艺术的知识同样是一门专业。技艺指向专业知识,那些掌握了技艺专业知识的专家间有不同社会职业的区分,由此形成了“专家知识”这个核心概念,它“蕴含理论性理解,即对特定领域内事物之本性和原因给出说理的能力”。[24]74而且技艺还由具体对象的生产程序,指向了关于某物的定义性知识:“技艺关于其对象的定义性知识解释了技艺关于其对象的绝对可靠性”。[20]382-387柏拉图关于专业知识的思想和论说,让政治家、哲学家、画家、雕刻家、工匠以及制鞋匠等所拥有的技艺在知识层面处于齐平地位。
第二,技艺理论追求确定性,决定了艺术表达的理论化可能。柏拉图在传统的手段论之上,将技艺自身指向一种确定的、可言说的具体知识。技艺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人类认知和把握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减少人类生存所需的不确定因素,确保人类平稳地步入未知领域。其哲学基石是对理论性知识和普遍性规律的诉求,必然会以理论化的学科性要求追循各专业的逻各斯原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对于确定性知识的热情,以及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思想家们“对一切确切、背景扎实、层次分明的知识构架的出现的期盼”。[13]19这样一种定义化的、确切性的、理论化的知识结构要求,促动艺术家将所拥有的技能不断理论化,从而构成了后世艺术学科化发展的前提。
第三,技艺是一种中介性存在,为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知识流通的可能。柏拉图借助希腊神话为技艺指定了一个灯塔式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一个由普遍性本质知识构筑的“神性”的真理世界,技艺是人类达至这一真理世界的中间通道,联通了理论化和实践化的两种知识体系。技艺一头连接着无所不能的神性智慧,一头连接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生存;一头追求严密确切的公理原则,一头连接着操作性生产程序。技艺被作为科学与人文知识的共有源头而存在,并以一种居间状态⑥,为现实生活生产赋予了神性意味和理性源头,具有了连接理论与实操经验的中介性存在意义。这正是中世纪末期乃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自由摇荡于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之间的历史根源。这一思想传统让理论知识有了从自由艺术下降到机械艺术的可能,也为手工操作的经验知识提供了从机械艺术上升为自由艺术的通道。
第四,各类技艺同属受理性引领的知识,决定了后世艺术的体系化发展方向。尽管柏拉图关于技艺理论的论述多是零散的,多变的,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技艺是一种专业知识”始终是贯穿其哲学思想的一个轴心式命题。在他体大虑周的体系中,技艺理论一毂统辐,联系起各层面的知识。技艺虽然表面是限定在日常之智识,但其中所包含的对象既有工匠的知识、也有政治管理的知识,其理论面辐射至美德、伦理乃至理念世界。在纯粹理性、政治伦理实践⑦及物性的感性经验三个层面,每个层级的专业知识又可进一步分类细化,形成了整一的、彼此有交错的技艺之网,联通起了整个人类生活实践与存在的意义,在逻各斯的驱动下朝向了理性的终极目标。这为后世“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提供了界限的同时,也标定了二者的共同目标,由此构建起一个受理性主义牵引的艺术学科发展模式。
概言之,柏拉图的技艺理论中一方面暗含着学术分科意识;另一方面则暗示出一切知识受理性精神的召引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其中的学科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因子,以一种宿命式的哲学精神,推动着从大艺术(technē)到小艺术(fine arts)的概念演进和变迁。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化的思维模式延宕到后世的艺术概念中,不断修正和调整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的学科领地和知识特征,最终以18世纪“美的艺术”概念和美学学科的诞生为标志,“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的二元对立被超越,现代艺术体系得以确立,[25]17-46艺术学科走向自主,最终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艺术学科的发生和发展。此乃另一话题,暂不展开。

② 关于柏拉图文本中苏格拉底的对话内容到底应该归于谁的思想,学界公认很难做准确区分。休·H.本逊赞同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的观点,即认为无论是早期还是中后期,柏拉图优先考虑的都是哲学,“无论在哪一篇对话中 ,柏拉图只会允许出场的苏格拉底言说他 (柏拉图)认为真的东西”,故而,对于柏拉图思想研究而言,这些对话都是值得深入的([英]泰勒主编,韩东晖等译《从开端到柏拉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371页)。本文亦采此观点,从思想的整一性角度来理解和接受柏拉图的对话内容。
③ 柏拉图之前,智者学派的哲学中心是逻各斯,柏拉图本人并未太多使用这个概念,他的哲学中心概念是理念,但他的技艺理论与逻各斯是相关联的(参见〔美〕夏帕著,卓新贤译《普罗塔戈拉与逻各斯:希腊哲学与修辞研究》,吉林出版集团,第51—53页)。
④ 矛盾的是,直到《普罗泰戈拉篇》的最后,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两人均未明确美德到底是不是一种知识,我们也很难直接判断出柏拉图的意图,但此处技艺一词中包含着神圣化的内容,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参考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49页)。
⑤ 最终在经过多途径的拆解与论证后,柏拉图将智者归结为:一是猎取年轻富豪子弟的受雇的猎人,二是出售作为灵魂营养的知识的商人,三是贩卖同样商品,四是出售自己制造的产品;五是具有论战的技艺,等等;他也承认,智者在一定意义上还是灵魂的净化者。(《智者篇224A-C》)(参考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8页)。
⑥ 国内学者周宪教授曾深入分析论证了艺术理论的居间性特质。见周宪《艺术理论的知识学问题:从西方学术语境来考察》,《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第76—88页。
⑦ 在柏拉图的技艺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并不对应于今日我们在理论型科学和应用型技艺之间的区分,而主要是在哲学沉思与政治生活间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