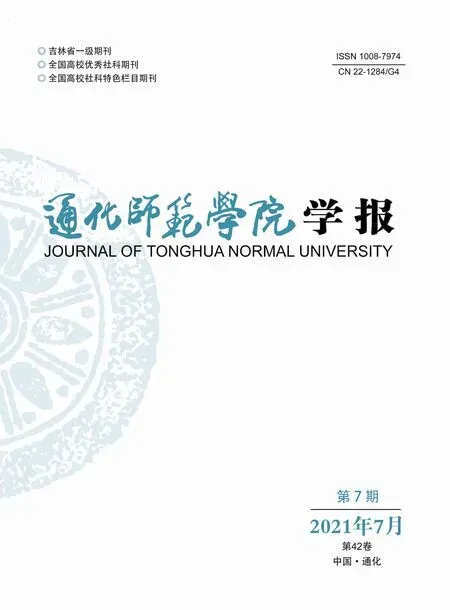宋代官府的图书控制活动
2021-01-07金雷磊
金雷磊
近年来,宋代图书控制活动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一,研究宋辽金边境图书控制问题。如:刘潇《宋朝对辽金出版物禁令及政策分析》(《出版广角》2016年第23期)认为,宋朝为防止泄露朝政及军事机密,制定并执行了针对出版物流入辽、金的禁令。由于执行的松紧度与辽、金关系密切相关,法令未能自始至终地得到贯彻,没有发挥禁令应起的作用,加之市场与文化交流不可逆转之客观事实,禁令最终未能阻止出版物在民族间的传播。王德朋《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书禁问题》(《历史教学》2007年第1期)分析了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书籍禁运问题,总结了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书禁政策。其二,从某一方面入手看宋代图书控制问题。如:郭志菊《从版印媒介技术发展看宋代的文字狱及书禁报禁》(《新闻大学》2018年第3期)认为,宋代版印媒介的高度发育,开启了“印刷交往”的时代并深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有宋一代文字狱和书报禁泛滥,首因是版印媒介发达,动因是党争,共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信息传播最终达致稳定皇权的重要手段。刑勇《从〈湘山野录〉看皇位之争对宋代书禁的影响》(《史学月刊》2012 年第8 期)认为,徽宗继位与太宗有很多相似,徽宗为太宗避讳,下诏把文莹《湘山野录》连同“三苏”等11人与变法有关的文集一并严禁。《湘山野录》遂成为宋史上纯粹因皇位之争而被禁的第一部书。其三,研究宋代出版管理问题,其中涉及出版控制方面。如:梁瑞《宋朝国子监对图书出版的管理探微》(《出版广角》2015 年第10 期)指出,国子监的重要职能就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业,监管学校教材及科举用书的出版,审查图书出版的内容,阻止盗版书籍及禁书的出版。①类似还有王海强《两宋图书出版管理述论》(《出版发行研究》2018 年第6 期)、孙永芝《两宋出版管理研究》(河南大学2014 年博士论文)、王海刚《两宋出版管理述略》(《中国出版》2007 年第8 期)、郭孟良《论宋代的出版管理》(《中州学刊》2000 年第6 期)、徐枫《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年第3 期)等文。通过某些方面的局部研究上升到整个宋代官府的图书出版控制活动,运用新的史料,总结其出版控制活动规律,显得很有必要。宋代以来,印刷术的普及为书籍大量出版和流通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对官府对民众的思想统治造成威胁。与之而来的,则是官府运用法律手段对图书传播活动实施控制。“自印刷出版业出现并日趋普及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开始运用法律手段对文字、出版业严加管制,使新兴的印刷出版业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禁绝各类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书籍。对文字、出版的法律箝制,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政府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的重点”[1]22。宋朝重视对书籍流通与传播现象的控制,曾下诏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特定内容、特定人群以及书坊所生产图书的传播,形成完善和系统的宋代图书传播检查和控制制度。宋代官府对图书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天文地理、阴阳卜筮类书籍的控制;其二,对元祐党人书籍的控制;其三,对商业性图书出版机构的控制;其四,对边境图书贸易的控制。通过图书控制,遏制某类信息的传播,有助于加强宋朝统治。本文试图从宋朝官府对图书控制的四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控制阴阳卜筮类书籍
阴阳卜筮类书籍是术师预测吉凶祸福之书,其内容荒诞无稽,属于朝廷禁止之列。宋朝皇帝诏书中多有规定,此类书籍不得雕印、出版与发行。比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宋太宗下诏,对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等,实行图书传播控制。诏书规定,天文、相术、六壬、遁甲等特定内容书籍,民间士人不得私自学习,刻书机构也不得私自传播。之前若有私自收藏者,在一个月期限内,必须送交官府,逾期不交者,则有杀身之祸。检举揭发者,则可以赏钱十万。地方官员隐藏不报,也要连带治以重罪。宋朝官府对此类书籍出版与传播规定严格,图书控制制度细致和完备,通过明确的赏罚制度,来限制图书出版活动。
景德元年(1004)正月,宋真宗针对卜筮、谶纬、星占、历日之书下诏,禁止此类书籍传播。无论是士人还是庶人,都不准传习、阅读,“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逐处官吏焚毁讫奏。敢违犯隐藏者,许诸色人论告,其本犯人处死,论告人给赏钱十万。逐处星算技术人,并送赴阙,当议安排;瞽者不在此限”[2]98-99。宋真宗对私习相术、星算之术的人采取检举揭发的办法,凡是检举揭发有功的人,赏钱十万。对被揭发之人的惩罚非常严厉,甚至处死。可以看出,宋真宗时代,对于天文星算之类书籍的控制相当严格,对于私自传播此类书籍相关人员的惩罚也是十分严酷。
景德三年(1006)四月,宋真宗又下诏,禁止出版天文兵法、玄象器物、相术占卜、六壬遁甲之书。诏书在出版与传播内容方面作出明确和严格规定:除了准敕出版的阴阳卜筮书籍,其他书籍都不允许私自收藏、传播、阅读和学习;在一个月内主动自首者,不追究罪行;超过一个月不自首者,处死;情节严重者,当行处斩;检举揭发者赏钱百千。诏书还指出,之所以禁止天文、相术等书籍出版和传播,原因就在于“用防奸伪”。
宋真宗分别在景德元年(1004)正月、景德三年(1006)四月、景德三年(1006)九月三次下诏,限制书籍传播。通过诏令形式,从内容方面,规定可以传播和不能传播的书籍,规定里面,连眼睛失明的人和在边境从事书籍贸易的人都考虑在内,非常细致和具体。可见,宋真宗对书籍控制相当重视,认识到书籍作为一种信息和知识传播媒介,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特定类型书籍,比如阴阳卜筮之书,它们的出版与传播会蛊惑人心,败坏道德风俗,增加社会动乱,不利世教,也不利朝廷统治,需要加强对于这类书籍出版活动的管理和约束。真宗通过下诏形式,控制阴阳卜筮书籍出版,只是宋朝皇帝中的一个代表。实际上,宋朝历代皇帝都有类似控书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客观上维护了宋朝统治。
二、控制元祐党人的著述
元祐党人著述控制始于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主要针对苏轼。苏轼任湖州知州时,遭到何正臣、李定、舒亶等人的弹劾。元丰二年(1079)七月,舒亶《劾苏轼奏》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3]65。舒亶先由苏轼赴湖州上任谢表说起,认为谢表有讥嘲时事之实。觉得“争相传诵”苏轼诗文之人,是“流俗”之人;而所谓的“志义之士”,则“无不愤惋”。舒亶认为,自己属于“志义之士”之流。紧接着,延伸到苏轼诗歌:“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3]65。从苏轼诗歌里面挖掘出些许诗句,附上自己的理解,认为其在议论陛下和政策,生拉硬拽、牵强附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挑拨离间,挑拨陛下与苏轼的关系,导致陛下对苏轼之憎恨。最后,对苏轼作品传播广、受欢迎的景象,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3]65。并呈上苏轼诗集三卷作为朝廷整治苏轼的证据。朝廷听信舒亶等人弹劾,以苏轼诗歌讥谤、议论朝政为由,将其逮捕,拘于御史台。同时,因苏轼受牵连的还有司马光、黄庭坚、张方平、王诜、范镇等人。“乌台诗案”的出现是诗文与政治的精密结合,为朝廷后来实施的图书控制活动作了铺垫。
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迫害元祐党人,禁止传习其诗赋,对书籍传播的控制严格,多次下令限制一些人的书籍出版。“三苏、黄、张、晁、秦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4]323,“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集,并毁版”[5]361,不仅限制三苏及苏门学士的文集出版,且明确规定“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6]141。作家和读者受到打击和迫害,主体性得到抑制,严重妨碍文学的传播与发展,科举考试也重经义而废诗赋。禁止传播二程文字及图书,“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察觉”[7]367。“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常切觉察”[8]323。以至于程颐迁居到洛阳龙门之南,并且不允许各地学生来求教,“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9]343。
党争环境下,凡是与元祐党人有关的学术、思想、文集、著作都被禁止,各地不许私自出版,也不允许学者私自学习。“元祐系籍人等石本,已令除毁讫。所有省部元镂印版并颁降出外名籍册,并令所在除毁,付刑部疾速施行”[10]29,“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版”[11]148,这些限制,显然不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正常发展。元祐党人著述的控制,主要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及其党争而展开。控制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的书籍,“是由于统治阶级排斥异己,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12]276。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以他们为代表的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论,使其在行为上与朝廷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中央统治。
三、控制书坊图书出版
宋朝以来,官府一直加强对商业性出版机构——书坊的控制,宋朝统治者通过一些诏令明令禁止书坊书籍出版与发行。
绍熙元年(1190)三月八日,宋光宗《禁雕卖策试文字诏》云:“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版,仍立赏格,许人陈告。有敢似前冒犯,断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13]72。该诏专门针对建宁府书坊刊刻、售卖科举考试用书的现象,下令禁止。并且规定其他州郡不得乱用公款刻印私书,以免影响后学,若有冒犯,仍会得到重罚。
绍熙四年(1193)六月十九日,宋光宗《严禁雕印奏章封事程文诏》道:“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14]140。对书坊所印奏章、程文,当场焚毁,焚毁名件报枢密院备案。该诏书还对四川、浙江、福建等全国主要印刷与出版中心之出版活动作出规定,指出各地图书出版要实行严格图书检查制度。
嘉泰二年(1202)七月九日,宋宁宗《禁雕印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诏》曰:“令诸路帅宪司行下逐州军,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15]197。诏书指出,事关国家大事和国家稳定等方面的书籍,需要进行内容审核与把关,只有审核与把关通过,才允许书坊雕印。这项工作主要由各地方官府机构安排官员来做。这些特定内容的书籍若不经审核,私自刻印上市,一旦发现,则要没收印版和书本,出版者也要受到重罚。
宋光宗、宋宁宗通过诏书形式规定图书审查内容,限制特定内容图书出版与发行,是从源头控制信息传播。该行为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皇帝下诏书直接禁止书坊从事图书出版与发行业务,这是宋朝官府的图书控制和文化管制政策。
除了皇帝下诏,通过诏书的形式直接规定,还有一些臣子奏书,也要求对书坊商业性出版活动实行图书审查,甚至禁止书坊书籍传播。绍兴十五年(1145)十二月十七日,孙仲鳌《乞民间书访镂版先经看详讨论奏》云:“诸州民间书坊收拾诡僻之辞……辄自刊行……欲申严条制”[16]151。绍兴十七年(1147)六月,赵公传《乞除毁书坊不经之书版奏》云:“诸路书坊将曲学邪说、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日下除毁”[17]104。庆元五年(1199)正月,黄由《乞选刊程文奏》云:“凡书坊雕印时文,必须经监学官看详……策复拘于近制,不许刊行”[18]399。大臣上奏一般是建议朝廷对书坊出版书籍实行严格“把关人”制度,即先要经过所管辖部门看详,然后要经教官讨论,最终择取可以出版的内容雕印。图书正是通过官府步步把关,层层审核,才得以出版、发行。
四、控制边境书籍贸易
宋朝沿边设有榷场,主要从事边贸活动,十分兴盛,书籍贸易也在其列。控制宋辽金边境书籍贸易也是宋代官府的一项重要文化管控政策。“宋朝始终与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处于对峙状态,和与战的矛盾斗争成了朝野政治议题的中心,反映在图书出版传播领域,凡涉及时政朝章、边机军务及相关文字,皆在禁止之列”[19]370,宋代官府对涉及重要信息的文字、书籍等,有所忌惮,往往会特别注意控制沿边图书贸易活动,禁止图书向外境传播。
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等皇帝都曾专门下发诏书,严格控制沿边书籍贸易活动,严格限制书籍向外境传播。景德三年(1006)九月,宋真宗《非九经书疏禁沿边榷场博易诏》道:“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20]256。康定元年(1040)五月二日,宋仁宗《禁将边机文字镂版鬻卖诏》道:“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21]437。元丰五年(1082)四月,宋神宗《谕王安礼捕匿名书者诏》道:“辽人方在馆,而此书滋多,脱流播外国者非便,亟为捕之”[22]206。大观二年(1108)三月十三日,宋徽宗针对文集中夹带重要、机密信息的情况,发布诏令,严令禁止,其《严禁擅行印卖文集诏》道:“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23]142。这些诏书对图书边境贸易类型作出了限制与规定。一般而言,宋朝对沿边书籍买卖类型只限于“九经书疏”,其他不符合要求的书籍禁止发行。违犯者论罪处理,其书也要被官府没收。
朝廷大臣看到涉及军事机密类书籍在外境广泛流传的情况不无担忧,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朝廷禁止此类书籍传播。比如,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论雕印文字札子》道:“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24]226。欧阳修觉得,书籍中一些重要信息不应该传播到“虏中”,否则,“大于朝廷不便”,表达出自己深深的忧虑。元祐五年(1090)正月,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道:“本朝印本文字……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25]359。从苏辙札子可以看出,“三苏”文字及书籍早已传到“北界”,在“北界”知名度很高,广受“北界”读者欢迎。但苏辙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是表现出对书籍传播到“北界”的担心和忧虑,认为这些书籍若都流传到此会泄露机密,也会被夷狄取笑,“皆极不便”。
苏轼更是强烈反对书籍向外境传播,认为某些特定书籍传播到高丽有百害而无一利。“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26]138。“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册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26]142?“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26]143。希望朝廷对书籍跨境传播进行限制。
苏轼不仅建议对书籍外境传播活动进行限制,还要求对从事外境书籍贸易的书商也加以控制和管理。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道:“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后并不得发舶往高丽,蒙已立条行下。今来高丽使却搭附闽商徐积船舶入贡。及行根究,即称是条前发舶。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据陈轩所奏语录,即是高丽知此条。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虽有条贯,实与无同。欲乞特降指挥,出榜福建、两浙,缘海州县,与限半年内令缴纳条前所发公凭,如限满不纳,敢有执用,并许人告捕,依法施行”[26]139。苏轼看到了书商在书籍外境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建议控制书商向外境流动。书籍之所以在外境普遍传播与售卖,主要是因为书籍有利可图,有些书商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苏辙认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25]359,苏辙指出了利益驱动是导致书籍传播到外境的根本原因。
五、余论
宋代官府的图书控制活动主要采取事前把关、事中检查、事后监督的方式。此活动始终贯穿于图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之中。“在刻印前对出版物采取‘看详’‘详定’‘看验’等预先审阅措施……国子监及各军州还随时对‘书坊见刻版及已印者’进行‘访闻’‘缴审’‘查验’,遇有突发事件,更是及时采取措施,对违法图书进行清查,限期收纳,毁版焚讫……置于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之下……实行举报奖励制度”[19]372。朝廷对书籍传播活动进行控制是典型地通过控制书籍流传来控制公众舆论。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宋朝重视舆论导向,这种舆论导向,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书籍出版为主流,其传播深深契合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