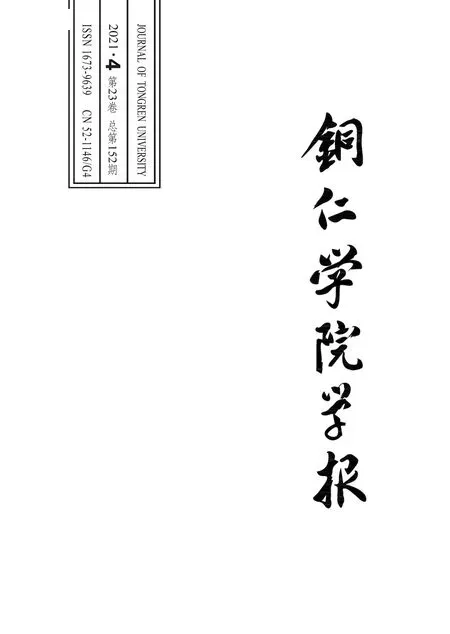属性与功能:制度的社会意义略论
2021-01-07马建华揭海业
宣 杰,马建华,揭海业
属性与功能:制度的社会意义略论
宣 杰1,马建华2,揭海业3
( 1.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2.铜仁学院 人事处,贵州 铜仁 554300;3.广东廉江市委党校,广东 湛江 524400 )
在社会意义上理解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在理论起点上,制度的属物特性应得到确认。于方法论而言,这一特性可表现为制度发展的客观性与相对稳定性;在运转机制上,制度规定信息与能量的传导通道,成为相应社会格局的定格力量;在文明系统的演化上,制度与社会存在一定交互发展的路轨与规律。由此辨明:制度文明的程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制度自信的树立。
制度; 制度自信; 社会意义; 制度发展; 社会运行
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离开社会谈制度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也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人们总是习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待制度,缺乏反向观照与审视。其实,社会就是通过制度组织而成的人类群体,离开制度的联结,人的集合无法成就完整意义的社会。用人所熟知的话来说:社会不能离开制度而存在。当然,这里的“制度”是广义上的制度。我们通常说“人是一种群体动物”,这个“群体”指的就是以制度化的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既强调“道路自信”,又强调“制度自信”,而且,把两者并列起来。没有制度自信,政治信念不容易保持其坚度与韧性。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本文尝试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探讨制度的属性与功能。
一、制度的属物特性与社会存在
制度之属物性,亦即制度之客观性。制度虽然由“人”来制定,但若非极端的条件限定,这里的“人”非指单个自然人,而是指群体意义的人;因而,规则一旦上升为制度,意味着“人”不可以任意选择和随意改变;在这个角度上,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组织对制度的制定、调整必须根据这些规律进行,必须充分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各种主客观条件,否则就会造成制度失灵。
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制度通常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现存的制度在马克思这里被理解为迄今所存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交往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交往中,“生产(劳动)交往”才是最重要的社会交往,他还说:对于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的新成员而言,世界历史的意义已发生改变,历史被看成两种过程:一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二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新成员对这两个过程“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196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生产不是个体行为的概念:生产实质上是个人之间的交往过程;生产的交往、分配的交往、交换的交往等等组成了经济活动的交往形式;生产交往决定着其他类型的交往,生产资料所有制也相应地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向世人揭示生产力与“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原理,以此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后来又进一步把生产的交往形式阐发为“生产关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关系原理为基础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在其所有论著中,马克思极少抽象地使用制度这一概念,而更倾向于在更具体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的概念组合中使用。
在社会存在的内层结构中,生产关系与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国内学者做了一些探索。学者辛鸣在《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交往形式”就是制度:当马克思后来喜欢用“生产关系”来代替“交往形式”的时候,就是把生产关系作为制度。[2]不过,辛鸣在这里只是说明马克思“有限度地”承认生产关系与制度的同一,至于同一的条件——“某种意义”究竟是何种意义,并未具体作出阐述。学者宋增伟也认为,“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3]他断言,用“制度”代替“生产关系”,可以涵盖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此观点与辛鸣异曲而同工。本文认为,制度与生产关系分属两个范畴,前者是“规范”,后者是“关系”,两者不能简单等同。诚然,两者的联系无疑非常紧密:制度尽管不可能是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本身,但它是实现了的、确认了的、巩固了的、稳定了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进而言之,社会关系的存在以制度的保障为条件,而制度是社会关系的初级实现。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制度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在功能、地位、重要性上并不一致。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经济制度是整个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基础。既然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实在,那么制度也必然具有客观实在性,从而具有属物性。
强调制度的属物性,并不等于说制度的刚性不可改变,而是在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制度观与历史唯心主义制度观的区别。看不到制度的属物性,就会将曾经处于某个历史节点的当机者置于制度之上,进而把“精神的动力”置于制度之上。与这个问题相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马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了与旧唯物主义决裂的原因。他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认为这种历史观最大的错误在于根据人行动的动机评价和判断历史。按照这种方法,历史人物可脸谱化为君子和小人,于是历史结局就如同人们通常所说那样:君子上当,小人得利。基于这种简单的方法,旧唯物主义得出令人沮丧的简单结论:不能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到多少有教益的东西。恩格斯批评道:这是在历史领域里面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一旦秉持这种方法论,就会把精神的动力当作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最终原因。当最终原因都自认为被发现了,那还有谁再去研究这些动力当中隐藏着什么、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哲学党性”的重大退却。承认精神的动力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不再进一步追溯动力的动因,这才是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哪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家,都不会认为历史人物的真实动机和表面动机就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原因;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动机后面肯定还会有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别的动力。历史唯心主义的缺陷在于:“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4]303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于:历史不是某些个别“小人”的天地,也不是单靠某些个别“君子”可以谱写,它应该是作为群体的人的合力所创造的。进而论之,制度不是某个历史人物的个人所为(无论他是多么的伟大),也不是某个小概率事件造成,制度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不管历史演化的结局怎样,人们总会根据每一个人追逐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自己的历史,“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4]302历史上以武力角逐权力的现象很普遍,但制度不一定是由征服者决定的。恩格斯列举过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历史现象:当某些战争结束后,征服者要定居下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他们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该适应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应当按照当地生产力发展程度合理设置治理方案,而不是按征服者原来的传统制度实施管理。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奴隶变主人”的奇怪现象:“……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1]578这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军事征服可以变成长久统治,而有些却不能。在中国历史上,蒙汉和满汉的民族冲突、体制选择的不同结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规律。
二、制度传动与社会运行
制度是联系人类个体的纽带,制度的存在产生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这种机制传导信息与能量,形成相应的社会格局;制度的存在进而也产生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机制。
人类早期的群居生活只以亲缘关系来维系。随着历史的推进,制度逐渐代替血缘成为联系群体的主要力量,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也开始制度化。在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1877年,摩尔根一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古代社会》出版。摩尔根在对北美洲印第安人血族团体的研究中,打开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古代历史的一些难解之谜。《古代社会》对人类的史前史提出新的分期,分别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把前两个时代按历史发展的层级再细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摩尔根重点研究的是前两个时代的状况以及这两个时代向第三个时代过渡的历史过程。摩尔根对古史中最古老的制度——家庭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发现,家庭制度是按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这样的顺序发展起来的规则系统:“从顺序相承的婚姻形态、家庭形态和由此产生的亲属制度中,从居住方式和建筑中,以及从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习惯的进步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过程。”[5]6而且摩尔根还发现,尽管在不同的阶段中相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大都不同,但人们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却是差不多相同的,且人们的需要也基本是相同的。由于“种族的大脑”相同,故心理法则也相同——这些特点跟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摩尔根还认为,人的财产观念不是本来就具有的,而是在蒙昧阶段中漫长地萌芽、缓慢地形成;但财产观念产生了以后,人类对财产的欲望开始超越其他一切欲望,“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5]14马克思在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研读了《古代社会》。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在研读此著作的时候进行详细摘录和批语,在批语中对摩尔根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来,马克思原计划在自己晚年时期结合唯物史观的理论及方法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人类学思想作重新阐述,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还没完成便与世长辞。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顺着马克思的思路,写就了石破天惊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家庭与私有制的系统演变提出一系列的新观点,这是古代制度史理论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古代社会》对史前社会资料的挖掘与分析,对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国家的形成、劳动对人类起源的作用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毫不吝啬地赞扬摩尔根在思想史上的伟大功绩,甚至认为他对史前史的研究远超于爱·伯·泰勒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和巴霍芬的《母权论》。《古代社会》研究表明,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并不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同步存在,而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得以产生。这为“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很好的理念素材。但是,摩尔根只看到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想萌发这个事实,并没有发现人类思想来源于何处,也就无法全面看待制度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里,恩格斯作了精辟的阐述。恩格斯首先认为,唯物史观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生活于一定历史时代、一定区域、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的现实的人;而社会制度不是孤立的,受两类生产的制约:一者制约于劳动的发展阶段,二者制约于家庭的发展阶段。劳动发展程度越低,劳动产品的数量就越少,社会财富就越匮乏,那么,血族关系也就越能强力支配社会制度。不过,尽管当时这种社会结构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劳动生产率仍不断地得到发展,当生产发展了,商品交换变得频繁,贫富差别开始增大,私有制也发展起来,这就增加了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为了阶级对立准备了更完整的基础。当然,变化不会来得很快,会历时几个世代,对旧的社会制度不断施加压力,直到制度的变革能适应新的条件。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展示了国家产生的宏大图景:由于新形成社会阶级之冲突加剧,基于血族团体的旧社会被这种冲突“炸毁”,取而代之的就是建立国家的新社会;国家出现之后,地区团体就开始以国家的基层单位的形式存在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4]16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最初的制度与“人的生产”(家庭的基本功能)密切相关,家庭组合与运行的规则系统中内容最为核心的是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比社会经济制度发育得更早,演化的历史更长,对社会运行的作用更直观。《古代社会》所提及的一些现象在当下的时代仍然存在:越是落后的地区,正式制度的作用越弱化,血缘关系就越能强化,宗族的力量就显得越强大,以习俗的形式出现的下位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越能代替上位制度和正式制度。而恩格斯的评论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观点:并不是有了“先在”的私有观念,才产生了私有制;相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制度(包括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不管是家庭制度还是国家制度,都是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对社会个体生活交往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已。
社会分工的进行也离不开制度的力量。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6]如果没有这些分工,人群在自然生存的竞争中未必能战胜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牛马为用,为什么?是因为人能“群”《荀子·王制篇》。能“群”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而是一个本质的不同——通过社会分工把人从简单聚合变成社会有机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飞跃,而社会分工的实现所倚仗的力量就是制度的功用。社会大分工从一开始就是和所有制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521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总共产生的三种所有制,都是与不同的分工水平结合在一起的。制度不仅使社会分工得以进行,而且,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群体功能,这种功能是单个个人力量无法达到的,更不可能是类人猿群所能达到的。
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中,我们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分散和彼此对立的,作为生物意义的单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然而,私有制出现之后,人与人的交往形式改变了,原本分散、对立的不同个体的力量汇合起来,产生了“总和”的生产力。劳动者在原来是彼此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又由于劳动者的力量只有在生产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开始逐渐表现为一种不依赖于劳动者个体(与劳动者个体分离)的东西,一个独立于劳动者个体的特殊世界。从个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生产力不归个人掌控,不再是个人的力量,“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是生产力的总和,这是一种制度(私有制)的力量(而非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1]580可以看到,曾经作为个人的力量的“生产能力”与“生产力总和”不一样:前者是个人的,在分工不存在(或是简单分工)的条件可以存在;后者是通过制度(生产关系)表现和实现的,不以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具有物的特征。在分工的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文化观念在一同发展。在最初的群居生产当中,最初的分工是为生育子女而进行的男女分工,然后是劳动中的男性主狩猎,女性主采集的简单生产分工。这些分工建立在生理差异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历史上有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从狩猎、采集者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商人阶层的产生。分工使劳动技能更为专门,劳动过程更为精细,生产效率大大增加。在分工中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通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巩固下来。如果没有财产的不同归属和私有观念,就不会有产品交换,那么手工业不会专门化,商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分工就只能停留在偶然的状态,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大分工”。
可见,制度对社会的粘合,无非是由于它调整利益,形成秩序,给人的行为提供预期。如果把人类单个有机体的内部系统作为类比,可以这么说:没有神经系统,各个组织器官的“分工”就无法进行;同样,对于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制度,人类的社会分工也无法形成。
三、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
制度是一个历史存在的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有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恩格斯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在古代社会较早的阶段,人们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着他们每天重复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了让个人服从于生产及交换的共同条件,也就让社会产生了一种依赖规则的需要,“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7]这一阐述也启示我们:在历史的逻辑上,制度源于规则,规则源于习惯,也就是说,制度是从习惯发展而来的。
以辩证法的思维来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相对的,发展性是绝对的。马克思在批评费尔马哈的“感性世界”的时候曾这么说:费尔马哈忽视了一个关键:这个感性世界本来就是工业、社会状况和历史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决不是什么自从开天辟地就开始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528我们以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费尔马哈没有看到实践的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这句话的另一个问题:这里的“感性世界”的制度环境没有可变性,是一个相对静止的闭合系统。费尔马哈的“人自身”是抽象意义的个人,而不是“现实的”和“历史的人”,不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当中的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客观存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实践的、现实的人;而且,现实的人之实践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进而言之,制度也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是随着人具体而丰富的时代实践之发展而发展的。
从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即使在史前史中,家庭制度也在不断变化着。摩尔根分析说,即使一个家庭也是一个能动的要素,不可能一直静止不动:家庭的变化伴随社会由较低阶段发展至较高阶段,由较低形式上升为较高形式;而亲属制度相反是被动的:亲属制度只不过是把家庭经历的较长时期所出现的进步记录下来,只有家庭出现根本变化,亲属制度才发生根本变化。[4]41马克思非常赞赏这一分析并作进一步补充:“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4]41马克思的补充不只是简单地拓展了范围,而是提示了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制度都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当它开始僵化了的时候,就不再匹配于发展了的生产力,这时必然要发生制度的新旧更替。
在一定意义上,本文认为制度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不妨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说起。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原因之一是制度的环节不可忽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生产力诚然是最根本的因素,但也不能归结为“生产力决定论”,因为制度的环节不可忽略。首先,生产力是抽象的概念,需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发挥出来,离开了制度化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现实作用无法向外发挥。对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更深一层的分析:个体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力量,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劳动者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当中;否则,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这就是生产力。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决不是单个人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而是“社会人”的一种整体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个人必须通过制度融入社会网络当中,通过制度化的生产关系联结起来,才能成为“社会人”。其次,生产关系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关系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设计,就只是一种虚幻的观念,只有制度化了的生产关系才具有物质载体。进一步言之,生产关系需要制度的巩固,否则就只是一种在生产中偶然产生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在中后期的著作中,逐渐以“生产关系”代替“交往形式”,这是原因之一。生产力是一种整体性的力量,是具有某种“物的形式”的“合力”“总和”,这个“物的形式”就是制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私有制作例证。他说:在私有制产生之前,没有私有观念,个人之间的交往还很狭隘,这些漠不关心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不能形成更高的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个人的力量通过制度化的交往关系表现出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把先进的生产关系巩固下来,使生产力以一种整体性的力量表现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推而论之,在社会的任何阶段,制度文明的程度都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通过制度的发展才能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自由联合体来表述共产主义社会,设想通过制度发展来把人从劳动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社会的整体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曲折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不朽的理论标杆。诚然,也应当清醒的是,从思想史上看,发展理论提出以后,很快就有了政治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的研究;现代化理论提出以后,很快就有了政治现代化理论、社会现代化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唯独制度发展、制度现代化的研究缺少建树。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发展理论,社会革新缺乏理论指导,那就无法进行顶层设计。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终究绕不开一个共同的问题——制度发展。没有制度的发展,经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政治的发展就会面临困局,文化的发展就会失去轨道。在现代化理论中也是一样,没有制度现代化,也谈不上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四、结论与启示
制度的属物性是对“人”自身一个理性认知的超越。人既然是社会动物,社会性相对于个体性必定更接近人的本质,自我意识范畴中群体理性相对优于个体理性。但是,由于自我意识“人自身”的自发关注,个体并不总是乐于自我扬弃,这样导致的局限性往往被主观意识呈现为合理局限性或局限合理性。因此,制度的属物性是属人性的第一个哲学的反思否定。日常思维中,人们易于接受“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窥察到了制度属物性的限度,但理性的演化却仍然不以“活制度”代替“死制度”,因为制度一旦“活”了,它的功能就消失了。反过来说,制度若失去发展性,就会变成真正的死制度,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也将失去活性。
具备了属物性,制度才有能力通过社会运行实现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实现之前,只是理念层面的、价值层面的;若无制度及相关载体,这种理念无法外化,价值无从实现。具备了属物性,制度才有能力确认生产关系。抽象的生产关系并不自具物质力量,因而需要物质力量的确认,其中,“看得见”制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生产关系的巩固和稳定成为可能,形成鲜明的社会形态。制度的属物性也是给人们提供行为结果的预估根据,使得利益的调整与秩序的形成能更有效地实现。
重温马克思思格斯的制度理论,对我们今天坚持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前社会上仍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把深化改革与制度自信对立起来,这是要不得的。我们恰恰要把两者统一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同时,又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是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到制度的属物性,特别是法律这种上位制度的至上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上百次提到制度,强调既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又要“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这是辩证法思维的深刻体现。在制度传动与社会运行关系的把握中根植规则意识与法治思维,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把握中统筹与推进改革,是这个时代理论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参考点。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5-36.
[3] 宋增伟.制度公正与人性完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24.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2.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Institutions
XUAN Jie1, MA Jianhua2, JIE Haiye3
( 1. School of Marxism,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2. Personnel Depart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3. Guangdong Lianji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Zhanjiang 524400, Guangdong, China )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in a social sense is the basic logic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ystem theory. From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confirmed.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is characteristic can be manifested in the objectivity and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In term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the system stipulates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information and energy, which becomes the fixed force of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pattern.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system, there is a certai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track and law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society.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is: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marks the degre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system, system self-confidence, social significance, system development, social operation
D621
A
1673-9639 (2021) 04-0086-07
2021-03-10
2017年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制度伦理与当代道德建设的困境研究”(XM2017124)。
宣 杰(1975-),男,广东廉江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哲学。
马建华(1976-),男,河南淇县人, 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揭海业(1974-),男,广东廉江人,讲师,研究方向: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薛 娇)(责任校对 张凤祥)(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