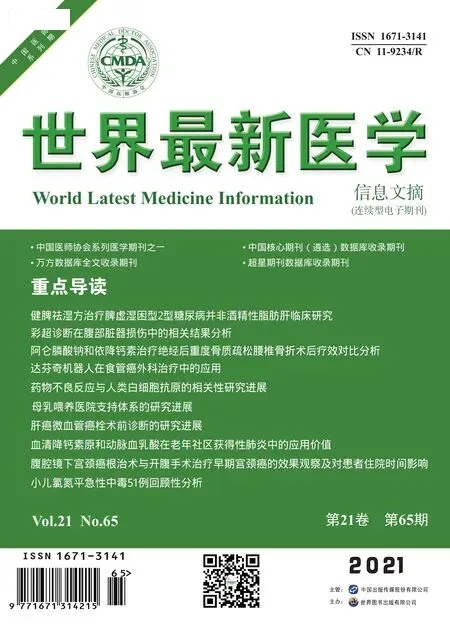李林默教授临床药对使用浅谈
2021-01-07张华李林默
张华,李林默
(1 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2 木易堂中医诊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 引言
中医学中认为,天人相应,生气通天,作为天地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应、在传统天人观指导下,中医学关注从天地自然的整体动态时空中去研究人的生合。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与时空自然协调协同的生命系统,人的生理病理与自然界的生态环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命学说强调生发和激活人体生机活力,认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即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病”,医学的目标任务是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其病理学说也非常重视成病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认为疾病就是由于人体不适应自然界时空而产生的,是人体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而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失衡状态,所以在治疗方面,主要从人与生态环境、时节气候的协调方面入手,以调整人体内外失衡的状态为目标,以期把人从疾病的时空状态转换到健康的时空状态。生生之机的观点,与生物医学模式的抑制和对抗原病灶的观点完全不同,其思路也与杀灭致病因素的“抗生”思路形成强大反差。名老中医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往往就是因为理解了“生生之机”的意义并加以充分利用,这也正体现了中医学所具有的优势。中医学观点强调为人类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治疗思路是协调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观点和思路贯穿于生理、病理等学说的各个方面,贯穿于疾病的病因检查、诊断治疗、保健预防各个环节中,全面奠定了中医学大生态、大生命、大综合的医学模式基础。西医也逐渐学习中医学的独特优势,开始了医学模式的转变。
1 文献溯源
药对的形成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是在古代临床药物使用中渐渐形成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虽然未见药对之名,但在其序例中提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1],及“七情和合”这些都成为药对形成发展的理论源泉。
而在早期以药对命名的文献中,包括《雷公要对》、徐之才的《药对》、宗令祺的《新广药对》等,虽多有散佚,但也能说明在当时的临床应用中,药对依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草经集注》在论述七情时记载“《神农本草经》相使止各一种,兼以《药对》参之,乃有两三,于事亦无嫌。其有云:相得共治某病者,既非妨避之药,不复疏出。”[2]而其中,相得共治某病的配伍方法也许就是现代药对配伍的前身,关于药对的记载,在《黄帝内经》中也可以看到,比如半夏与秫米配伍治疗失眠,乌贼骨与竹茹配伍治疗血枯,虽然未被称为药对,但已经具有了药对的组合特点,而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存在很多具有药对组合特点的药物配伍,如在《金匮要略》中以半夏配伍生姜,治疗呕而不渴的“支饮”。而对这个组合,陶弘景曾指出“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3]近代名医岳美中也说过“胃有痰涎而呕吐者,非半夏,生姜同用不为功”[4]。而张仲景以干姜配伍附子,来增强温中散寒、回阳救逆的功效,正如戴原礼所说“附子无干姜不热”[5]半夏配生姜,附子配干姜都成为后世常用的药对配伍。
知母与黄柏也经常作为药对使用,《本草纲目》在讨论七情时,以知母、黄柏为相须配伍为例,“知母得黄柏及酒良”,并指出“知母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而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黄柏则是肾经血分药。故二药必相须而行。”在黄柏条文下则有“古书言知母佐黄柏,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黄柏无知母,犹水母之无虾也。盖黄柏能制膀胱、命门阴中之火,知母能清肺金,滋肾水之化源。故洁古、东垣、丹溪皆以为滋阴降火要药,上古所未见也。”[6]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说明了药对的疗效卓著。
而现代医家对于药对也非常重视,秦伯未提出了“处方上经常当归、白芍同用,苍术、厚朴同用,半夏、陈皮同用等,这种药物的配伍,主要是前人经验的积累,有根据,有理论,不是随意凑合的。”[7]并列出了81 对药对的配伍。
在药对配伍中,有以功效相近者组方,有以功效相辅者组方,也有以功效相反者组方,这都归因于不同的治疗要求药对思想现代医家也阐发很多,陈维华在《药对论》中举出了以各种配伍法组成的药对,自从20 世纪80 年代施今墨先生的临床对药经验经其徒吕景山先生整理发表以来,对药的使用在年轻中医医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相比于对方剂各种配伍方法的分析实践掌握摸索,药对的简便效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临床中也能够随证加减,对于特定的病证的应对,一些在临床中久经考验的药对组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 临床思考
药对符合药物的配伍规律,但为什么还要使用药对,为什么不直接组合配伍单位药物,李林默教授认为药对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与临床意义,是真正地在临床治疗中经过了考验,证明了其只使用仅仅两味或者三味药物即能达到一个小的组合方剂的临床疗效。药对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但在遇到相对复杂的病情时,可以将几个药对组合使用。比如:大黄、芒硝配对,能够攻下实积;枳实、厚朴配对,能够宽中下气。如果实积兼有气滞,常以两对合用,攻积兼下气;黄连与吴茱萸,寒热配对,泄肝和胃,为呃逆吐酸常用,如果肝火犯胃,则黄连多于吴茱萸,如果肝寒犯胃,则吴茱萸多于黄连。通过病证变化,对药对进行组合加减,灵活变化,也使得药对的使用范围更广,更具灵活。
李林默教授更提出了药对的意义更在于药对配伍后,性能主治都发生了变化,或增强药效,或减低毒性、副作用。如麻黄,发汗平喘,利水消肿,与桂枝配伍则发汗力更强;与杏仁配伍则止咳平喘作用更好;与浮萍配伍,则利水消肿更好;与细辛或者干姜配伍,则可以温化寒痰;与肉桂附子配合,可以治疗风寒痹痛。而麻黄因性辛温而发散力强,一般不用于有汗者,但如果配伍石膏,则可以克制其辛温之性,就可以用于有汗而喘者。通过上面的例子,就能够明白了困扰很多初上临床的中医学生的困惑,一味中药效用很多,怎么确定其在方剂中到底发挥了其哪种效用,通过对药对的认识,就可以知道,很多药物在配伍不同的药物时,其功效的侧重点就会发生变化,熟记常用的药对对于年轻中医医生尽快的掌握遣方用药具有极大的益处[8]。
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以养生,阴阳平衡、辨证论治以治病,中医学从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出发,以气为本体,以明阳五行为结构模型,建立起了独特的生理、病理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正是中华传统哲学的全面渗透,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从宏观关系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9];而中医学之所以历经沧桑而经久不衰,也正是把握住了人与外在环境密切相连的规律,从心理、环境、社会等因素出发,全面揭示了人的生命规律。中医学强调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形体结构方面,人体由脏腑等组织器官组成,这些组织器官是相互沟通的,任何局部都是组成整体的一部分,与整体在形态结构上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基本物质而言,组成各组织器官,并维持其功能活动的物质是同一的(即精、气、血、津液),这些物质,分布和运行于全身,以完成统一的功能活动。就功能活动而言,组织结构上的整体性和基本物质的同一性,决定了各种不同功能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性,它们互根互用,协调制约,相互影响。所以,古人强调形与神俱,认为人的心理和生理功能有机融合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就病理变化而言,各脏腑组织之间,各局部与整体之间,在病理上可相互影响、相互传变而产生复杂的病理变化。
而在古代各类名方中,《伤寒杂病论》中所能够提炼出的药对也被大家认为是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的[10],在无法确定《伤寒杂病论》的组方规律的情况下,从药对入手来研究这些名流千古的传世名方也许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李林默教授对于药对的理解认识值得年轻医生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