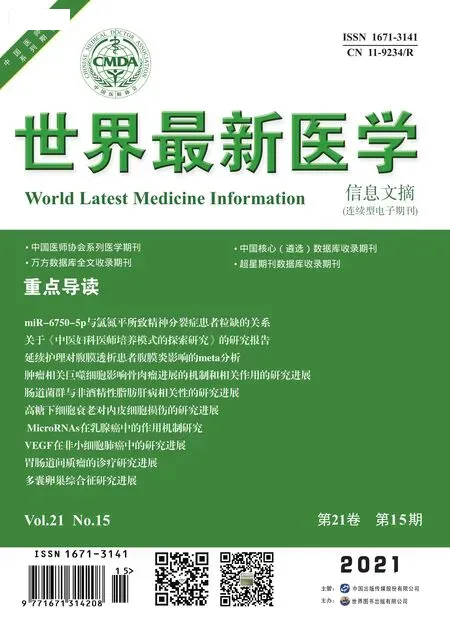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经验介绍
2021-01-06刘晓雪谢艳秋
刘晓雪,谢艳秋)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000;2.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天津 300000)
0 引言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再度活化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好发于年老体弱者,神经痛是其特征性症状,一般将带状疱疹1 月后仍有神经痛定义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1]。有研究发现[2],带状疱疹发病与周围神经病变、中枢神经病变以及精神因素均有关系。据报道,带状疱疹发病率约为0.14%-0.48%,而其中20%-50%的患者会发展成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3,4],且年龄越大,后遗神经痛的几率越高。
带状疱疹的西医治疗以抗病毒、消炎、止痛[5]、营养神经、缓解神经水肿为主,常用药物有抗病毒药物、抗生素、阿片类、激素、营养神经药物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以药物治疗、微创介入治疗、针刺治疗、臭氧治疗为主[6],但疗效较差,且毒副作用大。而笔者在跟师过程中,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则可缩短疗程,减轻了西药带来的毒副作用,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急性期治以清热利湿,解毒止痛
《医宗金鉴》论:“缠腰火丹蛇串名,干湿红黄似珠形,肝心脾肺风热湿,缠腰已遍不能生。”急性期以神经分布走形的红斑,红斑基础上出现粟粒至绿豆大小簇集样丘疱疹为主,常伴有神经痛,认为此多为心肝二经火毒炽盛,或肺脾二经湿热熏蒸所致,治以清热利湿,解毒止痛,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用于治疗肝胆实火上炎证以及肝经湿热下注证。方中龙胆即泻肝胆实火,有利肝胆湿热,泻火除湿,双管齐下,黄芩、栀子清热泻火燥湿,泽泻、木通、车前子引湿热从小便而去,给邪以出路,当归、生地滋阴养血,祛邪而不伤正,柴胡舒畅肝胆之气,引药归经,甘草调和诸药。全方泻中有补,祛邪而不伤正,实火得泻,湿热得清,循经诸证得愈。此外,急性期可用火针、刺络拔罐等方法治疗,使火热毒邪外散,可散瘀止痛,排脓消肿,加快皮损结痂脱落,促进皮肤修复。带状疱疹属病毒感染性疾病,急性期应及时予抗病毒药物以控制病情,常予盐酸伐昔洛韦胶囊0.3g BID,口服14天以抗病毒治疗,若患者病情加重或年龄较大或合并其他内科疾病,可与嗅夫定片 1 片/天,连续口服5 天。
2 后遗症期治以益气活血,通络止痛
带状疱疹后遗症期主要表现为皮疹消退,受侵犯神经区域仍有疼痛,疼痛持续或间歇发作,其性质多样,可呈针刺样、烧灼样、刀割样、电击样、走窜痛、放射痛或隐隐作痛。中医讲“不通则痛,不荣则痛”,故以益气活血,通络止痛为治疗大法。根据发病部位的不同,发于头面者,治以通窍活血汤,发于胁肋部者,治以复元活血汤,发于四肢者,治以身痛逐瘀汤。根据疼痛性质的不同,呈针刺样疼痛者,重用活血化瘀药,如桃仁、红花、川芎等;呈烧灼样疼痛者,可加栀子、紫草、白花蛇舌草、生地等清热药;呈走窜痛者,可加香附、柴胡、青皮等理气药;隐隐作痛者,可加黄芪、党参、白术、甘草等健脾益气药。
3 虫类药的应用
虫类药在带状疱疹后遗症期的治疗中不可或缺,一则虫类药乃“血肉有情之品”,缓中补虚。二则“久病入络”,虫类药可搜风通络,苛疾痼病无不用之。《临证指南议案》云:“考仲景于劳伤血痹之法,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强调病邪在络日久,气血交结成形,非峻剂可效,用虫蚁类辛咸之品,取其走窜之性,搜剔在络之邪,松透病根。三则“通而不痛”,张仲景说“若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虫类药有行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虫类善动,其活血通络之功是植物药不可比拟的,正如唐荣川所说“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大多数虫类药都具有抗炎、镇痛、镇静、抗病毒的作用[7-11]。
常用药物为全蝎、蜈蚣,全蝎、蜈蚣通络止痛,两者常相须为用,但全蝎性平,通络止痛之力不及蜈蚣,而蜈蚣力猛性燥,走窜之力强,通络止痛之效优于全蝎,两者同用,不论寒热虚实,均可应用。伴有瘙痒者,可加蝉蜕、僵蚕,带状疱疹后期神经损伤,除疼痛的表现外,还可伴有瘙痒,“风胜则痒”,僵蚕、蝉蜕祛风止痒。疼痛日久,病邪深重者,可加蕲蛇、乌梢蛇等蛇类药,《本草纲目》言蕲蛇“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言乌梢蛇“功与白花蛇(即蕲蛇)同而性善无毒”,两者均可透骨搜风,通络止痛,凡病久邪深,不论脏腑、皮肤均可应用。湿邪偏重者,可加蚕沙,湿邪凝滞经络,气血不通,则表现为重着酸痛,一般祛湿药,力量难以到达经络,加用蚕沙,直中病所。寒凝气滞明显者,可加九香虫,九香虫咸温,归肝脾肾经,理气止痛,温中助阳,辛香走窜,温通利膈而有行气止痛之功,可用于腰腹部带状疱疹后遗症期伴有腹胀、腹痛、便秘者。有瘀者可加土鳖虫,经络不通,日久必可致瘀,《本草经疏》言土鳖虫“治跌打扑损,续筋骨有奇效。乃厥阴经药也。咸能入血,故主心腹血积癥瘕血闭诸证,和血而营已通畅,寒热自除,经脉调匀”,且其性缓,对因虚致瘀者尤宜。若瘀滞重证则可酌情选用水蛭等破血逐瘀药,水蛭破血通经,逐瘀消癥,《本草经百种录》言:“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盖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之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反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入,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热象明显者用地龙,地龙长于通络止痛,且其性寒,尤善于热邪郁滞所致疼痛。
虫类药的有效成分往往是其毒性所在,在应用虫类药时,既不可恐其毒性而弃之,也不可因其疗效而擅用,应合理配伍,减毒增效,发挥其疗效。且虫类药大多性猛,易伤脾胃,在应用时应注意顾护脾胃,或制成丸剂,取“丸者,缓也”之意。此外,虫类药为异体蛋白,容易致敏,患者服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不适随诊。
综上所述,带状疱疹的中医治疗在不同的发病时期,病机不同,其治法也不同,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的原则,尤其是针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善用虫类药,优势显著。
4 典型病例
患者,男,63 岁,主因“右侧胁肋部红斑水疱伴疼痛2 天”于我院门诊就诊,患者2 天前右侧胁肋部出现红斑水疱,伴疼痛,随来我院门诊就诊,现症:右侧胁肋部沿神经走形分布的片状红斑,红斑基础上出现粟粒至绿豆簇集样水疱,疱液澄清,伴灼痛,纳食可,夜寐差,大便干,2-3 天/次,小便可,舌暗红,苔黄腻,脉弦滑。西医诊断:带状疱疹,中医诊断:蛇串疮,中医证型:肝胆湿热证,治法:清热利湿,解毒止痛,以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处方:龙胆草12g,黄芩15g,栀子20g,泽泻12g,木通9g,车前子9g,当归15g,生地20g,柴胡10g,薄荷9g,甘草6g。14 剂,水煎服,日一剂,早晚分服。盐酸伐昔洛韦胶囊0.3g BID,14天。皮损局部火针加刺络拔罐治疗,连续3天。
二诊:疱液干涸,部分皮疹结痂,未见新发皮疹,仍疼痛剧烈,口干喜冷饮,夜寐差,舌质红,苔黄,脉弦数。湿邪渐轻,热象明显,前方去泽泻,车前子,木通,加白花蛇舌草15g,紫草15g,炒酸枣仁30g,丹皮20g,生石膏15g,14 剂,水煎服,日一剂,早晚分服。
三诊:痂皮全部脱落,局部遗留色素沉着,右侧胁肋部间歇性刺痛,夜间尤甚,夜寐欠安,大便干,舌暗,苔薄白,脉弦。辨证为瘀血阻络证,治以活血祛瘀,疏肝通络,复元活血汤加减。处方:紫草20g,当归20g,赤芍20g,生地20g,柴胡15g,防风15g,蝉蜕15g,土鳖虫20g,地肤子30g,白鲜皮20g,全蝎5g,荆芥10g,生龙骨50g,酒大黄15g,天花粉30g,桃仁20g。14 剂,水煎服,日一剂,早晚分服。后随访,患者疼痛消失,右侧胁肋部色素沉着逐渐变淡,无其它明显不适。
按语:患者初诊时,湿热之邪互结于肝胆,故表现为胁肋部灼痛明显,此时应以清热利湿为主,故用龙胆泻肝汤为主方加减治疗,方中龙胆、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当归、生地滋阴养血,柴胡、薄荷疏肝解郁,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疱液干涸,部分皮疹结痂,湿邪渐轻,毒热渐重,故去车前子、木通、泽泻,加白花蛇舌草、紫草、丹皮、生石膏等清热凉血泻火,炒酸枣仁养血安神。三诊时,痂皮全部脱落,刺痛明显,表示湿热已去,久病入络,气血阻于胁肋部,“不通则痛”,故加用全蝎、土鳖虫等虫类药,搜剔经络,通络止痛。服药14 天后随访,疼痛消失,无其它明显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