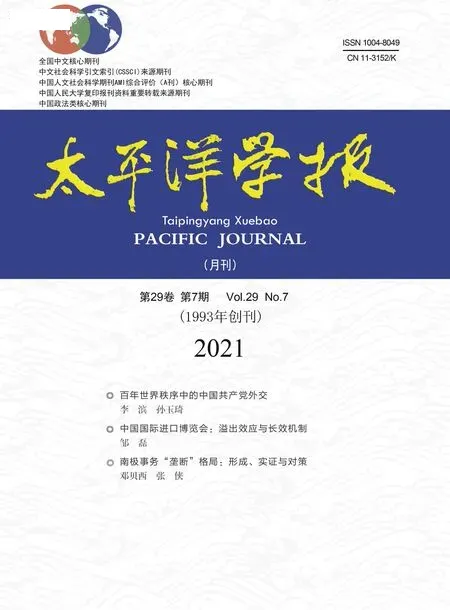百年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共产党外交
2021-01-06孙玉琦
李 滨 孙玉琦
(1.同济大学,上海200093)
世界秩序是一种历史结构。它一方面制约着国家形态,从而影响着国内的秩序;另一方面规定着国家间在国际上互动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按照结构理论,结构构成了施动者(agent)的“可能的限度”(limit of the possibility),施动者只能是结构下的被动者,自身缺乏主动性。如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结构主义的典型代表。①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这种结构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因此,世界秩序作为一种“可能的限度”影响并制约国家内政外交,特别是弱国的国家形态和对外交往。整个世界真正互为联动,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②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9.,这是因为当时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所致。经历百年变迁,世界秩序虽经变革但仍是强国主宰。然而,百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受人宰割的国家一步一步地摆脱外来的结构束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控制的、具有独特制度的世界强国。这种弱国“沧桑巨变”案例在百年的世界历史中并不多见。百年前,两个衰落的封建帝国——中华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是世界列强的支解蚕食的“禁脔”,处于危亡之中。但是,百年后的当下两者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无从比较。这一结果与作为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努力奋斗是密切相关的。中共的领导及其制度,以及中共的政治智慧是其克服外在束缚的法宝。在中共成立一百年之际,从世界秩序的结构角度,回顾中共带领中国人民突破“结构束缚”的成长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外部环境
世界秩序是一种历史结构。结构就是一种外部环境。它虽“不直接地、机械地决定行为,但施加压力与限制。人与集体在这种压力下行事,或抵制或反对它,但无法忽视它”。①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7-218.同样,国家在一种世界秩序下的行为也是如此。“国家的行为是以影响它的世界秩序方式为条件的。任何解释生产关系变革的尝试必须涉及国家与世界秩序”。②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05.中共百年的奋斗史就是改造了生产关系,这种改造首先是从民主革命开始,建立新的国家,重塑生产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共的百年对外交往是无法回避百年来世界秩序的。因为它对中共奋斗史构成了外部条件。
从20世纪20年代到当下,世界秩序经历了大体三个变迁。第一个阶段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冷战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两种制度相互竞争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是一个西方复兴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由盛转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三个世界秩序下,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起步,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
1.1 “大转型”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的影响
“大转型”时代意味着,传统的自由主义欧洲秩序走向没落和危机,世界向新的秩序转型。③Karl Polanyi,Great Transformation,Beacon Press,2001,p.3.在危机中西方衍生出三种不同政治经济体制——苏联式社会主义、英美改良式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体制为重塑世界秩序进行着殊死较量,同时这三种体制不同程度影响着世界各国。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55页。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成为转嫁西方社会危机的手段,革命成为改造世界的方式,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反抗外来统治与压迫的方式。这种混乱的秩序从19世纪末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是这一阶段。
这个时代给中国既带来了危机,也带来了革命与机遇。“大转型”时代代表了欧洲中心秩序处于衰败之中,帝国主义成为列强解决制度危机的手段,帝国主义瓜分、侵略中国造成了战乱与民族危亡,“国将不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同时,寻找解救民族危亡之道成为中国社会先进分子的共识。欧洲秩序的危机与解体产生的革命首先从俄国爆发,形成世界革命洪流,这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共的建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方式救中国的道路。所以有人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之路。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大转型”时代也是一种非霸权的世界秩序时代。⑥关于霸权与非霸权秩序的阐述见: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7.这种时代强国没有共同的制度、规范与意识形态得到认同。共同的约束下降,彼此矛盾协调机制丧失,纷争加剧。当时表现之一就是在殖民地势力范围之争强化。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带来了成功的机遇。
1.2 冷战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是一个两极的时代,是美国与苏联两个阵营与两种体制相互竞争的时代,也是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与主宰世界的时代。雅尔塔体系确定了两个阵营的范围。两个阵营在核恐怖平衡下保持着冷战的对峙,而广大“中间地带”成为两个阵营争夺的空间。由于美国与苏联都不是传统的殖民大国,都在一定程度反对旧的殖民体系,这为战后世界性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然而,在众多被奴役民族获得解放,成为新兴独立国家过程中,虽然它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但在冷战世界秩序的影响下,它们或以内战形式选择国家体制;或在独立后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选边站”。只有少数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才做到自主。
冷战阶段正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创阶段。两极的世界秩序为新生的中国既带来了安全与主权风险,也带来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机遇。安全的风险在于中国的制度必然招致西方阵营的敌视,国家安全遭受来自敌对阵营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受到干扰。同时,加入苏联阵营,也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对主权的干涉。机遇在于可以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争取“中间地带”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并获得外部资源。
1.3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对中国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冷战结束至今。在这一阶段由于苏联东欧集团剧变与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并且这一秩序正经历由盛转衰,进入“百年之大变局”。在这种世界秩序下,市场自由与西方政治“民主”成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国家制度的标配。几乎世界各国都加入了自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都不同程度地为了顺应世界经济的变化而进行了改造与改革。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规范被迫进行了改造。然而,新自由主义绝对化的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与社会危机,成为世界性动荡的源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新自由主义秩序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使世界秩序再度出现了变革可能性。这一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力增强的阶段。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既给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制度压力,也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机会。压力在于,这一制度是一种霸权的制度,它给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带来了巨大的结构压力,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与引诱中国改变社会制度。机遇在于它的经济特征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经济,使中国有机会借助世界市场发展自己。在这种世界秩序下,中国是少有的既能从这种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获得发展资源与动力,又能保持国家稳定与自主的国家。
1.4 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做到“沧桑巨变”的基本要件
可以说,中共的奋斗过程一直处于相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下。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在于中国革命起源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新中国建立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基础上,改革开放起步于相对贫困的不发达水平上——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这些都是造成外部环境恶劣的重要因素。
民主革命阶段,中共从诞生之起,就处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扑杀”之下,稍不谨慎就会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中共却能利用世界革命洪流、帝国主义之间争斗、大国之间在中国相互制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外部空间,避免了帝国主义与内部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结果。在两极的世界秩序下,中国的安全与主权也一直处于外部的威胁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先是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应对西方阵营的安全威胁,保障国家安全。之后中国积极通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对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主权和社会制度处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不断地干扰与压力之下,通过逐步的改革开放、战略隐忍,中共巩固与发展了自己的制度,并且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中共百年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都是处于严峻的外部环境之中,能做到“沧桑巨变”发展在于党及其领导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智慧。中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此,这个政党能够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以人民的需求为归依,动员、团结与带领人民完成一个个具体时期的任务。这个党由于建立在列宁建党学说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严密的组织性、高度的纪律性和相对的队伍纯洁性。这保证了党可以统一意志,以顽强的作风,不畏牺牲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中共建立的国家制度可以保障、动员与集中国家的力量,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党的性质与国家的制度是中共克服实力羸弱地位,获得强大执行力和组织效率,创造竞争优势的保证。政治智慧是政治艺术的体现,是发挥想象力有效实践的保障。正是中共杰出的领导人政治智慧使得党在逆境中,辩证地分析形势,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与决策,并有效地、艺术地确定和组织实施对外战(策)略,充分发挥能动作用。这种政治智慧一定程度与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有关,中共杰出的领导人从中吸取了精华。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共在百年奋斗史中能突破一个个外部世界的结构束缚实现中国共产党使命。这些可以从中共百年奋斗史不同的阶段体现出来。
二、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2.1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民主革命使命决定了党的对外交往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及其性质,使其一开始就把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作为民主革命任务。①中共二大就把这一任务作为民主革命的目标,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页。这既是中国人民当时普遍的愿望,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半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体现。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支持封建军阀相互混战,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成为当时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救亡图存,结束封建军阀战乱,破除封建传统,统一国家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因此,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有助于中共动员、团结与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只是中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当时的另一革命政党——国民党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共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是信仰所致,是在其他方式救中国失效后的选择。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东方农业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列宁《殖民地与民族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思想,共产国际二大做出决议指出,殖民地革命初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但共产党必须在这一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引导农民的革命性。。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这种选择符合当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现实。中共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只要坚持这一目标革命往往发展相对顺利,反之,超越这一目标或放弃领导权,革命往往遭受挫折。所以,目标选择正确是有效政治动员与团结人民的保证,中共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对外交往中就有了最大的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
这种选择必然使之把俄国及其领导的国际革命力量作为依靠的外部力量,而且这一依靠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一大就把联合共产国际作为纲领之一。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中国革命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其同盟军。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71-672页。所以,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在对外交往中依靠的最大力量就是苏联及其领导的国际革命力量。
2.2 党的成熟决定着党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成熟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分子成为领袖,中共开辟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逐步“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①见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摆脱了对苏联的盲从。这标志着中共的政治成熟。这种成熟首先体现党的战略的稳定,基本没有出现过像过去背离民主革命目标,脱离中国实际的过激政策。其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逐步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就对外交往而言,这种成熟表现为较好地处理与当时世界主要三种力量的关系。第一,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瓜分中国的矛盾,联合英美等力量,集中力量对付中华民族最危险、最直接的民族敌人——日本;同时也不盲从苏联的意志,较为艺术地处理与苏共的关系,如对王明等教条派的处理上。第二,高举民主建国的大旗,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美国部分人士的同情。抗战后接受美国在中国的调停,赢得美国与苏联对中共的认可,让国民党独裁与内战的意图彻底暴露出来。第三,利用美苏在二战结束初期在中国问题上的相互制衡关系,通过自身的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赢得对外的主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甚至让美苏都在争取新中国。这对避免美国直接出面干涉革命,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2.3 民主革命阶段党的对外交往总结
毛泽东曾经总结民主革命中中共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党的意志集中统一、党的政策具有高度的执行力、党的成员纯洁性和牺牲奋斗精神的保证。武装斗争是保证党具备坚强完成其任务的实力基础。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其任务的手段。没有党的建设所形成的队伍和团队精神,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没有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将无法建立自主而有效的统一战线,缺乏团结的资本。这三大法宝同样也适用于中共的对外交往。
由于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中共的军队成为一支非常有战斗力、有韧性的军队。中共军队建立之初由毛泽东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为中共的军队有别于中国其他武装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积极抗日的成果,才让美国认识到,中共的武装是抗日战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缺少这支力量不利于把日本“拖在”中国,因此,对蒋介石反共摩擦不认可,不支持,甚至反对。正是抗战中中共增长起来的实力,才让美国有意愿进行调停。正是解放战争中,中共独立的武装斗争战果,才能让美国对“扶蒋反共”有所节制,没有全面地介入中国内战。正是中共自主的武装斗争成功,才让美国对新生的中国政权抱有幻想,才让苏联认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不受指责”的。正是如此,中共利用了当时竞争的世界秩序,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的政权。
三、冷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大体上也是冷战之际。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中共最大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确保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是进行建设的前提。
3.1 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两极”中的取向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确立的对外政策是“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然选择。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帝,由此建立的新国家绝无可能继承它所打倒的旧体制国家的对外政策,绝无可能接受旧中国遗留下的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否则,革命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只有在此基础上,新中国才能与愿遵守和平民主平等原则的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同时,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使得新中国也不可能在世界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骑墙”选择,只能是“一边倒”,选择倒向社会主义的阵营,不存在与美国有“失去的机会”。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34、1473页。这一方针绝不是中共某个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革命的结果。
然而,这一对外政策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仇视;二是加入苏联领导的阵营会延续苏联对中国事务干涉的惯性。这都对中国安全与主权构成了威胁。
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安排,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中间地带”。但中国革命成功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清除西方在华特权,这招致西方阵营的担忧与仇视。中国革命胜利成为美国担心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证据,形成了军事遏制战略②1950年4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原子弹的成功爆炸等,都是美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证据,见FRUS,1950,Vol.1,pp.235-292.,全面介入亚洲,干涉亚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新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受到美国的直接威胁,如美国武装“保卫”台湾并在周边国家进行军事介入。这样,保卫国家安全与捍卫领土完整成了新中国头等大事。为此,中国与美国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正是由于中共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使得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赢得了极大尊重,也获得了急需的外部资源,还从苏联那里收回了过去失去的权益。
3.2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性决定了中共必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最初的一些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选择俄国道路成立中国共产党,其根本宗旨就是为了从苦难中解救中国人民,从危亡中拯救中华民族。这决定了中共从成立之日起把民族独立视为党的根本使命之一。虽然中共也谈国际主义,但绝不可能放弃经过艰苦奋斗获得的民族主权。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采取了“一边倒”外交方针,但不会长期容忍苏联/苏共的大国/民族沙文主义。
苏联/苏共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长期领导地位,以及特有的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及其盟国的主权已经成为习惯。过去苏联/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很大,中共在革命过程中走过的一些弯路也与苏共有关。因此,中共对苏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积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逐步成长,中国必然对来自苏联习惯性对其他党事务和国家主权的干涉“不以为然”。中共自然也不会接受苏联/苏共对中国主权事务上继续的“指手画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就一直反对苏联/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如1956年波匈事件中,中国就对苏共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与异议。后来又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共不惜与苏联“分道扬镳”。苏联的施压触犯了中国的主权,直至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末,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共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即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新战略。虽然这一时期对外政策有些方面可以进行商榷,但中共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严峻,在此条件下,中共再次调整对外战略,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提出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阻遏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一条线”战略反映了中共一贯在对外斗争中的务实而灵活的作风。
3.3 “两极秩序”下积极倡导践行国际关系新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从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苦难和自身对外交往中深感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与不公平出发,除反对各种霸权主义外,还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并顺应许多新生国家渴望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愿望,与一些国家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积极践行此五项原则,与周边一些国家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历史上苏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曾提出“和平共处”,也曾帮助一些弱小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传统,使其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弱小国家的关系。这从苏联没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就可以体现出来。但中共不同,中共建国后不但积极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且与一些周边相对弱小国家通过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可以说,这是新中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践行国家之间平等的新国际规范,团结众多小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民族压迫,促进民族平等,推动世界秩序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表现。这也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获得第三世界国家大力支持的原因。
3.4 党的绝对领导体制是新中国外交的组织保障
在这一阶段中共为维护新生政权的安全和独立自主,除自身的努力外,不断地借助国际统一战线,在两极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实现安全与自主。这其中离不开党与国家制度的优势:一是在于党的建设,党建的优势保证了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避免了在外交工作中出现不同声音,比如使新中国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转换中全党能步调一致,面对外部的压力,全党可以同心同德。二是在于有国家体制保障。就国家体制而言,新中国体制是处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排除干扰,动员民众力量去实现对外战略目的,不论是军事还是非军事的。这在抗美援朝、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的组织与绝对领导是中共与外部交往,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最大的体制优势。这种体制优势保证了全党、全国的“步调一致”,这也是弱国与强国在对外交往中最大的内在资本。
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4.1 党的工作中心任务的转移与外交的变化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共的中心任务转到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为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对外交往的中心任务。①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3页。同时,中共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突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两者建构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的外交战略,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外部环境以1989—1990年为转折点出现了变化。在这之前,由于冷战的余晖以及中国先行的改革开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战略需要,幻想中国体制转型以及外交根本转向,这也造成此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极为有利。但是此时中共比较冷静,没有因西方的“橄榄枝”而失去自主,而是及时调整了过去的“一条线”战略,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拒绝与西方结盟;同时开始与苏东国家与政党进行关系“解冻”,实现国家与政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样,中国率先走出冷战阴影,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践,成功地为中国的外交赢得主动。虽然中国与西方关系处于最好的历史阶段,也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中共始终告诫西方不要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抱有幻想。
4.2 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外交战略隐忍
1989—1990年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由好转劣。如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实现既定的对外战略目标,成为中共面对的巨大挑战。这一时期,已经无法借助外部大国力量来抵御西方对中国制度的冲击。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全局的眼光,提出坚守制度,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②邓小平在1989—1992年的有关谈话中,反复提到这三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三大策略应对挑战。没有党的领导及其相应的国家制度,中国无法抵御外部的冲击。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无法塑造与西方的共同利益,也无法增进其实力。没有战略隐忍与低调,国家的精力将无法聚焦于经济建设。从那时开始,中国基本都延续这一对外战略,一步步从外部战略环境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吸引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发展资源,使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增强了抵御外来制度改造的能力,使得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牢牢地稳固下来。
作为这一时期对外战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同于中共建党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对外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战略。一是不结盟,不当头。依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不在世界上参与集团政治对抗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二是广结善缘,少树敌手,“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并且发展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同时为了发展与各类国家的关系,搁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议,“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但是,这种隐晦战略并不是消极无为,而是隐忍中有所作为,即“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但这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一种革命式新秩序,而是兼顾各类国家利益与体制且体现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与发展,为的是从根本上改善国际环境。
江泽民和胡锦涛前后两任领导集体都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在坚定独立自主的“低调”外交基础上,也结合自身的力量和世界的变化有所作为。他们先后提出了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理念,具体并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比如江泽民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树立互信。②“外交部长李肇星谈学习江泽民同志外交思想的体会”,《人民日报》,2006年9月30日。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既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还涉及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为后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五个世界”的愿景奠定了基础。
4.3 隐忍战略成功的制度保证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席卷全球的时期。世界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不相容的众多国家要么改旗易帜,要么亡党亡国。而中共能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通过隐忍的战略发展起来,并保持与发展了自己的制度,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没有隐忍的战略,就会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国家的精力与资源将大量消耗在对外斗争之中,人民生活不会得到巨大改善,最终党的领导失去合法性,国家制度失去存在合理性。然而,隐忍战略与过去党的对外战略存在着差异,面对外部世界的不断挑衅,如何保证这一战略的成功得益于制度。党的领导和国家制度是其重要保证。没有党和国家的体制坚守(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外来制度与意识形态压力下,必然亡党亡国,隐忍战略就失去战略目标。同样,没有党领导下的体制,也不可能控制好内部的激进情绪,从而偏离隐忍而走向对外盲动对抗或自我封闭的道路。最后,没有这一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创造出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使得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利益,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互动中共赢的状态,隐忍中发展自己。
五、新时代党的外交
5.1 国内外变局催生新时代外交
2008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而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开始式微,新自由主义秩序自身矛盾重重,正当性与合理性正在丧失,有关国家在挫折中愤怒焦躁,担忧自己长期的霸权旁落,加紧了对中国发展的遏制。而这一时期中国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国力加速壮大日益使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构成了新的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所说,“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①“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新华 网,2018年6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6/25/c_1123029499.htm。可以说,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在这一阶段,中共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外部守成大国对中国焦虑与担忧却日益加剧,由此产生的“规锁”甚至是遏制也在加剧。为此,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去实现这一目标,是中国外交遇到的新挑战。
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新时代外交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中国自身能力发展,审时度势,在继承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工作方针的基础上,加大了奋发有为的力度,②有的学者用更加积极主动,见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8页。高举和平发展大旗,坚持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秩序的主张。这是一种新的对外战略,它旨在改革旧的世界秩序,从国际制度层面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同时也不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共赢的制度框架。这从新型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五大愿景③五大愿景,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各国共同的利益,人类共同的希望凝聚人心,用互利来促进合作,用共赢来化解敌对,用包容来反对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战略也是一种更大意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可以化解的消极因素,为今后的世界塑造一种国家交往的新模式。新时代的外交体现出中共既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创造有利的国际氛围,同时又兼具“达则兼济天下”为世界提供公平正义秩序的情怀。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中共正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践平台,积极推动着世界新旧动能的转换。除了从国家层面推动这一战略外,中共还从党际交往的层面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2017年11—12月中国共产党与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召开对话会就是这一体现。
5.3 新时代外交成功的保证
习近平在2018年5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10个坚持”,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时代外交。其中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共新时代外交的组织保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是制度保障。④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8页。这延续了中共外交的组织与体制的传统。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力量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优势,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与权威有助于在应对外部挑战中有效地维持战略恒定,排除各种干扰、向着既定的目标,协调各方资源,完成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体制赋予了中国外交在未来实现目标的战略自信。因为这种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应对危机的优势。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强国之梦的根本途径,这为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后盾。
六、总结与启示
中共建立百年以来,为什么能带领中国人民突破一个个外部结构的“天花板”,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保持国家的自主,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并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自己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外交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总结,可以抽象出什么样的经验?
6.1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中共的外交实践
中共带领中国“沧桑巨变”发展史,从西方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因为这种理论体现出来的结构决定论,决定了羸弱的施动者是无法抗拒结构设立的“可能的限度”。如沃尔兹就说,新现实主义是结构主义取向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而且往往并不主要取决于)国家性质,而且取决于国家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结构的变化。①[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中文版序,第16页。如果不是中共改造了国家性质,中国不可能在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世界结构下富起来,强起来,并使国际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即使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来看,这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这种理论虽然从国家内部因素出发,分析在外部结构下,国家会对外部的结构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但把这种不同归因于跨历史的国内政治传统或文化,如涉及中国的文化与对外战略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著作②这一方面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最为典型,他以明代中国为主要分析对象,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征。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就存在着这样的片面性。如果按这些理论的逻辑,中国文化具有某种跨历史的战略文化,那么离开了中共领导的、浸淫于中华文化的任何中国政府都可以做出百年来中共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民党政府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不可谓不弱,但结果非但没有“外争到强权”,反而寄人篱下。虽然中共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但如果不是中共性质及其相应制度,作为弱势地位的政党和国家,将无法突破外部的结构束缚,百年中国的巨变就不可能实现。
6.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外交经验总结
如果对中共百年来带领中国经历“沧桑巨变”成长史进行经验概括,总结其对外交往的成功经验,至少有如下几条。一是服务的总目标符合中国人民的需要,不论是反帝反封建、国家安全,还是人民富裕幸福,都是如此。没有正确的总目标就不能动员人民,团结人民应对外来的挑战。二是党的领导及其相应的制度(包括革命时代的武装力量、和平年代的国家制度),是意志统一、资源集中、激发奋斗与牺牲精神、组织效率的保证。三是适势的应对策略,这是一种政治艺术。不论是统一战线还是战略隐忍,都是依据实力与形势,为了实现目标的成事之道。前两者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也与战略分析的理论有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在于目标服务于广泛的大众,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内外的各种关系,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与国家学说。与战略分析的理论有关,这是因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领导下的军事武装制度和国家制度是弥补自身物质实力不足、实现组织行为高效有力的重要保障。第四个方面与实践智慧有关。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此使整个民族具有较高的实践智慧,而中共又高度重视实践智慧。300多年前莱布尼茨(Gottfried W.Leibniz)曾经对中西文明进行过比较,他说,“东西双方比较起来,我觉得在工艺技术上,彼此难分高低;关于思想理论方面,我们虽略高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实在不能不承认我们相形见绌。”③转引自:“300年后,他击败了牛顿”,快资讯,2021年1月7日,https://www.360kuai.com/pc/9db2948a0311ebf65?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中共在总结其革命与建设成功的经验时往往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事求是”等词语,这就是强调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从中共百年来的经历来看,只要注重实践性,不教条地照搬外国的经验(不论是苏联经验还是西方经验)或理解马克思主义,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党和制度的优势而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则挫折不断。这也是造成中共强调实践理性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实践智慧使中共可以破除教条,因时/因势地制定并实施相关的对外战(策)略,如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战略隐忍等。
另外,中共百年来应对外部挑战策略中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实施对外应对策略时“不媚强”“不欺弱”。百年来中共由于实力的不足,需要外部的援助与支持,需要妥协与变通,需要合纵连横或隐忍克制。但中共没有“媚强”,没有为了暂时的利益屈从外强压力而迷失自我,始终保持自己的目标与自主性;也没有“欺弱”,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助纣为虐或狐假虎威,没有侵略征服或剥削掠夺、欺侮弱小国家与政党。从毛泽东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邓小平要求任何时候对外都要谦逊,习近平讲“亲诚惠容”“正确的义利观”,都可以说明中共对弱小者的态度。可以说,中共是堂堂正正地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的目标,这与一些国家与政党为了自身利益“媚强欺弱”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6.3 未来的启示
这些经验对未来有什么启示?当下的中国,虽然国力取得了巨大的增进,但是今后面临的外部结构挑战依然严峻。当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的发展,预示着东方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强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使这个东方大国有了前所未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可以在国际舞台的中心发挥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作用。但它的崛起和影响还未达到改变世界结构和属性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①李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46页。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特色制度下的现代化不断建设,不仅会对西方的长期霸权者形成权力结构的冲击,而且在制度上客观上也会对其带来巨大压力。西方的焦虑与担忧,特别是美国的焦虑与担忧,将长期伴随这一过程。失落者的愤怒与疯狂引发的挑衅与限制,将会给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带来不断的麻烦与干扰。在这种可能的外部环境下,中共在百年的世界秩序中带领中国经历“沧桑巨变”的奋斗史能带来怎样的经验启迪?
首先是目标正确。中国百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没有正确的目标,就没有利益的驱动力、思想与道德的感召力。实现现代化强国梦及其由此伴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既造福中国人民,也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与需求的正确战略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才能动员与召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改革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种文明包容互鉴,建设一个清洁美丽世界。它既有利益普惠性,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是人类处在历史“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进步性的高度提出的目标。唯有坚守这一目标,才能团结动员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打破旧秩序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为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努力。
其次是制度坚守。百年的历史启示我们,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与国家制度才能克服物质能力的不足,战胜强敌;才能在统一战线或战略隐忍与克制中,保持自我,创造竞争优势。虽然中国目前国力已经具备了巨大实力,但仍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大国的整体实力仍远强于中国。这种现实将长期存在。如果丢掉这个法宝,目标将会发生偏差,精神将会懈怠,组织将会涣散,纲纪将会废弛,资源将会滥用,党的队伍就会失去斗争性与战斗力,动员团结群众的能力将会丧失。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共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做到“两个维护”的一个根本原因。
最后是大力提倡实践之道。百年的历史启示告诉我们,教条与迷信是事业成功的大敌。实践智慧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法宝。正是这种实践智慧,在中国革命中产生一大批经验丰富、不拘教条的“泥腿子”战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许多“不循洋教条”的政策措施。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建设阶段,进行的是全新的事业,面对的是不确定的外部世界,需要大量的具有实践智慧的执行者、聪明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应用在对外交往的各领域。洋教条与迷信盛行绝对无法推进事业。特别要提倡从历史中感悟、实践中体会的学风,切实改变“言必称西方”“文必从套路”的迂腐。学风其实在塑造行动者习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