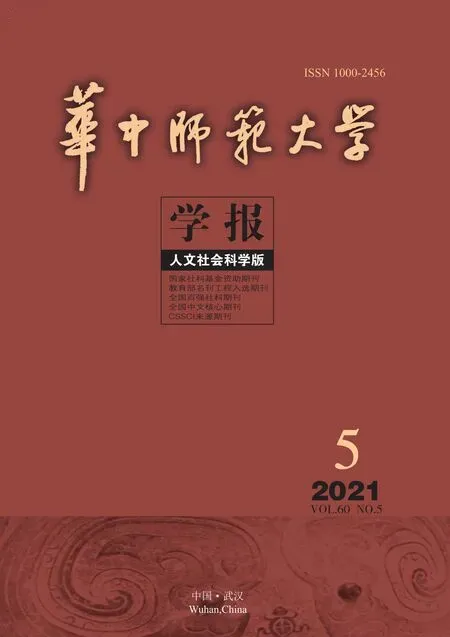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中的平民书写与城市伦理
2021-01-06何锡章张雯君
何锡章 张雯君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都市仿佛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代,战争血腥,混乱嘈杂。与30年代的摩登不同,上海市民还未从抗日战争隔绝、沉闷的“孤岛”状态中走出来,又陷入国民政府政治高压、经济崩溃的“至暗”时刻。战争将上海连同作家一起坠落到窘迫飘零的境地,如同末日来临的悲剧一样,此时的海派作家们陷入一种窘迫尴尬的生存境遇,成为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城市平民,每天去应付与生存相关的家长里短的问题,去品尝柴米油盐的艰辛。与此同时,40年代“海派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吁求是非常特殊的”①,既背离了传统,又与现代观念相去甚远,代表了极端生存环境下的城市伦理状态。本文拟从20世纪40年代海派都市小说入手,去探索动荡时局下的城市生活、生存样态、价值观念等核心问题,从而深入了解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城市的伦理嬗变。
一、“凡人”视角与日常生活伦理
这是一座缺乏“英雄”的城市,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围城,昔日繁华的上海都会已沦为兵燹浩劫之地,广大的精英阶层要么迁往内地要么逃亡海外,只有那些无力可逃或者无路可避的普通市民成为纷乱城市的留守者,只能作为劫后余生的“凡人”——城市平民苟存于世。如此“逼仄”的城市生态造成了写作的巨大困境,作家们要么放弃写作,要么将其简单地斥为“罪恶的渊薮”。但是,对于40年代的几位海派作家——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无名氏、予且、徐訏等人来说,“凡人”视角反而让他们的写作游刃有余,能够探入城市的肌理,去重新发现与开掘市民“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与美学意义。
表现之一是回到沉重的“肉身”。战争造成了上海经济的衰败,使得大量滞留沦陷区的市民陷入了生存困境。“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到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下降为53.6%,只有原来的一半。”②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军采取文化恐怖政策,对具有反日言论和倾向的人实行监禁和屠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回到沉重的“肉身”,回到感性,回到生活的切肤之痛成为许多上海作家迫于无奈的选择,正如无名氏所慨叹的:“谈论这二者(灵与肉)平衡的人不少,真能拿出一套理想的具体办法的人,并不多。”③返回“肉身”带来的一个城市伦理倾向是,海派作家回避“国家”、“民族”的宏大价值体系以及“革命”、“历史”等巨型话语,大多以生活在主流价值之外的“世俗生活”作为自我生存方式的标榜。
在40年代海派小说创作中,“饮食男女”成为这种“世俗生活”的普遍故事主角。予且的“石库门”系列短篇一本又一本地招引着读者,从1942年至1945年,他几乎成为《大众》月刊的头牌作家,用一种巴尔扎克描绘巴黎的写作方式创作他的上海沦陷时期的“民众百生图”。像《觅宝记》《寻燕记》《埋情记》《拒婚记》《争爱记》等作品,都市男女的人情世态成为予且写作的不竭动力。与30年代的爱情游戏和情爱追逐不同,他似乎更愿意表现成年男女在家庭日常生活样态中的情感纠缠,在撩拨广大市民情感的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上海市民特殊时期的风俗画卷。张爱玲的“上海弄堂”系列展示了“战争后的第二天”痛苦而漫长的日常生活状态,当炸弹把文明炸成碎片,劫后余生的人们只剩下生存的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④甚至当“饮食”受到威胁时,“男女”之事也可以不屑一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战争”与“孤岛”不过是其故事深远的背景,而比这些更加深远的是每天醒过来的日子,要愁柴米、要谈婚嫁、要勾心斗角、要求职谋生……在这个城市是没有英雄的,有的只是凡俗的人生,正如张爱玲所言:“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⑤
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返回“肉身”便是现代城市伦理道德水平的下沉。这种带有生命真实与存在真实的“身体经验”写作对那些被遮蔽的、未被发现的、边缘化的甚至是新出现的“日常生活”的挖掘,无疑具有新鲜度和开拓性,特别是对于城市“亚文化”和市民“生活伦理”具有“敞开”的意义。只不过在战争环境下,上海普通市民已经退守和龟缩到更加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甚至于是私人生活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只不过是从“高端”社会需求转向了“低端”的生存需求。与国家伦理“精英视角”的“俯视”不同,40年代的海派采用了日常伦理“凡人视角”的“平视”,海派小说的叙述者要么以“亲历者”身份要么与作者具有生命同构性的生存个体,实现了对市民生活的真实回归。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大多是以自我的生活实录,以唠叨式的本色语言,来展开战争情境下日常生活的叙述。那些不加修饰的平铺直叙,唠叨着“活着”、“过日子”的生活细节,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结婚生子、求职谋生的无尽话题,让读者在他们的唠叨中重新经历生活的流程,重新咀嚼凡人的艰辛。这也可以解释像予且的“石库门”小说、张爱玲的上海弄堂世界等带有沉重肉身的书写,能够风靡40年代上海都市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叙述中,这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自由的凡俗世界,所能写的只有平凡人物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长里短,这也恰恰迎合了战争年代已经疲累的广大市民的阅读口味与需求,于是作家与读者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把40年代的都市文学引入人间烟火。
表现之二是重返家庭的“本位”。40年代海派另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是离开了繁华、喧闹的街市与纷扰、混杂的社交场合,还原到波澜不惊的最小家庭单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成为这一时期海派文学的生动写照。除了“肉身”,其实家庭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头维系着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伦理,另一头则维系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钱穆说:“家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现有家庭观念乃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⑥。正因为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现代作家的强项,似乎热衷和习惯于讲述家庭的故事。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巴金的《家》、冯沅君的《隔绝》、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等,上演了一幕幕个人与家庭“冲突”或“出走”的正剧,以此显示出现代人格与封建传统文化的象征性决裂。对于海派作家而言,重返家庭不过是战争环境下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这里断不是栖息的乐土,而是寄生的暂时居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语),战争背景下的日常蜗居状态,让他们更加沉潜和冷静地探查身边的城市居所,从而深入地揭示出一种糅合着家庭琐碎性与冷漠性的伦理困境。
苏青代表作《结婚十年》的成功秘诀便是表现家庭生活的琐碎性,40年代的上海文坛,革命、抗战、反抗等主题都是写作的禁区,与读者们“同病相怜”的家庭故事于是成为作家们的主流创作,与此同时,一脱30年代海派奇巧诡谲的语言技巧,苏青的语言充满都市居家者的琐碎与亲切。絮叨话语和直线叙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表达形式。苏青按照生活的流程讲述了“我”从结婚、生儿育女、夫妻反目、愤而离婚、独闯上海、成为职业女性的十年人生路。语言平实、平铺直叙、牢骚满腹、好发议论是她的语言特色,结婚时的仪式在她的回忆中没有神圣和幸福感,反而在每分每秒的无聊中煎熬挪动,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也是她写作的主要话题,成为她人生中艰难翻越的坎坷遭遇。这种家庭生活的琐碎性既体现了作家们对于日常生活现场的抵近观察,也成为特殊时期上海市民晦涩、灰暗生存状态的“本色实录”。
师陀和徐訏在40年代的创作转型在于揭露了家庭生活的冷漠性。师陀早期的作品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抒情笔调,而徐訏的创作则富有东方色彩的神秘浪漫,然而他们在40年代关于家庭题材的写作,却一改往日的风格,充满了现实苦难的悲情。师陀的《结婚》前半部分以主人公胡去恶同乡下女友通信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叙述了主人公不幸的童年和生活的困境,同时也充满了对组建幸福家庭的热切愿望;后半部分则从主人公两段结婚梦的破碎来展示了家庭现实的残酷性——这也充分揭示了沦陷后的上海作为混乱凶险、弱肉强食的世界,能够毁灭所有家庭的温情脉脉。徐訏的《一家》则描写了“抱团取暖”式的中国家庭在战争环境下是如何分崩离析、渐渐瓦解的。故事中的林家是杭州一个典型大家庭,当战争的烽火打破了安静和谐的旧家庭生活,从杭州逃亡上海的过程中,兄弟、妯娌、父子之间,都是各怀鬼胎、各自算计,这种家庭道德的堕落最终在逃难路途中导致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悲剧结局。这种冷漠性的写作到了张爱玲那里变成了更加残酷的家庭禁锢与功利化生存,对战时的上海家庭道德状况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全面审视,这在后文中会有更加详细的阐释。
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作家重新捡拾起家庭的写作主题,重返家庭的故事现场,然而这次重返家庭的“本位”并非简单的回归,毕竟经过了几十年现代家庭理念的洗礼,这种家庭书写又呈现出某种“反家庭”倾向,长期以来家庭叙事和审美研究对此习焉不察,然而从伦理视角出发便能发现端倪——重返家庭“本位”并没有凸显家庭伦理的和谐、温情,也同时超越了单纯的批判和简单化的善恶标准,海派作家在家庭审视的层面走得更加深远,不仅析出了家人之间的隐恶与残酷,而且让我们见识到人性的扭曲与亲情的淡漠。
虽然都是一些都市中的平凡人物和普通的家庭生活题材,但是经过作者的细心观察和精心打磨却自有一番风味,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以往文学创作中对市民生活和伦理状况的忽略。安稳的生活幻想飞扬的人生,而动荡的生活更期冀稳定的人生——这是40年代“凡人”视角与日常生活伦理在海派创作中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长期混战,导致都市人紧张的神经逐渐麻木,加之孤岛世界的经济问题,市民生计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当如何生存下来成为首要的任务时,上海市民的行为、心理、伦理也会具有日常生活形而下的特征,许多海派作家正是以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顺应了都市特征的变化,才让读者与作者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共鸣。
二、“谋生”身份与底层生存伦理
城市伦理向日常生活的转向,自然会影响上海市民的身份定位与道德标准的微妙变化。自晚清以来,市民身份先后经历过几次大的历史变更:首先是五四时期的启蒙伦理推翻了宗法伦理体制和“臣民”封建等级身份;其次是建立了民族国家伦理体制和“国民”社会身份意识;再次是步入了现代商业社会伦理并出现了“市民”社会身份意识。然而到了4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沦陷区的广大民众失去了政治共同体的庇护,他们不仅“市民”身份跌落尘埃,连起码的“国民”身份都已经毫无保障甚至是彻底丧失了,“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中,活下去成为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带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价值体系,满足不了他们求生的卑微要求”⑦。从伦理的层面而言,这是市民道德标准的一次历史后退与身份上的“下沉”,他们既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也不甘心接受日本人所强加的“大东亚”的成员身份,从而转向一种底层生存伦理。
“谋生者”成为底层生存伦理的主要身份意识,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为了保证战争状态下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市民舍弃了那些带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标准,为追求个体生命的生存保障和利益成为最大的“善”与“正义”。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文学中充满了“谋生者”的文学形象与文学故事:像予且《七女书》中的钟含秀、朱如意早已将自己肉体甚至灵魂卖给了“物质主义”;师陀《结婚》中的原本善良的胡去恶最终将“都市恶宣言”当作真理信奉;巴金《寒夜》中的汪文瑄与曾树生忠贞的婚姻终于禁不起战争与贫困的摧残而宣告破灭;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等知识分子同时挣扎在婚恋围城与战争逃难的困境之中;丁谛的《人生悲喜剧》和周楞伽的《失业》《沉沦》充满了上海失业者的贫困潦倒;杜衡的《人与女人》与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前者为姑嫂后者为姑侄女)都讲述了都市的女性最终为了生存而向亲人出卖自己的故事……这一类的谋生者的故事“统属于‘社会——人’的构造。‘社会’的功用相当于一个杀手,它虐待人,残害人,而‘人’最终是个弱者,哪怕是个恶人,也是弱者,受害者,显出与左翼小说贫富对立结构的区别来”⑧。
这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城市谋生者们,从“战争的第二天”开始便摆脱了宏大的价值体系,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之处,转向思索生活的主题;从生存的基本需求开始,来理解什么是底层生存价值。谭惟翰的《海市吟》如今而言早已没有当年的风光,但是这本关于40年代都市人的短篇小说集,无疑是当时上海中下层市民的命运写真。传统文人“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与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在这本小说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有的描述着都市小人物的悲情,像《顽童》中的穷学生与《大厦》中老建筑人,在上海这座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中,充满了命运的坎坷,尝遍世间的冷漠;有的刻画了市民含辛茹苦让孩子出国留洋,却换来玩世不恭的纨绔作风与麻木不仁的冷漠灵魂,《荣归》同30年代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演绎着平民女性的牺牲与社会不公的控诉,《雨后的山岗》是市民版本的“祥林嫂”,凤英不仅受到了强人的抢劫和践踏,同时还要领受爱人的利欲熏心,而《舞台以外的戏》则展示了无论是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林芝草作为社会“三教九流”中的伶人艰难求生的悲苦命运。尽管在40年代海派中谭惟翰并非知名作家,且其小说情节过于简单,人物塑造也比较粗糙,但是他对于沪上市民的扫描,通过对笔下人物命运和内心世界的阐发,表现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他们排斥或者期望怎样的世界和生活方式,都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得以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市吟》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谋生者”身份的确立,为城市底层的平民世界提供了新的伦理标准。一种是“以生为善”。换句话说,就是“活下去是最大的道德准则”,这种伦理标准的转换,赋予了战争环境下,尤其是上海沦陷时期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他们放弃了宏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而为了个人生存而苦心经营因此具备了道义上的可能性,同时在道德层面上得到某种认同和宽恕。正如苏青谈到个人的文学创作时说:“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假使我赶时髦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⑨正因为如此,在文学写作中社会政治、革命运动、文化冲突等宏大的题材都消失了,反而是表现都市琐碎凡俗的底层生活成为叙事主流。30年代的上海生活,人们感受最多的“变”,像汪丽玲、周楞伽、丁谛都曾写过一个相同的小说题目——《变》,凸显了上海城市对于人的改造,像汪丽玲写出了憨厚淳朴的长者在都市的陷落;丁谛写出了十年前后两个大学生同学相遇后的身份对比,最大的讽刺是品学兼优者只能成为一名穷酸的教师,而昔日低才者却成为上海某银行的经理;周楞伽的《变》则写了老实巴交的女佣如何成长为八面玲珑的姨太太的成长史。到了40年代,同样几位海派作家,对于生活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们写的更多的主题是关于“沉沦”,像曾今可的《舞女丽丽》《春梅姑娘》中善良美丽的农村女孩最终成为都市的舞女,因为贫穷而堕落;周楞伽的《沉沦》《失业》则关注了都市底层男性在贫穷和饥饿面前的道德动摇,最终沉沦为城市偷窃者与抢劫犯。城市以自己的面貌和方式改造广大“谋生者”的人格:矫情、功利、重物质和敏锐、开放、通达,懂得处世艺术,总的来说,油滑比起老实呆板更加适宜社会环境,这是40年代上海都市严酷的生存法则。
另一种是“物质主义”。我们通常意义的文学多关注道德、关注精神,忽视物质,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离开金钱与物质,基本生存都很难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海派作家,他们不逃避金钱,不回避贫困,尤其在金钱和贫困之间的道德抉择,和都市人性密切吻合。史美钧是常被人忽略的一个海派作家,但是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他对上海社会的观察和描写比张爱玲早了十年,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写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直到上海解放都是笔耕不辍,抗战前有《晦涩集》,抗战期间又有《披荆集》,抗战结束后又有《错采集》《衍华集》,二十年间出版了9本著作,且大多是短篇小说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作品中对上海底层市民的密切关注和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表现。《错采集》收录了描写1944至1949年间上海市民的故事,题材非常广泛和丰富,如《寒蝉曲》描写的是落难歌女的凄凉命运,《豆萁吟》描写的贫困兄弟的悲惨命运,《穷城记》表现了投机走私者的狡猾奸诈,《儿女的憧憬》描写了教育行业里中学教师的困窘生活,《斯人憔悴》则关注了上海下等官员的众生相——这就是都市经验。我们经常说小市民生活,我们谴责他们的狡黠和追名逐利,但无论这种生活是富贵还是堕落,它在告诉读者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40年代的海派文学将人的物质追求合理化、道德化,这与我们农业文明所形成的传统有些“背道而驰”,然而在都市文学作品中,底层民众的物质化生存与追求,得到细致入微的阐释,也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演绎,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都市经验,同时也为都市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向度。予且在《我怎样写七女书》中有一段关于物质主义的深刻观念:“人是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他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吧!’”⑩这句话仿佛一句咒语,戳穿了所有的真爱幻想,既然在物质世界里我们无法升华,那么“就堕落一点吧!”予且的话至今令人黯然神伤。
文学创作总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尤其对于长期浸染在商业化、功利化、物质化的海派文学而言,在乱世中仍然能够艰难地存活下来,同时能够冷静地观察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风景,这本身便是一件令人叹服的事情。就生存伦理的角度而言,能够完成“国民”身份向“谋生者”身份意识的转换,并能够在民国政府西迁,外族势力入侵以及租界势力阻碍的困境之下,上海市民能够构建出一种日常生活为主体、底层生存哲学为标准的自我空间,是一种坚韧而务实的生活态度。尽管这种底层伦理标准也有很多令人诟病的地方,然而他们在战争环境下,尤其是生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能够建立起支撑日常生活和底层生存的价值体系,寻找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生存伦理的奇迹。
三、“利己”主义与功利价值伦理
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所折射出来的城市伦理表现出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样一个战争环境下相对封闭的孤岛世界,加上上海都市特殊的商业、市井、码头文化氛围,更容易孕育一座市民化的城市。在这里“城市平民更加关注个人吁求的满足,这一点成了新时代的立身之本,存身之道,长达几十年的政治伦理与民族主义,仿佛一夜之间被无数人声鼎沸的‘小我’生活所取代。然而,一旦欲望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又未建立起一种新的伦理思想,这种功利主义很容易滑入利己主义的深渊”。毕竟,都市生活是没有情感的,相对来说,乡土社会是讲究情感的,远亲不如近邻,让人很温暖、和谐。而城市是孤独的,冷漠的,城市的关系是一种实用性的交换关系。功利性交往成了商业、市场地带的铁定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它是商业社会共通的定律,是大家相互约定的、相互遵守的,它不存在对谁的不公平,不能简单地视为对弱者的不公平,对强者亦是如此。穆时英的《夜总会的五个人》里,昨天的金子大王,今天破产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昨天可以挥金如土,今天只能命薄如纸,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都市功利性。到了40年代的上海,这种功利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战争环境下,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与底层生存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呈现出将私欲化的个人利益看作道德目的,甚至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正如利己主义所倡导的:“每个人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个人利益。”
20世纪40年代海派文学的利己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利益至上的唯利主义。这是基于争夺个人利益的生存空间而表现出对社会集体价值的冷漠与排斥。这些社会集体价值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基本价值观,如真诚、善良、和谐、友谊、关爱、良心等,唯利主义对于这些核心价值观都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作为40年代四大女作家的潘柳黛,曾经根据个人经历创作了小说《退职夫人自传》,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女主人公柳思琼的不幸遭遇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塑造了一位唯利是图、虚情假意的情场浪子阿乘。此人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虽然大学毕业却不务正业,又爱慕虚荣和贪恋女色,用上海话来说是“吃白相饭的”。因为母亲早亡,父亲吸毒,阿乘寄宿在叔父家中,遂与婶娘方娴私通。方娴比阿乘大12岁,但是有钱,在叔父这里得不到的“恋爱”感觉在年轻的阿乘这里享受到了,哪怕二人之间是乱伦的关系,但是一个求“情”另一个求“财”,二人相处得倒是如胶似漆。后来,阿乘在一次交际场合认识了文化名人柳思琼,她是记者出生,文笔犀利,是职场能手,从新闻行业退职后转行为自由作家,同样混得风生水起。相较人老珠黄的方娴,柳思琼在阿乘眼中可谓有貌有才、有名有利,二者可谓高下立判。自从认识柳思琼之后,这个“恋爱专家”立马移情别恋,为博得美人欢心,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他的表演天赋和语言能力,最终让柳思琼深陷感情与心理的重重情网。当他与方娴的丑事暴露,柳思琼想与之分手之际,阿乘运用花言巧语反而骗取了柳的信任并与之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柳思琼怀孕失业,阿乘也丢了饭碗。此时,阿乘见柳思琼无利可图,于是谎称去内地发展,抛家弃子重又与方娴私奔。抗战结束之后,柳思琼最终找到阿乘,他以为柳又重返职场,于是又抛下了方娴母子,回到柳思琼身边,待知道柳并无营收之后,又对柳思琼冷淡粗暴,且暗中与方娴继续往来。阿乘的故事,令人瞠目结舌,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可谓是唯利是图的极致演绎,正如柳思琼最后意识到的:“阿乘要女人,也要钱,女人的钱没有了,对女人的爱便死了。”对于个人利益而言,金钱与美色是阿乘这种浪子追求的生活目标,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在阿乘这种人心中,钱又是重于色的。至于骨肉、亲情、爱情,在阿乘心中是没有分量的。这一形象,是唯利主义中“势利眼”的生动写照。
其二,人性异化的性恶主义。在西方的伦理学著作中,利己主义并非一个贬义词,反而是尊重和理解个人利益的一种体现。如果一个社会连尊重每个人最大的个体幸福都无法做到,那么这个社会的管理体制和价值观念是有问题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战争环境下,不少海派小说演绎了利己主义的极端化形式,那就是以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为了维护个人的幸福,甚至不惜抛弃、牺牲甚至戕害他人的幸福。长期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城市环境中,加上战争的催压,每个人的心态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这就是极致环境下的战争后遗症。在40年代海派作家中最善于捕捉人性异化状态的作家是张爱玲,她的诸多作品都充满了人性的畸变和灵魂的撕咬,哪怕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亲人也概莫能外,甚至他们之间的争斗显得更加酷烈。富有代表性的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成长史,她们虽然背景不同,家庭不同,但都出生卑微,梁太太年轻时家境贫困,可说是一个破落户,曹七巧的家境也好不到哪儿去,是一个开麻油店的,一直寄居在哥嫂家中。她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颗不甘久居人下、渴望向上攀爬的心,尤其是对金钱和权力的贪欲,是她们能够在困厄环境与家族倾轧中杀出重围的不竭动力。当她们在嫁入富家豪门之时,便是将青春换明天,以年轻与美貌为人生最大的资本,赢得经济利益和家族权力,一个嫁给了年逾花甲的老头,另一个则嫁给了佝偻症的患者。二者的成长路线虽有不同,但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梁太太以年龄的优势等到了“丰收的季节”,老头死后给她留下了豪宅与遗产;曹七巧拥有了一儿一女站稳了脚跟,并通过忍耐、排挤和报复获得了一家之主的特权。然而她们的代价也是惨重的,梁太太终身没有子嗣,而且在家族中声名狼藉;曹七巧则变得阴险毒辣、毫无人情,遭到众人怨恨。
当然,这只是她们人生迈出的第一步,获得经济上的个人利益,然而这些用物质金钱观念和都市生存法则培育出来的“恶之花”,又开始用商业交易的方式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给自己谋得更多的好处。不甘寂寞的梁太太,将豪宅变成了都市显贵的交际场所,同时她也收买和包装了一批年轻的女孩作为诱饵,让这里成为达官显贵趋之若鹜的风月场所,在缓解她爱情焦渴的同时也为她赢得经济上的利益,将这些干女儿们嫁给富豪们来营利。其中,还包括她的亲侄女葛薇龙,因为战争中经济困顿而来求她,梁太太却将她包装成一朵交际花来招蜂引蝶,令单纯质朴的女学生在锦衣玉食的诱惑下沦落风尘。曹七巧则连身边的儿女都不放过,还在孩子儿时她便用鸦片烟来控制他们,以至于方长安和方长白都成了“瘾君子”。对于曹七巧而言,儿女不仅是亲人更是她的“私产”,她是不允许私产离开或者逃避她的统治的,因此,她处心积虑地破坏一双儿女的婚姻。在儿子结婚的第二天,她便开始捏造儿媳妇的“丑行”,同时牢牢将长白拴在自己身边。对于叛逆想离开自己的方长安,听闻她自由恋爱,便在长安鸦片犯瘾的时候邀请女儿的男朋友来家中见识女儿的丑态,最终达到棒打鸳鸯的目的。曹七巧已经不仅仅是用虐杀和折磨的方式掌控儿女,而且见不得身边的女人比自己幸福,对儿女们的婚姻横加干涉,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当然曹七巧的结局也是可悲的,众叛亲离落得孤独终老,正如小说结尾处所描写的:“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可见,性恶发展的结局终究是末路。
利己主义是20世纪40年代海派文学发展的一个极致状态,并不代表大多数作家的伦理观念,更多的城市人物都挣扎在都市底层,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被不断消磨。与传统道义论强调人性的超越性不同,这一时期的部分作家,如张爱玲、予且、潘柳黛等作家更加强调对人性原欲的尊重,尤其是来自于人性真实的伦理吁求。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环境下城市市民的道德状态,对于现代城市伦理的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书写,在文学史中似乎书写了一段黑暗混乱、不堪回首的往事,由于战争的爆发,社会动荡,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沦为“孤岛”,政府的缺失,令市民的国民身份顿时“失效”,精英群体的内迁,让上海变成话语的“空城”。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正是上海的特殊时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广大平民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传统文学和五四文学经验不同,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伦理、物质化的底层生存伦理以及功利化的利己主义伦理,成为这一时期城市伦理的主流,传达出上海市民并不崇高但是真实可感的道德体验,带来一种全新的都市写作经验,甚至更加深入生活的原生态与人性的境界。因此,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民凄苦和悲哀的城市生存,反映了城市伦理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沧桑变化。
注释
①⑦杜素娟:《市民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第119页。
②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③无名氏:《无名氏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④张爱玲:《烬余录》,见《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⑤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页。
⑧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⑨苏青:《苏青小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⑩予且:《予且代表作·浅水姑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