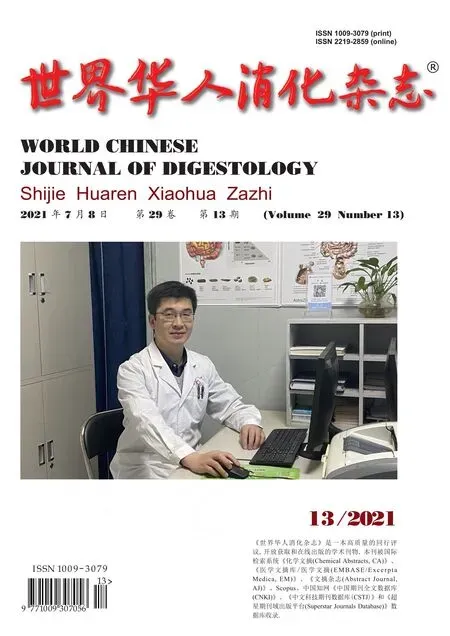药物性肝损伤发病机制及诊断标志物研究进展
2021-01-06杨晨茜姚冬梅
杨晨茜,姚冬梅
杨晨茜,姚冬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000
0 引言
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药、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所诱发的肝损伤[1].DILI作为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2],相关流行病学显示DILI占药物不良反应的10%-15%[3],近些年研究表明其发病率更高.冰岛的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冰岛年发病率每100000个案例中为19.1[4].法国DILI的年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有13.9例,住院率为12%,死亡率为6%.根据美国DILI网络的统计,抗生素为导致DILI最多的药物,约占DILI病例的46%[5].一项关于中国大陆普通人群的回顾性研究显示DILI的年发病率为23.80/100000,此结果高于西方国家.传统中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erbal and dietary supplements,HDS)和抗结核药是中国大陆导致DILI的主要原因[6].TCM是指在我国中医等传统民族医药学理论指导下生产和使用的各种草药和非草药类的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HDS一词来指代广泛的补品,包括维生素、矿物质、饮食元素、食品成分、天然草药、草药制剂以及用于补充饮食并可能诱发肝脏受伤的合成化合物[7].抗结核药物主要包括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8,9].
DILI的临床症状个体差异较明显,轻者可无明显临床表现,大多数患者表现为肝功能指标异常和不同程度的皮肤黏膜黄染、尿黄、食欲减退、乏力、恶心、呕吐等,严重时可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少数患者可有发热、皮疹、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等特异质反应.DILI依据R值R=(ALT实测值/ALT ULN)/(ALP实测值/ALP ULN)可分为:⑴肝细胞损伤型:ALT≥3×ULN,且R≥5;⑵胆汁淤积型:ALP≥2×ULN,且R≤2;⑶混合型:ALT≥3×ULN,ALP≥2×ULN,且2<R<5.基于病程分为急性DILI:酶活性升高持续≤6 mo.慢性DILI:DILI发病6 mo.后肝酶或胆红素未能恢复至发生前的基线水平,和/或有其他进展性肝病的症状或体征,如腹水、肝性脑病、门静脉高压、凝血功能异常等[1].
美国药物性肝损伤网络(DILIN)中强调了关于DILI几个目前正在进行的热点研究领域[10],多数工作集中在阐明DILI的病理生理及发病机制方面.本文就DILI的发病机制及诊断标志物的最近研究进展情况进行论述.
1 发病机制
DILI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迄今尚不十分明确.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与DILI发病机制相关的动物及细胞学等相关研究,目前在细胞毒性、线粒体失活、氧化应激、免疫机制、胆汁淤积、基因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11].大量研究证明发病机制涉及直接肝毒性、免疫反应、线粒体功能障碍、胆汁淤积和遗传易感性等多个方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DILI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1.1 直接肝毒性 目前,对于DILI直接肝毒性的研究比较明确的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APAP).一般如果在临床前研究中发现药物具有直接肝毒性则会被禁止进入临床,但APAP是例外.其在治疗剂量之内是安全的,一旦APAP超出治疗剂量则可能会导致肝损伤甚至急性肝衰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APAP的过量服用是导致急性肝衰竭的主要原因[12].药物进入机体后在肝脏中代谢需进行两步反应,分别为Ⅰ相、Ⅱ相反应.Ⅰ相反应通过将药物进行氧化、水解、还原,而后产生代谢产物.Ⅰ相反应中主要的代谢酶是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CYP)、CYP1A2、CYP2A6、CYP2D6及CYP2E1等,这些都是和DILI相关的关键性氧化酶[13].APAP在肝脏经肝微粒体酶 CYP2E1代谢产生N-乙酰-对苯醌亚胺(N-acetylene-P-Benzedrine mine,NAPQI),谷胱甘肽与之结合,在APAP过量的情况下会使NAPQI耗尽了体内储存的谷胱甘肽,几小时内则可引起氧化应激和广泛的肝细胞坏死.作为谷胱甘肽前体的N-乙酰半胱氨酸,其作用可促进谷胱甘肽的再生,是治疗APAP过量的主要方法[14,15].药物在体内经过Ⅰ相代谢反应后代谢为水溶性极低的化合物,此化合物作为Ⅱ相代谢反应的底物,该底物可以经葡萄糖醛酸化或者硫酸化代谢[16].Ⅱ相反应中的尿苷5-二磷酸葡糖醛酸基转移酶、磺基转移酶、谷胱甘肽S-转移酶等药物代谢酶的作用是促进药物排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基因在代谢酶的合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7].有研究表明[18],在编码涉及药物代谢物排泄的药物代谢酶和转运蛋白的基因中,其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与DILI的易感性增加有关[19].
1.2 免疫反应 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idiosyncratic DILI,IDILI)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发生常常与药物剂量无相关性,个体差异显著且临床表现多样化使其机制研究更加困难.近年来,有研究证实机体先天免疫系统参与了IDILI的发病过程,但具体机制尚有争议.主要假设是新抗原刺激巨噬细胞的Toll样受体,清道夫受体和甘露糖受体,从而刺激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并引起炎症损伤[20].当IDILI患者再次服用可能导致DILI的药物后,肝损伤迅速复发,此现象反映了适应性免疫可能参与了其过程.在某些条件下,肝脏中诱发免疫耐受的机制被破坏或发生损伤,便会产生自身免疫耐受丧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21].目前研究DILI发病机理的各种模型中为防止免疫失耐受的进展,Uetrecht-Pohl模型[22]采用了各种方法来减少对适应性免疫系统的调节,尽管该模型表明免疫耐受的丧失可能是IDILI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具体机制还不十分明确.
一直以来存在的“半抗原假说”也是阐述DILI发病的重要免疫学机制.药物进入机体后,药物或者药物的活性代谢产物与肝细胞内有特异性蛋白质结合形成蛋白半抗原.在正常情况下仅是半抗原不足以激活免疫反应,需要其他细胞或组织协助激活适应性免疫系统,因此提出“危险信号假说”,即在易感人群中,某些事件如感染和炎症导致危险信号的释放,从而激活先天免疫细胞[23].通常认为免疫应答的开始是需要通过诸如“危险相关的分子模式”来激活抗原提呈细胞后,被CD4+T细胞进行识别激活CD8+T细胞,进而促进了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肝损伤[24].基于药物代谢产物这一机制最近国外有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药物及药物代谢产物结构的DILI预测模型,但是此预测模型应用条件有限[25].
由某些药物引起的IDILI与人类特定的HLA基因型相关的事实,也表明IDILI由适应性免疫系统介导[26].一些不需要药物代谢酶作用的药物可直接或间接与HLA分子和T细胞受体结合,直接触发T细胞的激活和增殖导致肝损伤.临床中常用的抗生素氟氯西林引起的肝损伤被归为特异性肝损伤,因为DILI的发生取决于个体的药敏性、不可预测性和剂量依赖性.有报道HLA-B*5701基因阳性的患者接受氟氯西林治疗后有诱导进展为中度/重度药物的肝损伤的可能性[27].
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是在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反应中产生的,IFN-γ可能通过促进TNF-α等细胞因子的产生,促进肝细胞死亡和/或抑制肝细胞的增殖修复从而参与IDILI的发病.在基于人肝细胞与已知肝毒药物氟氯西林、阿莫西林和异烟肼的模型中观察到DILI上调了细胞因子,特别是IFN-γ和TNF-α.基于这些体外研究推测IFN-γ可能诱导TNF-α的形成导致一连串的细胞损伤,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同时结果表明,有可能是一种或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与药物直接协同作用而导致IDILI,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体内细胞因子与药物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28].
1.3 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 线粒体失活也是DILI中导致肝细胞坏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研究表明线粒体参与细胞死亡途径的调控,这种调控与膜通透性的转换有关.一些药物可导致细胞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MPT)的发生,从而使线粒体ATP的产生逐渐耗竭最后导致肝细胞坏死[29].临床前药物开发过程中,使用常规动物研究无法轻易检测到药物诱发的肝损伤.在一项确定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缺血对肝脏线粒体功能和下游毒理学反应的影响研究中,LPS诱导的短暂性缺血会破坏呼吸链复合物的活动而增加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尤其是在线粒体中,LPS显著提高了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开放的敏感性[30].有文章指出DILI的发病过程中氧化应激也参与其中,ROS是有氧代谢的副产物,在细胞信号传导和体内平衡中起作用.当机体内的ROS产生过多,氧化程度超出氧化物的清除,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失衡,从而引起氧化应激反应导致组织损伤.一些引起DILI的药物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增加ROS的积累进而破坏体内氧化还原稳态导致细胞成分受损进而引起细胞死亡[31,32].Goda及McEuen等学者的研究证实[33,34],药物亲脂性的增加与DILI有关.脂类药物在体内分布广泛,亲脂性药物更有可能形成有毒的反应性代谢物,此反应代谢物可以通过线粒体和随后的炎性免疫反应引起氧化应激,进而导致组织损伤.McEuen等的结果显示[34],药物亲脂性的程度与DILI风险之间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但两者的关联性较弱,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1.4 胆汁淤积 有研究表明胆汁淤积也是产生DILI的机制.肝脏可以将胆汁盐从血液转运到胆汁中,引起DILI的药物通过抑制胆汁盐输出蛋白降低胆汁酸外流致使胆汁淤积从而产生肝损伤[35].胆汁盐输出泵(bile salt export pumps,BSEP)是胆汁酸从肝细胞分泌到胆汁中这一过程的主要转运蛋白,对BSEP的抑制是胆汁淤积性DILI发生的已知危险因素.但是,单独的BSEP抑制不能很好地预测化合物引起DILI的作用,抑制其他代偿性胆汁酸外排转运蛋白如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ultidrug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MRP)可以提高DILI预测.多药耐药相关蛋白3(MRP3)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胆盐输出泵[36].Ali等学者[37]开发了一种针对胆汁淤积的预测性模型可以识别潜在的转运蛋白抑制剂,他们通过该模型应用三种MRP3抑制剂在细胞水平上证实了非达索米星、苏拉明和屈尼达酮对MRP3的抑制作用.
1.5 遗传易感性 HLA基因的特定等位基因与DILI有显著关联.研究已经证明HLADRB1*15:01与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DILI的风险增加有关.HLA-B*35:02等位基因与米诺环素DILI有关联[38,39].一项对照性研究表明[40],携带HLA-C*03:02等位基因的个体罹患甲基咪唑诱导的DILI的风险增加.抗真菌药特比萘芬致DILI患者最常见的表现为混合性或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在高加索人中证实了HLA-A*33:01与特比萘芬药物诱发的肝损伤之间有很强的遗传联系[41].据报道HLA-B*35:01是何首乌诱导的DILI(polygonum multiflorum-induced liver injury,PM-DILI)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最新的一项关于单核苷酸多态性和PM-DILI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性研究[42],招募了来自四家独立医院的382名参与者,其中包括73名PMDILI患者,118名其他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和191名健康对照者.结果显示HLA-A基因中的rs111686806,HLA-B基因中的rs1055348和HLA-DRB1基因中的rs202047044与PM-DILI相关,其中rs1055348特定于PM-DILI.作为HLA-B*35:01的标签,rs1055348可能成为PM-DILI的替代性预测生物标记.虽然宿主的遗传因素目前想要改变很难,但通过基因检测可以提前发现DILI的易感人群,减少和避免DILI的发生.
2 诊断标志物
2.1 传统标志物 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和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为检测肝损伤最常见血清生物标志物[43].然而,这些指标并不是DLLI的特异性指标.ALT和TBIL水平通常分别用于评估肝细胞的功能.血清ALT升高对肝细胞损伤高度敏感,如果伴有TBIL升高则对肝脏有很强的特异性,为评估DILI的可靠生物标志物.ALP升高通常表明胆汁淤积损害,孤立升高的GGT不足以作为肝损伤的标志物,因为它不仅仅提示肝脏的损害,GGT检测如果升高则需提供ALP升高源于肝脏的证据[44].在有关临床试验中使用这些生物标记物可能会使研究对象处于药物诱发肝损伤的风险中,或者导致对风险的过高估计,这可能会阻止安全药物的研发.此外,当小型试验的结果尚无定论时,越来越需要制药公司进行大型且昂贵的临床试验,以“捍卫”新药的安全性.现在正采用创新方法和一些新颖的生物标记物来最大化传统生化测试的价值[45].数据驱动的数学建模结合了传统生物标志物的释放和清除动力学,改进了它们在预测新药候选药物的肝脏安全风险方面的应用.国外开发了一款计算机模型DILIsym[46],开发该模型目的是更好地预测新候选药物的肝脏安全性.DILIsym模型利用连续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值以及凋亡与坏死的血清生物标志物,来估计由于总体肝功能丧失而导致的肝细胞损失百分比和总胆红素升高.临床试验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此方法以更精确地评估肝细胞损伤的程度及其功能影响,该方法有望在小规模的临床试验中更准确地定义DILI风险.
2.2 新型生物标志物 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为目前DILI的研究热点[47].新的生物标志物对于DILI的早期预测和诊断有重要价值,谷氨酸脱氢酶(glutamate dehydrogenase,GLDH)、苹果酸脱氢酶、对氧磷酶-1、嘌呤核苷磷酸化酶是最有潜力的能够反映早期DILI的新型血清学生物标志物[48,49].
目前研究最多的细胞因子生物标志物有细胞角蛋白18(cytokeratin 18,CK18)、高迁移率族蛋白(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protein,HMGB1)、细胞角蛋白18与全长细胞角蛋白18的血清比值、穿透素-3等[9,50].HMGB1是一种核蛋白,在大多数细胞坏死过程中会释放出来,可以作为一种损伤相关分子模式来激活天然免疫细胞[51].
DILI的其他潜在生物标志物包括免疫反应的标志物,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eceptor,MCSFR)是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上发现的集落刺激因子受体,集落刺激因子是一种控制巨噬细胞增殖、分化和功能的细胞因子.血液中MCSFR的水平可以反映先天免疫细胞的激活(如炎症),但其作为DILI的标记物仍有待进一步研究[52].
MicroRNA-122(miR-122)和GLDH都已被FDA批准作为肝脏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研究.基因组学的生物标志物miR-122为肝细胞特异性miRNA,在APAP过量摄入的患者血浆中数小时内可升高[53].肝脏中大约70%的miRNA含量是miR-122.尽管miR-122水平比ALT或AST水平对肝损伤更具特异性,但据报道,健康成年人的循环水平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差异和个体内变异[54,55].然而,尚不清楚这种变异与使用miRNA作为DILI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56].GLDH是一种线粒体蛋白,在一项对健康志愿者的大型研究中发现GLDH的个体间和个体内变异比miR-122低.
2.3 关于DILI预后预测的生物标记物 确定有关预测患者预后的生物标记物如肝功能衰竭或慢性DILI是目前关于DILI诊断标记物研究中学者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尽管国际标准化比率(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是预测肝功能衰竭的最佳单一生物标志物,但在最近的研究表明几种生物标志物如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CK18和MCSFR有望作为DILI死亡/移植的预后生物标志物.OPN在炎症细胞向肝脏的迁移和浸润中起作用,被认为是DILI的候选生物标志物,且在预测肝功能衰竭方面表现最好.与恢复的DILI患者相比,在发生肝功能衰竭的患者中观察到高水平的OPN[57].而在之前的观察肝功能衰竭与OPN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中显示,与康复患者相比死亡/接受移植的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血浆OPN水平降低.两项研究之间的差异可能与样本收集的时间有关[58].
目前尚无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DILI慢性化.然而,对DILI患者的大量分析表明与未进展为慢性DILI的患者相比,发生慢性DILI的患者在发病时ALP和TBIL水平升高[59].最近发表的一篇探讨DILI候选生物标志物在预测DILI慢性化作用的文章中,发现在DILI患者发病6个月后康复的患者和未恢复的患者之间候选生物标志物水平的无显著差异[45,57].
3 结论
总之,DILI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对于DILI发病机制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虽然在优化传统生物标记物的使用和新型生物标记物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对于DILI的诊断具有重大意义,但在临床应用中仍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