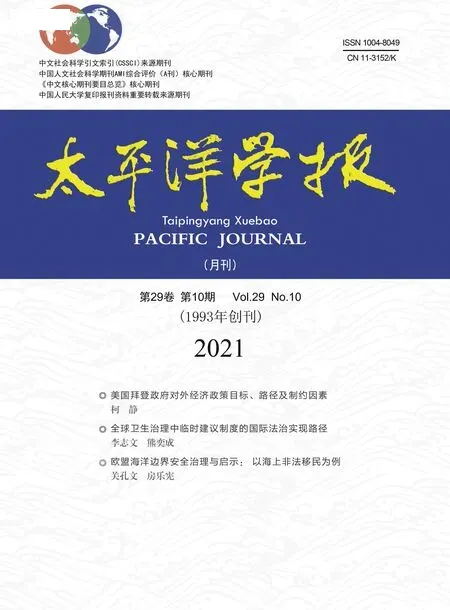全球卫生治理中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
2021-01-06李志文熊奕成
李志文 熊奕成
(1.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116026)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临时建议(temporary recommendations)制度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下简称《条例》)一系列改革中的一部分,它由各临时建议及其相关的措施、保障等规范体系和机制所构成。其中,临时建议是在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以下简称PHEIC)并构成特定风险时,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发布的,以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尽量减少对国际交通干扰”为目标的建议。自2005年《条例》修订以来,世卫组织共宣布了六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次事件中都发布了若干个临时建议,①在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发布了七次临时建议;在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中已经发布了二十八次临时建议;在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发布了八次临时建议;在寨卡疫情中发布了四次临时建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发布了五次临时建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已经发布了六次临时建议。数据统计自世卫组织官网,https://www.who.int/,访问时间:2021年7月4日。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条例》中,临时建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它凭借世卫组织的权威性而影响着缔约国,对缔约国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基于此种效力,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具有实现基础。目前在全球卫生治理框架下,该制度的法治程度却存在着明显不足。分析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路径的法理基础,研究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实现路径之应然与实然的差异,对填补现有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漏洞,更好地发挥临时建议制度的应有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效应。
一、全球卫生治理中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维度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临时建议制度,属于全球卫生治理秩序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际事务相类似,全球卫生治理同样探寻以“良法”和“善治”为核心要义,构建公正而有效的理想化国际卫生秩序。临时建议制度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软性规范定位,决定了其国际法治依赖于对该规范的良好遵守和制度设计的科学化。
1.1 临时建议制度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旨在通过凝聚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力量,共同应对影响超越单一国家领土范围的特定公共卫生问题的体系。①Peter S.Hill,“Understand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Global Public Health,Vol.6,No.6,2011,p.594.现行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格局复杂,由相互重叠而时有竞争的制度集群组成,涉及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等主体,这些主体通过不同的制度、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各种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中,②David P.Fidler,“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Working Paper of CF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May 2010,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pdf/2010/05/IIGG_WorkingPaper4_GlobalHealth.pdf,访问时间:2021年5月8日。共同推进国际卫生事务的有序化。临时建议制度是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下的制度安排,其软法规范性质与国际法治的高度切合性有效回应了国际卫生秩序构建的需求。
第一,临时建议制度可归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软法规范范畴。“软法”是一个与“硬法”相对的概念,通常将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而又有一定事实效力的行为规则称为软法规范。③曾文革、林婧:“论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我国的实施”,《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5期,第13页。软法规范需要同时具备“法”和“软”两方面的要素,前者指规范应当属于规则的范畴,后者则指规范缺失强制约束力。全球法律多元主义为临时建议制度纳入规则范畴提供了理论支撑,认为广义国际法不仅包括国家间制定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等传统渊源,还包括其他行为体制定的有事实效力的规范。④徐崇利:“跨政府组织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18-419页。作为应对PHEIC时采取的措施,临时建议通常由世卫组织总干事依据《条例》而草拟,并向突发事件委员会征求意见后发布。在法律地位上,世卫组织总干事是该机构的首席执政官,能够代表世卫组织作出符合《条例》规定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临时建议的发布者实际上是世卫组织,其以国家之外行为体的身份制定了有事实效力的规范,该规范属于一种广义上的规则,符合软法规范之“法”的要求。而从约束力角度,临时建议制度也切合软法规范之“软”的要求。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下存在两种不同治理形式的国际机制,一种是正式的治理机制,比如《条例》第一条规定的成员国向世卫组织报告严重疾病的义务,这种机制下的决策对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具有强制约束力;另一种是非正式的治理机制,该机制包含决议、标准、建议、指南等决策形式,⑤刘晓红:“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法学》,2020年第4期,第26页。主要运用软法规范,以牺牲强制约束力为代价,换取一定的时效性与灵活性。根据《条例》,临时建议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非强制约束性建议,属于典型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下的决策,其对缔约国并不发生强制的约束力,缔约国对临时建议也不具有强制采纳的义务。临时建议制度由此兼具了“法”和“软”两层要素,契合了软法规范的性质。
第二,临时建议制度可纳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国际法治领域。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国际法治,意味着将法治理念应用于全球卫生问题之应对,①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81页。要求各种参与者依据具有适当价值目标的规则行事。国际法治所包含的规则范畴并不局限于硬法,软法规范因其补充国际法和促进国际治理精神的作用而被纳入其中。②何志鹏:“逆全球化潮流与国际软法的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8-59页。软法规范虽然缺乏约束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能促进成本的降低,更有利于直接、快速的施行,③万霞:“试析软法在国际法中的勃兴”,《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134-135页。也更易于修改。临时建议制度作为软法规范,以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补充国际法的作用,覆盖硬法无法企及的领域。同时,临时建议的发布与修改,相较于冗长的国际硬法立法和修订,体现出软法规范所特有的节约时间成本的优势,进而实现对特定公共卫生问题的有效回应。而疾病的国际传播具有紧迫、时效性的特点,硬法规则无法及时为此类卫生问题提供法治基础,临时建议制度却能够凭借其高度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对疾病的国际传播作出快速的反应,并依据疾病的传播与发展情况实时进行调整,填补硬法无法发挥作用的空白领域。此外,临时建议制度还是一种蕴藏国际治理价值目标的规则,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以“软规制”的方式探索国际社会的理想行为模式。临时建议尽管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对其他行为体也缺乏硬性的控制机制,但因应于所蕴含的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内在理性,各国可能愿意对其遵行,并将其作为采取卫生措施的正当性支撑。
1.2 临时建议制度何以得到“良好遵守”
临时建议制度在国际法治层面中的“良好遵守”,要求各缔约国听取并遵从世卫组织所发布的临时建议,在临时建议的指导与安排下应对PHEIC。尽管临时建议制度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属于软法规范,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但源自于发布主体世卫组织在国家授予、道义、专业知识三方面的权威性而在缔约国中被不同程度的广泛接受,④[美]迈克尔·巴尼特、[美]玛莎·芬尼莫尔著,薄燕译:《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5页。并对全球卫生治理的未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外在体现就是缔约国对临时建议制度的“良好遵守”。
第一,临时建议制度“良好遵守”的国家授权性。根据比利时学者Jan Wouter提出的代理理论,国际组织职能的履行源自于国家的委托。⑤J.Wouters,P.De Ma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No.21,March 2009, https://www.peacepalacelibrary.nl/ebooks/files/336294018.pdf,访问时间:2021年5月8日。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公约《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方式,授予世卫组织行使该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二十二项与卫生有关职责的权力,而发布临时建议属于世卫组织得到各国授权的行为之一。前述权力的根本性来源是缔约国的共同委托行为,该行为代表了缔约国的集体意志。尽管在完成委托工作的过程中世卫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临时建议依然是委托工作成果的外化,本质上是听从委托人指挥而作出的行为,各国对临时建议之遵行是对其自身意愿的服从,发布与实施主体意志的趋同决定了“良好遵守”得以通过国家授权实现。
第二,临时建议制度“良好遵守”的道义性。《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一条阐释了世卫组织的宗旨为“使全世界人民达到卫生之最高可能水准”,这表明世卫组织在卫生决策上具有自主性,处于一种中立、公正和客观的立场,在全球公共卫生事务上能够对抗国家授权所带来的大国控制。而基于全球卫生治理之目的设置的临时建议制度,考量的是国际社会之共同利益,并非世卫组织或某几个缔约国的利益。此种道义上的权威性,使得临时建议即使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仍然对各国产生影响,并推动了临时建议制度的“良好遵守”。
第三,临时建议制度“良好遵守”的专业性。临时建议是由世卫组织总干事在征求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之后作出的。根据《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成员为总干事从专家名册和世卫组织其他专家咨询团中挑选的专家,这些专家因具备PHEIC的防控知识而得到各国的信任,并以一种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专业服务的身份存在。正是因为决策团队掌握了专业的卫生领域知识,临时建议才具有专业上的权威性,且外在表现为一种技术至上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政治性,使各缔约国更愿意接受。
1.3 临时建议制度何以科学化为“良法”
临时建议制度在国际法治层面的“良法”化,旨在提出契合国际法价值、反映全球卫生治理规律的临时建议,以达到科学化的标准,能够准确、有效地起到应对PHEIC的效果,且避免对其他领域造成危害和不利影响。
第一,临时建议的提出应最大程度地遵从卫生规律。临时建议制度科学化的最理想化状态是世卫组织所提出的临时建议完全贴合于卫生规律,从而以最具效率的方式应对PHEIC。然而,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有限性限制了这一理想化状态的实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自然规律与人类所制定的规范并非完全一致。①何雪锋:“人的理性为法律立‘法’——凯尔森的法律认识论及其现实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3页。临时建议由世卫组织根据对卫生规律的认识制定与发布,本质上依然属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范畴,这种认识与自然规律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导致临时建议出现错误而引发全球卫生治理上的不利后果。既然人类对卫生规律的认识难以做到完全准确,临时建议制度的科学化只能转而寻求规则设计路径,尽量保证临时建议最大程度地与卫生规律保持一致。
第二,临时建议的发布需要充分地考量各种价值。临时建议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领域的问题,在内容上还囊括了各缔约国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等应当采取的卫生措施”,涉及国际运输、国际贸易、人权等领域,需要充分考量这些领域的国际法价值。公共卫生措施对国际交通的干扰一般表现为拒绝或者延误交通工具、货物、集装箱、国际旅行者及其行李等的出境与入境。由于《条例》明确规定了临时建议需要“避免对国际交通不必要干扰”的要求,其包含的公共卫生措施对出入境的限制应当与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相符。临时建议还需要充分尊重人之尊严、自由。虽然公共卫生是限制人权的依据之一,②孙世彦:“疫情防控措施对人权的限制——基于国际人权标准的认识”,《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28页。但在不可避免地限制迁徙与人身自由、隐私权、集会自由、工作权等权利时,临时建议中应选择对人员创伤程度尽量较低的卫生措施。
第三,临时建议的适用应当尽量排除政治化。《条例》第四十三条将临时建议纳入缔约国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依据之一,使得其可能沦为部分国家用以谋求政治目的的工具。额外卫生措施,意味着缔约国能够采用世卫组织所统筹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外的措施,带有一定的自主性。世卫组织统筹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旨在保证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而缔约国所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其核心则是保障缔约国个体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产生关联。《条例》规定额外卫生措施合法性的考量因素包括“科学证据”“现有信息”以及世卫组织的“指导或建议”三个层次。在“科学证据”和“现有信息”皆不充分的情况下,临时建议会成为缔约国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决策基础。③张丽英:“新冠疫情下额外卫生措施的适用及其局限性研判”,《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第184页。过于严苛的临时建议可能会为不合理的额外卫生措施提供依据,成为变相实施贸易保护、歧视性行为等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临时建议的强度应当有所限制,需要兼顾各国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的平衡,尽量降低政治化的可能性。
二、软法理性视野下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实现之应然路径
临时建议制度是一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软法规范,其制度设计遵循了一般软法规范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理。着眼于临时建议制度的软法规范属性,探究其事前的科学性保障和事后的失当补救,是其实现国际法治的应然路径。
2.1 软法理性下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之结构
软法理性视角下,公共治理强调通过包含民主、反馈、区分等制度设计,完善软法规范的效力,为在《条例》框架下临时建议的事前制度构建提供了参考。通过适用强化软法规范效力的一般原则,形成三位一体的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制度结构。
第一,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国际软法效力完善的民主程序原则,为非强制的公共治理手段提供了以信息说明机制作为形式要件来保障治理的思想。软法制定中的民主化因素构成了软法有效实施的内在动力,①方世荣:“论公法领域中‘软法’实施的资源保障”,《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16页。出于此种民主化因素的必然要求,信息说明在通过软法进行公共治理时,属于必不可少的形式要件。与其他公共治理手段不同的是,为保障临时建议最大程度的遵从卫生规律,需要说明的信息不仅限于程序性事项,还包括实体性内容。基于临时建议制度的科学化考量,要求世卫组织公开临时建议的科学性来源,并接受缔约国、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等相关国际法主体的检视,进而从源头上保障临时建议的科学性。因此,临时建议发布的必要形式要件不仅包括有关目的、内容以及责任主体等程序事项的信息说明程序,还包括实体方面的科学性来源的公布说明程序。
第二,缔约国建议吸纳机制。非强制的公共治理中,接受对象的意见反馈与吸纳机制也是保障治理手段科学性的重要机制之一,软法的效力完善要求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②罗豪才、苗志江:“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法学杂志》,2011年第12期,第4页。临时建议的科学性保障机制同样也需要汲取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精华,将缔约国的意见和建议纳入临时建议作出前的考虑因素。当发生PHEIC时,相关缔约国直接受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威胁,该缔约国国内在疾病防控中会积累一定的经验,此种经验对于临时建议的科学性具有优化的意义。为此,需要在缔约国与世卫组织之间建立起对临时建议内容进行交流的畅通机制,以便能够有效地促进世卫组织发布的临时建议在吸纳缔约国的相关措施和建议后作出,保障其更具有科学性。
第三,建议对象范围的评估机制。临时建议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软法,体现出建议对象的多元性,存在着特定与不特定两个维度,其中,特定的软法规范针对特定的一个或多个对象作出,而不特定的软法规范则针对某一群体的全体作出。此种界分使临时建议制度能够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要求,覆盖的公共卫生治理层面更广泛、更精准。鉴于PHEIC的发生往往与特定缔约国有直接联系,且并非必然对所有缔约国的公共卫生都产生紧迫威胁。为此,世卫组织应当根据各缔约国受到公共卫生威胁的程度,以建议对象的特定性为分类标准,对建议对象的范围进行评估,充分考虑临时建议应当面向所有缔约国,还是仅需面向与PHEIC有直接联系的缔约国和其他受威胁较大的缔约国。针对不同建议对象发布临时建议时,世卫组织采取的具体措施应当有所区别。
2.2 软法理性下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之要素
软法理性指引下的公共治理应当包含补救制度。作为临时建议作出之后的事后机制,软法中的一般补救理论对临时建议失当时的补救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原则指引。
临时建议出现“失当”,表现为临时建议未遵从卫生规律或未充分考量各种价值,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失当”的认定,主要以临时建议提出后造成了危害后果为标准。软法理性为非强制治理手段的失当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指明了两种方向,分别构成了临时建议失当的两大情形:一是程序错误与实体错误导致了危害结果。对于软法理性下的公共治理,治理主体的错误行为引发不利后果时,对受害人都应当进行补救。而临时建议违反法定程序或其本身错误带来了危害结果,如因程序存在瑕疵或在实体层面对卫生规律认识不足,导致临时建议存在过轻的错误判断,致使缔约国疾病防控不力;或临时建议所规定的公共卫生措施未考虑贸易、人权等价值而过于严格,对缔约国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应当认定为构成了临时建议的“失当”。二是对正当预期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通过之前的行为使其他主体形成了某种确信,而之后的行为又违背了此种确信,导致其他主体承受了不利后果。正当预期与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在于禁止反言,其来源于软法救济的自然正义理念。①莫于川:“论行政指导的立法约束”,《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51页。全球卫生治理中临时建议制度的现有实践表明,针对缔约国的临时建议作出的同时,在同一份文件中还会包括世卫组织在PHEIC的应对中将采取的措施,对此种措施的说明可能会构成缔约国的正当预期或信赖。如临时建议文件中包含的内容使缔约国相信世卫组织会开展一定行动,但此种行动并未采取或采取不力,即可能构成对正当预期与信赖保护的违反,也应当认定为构成临时建议的“失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临时建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仅具有事实上的说服力,缔约国可以选择不遵守该建议,而当缔约国决定不遵守该建议时,即使该国发生了危害后果,并不能认定为临时建议的“失当”。
临时建议出现失当造成危害结果,即会产生相应的补偿与止损问题,软法治理理论为临时建议制度中的补救形式提供了传统与革新两方面的借鉴。传统理论认为,软法没有直接的法律效果,不能引发司法诉讼,只能通过国家补偿的方式进行补救。临时建议同样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因此,由世卫组织进行补偿将是临时建议失当后的唯一补救方式。鉴于世卫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卫生治理时,与一国政府在其本国领土范围内进行公共治理的权威性存在巨大差异,比照内国法中国家赔偿的方式要求世卫组织进行补偿,既不公正也不具有可行性。为此,可以考虑采用由世卫组织向受到危害的受害国提供公共卫生资源等人道主义援助方式,实现这一补救。革新的补救形式来自于日本软法补救理论中的“处分性扩大”解释论,它将不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软法规范行为纳入司法救济的框架之中,②闫尔宝:“司法解释放弃定义具体行政行为的策略检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第25页。通过判决取消、变更、确认无效等形式充实补救手段。依据此种方法,对于临时建议失当,可以通过增加确认临时建议失当、敦促修改临时建议、履行临时建议文件所产生的正当预期或信赖义务等方式进行止损。综合以上两种考虑,针对临时建议失当,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补救形式:对于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程序错误与实体错误,通过确认临时建议失当、敦促修改临时建议等方式止损,避免部分国家将失当的临时建议作为采取过度额外卫生措施的政治工具;对于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程序错误与实体错误,则通过向遭受危害结果的受害国提供公共卫生资源等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进行补救;对于违反正当预期或信赖义务的情形,通过及时履行临时建议文件所记载的行动等方式进行补救。
三、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之实然考量
全球卫生治理下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不仅需要考虑法律层面,也要顾及其他因素介入导致的事实层面与法律层面的不相称性的情形。现有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中,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之实然状态,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与应然状态既有契合,同时也存在偏差。
3.1 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之实践检视
现行临时建议制度建立在《条例》的框架之下,《条例》的规定构成了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的主要实践依据,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的实践检视由此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现有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考评。对科学性来源的说明,主要分为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实体角度是说明临时建议本身在科学上的可靠性,程序角度则是从作出临时建议的程序性事项上说明该建议的中立性和专业性。从国际实践看,目前实体角度的说明机制处于缺位状态。《条例》只规定临时建议的作出应当考虑科学原则、现有的科学证据与信息,但并未将实体角度的科学性来源之说明义务纳入保障机制。实践中临时建议也仅以单纯的建议形式作出,并不涉及对实体科学性的论证证明,实体科学性来源保障机制不足。而程序角度的说明机制相对完整,体现在临时建议由世卫组织总干事在咨询突发事件委员会意见后发布,而突发事件委员会组成的程序合法,是保障临时建议科学性的主要因素。突发事件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来自世卫组织下的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受《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的调整。该文件要求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成员不得以国际专家身份请求或接受其他国际法主体的任命,以尽量避免其他因素对科学性的影响;对于可能与专家身份具有利益冲突的各种情况,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应当进行透露。临时建议发布的国际实践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定,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中包含对此类程序性事项的说明,包括各委员和顾问对利益冲突透露义务的认知,以及对其不具有利益冲突的调查情况。
第二,现有缔约国建议吸纳机制考评。在《条例》的框架之下,缔约国建议的吸纳机制比较完善。《条例》将吸纳建议的缔约国范围限定于本国领土上发生相关卫生事件的缔约国,赋予相关缔约国参与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并向突发事件委员会陈述意见的权利,此种权利的行使不得影响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的按期召开。这种机制使得疾病防控的缔约国本土化经验得以被突发事件委员会吸收,为临时建议制度在PHEIC全球治理中的科学性提供了有效的事实支撑,同时又兼顾时效性要求,限缩了陈述意见的缔约国范围,避免因为缔约国数量的庞大性和背景的复杂性影响突发事件委员会对临时建议决策的效率。现有国际实践也基本遵循了该机制的规定,例如针对2019年突发新冠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根据《条例》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邀请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代表参与会议,以报告疾病防控状况和所采取公共措施情况的方式参与临时建议发布的程序。
第三,现有建议对象范围评估机制考评。《条例》中有关临时建议制度的具体规定暗含了临时建议对象的范围评估机制,即临时建议措施可针对遭遇PHEIC的缔约国或其他缔约国作出。该规定事实上将临时建议的对象分为遭遇PHEIC的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两种,两者在对象范围的特定性上有所差异,故世卫组织发布临时建议前需要先评估建议对象的范围。实践中,临时建议针对的对象也是多元的,以世卫组织就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中召集的突发事件委员会所作出的声明为例,除第一次会议未将COVID-19疫情宣布为PHEIC而没有发布临时建议之外,第二次会议的声明包含了对中国的临时建议、对所有国家的临时建议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临时建议;第三次及之后的会议声明则主要是针对所有缔约国的临时建议。①“世卫组织应对COVID-19疫情时间线”,世卫组织官网,2020年6月29日,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访问时间:2021年5月8日。由此可见,尽管现有实践并未严格按《条例》中有关对象范围的划分规定作出临时建议,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对象范围评估机制已经落实于全球卫生治理之中。
3.2 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之实践检视
《条例》中有关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基本上属于空白,不论是临时建议出现失当后的补救启动条件,还是临时建议失当后的补救形式,《条例》都没有涉及。在现有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中,临时建议失当造成的危害后果也不具有补偿或止损的途径。这种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的缺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临时建议的失当难以认定。临时建议失当补救以其欠缺科学性造成危害后果为前提,此种危害后果认定标准存在差异。虽然程序错误和对临时建议的正当预期或信赖的损害认定标准更加清晰,但从世卫组织应对PHEIC的历史来看,对《条例》中程序的违反,以及违背正当预期与信赖保护原则的情况较少,而实体错误所导致的危害结果认定,相对来说则存在更大的需求。一方面危害结果认定的时间和程度复杂,危害结果认定的标准难以确定;另一方面危害结果即使得以认定,危害结果与世卫组织实体错误间的因果关系依旧是巨大难题。世卫组织在应对PHEIC中的协调能力受到缔约国及时和准确通报的极大影响,①韩永红、梁佩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过度限制性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7期,第91页。危害结果的产生可能由当事国不配合世卫组织的行动,以及义务履行的不足所致,而非来自于世卫组织作出错误判断导致的实体错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临时建议的失当,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处于难以确定的窘境。
第二,临时建议失当的各补救形式不可行。对临时建议的补救,不论是传统观念下的人道主义援助,还是革新观念下的司法救济,在目前的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下都不具有可行性。世卫组织的司法豁免排除了司法救济手段。国际组织职能必要理论认为,为了防止国家通过司法方式干涉国际组织行使职能,各国会给予国际组织司法豁免权。②谢海霞:“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第25页。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具有专门的卫生领域的职能,这种职能排除了司法管辖。国际公约为世卫组织的司法豁免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权公约》的规定,世卫组织除特定情况表示放弃豁免权外,它能够豁免一切形式的法律诉讼。由此,针对临时建议失当补救的司法救济形式不具有存在的空间。此外,世卫组织通过细节与具体化的建议规避了其他形式补救手段。从世卫组织在历次PHEIC中发布的临时建议可以看出,临时建议往往具有较为笼统、保守的特征,这种抽象的特征使危害结果更难归因于临时建议。而对于PHEIC防控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细节化、具体化的措施建议,世卫组织往往并不以临时建议的形式作出,而是以专家报告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例如2020年6月5日世卫组织发布的《关于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使用口罩的建议》,详细地阐述了在COVID-19疫情期间使用口罩的注意事项,但它并不是临时建议,而属于专家报告出版物中的过渡性指导(Interim guidance)文件类别,是专家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对于专家小组委员会会议报告的结论与建议,按照《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的规定,世卫组织并不承担义务,这一规定排除了对细节、具体化建议的补救,使其他形式的补救手段也不具备正当性。
四、困境溯源下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再思考
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在应然与实然层面的不匹配,是法治治理理念与现有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冲突的结果。为此,剖析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困境的根本动因,将其放置于全球治理的视野之中,以探索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实现路径的远期规划。
4.1 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困境动因之分析
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困境之动因,外在层面聚焦于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失当补救机制的制度设计缺陷之缘起,内在层面则回归到现有国际卫生秩序下世卫组织权威性被稀释的现实状况。
第一,临时建议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与其载体文件性质不匹配。在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下的三个维度中,缔约国建议吸纳机制、建议对象范围评估机制的应然性与实然性贴合程度较高;但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方面,实体的科学性来源说明较为不足。从世卫组织在PHEIC中发布的各种文件来看,对于实体的科学性来源说明主要集中于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所发布的报告出版物之中,而临时建议中却往往并不包括该内容。究其原因,专家报告出版物虽然也是对缔约国进行指导的文件,但在性质上属于研究报告的范畴。由文件性质所决定,它对于实体科学性来源的论证比较充分。对比之下,临时建议主要在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的声明文件中作出,该声明文件作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一种官方文件,不宜占用大量篇幅进行科学性来源的论证。因此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困境的外在动因,实际上是临时建议作出的载体文件的性质与理想化的科学性来源说明机制之间有所冲突。
第二,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受世卫组织的制度局限性掣肘。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的应然性与实然性不相匹配,一方面归因于临时建议失当情形的难以认定,另一方面则是第三方介入的补救方式不具有采用的可行性。对于临时建议失当难以认定的问题,主要源于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等书面形式确定一个需要世卫组织承担责任的危害后果之标准,在多元化的国际卫生问题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都既不可行,也对世卫组织不利。全球卫生治理问题并非单纯的科学问题,临时建议的作出会影响到国际运输、国际贸易以及人权等方面。而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时,提出建议的主要来源依据是缔约国的通报,出于对卫生以外其他因素的考虑,缔约国可能选择不全面共享信息,①熊爱宗:“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70页。由此导致世卫组织非因自身原因出现误判。而补救的可行性缺失,主要来自于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得以排除司法救济,以及通过规范性文件排除义务以规避其他补救手段。这种对补救形式的排除和规避,实际上表明了世卫组织在面对PHEIC时采取的一种以专业判断为主导的处理模式,而单纯依靠专业判断作出的临时建议不应当带来义务,这也是《条例》排除其强制约束力的原因。除此之外,由于世卫组织可利用的资源不足,②刘铁娃:“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2期,第25页。故并未对其行为所导致的不利后果设立专项补救基金,各补救形式不具备经济上的基础。
第三,临时建议制度缺乏足够的遵行基础支撑。分析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机制困境和失当补救机制困境的动因,可以看出临时建议制度设置上的专业性与其作出主体的权威性之间发生了纠缠。世卫组织不仅属于专业性技术机构,还属于制定规范、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③汤蓓:“PHEIC机制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角色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45-48页。临时建议的作出既有以专业知识为主要依据的专业性质,又包含了对国际贸易、国际交通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侵扰等非纯粹的卫生专业知识因素,由此存在内在的专业层面与治理层面的冲突,形成了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了公共组织效率的缺失。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卫生合作的发源,由拥有国际经贸利益的工业化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主导,大国政治主导与经济利益的平衡成为全球卫生治理集体行动的主要阻碍,④刘蔡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审视与制度创新——以PHEIC为视角”,《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第143页。这种阻碍持续存在,甚至会导致部分大国对世卫组织的操纵。⑤晋继勇、郑鑫:“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互动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8期,第63-64页。由此便产生了国家“自利性”对世卫组织“公共性”的侵蚀,使得世卫组织在从事技术工作时,过度的政治考量会损害其作为卫生标准制定者的权威性和可信度,⑥Charles Clift,“Wha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Final Report from the Centre o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Working Group on Health Governance,Chatham House Report,May 2014.导致部分国家授予世卫组织权威性的意愿降低,组织本身的道义性也受到影响,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的“良好遵守”的首要和次要来源受到质疑。此外,世卫组织因其掌握的知识而树立的专业权威仅仅是一种推定,在临时建议发生谬误时,该权威性可能会发生动摇,进而影响临时建议制度的“良好遵守”。可见,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困境,本质上在于临时建议制度的“良好遵守”仅作为一种随时可能被打破的脆弱现实存在,既不能为“良法”提供理想的塑造环境,也不能保证各国的稳定遵行。
4.2 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实现路径远期论
为克服上述临时建议制度的局限和不足,需要从临时建议制度国际法治困境的根本动因入手破局,正视现有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之下临时建议制度的“良法”要素难以达到理想化的应然水平,聚焦长远期视野,推动世卫组织的权威性建设,加强“良好遵守”,营造临时建议制度的“良法”供养氛围,以国际合作推进更加完备的临时建议制度搭建。
第一,通过机构改革,带动临时建议科学性来源实体内容说明机制的完善。在世卫组织的机构改革中,正视临时建议制度的专业知识性和治理政策性混杂所带来的世卫组织权威不足问题,创设全新的首席科学家部门,由该部门专职负责收集PHEIC中作出临时建议的实体科学性来源。在临时建议科学性保障中,可以将世卫组织中负责治理的行政事务部门与专业科学部门的职能进行相对划分,由总干事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并发布包含临时建议的会议声明,而由新设的首席科学家部门以附件或其他文件的形式,公开说明作出临时建议的科学性来源实体部分内容。
第二,提升缔约国提供信息的动力,推动临时建议失当认定机制的建立。世卫组织做出临时建议的依据中,重要的一项是缔约国对疫情信息的提供。目前《条例》第六条规定了缔约国向世卫组织通报其本国领土内发生的、依据决策文件可能构成PHEIC的任何事件以及针对此类事件所采取各种卫生措施情况的通报义务,但对于这一义务违反的后果,现行《条例》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这一义务沦为实质上无约束力的规定。对此,以促进《条例》修订为契机,推动各国对权力的让渡,赋予世卫组织对未及时履行通报义务的缔约国采取措施的权力。虽然出于政治考量,这种措施不宜采取强制惩罚性手段,但世卫组织可以通过以获取国际资源等方式制约缔约国不履行义务行为,提升这一义务的约束力,促使缔约国更加积极地履行提供信息的义务,降低临时建议失当认定中非世卫组织因素带来的干扰。
第三,完善合作与投入机制,夯实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的物质支撑。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措施的缺失,源于目前世卫组织权威性不稳定、各补救手段都不具有可行性的窘境,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完善合作与投入机制,为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措施奠定政治与经济上的基础。一方面,促进启动全球性、区域性的卫生治理合作谈判,赋予世卫组织更高的国家授权权威性,为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措施提供更高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针对世卫组织融资困境导致补救资源的缺失、在经济领域限制了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措施实现等问题,通过重新商议严重限制世卫组织项目预算的评定会费“零增长原则”,以及整合其他全球卫生治理行为体资金等方式,①蔡洁、俞顺洪:“全球卫生治理重塑中的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60页。改善世卫组织的筹资机制,释放资金空间,设立世卫组织补救专项基金,为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措施的落实提供经济根基。
第四,推动《条例》修订,建立多元化的临时建议失当补救机制。在政治与经济基础皆具备的前提下,可以推动《条例》的修订,分别从世卫组织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建立临时建议失当的补救机制,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采用不同的补救形式。外部层面的补救形式宜采用传统理念,以世卫组织向受到失当临时建议不利影响的缔约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为主要形式。补偿的方式包括在其权限内为受到不利影响的缔约国增加国际资源获取的便利,以及使用补救专项基金等为缔约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内部层面的补救形式则采取革新理念,在司法机构无法介入时,在世卫组织的框架内专设纠错部门,通过确认临时建议失当,对失当临时建议进行问责等方式实现对临时建议失当的止损。
五、结 语
临时建议制度是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之下的一种软法规范,被纳入国际法治的领域。临时建议制度在国际法治维度中的“良好遵守”来源于国家授权、道义和专业赋予的权威性,而科学化的“良法”则需要克服人类对卫生规律认识的局限性,充分考虑国际交通、国际贸易以及人权等领域的价值,尽量排除政治化的影响。软法理性视角下,临时建议制度之应然构建可以适用软法规范中所体现的公共治理理念,检视现有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下的临时建议制度之实然性与理论分析下的应然性差异,针对临时建议制度在科学性保障机制和失当补救机制上不同程度的缺位和空白,以远期视野考量临时建议制度的国际法治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