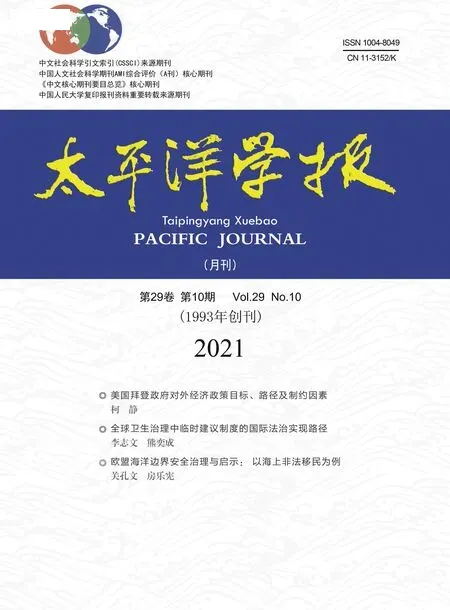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决定与国际法:应尽未尽的环保、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
2021-01-06那力
那 力
(1.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130012)
日本将其核污水排泄入海的决定,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疑虑与声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也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议论与批评。日本的决定及决策过程在许多方面是违反国际法,违背其应该担负的国际法义务的。本文从国际环境法的防止跨境环境损害问题入手,对日本的决定作一解析与评判。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证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一般国际法义务的存在,既有软法与条约义务,也有来自国际习惯法的义务;第二部分论述跨境环评义务;第三部分论述通知与协商义务;第四部分论述日本错在何处。四方面的论证,既论证各项义务的存在与内涵,也说明日本的决定没有适当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对于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国际社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其错误的决策,防止造成跨境环境损害。国际法学界应该聚焦于这个问题,建言献策,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了解日本所作所为的有害性、不合法性、非法性、违法性,给日本决策者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改弦更张,收回其实质与程序两方面都很不讲理、很不合国际法的决定。
在向海洋排放之前,核污水怎样储存与排放,是日本的内政,是其国内法问题。而一旦决定向海洋中排放,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跨境污染、域外污染、国际污染,成为跨境问题、国际问题。目前,决定尚未实施,我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皆有回旋的余地来扭转事态的恶性发展,救环境生态于水火,还人民以安全与公道。
一、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国际法义务与日本决定
1.1 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软法、条约义务与日本决定
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以防止国际环境与生态损害为宗旨与目的,国际法规定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同样,国际环境法以国家的基本环境权利与义务为骨架组织起来。在国际环境法中,国家的环境权利义务总结为三项: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责任,跨境环境损害与风险预防。①[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著,那力、王彦志、王小钢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环境法也可以说处理两个领域的问题,一是跨境环境损害问题;二是处理带有全球性、国际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等,以及全球公域的环境问题,如公海的环境问题、国际海底开发中的环境问题等。从历史和发展过程来看,跨境污染问题在先,如1938和1941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开了国际环境法的先河,孕育了现代国际环境法的诞生。而国际的、全球的环境问题是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发展势头迅猛,规模宏大,其背景与道理大家是有共识的。②崔盈:“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第41-44页。总之,规制、处理跨境环境问题,是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问题,要受到跨境环境污染的国际法的制约。
在跨境环境损害问题上,有两个论点得到了大力支持,可以看作是国际环境法的一般原则、根本原则,一是国家有义务不造成对他国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环境损害,防止、减少和控制域外污染及环境损害;二是国家有义务在减少环境风险和紧急事件中进行合作,其方式包括通知、协商、谈判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③同①,第99页。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其违背国际法之处,首先在于没有适当履行其防止跨境环境损害的国际法义务。
一国有责任使自己管辖与控制下的活动,不造成对他国和国家管辖控制以外区域环境的损害,简言之,不造成域外环境损害,是国际环境法得以产生与持续存在并发展壮大的基础。
(1)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及其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又称《斯德哥尔摩宣言》,标志着现代国际环境法的诞生。该宣言第21条中表述:国家有责任使其管辖控制下的活动,不造成对他国或国家管辖以外区域的环境损害。在这之前,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许损害他国环境,而只是涉及不得侵害他国的领土、财产、居民等。将环境因素引入国际关系中并且纳入国际法领域,成为国际法的规制对象与保护客体,这还是头一回。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可以说是其酝酿与前奏。由此,国际环境法得以成立,他国的环境,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环境(也称全球公域),二者统称域外环境,也不容损害。使域外环境遭到损害而听之任之,不采取防止、减轻、控制措施,是违反国际法的,因而国家是要负责的。这里的责任(respon⁃sibility),应该理解为义务(obligation),是相对于权利(right)而言,国家有国际法上的义务来防止造成对域外环境的损害。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国际环境法中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会议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支撑着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框架,还在于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再次高调宣示国家不得损害域外环境的原则。
《里约宣言》27条原则中,有几项条款特别适用于跨境环境损害问题。原则2规定国家要防止对他国及全球公域造成环境损害,原则17规定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原则18规定通报可能影响他国环境的紧急事件,原则19要求在从事可能对跨界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进行之前,进行事先通知及诚意协商。它们构成国家对跨境环境损害的一般国际法义务,即防止对他国和对全球公域造成环境损害的义务,以及通知和协商的合作义务。
以上文件皆属国际法中的软法。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国际环境法中,软法不软,其影响和发展前景不在硬法之下,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突出特点。
就国家与环境损害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这里,国际义务的承担者是国家,而造成域外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往往是企业,例如生产企业的排污,船舶的倾倒与泄露等。日本政府这次向海洋排污的决定,直接行为者是产生核污水的核电企业东京电力公司,该公司是日本管辖下的企业,日本政府负有国际法上的义务,防止、限制、减少、控制其管辖下的企业的排放对域外环境生态造成污染损害等。
(2)我们再从条约义务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决定。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要受到它所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制约。
首先,受到海洋法的制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设专章第12章来规定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表明海洋法极为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这在国际环境法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该公约也被誉为国际环境法中最大的一部法。海洋环境保护最本源的条款是第194条: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控制任何形式的环境污染与损害;第195条防止污染的区域转移;第196条防止引进技术与物种造成污染。
第194条和其后的各个有关规定,使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涉及各国的海洋环境,还将海洋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包括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等。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环境保护有重大意义,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污染海洋不再被视为默许的自由。第二个变化是船旗国与沿海国之间权利的平衡,指的是航行自由与沿海国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第三个变化是其重点不再放在环境损害的责任上面,而是主要放在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调整与合作。①[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著,那力、王彦志、王小钢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可见,保护海洋环境,并就此进行国际合作,是各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最根本的国际义务,这是国际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保护海洋环境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和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无论是在国际法中、国际环境法中,还是在海洋法中,都是重要内容,而且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我们评判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是否符合或者违反海洋法,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规定来对待,日本作为该公约的成员国,其决定没有适当履行其应该担负的防止损害海洋环境的国际法义务,特别是194~196条设定的义务。
其次,在《生物多样性公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简称《伦敦倾废公约》或《伦敦公约》),以及《核安全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属于国际核法的一系列条约中,也有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规定。日本作为以上条约的成员国,理应担负起其应该担负的条约义务,但是其决定实际上却没有适当履行其条约义务。我们审视一下与日本的决定直接相关的几个条约的有关规定。
一是《伦敦倾废公约》。在海上倾倒废物,尤其是在沿岸地区倾倒,对毗连国家或以渔业为主的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公共健康、环境安全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韩国渔民及渔业团体之所以对日本的决定反应非常强烈,是十分易于理解的。《伦敦倾废公约》的目标是避免或缩小给别国或海洋利用造成严重污染损害的风险,为此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进行事先影响评价,对海洋状况进行监测,记录所有的倾倒,向国际海事组织和其他各缔约方汇报情况等。这些规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196条、204~206条是一致的。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考虑保护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及有关程序,而单边地决定向海洋倾倒废物。
即使进行国际法允许的在公海的倾倒,倾倒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与有关条约的要求。而且,由于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的存在,在南极洲、亚太区域、非洲等地放射性物质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二是核能与环境问题中的有关国际协定。通过包括1994年《核安全公约》和1997年《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在内的与核能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以及国际习惯法的演化,将放射性废物倾倒在海洋中,或通过陆源渠道或空中方式排放到海洋环境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禁止。放射性物质进入公域环境中,就被认为是构成了应受到禁止的污染,而不考虑是否达到一定程度的重大伤害。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当放射性在某一特定水平之下时,需要一些证据来证明。
为确保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得到合理尊重起见,各国必须在发生严重的或可观察到的跨境风险的情况下通知和咨询其邻国。上述原则在诸如核设施引起的跨境风险问题上必须得到适用。
此处所说的情况与日本当前的决定和处境很是相关。即使日本决定了的排放是低放射性的,低到可以成为允许排放的例外,也必须履行必不可少的义务,经过必须经过的程序,包括进行环评,提交证据,通知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与其进行协商等等。
1.2 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国际习惯法与日本决定
在国际法院法庭的司法裁判中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中,有关跨境环境损害的法律形成、发展与编纂取得了重大进展。本部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论述与论证。
(1)国际法院对环境问题的判决与跨界环境损害
1995年以来,国际法院有一些重要的案例与环境问题有关①以下1、2、3案及对其的研究,均见[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著,那力、王彦志、王小钢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案例表,第11-26页。,包括:1.核试验案;2.“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案;3.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4.乌拉圭河纸浆厂案。
在案1中,新西兰请求国际法院命令法国在进行核试验前,应该依照国际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除非评价结果表明不会发生海洋环境污染,否则,这种试验就是非法的。这是对环评义务的肯定,也是对防止跨境环境损害义务的肯定。
在案2中,国际法院申明,国家在追求合法的军事目标的过程中进行必要性和比例性评估,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国家有义务保护自然资源免受武装冲突时期发生广泛的、长期的、严重的环境损害。国际法院又称:要求国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应该尊重其他国家或各国控制之外区域的环境,其为约束国家的一般义务。
在案3中,国际法院提及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当事方必须进行善意诚信的谈判。判决结果要求当事方在共同管理中进行合作,确立一个持续的环境保护与监督的办法。
案4为国际法院2010年的判决。在该判决中,国际法院对跨境污染问题中的公众参与、适用最佳可得技术等多个问题表明了意见与态度,跨界环评被称为事前救济,其作为国际法义务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此案对跨境问题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看到,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科孚海峡案、拉努湖仲裁案等国际法院与仲裁庭的裁决,都从不同角度给跨界环境损害提供了法律资源,有一定的影响。
(2)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后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国际常设仲裁庭、国际法院的有关判案
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以后,联合国海洋法法庭2011年就与国际海底开发活动相关的“担保国的责任与义务”发表了咨询意见①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States Sponsoring Persons and Entities with Respect in Activities in the Area,Advisory Opinions,ITLOSReports 2011,February 1,2011.,国际常设仲裁庭2013年就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两国共享的基申甘加河建水坝问题进行了国际仲裁②In the Matter of the Indus Waters Kishenganga Arbitration(Pakistan v.India),Final Award,PCA,December 20,2013.,2015年国际法院合并审理了“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以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道路”两案③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Rica v.Nicaragua),Judgement,ICJ,December 16,2015;“国际法院判决尼加拉瓜就其在与哥斯达黎加争议领土上进行的不法活动进行赔偿”,联合国新闻,2015年12月16日。。以上各案都涉及到对共享资源开发的预防和减轻重大环境影响的义务,以及开展环评的义务,同时也表明,国际裁判机构对环境问题更为积极主动。
(3)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跨境环境损害的工作
跨界环境损害的国际法编纂,是国际法委员会的一项工作,这一问题归属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主题,1996年产生了一个包括22个条款和评论的草案文本。
这个草案有三个要素:预防、合作、损害赔偿的严格责任。草案在性质上是有关法律的逐渐进展与发展,而非仅是法律的编纂。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一主题一分为二,将损害预防与损害责任分别处理,从此两个问题分道扬镳而并肩而立、而行。
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引人瞩目的版本,2006年《危险活动造成跨境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为目前的最新版本。④ILC,“Draft Principles on the Allocation of Loss in the Case of Transboundary Harm Arising out of Hazardous Activities”,UN,2006,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10_2006.pdf.该文本代表了在这个问题上习惯国际法以及国际法的进展与发展。该文件在编纂这个领域的现存国际法方面已具备充分的权威,是各国管理跨境风险的最低标准,它使《里约宣言》原则2得以落实。
该文本将“损害”(harm)定义为“对人员、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值得注意。处理损害问题,环境损害是排在人身、财产损害之后的。文本中,通知和协商同时适用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这样的规定反映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环境法对公众参与的重视。
该文本提出,确实需要进行跨境环评与相应的国际法,然而,环评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应该留给进行环评的国家的国内法。这与几年之后国际法院对纸浆厂案判决中的意见相一致。这正是跨境环评国际法的特点与特色,国际法在跨境环评上不适于也不能约束干预过多,过细,要尊重各国的主权与能力。留给国际法的,可能主要是制定原则与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委员会对跨界环境损害预防问题的编纂,特别是涉及对跨界环评问题的编纂,来源丰富,囊括了宣言等国际软法文件、国际条约的规定、国家实践、国际法院仲裁庭的判例等,加以融会贯通,总结提炼,提供了对相关领域法律的权威性解释。它的法理和法律基础是丰富而坚实的。现存的环境保护国际义务,包括进行跨界环评、通知、协商、监督、损害预防、控制污染,都在案文中得到了表达与体现。
总结起来,国际环境法的国际习惯法中不损害域外环境的义务,起源于“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经《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1条原则和《里约宣言》第2条原则的发展,后来在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使用和威胁的咨询意见”一案中,其国际习惯法地位被确认,在纸浆厂案中得到重申与强调。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系统化的编纂与发展,它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因此,日本向海排放的决定不仅受到条约法的约束,同时亦受到国际习惯法的制约。
二、跨境环评义务与日本决定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no remedy,no rights)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金句,将环评与跨境环评作为“事前救济”,将它与损害赔偿的事后救济相提并论,是2010年国际法院对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引人瞩目的名言名论,在国际环境法中有非常大的意义和影响。这一裁决使跨境环评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界对此非常关注。①国内国际法学者晚近的有关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刘惠荣、胡小明:“主权要素在BBNJ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期;戴羽西:《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构成之适当谨慎义务理论研究》,外交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邓华:“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国际法中的演进和实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刘恩媛:“论国家跨界环境损害的防治义务”,《法学论坛》,2015年第4期;何志鹏、高晨晨:“跨界环境损害的事前救济:国际司法实践研究”,《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2期;那力:“国际法院对纸浆厂案判决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兰花:“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评论与启示”,《世界环境》,2011年第2期;兰花:“跨界水资源利用的事先通知义务——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为视角”,《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边永民:“跨境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习惯法的建立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最近,在国际海洋法修改的讨论中,又一次聚焦于跨界环评问题,使讨论更为深入。
当下,应该敦促日本采取国际环境法中的预防措施,启动跨境环评,与有关国家和各利害攸关方及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充分协商,保证程序正义,确保决策透明合法。
2.1 跨境环评义务的一般性规定
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半个世纪以来各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中的重要发展成果。
环境影响评估最早出现在美国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中,其在历史上第一次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来管理对居民、社区和自然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对当代环境变化引起的科学关注和公众关切作出了法律制度的回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形式不同但实质相近的环评法律法规,由法律出场来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进行保护,预防污染与生态损害,是各国法律发展的重要历史现象。
跨境环境影响评估(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TEIA,以下简称为跨境环评)作为国内环评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语境下的延伸,被国际软法文件、国际条约所吸收采纳而成长发展起来。
国际软法文件中,对环评与跨境环评最初的明确规定是《里约宣言》第17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跨境环评有明确规定,其第206条规定:当国家有理由相信在其管辖或者控制范围内计划实施的活动可能引起对海洋的实质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的改变时,它们就应当切实地对这种活动对海洋环境存在的潜在的影响做出评估,并把结果汇报给有关国际组织。该公约第204、205条也与此有关。《伦敦倾废公约》的目标是避免或缩小给别国或海洋利用造成严重污染损害的风险,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在给予许可前进行事先影响评价,以便考虑倾倒对海洋利用和海洋资源的影响。②《伦敦公约》第4条,第5(1)条,第6条及附录3;《1996年议定书》第8(1)条、第9条及附录2“197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放射性废物建议B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1)条和《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8条,都对环境影响评估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两套自愿性指南补充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环境影响评估义务。一是《爱凯指南》(Akwé:Kon Guidelines),要求对拟定在圣地、原住民和地方性的社区历来居住或使用的土地和水域上进行或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开发项目,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二是《生物多样性内在影响评估自愿指南》。这两个指南的突出特色是重视当地居民的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使原住民和受影响的公众参与进来;确保他们的意见被纳入报告中,即使这些报告没有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在决策中也要考虑他们的意见。
下列文件也是关于跨境环评的重要国际法文件。
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影响评估目标及原则》(UNEP Goals and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是国际上最早规定环境影响评估目标和基本程序的国际文件。它强调各国之间的评估程序的协调,而不是统一规则。其中,原则4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估中最低应包含的内容,共有八项,是环评标准与步骤的雏形。原则7提出,作出某项拟议活动的许可决定之前,应与该项活动的利益攸关者进行协商,应允许政府机构、公众,相关领域专家和相关利益团体的成员对环评进行评论,这是对公众参与的早期规定。
1991年《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以下简称《埃斯波公约》)①请注意本文将context译为“背景”,而不是以往很多的译法“语境”,这一不确的翻译应该纠正。,由联合国经济贸易委员会1991年在埃斯波通过,1997年生效,经历了2014、2017年两次修订,现有成员46个,多为欧洲国家,向联合国成员开放。这是专门针对跨界环评的第一个国际公约,对公约成员国来说,跨界环评已经是一项条约义务。该公约是适用于跨境环境影响评估的最重要、最详尽的国际文件。其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的法律、行政或其他措施来实施公约的规定。附件1规定了22项可能造成重大跨界环境损害的活动列表,附件2列出了跨境环评的最低要素与内容。公约要求环评结论必须进入最终决策考虑,环评文件,有关评论,协商结果,都要进入决策及其文件。这种严格程度与高要求,是以往的任何有关文件所不具备的。
包含跨境环评内容的区域性条约,以及规定战略性跨境环评的条约亦在形成与发展中,其中包括1974年《北欧环境保护公约》、欧盟《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指令》、2003年《〈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战略环境评价议定书》(简称《基辅议定书》),《欧盟战略环境评价指令》(European SEA Directive 2001/42/EC)等。世界银行以及欧洲、亚洲、非洲开发银行,其支持的大部分开发项目定都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价。
2.2 跨境环评义务的国际习惯法
国际法院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几个判案,都肯定了跨境环评的国际义务的存在。国际习惯法对跨境环评的国际法义务确认的最近的权威话语,是国际法院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的第204段:“如果拟议的工业活动有可能在跨界背景下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共有资源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可以认为一般国际法要求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2011年,即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后一年,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就与国际海底开发活动相关的“担保国的责任和义务”发表了咨询意见,指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既是公约下的直接义务,也是习惯国际法下的一般义务。
跨境环评义务是建立在适当注意(due dili⁃gence)的国际法原则之上的,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很难说其履行了适当注意义务。此外,进行跨境环评,也是人们对一国及其政府的良好道德的期待,表明该国是善良、友好、睦邻、负责的。
无论从条约义务来看还是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来看,拟议中的活动可能引起相当的跨境损害时,国家有义务进行跨境环评。日本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毫无疑问是拟议的活动,而且必然会引起相当大的长期的环境损害,理所当然应该进行环评。而且环评应该在做出排放决定之前进行和完成,然后根据环评结果再进行决策,做出适当的决定。
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而且其直接的排放区域就是海洋,其承担的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环评义务是不容回避的。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看,1995年以来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裁判机构的一系列判决,都肯定了跨境环评义务的存在,到纸浆厂案,跨境环评已经确立为国际习惯法义务,并且在2011年被国际海洋法法庭再度确认。日本亦是《伦敦倾废公约》《核安全公约》的缔约国。
诸多国际文件,诸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影响评估目标及原则》《埃斯波公约》等,也表明跨境环评制度在成长,得人心,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大趋势,不能因为其尚未生效,或者某国不是其成员,而作相反的负面解释,来开脱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虽然其对某国不具有拘束力,但是其内容往往是与国际习惯法一致的,而且更具体,是重要的借鉴与参考,甚至是标准与规范。国际法院法官布兰达利(Bhandari)在2015年关于“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一案的判决中,发表法官独立意见时提出,可以用《埃斯波公约》作为跨境环评的一个基本标准。①“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Bhandari,”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Nicaragua v.Costa Ri⁃ca),Judgement,ICJ,December 16,2015,pp.10-11.
2.3 跨境环评的要素与标准
在启动跨境环评前,可能需要预评,来评估拟议的项目是否可能引起重大的环境损害。对于预计为轻微的,不严重的损害,则不需启动环评程序。对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害的活动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轻微的损害,而是会有广泛、重大、持续的环境影响,因此必须进行跨境环评,而不需要预判。
跨境环评的要素或标准,一般包括:
①筛选。
②确定评估范围。
③找寻替代措施(examination of alternatives):寻求是否有可以达到拟议的工程目的,但是对环境更为友好的方案。
④基准数据(baseline information):描述一个地区或环境可能受影响的要素,包括科技信息,比如生物体中的重金属浓度;可能也包括社科人文信息,比如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等。
⑤减轻环境影响措施与管理(mitigation and impact management)。减轻措施是为避免或减轻拟议活动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它可以有效地减缓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利影响。将缓解措施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估进程中,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实施,可以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其一般包括下列内容:对拟定活动及其目的的描述;考虑可替代方案及其影响方案;对可能受到影响的环境的描述;对影响程度的估计;描述减轻缓解措施;说明预测方法与基本假设;可能的知识差距和不确定性;监测与项目管理大纲;项目后分析;非技术性总结,如地图、表格等。
⑦监测与持续监测(monitoring and followup)。环境影响评估不仅需要在项目开始前进行评估,而且还要贯穿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项目结束后也应持续进行评估。国家有责任确保对其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影响的活动进行持续监测和项目后评估的义务。持续监测和跟踪分析被视为国家的通知和协商义务的组成部分。
简约概括起来,环评流程步骤一般包括:筛查,公告,协商,发布报告并向公众公开,审议报告/发布决策文件,监测和审查。环评要素、流程步骤虽然一般只是以附件、指南等形式存在,但实际上是跨界环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构成当事国的国际法义务的组成部分。
国际法中还有根据项目清单来启动环评的方式,列入名单的都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工程项目。例如,《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必须对附件一所列的22项可能造成重大不利的跨界影响的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Arhus Convention,即《奥尔胡斯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日本决定所涉及的事项,赫然列于名单中,包括第2项的“热能发电站和其他燃烧设施以及核电站和其他核反应堆”、第3项的“核燃料”和第19项的“废水处理厂”。
国际法院在对“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以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两案的合并审理中,就环评启动点考虑了三个因素:项目的性质、项目的规模和项目的背景。这概括的精炼也很切实。
总结起来,跨境环评是对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对另一国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环评在实践中是一个过程,在法律上是一种程序,其目的是求实,寻求的是某活动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真相。这种过程与程序与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实体义务紧密相连,各国一般会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就环评和跨界环评做出规定。环评的目的在于使决策者能够从环境角度做出活动或项目是否进行、怎样进行的决策,其可以防止减少一国拟议的活动对另一国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影响评估必须在项目开展之前实施,环评的结果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
各国对于可能对给他国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产生潜在影响的活动或开发项目,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这在国际法上已经建立起来。这是一种(相对于不作为义务的)作为义务(an obligation of conduct)①作者认为此应是“作为义务”,而不是目前许多人所译的“行动的义务”,而且这关乎对国际法义务的理解。。国家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可能对他国或海洋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损害的或者高风险的,拟议进行的活动,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还有通知受影响国家及与其协商的义务。
跨境环评,往往是在地理意义上的邻国之间进行,或者在河流的两岸或者上下游国家之间进行,相互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非常重要,只要双方都接受并且履行进行环评的国际法义务,具体步骤程序等完全可以双方协商而定,没有必要遵循一套国际统一甚至全球统一的规则。而且,这样的统一规则恐怕也很难制定出来,很难进而取得各国的同意而达成共识。然而,跨境环评、协商、谈判是必要的,也是国际法的要求,这一点不容否定。
环评是需要实事求是的,也是需要有透明度的。篡改数据,私下暗箱操作与交易,都是不符合环评的基本要求与道德的,当然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遗憾的是,日本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甚至在决定公布之后,都没有进行国际环境法要求的环评与跨境环评,没有出示任何环评报告昭告于其国人,昭告于邻国及利益攸关方,乃至昭告于天下。
三、通知、协商义务与日本的决定
国际法要求各国在预防、减少跨境环境损害与风险问题上进行合作,国家的通知义务与协商义务都是进行合作的具体体现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1 通知、协商义务的法律渊源
有一点需要指出,通知义务、协商义务往往是与不造成域外环境损害与进行跨境环评两项防止环境损害的实体性义务连在一起表述的,在国际软法文件中,多表现为前后文,如《里约宣言》的第2条、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在国际公约中,也往往如此。在国际法院仲裁庭的裁判中,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判词,往往是涵盖了上述保护环境、进行环评、通知与协商等四个条款中的几个或者是全部四个。因此,下文中的引述,与前文中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一般义务、开展跨境环评义务的引述有很大程度的重叠的地方。
(1)软法与国际公约
对通知与协商的国际法义务进行规定首先来源于国际软法。《斯德哥尔摩宣言》对此有规定。《里约宣言》原则18规定要通报可能影响他国环境的紧急事件,原则19要求对于可能产生重大不利跨境环境影响的活动,一国必须预先及时通知,提供相关信息给潜在受影响的国家,并且进行诚意协商。原则19是一个强有力的条款,它是跨境环境损害问题上关于通知与协商问题的最早的重要表述。
通知和协商义务,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气候变化《巴黎公约》等条约所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8条明确规定,当一国获知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害的情况时,应立即通知其认为可能受这种损害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该公约第210条的规定也与此相关。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环评作了三方面规定,其第三方面的规定为:就可能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活动进行通报、信息交流和协商。
《伦敦倾废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巴塞尔公约》《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有更为强有力的事先同意、事先评价及与国际组织协商的条款,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的力度更强。例如,《巴塞尔公约》规定的是事先知情、同意,要求过境国和进口国事先的、明示的、书面形式的同意表示,这是最严格的,也是同类案件中唯一的控制形式。其他的同类案件一般采用事先通知协商的方式。也就是说,事先通知和协商是必须进行的,是程序义务。然而,项目国的决策不受协商的结果或者无果的限制,这与知情同意有区别。事先通知不等于事先知情同意,协商未果不意味反对国有实质的否决权,不影响项目国的最终决策。
(2)与通知、协商义务相关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有越境风险的情况下,要履行事先通知和协商的义务,此为更广泛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在众多有关案例中,以下几个与通知、协商义务最为相关。
通知义务,在国际法中出现较早,当时并不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科孚海峡案雄辩地表明:一国有义务及时通知处于风险中的国家,以便后者能够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1957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拉努湖仲裁案,对跨境环境问题提供了多方面的规则与启示,此处集中讨论与通知和协商义务相关的内容。首先肯定的是,法国已经尽到了其在条约和习惯法下的善意进行咨询与协商的义务。法庭还肯定: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通过协商和相互让步的方式来加以协调。
无论是条约还是国家实践都表明,拉努湖仲裁案中所适用的基本原则已经扩展到了危险的或具有潜在危害的活动所带来的跨境风险管理上,其中包括在边境附近地区设置核设施,大陆架活动和倾倒、陆源活动等其他海洋污染源,长距离跨境大气污染以及工业事故。在这些情况下,双边、区域性或全球性条约都已经要求采取某种事先通知和协商措施。
处理跨境环境损害问题及环评的程序性要求也充分体现在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工程案中。此案裁决中要求当事方必须进行善意诚信的谈判。
国际法院在对“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以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两案的合并审理中申明,项目发起方为了实现它的防止跨境环境损害的义务,应当通知潜在受影响的国家,并就防止和减轻风险所需的适当措施,善意地与潜在的被影响的国家协商。从而,法院确认了项目发起方两项程序性义务,即通知与协商的义务。
(3)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条文将协商原则延伸到无论发生在何处的引起重大跨界风险的所有活动。对于核设施来说,问题在于跨境协商是否足够确保邻国和环境免受单方面决策的核风险的危害,要求和相关国际组织进行事前协商并获得事前同意。这个方案看起来比核活动的开展取决于邻国同意的方案更为可取,而且同时避免了现有法的过度单边主义。
3.2 通知、协商义务的法理
通知、协商义务是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程序性义务,是不损害域外环境原则(No-harm Principle)、损害预防原则(Prevention Principle)、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及国际合作原则的体现与发展,其概念与制度性安排体现了这些原则以及国际环境法所追求的理念与价值。
规定事先通知义务是基于损害预防的考虑。预防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内核与基本原则。在相当意义与程度上,国际环境法之所以建立、成立,就是要防止环境与生态损害的发生;一旦发生,就应该采取措施、办法,尽量减少、控制损害。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与日益严重、复杂,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加入国际法体系,又出现了风险预防原则,即有环境损害的可能性,但是又不能确定其必然性,其为一种风险,而不是能够确定的环境损害。对此种情况,也要采取风险预防原则。
无论是施行损害预防原则还是施行风险预防原则,都需要在损害发生前预先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他国、利益攸关方。这是损害预防与风险预防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开展国际合作的起码要求,因此,它被广泛规定在几乎所有的与国际环境法有关的条约中,也体现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判例中。它在国际法、国际环境法中的既定地位是坚实的,难以动摇的。
预防原则源于恪尽职守、合理注意义务(对due diligence的不同译法)。各国有义务在知悉的情况下,对本国境内可能发生的任何足以侵犯他国利益与权利的行为、活动加以控制。各国应该以各种可能手段,避免、减少损害,而事先通知、协商,以及上文论述过的进行跨境环评,这都是必要的、得到国际法确认的必须采取的措施。
事先通知、协商和谈判都必须在信息足够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环境监督与事先环评是与通知、协商义务紧紧链接在一起的,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足够信息而进行协商的要求,在国际法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支持。通知和协商是贯穿整个处理域外环境损害的全过程,持续监测和跟踪分析被视为国家的通知和协商义务的组成部分。
在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条约和国际实践中,通知和协商同时适用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这样的规定反映了国际环境法对公众参与的重视。环保事务与环保法律重视公众参与,是由环保的实质与环保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跨境环境损害问题上,公众参与还没有成为必需因素,这一点可以参考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然而,公众参与是有利于环境生态保护,也是发展趋势。日本的决定,没有起码的公众参与,连与排核污水休戚相关的本国渔民都没有问一问他们的意见,更不要说顾及韩国渔民的利益与感受了。
协商义务是一个程序性义务,但是它也是一个实质性的义务,而非形式主义的东西,不是走走过场就可以交待了结完事了。在处理跨境环境损害问题中,包括在跨境环评问题上,通知与协商义务特别重要,其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国际合作、友好睦邻、诚意协商是当代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不但不削弱国家主权及其原则,而且与国家主权及主权原则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因为它体现的是对他国主权的尊重。
总之,在有越境风险的情况下,要履行通知和事先协商的义务。为确保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得到合理尊重起见,各国必须在发生严重的或可观察到的跨境风险的情况下通知和咨询其邻国,这一原则是拉努湖仲裁案逻辑上的延伸。
各国需要通过一个影响评估、通知、协商和谈判的体系来进行合作,以避免对邻国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这个观点在国际司法实践、国际机构的宣言、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和认同,也得到了国家实践的支持。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受影响受害的利益攸关方起码包括韩国、中国等海上邻国及广大海域,长远看来影响的国家更多,波及的区域更广。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谈判可能是不适当的,因此人们修订了这个基本原则,以便能够通过一些代表国际社会利益的机构来通知和进行协商。日本的情况可能是符合上述情况,这可能是它没有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与利益攸关方协商,而直接与国际核能组织联络的原因。即使如此,日本的决定也与善意履行其各项国际法义务相去甚远,特别是在跨境环评问题上,在履行通知与协商等程序性义务方面,显然没有尽职尽责,更谈不上满足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对国家“恪尽职守”(due diligence)的要求。而且,日本的这个决定,缺乏起码的透明度,这也是令人诟病,让人指责,引起抗议之处。
四、日本政府的决定错在何处,欲往何方
日本政府的决定之所以是错误的而必须撤回,从实质来说,是向海排放必然会造成广泛长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违背了其防止域外环境损害的国际义务;从程序来说,日本没有适当履行跨境环评义务,通知与协商义务。
据披露出来的消息,日本政府在作出决定时,曾考虑是否批地给东京电力公司,使其能建造更多储藏罐来容纳还会增加的污水。其中一官员说,如果批准的话,还要涉及到关于用地的地方法规问题,不如不批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了。此言差矣。对日本政府来说,不造成域外环境污染是一种国际法义务,如果二者有冲突的话,日本中央政府有责任作出协调,确保其防止污染域外环境的国际义务的履行。
日本产业经济省就核污水处理问题进行过讨论,提出包括蒸发释放、电解排放,稀释入海、地下掩埋以及注入地层等五种处置方案。其中,日本政府决定的稀释入海方案最为经济,也最为便捷,但是在防止、减少环境污染效果上却不是最佳的。
在跨境环评中,就是要评判并找出是否有比现有方案更合理的更佳方案,称为替代方案,其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考虑与必需环节,从程序上来说非常必要,从实质上看,关系到环境法的根本目的——保护环境,防患于未然。
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出现的使用“最佳可得技术”(best technique available),可被视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避免和减少环境损害,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新标准。希望日本在选择核污水处理的决策中,切实找寻对保护环境与公共健康的最佳可得方法,而不是像目前这样行事。
日本的决定,并没有从保护环境生态、保护人民健康的角度出发,穷尽救济方法,找寻最佳方案,这是令人非常愤慨的,也必将在历史上给日本留下耻辱的一笔。日本政府拿千百万人民的健康与福祉当儿戏,置环境生态安全于不顾,而只打自私自利的小算盘的态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与讨伐。
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在环境法中也是如此。我们以这一原理为关照,从程序角度检视日本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合法还是违法。
(1)环评时间。环评必须在项目批准之前完成,决定应该视环评结果而定,决策应该建立在环评的基础之上。日本政府与此背道而驰,根本没有进行环评,更谈不上进行跨境环评了。
(2)全面如实公开相关信息。环评要求全面公开相关信息,拿出描述一个地区或环境可能受影响的要素,称为基准数据,包括科技信息,也包括社科人文信息,此乃环评报告的组成部分。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进行环评,至今没有拿出任何意义上的环评报告,而是妄言其排放符合国际标准,不会造成污染。这样的弥天大谎,日本政府难道还指望会取信于天下人吗?而且,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处理福岛核事故有多次篡改数据、隐瞒不报的劣迹,公布的数据不可信。近期,日本媒体屡屡爆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发生放射性泄露的新闻,这不能不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3)减轻环境影响措施与管理。这是为避免或减轻拟议活动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可以有效地减缓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利影响。在日本政府的决定中,看不到什么有效的缓解措施,只看到稀释二字,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任何稀释污染物终究是要全部排入海洋,造成污染的。
(4)监测与持续监测。环境影响评估不仅需要在项目开始前进行和完成,而且还要贯穿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项目结束后也应持续进行评估。国家有责任确保对其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影响的活动进行持续监测和项目后评估的义务,而日本至今没有拿出核查与监督安排。特别是日方声称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安全无害,但是缺乏可核查的安排。
(5)找寻替代措施。日方只从经济成本出发决定向海排放,未考虑排放对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当然没有寻求是否有可以达到拟议工程的目的、但是对环境更为友好的方案,应该使用最佳可得技术。
(6)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协商。日方迄今未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迄今也未认真回应各方合理关切,更谈不上与更广泛地域的利益相关国家诸如环太平洋各国进行协商了。此乃日本未尽国际环境法要求的通知与协商义务。
(7)公众参与。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进行跨境环评,连国内环评也没有进行。其决定侵犯了大量日本本国渔民的权益,人们极为愤怒,游行示威连连不断。环境事务尤其需要公众参与,日本政府对待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与民众进行沟通,更谈不上有程序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8)国外公众参与。在可能发生跨境环境损害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境外民众的公众参与。在最近十年内的有关案例中,例如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项目发起方的对方国受影响的民众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此问题提到了国际法院的审理与判决中,被承认为“或多或少地有公众参与”,尽管程度不深。这是国际法院裁判对跨境环评中公众参与的肯定,当然也表达了对此不能要求过高。反观日本,其排海决定对其海上近邻韩国渔业渔民负面影响极大,他们是潜在的受害者。可是,日本政府罔顾韩国渔民的强烈反应,没有给他们任何发声表达参与的机会。
据报道,最近日本又拿出了另外一个方案,欲将核污水通过挖排水沟的方法引入海底,有人指出此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规避伦敦倾倒公约的适用,而非日本良心发现。这种方法造成的环境与公共健康危害并未减轻。日本当局还是应该从保护环境出发,切实履行自己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把核污水问题处理得当,而不是玩弄些自欺欺人,损人也未必利己的把戏。
结 语
国际法要求各国采取充分的措施来控制和管理它们领土内的或是它们管辖下的那些可能导致严重的全球环境污染或是越境危害的污染源,这一点无须更多质疑。这是一种防止危害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在危害事件发生后进行补偿的一个基础。对于这样一种防止性义务的支持,特别体现在斯德哥尔摩宣言、里约宣言、广泛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条约以及一些仲裁和司法的裁决之中。尤其是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对国际环境法具有重大意义,它肯定了事先通知协商义务与跨境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对国际环境法的规则的形成和国际实践提供了规制与指引,对未来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与国际司法有影响。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质疑与反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进行适当的环评与跨境环评、未全面公开相关信息、未拿出可监督核查安排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是违背其应该担当的国际法义务的,也是缺乏良知与诚信的。
核污水处置事关重大,必须慎之又慎,不容有失,日方绝不可以将核污水一排了之。日本政府首先应该正面回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和关切,在同各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协商并达成共识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我们强烈敦促日方重新审视该问题,撤销错误决定,回到切实履行其应该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的正道上来。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会走向何方?现有的国际法能起什么作用?多少人正拭目以待。不是一般的围观,因为事关重大,也因为对相关法律及其能否执行抱持疑虑。希望国际法能够惩恶扬善,改变日本的错误决定,还环境清洁安全,给人们带来福祉,而不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