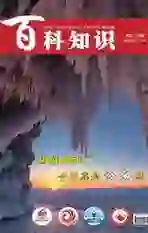零下40℃寻觅猫头鹰
2021-01-04保冬妮
保冬妮
冬季的乌尔其汉国家森林公园,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40℃。那可不是我们在城市里逛的人工景致的公园,而是古树参天、野生动物出没的原始森林。这处森林公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乌尔其汉镇境内,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南北长约32千米,东西宽约13千米,总面积近370平方千米。冬季这里没有游人,只有少部分的林业工人巡逻。道路已经被大雪掩埋,不了解森林每一条道路的人,只会迷失在森林深处。我在一年中最冷的1月去看猫头鹰,冷到什么程度?把保温杯里的热水洒过头顶,一瞬间就会变成冰花洒下,就这么冷!
雪中去看猫头鹰,是我好久的一个心愿。猫头鹰并不是一种猛禽,而是鸮形目猛禽的统称,有超过130种呢。它们是夜行性食肉动物,因面盘似猫而被称为猫头鹰,有的还有耳羽簇。所有的猫头鹰都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这也是我想记录它们的原因。
抵达海拉尔的东山机场后,事先联系好的鸟导张老师接上了我们。这位曾经的乌尔其汉森林猎人,现在已经是一名动物守护者。他在乌尔其汉生活了一辈子,知道林海雪原里每一棵树上有什么猛禽、什么鸡,也知道每一片草地上跳跃着什么鹀、什么雀。
海拉尔是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区,东部、南部与鄂温克族自治旗接壤,西部、北部和陈巴尔虎旗毗邻,距离中俄边界仅有110千米,距离中蒙边界160千米。我们要去的乌尔其汉距离海拉尔150千米,比去中俄边界还远些。
早上7点我们就开车上路了,没一个小时就变天了。风雪越来越大,不仅四周的景色全部陷在了白色雪雾之中,而且风吹得越野车直打飘,如果不是有经验的司机,在这样白毛风的天气里上路,没一会儿就得翻车。
我们先是到达了陈巴尔虎旗哈达图牧场。哈达图牧场靠近中俄边境,宽广的草原视野开阔,但是由于风太大,小鸟都躲进了草中,猛禽也似乎从日常出没的地方消失了。张老师说:“注意两边的建筑,纵纹腹小鸮就在这附近,情况很稳定,注意观察和发现。”我的眼睛扫过每一幢房屋,连纵纹腹小鸮的影子也看不到。我又向犄角旮旯看去,砖缝、墙缝也不放过,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有经验的张老师用望远镜一看,报告说:“屋顶侧面的铁架子上有红隼。”
红隼是猛禽里身材比较小的,雄鸟头为灰蓝色,背和翅上覆羽是砖红色的,眼睛下有一条垂直向下的黑色口角髭纹。红隼的下体、下颏、喉部都是白色或棕白色的。背部的羽毛有黑色和棕褐色的斑点。红隼大多单个活动,猎食的时候常在高空翱翔,捕食大型昆虫和小鸟以及小型的哺乳动物,在我国南北方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很快,纵纹腹小鸮也出现在牧场仓库的屋顶上。这是一个可以萌翻众人的毛绒绒的小猫头鹰,体长一般只有23厘米。别看人家袖珍,可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纵纹腹小鸮在我国分布也很广泛,它们喜欢低矮的灌木、丛林、丘陵、农田和荒漠,一身斑驳的羽毛很适合隐蔽。纵纹腹小鸮浑身上下全是沙褐色的,背羽上带白点,像是落在身上一片片大雪花,前胸是白色的,有沙褐色的纵纹排列,柠檬色的喙和眼睛非常卡通。纵纹腹小鸮没有耳羽簇,显得像个小秃瓢。作为留鸟,它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点,很少改变。
纵纹腹小鸮是一个善跑的“运动员”,别的猛禽都是在飞行中捕食猎物,纵纹腹小鸮竟然独特地用奔跑的方式追赶猎物。只要不受惊,它可以在原地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几小时,偶尔睁开双眼或者一只眼睛看看周围,有时又会神经质地点头和转头,这样的表情太惹人喜爱了。
风雪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我们还是继续开车上路了,去寻觅雪鸮—白色猫头鹰,它可是我们此行的目标物种。雪鸮是鸮形目鸱鸮科雕鸮属的一种大型猛禽,它们每年11月从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飞到哈达图牧场附近,第二年3月就飞回去了。
远远望过去,极为开阔的草地上有大飞过。这种鹰科属的猛禽浑身是褐色的纵纹,头顶和后颈都是白色的。也许高空的风实在是太大了,大仓皇地钻进草里不出来了。远处的毛脚落到地面,被不知道谁家的狗撵得低飞起来。它们自带“毛裤”,因腿上有厚实丰满的羽毛而得名。
走到雪鸮的领地,忽然发现牧民们拉的分界栏杆上,端坐着一只雪白的雪鸮,它几乎和雪原融为一体。也许距离遥远的缘故,本应是大型猛禽、足有59厘米高的雪鸮看上去显得小巧可爱。雪鸮属于颜值很高的猫头鹰,它浑身全白有淡色的横斑,头又小又圆,也是没有耳羽簇,光秃秃的脑袋显得圆润光滑。可惜的是,由于风雪大、距离远,没有办法看到雪鸮金黄色的虹膜,更看不清楚它暗色的横纵纹。雪鸮飞到了草地上,白茫茫一片的草原隐蔽了它绝美的身影,瞬间让它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小棉花团儿。没有找到食物的雪鸮忙着去寻觅小鼠去了,我们只好开车走进了风雪之中。

很快,我看到蒼茫的雪野中,一只金黄色的小狐狸在远处观察我们。这是一只沙狐,沙狐比赤狐略小,身材优雅,脸短吻尖,一双大耳朵尖且耳基宽。它们生活在亚洲北部的干旱草原,夏季是淡红色的,冬季背部是浅红褐色的,底色是银色的。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沙狐被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在白色的原野的映衬下,眼前的沙狐显得活泼顽皮,打哈欠的表情更是如同微笑。车停下来,沙狐竟然慢慢向车跑过来。张老师一眼认出了它:“我以前路过此地,给过它食物,它认识我。”果然,沙狐不太怕我们的越野车,它跑过来,从雪地里刨出一只自己储藏的冰鲜老鼠,当着我们的面吃了起来,那表情好像在说:“这次我有食物。”
两辆车里一阵噼噼啪啪的按快门的声音,大家对沙狐的好感与时俱增,纷纷抛下面包和食物在雪地上,沙狐迅速地刨了个雪坑,把这些食物统统埋藏在大雪之下。它利用天然大冰箱,把吃不完的食物统统冷冻起来,留待自己下一顿再刨出来吃,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小家伙!

当晚,我们抵达了乌尔其汉镇。接下来的3天,都将在乌尔其汉镇附近的森林里寻觅和观察鸟类与兽类。乌尔其汉的地名来源于鄂伦春语,意思就是“树林”。这里有各种植被500多种,以兴安落叶松、白桦树和山杨树为主,茂密地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大雁河和库都尔河流淌过小镇的东西两侧,形成了寒温带大陆性季风半湿润森林气候。这里年平均气温仅有2.6°C,夏天最高34.5°C,冬天最低零下47.6°C。冬天来乌尔其汉看雪,算是来对了。第一次体验零下40°C在户外拍摄野生动物,也真是爽到家了。
从乌尔其汉镇到中国首个高纬度地区森林湿地—兴安里湿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的这段公路叫乌兴干线,桥龙支线、越岭线是乌尔其汉森林里的支线公路,这些地方是狍子、猛禽和林鸟频繁出现的地方。寻找和拍摄野生动物就是在这一带。
张老师带着我们就这样穿越在零下40℃的林海雪原里,赶上降温,林地里的白桦树全是冰清玉洁的树挂,林子里无风的时候,茫茫林海安静得听不见一点动静;若有声音,除了树枝禁不住雪压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叹息声,就是小鸟叽叽喳喳欢悦的聊天声和啄木鸟咔咔啄木头的声音。狍子是非常容易受惊的动物,也是非常有好奇心的动物,如果不惊吓它们,它们会睁着大眼睛好奇地张望你;一旦有一点动静,它们就惶然狂奔,白色的臀部在清晨的树林里特别显眼。
林子里生病有虫的树真不少,有的病树已经被三趾啄木鸟、小斑啄木鸟啄得彻头彻尾地变成一棵没有了皮的裸树。失去树皮的树木,露出铁锈红的枝干,在白桦树林里异常显眼。这样的树一般无法成活,只能等待变成朽木。但是,林子里也不能没有朽木,高大而又光秃秃的死树,是猫头鹰最喜欢栖息的地方,也是一些鸟儿喜欢钻洞筑巢的地方,因为没有树叶遮挡,便于放眼四野,观察情况。

乌尔其汉国家森林公园的原始林地里有众多的小鸟:雪雀、红腹灰雀、褐头山雀、长尾山雀、三趾啄木鸟、粉红腹岭雀、长尾雀、北朱雀、白腰朱顶雀、黑头、褐头山雀等都相当漂亮,它们不仅吃得饱,而且穿得暖,个个像个小毛线团,而且羽毛的颜色十分鲜艳。
北朱雀在我国是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二级保护动物,它们仅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西部、贝加尔湖地区以及蒙古、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它是无危的,但是由于它羽毛华丽、歌声动听,一直作为笼养鸟,野生北朱雀并不是容易看到的鸟类。我面前的这只雄性北朱雀,简直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小毛线球,我走一步停三分钟,一点点猫着腰接近,当距离3米左右时,把它拍得羽毛毕现。这时雌鸟也飞过来了,雌鸟不像雄鸟那样体羽大都为粉红色,而是羽缘粉红色,有黑褐色羽干纹,背上淡黄色和淡粉红色相杂,前胸是橘红色,下体是棕白色。北朱雀羽色艳丽,气质活泼而天真,在野外特别醒目。我一向认为观赏它们的最佳场合就是在大自然中,任何笼养野生鸟都是违法网捕、牺牲众多鸟儿的生命换来的。独享不如众享,只有杜绝野生动物的买卖,才有大自然的美丽。

北朱雀双双飞走的方向,是一片灌木草地,中午的太阳照在上面,点燃了萧瑟的灌木丛,温暖的金色把每一根枯草都染得异常温暖。秋天结的草籽挂在枝头,引来了一群足有十几只的白腰朱顶雀。这些金翅雀属类的小鸟无论雌雄,脑门儿上都有一顆红点儿,雄性的前胸有红色羽毛,背部黑色的羽干纹与枯草黄的羽毛相映成趣,而雌性的后背与雄鸟大致相同,只是前胸和下身全部是奶白色的。它们跳在被种子压弯的草秆上,在草与草之间闪转腾挪。


白腰朱顶雀在南方是看不到的,它们在北极地区、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一带活动。这种鸟迁徙的时候可以达到上百只的群体,它们铺天盖地冲向高粱、小麦和荞麦的谷物种植地,吃大量的种子和昆虫,是令农民头疼的雀类。但是,它们平时也就顶多十几只小群活动,不至于构成农田和果园的损失。
红腹灰雀和灰腹灰雀都是雀形目雀科灰雀属的鸟,它们体长15~18厘米,在我国分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都是无危鸟类,数量平衡。红腹灰雀有极致的美,雄性前胸和颈下全部是橘红色,在雪地里看见它们的时候,就像一团小火焰在白色的雪地上跳跃着,超级艳丽。而雌性为了繁殖的安全,显得很低调,全身羽毛为灰色,背部稍微有点暖色的浅棕。灰腹灰雀则雅致很多,它们的头顶、眼周、枕部都是黑色的,好似缎子一样极具光泽。它们的腹部、背部暗淡很多,腹部是淡豆沙色的,青灰色的背部稍沾了点红,颊部、喉部都是暗红色的。雌鸟头部和雄鸟一样,只是背羽是灰褐色的,后颈是暗灰色的。这种配色不失为一种低调的雍容,静雅美好。



黑琴鸡和花尾榛鸡、雉鸡都很胆小。张老师讲起过去猎杀花尾榛鸡的情景,说那时没有保护意识,家中贫寒想改善生活,就在林子里猎杀花尾榛鸡。当地管花尾榛鸡叫飞龙,那时飞龙很多,一枪一只,发发必中,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打几麻袋。这样无节制的猎杀导致即便禁猎已有多年,林子里花尾榛鸡的数量仍旧恢复不过来。
花尾榛鸡有长而弯曲的颈骨,像龙骨一样,同时爪上有麟,酷似龙爪,所以被称为飞龙。飞龙在古代是进贡皇室的“岁贡鸟”。现在花尾榛鸡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花尾榛鸡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北部,从世界范围看并不濒危。这种典型的森林鸟,喜欢住在植被丰富的地方,浆果繁多的红松、冷杉和云杉等针叶林,柞树、桦树林等阔叶林和混交林是它们的最爱。花尾榛鸡在凌晨就开始觅食,这是躲避天敌的好方法。花尾榛鸡实在是没啥战斗力,它们浑圆的身体看上去肉多肥硕,紫貂、狐狸、猞猁、长尾林鸮、金雕、雀鹰都把它们当成美味。为了蒙蔽敌人,特别是紫貂,它们藏在雪堆里,把身上盖上雪,试图不让天敌发现。随着季节的变化,花尾榛鸡也有垂直迁徙的现象,冬季飞到有枝芽的林地,在树上吃嫩芽。


对滥捕滥杀的恐惧被写进了黑琴鸡的基因,导致它们十分怕人。黑琴鸡体重1~1.6千克,它们宁愿冒着被天敌猛禽发现的风险,拖着胖乎乎的身体飞到高高的树梢上,也不愿意被人斩尽杀绝。野生黑琴鸡在中国仅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河北围场,它们是留鸟,但是冬季会在内蒙古的牙克石到海拉尔一线游荡觅食,在喜欢的河畔和山谷间四处活动。冬季的乌尔其汉,如果是晴天,下午两三点钟是最温暖的时刻,黑琴鸡会来到食物丰富的山谷觅食。到了黄昏时分,它们开始在雪地上用爪子刨出一个直径三四十厘米的雪窝,作为夜晚的巢穴,抵挡冬夜的大雪和凛冽的寒风。
黑琴鸡尽管分布广泛,但是每个地区都是孤岛型的,数量因滥杀而呈下降趋势,我国已把黑琴鸡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范围内黑琴鸡依羽色和体形,分为7个亚种。中国境内有3个亚种,即新疆亚种、北方亚种及东北亚种。这3个亚种体羽上有差别,我们看到的属于东北亚种,它们结实、喙短,鼻孔和脚均有被羽,以适应严寒。雄鸟全身羽毛都是黑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头部、颈部和喉部闪耀着蓝绿色的金属光泽。它的翅上有白色的翼镜,尾羽叉状,外侧的尾羽长,向外卷曲成了琴状,它们的脚是橘红色的。自带高贵的雄性黑琴鸡浑身闪耀着蓝黑色的金属光芒,它拥有三妻四妾,一群雌性跟随着它,雄性黑色的羽毛有利于收集冬季有限的阳光自主取暖;雌性羽毛不是黑色的,浑身黑色与淡棕色交织的横向斑点,使其看上去更显温柔敦厚。
雉鸡俗称野鸡,也叫环颈雉。雉鸡的亚种很多,乌尔其汉的雉鸡属于内蒙亚种,羽色也非常艳丽,在雪地里看到的雄鸟眼先和眼周的红色裸皮在雪地的映衬下异常鲜艳,白色的眉纹与白色的环颈羽毛在脸部黑色和喉部蓝绿色羽毛的对比中分外醒目。雉鸡的背部羽毛有着繁复的斑纹,赭石红、麦色、姜黄交织出织锦一般的纹理和高贵色彩。

长尾林鸮和乌林鸮都是此行的重头大戏。在乌兴干线上,到晚上6点快收工的时候,已经被雾霭遮蔽的森林,全部淹没在暗蓝色的夜幕中,在高高的、茂密的白桦林树干之间,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张老师的注意,他拿望远镜一看:“长尾林鸮!”
长尾林鸮站在树上也太难以分辨了,网格似的羽毛斑点与白桦树完全融为一体,只有用长焦相机对准它时,才看得清楚这一坨的黑影原来是裹了大披肩似的猫头鹰长尾林鸮。长尾林鸮是中大体形的猛禽,以鼠类为主要食物,它们体长45~54厘米,体重452~842克,從数字上来看,真不是小家伙。但看面相,长尾林鸮简直就是一个可爱的套娃。心形的脸盘好像一个乖巧的娃娃,黑白、浅褐色相间的羽毛纹理,和俄罗斯大披肩似的。当晚由于天色太暗,我们只好告别了这只等待猎物的猫头鹰。
第二天早上,在进入乌兴干线之后,我一眼就发现了朝阳中的山杨树上站着一个大大的长尾林鸮,它的喙是金黄色的,前胸和下体都是纵向的纹理,而尾羽比较长,呈圆形,有显著的横斑和白色端斑。不知道是因为太阳光刺眼,还是它正用耳朵倾听田鼠的声音,它基本是眯着眼的,睫毛上全是小雪粒。我们走在没了膝盖深的雪中,艰难跋涉,按下几次快门,手已经冻得全无知觉,如同木头一般了。

这天又是在晚间,在伊力根德沟还看到了乌林鸮,但是一晃而过,错过了仔细观察的好时机。伊力根德沟是乌尔其汉林业局最早开发的沟系之一,因为过去用流送的方式运木材,现在这条沟已经失去了原初的作用。
待到又一个清晨,再次来到乌兴干线的时候,乌林鸮就在白杨树梢迎接着我们。乌林鸮是鸱鸮科林鸮属的大型猛禽。乌林鸮也是没有耳羽簇、圆盘大脸的猫头鹰。因为脸上有暗色圆环,加上有两个新月形的白斑,特别像有胡须的老爷爷,连身上的羽毛斑纹,也显得沉稳老气。自带老相的大乌林鸮始终眯缝着眼,一副浑然不理世界、唯我独睡的神情。
我们离开乌尔其汉的当天,乌林鸮和长尾林鸮简直像欢送我们,频繁出没在我们走的林间车路两边的林地里。尽管冬季拍摄野生生境的猫头鹰(绝无人工投喂)实属不易,但是我还是在短暂的五天四晚中收获了辽远、壮阔的乌尔其汉森林地带的一份丰厚礼物。
(本文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