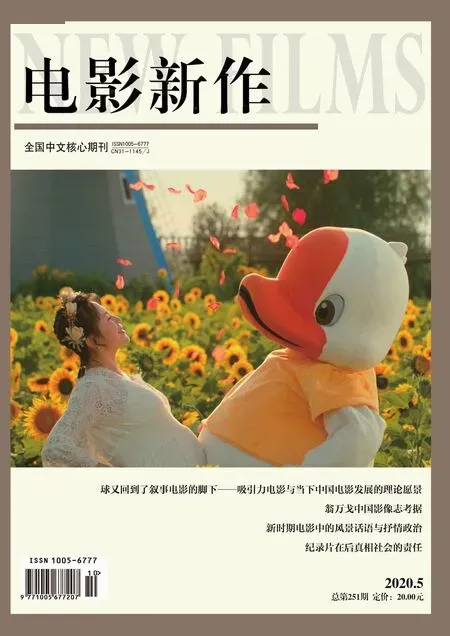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与抒情政治
2021-01-04马楠楠
马楠楠
告别了革命的宏大叙述和创伤语境,新时期中国电影呈现出迥异于前一阶段的美学风格,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便是风景镜头的大量出现。如《巴山夜雨》中“激流奔涌、漩涡密布的川江航道,两岸危耸的峡谷和峭壁,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这类写意的风景镜头占了影片将近三分之二的镜头。”此外,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青春祭》等影片中,河流、群峰、丛林等风景意象亦反复出现,构成了一幅交织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死亡与新生、破坏与憧憬的景观,召唤着新的民族认同。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承担了美学与道德的双重实践功能,游离于叙事情节的风景镜头昭示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标志着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自觉探索。在情与景的融汇互渗中,新时期电影用诗意和抒情抚慰创伤,救赎历史,以“逃逸”和“决裂”的批判姿态参与新的社会现实的建构。
一、双面雅努斯: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创伤与记忆
在《性宇宙学:处于自然和文化概念间隙中的民族与风景;抑或,风景到底意味着什么?》(Sexual Cosmology:Nation and Landscape at the Conceptual
Interstices of Nature and Culture;or, What does Landscape Really Mean?)
一文中,肯尼斯·罗伯特·奥维格(Kenneth Robert Olwig)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风景(landscape)、自然(nature)、民族/国家(nation)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Kenneth指出在英文中,landscape和nature两个单词经常可以互换,而自然(nature)和本土的/本地的(native)、民族/国家(nation)则享有共同的词根nat。因此,landscape和nation、nature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共同点。landscape的后缀scape在当代英语中有时意味着ship,即状态;或者动词shape,即形塑。scape与nature的最初意思相近,landscape中的land指的是属于某个民族的领土(territory),经常与国家(nation)的名字放在一起使用,如英格兰(England),荷 兰(Holland),瑞 士(Switzerland)。Landscape在瑞典语中,指的是区域/地区认同的地点;在德语中,landscape与领土(territory)同义。Landscape的含义是基于部落或血缘的文化认同的领域,而民族/国家nation的构成要素除了本地出生的人民,另外就是领土。英文中culture(文化)的拉丁语词根是colere,意思是栖居、栽培、保护,带着崇拜的尊敬,cult的意思则是照料、爱慕。Culture最初的含义是对自然(nature)的崇拜,同时也意味着开发土壤的潜力。因此,当风景(landscape)与自然(nature)、文化(culture)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便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如《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言,“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均有想象性的建构投诸其上。”在早期中外电影中,风景常常承担着建构民族认同的功能。如好莱坞西部片中雄伟、荒凉、连绵无际的风景不仅是骑马持枪的英雄牛仔的活动空间,更是年轻、充满活力、冉冉上升的美利坚民族的象征。第三帝国时期的“山川电影”(mountain film)用壮美崇高的风景来隐喻雅利安文化的优越性,通过风景和人的映照比较来凸显德意志民族的纯粹性。我国最早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拍摄的“风景片”也“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影片商人来中国拍摄的猎奇的污蔑中国落后的那种所谓风景片。这些影片比较严肃地介绍了祖国的美丽河山、人文风俗、悠久文化和历史建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巴山夜雨》《没有航标的河流》《青春祭》等新时期影片中,山川、河流、丛林等风景意象反复出现,在承担抒情写意的美学功能的同时,亦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
《没有航标的河流》剧本故事发生在湘南山区的潇水两岸。影片开头,随着一望无际的宽阔河流不断向前延伸,平静而又饱含深情的画外音响起:“潇水,古老的河流,我们生活在它的岸边,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它用清水和泥土养育着我们的身体,它用风雨和烈日锻炼着我们的意志,它用古老的经历启迪着我们的心灵。”银幕上,清澈明净的潇水夹在两岸青山之中,一只木排缓缓流驶,岸边郁郁绿树,鹰翔碧空,仿佛能闻到泥土的气息。主人公盘老五在这条原始古老的河流上放排维生,沉默不语的潇水承载着他的青春和爱情,炎炎夏日,他在河里游水嬉戏;夜阑人静时,他对着河水发泄自己的苦闷和寂寞。《巴山夜雨》中的川蜀航道载着船舶日夜穿行,养育一方人民。根据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的《青春祭》,以几个傣寨村民锄地、劳作的远景镜头开篇,缭绕烟雾,古刹钟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赋予这个原始神秘的村寨仙境一般的梦幻美。瀑布、河流、茂密的竹林、洁白的荷花……所有的风景都洋溢着勃勃生机,孕育着美、希望和生命。
然而,风景同时也蕴藏着强大的破坏力和毁灭性。《巴山夜雨》中,大妈的儿子在一次武斗中丧生,尸体被江水淹没,那湍流不息的漩涡象征着历史的无名力量,它无情地吞噬了个体,埋葬了一代人的青春,乌云遮掩的月亮,徐徐移动的山影渲染了一股浓厚的悲剧氛围;《没有航标的河流》中,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盘老五、石牯、赵良们唯一的栖身之所——木排被老虎滩的急流冲散,盘老五为了保护大家最终葬身潇水;《青春祭》的结尾,淳朴古老的傣寨在一场山洪中被泥石流吞没,这里曾经记录着主人公美好的青春和懵懂的爱情,如今全都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片废墟。在此,山川、河流等自然风景不再是默默奉献的大地母亲,而是以其蛮荒、原始之伟力带给人们创伤和灾难。创伤,是新时期电影无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我们把创伤视为不仅仅是对个体身体和心智的撞击,而更是对维系个人和社群的象征意义体系、感情纽带和语言实践的全面震动,那么,文化大革命后大约十几年,可以恰当地称为创伤后状态(posttraumatic)。这段时期,集体的心理被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梦魇笼罩着,同时又力争逃离。”而逃离梦魇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回创伤语境,直面历史和灾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文革’作为典型的现代性创伤,要想根本治愈,就必须提供创伤记忆‘重演’的空间,……因为‘倾诉’和‘搬演’是治疗精神创伤的必要途径”。通过“重演”“倾诉”和“搬演”创伤,新时期电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舔舐伤口,救赎自我的精神出口。

图1.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剧照

图2.电影《巴山夜雨》剧照
作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呈现出双面雅努斯的矛盾性,它一方面以毁灭和破坏的力量残忍地吞噬个体,唤起人们的创伤记忆和痛苦经历,同时又内蕴着一种新生的希望,就像《青春祭》中盘踞傣寨村口多年的大青树一样,它被当地人视作龙的化身,传说中它既可保佑一方安宁,又能招来狂风暴雨,淹没此地。正是在这种死亡与重生、过去与未来、破坏与憧憬的张力中,新时期电影弥合了历史的裂缝,建构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指出,战前电影是一种“运动-影像”,其遵循的是线性因果联系的叙事逻辑;战后现代电影则是“时间-影像”,其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离散的、间隔的、跳跃的时空观,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感知和情感发生了变化。德勒兹强调了纯视觉情境的意义,他认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视觉情境或视觉描述代替了运动的动作,“构成新影像的,是纯视听情境,”“通过不受约束的感觉器官获得的梦一般的关系”。同样的,在新时期电影中,电影的戏剧性、动作性和冲突性被极大地弱化,
二、结晶体影像:风景的逃逸与救赎
在《时间—影像》中,德勒兹曾经占据统帅地位的史诗性叙事被散文化、诗性的影像风格所取代,线性因果的时间链条被打断,闪回、倒叙、想象的镜头不断穿插,零散、随意的个人记忆置换了历史叙述的整合逻辑。而大量出现的风景镜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德勒兹所谓的“时间-影像”,其中,时间摆脱了作为运动附属物的状态,获得纯粹、独立的地位。
(一)风景对人的主体性的救赎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认识装置,风景的发现其实是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在西方,风景画最初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人们从宗教势力中解放出来,注意力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自然的关注,到了17世纪的荷兰,风景画作为一门独立的绘画门类得以确立,画家们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景物的情趣出发,在透视法则的基础上,描绘其主观视点所看到的自然风景。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追求的是革命的宏大叙事和史诗风格,“叙述力图达到超验理想和日常现实之间的统一。在其想象的世界中,‘个体并不与现存的社会人群长期疏离’(Lukacs,Theory of the Novel 29),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命运融为一体。”十年浩劫期间,个体被彻底淹没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私人情感被放逐。因此,新时期电影的一个首要叙事冲动就是彰显人性,重建人的主体意识。无独有偶,《没有航标的河流》《青春祭》《巴山夜雨》等影片均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悬置、静止、似乎与外界隔离的空间:一只木排,一艘轮渡,一个傣寨。在这个封闭、脱节的空间中,主人公得以摆脱纷乱世界的干扰,暂享片刻的宁静。
在《知觉的悬置》中,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思考了“在现代性内部,视觉何以仅仅构成可以为一定范围的外在技术捕捉、塑造或控制的身体的一个层次;与此同时,视觉又是如何成为能够回避体制性围剿,能够发明新的形式、影响及紧张关系的身体的一部分的。”克拉里认为“视觉”具有一种无法测算、不可控制的本原性力量,并阐发了“注意力”所展现的无法控制、难以规训的“逃逸”的面向。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对象,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镜头摆脱了对角色、事件和动作的从属,不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setting),而是以独立的美学姿态具有自主性。风景放慢了电影的叙事节奏,为观众提供了沉思的时间,在对风景的“凝视”和“静观”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被激活。《巴山夜雨》中,当大娘讲述儿子当年的悲惨遭遇时,画面上是特写镜头下奔腾不息的河流,观众和剧中人物一样,在对激流和漩涡的凝视中陷入悲伤和沉思。当秋石说出“你是精神上的囚犯”后,刘文英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船外的疾风骤雨和汹涌波浪,壮烈的自然风景唤醒了她被扭曲、被蒙蔽的灵魂,令她开始反思真与假,对与错,开始独立思考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青春祭》中,大爹告诉李纯傣寨的姑娘们不喜欢她是因为她穿的衣服太土。李纯一个人蹲在河边,看着池塘里盛开的洁白荷花,她第一次意识到“美”是如此重要,美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是生命力的象征。
在新时期电影中,风景除了以美学的形式来表达情绪,渲染氛围,同时也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沉默的在场,具有超越现实,反思历史的能力,风景见证了主人公的痛苦、失落、缺憾和丧失,也赋予其真诚、善良和勇气,在对风景的凝视和对自然的捕捉中,人物获得了穿透苦难岁月的力量,实现了个体的救赎和心灵的自由。
(二)风景对电影美学的救赎
进入新时期,电影理论家和工作者都致力于确立电影艺术主体性。白景晟的《关于电影艺术的特性——从电影艺术发展史角度谈起》(《人民电影》1978年第1期)、《谈谈蒙太奇的发展》(《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等文章都重新提出和强调电影艺术的发展规律和美学特色,倡导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强调“电影和戏剧的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从而推动了一场电影美学革命。如钟惦棐所言,中国电影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思考它的对象的同时,也在思考其自身”。
在对过去历史的回眸和对创伤的治愈中,新时期电影呈现为一种交叉着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知觉与回忆、显在与潜在的结晶体,“结晶体的清澄的面就是当下的经验的存在,而昏暗的面是同样存在于同一个结晶体内的、与这个现在同时存在的过去。换言之,结晶体乃是一个由过去和现在构成的存在,它是一个过去和现在的内部循环,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如同柏格森的记忆锥体模型,“‘时间—点’并非仅仅局限于线性的延伸,而更是本身就凝聚着记忆的庞大本体之中的无限交织的时间维度和层次。”《没有航标的河流》以第三人称旁白展开叙述,告诉观众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不久的过去。随着故事展开,主人公盘老五的回忆又一次次地把观众拉回到过去的过去。追忆似水年华的《青春祭》从始至终都伴随着女主人公李纯梦呓似的画外音,那氤氲着朦胧雾气的雨林、非饱和的、凝重的色彩基调让整部电影变为一场回忆,一个梦境。《巴山夜雨》整部影片的剧情时间只有一天一夜,但是这一天一夜中发生的故事和回忆却折射了一个时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十七年”电影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美学机制,在叙事时间上,其严格遵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序想象,在乌托邦理想与人生现实的融合中铺陈出一系列初始艰难,但最终成功的社会主义史诗叙述。然而,十年浩劫见证了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荒诞、残酷的面向及其最终崩塌。新时期电影于是以去戏剧化的、打破时空顺序的散文化风格告别宏大叙述,凸显个体主观感觉,大量出现的河流、山峰、雨林等风景镜头通常游离于电影情节和叙事的连贯性之外,逃逸出线性、因果的时间链条,带有浓厚的主观、象征、隐喻色彩和朦胧的抒情意味,呈现出脱节、碎片化的特征。这些独立于剧情的风景镜头/空镜头,如同德勒兹笔下的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静物”,或施拉德所说的“停滞”,作为直接的“时间-影像”被放大,被凝固,展现了“片刻的纯粹状态时间”以及时间的绵延性。“静物就是时间,因为变化的一切寓于时间之中,但时间本身不变,它或许只能在另一种时间中,即无限的时间中发生变化。”在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塔可夫斯基等导演的现代主义电影中,风景镜头同样占据大量的比例。这些沉默的风景以缓慢、抒情的姿态,将时间空间化,使时间和思维成为感觉的,让它们有形有声,并通过营造一种纯视听情境来凸显电影的视觉媒介属性以及观众的“观看”行为。
三、抒情的批判性:抒情的何以成为政治的?
在经典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一文中,白景晟发出历史的诘问:“‘四人帮’时期,有人说《海霞》是散文电影,便被认作是大逆不道。其实既然有戏剧式的电影,为什么不可以有散文式的电影?为什么不可以有诗的电影?”白景晟的诘问或可从黑格尔对文本形式的观点中找到答案。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是历史必然运动的缩影,因为艺术想象力求达到超验精神和日常现实有机的融合。某种程度上而言,艺术形式本身便蕴涵着政治讯息。在革命、主义、口号大行其道的时代,宏大叙事和史诗风格备受推崇,到了新时期,经历了剧烈动荡、劫后余生的人们需要更加个人化、更加随意的文体来倾诉和悼念。《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的隐隐青山、粼粼波光、皎皎月华;《巴山夜雨》中的滔滔逝水、蒙蒙细雨;《青春祭》中笼罩在晨光暮霭下的雨林……这些风景镜头赋予影片一股浓郁的抒情气质和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化风格。然而,很多学者却指出这种抒情色彩弱化了影片的批判意识,使其对灾难的表现过于感性,缺乏理性的思辨……这些批评其实是对“抒情”的误解和囿见。

图3.电影《城南旧事》剧照
自2 0世纪中期以来,陈世骧、高友工、萧驰、捷克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ek)等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频频致敬,尤为钟情。近年来,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抒情之现代性》《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等专著、论文集中,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对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抒情”进行了细致的词源学考察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研究,系统梳理了有关“抒情”的种种话语,如陈世骧的“兴与怨”、沈从文的“情与物”、普实克的“诗与史”,揭示了“情”与“史”,“情”与“志”之间的复杂联系与互动。王德威指出,英文中的“lyricism”(抒情)与中文的抒情都指向音乐或诗歌等艺术形式中个性情感的强烈诉求,时间流程的暂停凝结,主体意识的反观内省,以及意象文字的丰富表达。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更意味着一系列“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价值观念、知识方法、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充满了辩证的张力。在西方,从海德格尔到阿多诺,从布鲁克斯到德曼,诸多理论巨擘均曾援引抒情主义作为批判时代种种征候的依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透过我们的情感,我们才得以触碰到最深沉的道德和宇宙的真理。”换言之,情感是现代主体意识的生成动力。对阿多诺(Theodor Adorno)来说,“抒情诗固然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但仍然可在现代社会善尽批判功能。就社会层面来看,他认为抒情诗反映个体从集体——或主体意识从现实客观世界中——的‘脱离’或‘决裂’:‘抒情作品总是主观地表达(诗人对)社会的敌意。’如果‘所有个人诗歌都建立在对集体的理解上’,那么抒情作品既表达了社会的不安,也提供了救赎的手段。阿多诺因而认为抒情诗拥有批判社会的能量。”
在我国古代,陆机提出的“诗缘情”可说是抒情传统的开端。“虽然‘诗缘情’强调情感及其抒发渠道,但陆机的‘情’其实包含了‘以情为志’或‘以志为情’的双重概念。”唐代文人所言“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则提醒我们“情”的历史感及“情”的历史意义。近代更有学者对抒情论述与古代中国伦理实践、知识体系进行细致研究,发掘诗歌在调节公私领域的情感、促进知识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综上种种,王德威认为,“当‘情’当作动词的时候,是一个审时度势、判断生命各种现象、情之以理的‘情’,是相当入世的一个观念。”
正因为“情”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政治和历史讯息,因此,经历了十年浩劫,时至80年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呼吁新时期的中国人应该重拾“新感性”和审美判断力,以其作为弥补、延续启蒙与革命所未完成的现代性大计。李泽厚认为中国的“道”始于“情”,儒家思想中的“情”有助于调和伦理关系和社会政治网络,从而产生愉悦的美感。“一代国人面对‘文革’后的精神废墟,必须反思启蒙与革命范式的不足;眼前无路思回头,中国主体性的自我更新离不开对‘情’的思考与培育。”
在展演了关于“抒情传统”的种种论述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新时期电影含而不露,隐而不言的抒情风格,便发现其所针对的是独断、暴力的历史叙述,是对某种僵化了的进步、革命的宏大叙事的反拨,借助抒情,借助对风景的描摹和对静止时间的沉思,新时期电影让人们获得慰藉与救赎,人生的意义得以重新安顿。渗透银幕的“景语”与“情语”潜藏着中国人内在的情感结构,表达了一代人对逝去青春的怅惘,对历史创伤的喟叹,对记忆的埋葬与钩沉,从而超越了狭隘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私情,最终指向了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以及亘古不变的对生命、对个体的关注。故而吴贻弓如此评价其执导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全片不谈一句政治,但都是关于政治的。
结语
新时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最终指向中国文学和艺术的抒情传统,上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孙瑜、费穆、吴永刚等导演的诗化电影与写意风格,中则延续了“十七年”时期以《枯木逢春》《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林则徐》《李时珍》等为代表的电影美学民族化的探索和实践,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长江图》《不成问题的问题》《春江水暖》等影片中觅见其遗绪与踪影。“艺术的色相是繁复的,正如人世的色相。壮阔的波澜,飞扬的血泪,冲冠的愤怒,生死的搏斗,固足以使人激动奋发;而从平凡中捕捉隽永,猥碎中摄取深长,正是一切艺术制作的本色。”这是1944年柯灵评价桑弧新作《幽兰谱》时写的短文《浮世的悲哀》中的一段话,用它来描述新时期电影的美学风格似乎也颇为恰当。
【注释】
1吴永刚.我的探索和追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35.
2 Barbara Bender, Landscape:politicsand perspectives,Oxford:Berg Publishers,1993:307-339.
3 Schama,Simon,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Knopf,1995:6-7.
4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31-32.
5[美]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2.
6张蜀津.创伤记忆的抚慰与新的民族记忆共同体的建构——“新时期前期”电影中的民国叙述[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01):64.
7[法]德勒兹.时间-影像[M].谢强、蔡若明、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4.
8同7,6.
9同5,124.
10姜宇辉.重释时间-影像:一个电影考古学的视角[J].文艺研究,2019(04):19.
11白景晟.丢掉戏剧的拐杖[J].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01).
12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672.
13应雄.德勒兹《电影2》读解:时间影像与结晶[J].电影艺术,2010(06):103.
14同10,19.
15同7,26.
16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6.
17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371.
18[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64.
19同18,17.
20同18,12.
21同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