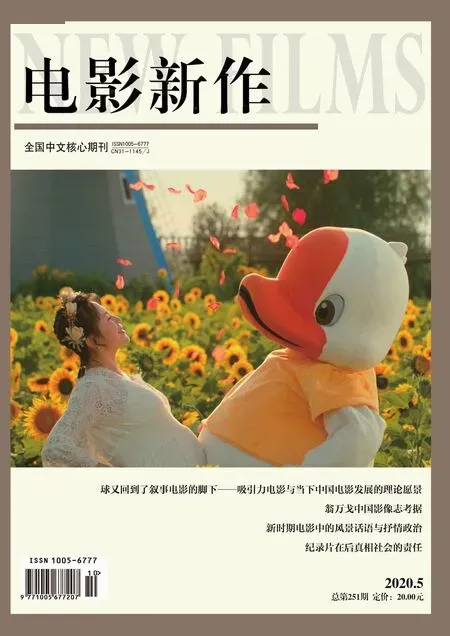乡关何处?
——“藏地新浪潮”与松太加的“家庭三部曲”
2021-01-04潘婷婷
张 斌 潘婷婷
近年来,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藏族导演群体持续崛起,形成了所谓的“藏地新浪潮”现象。作为藏地新浪潮的核心成员,松太加和他的电影受到的关注和讨论相对较少。事实上,以“家庭三部曲”(《太阳总在左边》《河》《阿拉姜色》)为代表,松太加展现了自己对藏族文化和社会的独特观察,并形成了自己的电影风格。他的电影总是围绕家庭情感创伤修复、宗教经验世俗化的母题展开一段“心灵旅程”。他一方面以藏族导演身份的内部视角直接审视藏族文化和藏地风情;另一方面,电影通过旅程片的外在类型承载内部的文化反诘:左边是哪边?河有没有彼岸?“阿拉姜色”是什么色?这使得松太加的影片既具有类型元素,又高度作者化,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一、藏地新浪潮与松太加的旅程片
万玛才旦认为,“藏地新浪潮”是基于创作方法和现象转变,对藏族电影区别于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总体的概括或称呼。作为万玛才旦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松太加凭借“家庭三部曲”崭露头角,成为“藏地新浪潮”的代表。
(一)从藏族题材电影到藏族电影:“藏地新浪潮”的兴起与藏族电影的新生态
以往藏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大多并非藏民族自身,因此通常对藏区文化的呈现带着某种程度的想象性,如《盗马贼》(田壮壮,1986)、《红河谷》(冯小宁,1996)、《冈仁波齐》(张扬,2017)等,创作者试图展现某些影像再造的、定型的藏地视觉符码,营造出一个丧失了欲望和矛盾情感的西藏,来满足观众对藏区的期待和凝视。正如饶曙光所指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一种被‘表述’,两者构成了一组‘汉族/主体/中心主义/看’与‘少数民族/客体/边缘/被看’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少数民族电影只是多数人眼中的少数而已,可谓以彼之酒杯浇我之块垒。
本世纪初,藏族本土电影创作者的陆续出现,使藏族题材电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2005年,万玛才旦创作的《静静的嘛呢石》宣告中国藏语电影的诞生,万玛才旦也由此被外界称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者。十多年来,万玛才旦及其团队中的录音师德格才让、摄影师松太加及《塔洛》的执行导演拉华加等,逐渐成为藏族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这些藏族导演站在民族内部审视“藏式生活”,展现藏民族在神话与现实、现代与传统、民族与国家、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的冲突交织下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多重现代性。他们规模化的创作实践不仅形成了“藏地新浪潮”,而且其内部的异质性和多元化也渐渐显现。“藏地新浪潮”之所以“新”,在于创作视角、思维、形式、题材和类型的多元化革新,以此展现日常生活中当代“藏民”“藏地”和“藏文化”,并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因而,我们以前熟悉的藏族题材电影在这一浪潮中就被转型为藏族电影,开启了新时代少数民族电影新的生态建构之旅。
(二)“藏地新浪潮”中的松太加电影创作
先后毕业于师范类藏语言文学和油画专业的松太加,在结识了万玛才旦后前往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一年,后作为万玛才旦的美术指导和摄影师,协助万玛才旦拍摄了《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7)和《老狗》(2011)。在经过学院化的训练、专业实践和世界性的电影文化接触后,松太加充分利用藏族文化的养分,剥离被外来视角奇观化和符号化的藏地外衣,拍出极具个人印记的藏地电影,如藏传佛教文化中冥冥的生命轮回成了松太加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对儿童的关注、对疾病的追问、对夫妻、父子、父女、爷孙(女)情感关系的探讨、对宗教文化的世俗性表达始终贯穿于电影之中。这些情节元素和主题探讨都来自于松太加自身的生活经验——松太加的父亲离世时仅53岁,同年,松太加结婚并生下女儿,“后来经观众提醒,我才注意到,似乎总有一个治愈不了的人在我的电影中贯穿着,一个拒绝治疗的人,也是因为父子关系,我才发现,虽然是无意识的表达,但我的确在自己的电影中反复叙说这种父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补偿,补偿父亲缺席人生的遗憾,补偿我们没有持续下去的父子关系。”因而,相比其它藏族电影,松太加更专注于对藏族家庭内部情感结构的观察,以私人成长经验结合公路片的类型意识哺育自身的电影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藏族电影的题材路径和美学方向。
(三)向后的公路:回归秩序的旅程片
“公路”是世界性的电影类型元素,是一个载体,一个形态,一个题材,而非一个单一的类型概念,是随着现代性社会发展,现代生活空间的拓展而诞生的和发展的,其本身是一个空间概念,可以承载多种类型表现形式。松太加三部作品以藏文化、个体经验和家庭伦理为“价值观”内核,与公路的类型外壳相结合形成一种旅程片样式,对藏族及世界电影类型的拓展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图1.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剧照
公路片以往或许是为了寻找一个飘渺无定性的乌托邦而感到迷茫困惑,而松太加影片的核心不是关于路,也不是关于风景,而是关于对家庭生活、个体情感和欲望的困顿体悟,“和常规意义上的公路片不太一样,我不想刻意去表现朝圣的过程,我关心的是人的故事”。这打破了传统公路片中冲突和事件基本来源自外部事件和环境的设定。正如英国学者裴开瑞所言,需要把公路电影看作是一个更大的类型框架。松太加的电影显然在公路片这一变体的范畴内,主人公不会进行跨民族边界的旅行,始终和西藏的土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血缘与社会关系的家庭层面上,着意于家庭道德困境的“旅程式”解决。松太加将电影旅程设置为“环形”,叙事起点和落点都是关于“家”的建构,随着经历家庭情感挫折的主人公走出一条弧线,更完整的内核是通过“旅途”所象征的历程,讲述主人公与沿途的风景、人、事、其内心世界及宗教文化所进行的互动,由此逐步地接近旅程片文化批判、自我探索的精神内核。因而,松太加电影中所有的旅程都是回程旅行,正如“太阳总在左边”的隐喻那样,其与传统公路片的不同之处也由此显现——松太加的旅程片不再以向前看的方式,不断地在观众面前呈现一路上遇到的新人新事,因而不具备传统公路片的反叛、萧条的反秩序精神;而是以向后望的姿态,用向内的对话方式,解决了曾横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巨大芥蒂,完成的是“奥德赛”式的、“绿野仙踪式”的归家旅程。由此,松太加的影片是极具想象性治愈力、回归主流情感秩序的旅程片。
二、“朝圣”结构与松太加旅程片的叙事动力
松太加的电影通过对“朝圣”这种藏民族标志性文化模式的再现,在显性和隐喻的双重层面架构了多种不同方式的“朝圣”叙事。这一旅途的终点不再必然是拉萨,也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前进。这种“朝圣”结构与影片中人物情感复杂的往复纠葛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并在死亡和新生、宗教和世俗、创伤和疗愈等人类面对的共同命题中得到升华,同时也构成了故事发展的驱动力。
(一)“朝圣”结构:旅途中情感关系的起承转合
松太加以一种满足自身强烈愿望的“朝圣”结构方式,为旅程注入了某些新的叙事特质,“朝圣”成为一个特殊的空间而具有广延性,既是剧情主线,又是故事的外在载体,用以承载旅途中情感关系的起承转合。
一是以“家庭失意者”为开场。这些“失意者”性格往往疏离且孤僻,但这不是对生活规则的反叛,而是遭受了诸如缺父失母、身患疾病、历史遗留芥蒂等无处安放的情感,如《太阳总在左边》的尼玛,《河》中想见父亲却反复犹疑的格日,《阿拉姜色》中身患绝症的俄玛。当内心的不安不可抚慰时就是身心对既有家庭的拒斥和逃离,从而也就有了试图找回秩序的种种行径。
二是路途上有“家人”及自然属性伙伴的加入。在松太加的影片当中,伙伴不再仅仅限于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物,而是旧有家庭成员的陪伴,或独立于家庭人物之外,给予“亲情”但无血缘关系的“父辈”。如《太阳总在左边》中的老者,《阿拉姜色》中无血缘关系的罗尔基父子。基于藏文化人与自然生物的敬畏关系,伙伴还会以动物,如《河》中的羊羔、《阿拉姜色》中的黑驴等生命体现出,与人物同构为家庭情感的失意者,陪伴其前行。
三是旅途当中景观的抚慰与祛魅。“朝圣”路途暂时抽离城镇和现代性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情感酝酿空间。与以往公路风景不同的是,藏区的原生态风景和独有的宗教习俗给影片注入了新的景观与文化元素,如《太阳总在左边》中巍峨的雪山,《河》中荒凉的牧场,《阿拉姜色》中的酥油灯、煨桑神灵等。但松太加不刻意展现地貌景象,而是将这些风景和习俗后置,将朝圣背景下藏民深层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个体的欲望和情感前置,减少地理式图解,达到一定的对景观文化的祛魅。
四是角色弧的成长。“旅程式解决”并不是“回归”式的成长,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新旧家庭秩序抑或伦理亲情的回归,而是竭力呈现家庭道德困境下,人物的复杂心理结构是如何一步步明朗化,以及如何追寻旅途中新的家庭共同体带来的归属感。三部影片都通过新生和死亡等人生情感力量提供想象性解决途径,在旅程中建立一种新的情感和关系轨迹。
五是回归家庭的结局。三部影片中,“朝圣”结构以“家——陌生空间——家”的形式呈现出人物的“归家之旅”。“在道路式母体的呈现中,由起点到终点,目的地的抵达应同时意味着意义的获取与价值的确认/否认。”影片中,获得新的家庭情感体验的人物,如《太阳总在左边》中最后对着母亲丧生之地流下热泪的尼玛;《河》中遇新生和重疾,在河岸边无言却默默流泪的格日;《阿拉姜色》中相互认同的罗尔基父子,都带着旧有的创伤经验最终回到了熟悉却又陌生的家。
借此五个核心情节构筑的“朝圣之旅”,松太加注入了不同的现代性情感矛盾和解决力量。朝圣之旅总是与家庭成员的成长相关联,一次次的冲突与和解、出走与回归描画着情感嬗变的轨迹,并最终回奔“家庭”,让原本充斥着裂隙和创痛的“家”的意象重新回归为“爱的港湾”。
(二)叙事动力:缺席与缺陷的双重激发
松太加常常将影片主人公设置为具有某种“病态”的家庭成员,所有主角都面临着某种解不开的情感困境,这些困境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内部,而非社会的外在压力。“很多人把冲突只是理解为一个表面的冲突,我更希望是一个内部的,心理依据的戏剧冲突,让它更有冲击力。”松太加的电影中个体在困境中如何从挣扎到突围成了上路的叙事动力。
首先,松太加的三部影片局限在家庭内部的关系建构,都设置了孤僻而倔强,有着明显道德瑕疵的人物。这些角色往往缺失了某种家庭情感,可能是男性成员在家庭结构中的缺席(或名存实亡),导致“父子”关系中“子”一辈的创伤体验;或者母亲因病和意外死亡,“不完整的家庭”给个人造成的情感创伤。主人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体会着“失父”“失母”的寂寥。父与子、夫与妻等家庭人物关系之间面临的现实与愿望、定局和心理的冲突给了故事以“出走动力”。如《河》中怨恨父亲的格日和“失宠”的央金拉姆,格日提早从城镇中的家搬到牧场放牧,主要原因便是想躲避周围人对父亲的讨论和关怀。央金隐秘的失落同样来自一个隔着心幕的父亲。格日和格日的父亲可谓是“在场的缺席”,因为得不到父亲的认同和陪伴,这种仿佛宿命的创伤经验直接反映到了父女两代人自身情感缺位上。格日无论作为“丈夫”“父亲”,还是“儿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瘫”了,这促使人物在克制和隐忍的张力中踏上“寻父之旅”。正如《阿拉姜色》中俄玛去世后,罗尔基和诺尔吾的父子情感培养。
其次,家庭成员意外死亡或被告知得了严重疾病,这往往导致了一个家庭的失衡,疾病中的身体基于不同的文化观念产生不同的叙事途径,呼唤脱离现有环境和生命情感体验,激发人物欲望并导致人物关系变化。《阿拉姜色》中俄玛对丈夫罗尔基隐瞒了自己与前夫的承诺,家庭情感的相互欺瞒,内心的创伤以外化成身体疾病和死亡的形式——“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构成故事的枢纽与关键。因而,俄玛患病的身体作为“开放的伤口”迫使她去面对历史情感的遗憾而走上朝圣之旅。“最悲伤,也是最好的开始。所以,死亡是一段旅程的开始,跟我自己的认知是相关的,和整个民族的文化也是相关的。”俄玛没有试图逃离或者抵抗死亡,反而流露出一种促进自身和过往、当下沟通的欲望来让情感更加清晰。疾患和死亡已经不再是一种凋敝的阻碍,而是一种催发力,要求家人的情感融合。《河》一开头便是格日被告知父亲患了重病,修补父子心结成为格日心里必须面对的修行。“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在影像中,疾病有时不仅仅代表肉体的衰败,更指涉精神上的困境。”除了构成情境设定起始段落的叙事功能外,疾病还有着更为复杂的隐喻功能。格日父亲在“文革”中被迫还俗,陷身世俗,格日就变成了自身破戒的证明。格日和父亲的不同的心疾,成为出走的另一叙事推动力。
再次,现代化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叙事的动力。越野车、重型卡车、家用汽车以及拖拉机等都代表着西藏城市化发展的现代符号,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为一种边缘性的故事背景。三部影片中都出现了摩托车这一交通工具,一方面成为空间转移的推动性因素和物质载具,如《河》中格日三次过河都依靠摩托车;另一方面摩托车成为造成死亡的现代性工具,是对现代藏区社会化进程的一种观察。《太阳总在左边》中,尼玛朝圣返乡途中摒弃快速的汽车徒步,正是因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无法抵抗的力量让他剥夺了母亲的生命。“坐车,太快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尼玛回答老人的疑问时说。藏区交通工具衍变所映射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藏区百姓对时间和空间的空洞感知,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增进人与人的理解和融合,反而加大了情感的疏离与断层。
由此,以公路为载体的旅程片将破裂的家庭成员以不同身份和目的送上旅途,主人公经历了肉体死亡战争、伦理边界战争、内心情感斗争,直至重构家庭情感关系。
(三)不见拉萨的“朝圣”:对“朝圣”叙事的三种编码
松太加直接将“朝圣”作为编码模式,进行“旅程化”的流动叙事。在共同的旅途空间中,“朝圣”的终点不再是拉萨,它被意象化成了各种形态的地点和非线性的时间。《阿拉姜色》止于拉萨之前,《太阳总在左边》始于拉萨之后,《河》中的“拉萨”则是格日父亲的修行洞。“朝圣之旅”以“不见拉萨”的方式揭开了藏地家庭现代情感的困境和个体的内心秘境。
《太阳总在左边》中,尼玛在意外“弑母”后,为化解内心的罪感,前往拉萨朝圣,而影片则是从朝圣结束后开始讲述故事。尼玛朝圣之后在道德层面上依然无法宽恕自己,便漫无目的一言不发地朝西行走,半张脸被太阳灼烧开裂而浑然不觉。尼玛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远离集体生活,游荡的旅途成了人精神和思维的外化载体,一种现实与价值体系的冲突与裂缝、异化与分裂的体验在荒野背景下展现了出来。因而,《太阳总在左边》实际上是一个“反朝圣”的故事。影片试图通过主人公特定的经历和心灵体验,探寻和追问生活迷茫和内心失落的背后,宗教是否能重塑生存价值和生命意识。
《河》是以修行洞为目的地的“异构朝圣”。格日父亲一生在修行洞内向佛法“朝圣”,格日三次过河向父亲迈进,也正是从犹疑到解脱的过程。影片中的“河”从地理上将格日和父亲分隔两岸,而河两岸所代表的“宗教净土”与“世俗尘世”也就成了交流与沟通的障碍,在心理上也是格日心间一道无法化解的伤痕。河以一种隐喻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在影片中消隐并出现,从严冬到暖春,从冰封到消融,它的物理状态展现的也正是格日三次修炼的“朝圣之旅”。

图2.电影《阿拉姜色》剧照
《阿拉姜色》关于“朝圣”,却不为描摹朝圣,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见终点的朝圣”,对“朝圣”的叙事是松散而断裂的。影片用了更多的笔墨去刻画人物情感成长经历,用“不见终点的旅程”来消解情感的二元对立,延续家庭个体死亡带来的情感汇聚。与内在情感相对立的,是外在表达的凝滞。在藏传佛教的宗教环境影响下,藏民把对他人的情感附着在对宗教的虔诚之上,用神明替代与他人的沟通,所以隐秘的内心情感反而隔离了外在的情感交互。影片中,踏上“朝圣”之路的原因在于个体对内在情感的坚守——俄玛对亡夫的愧疚,罗尔基对俄玛的爱与对诺尔吾的责任,而诺尔吾则是从对母亲的依恋延续到对亡父亡母的思念。家庭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维护着隐秘的情感,正是这一趟朝圣之旅打开了情感外露的空间,让松散的一家人在艰辛的旅途中通过理解和包容消除了情感隔阂。
由此,这种朝圣旅程文化意义的变革,与各种不同的藏地家庭关系相结合,时刻将人的情感症结修复之旅放置在前景,后景才是宗教文化等元素,构筑的是饱含人世情感的意象化“朝圣”旅程。
三、空间的流动与游疑:族群仪式神圣性的构建与消解
在地理、文化与生活习性上一直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西藏,是集列斐伏尔笔下的“绝对自然空间”“神圣空间”“差异空间”“历史空间”以及“抽象空间”“矛盾空间”于一体的特定空间场域, 这有助于影片主人公“情感本能”的重新觉醒,从而帮助他们再次感知到个体、家庭和地域文化间的意义,最终突破个人情感或精神的困惑与迷茫。在影片中,流动的公路空间和临时搭建的家,通过抽离日常生活空间,暂时性投入自然母体空间汲取力量,试图解决精神焦虑,重塑伦理观念,为情感回暖和重新“入世”提供了机会。而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世俗与宗教空间的融合碰撞也展现了新的民族情感叙事。
(一)去奇观化:流动的朝圣空间与临时固定的“家”
“朝圣之旅”是旧有核心家庭崩解的开始。松太加将家庭关系的重建置于稳固的日常家庭空间之外,通过帐篷、汽车、旅馆等狭小的封闭空间,在流动的行旅中建立短暂的日常化空间,成为家的一个指代符号,提供交流的契机。
《阿拉姜色》中流动的居所——帐篷,暗示了家庭情感的不稳定性。帐篷作为一个重要意象,这个沿路搭建的临时空间,是可以短时间固定下来的家庭居所,镜头在狭小的空间中移转,营造了极强的飘零感。帐篷内充斥着猜忌、争执与和解等多重情感,情感交锋与转折的重场戏皆发生在这临时的“家”中:俄玛临终前的嘱托,俄玛去世当晚罗尔基独自在帐篷里陪伴妻子、给脚受伤的诺尔吾敷药。在封闭的空间内,出于夫妻彼此扶持的需要和对亡者的承诺,家庭个体之间关系的和解,及血缘意义的重新阐释,表现了文化与人伦的双重完满。《河》中村镇里一排排整齐的红顶瓦房中是格日难以称其为家的“家”,各种琐事和邻里亲戚间的合与不合掩盖了这个家庭的危机,而他提前逃离到安静的夏季牧场完成了“家”的置换,这给他提供了情感思考和转机的场所。偌大的牧场中,以帐篷为符号的“家”尽显孤独无助,很容易联想到格日父亲在修行洞里的情形,但恰恰是这两种寂寥感,提供了三代人“明心见性”所需要的场所。在青黄相接的牧场上,时间在这个溪水盘绕的清净之地流动,央金和格日、格日和父亲之间的情感也随着化冻的河水逐渐回暖。《太阳总在左边》中尼玛自我遗弃的边缘化推动他获得与陌生人、自然空间体验和实践的可能性。尼玛和老者几次在路边荒野烧食交谈。这缺乏遮蔽物的广袤自然空间加剧了人的渺小感和痛苦,人像是空间的俘虏,孤独地、默默无言地与之交会。而宾馆这个更具现代性的封闭空间让二人有了新的情感交流契机——老者和孩子于电话内的交流,宾馆老板娘将二人默认为父子等让尼玛无序的情绪有了新的感知点。
旅途空间和短暂的封闭空间所带来的“自我距离化”,是对既定现实的逃离,也是对自我与这种既定现实之间单一关系的改变,在时间和地域上都建立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也让对藏区“朝圣”故事的观看成为一种去奇观化的双重实践:既保证了日常生活的原貌,又满足了地广人稀的疏离感。由此,松太加尝试建立了一个更为平等的视觉秩序——流动的风景后置,家庭生活、人的欲望成为新的景观,从而将电影情感和空间引领至更为宽阔、开朗之地。
(二)和解的入口与契机:宗教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对峙与融合
对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松太加曾说道:“藏族人对二者没有一个严格的分界线,它们就像骨与肉一样分不开。对藏族人来说,生活同时也是哲学。”随着电影叙事的发展,叙事空间不再是简单地呈现自然空间或社会空间,而是以空间为基础建构抽象化的空间状态和意义高度集中的符码空间,即影片所塑造的“宗教空间”和“世俗空间”。如《河》中格日父亲所在的修行洞从未在影片中得到直接展示,形成了一个抽象化的宗教空间,成为观众想象的空间符码。而河的对岸,格日一家所居住的游牧帐篷,充斥着日常家庭生活的情感矛盾,形成了一个世俗空间。影片的开头格日醉酒所唱的歌谣,“骑马要在人间骑,阴间没有骑马的说道;喝酒要在人间喝……”体现的正是现世精神。
格日父亲经历了中国的特殊年代,一个潜心修行的僧人被迫还俗并被强制组建了家庭。虽然有了儿子,但他依然执念修行,不想陷身俗世。当医院的医生问起格日父亲的名字时,儿子说是“革命的救赎”,父亲说是“佛法的海洋”,正体现了历史造成的宗教和世俗的撕裂。父亲说折腾了一辈子,还是叫“佛法的海洋”吧,表明回归修行的信念。但儿子的存在让他显然没办法完全抛开世俗,就只能一只脚在河的这边,一只脚在河的那边。儿子不懂父亲的心理,也不理解他所信奉的宗教伦理,不能接受父亲对家庭关系的态度和方式。表面的父子矛盾其实隐含着巨大的历史悲恸,因而也让这个家庭故事具有了深刻的含义。通过父子、父女、爷孙的表层情感关系,表现一个重返佛门的僧人如何承受子嗣的情感,如何处理家庭的羁绊,所揭示的其实是宗教情怀如何面对世俗感情。
另外,藏地作为空间叙事场域的最特别之处,还在于其独特的宗教象征意指。朝圣是藏族电影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电影的特殊形式所在,是集“神性”与“社会性”于一体的宗教空间,它为人物解决情感矛盾提供了入口和契机。《阿拉姜色》中俄玛为完成前夫的心愿而开始朝圣。俄玛去世后,罗尔基进寺院请僧侣念经超度,罗尔基将俄玛与前夫的合影贴上墙的时候,忍不住把照片撕开分贴在墙上,最后又把他们粘在一起。这场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和场景的戏中,侧重点仍是罗尔基的内心情感,世俗情感的牵绊成为超越信仰、血缘的强韧纽带。《太阳总在左边》中,尼玛想通过“朝圣”完成内心苦难的救赎,但最终宗教的“神性空间”对主体的救赎并不是影片的核心,朝圣返程中陌生人的世俗慰藉成为了治愈的力量,使得旅途转变成为具有一个化解伦理冲突、寻找内心平衡的空间,从而将朝圣信仰化解为世俗情缘。
因而,在松太加的“家庭三部曲”中,“朝圣”作为一个契机和文化入口勾连起宗教空间和世俗空间。他在建构外部“神圣宗教”空间的同时,也从人和人、人和家庭多层次的世俗情感空间中,由内而外地解构了族群仪式的神圣性。格日、央金拉姆、诺尔吾、尼玛在路上放下了心结,放下了对历史情感的执着,而这也是旅途的意义所在:通过情感、文化的再缝合将两者融为一体,重新建构了环境与个人、朝圣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四、向内的现代性与超民族性的类型书写
松太加的“家庭三部曲”体现出了鲜明的藏族电影风格。他在一个更为具象的家庭情感面向中去重新理解其和藏文化之间的关联,以民族学的视野和个体书写的方式重新激活了藏地本土文化话语,表达出一种独特的民族血肉感。他的电影表达了在西藏特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氛围下,个体直面现实情感欲望时如何平衡内心固有的价值秩序和现实伦理窘境,并在矛盾中寻求藏文化所能提供的解决力量——一种原乡旅途式的心灵净化。松太加在“痛苦-逃避-面对-解脱”的故事结构中,通过对朝圣等宗教文化的神圣性消解和现代性价值探讨建构出一套与自己和民族生命体验相关的故事脉络和另一种西藏社会的“真实”面向。“家庭三部曲”可看作是旧有的家庭结构在原乡土地上进行旅途式情感、文化观念重塑后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朝圣等宗教文化在藏区现代性变革下的价值观再塑,藏民如何借用朝圣智慧回应自身的生活情感困境,用旅程去体察个体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在路上的方式继续与西藏土地和宗教文化保持密切关系。其间的生死命题、血缘亲情、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民族化表达与镌刻在其中的语言、文化印记一道成为藏族电影新的民族叙事路径。松太加更倾向一种“和”的内向视野去解决矛盾冲突,藏文化的独特性被置放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理之中,由此展现了民族文化性格的本质差异。
另外,松太加想要借电影探求的,不只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是普遍的人的现代性存在境遇与情感反应。“我的电影还是在关注人,而不是藏族。汉族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我也能驾驭得了,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就是东方文化。”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原乡为叙事背景,以民族意识为文化根源的叙事选择有着模糊的边界,却拥有巨大的普遍可能性。对藏地家庭情感的普遍性困境进行现代性反思,从人而非族群的角度出发呈现个体的处境和精神世界,这样族群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小,人类共通的情感则转而浮出水面。“作为人类的一员,不管我是什么民族、宗教信仰,甚至是性别,我想讨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这使你的作品一下子有了普世的意义,它超越了很多人对藏族题材的想象。”一方面,松太加依靠公路母体与家庭伦理的类型融合,创新了藏族电影的叙事路径,其电影虽描绘藏地,但故事却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其独特的民族情感结构也就在这普遍性的生存之困的体验中获得共鸣,借此逐渐破除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僵硬标签。另一方面,电影从个人到家庭,从藏地空间到藏文化空间,将地域性做减法,为人物做加法,文化的广延性得以超越民族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民族即世界”的方式。因为“个体情感”要比“民族寓言”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松太加的电影可以说是把藏族文化和物理空间看成西藏暗含的宝藏,而在解决家庭情感问题这一过程中去探寻宗教、个体、土地和文化之间未来的关系。
结语
太阳东升西落;河能冰封也能解冻;酒可以冰凉如水,也可以热烈如火。路上的故事从精神放逐到情感回流,就如同《太阳总在左边》《河》《阿拉姜色》中三个家庭从破碎到弥合的隐喻。面对疾病、死亡、新生、血缘等世俗问题和情感纠葛,每个家庭都面临复杂的困惑性,都需要做抉择。这条被太阳、河水、酒与歌连接起来的“朝圣”之路,基于民族又超越“少数”,力求恢复家庭、宗教共同体,民族叙事与普通大众的在地想象、心理认同与情感契合,给普通大众表达了一个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藏地空间。这应该是松太加的“家庭三部曲”最值得肯定的意义。
【注释】
1万玛才旦.开启“藏地新浪潮”[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44758.
2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J].当代文坛,2015(1).
3该片亦被谢飞导演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
4松太加,崔辰.再好的智慧也需要方法——《阿拉姜色》导演松太加访谈[J]当代电影,2018(9).
5李彬.“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分辨与价值观解析[J].电影新作,2013(6).
6正如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对《阿拉姜色》的评语:“该电影坦诚而深刻,勇敢不妥协,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问题时刻的希望和救赎。每一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如果人类牺牲了他的欲望、他的自我,那么他就可以维持上升的旅程。我们想把这个奖项颁给邀请我们参加人类精神旅程的人。”
7同4.
8 Chris Berry. Pema Tseden and the Tibetan road movie: space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film’.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2016:89-105.
9戴锦华.电影批评(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5.
10龚艳、万玛才旦、袁海燕.当我们在谈万玛才旦时我们在谈什么?——万玛才旦导演访谈[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7(2).
11同4.
1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1.
13李金秋.户外视域下的“藏地”文化空间再生产[J].当代电影,2019(2).
14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6.
15同4.
16《阿拉善色》为何获得如此高的口碑?导演松太加真的不一般……[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77327055884568 75&wfr=spider&for=pc.
17松太加、杜庆春、祁文艳.一路走下去——关于《阿拉姜色》的一次对谈[J].电影艺术,2018(5).
18秦宗鹏、刘军.从民族寓言到个体情感 ——从万玛才旦到松太加谈藏族题材电影的民族化叙事转向[J].电影新作,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