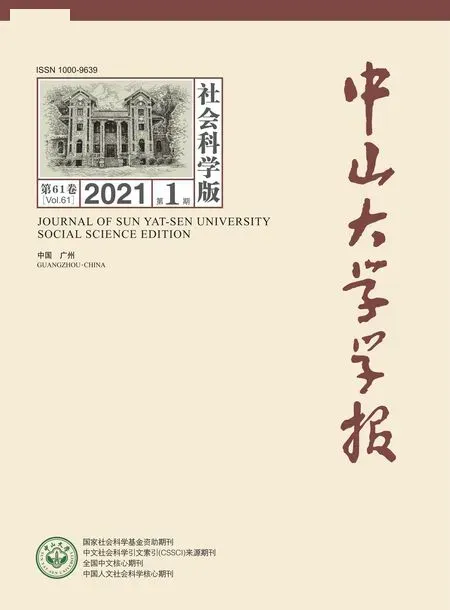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
——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2021-01-03郭嘉辉
郭嘉辉
随着近年中国与友邦交往日益频繁,加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都令“朝贡制度”等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渐受海内外学界重视,成果相继涌现①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莫翔:《“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骆昭东:《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David C.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相关讨论更从历史学扩展至国际关系学②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4—133页;黄纯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 年第1 期,第55—64 页;孙卫国:《从“同心圆”论到“两极模式”论——美国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学说》,《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第159—170页;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总第22期,第33—62页;戚文闯:《明清朝贡体系述评》,《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114—120页。。但各种讨论其实都忽略了“朝贡制度”作为近代知识体系“产物”的本质。目前种种分歧与争议,或多或少都源于这一概念在形成之初的定义与框架。
因此,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先从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中的分类,进而分析它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同时更要探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朝贡制度论”的形成对日后“朝贡制度”研究造成怎样的局限与影响③John E. Wills,Tribute,Defense and Dependency,American Neptune,Vol. 98,No. 4(Fall 1988),pp. 225-229;Jame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9-15;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第3—24 页;冈本隆司:《“朝贡”と“互市”と海关》,《史林》第90号第5期(2007.9),第749—771页。。简而言之,以下讨论希望透过剖析“朝贡”知识从传统到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为“朝贡制度”研究从范围、概念、史料找到新的突破。
一、传统经典下的“朝贡”
“朝”与“贡”在先秦典籍中本是分开使用的。“朝”屡见于《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其中以《周礼》的论说最具代表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18《春官‧大宗伯》,《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6页。,而贾公彦、孙贻让(1848—1908)认为“邦国互通”都是指“诸侯”②《周礼注疏》卷2《天官‧大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7册,第29页;孙贻让:《周礼正义》卷2《天官‧大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页。。所以郑玄(127—200)注《周礼‧秋官‧大行人》“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一条,也指“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总而言之,“朝”的古义,只适用于诸侯,主要指天子见诸侯。《礼记》的《曲礼》《王制》与《明堂位》亦提到“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与“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4、12、31《曲礼下第二》《王制》《明堂位第十四》,《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2、12、14册,第143、432、1085—1086页。。
“贡”则据《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郑玄认为是“从下献上之称”。孔颖达(574—648)则进一步解释为“禹分别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史录其事,以为《禹贡》之篇”④《尚书正义》卷6《夏书‧禹贡》,《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2册,第158页。,所以“贡”必然是“九州之界”内“从下献上之称”。而这一点正与《周礼‧天官‧大宰》的“以九贡致邦国之用”⑤《周礼注疏》卷2《天官‧大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7册,第45页。与《职方氏》的“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⑥《周礼注疏》卷33《夏官‧职方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9册,第1033页。意义相通。所以“贡”也是用于“邦国”“诸侯”而不出“九州”的范围。
既然如此,“朝”与“贡”是于何时开始连用?并延伸至“九州之外”?关键则在于《周礼‧秋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
而郑玄注“其朝贡之岁,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⑦《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9册,第1175页。。孙贻让指郑玄此义其实与马融(79—166)相通,同时利用“大宗伯四时朝觐,并云‘见’”,说明“朝、觐、遇、宗”与“见”是等同的。因此《大行人》提到侯服、甸服等六服中的“岁壹见”“二岁壹见”中的“见”,便与“朝、觐、遇、宗”的意义是相通的。当中区别只在于“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盖谓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别四分之,四时迭来”⑧《周礼正义》卷71《秋官‧大行人》,第2978—2979页。。换言之,《大行人》“六服”诸侯根据所在的“四方”而按“四时”来“见”,就是“朝、觐、遇、宗”。而“六服”的“岁壹见”又是与“其贡祀物”等一同进行。因此,在郑注下,“朝”因与“六服”的“见”相通,遂与“贡”共同成为“六服”诸侯的义务。因此,郑注《大行人》的“六服”为“朝”与“贡”提供了连用的根据。
而更为重要的是,“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无朝贡之岁,以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必须注意的是,郑玄此处主要指蕃国“无朝贡之岁”,是基于“以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的“世壹见”①《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9册,第1176—1177页。,而非蕃国“九州之外”的身份。
换言之,“朝贡”其实也适用于“九州之外”,特别是郑玄曾引用“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其余则《周书‧王会》备焉”,说明“朝贡”曾用于域外的事实。孙贻让在《周礼正义》亦解释到:“《王会》,《周书》第五十九篇,记成王会诸侯献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世,作《王会》。’所贡贵宝,若稷慎大尘、秽人前儿之类,名数甚多,故不备引。此九州之外所献贵宝,即怀方氏所谓致远物也,与上六服有贡异,然通而言之,亦得谓之贡。”②《周礼正义》卷71《秋官‧大行人》,第2982页。
《汉书‧王莽传》中《谢益封国邑》载“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③(汉)班固:《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51—4052页。,反映“朝贡”在西汉已具有政治臣服的意义。但郑注则为“朝贡”赋予更丰富的意涵与经典的依据。同时,东汉的“朝贡”亦渐与外夷相关,特别是应劭(153—196)《汉官仪》与蔡质(132—192)《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于“正旦朝贺”都提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④(汉)应劭著,(元)陶宗仪辑:《汉官仪》;(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210页。。“朝贡”遂成为描述域外政权与中国建立或维系政治关系的一种方式。
《史记》与《汉书》奠定了正史“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撰述模式⑤钱云:《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7—70页。。而“朝贡”自东汉起渐与四夷论述关系密切,“朝贡”的记述也自然落入到正史的相关记述,尤其是四夷传、外国传。因此,王赓武透过“正史”讨论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优越感⑥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in 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34-62.;陈鸿瑜从“二十五史”搜集民国以前中国与东南亚的外交关系史料⑦陈鸿瑜:《民国以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料编注》,台北:新文丰出版,2018年,第1册《编注凡例说明》,第vii页。;韩国学者全海宗以《史记》与《汉书》讨论“汉代朝贡制度”⑧全海宗著,全善姬译:《汉代朝贡制度考》,收入《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129页。。
随着魏晋南北朝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佛僧法显(约338—424)从长安出发往印度取经,并书成《佛国记》。而在《隋书‧经籍志》“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的原则下⑨(唐)魏徵:《隋书》卷33《经籍二‧史‧地理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988页。,《佛国记》与《遊行外国传》《交州以南外国传》《扶南异物志》《张骞出关志》《外国传》《历国传》《林邑国记》《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诸蕃国记》等被编入《经籍二‧史‧地理记》。可见,《隋书‧经籍志》为涉外知识典籍的分类提供了依据。而“朝贡”因与对外关系密切,也落入到“史部地理类”的分类。
明人黄省曾(1496—1546)于正德十五年(1520)集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等二十三国史事编成以“朝贡”为题的《西洋朝贡典录》,正是最好的例证。《西洋朝贡典录》于万历《国史经籍志》分属“史部‧地理‧蛮夷”⑩(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3,收入冯惠民主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295页。,继在《明史‧艺文志》亦属“史类‧地理类”⑪(清)张廷玉:《明史》卷97《艺文二‧史类十‧地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19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于“史部地理类”再细分为“外记”①(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8《史部三十四‧地理类存目七‧外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072—2073页。。而清末王韬(1828—1897)所著的《琉球朝贡考》亦于《清史稿‧艺文志》属“史部地理类”的“外志”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46《艺文二‧史部‧地理类‧外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04页。。可见,“朝贡”作为涉外知识的典籍在传统经史分类下,自《隋书》以降一直附于“史部地理类”直至清末民初。
此外,前述《汉官仪》与《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提到“蛮、貊、胡、羌朝贡毕”,说明了“朝贡”为当时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制度。因此,梁武帝萧衍(464—549)于大同七年(541)就编有《职贡图》,记载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楼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等使者的绘像与题记③岑仲勉:《现存的职贡图是梁元帝原本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第42—47页。。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会昌三年(843),宰相李德裕(787—850)“以黠戞斯朝贡,莫知其国本”,命给事中高少逸撰成《四夷朝贡录》十卷载“凡二百一十国”④(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0页;(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上《本纪第十八上‧武宗‧李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5页。。可见,至少自梁武帝始,王朝为了处理“朝贡”事务,而陆续编纂《职贡图》《四夷朝贡录》《黠戞斯朝贡图传》等典籍⑤(宋)欧阳修:《新唐书》卷58《艺文二‧乙部史录‧地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08页。。
而元明两代则进一步将“朝贡”编入政典。元代《经世大典》虽已失传,但《国朝文类》辑有《礼典总序》,记载“十有七曰朝贡,十有八曰瑞异。为礼典上篇”及“朝贡”的序录⑥(元)苏天爵辑:《元文类》《杂著二‧礼典总序》,《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367册,第506—507页。,都证明“朝贡”是《经世大典》中《礼典》的内容。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成的《诸司职掌》当中的礼部主客司也正是以“朝贡”为目,收录该司处理朝贡相关事宜的规章。其后明孝宗下令以《诸司职掌》为基础编纂《大明会典》⑦《正德大明会典》《会典序》,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4页。,使得正德《大明会典》沿袭了《诸司职掌》礼部主客司“朝贡”的类目体例⑧《正德大明会典》卷96—98《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二、三》,第354—369页。,并延续至万历《大明会典》。《皇明外夷朝贡考》虽以“外夷朝贡”为题,但实际上也是记述礼部主客司的职掌⑨《皇明外夷朝贡考》,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礼部志稿》亦有“朝贡备考”⑩(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90—92,《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598册,第618—687页。。可见,明代大抵奠定了于政典记述“朝贡”的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清承明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五朝《大清会典》在《大明会典》基础上发展。清代五朝会典以及相关的事例、则例,也因而沿用《诸司职掌》于礼部主客清吏司以“朝贡”收录条文、规例及记述的模式⑪郭嘉辉:《明清“朝贡制度”的反思——以〈万历会典〉、〈康熙会典〉中〈礼部‧主客清吏司〉为例》,周佳荣、范永聪编:《东亚世界:政治‧军事‧文化》,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第42—79页。。而这种记述方式,本以协助官署执行相关事宜为宗旨,自然并不能反映“朝贡”的全貌,但可惜费正清“朝贡制度论”却赖以为据,遂对日后朝贡制度研究造成极大影响。要之,“朝贡”由于作为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制度或方式,凡此种种涉及的规例也被编入政典,使得政典也成为传统经史架构下“朝贡”知识的另一重要载体。
不仅是政典规章,《汉官仪》与《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提到的“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同時说明了汉代“朝会仪”等礼仪亦是处理“朝贡”的重要一环。晋续汉仪,《咸宁注》也沿袭了“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为朝会仪⑫(唐)房玄龄:《晋书》卷21《礼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9—661页。。更重要的是,西晋按《周礼》编成五礼的国家礼典——《新礼》,而据《晋书‧礼下》的分类则知《咸宁注》所代表的朝会仪,正是属于当中的“宾礼”⑬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93—495页。。朝贡礼仪,也因而与五礼的国家礼典变得密不可分。
虽然随着地方控制的加强与一元君臣关系的确立,盛唐《开元礼》将朝会仪转属“嘉礼”①[日]渡边信一郎著,周长山译:《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日]沟口雄三等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朱溢:《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从〈政和五礼新仪〉的宾礼制定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第124—125页。,但同时也将《蕃国主来朝以束帛迎劳》《皇帝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皇帝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与《皇帝宴蕃国使》编成“宾礼”②(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79、80《宾礼‧蕃国主来朝以束帛迎劳、皇帝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皇帝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东京:古典研究会,1972年,第386—392页。。这大抵佐证了“朝贡”奠定于汉代而无古礼③(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36《嘉礼九‧朝礼》,台北:圣环图书馆公司,1994年,第1a页。,相关礼仪其实是因应各朝政局与对外关系发展而衍生,所以范围不一,同时也散见于礼典。正如北宋因澶渊之盟有别于前代,分别为契丹、高丽、交州、西南蕃等制定区别仪注④朱溢:《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以礼仪制定原则的讨论为重点》,《学术月刊》2014 年第4 期,第124—136页。,蕃国接诏、宴蕃使在《大明集礼》是“宾礼”⑤(明)徐一夔:《大明集礼》卷31、32《宾礼二‧蕃使朝贡‧锡宴仪注》《宾礼三‧遣使‧蕃国接诏仪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1530)内府刻本,第30a—31a、17a—19a页。,但朝鲜迎接诏书、燕外国贡使于《大清通礼》则为“嘉礼”⑥(清)来保:《大清通礼》卷28、37《嘉礼》,《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55册,第337、398页。。这正是近代费正清等人难以从“礼”诠释“朝贡”的缘由。
“朝贡”概念虽大抵成熟于郑注《周礼‧秋官‧大行人》,但《大行人》本身提到的“春朝、秋觐、夏宗、冬遇、时会、殷同”,正是《春官‧大宗伯》的“以宾礼亲邦国”,再加上涉及“朝贡”的礼仪如朝会仪早于西晋已属于“宾礼”。宾礼礼典因此成为了朝贡礼仪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大明集礼》是以洪武二年(1369)《蕃王朝贡礼》为基础编成“宾礼”三卷,说明了“宾礼”在明代以来的朝贡礼仪,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⑦郭嘉辉:《元明易代与天下重塑:洪武宾礼的出现及其意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7 卷第1 期(2020 年6月),第1—50页。。《大明会典》等政典也是以《蕃国礼》等辑录相关礼仪⑧郭嘉辉:《天下通礼:明代宾礼的流传与域外实践的纷争》,《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9 期(2018 年6 月),第1—40页。。《大清通礼》的“宾礼”亦载“朝贡之礼,凡四夷属国按期修职贡,遣其陪臣赍表文方物来朝”⑨(清)来保:《大清通礼》卷43《宾礼》,第427页。。总而言之,由于“朝贡”运作涉及礼仪,所以与之相关的礼典仪注特别是“宾礼”,也成为了承载“朝贡”在传统经史脉络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宋代的类书《玉海》虽以“朝贡”为编目⑩(宋)王应麟:《玉海》卷152—154《朝贡》,《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947册,第1—76页。,但在整个传统中国学术脉络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亦大抵说明了“朝贡”在传统经史的架构,并未能形成其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或是独立领域,只能因涉外知识或政务,而散落于:(一)正史;(二)史部地理类;(三)政书;(四)礼典仪注等四大传统知识框架。正由于“朝贡”知识的散落,这亦埋下了其在近代转型时所出现的问题。
二、中西交通史的错落
梁启超(1873—1929)于1901 年的《中国史叙论》提到“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大声疾呼要构建新国民,故其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到,“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页。。中国从传统王朝重构成民族国家之际,传统对外知识是如何转型至近代学术体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中西交通史”作为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①李孝迁:《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5—117,109页。,正反映传统对外知识在近代的转型。诚如张维华所说,这一学科在出现初期相当混乱,直至张星烺(1888—1951)、向达(1900—1966)于上世纪30年代才正式提出“中西交通史”为专门史②张维华、于化民:《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1期,第3—9页。。由此可见,这一学科的出现并不是系统引入,而是靠学者共同构建。但张星烺、向达等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中西交通史”的概念?
张星烺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的《自序》记述,“中国史地,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吾则安得不学他人,而急欲知彼对我研究之结果何如乎”③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民国丛书》第5编第2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自序》,第5页。,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则写道:“我以前读Henry Yule编译和Henri Cordier 修订过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这一部书的时候很是心服,书中关于中古时代西方人士,说到中国或亲自到过中国而写成的纪行之作,收罗很详,考证也极详审。第一册为导言,专言好望角航路尚未发见以前,中西交通的概况,提纲挈领,颇为得要。我因以此册为张本,写成这一部中外交通小史。”④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作者赘言》,第1页。而最早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的陈衡哲,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并以中西交通史为其硕士论文题目⑤李孝迁:《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5—117,109页。。所以“中西交通史”的出现,更多的是受西方学术刺激反应而成,并非从传统典籍的脉络下衍生,这亦造成了其与传统知识体系的脱节。
故此,中西交通史大多聚焦于古往今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商业往来。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等分为七编五册。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分《中国民族西来说》《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哥孛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以后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十三洋行》与《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问》。中西交通史以迥异于传统学术的框架重构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面貌,这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被碎片化,失落于这一近代转型过程,而“朝贡”则正是当中遗落的一块。
三、中国近代史的出现与费正清“朝贡制度论”
中西交通史的错落,使得“朝贡”在近代学术体系的转型,落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1905—1988)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刊登的《清代朝贡制度》⑥John King Fairbank,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No. 2(1941),pp.135-246.,奠定费氏“朝贡制度论”的主要观点,特别是认为“朝贡制度”是基于中国悠久文化的优越性并以贸易为基础形成⑦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 23-38,462-468;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pp.1-33.。因此,透过剖析当中观点的形成,可以从根本上揭示这个理论于概念、框架到史料等方面所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同时更揭橥“朝贡制度”作为近代学术概念在形成之初存在的种种问题。
费正清将“朝贡”视为外交问题,其实是继承自蒋廷黻(1895—1965)“强调中国传统‘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差异”的观点⑧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载[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0页。。“朝贡制度”亦因此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从一开始便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关系密切。蒋廷黻与罗家伦(1897—1969)作为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于“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并视鸦片战争为起点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香港:龙门书店,1964年,第83页。。近代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焦点②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14—16页。。“朝贡”也因而被视为是外交问题而非对外交流,成为近代史而非中西交通史的议题。
1932年张德昌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写道:“清朝由康熙到道光年间,粤海关的设施,通商的制度,大半沿照明代的旧规,清朝对于通商,在精神上和明代是一贯的。换言之,这一百五十余年间诸种问题之发生,其症结根源之所在,是有较长期的历史背景的。为要明瞭清代鸦片战争前广东通商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上所寄托的精神,不能不追溯到明代的通商制度……明初到嘉靖年间,贡舶方式的贸易盛行,藉朝贡之名义,行贸易之实。”③张德昌:《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1932年),第1页。这清楚地显示出当时学界对“朝贡”的关怀,是建基于了解近代中西冲突的前题下。
日本学者百濑弘于《东亚》发表的《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也不约而同提到,“乃是看做它的源头所谓‘西力东渐’时期欧洲诸国的对华贸易的内容,而以阐明这个和旧来的中国之对外贸易的不同为主旨”④[日]百濑弘著,郭有义译:《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第42页。。在这样的脉络下,“朝贡”研究的焦点被导向以“贸易”为主。所以1935 年内田直作发表的《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正是讨论“非朝贡不得互市”,“有抽分之例,无抽分之实”的朝贡贸易性质。而这些研究和观点于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内田直作《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先后被王怀中、朱胜愉以及署名“让”的作者分别翻译和介绍在《食货月刊》⑤[日]内田直作著,王怀中译:《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食货》第3 卷第1 期(1935年),第32—37页。《商业月刊》⑥[日]内田直作著,朱胜愉译:《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商业月刊》第15卷第10 期(1935年),1—5页。和《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⑦让:《明代朝贡贸易制度》,《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2卷第3期(1935年),第13页。。而百濑弘的《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则影响更大,不仅于1936 年被郭有义、袁干君翻译并刊登在《食货半月刊》《中国经济》,而且与张德昌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同被征引于费正清《清代朝贡制度》一文⑧John King Fairbank,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239-241,p.139,p.199.。1941年,秦佩珩发表在《经济研究季报》的《明代的朝贡贸易》以及1943年管照微发表于《贸易月刊》的《明代朝贡贸易制度》都是延续“藉朝贡之名义行贸易之实”的观点。
费正清的《清代朝贡制度》正是在这脉络下,形成朝贡制度就是贸易晃子的基础观点⑨John King Fairbank,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239-241,p.139,p.199.,费氏透过梳理《康熙会典》规章,花了很大力气从《清史稿》统计出整个清代朝贡次数的数据,指出“入贡”的增加正是由于商业利益驱使⑩John King Fairbank,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239-241,p.139,p.199.。从这一点可见,费正清“朝贡制度论”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蒋廷黻、张德昌的基础上发展,只能代表民国早期的观点,置于时下日渐成熟的学术体系早已显得局限不足。而且不单是框架、观点的问题,史料取材也存在很大的缺憾。
发表于1941 年的《清代朝贡制度》其实是费正清与邓嗣禹在哈佛大学研读清代文献,讨论内阁、军机处、文书传递等制度的衍生之作,由于对制度建置与运作的重视,对《大清会典》的解读无疑成为重中之重⑪[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台北:五南文化事业,2014 年,第186—187 页;John King Fairbank & S. Y. Teng,“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4,No. 1(1939),pp. 12-46;John King Fairbank & S. Y. Teng,“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5,No. 1(1940),pp.1-71.。故此,费正清等正是在这一脉络下透过“会典”来研究“朝贡制度”。虽然费氏并不是始作俑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早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已引用《大清会典》扼要交代朝鲜、琉球、安南以至荷兰使节入贡的情况①H. 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Period of Conflict,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1971,pp.50-51.。但费正清却是首位以《大清会典》勾勒“朝贡制度”内容的学者。由于这一史料选取的偏好,导致朝贡制度研究出现无可挽救的盲点与误区。
《清代朝贡制度》虽以万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各朝会典及其事例、则例为基础,但当中征引会典的25 处大半都是出自各朝会典的“礼部主客清吏司”,而第四节Ch’ing Tributaries from the South and East-General Regulation、第五节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更是直接翻译自《康熙会典》中的《朝贡通例》《外国贸易》以至“西洋国”入贡事例②(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72、73《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通例、外国贸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 年,第3701—3706、3761—3766 页;John King Fairbank,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163-181.。换言之,费正清于朝贡制度的理解,其实是建基于“礼部主客清吏司”一部。但朝贡的运作兹事体大,《康熙会典》的礼部主客清吏司虽提到“凡遇圣节、元旦、冬至具表御前,进贡方物,具笺中宫、东宫前”,但其运行详情其实见于卷40《朝贺》的《元旦朝贺仪》《冬至朝贺仪》与《万寿节朝贺仪》③《(康熙)大清会典》卷40《礼部仪制司‧朝贺》,第1915—1942页。。单是与礼仪相关的部分已牵涉甚广,更不用说负责护送的兵部、赐谥致祭的内院、安排朝会的鸿胪寺与安排宴会的光禄寺等等。而这种以礼部主客司为主的朝贡记述对日后研究造成极大困扰。
首先,如前所述,“朝贡”兹事体大并非礼部主客司所能及,若只参考主客司的记载则导致对“朝贡制度”的定义与界线含糊不清,尤其是册封、致祭虽在记述之中,但并不代表是由礼部主官司处理④孙成旭指出清廷就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否册封朝鲜王世弟,主客司与仪制司就持不同意见,需要上级定夺。孙成旭:《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122页。,究竟这些范畴是否属于“朝贡”,则成为了学界至今仍然争论的问题。
其次,礼部主客司的权责在于处理朝贡国贡道、贡期、贡物与回赐,《大清会典》自然附以相关条文为记载。但在这种记述的引导下,费正清自然聚焦于贡物、回赐等问题上,而这恰好配合其认为朝贡制度具有经济贸易的性质,导致朝贡制度的研究日渐倾向“贸易”一途,漠视朝贡涉及的礼仪、文书、制度等方面所反映的天下概念、华夷思想、权力变化⑤郭嘉辉:《天下通礼:明代宾礼的流传与域外实践的纷争》,第1—40页。,尤其是近年的《燕行录》研究大大丰富了外国使节在朝贡制度下的东亚文化交流现象⑥裴英姬:《〈燕行录〉的研究史回顾(1933—2008)》,《台大历史学报》第43 期(2009.6),第219—255 页;吴政纬:《从中朝关系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录〉为中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1期(2014.6),第209—242页。。
再者,费正清虽标榜以清代五朝会典为研究对象,但除了朝贡国、贡期、贡道外,大体仍以《康熙会典》为据,这种漠视文本差异的分析,不仅忽略了制度的演变,更造成学界争论。费正清对朝贡规例的理解,大抵建基于《康熙会典》的“朝贡通例”。然而随着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编纂,乾隆及以后的嘉庆、光绪会典已不再沿用这一体例。即便《雍正会典》继承“朝贡通例”,但在内容上却有差异,撇除雍正新增的内容外⑦“康熙四十二年,覆准嗣后喇嘛进贡,不给驿递。”(清)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雍正朝)》卷104《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通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79辑,第6953页。,先是于“崇德间定,凡归顺外国,俱颁诰册,授封爵。嗣后一应进奏文移,俱书大清国年号,凡遇圣节、元旦、冬至,具表御前,进贡方物。具笺中宫、东宫前,进贡方物,差官朝贡”删掉“东宫”,继将“凡外国船只非系进贡之年,无故私来贸易者,该督抚即行阻逐”删去⑧《(康熙)大清会典》卷72《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通例》,第3701—3706页;《大清会典(雍正朝)》卷104《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通例》,第6949—6954页。。冈本隆司、廖敏淑藉“互市”批评“朝贡制度”忽略了通商,以致无法代表清代的对外关系⑨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第3—24页。。然而“互市”其实要到《嘉庆会典》才于礼部主客司中“朝贡”载“余国则通互市焉”,始将“互市国”与“朝贡国”明确区别①[日]松浦章:《清代中国の朝贡国と互市国》,《或問》第32号(2017),第1—12页。。换言之,“互市”的出现及其与“朝贡”的划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并且长期与“朝贡”存于模糊状态。所以费正清的片面选取正忽略了发展演变,引起各种争议。
费正清欲藉会典建构“朝贡制度”,但他只选取了当中礼部主客司与理藩院的部分,导致讨论聚焦在贡物、回赐等所谓“贸易”的问题上。在时间的纵深上,费氏主要依靠《康熙会典》来分析,缺乏对五朝会典的系统分析与整理,漠视文本差异所反映的制度、概念变化,终使得对“朝贡”的范围、定义至今仍然无法清楚说明。
费氏其后也曾于《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国的世界秩序》等著作提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等内容,以丰富其意涵②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1842-1854,pp. 23-38;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pp.1-19.,但由于缺乏对史料的重新梳理,仍延续着“朝贡”作为古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媒介,“朝贡”为维持朝廷的威望而使得对外贸易从属于此体系等观点。这大抵反映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作为近代学术体系转型的产物,无论从其学科分类、观点及采用的史料,深受当时学术潮流所影响。而所引的史料又大抵以会典为主,过于单一化,造成了对“朝贡制度”的定义与范围含糊不清,漠视制度长时间演变的差异,引起目前“朝贡制度”研究的种种争议。
虽然费氏“朝贡制度论”一开始就存在不可挽救的结构性缺憾,但若回归当时的学术脉络来说,他却提供了最为完备的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制度解释体系,这亦诠释了何以当今学界仍然惯用“朝贡制度”这一概念。滨下武志虽然打着修正“朝贡制度论”的旗号,但却是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朝贡贸易圈”③[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44页。概念。费氏“朝贡制度论”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尝试,在近代知识体系缔造出处理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知识的路径,同时也为学界展示出了解“东亚世界”的一种面向,并影响至今④John King Fairbank & Edwin O. Reischauer ed.,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89,pp.199-201.。但正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指出其理论局限,并透过近年出版的韩国、越南、琉球等地的域外文献,附以故宫档案、奏稿文集等史料,不仅要从皇帝、国王、外国使节、主事官员等多角度思考“朝贡”所涉及的范畴及其衍生的意义,同时更要“多国度”地整体呈现“朝贡”的真象,才能弥补史料单一化所带来的问题,从结构上修补不足。
结 论
“朝贡”自汉代始形成域外政权对中国臣服的意涵,并落在正史、史部地理类、政典、礼典仪注等四类传统经史的范畴。但随着晚清民初国族意识的形成,中国的历史知识面临从传统至近代的转型。而转型过程中,“朝贡”作为对外关系的知识,却失落于本应关系最接近的“中西交通史”。反而由于被视作引发中西贸易冲突的外交制度,而落在“中国近代史”的领域。费正清的“朝贡制度论”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出现,当中的观点正反映当时的学术脉动,诸如重视“朝贡”当中商业贸易的性质,以会典为依据。但因此导致其“朝贡制度论”存在根本性的缺憾,诸如对“朝贡”的定义模糊不清,以会典为史料令研究视野过于狭隘,集中于“贡物”与“回赐”上,忽视了礼仪、文化交流等种种范畴。
因此,本文希望“正本清源”,指出“朝贡制度”作为近代学术概念于形成时,其定义、范围、史料等根本性问题,以利日后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