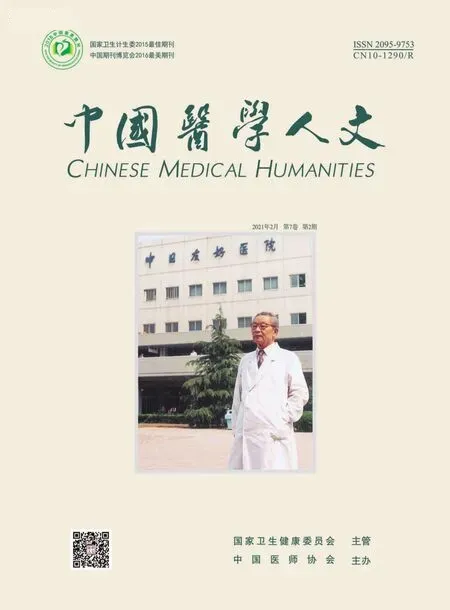唐代政府对疫疾的应对举措
2021-01-02郑言午
文/郑言午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疫疾低发期,这一方面与当时社会安宁稳定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同时也离不开当时政府对疫疾的重视以及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对唐代政府的疫疾应对举措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对当今的疫病防治有着借鉴意义。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夺去了人类数以万计的宝贵生命,造成沉重的伤痛和难以估量的损失。我国历朝历代都无一幸免饱受疫病之苦,先民们和瘟疫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任何时期,政府官方都毫无疑问地是疫病防治的核心力量,历史上几次大疫之所以危害惨烈,正因为其发生于无政府或是政府控制薄弱时期,如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当时皇权虚弱无力,地方豪强势力兴起;1232年汴京大疫死亡近百万人,正值金政府刚南迁至汴京,政局江河日下;明崇祯年间疫病肆虐,背景是全国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政府威信扫地。而学界普遍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疫病低发期。这一方面与当时社会安宁稳定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同时也离不开当时政府对疫病的重视以及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唐代政府的疫疾应对举措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对当今的疫病防治有着借鉴意义。
政治应对举措
建立报灾制度
众所周知,第一时间对疫情进行控制可以将其危害降至最低,由于古代缺乏先进的通讯方式,信息传递存在一定的时差,故如何对地方突发的疫情进行及时上报,是政府可以迅速开展救济并控制疫情的重要前提。唐代中央政府为了能保证及时掌握灾情并迅速制定救灾措施,建立了逐级信息奏报与核实机制,《唐律疏议》规定:“其应损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谓里正以上。里正须言于县,县申州,州申省,多者奏闻”。对于隐瞒、缓报和谎报的官员,依法严厉惩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若致枉有所征免,赃重者,坐赃论”1。对于重大疫情和地方的应对情况,皇帝有时还会要求直接上奏,如太和六年(832年)剑南至浙西的大疫,文宗痛感百姓受苦,要求“中外臣僚,一一具所见闻奏,朕当亲览,无惮直言”2。
下诏赈灾恤民
在大疫发生后,皇帝通常会下恤民诏,一方面通过大赦、罪己等方式来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制定各项应灾措施,颁布施行,如文宗《拯恤疾疫诏》云:“自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屡降诏书,俾副勤恤。发廪蠲赋,救患赈贫,亦谓至矣。……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馀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国用常限,或虑不充。其度支盐铁户部及百司,除诸军衣粮布帛及宗庙祭享切急所须并常科用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别举处分。”3此诏令所载的疫灾后的应对措施较为详细,首先,对于一门都死尽的家庭,由官府提供棺木并收殓埋葬,对于疫死一半和疫死一半以上的家庭,分别给予不同级别的税钱减免;其次,派遣官员到灾区进行救济,并巡视灾民情况;再者对于家人死尽,十二岁以下的未成年者进行了特别关照,由地方官劝其亲戚收养,并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最后,减免疫区的赋税徭役,缓解地方救灾压力和百姓生活负担。唐代类似的救济政策还有很多记载,如永淳元年(682年),关东大疫“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2;长庆年间浙东地区疾疫,穆宗“诏赐米七万斛,使赈饥捐”4;元和二年(807年),对去年淮南江南等疫灾区实行“租税节级蠲放”3;太和九年(835年),“淮南浙西等道皆困于饥疫,……赐粟五万石”5;开成五年(840年),“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4等等,这些应对举措与皇帝的自我反省相结合,尽可能地减轻疫灾对百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
举行傩礼禳灾
傩源自上古时代的原始祭礼,《周礼》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6;《吕氏春秋》曰:“命有司大傩,旁磔”;高秀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7,可见傩自古便具有驱疫的含义。傩礼作为官方政治性宗教礼典,到了唐代亦不例外,《新唐书·礼乐志》详述了当时宫廷傩礼的具体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人员安排和牲品摆设等,其中描述:“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近仗入陈于阶。鼓吹令帅傩者各集于宫门外。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4,可见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驱疫。这一套傩祭流程实际上延续了周代的“国傩”和汉代的“大傩”,虽然在唐代也有民间傩礼,且存在世俗化和娱乐化的趋势,但官方傩礼的重要地位依然不可忽视,国家政府通过这样盛大的方式满足了民众渴望远离疫病的心理诉求,并起到了人文关怀的作用。
地方自行救灾
与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举措不同,地方官员作为“父母官”,无论是为了真心保护百姓,还是出于自身政绩的考量,在疫病流行时往往也会积极组织人员救治。例如《太平广记》载:“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醼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坐。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8文中李吉甫出镇淮南期间刚好遇上地方大疫,日夜忧心。后听从建议请来道士王炼师,在城内摆“大镬巨瓯”煎药,分发给民众,方解除疫情。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时,社会上迷信巫祝,“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2,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元和初年,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发生大疫,“州疫旱,人徙死几空”,王仲舒出任刺史期间开展自救工作,五年之后,“里闾增完”4。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地方官员的积极作为是社会疫病防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医学应对举措
遣医赍药诊治
由于民间医疗条件有限,故在大疫之际,皇帝会下诏让宫廷医师去地区巡诊、发放药品。例如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地区疾疫,太宗“命医赍药疗之”2;太和六年,剑南至浙西诸道疫病肆虐,文宗下诏“疫疾未定处,官给医药”2。此外北宋类书《册府元龟》中还补充有六条中央遣医的记载,分别在贞观十五年(641年)、贞观十六年(642年)、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以及景龙二年(708年)。复原的唐《医疾令》载“诸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疮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9,可见太医署也会对庶民进行医疗救助。有学者认为将这些中央遣医赍药的行为是偶然事件,属于特例,“主要是在出现大规模传染病时用来体现皇帝体恤关怀之情”10。这样的说法亦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否认,唐代中央派遣医师赍药诊治的作法,对防治疫病扩散和保护民众健康都起到了积极效果。
设置“病坊”避疫
“病坊”最初源自佛教中的“悲田养病坊”,后得到国家重视,“置使专知”,并进行财政资助。从寺办寺养成为寺办官助,演变成具有官办性质的慈善机构。由于得到了国家支持,“病坊”发展十分迅速,自两京周边推广至全国各州,无论是在收留规模,还是医疗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成为了唐代社会防疫的重要保障。但到了玄宗时期,“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11。“病坊”在唐中后期不仅仅只收留病者,还会容纳乞丐、老幼、贫困者等,“兼‘收容院’‘养老院’‘孤儿院’等诸种功能于一体”12。如此一来,“病坊”里面人员混杂,若有患者藏匿其中,反倒会加速疫病的扩散,存在一定的隐患。不过,中国自秦代就建有“疠迁所”,宋代亦有“安济坊”,隔离避疫的传统一直存在,故推测唐代政府应当也有这样的观念。
收埋暴露骸骨
唐代皇帝常下诏掩埋战后或灾后散落的无主尸体,如《唐大诏令集》集中收录的收瘗诏令:武德三年(620年)《收瘗隋末丧乱骸骨诏》、贞观二年(628年)《掩暴露骸骨诏》、贞观四年(630年)《瘗突厥骸骨诏》、贞观五年(631年)《刬削京观诏》、贞观十九年(645年)《收葬隋朝征辽军士骸骨诏》、天宝元年(742年)《埋瘗暴露骸骨敕》、至徳年间《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宝应年间《收瘗京城骸骨诏》13。上述八篇诏令以收埋军士骸骨为主,而永淳元年(682年)《埋瘗关中疫疠死者诏》、宝应元年(762年)《恤民敕》、太和六年(832年)《拯恤疾疫诏》则主要是收埋因疫疠而亡的民众骸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尸体腐败后会滋生大量细菌,容易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人畜共患病、虫媒病等各类传染病,通过蚊虫、老鼠、蟑螂等生物传播,以及污染周围的空气、土壤、水源等方式致使疫情蔓延开来,故对尸体进行及时有效地掩埋处理,无疑会大大降低疫病流行的风险。只是唐代政府这种收埋暴骸的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标示德政”,缓和社会间的一些矛盾,但间接地起到了防疫的作用。
颁示药方天下
这主要体现在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七日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八月又敕:“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德宗也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二月十三日,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11。正如《颁广利方敕》中所言:“当使疾无不差,药必易求,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13,广济、广利二方使医药知识在民间得到了极大地普及,为百姓防疫治病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此外,“百姓亦准《医疾令》合和药物,拯救贫民”9也可以看出唐政府对百姓的医疗照顾,这对控制疫病的流行大有裨益。
结语
综上可见,唐代政府有着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官方医疗机构,应对疫情不仅有宏观上的政策调控,也会进行具体的医疗救助,虽然有些手段例如举行傩礼禳灾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整体上来看既有疫前预防,又有疫后应对,不失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疫疾应对举措。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官方医疗机构根本性质还是为皇权服务,皇帝虽下诏恤民、遣医诊治、设置“病坊”、制定药方,但这些措施多为宏观上的调节,很难照顾到社会上每一个个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标榜德政,并没有制度化、常规化和体系化,实际执行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疫病流行时几乎无人能置身于外,特别是社会上的每一个民众,他们是面对疫情最直接的受害者,更需要在灾难来临时团结一致,共度难关。无论出于主动或是被动,社会力量对疫疾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政府救济的不足。而正是因为二者力量之间的有机统一,才使得唐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疫情低发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