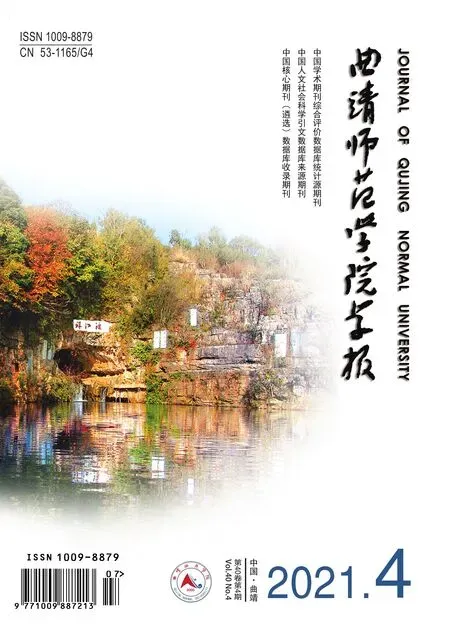论柳青《创业史》的政治觉悟和农村妇女解放的关系
2021-01-02孔莲莲
孔莲莲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关于《创业史》所呈现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多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创业史》中女性的真实状态,认为《创业史》中的女性解放呈现的是一种“假象”。女性主义批评是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长期发展的产物,当时的西方女性已经在社会层面上基本完成了针对男权社会的平权运动,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女性主义理论根源于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在思想文化层面对男权文化的反叛态度,即中产阶级女性在已经充分实现生存和发展等权利的状态下在为思想自由而战。从这种背景来看,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和《创业史》反映的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状况是极不匹配的,《创业史》里的中国农村女性,此时正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之后的土改、合作化运动等政治生活,迅速实现从封建文明向现代文明地蜕变,现代国家正在从政治层面促成农村妇女现代意义的解放,这种以政治“制度性”的方式完成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状态的剧变,和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渐进式改变在呈现方式和内在特征上有诸多不同。所以,以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去阐释《创业史》里的中国农村女性解放状态,并得出“在女权主义理论和人性话语的观照下, 1950~ 1970 年代的合作化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是男权意识与极左政治合谋压迫下的附庸和第二性, 只有妇女解放之名而无妇女解放之实的神话, 在女性意识的匮乏、妇女形象的改写和负担的加重等方面成为不攻自破的肥皂泡”[1]的结论观点就显得悲观和消极了。
更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从农村女性的真实境况中考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政治运动过程中,妇女们在婚姻层面、社会权利、社会分工等领域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而更深入的思考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对农村妇女解放带来的多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最终根源来自于私有制,而经济不独立,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依附于男性,则是女性受男性压迫的主要因素。恩格斯断言:“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能实现。”[2]。毛泽东在1955年说过:“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才能实现才能让广大农村妇女真正实现解放”。[3]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中国全面进行三大产业的改造,从私有制开始向公有制过渡。《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就是讲述的这个时期,陕西省渭北平原下堡村的这一次公有制改造对不同农民阶级的生活和灵魂触动,以及造成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改变。本文以《创业史》中的四个主要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考察她们在这次公有制改造中的真实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此思考更为普遍的农村妇女解放问题。
一、现代女性徐改霞
《创业史》刚出版后,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徐改霞这个人物形象。如柳青所言:“有些读者来信对改霞的看法,和我的意图有相当距离。首先,不是为了写恋爱而写改霞,是为了写梁生宝而写改霞”[4],柳青多次谈到,他塑造改霞这个人物,并非是为了让她和梁生宝结婚,从一开始,柳青就认为,徐改霞和梁生宝不合适,徐改霞一定会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而徐改霞的这一形象,也成为50年代,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农村女工的典型。
一直以来,关于徐改霞身上超前的现代女性气质是评论界批评的焦点。这种现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是不是作家主观想象出来的?柳青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特别注重描写人物成长的“典型社会环境”。改霞是农村中少有的积极跟党走的女青年,正如柳青深情地表达:
“改霞啊!改霞啊!她也许是汤河上顶俊的女子,也许并不是哩!要不是她参加社会活动,要不是她到县城去当过青年代表啊,要不是她在黄堡镇一九五一年‘五一’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过话,那么,一个在草棚屋里长大的乡村闺女,再漂亮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名气和吸引力呀”。[5]
徐改霞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的推动者是现代国家体制下的政治活动,如果落实到个人应该是下堡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郭振山,改霞的退婚成功,在村里上小学,甚至到最后,决定离开农村去北京做铁路工人,都是徐改霞积极实践了郭振山的政治引导而实现的身份蜕变[注]关于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女性和男性的关系问题,有很多研究,如:“女人追随男人,而男人追随革命、追随党,因此女人实际上以追随男人的名义追随革命、追随党。这是20世纪50-70年代红色叙事最经典的模式。”见王宇著:《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版,第86页。。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徐改霞选择城市道路是下堡村共产党员郭振山的引导,而徐改霞认清郭振山的自私面目,主动放弃西安国棉三厂的招聘,与郭振山渐渐疏离,则体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政治觉悟上的敏锐和坚定,此时,她在公共领域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显然都超越了她的人生领路人郭振山,有着和梁生宝相比肩之势。而改霞到最后毅然离开农村,选择城市,走城市工业化之路,则是她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表现出从认同梁生宝的政治方向,到自觉地选择一种不同的人生道路的独立意识。
柳青用更大的笔墨表现徐改霞在婚姻爱情上的现代气质。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乃是传统观念下订的娃娃亲,建国后,国家推行了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徐改霞顺应国家的婚姻政策,完成了退婚。徐改霞的这个行为让我们想起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笔下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女性,其婚姻自由权应该发生在1950 国家《婚姻法》颁布之后,这和早在20世纪初,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知识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后者抗婚的精神动力是“新文化”,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抗婚的精神动力则是“新政治”。徐改霞先进的觉悟并没有获得农村人的广泛理解,比如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就对徐改霞的退婚很不以为然。正是在这一点,出身农村的徐改霞表现出不一般的勇气。在对待和梁生宝的感情问题上,徐改霞依然是积极主动的一方,和梁生宝的三次约会,都是她主动寻找机会和男方见面。最后,徐改霞决定放弃梁生宝,奔赴城市前,也是她衡量很久以后的主动选择,有一段心理描写,被很多学者引用:
“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6]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改霞思想意识在当时确实具有超前性,但是她的这种现代意识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改霞多次去县城参加活动受影响的结果,比如她最后一次主动见生宝:“改霞决定:当她和他一块在田间小路上走着的时候,她将学城里那些文化高的男女干部的样子,并肩走路,而不像农村青年对象一前一后走路。”[7]可见,改霞的现代意识是在她从事的社会工作、所受教育、所见世面以及对城市文明的追慕等环境下共同形成的,归根结底,还是现代国家给一个农村女性带来的发展契机。
当然,在徐改霞身上依然可以看到传统观念对她的影响,如她在面对自己的爱情问题上的羞涩之情,她看不上白占魁的女人李翠娥,并用世俗的标准评价她“烂脏”,收到永茂的情书的娇羞和愤怒,甚至把情书交给郭振山,这些特点都体现出一个农村姑娘不能完全摆脱旧文化的影响,这正体现了徐改霞这个人物形象乃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艺术真实性。
二、劳动妇女刘淑良
刘淑良和徐改霞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总体上,柳青是要将刘淑良塑造成为一位优秀农村妇女的典型。
刘淑良从小就在家帮父亲耕作农忙,后来嫁到范村,依然是一个重要劳力,刘淑良的外貌很有特点:“红红的脸盘、宽阔的前额、剪整齐的短发、挺刚强的后脑勺,浆洗得很干净的昌蓝衣裳和薄底的方口鞋”[8],这是一个劳动妇女的相貌,与改霞相比,她没有改霞的美貌,更不像改霞有柔软的手和白皙的脸,而是一副朴实又干练的样子。有万的岳母在向梁生宝的母亲介绍刘淑良时,也特别强调她的能干和懂事:“淑良在家里种地,干活可泼辣呢。她跟爹学会了犁地,连撒子都会哩。她就是没吆过车,挑挑担担,也顶个男子汉……”[9]
然而刘淑良不光是一个劳动能手,她也热衷公共事务。在范村的时候,她就组织土改与互助合作,无论是村上,还是婆家,都对淑良的为人和工作甚为满意,后来离婚回了娘家竹园村,她也快速成了互助合作的骨干。关于淑良热衷公共事务,应该源于前夫范洪信的影响甚至引导。范洪信在县城里读书,到后来念大学,一定是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更重要的,范洪信的同学里面热衷政治的人很多,比如后来负责合作运动的干部牛刚就是范的中学同学。可以想见,经常奔走于县城和丈夫见面刘淑良,必然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让她渐渐摆脱了农村较传统的观念,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刘淑良后来在农村念书,也是丈夫的鼓励。当然,旧社会刘淑良的家庭所受地主的压迫,也是她对新政治充满热情的原因。
有研究者认为,刘淑良在婚姻领域,并没有徐改霞那样的自主意识:“从自主性上来讲, 徐改霞是主动抛弃了包办婚姻的男人, 刘淑良则是被男人抛弃后才提出离婚的”[10]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说她的第一次婚姻表现为对家人意见的遵从和被动接受,那她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则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是离婚。按照旧伦理,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显然不符合传统女德标准。丈夫因为妻子文化不高,将来不能一起留在城里工作,渐渐不回家,刘淑良主动去了城里,看到丈夫的真实情况:“淑良心里就思量:哪个村里不是鸡叫?那个村里不是牛嚎?那个村里不是共产党领导?她和一个大学生别别扭扭拉扯在一块有啥好?她和一个庄稼人情投意合一辈子有啥不好?迁就人家,才不合她的心思呢!”[11]。可见,刘淑良并非没有自我的旧式妇女,她不愿意没尊严、不被尊重的和丈夫生活,于是回来后主动提出了离婚。之后,在婚姻问题上,她的态度几乎和改霞如出一辙,如果不能嫁到自己合适的伴侣,宁愿终生不嫁,这也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所具有的态度。刘淑良看上梁生宝,不顾传统观念,自己主动跑到了蛤蟆滩,被众人围观谈论:“甚至于听见过女人们在草棚屋外面说话的声音:‘嘿!竹园村这女人寻对象这么文明,自己跑来寻咱主任!……’是的!刘淑良既然有勇气到你们蛤蟆滩来,她就不怕人看,也不怕人说!从前范村的这位互助组长总是带着老练的自信的大姐风度,淡淡地笑着。”[12]
这正是刘淑良的“心胸大”,梁生宝最为看重她的这点品格,因此有人说刘淑良性格中带着传统女性的顺从。笔者认为不能把这个问题这么狭隘的理解,“心胸大”于私而言,不计较,不敏感,有利于家庭和谐;于公而言,“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大境界和大格局,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文明中,无论男性或女性,“心胸大”都是一个优秀的品格。
有一个问题是一直没有研究者讨论,为什么离婚的刘淑良能够得到农村人的认可,甚至是梁三老汉的认可?想想梁三老汉对退婚女子徐改霞的偏见,一个离婚女人难道比一个退婚女人更光彩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刘淑良和梁生宝结合的时候,已经是1954年了,从建国后1950年改霞的退婚,到此时,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婚姻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说明一点,政治力量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广泛而深入的。
应该说,刘淑良是农村妇女解放的典型,这一形象很好的诠释了农村妇女解放的途径,跟随国家形势,参与公共劳动,实现婚姻自主。
三、随军女性梁秀兰
在《创业史》所有的女性中,梁秀兰是生活比较顺利的。在从旧时代向新中国的过渡中,梁秀兰似乎实现了无缝连接。梁秀兰生活在一个母慈父正哥哥政治觉悟很高的家庭。秀兰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她善良又朴实的品质。秀兰是蛤蟆滩最早的女共青团员,她还是村里少有的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学生。从这两点来看,秀兰的生活受惠于新政权的发展,并自觉跟从新政权的轨迹发展。毋庸讳言,她的政治觉悟来自于哥哥梁生宝的影响。秀兰后来因为婚姻的原因,离开了蛤蟆滩,随军去了东北吉林,但是从生宝和刘淑良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秀兰在东北做军属有点闲,她更渴望回家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建设。
秀兰的婚姻是小说里从旧式状态顺利地转变为新式婚姻的典范。秀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定了娃娃亲,未婚夫杨明山是一名志愿军战士。更可贵的是,杨明山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英勇受伤,成为民族英雄,提升为炮长。在众多农村女性中,秀兰应该算比较幸运的,她没像改霞那样,遭遇一个不满意的未婚夫,必须通过退婚的方式来彰显新女性的勇敢。那么?是不是梁秀兰接受了父母定的娃娃亲,就代表着她屈从了旧传统?这是许多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比如有论文观点认为:“虽经作品全力歌颂, 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看, 梁秀兰这个角色是不可取的。”。我们怎么看秀兰的婚姻选择?可以从改霞的角度来看看她是如何看待秀兰的志愿军未婚夫的:
改霞从心眼里偷偷羡慕秀兰:爱人是朝鲜前线立了战功的英雄,自己在家里安心得意学文化。有这样的爱人,大概走路时脚步也有劲,坐在教室里也舒坦,吃饭也香,做梦也甜吧?有这样的爱人,等他十年八年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改霞恨死了村内一些庸俗的人,竟说她和周村家解除婚约是嫌女婿不漂亮。社会上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拿自己的低级趣味,忖度帮人崇高的心情。[13]
可见,改霞非常羡慕秀兰的爱情,改霞并非执意要和旧制度对抗,她主要是不满意自己在旧式婚俗下的订婚对象。因此可以推断,秀兰也并非执意接受旧式婚俗,她是因为自己的爱人是国家的英雄,是她心目中倾慕之人,是她真正爱的人她才坚持的。实际上,从她经常奔波于区里的邮局查信件,就能看出来秀兰对自己的未婚夫有多喜爱。柳青让这个幸运的姑娘在旧式的婚俗下,找到了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志愿军英雄,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是作者对秀兰的爱戴。
然而,秀兰的婚姻和爱情还是经历了考验,未婚夫在战争中受伤了,毁容了。在这个时候,很多周围的人都认为秀兰的过激表现是因为她嫌弃了杨明山,就像欢喜母亲安慰秀兰:“好在生米还没做成熟饭。他杨明山日后从朝鲜回来,你再看。不合适,咱另瞅对象!”[14]然而,秀兰和改霞一样,并没有那么浅薄,只在意对方的相貌,而男人的品格才是她们最在意的。她毅然决然地决定在未婚的状态下去照顾婆婆。有研究者这么看待秀兰的行为表现:
秀兰的行为曾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所倡导的, 从倡导妇女嫁给老干部、嫁给战争中的英雄和残疾人, 到嫁给因公负伤的伤残人,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现象。这种为传统妇德披上美丽政治 外衣的做法, 文本中几乎得到所有人物乃至作家的一致赞赏。在这个角色身上。‘新道德’对妇女的要求与传统的妇德惊人的一致。[15]
将秀兰的行为理解为富有牺牲精神的“大义”之举,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服,这一点应该没错。但是,研究者可能忽略了秀兰的个人情感倾向。文中有一段反映秀兰心里的文字:“婆婆思念儿子成疾,想看看她这个宝贝儿媳妇,她却在过门的旧乡俗上思量!简直糊涂!怕生人看做啥?秀兰想:她是光荣的志愿军的未婚妻,谁爱看谁看!看!看!看!她就是她!她将在北杨村表现出磊落、大方;她绝不允许女性的弱点,在她的行动上显露,惹人笑话,给亲爱的明山哥哥丢脸!”[16]从这段话里,体现了秀兰在一个除旧革新的过渡时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需要巨大勇气的,这个勇气一点也不亚于改霞的退婚。是什么给了她这个勇气?一方面来自于新中国政治背景下的一种女性的觉悟和新时代的风尚,更重要的一面是爱情给她的力量,秀兰是因为深爱着这个志愿军英雄,才毅然冲破旧风俗,去婆婆那里照顾她。从这个角度来说,秀兰放弃上学去婆家生活的做法,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在婚姻上的主体意识。所以,并不能因为秀兰婚姻的顺利,就否认她是一个被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启蒙过的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
四、自卑女性赵素芳
素芳在作品中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素芳小时候出身于一个地主之家,本来应该过得扬眉吐气,但是父亲因为被人拉着吸大烟上瘾而家道中落,村里人和亲人们瞧不起父亲,母亲也和邻居叔叔相好了,“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17]素芳在一个很不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其价值观也是歪曲的,必然形成一定的性格悲剧。
果然,正值花季的16素芳,被一个饭铺堂倌引诱怀孕,母亲被迫将其下嫁给了憨憨的拴拴。本以为到了婆家生活会随心些,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个封建顽固的公公,瞎眼公公为了驯化素芳心性,不但打掉了孩子,而且变本加厉:“由他指导着,由老婆帮助着,让栓拴用顶门棍,有计划地捣过几回”[18],从此,机灵的素芳的心性变了,“规规矩矩”跟拴拴过日子。可以想见,素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怎样的身心折磨,她应该是农村中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妇女典型了。
正常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出台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和现代性观念,素芳可以实现一定的解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封建老顽固的公公瞎子王二并不让素芳参与公共活动,哪怕是一次群众会,这样,素芳依然保持了封闭的状态,与已经革新的世界没有什么交集。实际上,素芳当时能够接触到的思想先进的人就只有梁生宝,她暗恋梁生宝,但是当梁生宝发现她的动机时,却严辞拒绝并教训了她,让这个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的弱小女子仅存的生命亮光熄灭掉。生宝有一次在村里的大会上把素芳作为一个“伤风败俗”的女性教训,素芳此时,表现出一个下层女性的反抗精神:“向村干部梁生宝哭诉,她还没有解放。她没有参加群众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要求村干部干涉”,这是素芳对生宝一种情感上的吁求,更是一个被压迫者向解救者的吁求,但是,“生宝硬着心肠,违背着他宣传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主张,肯定地告诉素芳:暂时不能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将来看社会风气变好了再说。”[19]梁生宝作为一个具有极高政治觉悟的男性,党的好儿子,却不能跳出男权思维和封建伦理,并不能理解一个底层女性身心的悲苦,这是梁生宝的局限性,也
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男权化倾向。[注]关于此观点,如王宇认为,在17年红色叙事中,“性别主体依然是虚位状态,呈现在文本中的主体不过是主体的镜像,而政治父亲的身份却借女儿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参见王宇著:《性别表达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版,第93页。更重要的是,梁生宝对素芳的态度,加重了素芳的自卑感,试想一下,被一个心中最神圣的倾慕者所瞧不起,素芳会有多自卑。而之后素芳去姚士杰家伺候月子,又受到富农姚士杰的欺侮,这于素芳来说,又是一次心灵的创伤,无论她内心深处多么渴望男人的滋润,但是姚士杰,依然因他的阶级属性和男人属性给素芳留下了深深的伤害。
而真正让素芳的命运发生转变的事件是合作社在农村的全面开展。农村的私有制被合作化运动取代,国家权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摧毁了压在素芳身上最大的大山——公公死了。此时的她参加了妇女小组学习,也慢慢有了政治觉悟,然而过往的黑历史依然让她在众多人群中抬不起头来:“她低下头把脸埋得很深很深。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她的男人拴拴从山里回来以后退了组,和毒辣的富农搭火种地。尽管这事素芳不愿意,是顽固的瞎眼公公坚持,但当时她正在富农家熬汤,人家会怎么想呢?羞耻啊!羞耻!要是当场有个地缝,素芳愿意进去。”[20]
和以前工具人的无望生活不一样,素芳此时的自卑来自于政治觉悟提高之后对不觉悟时期行为的羞耻感。知耻而后进,这种羞耻心,正说明了此时的素芳开始慢慢转变。
柳青在塑造这个底层的农村妇女觉醒时,除了抓住她的惭愧之心以外,在外在表现上则抓住了素芳的哭。素芳为什么哭?素芳哭在公公去世的时候,不知道的人以为素芳哭公爹,知道的人才知道她哭的是自己的亲爹在旧社会所受的欺辱和陷害,哭的是自己家庭的卑微,也是在哭自己的命运。这是在新旧对比的巨大转变时刻,一个渐渐看到新社会曙光的农村妇女思想转变的一个情感表现:“她在被子里又哭起来。她呜咽着。她哪里来的这么多眼泪呢?”这场痛彻心扉的痛哭,是素芳向压迫她的公公的告别,更是给旧我的告别。在合作化的大潮中,素芳被卷裹进来,对于这种从来都被人低看,又自我低看的人来说,政治制度层面的认可为她的自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就像王亚梅安慰素芳的:“为什么这样伤心呢?嗯?不要那么冤嘛!现在你解放了。你爱人在男社员里是一级强劳力,你自己在女社员里也是一级强劳力。你俩在农业社劳动,日子会过好的! 哭得眼皮浮肿的素芳,哑着嗓子说:“我一定在农业社好好劳动。王同志放心!我哭是为以前的事!”[21]
这么来看,真正尊重素芳的人,是来自于女性的力量。这也说明了男性作为女性的启蒙者本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像其他三个女子一样获得自己想要的婚姻,她还没有实现婚姻的自由,这也说明了女性解放的道路在建国之初的不彻底性。但是,从人格的层面上,素芳较之她人生的其他灰色时刻,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人的尊严,这是素芳这样的底层妇女不小的进步。
结 论
从以上农村妇女解放的途径,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农村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中完成的。中国共产党以制度的方式强行干预了中国农村妇女自发的解放进程,让她们迅速进入了现代国家建设者的行列。但是,这种政治的干预性也为女性的主体性建构带来了一些弊病,就像福柯说的:“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或者,像古代那样的情形,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基础之上。”[22]女性在政权干预下实现了一定的解放,也产生了一定的“奴役”。比如,妇女们可以和男性“同工同酬”的参加公共劳动,但是由于过于突出生产的重要性,忽略了女性在身体机能上与男性的不同,更没有关注到女性在参与了公共劳动之后,在家庭生活中依然担负着重要的劳动量,而这种“增负”的状况在1950年代妇女解放进程中一直被忽略。因此,像刘淑良这样既能像男人一样进行公共劳动,又能在家里做女工的农村妇女,是被柳青和梁生宝们看为“合适的对象”。
其次,农村妇女的现代性之路都是在男性觉悟者的引导下完成的,郭振山之于徐改霞,范洪信之于刘淑良,梁生宝等之于梁秀兰,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党的好儿子们”之于素芳等广大农村下层妇女。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政治一体化的年代,依然看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当然会造成农村妇女的觉悟,这是一种“人”的觉悟,而非“女人”的觉悟,这也是为许多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创业史》中的女性,发现她们并没有真正的性别意识的原因。
再次,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呈现很多未完成之态。这里所谓的未完成之态是相对于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力量而言的。即使是改霞这样的女性,依然能看到她在评价李翠娥这样的女性时,带着传统男权伦理的痕迹,而她自身的很多思想和行为,也没有摆脱传统道德观的束缚。而像素芳这样的底层女性,她们背负的旧文化毒害更为巨大,她们在婚姻自主,人格独立等方面,与此时的改霞等人相比,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妇女解放之路任重道远,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中国的妇女解放之路表现出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而这种“本土”化的探索,于研究者而言是更为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