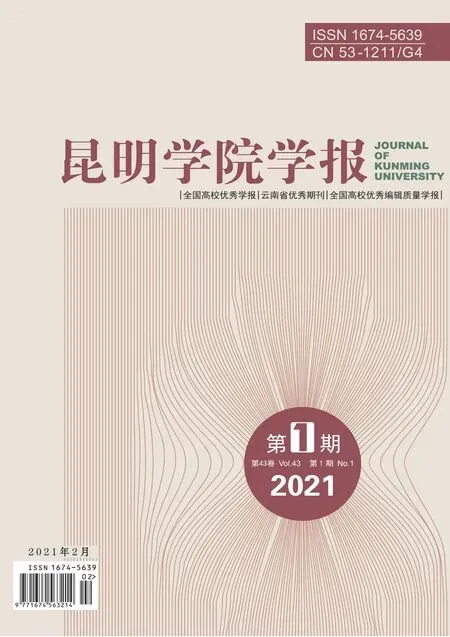《咏怀·西方有佳人》和《洛神赋》的对比分析
2021-01-02何霭茜
何霭茜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在魏代后期,政治上出现了曹魏皇权的维护者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司马氏篡夺曹魏之心昭然若揭,而且斗争也没有持续太久,司马氏很快就夺取了实际的统治权。而正始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在邺下诗歌高潮后面临了群体创作风气的衰微,诗风趋于模糊、肤浅的局面。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可见阮籍、嵇康二人在正始时期的创作犹如两座异峰拔地而起,从正始时期诗学整体衰微的“死水”中脱颖而出。也无怪乎钱志熙在《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这样评价:“尤其是阮籍,他出现于魏末,犹如后来的陶渊明之出现于晋末,真正可以说是一种奇迹。”[1]148
但是在阮籍的创作过程中仍可以看到许多所处时代影响的影子。“魏代诗歌创作相对于前后的邺下与太康,最突出的特点是群体风气衰落,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自然化的个体创作的状态。”[1]149钱志熙的这种分析也给阮籍、嵇康富有创造性的个体写作更多理解的角度。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无疑是鸿篇巨制,而且是他的“忧思”之作,是“个人的带有隐秘性的写作”[1]149。导致他“感激生忧思”的因素很多,有当时的时事政局中司马氏的夺权篡位带来的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有他对社会中种种见闻所持的批评态度,也有他崇敬庄老之学后哲理思索等等。就内容而言,钱志熙将其大致归为以下几类:“从直抒感激忧思之怀开始,进而为荣衰无常主题、自叙生平、平居忧思怀人、登览或怀古、悯世刺时。”[1]164进而认为这其中体现了逻辑上的发展层次,并从现实的层次继续向塑造超现实的理想人物与理想境界发展。
在阮籍的五言《咏怀》诗中,其十九的《西方有佳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不少选本中都没有选录该篇,如《昭明文选》就没有选录。钱志熙言:“然论其近源,实出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盖拟其句意而易其词也,为魏晋间诗人常用之法。”[1]166并将这首诗的整体构思与形象归为受到《洛神赋》的影响。从两首诗的内容和结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承继,比如在内容上,两首诗都是铺展开来叙述神女的翩然之姿和美好的品格,然后写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最后抒发神女若即若离,可遇而不可求的怅惘之情,都是先铺陈叙述最后抒情表达。但是有不少人直接将其看作是《洛神赋》的简写版,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两首诗还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一、 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差异
从《西方有佳人》和《洛神赋》的抒情主人公在诗中的形象来看,两首诗是存在风格上的差异的。在《洛神赋》中,抒情主人公表现得积极而热烈,面对这样一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神女,他立刻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真挚的情谊,对神女的渴慕与追求一览无余。“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而要之。”这一句中的 “通辞”和“解玉佩要之”,是全赋在对神女的登场进行若干描述铺陈后的首先出现的两个动作行为描写,发出者都是抒情主人公,可见抒情主人公在这次相见中把握了主动权。随后,眼见神女也给予回应并许下诺言,却出现了对主人公内心思考作刻画的诗句:“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面对神女的青睐,抒情主人公明显产生了疑虑,给出了更多地回应,即“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在后文的叙述中,我们都能看到洛神和主人公在行为、情感上的互动。虽然在中途主人公有过情感上的收敛,但是从曹植的描写视角来看,读者受众始终是从上帝视角俯瞰的,对于主人公内心的爱慕、纠结和行状上的反复我们都能通过内心描写得到解答。此外,文末的“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一段中主人公对洛神的爱慕、思恋可谓一览无余,因人神不能相恋相守的痛苦哀怅和辗转反侧的愁思都宣泄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洛神赋》中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表达始终是恣肆而不加约束的,犹如大江大河的浪潮奔涌而过,无遮无避。
但是在《西方有佳人》中,对神女的容貌姿态进行描写后,“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率先投来流转目光的人是神女,而抒情主人公在仰慕已久,渴求已久的人终于相遇甚至目光相对时,却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这真正是屈原所说的“目成心许”的境界,一切尽在不言中,在眼神的瞬间的交汇中,抒情主人公与神女的心靠得那样近,然而他在飘飖恍惚中没有来得及把握住,没有给出更多地回应,神女就飘然而去了,最终只能“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只有在神女离去后,抒情主人公才透露出含蓄的感伤。在“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 这一句的言外,我们能够感受到抒情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动实际上是达到顶峰的,仿佛宽大平静的帷幕后已然有一张大弓拉到极致,弓弦绷得发抖。然而阮嗣宗并没有在诗中给主人公一个情感宣泄直抒胸臆的喷发口,而是在这种隐藏的情绪抵达高潮时,把恍然一顾的无限欣喜和愉悦始终掩盖于其下,直到 “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一句的最后,我们才能感受到高潮退去后情感恢复平静时主人公浅浅溢出的感伤。像是平静深邃的冰面下涌动着的激流在即将冲破冰面时重新被寒流封冻其中,在深处涌流不止,逐渐趋于平缓,最后在下游溪流细碎的融冰口才涓涓而出。但是在曾经遇过你理想中至高的完美的神女又错过,就像曾经窥见过一丝光明和希望后重新落回普通平庸的生活中,内心的大起大落又岂止是感伤可表达尽致的?这两句诗里面没有如“俯仰”“南北”“朝夕”那样字词上的对举,然而前后两句间巨大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以及诗句描写的曾对一种理想中的至高至善的形象的触手可及又错失理想,与诗句中浅淡的“感伤”情感描写之间又构成了一重落差,这里的双重落差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又因这种落差存在于言外之意中而更引人反复品读,反复体味。但无论如何,这些都需要通过对言外之意的分析解读才能够了解一二,《西方有佳人》的抒情主人公的内敛和含蓄都是相当明显的。错失神女这其中有一种神光离合间来不及把握的缘由,但也有抒情主人公从情感上过于内敛和含蓄,只能“神交”一瞬的缘故。造成这种情感上的内敛含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时局带来的避讳、老庄无为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文必须提到的阮籍在诗歌主人公身上不自觉地体现的人格印记。
二、抒情主人公形象区别的根由
虽然从描写上而言,赋的文体使曹植有更大的书写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细节,但是《洛神赋》中抒情主人公始终参与并投入互动中并不是因为赋文体的篇幅优势,《西方有佳人》的含蓄内敛也并非是五言诗限制下的结果。钱志熙指出“嵇、阮诗歌的风力直接来源于他们‘师心’、‘使气’的个性特点”,“是与曹植‘骨气奇高’的个性化一脉相承的,但更具有个人色彩。”[1]150在这两首诗的抒情主人公行态的对比中,能够看出这其中感发力量的形式的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又有两人身处的时代背景下遭际有别和两人个性不一的根由。
实际上,《洛神赋》的写作年代并没有处在曹植人生中最得意的年华里。在《洛神赋》的序中,曹植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这里的“黄初三年”可能是“黄初四年”的误写,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曹植在黄初三年并无朝京师一事。因此这里他的思想感情应该与《赠白马王彪·序》中表达的有一种承继关系。虽然在《赠白马王彪·序》中,曹植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曹丕,但是他的愤恨都没有太多的掩饰。到写作《赠白马王彪》时,他的哥哥曹丕已死,他的侄子仍然对他进行严密的管制并将他驱逐出京,面临与兄长的大别以及侄子沿袭自曹丕的管制,都让曹植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产生了绝望,《洛神赋》最后人神永隔不得相恋的结局,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破灭的委婉表达。但是即使此时的曹植已经面临了哥哥曹丕和侄子政治上的压制,《洛神赋》中仍然很明显地体现出曹植的才情以及鲜明的个人特点,这与他个人性格是分不开的。
针对这一点叶嘉莹指出:“曹植的诗实际上是以才与气取胜。他的辞藻很华丽,这是才;他写诗的口吻带有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这是气。”[2]186她援引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论及小说感动人的力量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同,认为“曹植这种以气势取胜的作品,其感发力量就属于刺和提的力量。”[2]186在《洛神赋》通篇对神女的描写中,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他在使用辞藻和骈偶对应上下了很大功夫,有很多的细致地雕琢和选择在里面,在《洛神赋》中段对洛神身边诸神的描写“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銮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中,我们注意到这里引入的众多女神都是作为陪衬并且安排在一种神光离合,若隐若现,如梦似幻的朦胧场景中,有意以周围的一切人与境来烘托出洛神的美,这种安排布阵不经意让人联想到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可见洛神在此处的形象也可以称得上是“东方维纳斯”了。但是这段中的诸多女神的出场,能让人感觉出曹植在此处是有意地下浓墨重彩,在营造气势上费了很大的心神。这种营造气势和辞藻的运用并非是指曹植刻意堆砌华丽辞藻,而是如叶嘉莹所说的一般“曹子建的逞才使气”[2]187。曹植一类的诗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心随物转,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就是说,这一类人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2]156。这一点在曹植的诗赋上也体现得很明显。曹植在诗赋中抒发的情感往往不加反省和节制,任凭情感泛滥宣泄,在诗赋上就结合并体现在这种铺排整饰中。这种诗赋中的“意气”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跟曹植本人的放纵而不受约束、充满自信和勇气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阮籍的个人命运与曹植相比就更不如意了。无论如何曹植跟曹魏统治者身体里都流着同源的血液,虽然政治抱负不得实现,但是创作《洛神赋》时他个人的生存环境仍然是得到了保障的。阮籍写作《咏怀》八十二首的时间就要更晚一些,根据对臧荣旭《晋书》中的记载和其他文献的对比分析,基本可以将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写作时间范围缩小到他“任东平太守前后开始创作的”[1]158。这时距他五十四岁去世还有八九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司马氏与曹魏统治维护力量的较量已成定局,而“从外表的形迹上看,阮籍事实上已经完全成为司马氏集团的一员”[1]156。《晋书》本传称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也与这一时期阮籍个人思想上的成熟以及高压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所谓“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文选注》引颜延之语),“阮旨遥深”都是因为阮籍的诗用意深藏,难以确定,有时也不免惹来一些强合史实,穿凿附会的解读。
在这首《西方有佳人》中,抒情主人公情感上的压抑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后的结果。此时司马氏当权已成定局,阮籍虽然表面上放浪形骸,但是骨子里仍然坚守儒家的忠孝观念,司马氏的篡权以及阮籍表面上归属司马氏一派都让阮籍内心难以接受。在这种境况下阮籍不得不“发言玄远”,以求在司马氏一派不断壮大的势力和自己难以安顿的心灵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很多时候阮籍在诗歌中表达的情感都显得委婉曲折,将幽微的无法明说的思绪都隐藏在诗文里。对此,钟嵘在其《诗品》中说道:“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虽然《西方有佳人》并不能找到什么政治上的指向,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上与阮籍的其他诗作是一脉相承的,仍然显得幽微曲折,有意在约束诗歌中的情感表达。明明是自己心驰神往的佳人,主人公却连给出回应都难以做到,将自己的涌动的情感都封闭在躯壳里,只有在佳人芳踪已逝后才那样浅浅地显露出来。佳人激活了主人公心灵中对一份美好的追寻求索,然而在这种远离政治暗喻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阮籍自我抒发中无意识地压抑和隐藏。
阮籍喜好老庄之学,尤其对“无为”颇为推崇,他在所著的《达庄论》中阐述了老庄无为精神的可贵,这种无为的精神也影响了阮籍的诗歌创作。即使是在魏晋风雨飘摇之际、黄老之学盛行之时,阮籍诗歌的内敛含蓄仍然有别于其他同时期诗人的作品。这与阮籍的独特人格和行为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爱好游历山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在无人监视并将他的行为穿凿附会上报的私人活动中,阮籍仍然表现出了与政治上屡次出仕又不断辞官一样的矛盾行为。他的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是复杂而难解的。深山中不走人径就会止步于密林乃是常情,然而阮籍却要时常独驾到车架无处可去的尽头感受这种挫败感,大声恸哭,可见他将这种个体受挫带来的痛苦以及对人力不可为的伟力的感触都化为了他对自然与自我,时代与个人间的矛盾和悬殊力量的独特思考和理解。车迹所穷处他却不再开路,也与他在自己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如各方政治势力、飘摇的整个时代)前消极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以至于在《西方有佳人》里,他开篇就描写神女的目光“流盼顾我傍”,主人公却在“神交”的一刹那没给出任何回应,甚至通篇没有流露出任何主动“神交”的意愿。这种对非人的超然存在的消极和无为以及随后的失落乃至苦痛与阮籍的人格特质是高度统一的。
三、《西方有佳人》的玄学色彩和主题多义性
此外,《西方有佳人》一诗也能反映出阮籍个人在庄老之学上的高深造诣。这首诗在《咏怀》八十二首中,属于阮籍向塑造超现实的理想人物与理想境界发展的产物。这种超越现实的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带有魏晋盛行的玄学的色彩。阮籍在《西方有佳人》中,并不是简单地承袭《庄子·逍遥游》中姑射神人的美人形象,而是通过“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两句传达出一种对理想中的至美至善的追求以及求之而不得,只能望而兴叹,无法企及的悲哀。如果阮籍能够接受现世中世人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并也跟随于其中,没有更多的追求和觉悟,那么他也就能“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然而阮籍正是睁开过慧眼,见过理想世界的模样的人,哪怕只是一面之缘,都让他心驰神往,再难回到尘世的生活中。但也正是在与佳人飘飖恍惚如真如幻的相遇中,佳人本身的完美形象也暗示了这种追求本身的不可实现性。
由于“阮旨遥深”,其实《西方有佳人》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主题的多义性。曹植《洛神赋》的主题结合写作的背景和时间来看,“感甄说”没有太多的实际证据,带有太多民间谣传的色彩,更多的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的传统比象。而《西方有佳人》则不同,方东树在所评的《古诗选》中说:“此不知其何指,若为怀古圣贤则为泛言,不可确指矣,故可以不选。”[2]272可见方东树对于《西方有佳人》一诗的所指并没有什么把握。这个佳人暗示的是什么?是一个能与自己神交的知己,一类至高完满的形象,一个理想境界,还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理念?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深究,因为主题的多义性并非由此而始,同样运用了佳人形象象征一种于宇宙间最完美的至高至善的追求,如《诗经》中的《蒹葭》一篇,《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一篇。主题的多义性反而成为这些诗的优势所在,这种含混模棱使得读者的各种感受和解说都变成这个主题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反而具有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因此也具备更多西方理论中的“语义潜能”,能够引发多种丰富的联想解读。这也使得这样的作品的内涵不能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读者所穷尽,而是由不断展开的接受链条中的各个读者不断展开,因此这些诗作流传千古而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艺术价值是永恒的。
四、求之而不得的矛盾之恒常性问题
纵观《洛神赋》与《西方有佳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有诸多差别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相似之处,即于不甘的追求与求不得的悲哀中体现的矛盾的恒常性。至高的追求总是让人难以放弃割舍,但是理想的实现永远遥不可及,这种永恒的矛盾痛苦是伴随着所有理想追求者整个求索道路的。屈原在《离骚》中有这样的痛苦和反复徘徊,《诗经》中的《蒹葭》反映的也是对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形象在生命长河中的不断溯游追寻,《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中的女子实为叙述主体的投射,追求向往而又难觅理想中的知音的人正是叙述者本身。近代王国维在《浣溪沙》一词中也有“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的失望与悲愤,因为得天所垂怜开了天眼,却发现自己在漫长的求索后仍然是滚滚红尘中人,从来没有跳脱出尘世的束缚。无论这种追寻求索的是贤君、知音,抑或一个形象、一种境界,都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拷问,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和实现。可以说千古以来的文人墨客无不有这样的痛苦,诗人不得不寻求一个迸发的出口,这种感伤、哀愁、悲慨之情,也许正是诗歌拥有强大感发力量的原因所在。这种企慕情结也在千古流传的诸多诗作中得到了一种承继,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