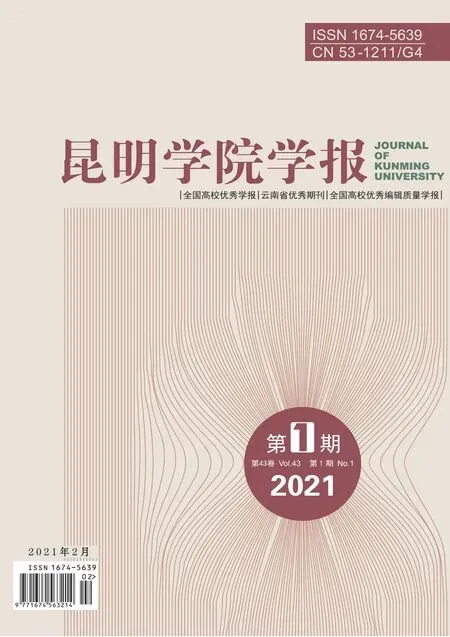生态文明内涵的逻辑辨析
2021-01-02吴立利
吴立利,李 伟
(1.云南师范大学 校医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人类从远古走来,完成了从动物到“上帝”的转变。从一个处于自然界食物链中端的物种,演化为一种可以塑造自然,甚至可以中断人类历史的力量。从自然走出,到具有毁灭自然的能力,人类与自然或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根据尤瓦尔·赫拉利的“简史三部曲”观点,人地关系从适应到紧张,再到对立。出现了人类社会越发展,自然环境越恶化的现实问题。人类与自然的逆向运动,使“生态文明”这一话题成为全体人类的关注热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以43处“生态”、15处“绿色”、12处“生态文明”的论述,向全世界发出了庄严承诺:中国不会把解决贫穷问题与发展经济同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获取发展和人类幸福;同时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综合治理,为全球环境保护与生态正向发展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
当“生态文明”成为社会热词后,学术的内涵与社会的想象相互激荡,对“生态文明”的各种理解,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表达,说明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文明”本体进行学理性的深入思考,对生态文明概念内涵进行逻辑辨析,使学术研究和舆论导向更加符合国家的需求,更加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一、生态学对生态文明逻辑起点的启示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创立生态学。“生态”就是生物的生活状态。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ecology)已被定义为是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1]因此,生态强调的是以(某种)生物为核心,与周边环境所形成的一个整体。1935年生态系统的概念提出后,“生态”事实上是指“生态系统”。
由此可见,抛开汉语中“生态”词义中的“健康”“美好”“和谐”等形容词的性质看,当“生态”这一科学概念引入到人类社会后,生态学意义上所理解的“生态文明”应该指以人类为中心,人类及其所依托自然环境构成的整体表现出来的文明形态。即人类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形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综合表述。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展示了人—地系统中“人”的主动性能力,即人可以破坏自然,也可以保护自然,并维持自然的正态化发展。人—地系统不仅不会崩溃,而且会在人的主导下进化到新的形态。这一点得到了现代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证明。生态问题的本质是对人—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考量,而自然子系统的抵抗性与恢复性、持久性与变异性又是这一考量的重点方向。近50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人类社会在从自然环境获取物质能量的同时注重对环境的投入与建设,自然环境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就会增强,持久性也会逐渐显现,被破坏的环境恢复能力会上升,逆向变异会逐渐减弱。由此导致人—地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并正向发展。目前所取得的沙漠化治理、石漠化治理,甚至沙尘暴、雾霾治理等取得的成效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以看出,从生态学角度对生态文明认知的逻辑起点是:第一,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地关系的调节,是人—地生态系统的优化;第二,人作为人—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自然的干扰可以决定自然环境的演化方向,可以由人主动进行并完成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物演化史对生态文明逻辑进程的表达
地球大约诞生于45亿年前,在距今35亿年前的震旦纪出现了单细胞生物,在距今5亿年的寒武纪出现了生命大爆发,生物经历了海生无脊椎动物、海生脊椎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演化。在距今260万年前进入第四纪,人类的出现与进化是第四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距今1.17万年起,现代人开始分布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2]
人类诞生前,自然演替过程中的生物种灭绝是一个完全意义的自然现象。但据《人类简史》统计,人类在4万年前到了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大陆,体重在50 kg以上的24种动物,瞬间灭绝了23种,不计其数的小动物也由此消失,这是澳大利亚大陆数百万年以来最大的生态变化。来到美洲的人类也同样对野生动物进行了灭绝式猎杀,北美47种特有大型哺乳动物种已有34种灭绝,南美60种特有哺乳动物已经消失了50种。在10万年左右的时间内,人类对全球物种进行了重新洗牌。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物种灭绝的速度预计是正常速度的1 000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曾经估测,目前地球每小时就有3种生物灭绝,一天灭绝近72种生物。同时该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16 300种动植物物种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41 000多种生物则受到生存的威胁。[3]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地球的演化有其自己的历程,以生物圈为标志,自然界表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称为正向演化,生物的繁衍或灭绝遵循其自身的法则;二是人类这一物种在最后一刻出现,加快了物种灭绝速度。因为人类并非靠生物基因遗传优势适应并统治世界,而是以文化的创造、扩散和传承,迅速从一个边缘性的、处于食物链中端的物种,成长为一个居于生态主体地位,上升为一个食物链顶端的物种,造就了人类文明。
如何判断不同文明进程对环境的压力缺乏系统研究。我们所能做出的推测是:早期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分子,与其他物种一样,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由自然环境控制其种群数量。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使自然系统由复杂变得单一,抗干扰能力减弱,人—地关系表现出轻微烈度的紧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还未超出环境的自我调整能力,仅是区域性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自然调控抑或人类迁徙解决环境问题,并未产生全球性的环境危害。工业社会多次工业(技术)革命,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力和污染能力产生了巨大飞跃。自然环境转变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全球性环境问题出现。如全球变暖、极端性气候频繁、臭氧层耗损、有毒有害物质转移和扩散、生物多样性存在威胁等等,表现出人—地关系的强烈对立。
由此可见,以物种灭绝为标志,人类的出现,人类的发展,使自然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地球演化史说明,人—地关系展现出的“逆向”式发展的性质,并不随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而转化。很多人愿意或“喜欢”把当今的环境恶化归咎于工业社会,但事实上,早在农耕文明前,人类已成为自然界物种的超级杀手,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差异仅仅是程度与速度不同而已。所以生态文明并非只是对工业文明的反动,而是对人类自身发展历程的反思,即人类发展始终伴随着环境的“逆向”式变化。从这个角度看,生物演化史表达了人类生态文明的逻辑进程,生态文明是伴随人类终生的文明形态。
三、生态文明内涵的逻辑辨析
文明本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成果的表现。后引申为社会和文化阶段性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
那么生态文明内涵究竟为何?是一种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文明状态?还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结构性组成部分?
一些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总结的结果,是继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形态。如“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4-5]“生态文明表现为对给定的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的超越。”[6]“人类至今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阶段。”[7]“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是世界史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从人统治自然的文明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这是人类新的第三次文化革命。”[8]等等。把生态文明置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演替和变迁过程中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相对应。
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并非一种全新的社会文明形态,而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见诸各种文明形态中的一个基本形态结构和重要组成部分。如“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一起,共同支撑和谐社会大厦。”[9]“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10]所以,“生态文明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的综合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生态化”[11]等等。此类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属于社会文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
还有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实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更大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12]等等。
此三类观点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各有偏向和误区。第一类观点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生态文明是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文明形态。在逻辑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社会文明形态的基本标准,即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弓和箭标志着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正如铁剑标志着野蛮时代,火器标志着文明时代一样。”[13]一个以产业或技术推进方式为标志的文明形态,接入“生态”这一概念,显示了这一思想的误区。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4]
第二类观点出现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两种倾向。一是如果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所有社会文明相并列,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则造成一种结构性割裂,复杂性的人—地关系范畴,简化为一个单一文明观念建设,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现;二是如果强调生态文明不是一种文明形态,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生态化的观点,不仅令人费解,而且未突出生态文明就是调整人—地关系的主题,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第三类观点认为社会制度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承担起改善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责任的观点,明显属于对生态问题本体的认知错位。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与社会制度相关,但不是问题的本质。把社会问题的理念用于认知人—地关系问题,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其加速度是不断提升的,上万年的渔猎文明,上千年的农耕文明都使人—地关系处于环境可自我调控范围内,工业文明使人类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三次技术革命不到300年的时间,人类拥有了可以“毁灭”世界的能力,人—地关系中主导地位发生了转化,从人是环境的组成分子变为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不能抑制或阻止人类的发展,更不能指望自然环境自己有能力停止退化,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平衡”已不复存在。靠抑制人类自身发展欲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只是争取了短暂时间,期望在人类“毁灭”自然环境之前,进入新的文明状态。而打着“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展”旗号,把环境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仅是一种“鸵鸟”思维,更是一种从掠夺资源和市场转为掠夺环境的“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真正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一是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使人类不仅可以利用自然,也可以再造或重塑自然。目前人类虽然具备了毁灭地球的力量,但还没有把控自然演化的能力,科技不仅仅是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自然环境进化的引擎,全球性环境问题,会在科技进步支撑下予以解决和完成。二是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指出,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这就是现时状态下,“生态文明”提出的确切内涵,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目的,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在现时人类发展状态下,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发展理念,其本质上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表达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观念的具体表现。
四、生态文明理念下的人地关系逻辑
早在第一个“轴心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自然万物都要追求自己的内在目的,因而以自身的形式为目的将其质料组织成一个有机体。[15]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所阐述的人地观是一种有机整体观,即人、地两个系统出于各自目的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智慧物种,“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理性的生活”[16]。此处的“理性”在古希腊哲人的视域中被理解为依靠人的智慧获得道德真理的人性能力,以人的理性制约自身的欲望,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平衡态的生活样式。人“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17]。恰因如此,才建构起生态文明的逻辑起点。
康德在人的道德性中找到了人与自然正确的逻辑关系,有了人和人的道德,才能建造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康德以人的道德为基点,对整个自然界提出了一种生态观点:自然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为人的道德而存在,为人的自由发展而存在。
马克思的实践观从理论上彻底阐明了人—地关系的内在逻辑。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劳动是“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实践观明确指出人—地关系表现为现实中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的劳动对象,也是人的劳动成果。体现为人的力量对象化和对象人化的统一过程。“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能进行生产,……”[19]。因此,人类一方面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据自然规律来构造人—地关系,按照自然法则和人类生态的标准塑造自然。这种对“肉体需要”的超越性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的主动性体现。生态文明不是对自然,以及对想象中旧日生活的一种乌托邦式感伤,不是对工业文明的拒绝和憎恶,而是把自然作为人类社会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解人—地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发现人—地反向发展的平衡点,用于现时状态人—地和谐关系的建设。将传统认知中“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转化为现实的“自然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把“人—人”道德规范应用于“人—地”关系,才能生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在对人文主义造成人的中心性与至上性反思的同时,马克思推进了人的道德和能力辩证统一在人—地关系中,注重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主动性。在强调作为“类”的人的存在意义在于其自我规定性的同时,说明了在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
生态文明内涵有以下三个层次的逻辑关联: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基于危机的思想。人类虽然已经具有了毁坏地球的能力,但却不完全具备建设自然的能力,危机意识导致人类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其次,生态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倡导要求把人—人道德观念扩大到人—地系统范畴,强调将人类的行为后果放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回应中评价与审视自己。第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在实践中强调人类的发展要对环境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而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科技的发展,靠科技的力量把控自然变化的方向和程度。
总体看,生态文明持续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文明阶段,生态文明有不同的表现。但在现时状态下,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及对自身生存的关注迫切要求在工业文明环境中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需求,生态文明走向大众视野,并逐渐成为全体人类的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