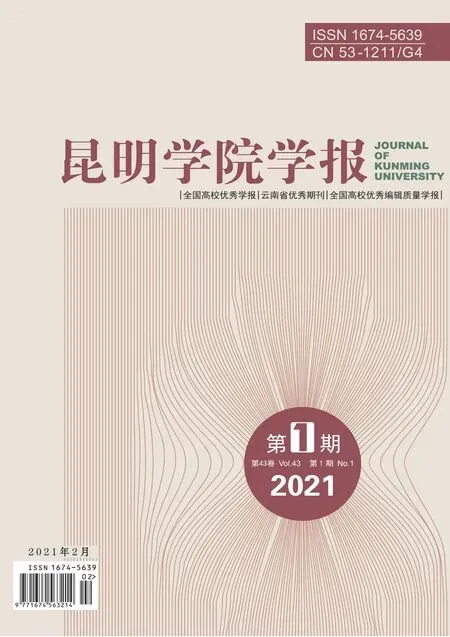何谓“信息图画书”?
——暨对“科普绘本”概念的反省
2021-01-02江渝
江 渝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一、定义“信息图画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图画书热”中,以《神奇校车》为代表的国外知识类图画书占据了相当比例。近年来国内原创的类似书籍也开始逐渐崛起,数量巨增,出现了如“小蜗牛自然图画书系”(海燕出版社)、“趣味科学图画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较为畅销的系列童书。
但在此过程中,却少有人注意该类书籍的学科名称是否恰当。业界习惯将以上书籍归类命名为“科学图画书”“科普绘本”或者“科普图画书”,(1)“绘本”和“图画书”这两个概念都指的是英语中的“picturebook”,往往被不加区别地同时使用,意思完全一样。“绘本”一词继承自日语的翻译“絵本”,“图画书”是我们自己的译法。这种略显混乱的局面在英语学界也能看到,研究者同样不加区别地使用“picturebook”“picture book”,或者更早的“picture-book”。一方面,表明了当下图画书研究还处在起飞阶段;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研究对象本体的混杂、多元性质——漫画(comic)、图画小说(graphic novel)、图画书和艺术书(artists′ book)等多种多样的创作形式时常被混合使用。本文将主要使用“图画书”的说法。大体将其归入“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类别,而该类童书在国外教学、研究和图书市场,却首先被命名为“信息图画书”(information books)。该类书籍之所以被命名为“信息图画书”,是因为它们的目的和任务并非是专门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是要借此发展儿童读者应对信息的能力。(2)日本绘本学界没有采用英美“information books”的概念,而是继续沿用20世纪早期的术语,将此类童书分为两类:一类袭用英语“non-Fiction”,直接用假名音译为“ノンフィクション絵本”,包含人文历史事实;另一类被单独归为“科学絵本”,涉及自然科学知识。或许这第二个“科学絵本”的概念,与“science Books”一同影响了我们“科普绘本”的称呼。而科学类图画书的内容仅仅关系“科技知识”(而非人文历史信息),才能将之称为“科学图画书”(science books),也就是说,这些关于科学知识的图画书,只是属于“信息图画书”类童书的一个分支而已。而更为关键的是,权威的《剑桥英文童书指南》(TheCambridgeGuidetoChildren′sBooksinEnglish)将“信息图画书”定义为:在儿童的正式教育过程中,会接触到不同学科的众多问题、事件和观念,于是许多不同类别的文本被特意设计出来,借助于文字与图像的混合形式来吸引、教导和扩展年轻读者的相关知识。[1]另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来自美国“罗伯特·F·西伯特信息图画书奖”(The Robert F.Sibert Informational Book Medal),评奖委员会规定:信息图画书,指的是那些采用文字与图像来共同呈现、组织和解释具有记录价值的事实性材料的图书。[2]以上两个定义都非常明确地指出:此类书籍处理的内容涉及各种问题、事件和观念,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可能囊括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事实、信息。于是,如果单单将其称为“科学读物”,那就太过狭隘了。比如我们看到,著名图画书《大峡谷》(TheGrandCanyon,2017 年),同时获得了2018年的西伯特奖和凯迪克奖(Randolph Caldecott Medal),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大峡谷的自然科学读物;而另一本图画书《自由之声》(TheVoiceofFreedom:FannieLouHamer,2015 年),也同时获得了2016年的西伯特奖和凯迪克奖,这却是一本关于美国人权运动的人文历史类图画书。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类型的图画书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首先,它们都基于非虚构信息构成,故亦被统称为“non-fiction”,即书中含有虚构故事;同时包含非虚构事实和虚构故事的,被特称为“混杂文本”(hybrid texts)。其次,20世纪90年代该类书籍实现了“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即图像部分成了信息呈现的主要途径,文本不再是主角,反倒成为图像的附庸。这一转向改变了过去文本为主图像为辅的信息读物组织方式,由此让信息的组织、理解与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所以,“图画”至此成了该类型书籍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books”在此就约定俗成地成为儿童文学中“图画书”的简称。在西方学界,信息图画书理所当然地被归属于儿童图画书。
二、“信息图画书”“非虚构”与“科学图画书”三者的关系
在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一般采用三个概念来讨论该类型图画书:“信息图画书”“非虚构”与“科学图画书”。第一,“信息图画书”的说法在学界使用最多,也最为常见,是对这一类型童书的本质定义。第二,“非虚构”一词来历最为久远,在20世纪70年代被信息图画书概念取代以后,逐渐作为一个泛称或描述性概论被人使用。一方面,当需要概而言之地指称各种区别于故事图画书的作品时,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统称;另一方面,可以把非虚构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来使用,指出某本图画书是基于真实信息而建构起来时。第三,“科学图画书”,特指某本信息图画书处理的信息属于自然科学知识,而非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
“非虚构”概念最早出现,用来描述信息类童书(和其他类似成人读物)。这个称呼,源自西方图书分类学的重要建立者麦尔威·杜威(Melville Dewey)。由于公共图书馆中小说、故事等虚构作品读者最多,流通最频繁,故而被集中摆放,方便借阅;而其他类别的书籍(包括诗歌、戏剧等虚构作品)就以非虚构这样一个标签归为一类,安放在一起。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偶然,并无学理上的根据。但是,当代儿童信息读物,却典型地具有这种杂糅多元的性质,天文、地理、历史、社区、游戏等各个门类的事件信息都能够成为作品的内容,日记、菜谱、报告、图表、书信等各式各样的文体都可能出现。故而非虚构这个称呼仍然具有用武之地,因为它能够很好地将这些种类繁多的书籍统括在一类。所以,著名的“皮克特斯奖”(The NCTE Orbis Pictus Award)就使用了这个词,奖励那些优秀的非虚构儿童作品,比如2018年的获奖作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于地质科学的《大峡谷》(TheGrandCanyon);有关于民间艺术家的《本的床单》(TheQuiltsofGee′sBend,2017 年);也有关于建筑的《世界并非矩形:建筑师扎哈·哈迪德》(TheWorldisNotaRectangle:APortraitofArchitectZahaHadid,2017 年);还有关于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她的右脚》(HerRightFoot,2017 年)。“非虚构”包含着内在的弊病,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首先就是它在用否定虚构来定义自身,这种消极的方式,使其并没有指出它所包括的作品具有什么共同性;其次,非虚构概念极易陷入事实/虚构的无谓争议之中,比如,面对那些利用了虚构故事的科学作品,非虚构概念就不得不发明一个无用、多余的“附带虚构”(incidental fiction)的说法来画蛇添足地进行解释。[4]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信息图画书”这一概念所取代,很多时候仅仅被作为一个形容词使用。
有感于“非虚构”概念的消极性,泽纳·萨瑟兰(Zena Sutherland)与玛格丽·费舍尔(Margery Fisher)两人不谋而合地在1972年提出了“information books”[5]“informational books”[6]这两个相近概念成功取代了“非虚构”,至今一直来都被人们广泛使用。比如,著名的美国“罗伯特·F·西伯特信息图画书奖”就使用了这个术语。一方面,信息图画书的说法,十分敏锐地抓住了这类书籍的核心本质:它并非在罗列科学事实,而是在处理信息,以此来让读者获得知识的能力。事实(facts),只是原始的、未经加工的数据集合,它们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转化为信息(information),即具有了条理性、规则性与逻辑性。知识(knowledge)的获得,是读者主动、积极参与信息接收的结果;知识并非是对事实的简单记忆,它来自读者对信息的主动加工,故而它并不等于信息,并非独立于读者而存在的某种纯粹客观的存在。所以,一本优秀的信息读物,就需要在信息的组织上具有三方面优点:首先,它必须对事实进行选择、整理与解释,即使用文字与图像对事实展开编码,如此将事实转换为富有逻辑性、便于接收的信息;其次,信息读物必须能够友好地帮助读者展开解码工作,让读者易于、乐于阅读,从而能够高效地将书中信息化为读者的知识(能力);再次,虚构故事、图像修辞等手段的使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7]但另一方面,信息读物的说法也有自身的缺陷:其一,任何一本书,其中都必然包括了一些信息;严格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非信息书籍”(non-informational book)[8];其二,这一术语易于让人将其与百科全书、课本教材之类联系在一起,从而忽视了信息读物还包括历史、传记、回忆录、新闻报道等等文类。
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多媒体(multimedia)、多模式(multimodal)的儿童科学书籍大量涌现,“科学图画书”的说法又开始被人们大量使用。但这一称呼并不能取代“信息图画书”,只能作为一个特称而存在,原因很明显,科学图画书的称呼太过狭隘,几乎不会让人把它与人文知识读物联系起来。而“信息图画书”尽管具有过于笼统的弊端,但确实表达出了这类书籍的本质,即对信息的处理。这些广泛涉及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知识的作品之于儿童的意义,并不完全是让他们了解一些科学事件、文化常识,也并不仅仅在于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而是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懂得与他人合作,从而具有团队精神,一同自主地发现知识、创造世界。所以西方学界一向非常强调在儿童教育领域使用信息图画书进行教学,并因此出版了大量的配套教材。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英语教学计划(reading scheme)——《牛津树》(OxfordReadingTree),不仅包含有一套故事图画书(storybooks),还有另一套单独的信息图画书——OxfordReadingTreeFactFinders,其中包括了人体科学、家庭、社会、文化等五花八门的信息内容。与之类似,著名的科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大猫图画书系列”(CollinsBigCat)小学英语教学计划,就同时包括了三种类型的图画书:故事(fiction)、非虚构信息图画书(non-Fiction)和剧本(plays),其中的信息图画书类,不仅涉及昆虫、动物等科学知识,也包括了古代维京历史等人文信息。
如此反观国内当下的“科普绘本”概念,“科普”一词在此显然不大适合。“科普”,为“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主要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知识社会化传播过程[9]。一方面,它让人难以将其与人文历史知识等信息内容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没有突出读者的能动性。对比“科普绘本”与“信息图画书”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区别:“科普”,面向的读者为全体社会大众,着重于由高到低的普及;儿童信息图画书则主要针对儿童读者,更加强调读者能动地、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培养。故而,信息图画书尽管以自然、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真实信息为基础,却并不以将其输入读者头脑为最终目的,信息图画书的作用就是培养儿童善于发现、乐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使其具备思考与创造的能力。
三、信息图画书研究的兴起
一直以来,西方童书市场中非虚构类的儿童信息图画书都位居虚构作品之下。[10]这种高下之别,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每年的各大获奖图画书,其中虚构类故事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回顾历年的“凯迪克奖”,每年有5本左右的图书获奖,一般来说其中非虚构类图画书顶多只占1本;同样,每年的“凯特格林威奖”中(The CILIP Kate Greenaway Medal),虚构故事也明显多过非虚构类图画书。
按照佩妮·科尔曼(Penny Colman)的说法,人们普遍存在对非虚构信息图画书的偏见,认为它们太过无聊,孩子们对它们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书籍只适合让儿童翻阅浏览,因为它们并非真正的书籍,只是一些信息的堆砌罢了;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些信息图画书没有美感,不具有创造性,故而不能帮助儿童成长发展。[11]当然,这些说法都只是一些偏见而已。儿童信息图画书同样能够产生阅读的愉悦,它们并不仅仅包含信息,而是在以审美的方式、创新的手段将读者引入知识的收获与创造活动之中,从而让读者得以成长与进步。事实上,实证研究早已表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与虚构故事相比,他们都更加喜爱阅读非虚构类型的信息书籍。[12]如果你去图书馆或者书店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陈列的信息图画书数量时常多过故事图画书。
其他儿童文学作品研究的情形,也与之类似。相较于汗牛充栋的《哈利·波特》(HarryPotter)研讨专著,关于大卫·麦考利(David Macaulay)《万物运转的秘密》(TheNewWayThingsWork)的少量研究明显相形见绌。众多的儿童文学研究手册、入门指南、百科全书,对儿童信息图画书或者不加理会,或者只是寥寥几笔带过。[13]正如《剑桥英文童书指南》(2001年)所描述的那样,即便是在儿童文学发达的英国,儿童信息图画书也并不被那些重要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看重,较少被关注。[1]
但情况确实在发生着变化。随着数量众多的引人入胜的信息图画书相继出版,研究者的激情也日渐炙热。一方面,许多重要的儿童文学评论期刊,例如《图书收藏》(BooksforKeeps)和《学校图书馆员》(TheSchoolLibrarian),开始将信息图画书纳入评论对象;另一方面,各国开始相继召开关于这些出版物的专题研讨会议,例如2008年的“非虚构:超越信息”(Non-Fiction:More Than Information)研讨会。同时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之前研究对儿童信息图画书文学性的忽视、对其图像艺术性的回避[14],研究者开始努力扭转这种局面,力求呈现出信息图画书在叙事与图像上的特殊价值,并进一步强调它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15]
当代信息图画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能够积极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更富挑战性,从而提供给读者锻炼能力的机会。就像科学家面对实验数据,创造地、逻辑地对其展开分析与追问一样,一本优秀的信息图画书,也能够引导读者一步步地掌握科学地观察、思考、批判、创造的思想能力,并能够训练读者使用图像与文字等手段将自己的收获表现出来。
而为了实现以上目的,信息图画书始终对自身形式进行着改进,有三方面趋势尤其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对图像的重视程度日渐增强,大量使用漂亮的插图、高品质的照片,文字也变得更加精炼短小;其次,将虚构故事与科学知识有机地融合,积极地引入有趣的故事、想象的场景来提升书籍的吸引力;再次,“创新图画书”(novelty picturebooks)采用新颖的表现形式,如立体书(pop-up picturebooks)、翻翻书(lift-the-flap)、电子图画书等。这些形式并非仅仅为了提升书籍的趣味性,而是立足于内容,试图采用这些手法来更好地组织、呈现书中的信息。
伴随着以上进步,自然也产生了相应的理论问题,这构成了当代信息图画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例如,对于是否应该以故事的形式来展开科学阅读教育,研究者一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故事能够有效地辅助教学,儿童可以通过它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从而掌握信息;与之相反,也有学者反对过分依赖故事的策略,他们认为,儿童信息读物阅读教育的最终结果,是让读者能够进行抽象的思维,能够运用科学概念、逻辑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活动的特点都与虚构故事的语言特性大相径庭。
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开展信息图画书阅读教育,学界一直在不停探索恰当合适的教学模式,这是信息图画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者陆续建构了“5E”(5E model)、“EXIT”(extending interactions with text)等教学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基于对“学习”的社会性(即学习是一个集体互动的合作过程)、语境性(即学习是在一个实践的具体场景中展开的,离不开相关背景知识的影响)和自反性(即学习者必须学会反省自身的学习过程)等特征的强调,立足于信息图画书阅读教学方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对儿童阅读教育研究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①
①关于这两方面研究的详细内容,将另外撰文论述。
四、结语
明确“信息图画书”的思想内涵和重要价值,反思“科普绘本”的概念,直接的理论意图,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信息图画书阅读教育与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背后隐含的是两种不同的儿童教育观念。信息图画书阅读教育,强调的是借此锻炼儿童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合作处理信息的能力。而科普绘本的概念,所着眼的仍然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以笔者在英国考文垂市某小学和数所图书馆的调研经验为例,小学二年级(Year 2,相当于国内小学一年级)2019年春季学期(共计10周)的“艺术与设计”(Art and Design)课程,整个学期只包含一项教学任务——“鞋盒子车”,师生一起集中3周左右的教学时间,综合美术课、英语课、科学课等课程内容,要求学生两人一组,全程独立动手设计、制作和装饰一辆鞋盒子车,最后参加学区比赛。而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学习相关信息图画书,课后需要查阅制作信息、完成作业时,还可以就近在社区图书馆找到相关书籍,它们被专门归类存放在“家庭作业”区。
可见,英国小学教育尤为注重跨学科的综合教学,强调深入细致地开展教学活动,这正是其信息图画书阅读教育主张的宗旨。本文讨论信息图画书、科普绘本等概念的理论意图与实践指向,正是希望能够参考与借鉴以上教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