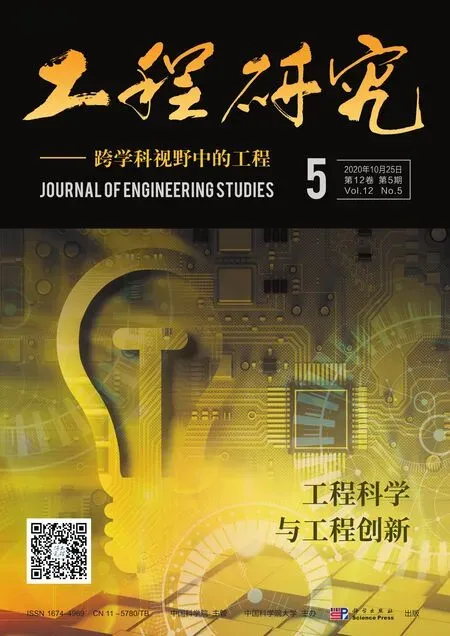俞鸿儒院士:激波管爆轰驱动新方法开创者
2020-12-30张志会
张志会
“工程科学与工程创新”专刊
俞鸿儒院士:激波管爆轰驱动新方法开创者
张志会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俞鸿儒早年攻读数学和机械工程学位,打下了理工结合的坚实基础。1956年他考取了中科院力学所郭永怀先生的研究生,在钱学森、林同骥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和文化熏陶下,加上他本人固有素质悟性,走上了开拓“激波现象及其应用”的实验研究之旅。俞鸿儒急国家之所需,不循国外老路,探索出费用低廉且高效的高焓试验气流实验方法——爆轰驱动,被国际同行广泛推崇。他还积极推动激波管和激波风洞技术在国防、航空航天与民用领域的应用。在21世纪初他又开展了高超冲压发动机性能研究,并探索采用催化复合方法提高冲压发动机推力的新概念。俞鸿儒还为中国气动中心的发展倾注心力,献计献策。他甘当铺路石,为后来者助行。
俞鸿儒;激波风洞;爆轰驱动;工程科学
俞鸿儒作为享誉世界的气体动力学家、激波管与激波风洞领域专家,不仅为我国创造了多种高性能的气动实验装置,还在高超声速、高焓流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不遗余力地推动高温气体动力学在中国的发展。由俞鸿儒指导,中科院力学所姜宗林等人建成的长试验时间激波风洞JF-12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和国防技术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还积极致力于培养和提携年轻科研人才,传扬工程科学,赢得了力学界的赞誉与尊敬。
作者尽量查阅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档案,对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团队的俞鸿儒院士及团队成员、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奥利弗(H.Oliver)教授等开展口述访谈,以图真实还原俞鸿儒先生在开创爆轰驱动新方法,推动激波管在航空和民用领域的应用,以及传承工程科学精神的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完整展现俞鸿儒作为一名工程科学家的学术发展轨迹。
1 理工结合的教育
1928年6月15日,俞鸿儒在江西上饶专区广丰县的杉溪古镇呱呱坠地。此地人杰地灵,唐代广丰籍诗人王贞白的著名诗句“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千古传诵[1]。当地民风较为开化,早在清朝末期已经有人远赴东洋,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俞氏宗族在当地曾专设公有资产,专供赈灾、开办学校与修桥、补路等活动。俞父曾贩卖烟叶赚取营生,因为诚信经营,对乡邻们热情相助。俞父50岁生日时,将办生日宴的钱省下,把河边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改建成好走的石板路,以便行人通行。其在杉江中学创建时还慷慨捐资100大洋[1]。俞鸿儒从小喜欢安静,爱看书,知礼仪。他在1933年秋进入杉江中学附小学习,脑瓜聪明的他成绩优异,数学成绩尤其拔尖。俞父经常教导他,凡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事要做精做深,做一个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1],这些话在他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39年秋,他小学毕业后,因误了中学报到的时间,只好读了半年私塾。1946年高中毕业后,他和同学们一同去上海参加大学入学考试,顺利考取了同济大学的数学系。在学校期间,他勤奋读书,热切追求进步,多次参加过罢课游行,反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东北老解放区,将其建设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党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招生前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宣传这所大学将对学生实行供给制。俞鸿儒认为工程学科对经济建设可以直接发挥作用,受这一观念影响,他以肄业生的身份再次参加高考,考入了大连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先后改为大连工学院和大连理工大学,图1)[1]。1953年毕业时,他在大连工学院留校担任助教,被分到机械制造教研室,王大珩教授他们物理实验,老师对实验的一丝不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不喜欢单纯的机械制造,他向时任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的雷天岳申请,希望把他调到一般人不爱去的基础课(力学)教研室。雷立即安排他去担任陈铁云教授的流体力学助教,后来又在化工系“泵与压气机”课当助教并授课,还被借调到土木系参与水利实验室的建设。这些在不同岗位上将基础理论和工程相融合的“万金油”式经历,为他后来开展工程科学研究提供了过硬的根基。

图1 1956年俞鸿儒在大连工学院
1956年初,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人心向院”,很多人都希望到科学院来。俞鸿儒也萌生了到科学院的愿望,目的是向高水平科学家学习科研。钱学森1955年回国,因学术造诣颇高,又有强烈的爱国心,报纸上关于他的宣传很多,1956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同年,中国科学院首次招收副博士,俞鸿儒顺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报考的导师是钱伟长,开学后导师变为郭永怀,研究生论文的指导老师又变为林同骥[2]。这三位都是著名科学家,其中前两位都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航空航天界的科学泰斗”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攻读博士学位。
1957年3月研究生开学报到以前,他在清华大学与力学所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当助教。郭永怀担任授课教师,给同学们讲授流体力学。郭老师非常重视实验,带领流体力学课程的助教们到北京航空学院拜访陆士嘉,并参观该校的气动实验室。1956年,郭永怀受同窗兼好友钱学森的号召回国效力。回国前郭预见到中国发展航天事业需要研制地面模拟试验设备。虽然美国当时已建立了加热轻气体驱动的高超声速风洞,但这种装备耗电量惊人,且总温有上限,不能很好地研究超高速飞行伴生的高温效应。于是郭永怀在回国前将康奈尔大学亚伯拉罕·赫茨伯格(Abraham Hertzberg)[3]和坎特罗威茨(A. Kantrowitz)发展的激波管技术的相关材料带回中国。
1957年春夏之交(至1960年),郭永怀指定俞鸿儒探索激波管加热方法,用于产生高超声速风洞气源[4]。1958年初,力学所成立激波管组,该组由俞鸿儒和陈致英、范良藻三名研究生以及从北大分配来所的张德华、何永年等五人组成。1958年2月,郭永怀钦点俞鸿儒,让他以研究生的身份担任激波管研究组的组长,有意思的是,研究所内几个小组的组长全是知名科学家。俞鸿儒和同事们经过一番奋战,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激波管,在当年“八一”节向党中央献礼。那时“两弹一星”很热门,激波管研究组没有直接参与军工任务,却一直得到郭先生的支持,后来在国家急需的时候果然派上了用场,可见郭先生的深谋远虑。
因俞鸿儒是以在职青年教师身份攻读研究生,学校一直在催促他早日回大连工学院。当时他在北京已经成家,自然很想留在北京。殊不知,钱学森已然看重了俞鸿儒的才能,在1962年广州科学会议上和大连工学院校长钱令希教授达成约定,俞鸿儒毕业后留在力学所,作为人才交换,钱令希挑中了钟万勰。俞鸿儒在1963年毕业后顺利留所工作。不曾想到,若干年后二人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故事遂成为佳话[5]。
在力学所,俞鸿儒深切感受到钱学森和郭永怀等大师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以身作则、不图虚名的作风。他曾在钱学森指导下做过一些工作。那时太原自己研制的火箭发射失败,拟请钱学森去解决问题,钱师打电话叫俞鸿儒帮着干,他从中体会到处理问题的宝贵思路和方法,偶尔还随钱师去拜访前辈[1]。
虽然郭永怀不喜欢当面表扬人,俞鸿儒却始终感受到了老师的默默关怀。1959年群众掀起技术革新高潮,党中央要求中国科学院对最重要的十项技术革新进行评定。钱学森所长从院部领回了超声波和涡旋管两项任务,并指定俞鸿儒做他的助手来评定涡旋管的制冷效果。因任务紧迫,当他深夜从所长办公室出来时,见郭永怀先生已在门外等候,并交给他几份涡旋管论文抽印本,支持他如期完成了任务[1]。
2 研制激波风洞
在力学所这片广阔的天地里,俞鸿儒“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激波管领域潜心研究,做出了成绩。三年困难时期,力学所的许多项目都被取消了,激波管组的项目却被保留下来。1958年12月至1959年底,激波管组的科研人员都被调到该所承担国防尖端任务的气动实验部(又称140部),从事超声速风洞测量仪器的配置与研制,俞鸿儒被委任为风洞部测量组的组长。
风洞设备是一国重要的科技基础设施,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提供丰富的知识,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贡献。二战以后,伴随着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崛起,高超声速风洞发展势头强劲。为了更真实地模拟高超声速流动及其流动过程中的热化学反应进程,又不使高温对风洞设备和试验模型造成损坏[6],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世界航天大国,探索了不同类型的超高速地面试验装备。其中的关键是尽可能改进风洞的驱动方式,提高驱动能力。目前世界上高焓激波风洞驱动主要包括加热轻气体(氢气、氦气等)、自由活塞和爆轰驱动方式三种。爆轰驱动未出现前,欧美主要采用前两种驱动方式。
爆轰现象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爆轰驱动却因一系列技术瓶颈而停滞。1954年,赫茨伯格和史密斯(W. E. Smith)在燃烧驱动激波管实验中发现异常现象,测得入射激波马赫数超过了按等容燃烧假定与激波管流动理论计算求出的数值[7],他们提出“等压燃烧”模型来解释这一异常现象[8]。1962年,俞鸿儒率领的激波管组建成直通型风洞JF-4。同年,在钱学森“搞研究不能一味模仿别人,要走出自己的路”的教导下,考虑到赫茨伯格的“等压燃烧”模型难以理解,他尝试采用膜片处多火花点火的反向氢氧燃烧驱动方法进行实验,期间发生了几次事故,其中有一次因试验压力过大,试验设备的螺丝被打松了,实验室的墙壁也给炸坏了。然而每次事故后他都未遭责难,反而得到安慰与鼓励。原来郭先生已预先向党委和钱所长说清了情况。
在分析某次激波管氢氧燃烧实验事故时,俞鸿儒发现根源是出现了爆轰。爆轰是极其危险的事,应尽力避免,但俞鸿儒很想弄清爆轰驱动的规律。郭永怀也鼓励他把风洞试验继续做下去。之后试验中又数次偶然起爆。他分析认为,反向爆轰驱动的激波衰减率显著降低,且重复性较高,其产生的入射激波较氢氧燃烧驱动形成的入射激波更强[1]。之所以与博尔德分析结果不同,是因为博尔德没有考虑燃烧或爆轰过程中通过管壁的散热影响。但因爆轰时对激波管的高机械载荷容易出现危险,又没有安保措施,这种方法未能应用[9]。此后他做实验再未发生严重事故,科研上也不断出现了自我突破。
1961至1963年经过导师林同骥指点,俞鸿儒进行“激波管风洞及其在传热实验研究方面的应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探索了激波管风洞的气动力原理,设备设计及测量技术等,是中科院当年为数不多的取得学位的研究生。
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郭永怀鼓励俞鸿儒这些年轻人要学会用最省钱的办法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1964年他建成反射型激波风洞JF-4A,开始设计大型激波风洞JF-8。1967年春俞鸿儒和同事搭建起一座高性能大型激波风洞。郭永怀看到安装起来的风洞后,误以为花费了几百万元经费而非常生气。当听说通过利用废置设备,找寻便宜靠谱的工厂,仅花费8万元加工费后,郭永怀非常满意。
受国防科委委托,中科院于1965年10月5日正式向力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和地球物理所下达“640-5”任务,由力学所抓总,开展导弹再入物理现象研究,俞鸿儒所在的激波管组也参与了这一任务。1968年11月,俞鸿儒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被撤销组长职务面临审查。这一年,郭永怀将俞鸿儒和崔季平所在的两个组从研究室抽调出来合并,调到绵阳地区的中国气动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国气动中心),俞鸿儒很快恢复了科研工作。上级将他所在的研究室编入部队系列,但不穿军装,办公地点也仍在力学所院内。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公殉职,他永远失去了聆听恩师教诲的机会。1972年初,他参加了为返回式卫星提供设计数据的工作,并在1975年参与了气动攻关的协作研究[1]。由于“文革”十年动乱,他的头脑中不停思考爆轰驱动技术,却苦于没有实践机会。
3 开创爆轰驱动新方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随着钱学森逐渐淡出中科院力学所,郭永怀因公牺牲,国内激波风洞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爆轰驱动研究在国内外沉寂了二十多年。但俞鸿儒内心一直未放弃激波风洞技术研究。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随着科研秩序和国际交流的快速恢复,俞鸿儒及其团队的努力为爆轰驱动带来了新生。1979年,俞鸿儒作为负责人的“激波风洞及实验技术研究”研究成果获国防科工委三等奖[10],他和同事建成JF-4B激波风洞,发展了瞬态测试技术。同年,他第一次到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访问,在该校图书馆阅读到大量文献。他发现,1959年Edwards D H[11]关于爆轰驱动出现试验事故的解释,竟与他1962年时对实验事故中的爆轰现象的解释一致[12]。1979年和1987年亚琛工业大学两次召开了国际激波管大会,俞鸿儒均参会交流,结交了不少国际同行。
1979年应西德学术交流协会(DAAD)邀请,俞鸿儒在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工作3个月。1988年9月~12月,作为西德马普学会向中国科学院提名邀请的科学家,他在亚琛激波实验室参加“高超声速、高焓流动”专题研究,为期4个月。同期出访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在国际激波管学术会议应邀作报告[1]。20世纪80年代末在吕尼希教授、张帆等人支持下,俞鸿儒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重新启动了爆轰驱动激波管实验,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内继续潜心钻研(图2)。

图2 1987年俞鸿儒在实验室(俞鸿儒院士提供)
1988年9月~12月,俞鸿儒在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完成爆轰驱动的原理性实验,回国后成功发展成反向爆轰驱动技术。基于对激波管理论的充分认识,他在1989年提出了在高起始压力条件下,在由膜片处直接起爆的氢氧爆轰驱动试验的驱动段尾部串接一卸爆段,来产生高焓试验气流的设想[1]。
由于俞鸿儒在激波管与激波风洞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1991年他顺利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也是中国科学院在1981年后评选出的首届院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水平。1992年俞鸿儒和吕尼希二人关于爆轰驱动激波风洞的研究成果联合发表[13],引起了国际关注。
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失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真实气体效应研究经费剧减,尽管德国的宇航研究院实验流体研究所(HEG)和日本高焓风洞都在建设,但研究高潮已过。当时中国学术界以仿真高温气动为主要研究手段,地面设备研制失去了政策支持。幸运的是,俞鸿儒取得了很多同行专家的支持,1995~1996年还得到中科院计划财务局以及“863—2”项目的资助。
俞鸿儒还非常注重与欧美学界保持密切的科技交流,搭建国际学术网络。1991年俞鸿儒陪同林同骥先生接待西尔斯(Sears)夫妇参观应用流体实验室,西尔斯也是冯·卡门的弟子、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图3)。

图3 1991年林同骥先生接待希尔斯夫妇参观应用流体实验室
1993年2月,中科院力学所与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签订“激波风洞与激波管爆轰驱动研究”科学合作协议。1993年5月,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主任吕尼希(Hans Grönig)教授拜访俞鸿儒,调研力学所爆轰驱动激波风洞技术进展(图4),俞鸿儒还陪同他调研了南京、绵阳和杭州等地的相关领域的高校与科研机构。1994年7月,亚琛工业大学已完成爆轰驱动段并开始实验,俞受邀于9月1日~10月1日赴德工作四周,参加高起始压力直接起爆方法实验工作,与双方共同培养的博士生王伯良一起参与德方对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的研制[14]。1994年9月1日~10月1日,他因《新颖的低温风洞冷冻方案研究》项目赴德国合作研究。10月27日~11月27日,他因《激波风洞与激波管爆轰驱动研究》项目再次出访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吕尼希教授大力推荐爆轰驱动技术,使该项由我国创立的技术很快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1996年吕尼西教授再次到访中科院力学所,与俞鸿儒开展深度国际学术交流。

图4 1996年陪同吕尼西教授夫妇在国内调研
在经费缺乏的情况下,俞鸿儒优先解决技术难题,再去改建风洞,这一技术战略使得他的工作反倒后来居上,1998年率先将JF-4B激波风洞/炮风洞改造成为JF-10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也是世界上首例此类型的风洞。JF-10风洞可产生8000K、80兆帕的高焓气源。1998年,JF-10高焓激波风洞通过验收(图5)。而后,俞鸿儒再次到亚琛工业大学访问,帮助吕尼希将该校原来的激波风洞改造成可爆轰的TH2-D风洞。

图5 JF-10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验收(来源:俞鸿儒院士提供)
JF-10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建成后,吸引了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前来观摩学习(图6)。2000年5月4日,国际知名的激波风洞专家、日本学者高山和喜教授也前来参观JF-10风洞,并在国际上积极宣传这一先进成果。

图6 2000年5月4日日本激波风洞专家高山和喜参观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俞鸿儒院士提供)
4 推动激波管在航空和民用领域的应用
粉碎“四人帮”后,步入“不惑之年”的俞鸿儒,嗅到了“科学的春天”的气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激波风洞应用研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同时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他和同事们的科研热情高涨,通过国内外学术交流,将视野扩展到基础和工业应用。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俞鸿儒领导开展的激波管与激波风洞研究集中于研究导弹再入气动力、气动热和气动物理现象,从而为“两弹一星”工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支撑。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则着力推进激波管与激波风洞在航空和一般民用领域的应用。
1988年,他组织课题组成员用激波管研究导弹再入现象,开展“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级间分离研究,为长征二号戊(CZ-2E)的研制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火箭发射后分析故障原因时,他凭借广博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领导课题组应用激波管与激波风洞,运用巧妙的构思开展了游机喷管辐射加热影响研究,在一个月内分析出澳星事变原因,为澳大利亚通讯卫星奥赛特B-1在1992年3月按期发射消除了障碍,帮助中国长征火箭在国际卫星商业发射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机会[15]。这些事情使得他在航空航天领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他还积极利用激波管开展应用基础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他建成国内首座竖直含灰气体激波管,运用这一装置开展了含灰气体流动及激波特性研究,首次观察到无间断前沿的含灰气体激波结构,同时,开展了气固二相流与物面传热特性研究,理清粒子运行对飞行器作用的机理。1985~1988年间,他与第三军医大学王正国等人合作,研制成可开展生物冲击伤试验的生物激波管,研究成果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还曾积极推动激波管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20世纪80年代,他首先用激波管理论解释分析热分离器内流动特性,指明其中关键机制和问题。1998年他完成了“籍热分离器降低总温的低温风洞”,获中国科学院发明奖一等奖。1999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与中国气体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设计所合作建成国内首座原理型新颖低温风洞“空气低温原理性风洞”(图7)。这一发明克服了国外用液氮制冷的低温风洞费用昂贵和污染环境的难题,开拓了建造高雷诺数低温风洞的新途径。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GXJ-100S高压校准激波管系统研制”项目在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乙烯是评价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钱学森就提出了将气体动力学作为反应气体,创造急速升至高温和高压的反应条件,实现快速反应,将生成的化合物通过迅速膨胀冷却进行“冻结”的思路[1]。俞鸿儒从1980年代就开始探索工业化裂解乙烯研究,提出反向射流混合加热法[1]。到了1990年代,他积极推动“用于裂解制造乙烯的气动加热方法研究”。后来,他又尝试用新型方法进行推进,2001年73岁的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反向射流混合加热裂解装置及生产乙稀的方法”获得发明专利。这一气动领域的新思想如能在化工中实用,将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图7 1999年俞鸿儒参加中国气动中心合作研制的新型空气低温风洞(俞鸿儒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拍摄于中国气动中心)
5 培养年轻人
古稀之年随着体力下降,俞鸿儒逐年缩小了自己的工作量。20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还鼓励老年院士继续工作。那么,老年科研人员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对自己提出两条约束:不要和年富力强者争做适合他们干以及他们特别愿意干的项目;尽量少占资源并选择风险较大的项目。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放松了要求,相反,他虽年事已高,却依然耕耘在科研第一线,孜孜不倦地探索,学术思想活跃,善于从战略角度理性地看问题,如前辈钱学森和郭永怀一样,不断开辟新的方向。在瞄准某个方向后,他往往先刻苦钻研摸清思路,遇到技术难题时,再带着一个团队去攻克。等把主要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自己就去另找一个难题去攻克,给年轻人发挥的空间。
2001年,俞鸿儒和陈宏二人首创双爆轰驱动方法。他提出在正向爆轰驱动段上游增设辅驱动段,在辅驱动段起始反向爆轰波,将正向爆轰驱动段中的泰勒波完全消除,从而克服了正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强激波衰减严重的难题。同年,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方法研究被评为863计划15周年成果展览新概念新技术探索项目之一。
高超声速①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预期飞行高度为30 km~100 km,飞行马赫数5~30,高超声速流动的总温和总压分别高达10 000K和100 MPa。这样的飞行速度会在飞行器头部形成激波,这道激波将飞行器周围的空气加热至几千度,空气分子由此不断进行振动激发、解离、化合乃至电离等热化学反应。科技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格局[16],给航空航天技术带来巨大挑战,而这种影响正是经典气体动力学理论所不能预测的[17]。21世纪初,全世界都对研制高超声速超燃冲压发动机热情极高。2003,美国的国防部(DoD)和航空航天局(NASA)联合提出了国家空天发展的启动规划(National Aerospace Initiative,简称NAI)。高超声速技术(包含超燃冲压发动机)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家重大科技重大专项”的三个保密项目之一。基于国家重大科技研发的需求,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在2005年提醒和督促78岁高龄的俞鸿儒积极关注“高超”问题研究(图8)。俞鸿儒由此选定了创建可靠的地面试验装置与增大冲压发动机的推力这两项关键性工作。他在2006年向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了建造复现高超飞行条件的脉冲风洞的建议。
当时国际上高温气动研究都在采用污染气体(试验气体中包含大量水和二氧化碳等非空气组份)作为试验介质的试验装置,难以提供可靠的试验数据。自由活塞驱动与加热轻气体驱动均不能提供足够长的试验时间。面对延长试验时间的难题,不同于和国内一般做法,俞鸿儒反其道而行之,从开展超燃相关地面实验的大型科研装备入手,探究美国超燃发动机研究为何未见起色。他的目标是在地面复现三四十公里的天空,并大幅度延长爆轰驱动激波风洞实验设备的试验时间。在反复思考后,他发现采用小直径驱动段,再将被驱动段长度增长并增大直径,用“以小驱大”的方式,并充入适量惰性气体,既可达到缝合界面运行条件,但又不部分降低激波马赫数,就可以将试验时间延长到100毫秒。在明确了概念设计后,他在2006年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建造复现高超飞行条件的脉冲风洞的建议[1]。

图8 2006年中科院院士大会上路甬祥和俞鸿儒亲切交谈
2006年,为了突破高超声速推进关键技术,他又提出冲压发动机采用催化复合的方法提高发动机推力这一颇具创新性的方法。后来还深入探索高铁气动力学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力学关键问题。
在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张杰副院长、及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支持下,2008年1月长试验时间爆轰驱动激波风洞项目正式启动,并被列入财政部和中科院共同支持的8个国家自主创新的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之一。他一再强调,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花比较少的钱、小的代价去解决大的、重要的问题”,不能落入“花钱越多、成果越大”的误区。这套世界水平的重大科研装备的研制经费,如若在其他部门,可能申请几亿经费,而在俞鸿儒省钱办大事的方针下,他们用4000多万元就建成了。
2008年起在财政部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专项的支持下,运用俞鸿儒独创的爆轰驱动理论及技术,姜宗林研究员率领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体动力学实验室用4年时间进行风洞建设,2012年这一风洞顺利建成(图9),可复现25~40公里高空、5到9倍声速的高超声速飞行条件,试验时间大于100毫秒,对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防部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及了JF-12激波风洞,认为“中国科学院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基础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高山和喜(Takayma)教授2012年评价说,“在俞鸿儒的指导下,你们研究所开发的爆轰驱动系统是独有的。它的工作模式完全没有移动的活塞,后者显然是现有自由活塞激波风洞的缺陷。”[18]

图9 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激波风洞JF-12(来源: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团队提供)
6 为中国气动中心倾注精力
大型科研装置是我国航空航天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气动中心)是为适应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由钱学森、郭永怀规划,经毛主席批准,于1968年2月组建的,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级空气动力试验研究中心。气动中心主要通过基础性的大科学装置为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研制服务,每年国家投入数以亿计的科研经费,现在已经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风洞群。
俞鸿儒和中国气动研究与发展中心有很深的渊源。1968至1976年,他曾经在气动中心工作过六年。气动中心空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11月通过科技部组织的建设期验收,俞鸿儒担任了该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建议重点实验室要凝聚方向,不能太散,选题要准确,选取一些基础性的、共性的,而且是国内还没人做、国外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去开展研究。1999年12月,他在四川安县参加中国气动中心“2.4米跨声速风洞性能评审会”。2000年开始,他受邀担任军队“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廖达雄的指导老师。从2007年开始,气动中心重新成立专家顾问组,庄逢甘先生任组长,俞鸿儒不仅是该专家顾问组的专家,还是顾问组的核心成员。专家顾问组每年开一次会,每年一次,连续五届,俞鸿儒均到会参加。气动中心几个很重要的规划纲要都是俞鸿儒主持审议的。他从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角度,对气动中心科研工作的建设发展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建议。
在2007年3月份召开的气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俞鸿儒曾说,从事基础研究、创新研究,不可能全面创新;全面创新是空谈,做不到的,这对于中国气动中心的工作很有启发。2008年,“5·12”特大地震对气动中心的影响很大。由于空气动力学研究是国家的重大战略资源,为了使其免遭地质灾害的影响,气动中心在绵阳建了一个占地4000亩的科研实验新区。俞鸿儒对气动中心的灾后恢复非常关心,新区建设自始至终也都贯彻着他这位老人家的心血。从震后恢复和各种科研专项的配套,到整个新区的建设,从一开始立项论证、顶层设计、可研研究、到反反复复几次具体的规划设计和实施方案评审,共四十余次会议,他悉数参加,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一些科技干部还去他家里请教,他都非常细致地分析,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气动中心设备能力不断提升、任务量成倍增长、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俞鸿儒深刻地指出气动中心创新研究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是气动中心一直在讨论的“俞院士之问”。气动中心原主任阮祥新曾经常和俞鸿儒讨论,气动中心究竟应如何发展?俞鸿儒认为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重视基础研究,二是要培养拔尖性人才。
7 理解创新
工程科学的一大特点是介于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之间,充当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1947年钱学森回国时曾在国内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所学校进行了“工程和工程科学”为主题的学术讲演[19]。1957年,钱学森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技术科学》的论文。后来国内为了与西方对接,又把钱老的思想称之为工程科学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俞鸿儒衷心希望能把钱学森、郭永怀两位先生奠定的“工程科学”思想能够薪火相传,他多次参加关于钱学森、郭永怀两位老师的纪念活动(图10),向广大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分享他在科研实践中关于“工程科学”思想的体会(图11)。

图10 1999年俞鸿儒参加郭永怀先生诞辰90周年留影

图11 俞鸿儒给中国科学院大学工学院研究生(2016年12月20日,张志会拍摄)
(1)以创新为己任
“钱学森之问”是钱老晚年的一大忧虑。他注意到,人们通常认为,钱老说的是杰出人才的培养。但在俞鸿儒看来,钱老说的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钱所长的另一个忧虑是“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钱学森在1995年给王寿云等六同志的信中曾提到,1960年代,我国科技人员先于“夸克”理论提出了“层子”理论、率先合成了人工胰岛素、成功实现了氢弹引爆独特技术。但是今天呢?他强调钱老的两个忧虑的核心都是关于创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新? 他认为,“创新”包括革新(innovation)和创造(Creation)两方面内容。钱学森所指的“创新”,是创造而不是革新。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革新很重要,大多数人要做革新,但是,不能让革新代替或消灭了创造。而如果对“创造”活动采用同样的方法管理,将使其处境艰难。
作为一个视创新为科研之生命的科学家,俞鸿儒深知选题的重要性。他常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也非常赞同钱学森的一句话:做科研就是要做国外没有解决的事情,或者国内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常常跟实验室的同事和学生说,做科研就是要有这样的抱负,否则说明我们的民族信心是有问题的。
他还特别愿意对年轻人传授选题的方法:首先,选题要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否则就是空中楼阁;第二,理论上要正确;第三,要有可行的方法;最后,要值得长期去奋斗。他自己做爆轰驱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国的科研大环境一度重论文发表、重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在这种科研导向下,很多人不得不在科研时以论文马首是瞻。俞鸿儒却不为所动,以解决科学问题为目的,还专门挑选那些难题去攻克。很多跟随俞鸿儒多年的学生和团队成员发现,在俞老的影响下,自己的科研观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笃定方向做深做透
同辈人里多少人因各种原因经历过科研方向的转变,科研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成就。俞鸿儒则是一个例外。郑哲敏院士曾这样评价俞鸿儒:“毫无疑问,他是激波管和激波风洞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俞先生做事情、搞科研很实在,在业务上也比较专一,一直做激波管,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激波管技术的发展,是位真正的专家。不像我,我还换过几次研究方向(笑)。”[20]
他深知科研是要不断聚焦,才能更加精深。如他自己所言:科学研究工作的目标是认识未知世界的规律,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难题。其实在参加科研工作之初,他曾深感极其困难。当在物质条件、学术交流、评价标准等处于不利环境,特别是个人条件并不优越时,难以获取重大成就。但必须抵御住追随、临摹他人的诱惑,尽全力做出有特色的工作。他也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专一于激波管与激波风洞研究,攻坚克难,终于突破了爆轰驱动试验时间短、实验气流不稳定的世界级难题。
俞鸿儒本人身兼工程师和科学家于一身,却也始终面临着一些质疑。有人说,这种大型装置虽然可以做很多实验,但对基础研究的推动比较弱。对他而言,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在个人研究上,他更倾向于在遇到问题时从理论上透彻地分析问题,再以公式或其他方式来解决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靠模拟去枚举。以风洞实验推动基础研究,他能信手拈来国外不少实例。
(3)独特的辩证思维
受到父亲的影响,俞鸿儒很小就形成了辩证思维,这一点在他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一是以平常心看待反对意见。一般人听到批评的话和反对意见心里就不舒服。他却从内心真心欢迎反对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可以提醒自己未注意到的问题,指出错误。这些指责也可以促使人深入思考。他还认为,反对者的多寡反映了一个人工作的新颖度。反对者愈多,说明新颖度愈强。而那些获得普遍赞成的项目难有重大创新。当然也有可能是反对者的意见提错了,你最好能回答出来他的错误,想问题也会更加深入。他经常回忆起自己当初做爆轰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因为当时做爆轰实验太危险了,且爆轰机理很难理解。
二是看事情要看两面。2003年,他书写治学格言:“读书要用两只眼睛,一只看纸面上的,另一只看纸的背面。”[21]他认为,读书和做学问就是要认真思考事物背后的本质。其次,高投入未必带来高产出,科研工作者不应该把精力耗费在“找钱”上。尽可能采用简单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有效途径。对于探索性项目的遴选,应在执行中挑选优秀项目并在实践中逐渐强化支持力度,摒弃“经费万能论”。
三是不迷信权威,树立科研信心。创造性创新研究的基石就在于发现错误和异常。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确实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抱着虚心的态度向他们学习是应该与有益的,但千万不能陷入到迷信盲从的地步。
对于现有的科技领域评奖机制,俞鸿儒也有不同的看法。周恒、张涵信、俞鸿儒、崔尔杰早在2007年就曾指出:我国的各种科学技术奖项太多,已经产生了若干负面影响,有必要考虑改进的办法。事实上,许多在科学和技术上比我们先进的国家并没有国家级的奖。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探讨取消所有的国家级奖是否可行[22]。
8 甘当铺路石
他对科学事业有着执着追求与创新奉献精神。自从1958年以来,他在激波管与激波风洞研制,以及气动力与气动热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17年底,他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首届“钱学森力学奖”何梁何利奖、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中国力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证书等各种科技成果奖共17项。2002年10月,美国航空航天协会出版的《Advanced Hypersonic Test Facility》全面介绍了力学所爆轰波驱动高焓激波风洞的研究进展。2000年,他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几十年来,他心里一直牢记郭先生的话,要甘做铺路石。他深深懂得,中国高温气体动力学事业要不断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青年人才是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因此,他积极推动高温气体动力学实验室的发展。自1958年担任力学所激波管组组长以来,俞鸿儒一直是力学所激波管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在原气动力学和气动物理联合实验室的基础上,在他和竺乃宜等人的努力下,1994年中科院批准力学所成立高温气体动力学实验室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第二年主持中科院气体动力学实验室,第三年该机构又升级为中科院开放实验室。1999年,71岁的他作为高温气体动力学开放实验室主任,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姜宗林,这一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他曾担任过该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荣誉主任。80岁后他还依然审慎思考实验室的长远发展,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
俞鸿儒对名利看得很淡,科研工作中总是选择“及时退出”,主动把荣誉让给年轻人。长试验时间激波风洞JF-12建成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他自己则退居二线。虽然这一耀眼的成果是在他的技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但是他却总是把自己列在功劳簿的后面位置。他经常说,排名对我们这些老人已经不重要了。爆轰驱动激波风洞的台子搭好了,戏唱得好不好就看年轻人了,应该多让年轻人走向台前。也正是因为俞鸿儒善于给“后浪”充足的发展空间,高温气动实验室的薪火传承愈加旺盛。
2016年3月27日,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将地面试验大奖授予俞鸿儒选定的接班人姜宗林,这一地面试验奖自1975年设立以来,一直无亚洲人获奖[23]。2015年8月16日中国力学大会授予力学所“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激波风洞”(JF-12)首届中国力学科学进步一等奖,2017年JF-12又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中科院杰出科技奖第一名。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研究团队几十年专心科研的结果。
张涵信院士曾这样概括迄今为止俞鸿儒的学术成就,认为他是“我国激波管和激波风洞研究及应用的开拓者”,是“我国爆轰驱动方法和原理以及低温新风洞的发明者”,“他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4]。如今,俞鸿儒院士已经92岁高龄,他依然在关心着我国高温气动与航天事业的发展。
[1] 张志会. 俞鸿儒:大音希声[N].中国科学报, 2017-07-31, 第8版.
[2] 童秉纲. 俞鸿儒论文选集·序[M]. 内部出版, 2013.
[3] Hertzberg A, Smith W E.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strong shock waves[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954, 25(1): 25.
[4] 俞鸿儒. 激波管风洞及其在传热实验研究方面的应用[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63: 1.
[5] 张志会. 一场被动的人才交换促成一双中科院院士[N]. 中国科学报, 2016-2-19, 第7版.
[6] Bertin J J, Cummings R M. Critical hypersonic aero thermo dynamic phenomena[J]. Annu. Rev. Fluid Mech., 2006, 38: 129-157.
[7] Hertzberg A, Smith W E.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strong shock waves[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954, 25(1): 130-131.
[8] Warren W R, Harris C J. A critique of high performance shock tube driving techniques[R].Aerospace Corp El Segundo Calf Lab Operation, 1969.
[9] 俞鸿儒, 赵伟, 袁生学. 氢氧爆轰驱动激波风洞的性能[J]. 气动实验与测量装置, 1993, 7(3): 39.
[10]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激波风洞及实验技术研究[G]. A011-208号.
[11] Edwards D H, Williams G T, Breeze J C. Pressure and Velocity Measurements on Detonation Waves in Hydrogen-oxygen Mixture[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1959, 4: 497-517.
[12] Yu H R.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hock Tube Application[A]// Takayama K(ed) Proc. Of the 1989 Nat. Symposium on Shock Wave Phenomena, Shock Wave Res. Centre[C]. Sandai: Tohoku University, 1989: 1-2.
[13] Yu H R, Esser B, Lenartz M, Grönig H. Gaseous detona tion driver for a shock tunnel[J]. Shock Waves, 1992(2): 245-254.
[14] 中科院力学所档案. 关于俞鸿儒同志赴德国合作研究一个月的请示[G]. 中科院力学所[(94)力发外字第097号], 1994年7月27日[A].关于出访欧洲人员请示批复. 1994-03-008: 80-92.
[15] 张志会, 马连轶. 20世纪末中美航天商业发射的合作与冲突[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25(3): 76-85, 127.
[16] Anderson J D. Hypersonic and High Temperature Gas Dynamics,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J]. Inc.: Reston, VA, USA, 2006: 395-406.
[17] 姜宗林, 俞鸿儒. 高超声速激波风洞研究进展[J]. 力学进展, 2009, 39(6): 766.
[18] 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实验室提供. 日本东北大学流体科学研究所高山和喜教授给姜宗林的来信[G]. 2012-2-15.
[19]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10卷——竺可桢日记五集(1946-1947)[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495.
[20] 张志会. 郑哲敏口述访谈整理[G]. 2016-1-18.
[21] 科学时报社编. 中国院士治学格言手迹[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291. (又见:李浩鸣, 蒋晶丽主编. 院士心语[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44)
[22] 周恒, 张涵信, 俞鸿儒, 等. 应改进科学技术奖项设立及评审[J]. 气象软科学, 2007(4): 157-157.
[23] 中国空气动力学会. 姜宗林研究员赢得国际航空航天地面试验大奖[J]. 空气动力学学报, 2016, 34(2).
[24] 中国空气动力学会. 序祝贺俞鸿儒院士八十华诞[G]. 近代高温气体动力学研讨会论文集, 2008 (内部资料).
Academician Yu Hongru: Pioneer of New Detonation Driving Method for Shock Tubes
Zhang Zhihu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China)
Yu Hongru stud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his early year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1956, he was ad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Qian Xuesen, Lin Tongji, and other masters, as well as his inherent quality and understanding, he embarked on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journey of “shock wave phenomenon and its application” . Yu Hongru abandoned the techniques used in other countr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country and explored a low-cost and efficient high-enthalpy experimental method detonation drive, which was widely praised by his international peers. He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application of shock tube and shock tunnel technology in national defense,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he researched the performance of a hypersonic ramjet and explored a new concept of using a catalytic composite method to improve the thrust of ramjets. Yu is also active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neumatic Center. He paved the way for the later reseachers.
Yu Hongru; shock tunnel; detonation drive; engineering science
2020–09–11;
2020–09–18
中国科协俞鸿儒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Y540011)、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人才项目(E0290132,Y9210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工程推动基础研究”(71603254,Y611113)
张志会(1982–),女,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zhangzhh@ihns.ac.cn
O4-33
A
1674-4969(2020)05-0509-14
10.3724/SP.J.1224.2020.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