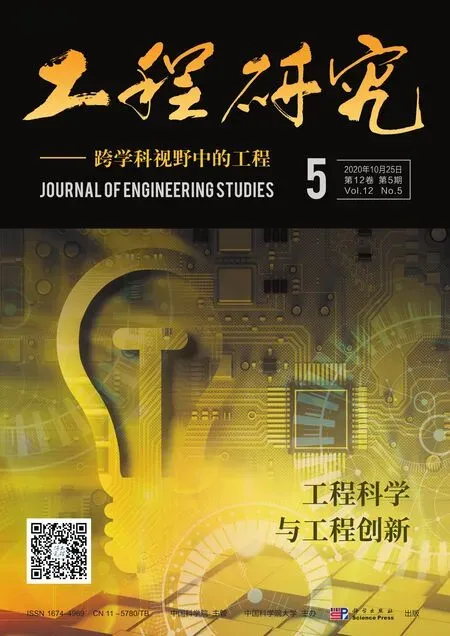生命的创造与延续——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
2020-12-30周琪
周 琪
“工程科学与工程创新”专刊
生命的创造与延续——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
周 琪
(中国科学院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北京 100101)
生命科学旨在探索和揭示生命本质,运用多种生物技术造福人类。受限于早期生物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人们难于一窥生命的起源、发育和遗传奥秘的全貌。经过长达百年的知识累积和技术进步,工程学理念逐渐被引入现代生物学中,人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日趋深入,并逐步具备改造甚至创造生命的能力。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拓宽了工程科学的疆域,工程科学的宽阔视野和方法则促进基础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逐渐在当代为造福人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结合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创新实践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了生命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生物技术与工程科学结合路径的设计与发展前景。
生命科学;生物工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工程科学
生命本质如何、起源于何处、将发展至何方,这些极富哲学意蕴的科学命题,是生命科学领域长期以来的未解难题。历经数十亿年的进化,地球从没有生命形态到出现生命形态,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再到今天的人类。人类自身所承载的信息量,迄今仍难以被完全破解。工程科学是将基础科学中的真理转化为人类福利的实际方法的技能。工程科学在上天、入地、下海等方面,已达到空前水平。然而,人类对生命的了解仍然是沧海一粟。随着工程科学的引入,人类对于自身和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从以往诸如对外形、身高、语言、举止等的形态描述,发展到基因解读、遗传分析和分子识别。从基因组计划、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到近期的生命创造技术,这样的发展路径提升了人类认识、解读和改造生命的能力。工程科学的发展让我们有可能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质。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将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与生物技术、工程科学相结合,从而加速人们对生命过程中遗传、发育、疾病、衰老以及进化等现象的深入探索与解析,改造甚至创造生命系统。
1 工程科学理念引入生命科学,增强人类认知生命本质的能力
《Science》创刊125周年时公布了125个科学问题,其中,多达40%与生命科学相关。如:人类寿命到底可以延长多久,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记忆如何储存和恢复,大脑如何建立道德观念,人的道德感、羞耻感由何而来,为什么人类基因会如此之少,基因组中的“垃圾 (junk) ”有何作用,除了继承突变,基因组如何改变,等等。解答此类科学问题是基础科学的驱动力。而科学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工程科学的理念和技术支持。
钱学森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工程科学最重要的本质是将基础科学中的真理转化为人类福利的实际方法的技能”[1]。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生物体与机器在自动控制、通信和统计动力学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共性。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遭遇的瓶颈阻碍,也让生物学家开始从崭新的工程科学视角出发,试图通过工程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解决领域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疑惑,进一步探寻生命的本质,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目的。
生命科学与工程科学的汇聚非常重要,以笔者的研究领域——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为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生命科学与工程科学的结合体。生命的起始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受精开始形成胚胎、胎儿、胎儿出生发育为一个健康的个体。然而,生命的形成实际却非常复杂。人的十月怀胎,从工程科学角度来讲,是最复杂的系统:从最开始一个受精卵细胞,历经多个发育阶段,最终构造成完整的个体——健康的人。随着人的生长发育、年龄增长,体内细胞的数量和功能的增殖和衰减彼此交替,便是生命体发育、衰老直至死亡的完整过程。生命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细胞死亡,但我们依然活得很好,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干细胞不断增殖,在更新着我们的机体。干细胞,简单说就是可以不断增殖、自我更新、具有多向分化潜能,能够分化形成多种细胞类型的细胞。干细胞种类多样,有具有高度发育潜能的胚胎干细胞,也有出生后支撑皮肤、毛发等多个器官生长的成体干细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干细胞,来逆转发育和衰老的进程?
过去这些年,基于干细胞,我们尝试建立一些生命逆转的手段。我们从体细胞创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生命——第一个来源于诱导多能干细胞即非胚胎来源的生命[2];创造了一种从来不存在的干细胞——单倍体干细胞,这类细胞甚至可以替代精子或卵子,最终发育成一个健康的生命体[3];我们用干细胞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命[4],它所继承的父本和母本基因组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干细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人造的生命;利用这些细胞,绕开哺乳动物的同性生殖障碍,我们实现了由两个雌性小鼠生成健康后代[5],也创造出了来自两个雄性小鼠的后代[6](图1)。我们也创造了一种在自然界不存在的细胞类型[7],这种细胞的基因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一半来自于小鼠,一半来自于大鼠。一方面,这些人造细胞为回答进化和发育生物学的众多科学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模型和工具;另一方面,这种种间杂合方式也为未来创造能适应新的极端环境的新物种提供了可能。上述这些成果说明,基础科学的目的是回答那些以前所不知道的问题、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科学需要知识的不断累积、技术的不断突破去发现自然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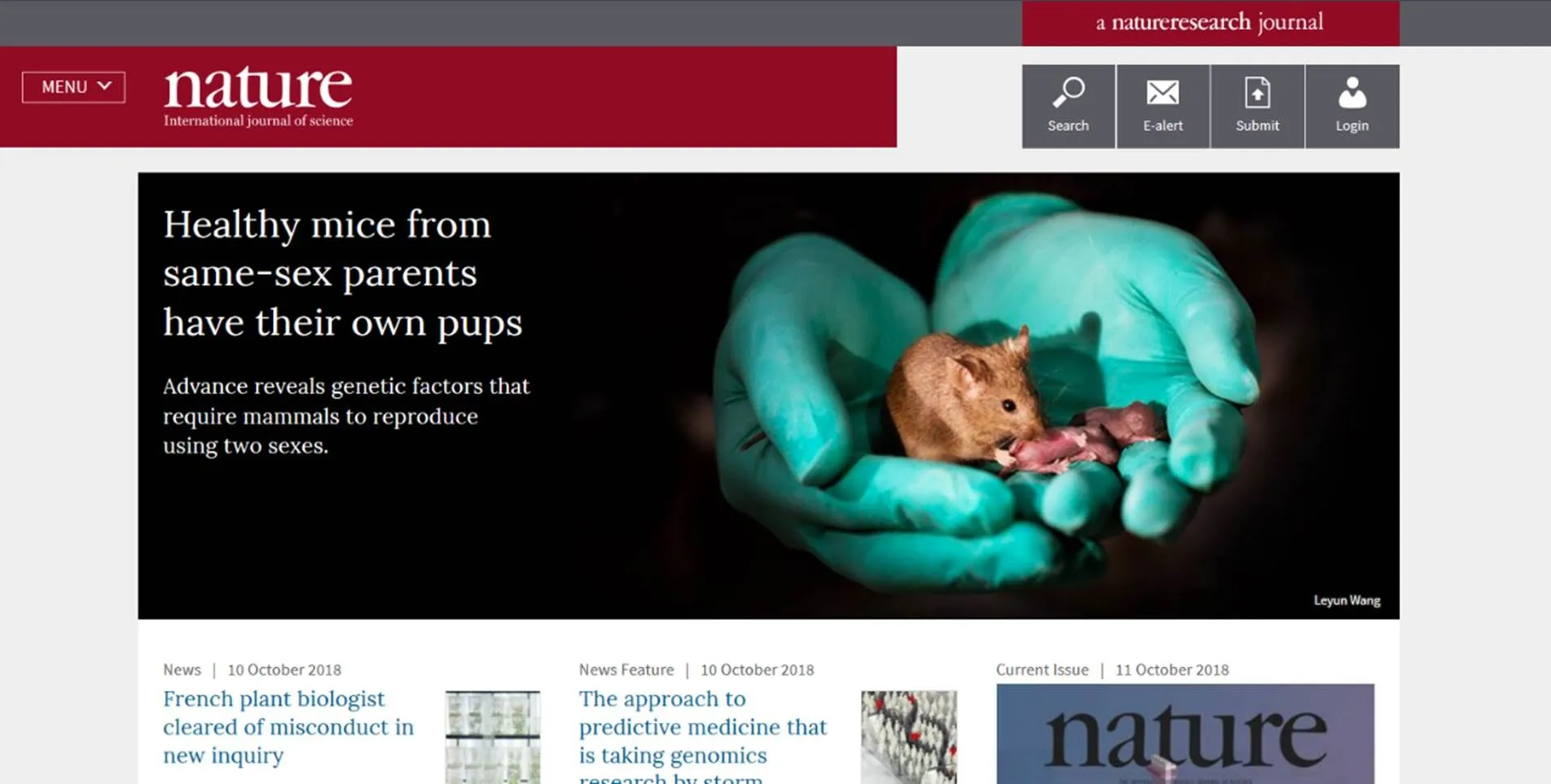
图1 Nature网站报道同性生殖小鼠成果
然而,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真正的科学价值在于服务人类。我们说,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第三次医学革命。革命在哪?我们尝试将干细胞发展成为药物,挑战的是一个全新类型的药物,这是一个历史性、革命性的跨越。要跨这一步很难,因为细胞是活的,由细胞构成的药物是活的药物。活的药物怎么研发?除了要考虑到药物研发中所有的问题,还要关注很多活细胞作为药物特有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工程学路径。众所周知,工程科学中设计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从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布局,从开始就把全路径以及各环节设计好。我们也清楚,系统性的任务,尤其是工程领域,特别要注意短板效应。从最开始设计到执行和完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累积。
以干细胞应用方面的一个案例来说明。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其主要发病原因是大脑黑质中多巴胺神经细胞大量死亡,导致纹状体中多巴胺的水平下降。我们设想研发一种细胞药物替代传统药物治疗,通过将胚胎干细胞在体外分化出的多巴胺神经细胞移植到帕金森病人的大脑中,来替代受损的神经细胞。分化后的多巴胺神经细胞如果具有自然存在的多巴胺神经细胞的功能,就可以在脑内进一步分化成熟并分泌多巴胺递质,从而改善患者行为。而这一治疗方案的实现,离不开工程科学的设计思路,从细胞资源库干细胞的存储和运输、细胞分化和质控的关键技术、细胞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系统评价、到临床研究体系等需要建立多种平台和流程。
其中,为更好地判断干细胞能否用于治疗帕金森病人,我们在扎实的体外实验和小动物验证的基础上,又选择了帕金森症猴模型进行长期评估。将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多巴胺神经细胞移植到猴脑里,在多个时间节点(7个月、1年和2年)分别进行评估,证明人的神经元可长期存活于猴脑,而且细胞是安全且有功能的[8]。在此基础上,我们启动了经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式备案的首批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同年9月份开始第一例临床研究,1~2年评估之后启动了下一期临床实验。在启动临床研究项目不久,一直对中国干细胞研究非常关注的《Nature》新闻发表了一篇长论,评价其为“中国首个基于人胚干细胞的临床研究,世界首个利用受精卵来源人胚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临床研究”。这是一个前后布局了12年的项目,期间解决了适应症的选择、细胞资源的获得、关键技术的建立、标准与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动物模型的创制和使用、临床机构的沟通和培训等各种瓶颈,并针对潜在风险形成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从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汇聚和关联及其造福于人类的潜力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 新时代工程科学拓展生命科学研究的广度、维度和尺度
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对技术发展和生产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工程科学则更倾向于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付诸生产实践和应用,其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实践性、预期性等都更强。可以说它们对应的是两种精神。基础科学对应的是科学精神,求真、求实、追寻那些未知科学问题的解决;工程科学对应的是工匠精神,敬业、精益,追求极致的高质量产品和工序。学科各有分工,基础科学、工程科学之间并不矛盾。它们互为依托、互为依赖、相辅相成。工程科学融入生命科学,以生物技术的形式体现,拓展了生物技术的广度、维度和尺度,这必将带来生命科学领域革命性的突飞猛进发展。
第一,生物技术发展的广度不断拓展。多学科聚集、综合交叉汇聚,并以目标导向集成不同领域的人和物,联合攻关,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学科不应越做越窄,越做越小,发挥多学科的特色,有效整合多学科的优势是最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和学科发展的广度也会推动生物技术领域向其他多学科领域渗透和扩展,并最终推动生物医药技术、生物农业技术、生物工业技术、生物能源技术等相关领域的发展。
第二,生物技术发展的维度不断拓展。生物技术向组学计划、谱系计划等多维发展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前面讲到生命孕育,从维度上讲,早期胚胎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细胞从几百个扩充到几千个,从单一细胞群体变成多种器官的雏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提出包括时间维度在内的三维的基因表达谱系计划,这样就把研究维度扩展到了四维[9],更加有利于人类理解和认识生育和生命过程。
第三,生物技术发展的尺度不断拓展。生物技术自身的发展将会拓展至更精细和宏观的研究尺度,包括个体、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器、基因组等。最开始发明显微镜的时候,人类在显微镜下看到细胞。今天,有了冷冻电子显微技术,可以看到更为精细的细胞和蛋白结构。未来还会有更先进的技术,将使我们能对事物分解得越来越细。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尺度的放大。把不同尺度的小的元件整合到一起,在另一个尺度,新的生命就出现了,这一梦想在未来十数年可能变为现实。
3 工程科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与发展进程
工程科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一方面拓宽了工程科学的疆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有可能革命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进程。至少可能体现以下这几大方面。
第一,改变我们的生活。推前5年我们不会相信微信在如此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不会相信共享单车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且覆盖面这么广。互联网和大数据依托的技术体系改变了人们很多生活方式,例如支付手段的变化,让人们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带着信用卡、现金出门,一个手机刷遍天下。那么生物工程技术的未来呢?今天看到的业态是,人们吃的牛排一定要从牛的养殖开始,从牛的屠宰开始,从冷链加工开始;我们的粮食一定从种植开始。未来还会不会这样?俄罗斯已计划在空间站尝试生物3D打印机,以规模化生产和制备可供地面和宇宙环境里食用的食品。工程技术、生物技术逐步改变着传统的饮食结构:餐桌上的牛排未来可能来自于细胞墨水的3D打印、细胞培养和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第二,改变我们的生理。众所周知,很多生理性的差异源于遗传。比如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登上高原,如果从事剧烈的运动或长时间的体力活动,会出现心、脑水肿和高原病。而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没有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差异,他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性进化。再比如人体机能的衰减,人过了40岁以后平均每年肌肉的衰减量是1%。迄今为止公认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延缓肌肉衰减,就是运动。我们也在尝试很多办法,试图让肌肉的衰减、细胞功能的衰减、身体机能的衰减等通过其他办法来延缓。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发表了世界上首例遗传增强的人类血管细胞[10]。科学家通过对这种细胞的基因和遗传特性进行“优化”,在细胞水平上验证了这些基因修饰可以改变人类的生理机能。也许未来通过基因修饰,可增强人体机能,使人长寿不易患病。
第三,改变我们的认知。《Science》125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是“人的意识本体是什么?”解读了基因组以后,人们仍然不知道意识存在于哪里。父辈和子代之间的基因被传递,但记忆没有传递。如果有一天可以知道了记忆在哪里的话,是不是可以存储和复制记忆?知识是不是可以转移?到现在为止,人工智能一直仿照人类的生物神经网络。生物神经网络是指大脑里面的神经元细胞、突触等形成的网络,实际上是产生意识的关键部分。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有一天可能会在生物神经网络的功能连接里面找到记忆的载体,找到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基础,那可能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和时代。
第四,改变人类的繁衍。哺乳动物的繁衍和人类的繁衍是相似的,都是从受精卵开始到下一代。人类一直在尝试构建人造子宫,希望能够体外支持生命的发育。众所周知,临床上极早产儿存活率非常低,科学家报道极端早产的胎羊可以在工程化构建的生物袋(人造子宫)中完成后期发育。与此同时,我国科学家第一次把非人灵长类食蟹猴的受精卵,在体外培养发育超过20天[11]。20天的时间意味着胚胎在发育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多系统和器官的早期发育雏形的构建。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发育和工程的角度,实现了灵长类动物胚胎在脱离母体子宫的情况下发育到这一时期。未来胚胎体外发育的探索,从起始往后以及从终末往前双管齐下,最终有望实现哺乳动物生命全周期的体外孕育。近期我们也在组建一个新的工程实验室,希望搭建人造子宫,完成人造生命在人造子宫里的发育。
第五,改变生命发展进程。2019年11月28日,来自以色列威茨曼科学研究所的Ron Milo教授与其合作者们在《Cell》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他们在实验室内构建出只利用二氧化碳(CO2)作为唯一碳源的自养型大肠杆菌的研究成果[12]。以前我们知道,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可以不吃不喝,而动物做不到。这种利用能量维持生命的方式,是数十亿年生命进化的产物。现在科学家们第一次报道将异养型生物细菌改造为自养型,其改造时间仅用了200天。如果以色列科学家这篇论文是可重复的,生物进化限制就不存在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命题:将来这种建立在工程生物技术基础上的生命进化,连同我们对于植物、动物、微生物最简单的界定,都会发生本质变化。
生物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伦理争议与挑战。这些年在社会伦理方面,比如说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困惑和挑战就非常多。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这个领域里就一直争议不断。如何化解科技飞速发展与包括伦理治理在内的科技治理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是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乃至整个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的挑战会非常大。当前,新兴技术、学科不断涌现,技术汇聚,学科融合,前沿领域不断延伸。在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等基础科学领域,人类正在或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常常回顾先前几次科学和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变革,如果回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回溯到量子理论的产生,不难发现,这些时代距今已有很长时间。那么,当前科技革命之后,预测下一个科学革命在何时?前述所提及的《Science》125个科学问题,诸如物质与意识的本质、物种的繁衍等,无论哪一条,一旦被攻破,都将带来新一轮科学技术和产业变革,也将革命性地改变整个社会。
4 结语
基础科学为工程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工程科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检验手段和新经验。二者互为依托、互为依赖、相辅相成。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拓宽了工程科学的疆域,工程科学的宽阔视野和方法则进一步促进基础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基础科学与包括工程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的融合汇聚是基础研究飞速走向实际应用的根本路径,是更好地服务人类健康和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1] 钱学森. 工程和工程科学.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J]. 2010, 2(4): 282-289.
[2] Zhao X Y, Li W, Lv Z, et al. iPS cells produce viable mice through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Nature[J]. 2009, 461(7260): 86-88.
[3] Li W, Shuai L, Wan H F, et al. Androgenetic haploid embryonic stem cells produce live transgenic mice. Nature[J]. 2012, 490(7420): 407-411.
[4] Li X, Wang J Q, Wang L Y, et al. Co-participation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 genomes before the blastocyst stage is not required for full-term development of mouse embryos. 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J]. 2015, 7(5): 486-488.
[5] Li Z K, Wan H F, Feng G H, et al. Birth of fertile bimaternal offspring following intracytoplasmic injection of parthenogenetic haploid embryonic stem cells. Cell Research[J]. 2016, 26(1): 135-138.
[6] Li Z K, Wang L Y, Wang L B, et al. Generation of Bimaternal and Bipaternal Mice from Hypomethylated Haploid ESCs with Imprinting Region Deletions. Cell Stem Cell[J]. 2018, 23(5): 665-676.
[7] Li X, Cui X L, Wang J Q, et al.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use-Rat Allodiploid Embryonic Stem Cells. Cell[J]. 2016, 164(1): 279-292.
[8] Wang Y K, Zhu W W, Wu M H, et al. Human Clinical-Grade Parthenogenetic ESC-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Recover Locomotive Defects of Nonhuman Primate Models of Parkinson’s Disease. Stem Cell Reports[J]. 2018, 11(1): 171-182.
[9] Peng G D, Suo S B, Cui G Z, et al. Molecular architecture of lineage allocation and tissue organization in early mouse embryo. Nature[J]. 2019, 572(7770): 528-532.
[10] Yan P, Li Q, Wang L, et al. FOXO3-Engineered Human ESC-Derived Vascular Cells Promote Vascular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Cell Stem Cell[J]. 2019, 24(3): 447-461.
[11] Ma H X, Zhai J L, Wan H F, et al. In vitro culture of cynomolgus monkey embryos beyond early gastrulation. Science[J]. 2019, 366(6467): 836-844.
[12] Gleizer S, Ben-Nissan R, Bar-On Y M, et al. Conversion of Escherichia coli to Generate All Biomass Carbon from CO2. Cell[J]. 2019, 179(6): 1255-1263.
Cre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Life: from Basic Science to Applied Science
Zhou Qi
(Institute for Stem Cell and Regener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Life sciences aim to benefit mankind through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life by means of various bio-techniques. Due to the lack of advanced techniques in the past,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life has remained remarkably limit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ife has been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t is no longer impossible to modify or even create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uxiliary to each other and jointly benefit humans, the advancement of biotechnology expands the scope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and the broad vision and methodolog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stem cell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discusses how basic research, bio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can be combined to improve human life.
life sciences; bioengineering; stem cell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engineering sciences
2020–06–10;
2020–09–15
周 琪(1970–),男,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为生殖、发育、干细胞的研究与转化。E-mail:zhouqi@ioz.ac.cn
Q2;N03
A
1674-4969(2020)05-0457-06
10.3724/SP.J.1224.2020.00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