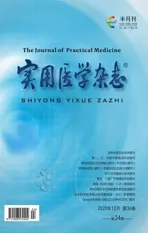抗结核药物致肝损伤的预防与治疗药物选择
2020-12-30钟洪兰
钟洪兰
广州市胸科医院(广州510095)
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DILI)是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表现,发生率高、危害性大,占我国药物性肝损伤的五分之一多,临床表现可为转氨酶一过性轻度升高,严重可引起肝衰竭,甚至死亡,部分患者会因此被迫中止抗结核治疗,结核病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起耐药和治疗失败。
ATB⁃DILI 产生的病理过程是抗结核药物或其代谢产物直接毒害损伤肝细胞或抗结核药物及其代谢产物激活触发多种炎症免疫通路造成变态反应性肝细胞免疫损伤和诱导肝细胞凋亡。ATB⁃DILI可以是转氨酶一过性轻度升高[1],也可表现为急性肝炎,严重的发展为暴发性肝细胞坏死,少数患者呈慢性肝炎表现。肝损伤的确认主要依据血清生化检测结果:谷丙转氨酶(ALT)>3 倍正常值上限(ULN)和(或)总胆红素(TBIL)≥2倍ULN;或碱性磷酸酶(ALP)、天冬氨酸氨基转氨酶(AST)和TBIL同时升高,且至少1项≥2倍ULN。ATB⁃DILI 发生率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有较大差异,多介于2.0%~28.0%之间,究其原因可能与种族、社会经济水平、地域差异、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情况及研究方法不同有关,包括纳入研究对象不同(结核病程度、分型、合并基础肝病与否、危险因素等)及ATB⁃DILI 的诊断标准不同等。
ATB⁃DILI 的正确处置思路为:(1)判断抗结核化疗时是否预防护肝及选择护肝药的品种;(2)确认肝损伤;(3)确定损伤与抗结核药物的关系;(4)判断肝损伤的分型和分级;(5)选择确定肝损伤治疗方案,具体可参照《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2019年版)》(以下简称指南2019)。该指南明确了ATB⁃DILI 的诊断是基于血清生化检测指标的异常,且肝损伤应与抗结核药物存在对应关系,排除其他非抗结核药物因素。
1 ATB⁃DILI 的危险因素
明确和了解危险因素对于ATB⁃DILI 的预防、及早发现和诊断、及时干预有重要意义。ATB⁃DILI 的危险因素可分为宿主因素、药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目前我国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危险因素有高龄、酗酒、妊娠、女性、基础肝病(各种病毒感染肝炎及携带者、化学性肝炎、血吸虫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炎、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纤维化、原发性或继发性肝肿瘤等)、营养不良、HIV 感染、重症结核、合并肾病、风湿病、糖尿病、脂代谢紊乱、肿瘤、心脏病等;慢乙酰化者、N⁃2 酰转移酶、P450 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多态性者;合并使用其他肝毒性药物[部分抗菌药、唑类抗真菌药、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降血糖、降血脂药,肿瘤内分泌治疗药、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类等)]。这些危险因素的提出有助于临床医生有效甄别ATB⁃DILI 高危人群[2-3]。老年人营养不良、代谢功能减退导致这部分人群发生肝损伤的风险升高;HIV感染人群也呈现逐年增多态势;Meta 分析显示,合并肝炎病毒感染的结核病患者ATB⁃DILI 发生率明显高于非肝炎病毒感染结核病患者[4]。在抗结核化疗中应特别关注合并这些高危因素的易感人群。另外需了解和掌握的是,不同的抗结核药物其引起ATB⁃DILI 发生率也有较大的差异,易致ATB⁃DILI 的有异烟肼、吡嗪酰胺、利福霉素、丙硫异烟胺、对氨基水杨酸;发生肝损伤频率较低的有氟喹诺酮类、氯法齐明、贝达喹啉、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德拉马尼、乙胺丁醇、克拉霉素、美罗培南等;发生率极低的有氨基糖苷类、环丝氨酸、卷曲霉素、利奈唑胺。如上述危险因素所述,合并用药时肝毒性的叠加和协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是ATB⁃DILI 发生风险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抗结核药与肝毒性药物合用时,ATB⁃DILI 发生率增加[5]。另外,食品安全、中药炮制污染、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大等社会问题也会增加肝功能损害的风险。
2 ATB⁃DILI 的发生机制
ATB⁃DILI 发生机制较复杂,主要涉及免疫机制、非免疫机制和遗传因素机制等[6],单一机制引起ATB⁃DILI 不常见,多为多种机制递次或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免疫机制主要涉及抗结核药物、活性代谢物及代谢产生的超氧化物、过氧亚硝酸盐、自由基直接进入肝细胞损伤线粒体、微粒体,表现出药物、活性代谢物的直接肝毒性和超氧化物、过氧亚硝酸盐、自由基的氧化应激损伤。这类ATB⁃DILI 具有可预见性和剂量依赖性;免疫机制主要为抗结核药物及其代谢产物激活触发多种炎症免疫通路造成变态反应性肝细胞免疫损伤和诱导肝细胞凋亡,是ATB⁃DILI 的主要发生机制,表现出不可预见、无剂量依赖性的特异性肝毒性作用[7]。具体表现:抗结核药物或其活性代谢物使机体组胺蓄积引发I 型变态反应。活性代谢产物作用于肝脏蛋白质引起损伤和凋亡,产生TNF⁃α和IFN⁃γ等危险信号激活细胞免疫,诱导产生适应性免疫攻击。部分抗结核药物或代谢产物作为半抗原与宿主蛋白结合以半抗原形成免疫复合物引发Ⅱ、Ⅲ、Ⅳ型变态反应而致肝损害,根据识别抗原的不同,表现为自身免疫应答(识别宿主蛋白)和抗结核药物免疫应答(识别抗结核药物或代谢产物)[8-9]。适应性免疫攻击可引起肝和肝外损伤,肝外损伤可表现为发热和皮疹等。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等导致肝毒性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且抗结核治疗往往需要多药联用,故肝毒性的发生很难精确确定是哪一种单药引发抑或是多种药物共同叠加或协同引发。
3 ATB⁃DILI 的临床分型和诊断
根据患者病程ATB⁃DILI 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病程通常发生在6 个月内;临床上ATB⁃DILI 绝大部分为急性,胆汁淤积型DILI 易进展为慢性。根据受损靶细胞类型可分为四型,具体是根据血清生化指标值结合R 值综合判定[R=(ALT 实测值/ALTULN)/(ALP 实测值/ALPULN)]。肝细胞损伤型(ALT ≥3 倍ULN,且R ≥5)、胆汁淤积型(ALP ≥2倍ULN,且R ≤2)、肝血管损伤型和混合型(ALT ≥3倍ULN,ALP ≥2倍ULN,且2 ATB⁃DILI 临床表现各异,程度不一,无特异性,多发生在用药后1 周至3 个月内,主要包括肝脏系统异常导致的临床表现和超敏反应的全身表现,可以是转氨酶一过性轻度升高,严重的发展为暴发性肝细胞坏死。指南2019 根据不同临床表现分为6 类,包括肝适应性变化、急性肝炎或肝细胞损伤、急性胆汁淤积、超敏反应性肝损伤、急性肝功能衰竭和慢性肝损伤,囊括了从无临床症状到肝衰竭的所有类型。 肝损伤的诊断往往通过血清生化检查和临床表现得出,而肝损伤是否与抗结核药物存在对应关系需要综合分析,因为影响因素众多,常常很难得出确定性的结论,主要是排除性诊断,可通过RUCAM 评分量表完成。完整、详细地采集患者的既往史、用药史(尤其注意包括中药膳食补充剂等服用史)、过敏史以及危险因素(高龄、酗酒、营养不良、肝病基础等)尤为重要。指南2019 给出了4 条诊断标准:(1)肝损发生在抗结核药物治疗5 d 至2 个月内,有特异质反应者可在5 d 内发生。(2)停药后异常肝脏生化指标迅速恢复。(3)必须排除其他病因或疾病所致的肝损伤。(4)再次用药反应阳性。“再次用药阳性”对于判定ATB⁃DILI 是重要依据,但实际上这一操作却很难实施。它存在很大的治疗风险,尤其对于严重肝损伤的患者,可能产生致命风险,且再次用药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上一次肝损伤不是该药导致的嫌疑,需结合临床情况综合分析。 由于临床实际情况复杂,确诊ATB⁃DILI 通常是困难的。指南2019 推荐RUCAM 评分表量化评估作为疑似病例诊断标准。多篇文献[10-13]报道,改良的RUCAM 评分系统应用于药物性肝损害的诊断,更加简便可行,具有较高的诊断可操作性和准确率,更符合临床诊断。 如上所述,ATB⁃DILI 的诊断和分型目前主要是基于血清生化检测指标ALT、AST、TBIL、ALP 及R 值等动态变化结果进行判断,且R 值的动态变化有助于准确地判断ATB⁃DILI 的临床类型及其演变。ATB⁃DILI的确诊和分型对于护肝治疗药物的选择及ATB⁃DILI 处置对策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在临床实践中,抗结核化疗前、化疗过程中及时全面的检测上述生化指标及在病程中的不同时机计算R 值很重要。 首要措施是停用导致ATB⁃DILI 的可疑药物。(1)对于无明显症状及黄疸者且ALT<3倍ULN,停用肝损伤发生率高的抗结核药物,同时保肝治疗并密切观察进展;(2)对于总胆红素≥2 倍ULN,或ALT ≥3倍ULN,停用肝损伤相关抗结核药并保肝治疗;(3)或总胆红素≥3倍ULN,或ALT ≥5倍ULN,或ALT ≥3倍ULN 伴黄疸、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停用所有与肝损伤相关的抗结核药并监测PTA 变化,积极保肝治疗。 炎症几乎存在于所有肝病之中,包括ATB⁃DILI,是肝脏疾病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癌的主要驱动。对于ATB⁃DILI 的治疗,应秉承抗炎保肝的理念[14-16]。 保肝药物品种繁多,保肝机制各有不同,保肝药物的合理使用不仅可使保肝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用药。保肝药物选择原则应考虑药物的护肝机制、肝损伤类型及程度、临床表现等因素,同时应兼顾药物的性价比。 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抗自由基、稳定肝细胞膜、降酶退黄药物、多重护肝机制的保肝药物。主要代表药物有还原型谷胱甘肽、硫普罗宁,水飞蓟素,甘草酸制剂,双环醇。还原型谷胱甘肽、硫普罗宁分子中含有巯基,具有还原性,可结合抗结核药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自由基,切断自由基对肝脏蛋白和酶蛋白分子的氧化应激损害,保护肝细胞和改善肝细胞内重要代谢;水飞蓟素和细胞膜组分结合,稳定肝细胞膜,可避免氧自由基或活性代谢物对膜磷酯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攻击损害;甘草酸制剂含中药甘草有效成分,具有类固醇样作用,有较强的抗炎抗变态反应,稳定肝细胞膜,减轻肝细胞损伤;双环醇具有保护细胞膜、线粒体、细胞核,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和活性抑制自由基的生成等多重作用机制。降酶退黄药在ATB⁃DILI 的治疗中有一定的意义。ALT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浆中,AST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肝细胞损伤后ALT、AST 释放入血,血生化检查转氨酶升高;高水平ALT 可致乏力、恶心、呕吐、纳差、腹胀等消化不良症状;使用降酶药物可以显著改善转氨酶升高引起的相关症状,如乏力、纳差、恶心等,单纯降酶护肝近期作用肯定,但无肝细胞保护作用,远期疗效差,易出现停药反跳现象。预防性应用单纯降酶药可能掩盖肝损时的ALT 升高,干扰诊断和延误正确处置,不建议将降酶药视为常规保肝药物而过多使用。“胆管”实际上是肝细胞膜的一部分,胆汁成分最初形成于肝细胞,胆汁代谢尤其是胆红素代谢异常也是肝细胞损害的表现之一。因此退黄有相应的保肝意义,尤其对于胆汁淤积型肝损伤。联苯双酯、熊去氧胆酸、腺苷蛋氨酸、茴三硫、门冬氨酸钾镁是降酶退黄的代表药物。腺苷三磷酸、辅酶A 和维生素类药物通过结合活性代谢产物起保肝作用,但应注意大剂量脂溶性维生素会加重肝脏负担。糖皮质激素宜用于治疗免疫机制介导的ATB⁃DILl,但可能引起结核病病情加重,需充分权衡利弊。重度肝损伤及肝衰竭可在上述不同保肝机制的联合用药下,加用N⁃乙酰半胱氨酸,必要时人工肝、人工肾支持治疗或肝移植。 合并基础肝病、致免疫力低下的疾病、合用其他肝毒性药物等危险因素的结核患者预防护肝的意义是肯定的。目前相对公认的危险因素包括:合并其他疾病者(肾病、风湿病、糖尿病、脂代谢紊乱、肿瘤、心脏病等);严重结核病患者等;遗传易感性因素(已知的慢乙酰化者,N⁃乙酰转移酶、P450 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多态性者);合并使用其他肝毒性药物(部分抗菌药,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降血糖,降血脂药,肿瘤内分泌治疗药等);合并使用免疫抑制剂(如糖皮质激素类等)。多篇文献[17-18]报道有基础肝病等危险因素的结核患者预防用药可有效降低肝损害发生率及其肝损程度。 无基础肝病等危险因素的结核病患者抗结核化疗预防保肝用药的意义存在争议。接受标准抗结核治疗方案后的患者约20%只是早期出现单纯的转氨酶升高,通常不需处理可自行恢复。无合并高危因素(高龄、嗜酒、营养不良、肝炎病毒感染、既往肝病病史、HIV 感染)的初治结核病患者预防护肝对抗结核化疗的药物性肝损害发生率无降低作用,与非预防护肝组药物性肝损害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19]。杨雪迎等研究[20]显示,两组预防护肝试验组的肝损伤发生率分别为14.7%和22.4%,而非预防对照组为11.0%,这可能与护肝药本身加重肝脏负担有关,也或与患者的原病(结核病)的分型、严重程度有关。另一研究[21]发现,对无高危因素(无肝炎、心、肾疾患、糖尿病)的初治活动型肺结核患者预防护肝仅能减少轻度肝损害的发生率,对中重度肝损害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一篇纳入了94 篇抗结核治疗预防护肝临床研究的Meta 分析[22]认为纳入文献质量差,绝大多数研究未进行特定人群和一般人群的亚组分析;大多数为伪随机分组;绝大多数研究未报告随机化方法、样本量的计算、分配隐藏等,无法确定预防护肝作用是否有效。 笔者通过对32 篇文献报道的5 507 例抗结核药物肝损害的预防用药进行成本⁃效果分析[23],发现预防护肝用药能有效降低抗结核药物化疗过程中肝损害的发生率(31.48%vs.16.05%);注射剂方案与口服用药的预防护肝疗效无显著差异,口服组性价比显著优于注射剂组,相同的护肝疗效口服组的成本远低于注射剂组。口服2 个月的预防疗程可经济、有效地降低ATB⁃DILl 的发生。 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建议给予预防性保肝治疗,尽量少用或慎用肝损伤发生频率高的抗结核药物;预防性保肝治疗不推荐用于无高危因素的患者。预防性保肝治疗者,建议给予一种口服护肝药给药,不建议给予注射剂型,亦不建议联合用药;对有吞咽困难或严重胃肠道不适等不能口服者,可考虑使用一种注射用抗炎保肝药。预防性保肝治疗者,不建议使用降酶药,以免掩盖肝损伤进展。 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发生药物性肝损伤时停用致因药物非常重要,但停用致因药物后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转氨酶不能恢复正常,胆红素持续异常,需要适当使用保肝抗炎药物,但也不能长期“标本兼治”滥用保肝药物。 保肝药物的运用是否合理不仅仅要从“适应证”、致损机制、护肝机制和疗程等方面考量,还应考虑到,保肝药物自身也有肝脏代谢负担及其代谢产物也可能有毒性,两种以上药物在体内相互作用或化学反应后的产物对肝损的影响难以知晓和判断。因此临床上保肝药物联用过多品种时,容易忽略其本身的不良作用,从而使保肝的意义适得其反。4 ATB⁃DILI 的临床处置和治疗药物选择
5 ATB⁃DILI 预防护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