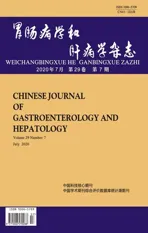结肠癌靶向治疗研究
2020-12-30王嘉源董卫国
王嘉源, 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湖北 武汉 430060
在我国,作为一种严重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无论男女结肠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前五[1-2]。其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人们筛查意识的不足及结肠镜筛查普及程度低有关。尽管我国结肠癌外科手术治疗及内镜下治疗取得一定进展,其死亡率却无明显下降,一方面是结肠癌的早期症状难以引起患者重视导致确诊时疾病往往已经进展,其预后明显差于早期确诊者[3]。另一方面,结肠癌死亡率的下降也需依赖于规范化的综合治疗及后期随访[4]。结肠癌无切确的病因,发病机制尚无定论,目前认为遗传、免疫、饮食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结肠癌的发生。根治性手术治疗仍是结肠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单纯手术治疗容易再次复发或发生转移,因此,目前提倡对结肠癌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其中靶向药物因其能用于治疗复发转移的晚期患者,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结肠癌的靶向药物主要分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V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抑制剂(EGFR)、多激酶抑制剂、PD-1抑制剂、CTLA-4抑制剂、小分子酪氨酸抑制剂等。本文将对目前针对结肠癌的靶向治疗药物及进展作一概述。
1 VEGFR
VEGFR新生血管的形成贯穿于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转移的全过程,因此抑制血管生成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思路。VEGFR能调控血管的生成,成为各大肿瘤药物研究热点。在结肠癌靶向治疗药物中,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是第一个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VEGFR。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它来源于小鼠VEGFR,其中93%为人源化部分构成了单抗的框架,而它的互补决定区则为鼠源性蛋白序列。这样贝伐珠单抗既降低了其免疫原性,又具有特异性结合VEGF的能力。有研究[5]表明,VEGF-A与肿瘤的侵袭性和易感性密切相关,在肿瘤患者体内表达水平显著升高。通过抑制VEGF-A能够抑制新的肿瘤脉管系统形成和促进已形成的肿瘤血管消退,并使肿瘤血管正常化,从而缩小肿瘤体积,抑制肿瘤生长及侵袭[6]。贝伐珠单抗能靶向结合VEGF-A的所有亚型,阻断VEGFR-2(KDR/FLK-1)和(VEGFR)-1(Flt-1)与其结合。另外,贝伐珠单抗还具有改善肿瘤细胞缺氧的作用,减少肿瘤细胞刺激性分泌VEGF-A。有研究[7]表明,当贝伐珠单抗与化疗药物合用时能改善血管通透性,有利于化疗药物进入肿瘤细胞,发挥更有效的杀伤作用。微血管密度(MVD)是评价肿瘤血管生成的一项关键指标。动物实验结果支持贝伐珠单抗能抑制VEGF表达,从而减少肿瘤内MVD[8]。在结肠癌小鼠模型上,VEGFR显著缩小了肿瘤的体积并减少了肝脏转移结节的数目和大小。贝伐珠单抗的临床试验从1997年就开始进行了,在多年国外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贝伐珠单抗被证实与以5-氟尿嘧啶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一起应用时能显著提高转移性结肠癌患者的生存率[9]。我国于2010年引入贝伐珠单抗,随后在我国患者的治疗中也证实了其作用[10]。同时,贝伐珠单抗的不良反应也时有报道。它有增加动脉血栓风险的可能,最终导致脑血管意外、心肌梗死等严重后果。此外,由于它可能导致非胃肠型瘘、延长伤口愈合时间、鼻中隔穿孔、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等多种不良反应,FDA曾多次针对贝伐珠单抗发出安全警示。根据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结肠癌临床实践指南,Ⅱ、Ⅲ期结肠癌患者除入组临床试验外并不推荐使用贝伐珠单抗,因为尚无足够数据表明该类患者能明显受益。在进行贝伐珠单抗治疗前一般可不常规对患者进行基因检测,这是由于贝伐珠单抗主要作用机理是抑制血管生成,有多个作用位点,在人群中高表达。希腊一项研究[11]曾尝试寻找对贝伐珠单抗获益有预测作用的基因,它检测了16例接受贝伐珠单抗的结肠癌患者的全部基因组,选择5个与可能治疗效果相关的基因作为预测基因,再进一步应用qPCR技术对接受单纯化疗患者和接受化疗+贝伐珠单抗治疗患者相关基因进行研究,最终还是未能验证其在贝伐珠单抗治疗的预测意义。VEGFR中除了贝伐珠单抗外,还有多种药物相继被开发。阿柏西普[12](Aflibercept)主要与VEGFRA、VEGFRB及胎盘生长因子(PIGF)亲和力高,抑制其与内源性配体结合和活化,从而减少新生血管生成及降低血管通透性。同时它也可能通过促进坏死和炎症来调节肿瘤免疫,但其确切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它主要用于眼底疾病,也已经有部分临床试验证实了其在转移性结肠癌的作用[13-14]。但由于其价格是贝伐珠单抗的两倍,而其疗法较贝伐珠单抗并无明显增加,因此它并不具有临床优势[15]。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是一种全人源化的VEGFR,其结合靶点是VEGF-A、VEGF-C和VEGF-D,抑制VEGFR-2激活,进而达到抑制肿瘤增长的效果[16]。基于一项全球的随机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显示,与贝伐珠单抗相比其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它被列为晚期结肠癌的二线治疗。但其不良反应发生率较贝伐珠单抗及安慰组明显增加,因此它的应用前景有待进一步研究[17]。西地尼布和阿帕替尼也属于VEGFR,目前也在积极地进行结肠癌的临床试验,我国也积极参与开发这类药物,呋喹替尼(Fruquintinib)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口服VEGFR,是一个高效高选择性的VEGF-1,-2,-3的小分子抑制剂,针对它开展了一项纳入416例化疗失败的晚期结肠癌患者的临床试验,并获得了喜人的效果—中位生存期较安慰组延长了43%,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了106%[18]。
2 EGFR
EGFR是一种跨膜受体,配体选择性与其结合后发生磷酸化,触发一系列细胞内通路,调节细胞生长、增殖与分化。西妥昔单抗(Erbitux)是一种镶嵌型单抗,与肿瘤细胞表面的生长因子受体特异性与亲合力高,竞争性阻断其他配体结合,以此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达到抗肿瘤目的。有证据显示,西妥昔单抗还可以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激活免疫应答。西妥昔单抗对转移性结肠癌安全且有效,被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MSO)及NCCN等多个指南推荐为联合化疗的一线靶向药物[19-20]。Ras基因与西妥昔单抗的疗效密切相关,这是由于磷酸化的EGFR是Ras的上游通道,当Ras基因发生突变时西妥昔单抗也失去了对其的调控作用。因此进行西妥昔单抗治疗前必须检测Ras基因(包括K-Ras及N-Ras基因),只有Ras基因为野生型的患者才能从西妥昔单抗使用中获益。另外,西妥昔单抗疗效还与肿瘤的部位有关。左半结肠癌患者相较于右半结肠癌患者更能够从西妥昔单抗的应用中受益。这可能说明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是来自不同器官的两种实体瘤[21]。贝伐珠单抗和西妥昔单抗是目前应用最广的两种结肠癌治疗靶向药物,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由于治疗时很少采取单药治疗,而是与化疗联合应用,目前缺少单纯两者疗效对比的试验。一项Meta分析显示,对于野生型Ras患者,当病变发生在左半结肠时使用西妥昔单抗可明显获益,当病灶位于右侧时越来越倾向使用贝伐珠单抗[22]。过去尽管存在争议,但优先使用何种靶向药物一般是根据Ras基因突变结果来决定。但最新研究显示,右半结肠癌即使Ras基因为野生型也很难从西妥昔单抗治疗中获益[23]。因此,2017年NCCN指南明确指出EGFR一线治疗的指征仅限于左半结肠癌。尽管贝伐珠单抗和西妥昔单抗已经分别被证实有利于延长进展期结肠癌的生存期,但新英格兰杂志(NEJM)的一篇文章表明,当这两种靶向药物联合应用时并不能达到效果相加的作用,甚至会明显缩短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降低生活质量[24]。2019年NCCN结肠癌指南强烈建议不要同时使用VEGFR及EGFR两类靶向药物。帕尼单抗(panitumumab)是第一个完全人源化单抗,其作用机制与西妥昔单抗相似,其疗效及安全性也与西妥昔单抗无差异[25],目前也是临床上应用较广的结肠癌靶向药物。
3 多激酶抑制剂
瑞戈非尼(Regorafenib)是一种新型的口服多激酶抑制剂,可阻断包括KIT、PDGFR、RET、VEGFR、RAF等多种蛋白激酶的活性。柳叶刀[26]报道了一项由16个国家114个中心参与的3期临床试验,500例患者接受瑞戈非尼治疗,253例患者给予安慰剂。两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6.4个月和5.0个月(危险比为0.77,95%CI: 0.64~0.94),且瑞戈非尼并无明显严重不良反应,它的最常见不良反应是手足皮肤反应。亚洲地区的临床试验[27]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相较于安慰剂组,使用瑞戈非尼治疗的患者其OS增加了2.5个月,PFS延长了1.5个月,单纯化疗失败的转移性结肠癌患者疗效更显著,其OS延长至9.7个月。它为难治性晚期结肠癌治疗提供新思路,目前也被NCCN结肠癌指南推荐为三线治疗药物。
4 其他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28]能通过与PD-L1/2J结合传递抑制信号,调控T细胞的活化。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共同作用使得持续激活PD-1:PDL通路,降低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促进肿瘤免疫逃逸。PD-1抑制剂能阻断此通路,促进T细胞功能恢复,提高免疫应答,实现抗肿瘤。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是此类单抗的代表,作为一类广谱抗肿瘤药物,它适用于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或错配修复基因缺失(dMMR)的肿瘤患者[29]。而结肠癌中有90%是微卫星稳定型(MSS),既往认为PD-1单抗对此类结肠癌疗效欠佳,然而在2019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日本学者公布了一个Ⅰb期试验结果,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单抗用于治疗MSS结肠癌患者,其客观缓解率(ORR)达33%。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若更大量的试验数据能呈现相同的结果则可证明瑞戈非尼能抵抗PD-1单抗的耐药,为MSS型结肠癌患者带来好的消息。依匹单抗(Ipilimumab)是另一种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其主要作用靶点是细胞毒性T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又称CD152)。BRAF基因是调控锯齿状腺瘤癌变通路的重要调节因子,该基因突变时导致BRAF蛋白持续产生,细胞异常增殖而癌变[30]。V600E突变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6%~10%结肠癌患者存在此突变。回顾性研究发现该突变能明显影响结肠癌患者的生存率,因此目前也提倡作为一个结肠癌常规检测的一个生物标志物[31]。维罗非尼(Vemurafenib)是小分子酪氨酸抑制剂,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中已广泛使用,而对相同BRAF突变结肠癌患者的反应率仅为5%,且有报道指出,应用维罗非尼似乎会导致异常的RAS基因突变,进而导致耐药[32]。因此它在结肠癌的应用价值有限。2020年NCCN指南去除了包含维罗非尼的治疗方案,推荐BRAF V600E基因突变的结肠癌患者治疗选择西妥昔或帕尼单抗[33]。
综上,靶向药物应用于结肠癌治疗已有十余年历史,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去探索靶向药物在结肠癌治疗的作用机制、适应证、最佳配伍方案等,以期获得最好的临床应用。其中,贝伐珠单抗是应用最早的分子靶向药物,有许多大型临床试验也证实了其疗效,但意大利的一项长达5年的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中[34]将376例患者随机分成单纯接受化疗(FOLFIRI or FOLFOX4)及接受化疗和贝伐珠单抗靶向治疗两组,结果显示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客观缓解率及总生存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明确贝伐珠单抗的作用人群。除此之外,许多药物也在推陈出新,包括适用于K-ras基因野生型患者的西妥昔单抗、作为三线治疗的瑞戈非尼以及许多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VEGFR、EGFR等,不同通路的分子靶点也在不断地被挖掘。目前转移性结肠癌患者进行靶向治疗前可先检测Ras、BRAF、MSI等基因,根据基因型及病变部位优先选择VEGFR或EGFR类药物联合化疗(多选择FOLFOX/FOLFIRI或伊立替康),瑞戈非尼可作为三线治疗药物用于前者治疗无效的结肠癌。此外,关于单靶点或多靶点治疗方案选择问题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通过作用于上下游通路上的不同靶点来实现双药乃至三药的靶向抗肿瘤治疗是其理论基础,例如MAPK信号通路可以选择两种靶向药物同时阻断上游的EGFR信号及下游的MEK位点来提高抑癌效果[33]。目前已经有相关研究在开展,这也是靶向治疗的新思路。尽管相较于传统化疗药物,靶向药物被认为是具有更好的疗效及更轻微的不良反应的一类药物。但随着越来越广泛的靶向药物应用,其不良反应与其处理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临床医师应关注的问题。由于靶向药物在晚期结肠癌治疗中仍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对于多数靶向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最佳处理方式不是减小药物剂量而是对症治疗适当预防[35]。晚期结肠癌治疗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未来还会有大量的临床医师及药物研发公司前仆后继地投入研究靶向治疗的行列中,期待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