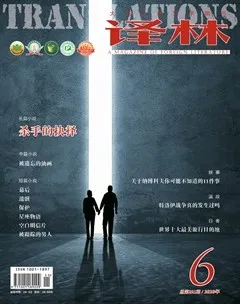遗 骸
2020-12-29比尔·普洛奇尼
我坐在农场房子的门廊上,无所事事。像往常一样,晚餐过后,如果天气尚好,我有时会坐在这里休息。就在此时,查利·林德曼突然造访,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
时值夏末,晚间仍有暑气,蟋蟀和树蛙的叫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金银花的香味。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一切又是那么寂寥。22年前,玛丽·安妮因癌症去世。17年前,我们唯一的孩子海军下士小克莱顿·德莱瓦斯在伊拉克阵亡。此后,我一直独居生活,不爱与人交往,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可是人老了总难免寂寞,特别是在这样的傍晚,真是百无聊赖。
所以看见查利那辆破旧的福特车轰隆隆驶入院子,我倒也不排斥,只是有点意外。今天这么晚了,他怎么还来找我呢?他大概是我唯一的朋友,跟他结识也仅仅因为他以前在这里送邮件。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可我还在农场干活,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们每月聚一两次,大多在周日下午。聚在一起也无非是喝点啤酒,玩玩克里比奇纸牌而已。
他一个急转弯,把车停在院子里,急匆匆地奔向我。他矮小精瘦,体形和体重估计只有我的一半,激动起来,满脸通红,左蹦右跳,活像一只矮脚公鸡。查利这个人,天生就喜欢小道消息。但凡听到什么风声,或者探得一些众人不知道的事,他肯定会找个人添油加醋地抖搂出来。
“克莱,给你爆个料,”他说,“是个猛料,你肯定很想知道。”
“当然是重磅消息,否则你也不会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儿来。”
“边喝边说吧,给我来一杯呗。”
我去厨房开了一瓶百威啤酒,回来后递给他。他拿起酒瓶,一顿痛饮,接着用手背在嘴上一抹,擦去胡子上的泡沫。此时暮色渐浓,他的眼神显得格外狡黠闪亮。
“那个消失很久的女孩终于有下落了,”他说,“至少他们能肯定就是她。没错,不可能是别人。”
“什么女孩?我没听说有谁失踪了啊。”
“不是失踪,而是遇害,跟大家推测的一样。”
“等等,查利。你说的究竟是谁?”
“汉森姑娘,全名琳内·汉森。可能她当时就已经死了,而不是失踪。克莱,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这件事还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我想了几秒钟,说道:“想起来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差不多20年了。想不到她竟然被人找到了,真是够巧的。”
“在哪里找到的?”
“离这里几英里的鲍尔德山,在山的一侧被人发现的。有人杀了她,把尸体藏在一个小山洞里,洞口用大石块和灌木掩盖起来。几位地质学家在野外考察,偶然发现了山洞,进去一看,发现了她。不过,躺在那里的只是一具遗骸。”
“遗骸。”我重复了一遍。
“还有一些破烂的帆布块,她应该是被帆布包裹着抬进山洞的,”查利说,“凭这一点,他们断定她被带进洞之前已经死了,是被人谋杀的。还有一点,从骨架上看,她的脑袋向下垂,舌骨受损,第一颈椎断裂。一个人被掐死之后脖子会断,骨架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侄子告诉我的,这应该就是事情的真相。”
他侄子叫托尼·彼得斯,是卡勒姆县的警员。“他们怎么能确定那就是琳内·汉森呢?”
“呃,他们还不能完全确定。遗骸已经送到州首府做法医鉴定和牙齿检测。肯定是她,准没错,不可能是别人。”
“我看未必。”
“或许,法医能发现一些线索来确定凶手,但是希望不大。我的意思是,找到凶手的希望渺茫,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嫌疑的人太多了。”查利将一侧突起的髋关节靠在门廊的栏杆上,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润润喉咙,“大美人,真是个大美人,还有一头金发。黄金一般的秀发,当时报纸就是这么形容她的吧?”
“想不起来了。”
“没错,就是黄金一般的秀发,还有天使一样的脸庞,可美貌之下却潜藏着一个恶魔,尽管她还只是个孩子。真是十足的野猫做派。她可以跟任何人行苟且之事,不管老少,然后拿钱走人。为了达到目的,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她都做得出来。她曾因两项盗窃罪受到指控,其中一项还让她丢了杂货店的工作。千真万确,她就是个女魔头。杀她的那个人算是为民除害了。”
“没有谁是应该被杀害的,查利。”
“嗯,或许是吧,”他表示赞同,“反正她失踪以后,霍斯金斯警长审问了十来个跟她有染的人,到头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能还有些人警长没有查到,或者凶手现在已经死了也不足为奇。”
“查利,这真的重要吗?”
“什么真的重要?”
“杀人凶手和杀人动机。毕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然重要。你也知道,我们这里平时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所以,在山洞里发现她的遗骸估计就是自从……让我想想,自从她失踪以来,真面目公之于众后最重大的消息。你该不会一点兴趣都没有吧?”
“好吧,我还真没什么兴趣。”
他摇摇头,似乎觉得我很没劲,对我的反应也大为失望。随后他举起酒瓶,一饮而尽,顺手把瓶子放在栏杆上,说他得回城里了。而我也不想多留他。
查利离开时已是暮色逼人,而我仍坐在那里,看着天空慢慢暗下来,逐渐由深紫变得漆黑,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此时,蟋蟀和树蛙的低鸣好像离我很远,金银花的香味也惹人生厌。远处的鲍尔德山现出黑色的轮廓,在满天繁星的映衬下依稀可见。
曾经,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一切都发生在我眼前。只是那天的夜更深,月圆未满,高悬苍穹。此刻只要闭上双眼,我就又看见她直挺挺地躺在绿草如茵的河岸上,皎洁的月光下,冰冷苍白的脸上污迹斑斑,喉咙印着深深的指痕,脑袋扭向胸口,脑后是散落一地的金色长发。
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丑恶。一片死寂。
片刻之后,我站起身,回到屋里,把晚上吃的东西全部吐进了马桶。我漱了漱口,把手和脸洗干净,又走到外面。不过我没有坐下,而是离开门廊,经过车库,走出院子,然后沿着苜蓿地走在泥土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欲罢不能,仿佛背后有双无形的大手在驱使我前行。虽然这种状态以前也曾有过,还不止一次,但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
我来到路口,泥土路在此与一条从县道分出来的乡道交会,我穿过路口,爬上道路后面的小山丘。站在山顶远眺,可以看见400米开外一条宽阔蜿蜒的河流和对岸成排的柳树。一钩弯月正慢慢升起,河面上泛起点点微光。月色朦胧之中,河岸上琳内·汉森遇害的位置难以辨认,只有一片阴影,晦暗不清。
我走到半山腰那块长椅状的巨石旁,坐在冰冷的石面上,控制自己不朝下面的阴影处看。然而,记忆中的画面纷纷涌现,这次我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幕幕往事跃然眼前,像无声电影的片段一样轮流播放。
我看见自己戴着手套,把她抱起来,用一块旧防水帆布包住,拎起来,放进皮卡车尾箱。我看见自己开车从乡道驶入县道,再经县道飞驰在鲍尔德山一侧弯弯曲曲的旧防火带上。我看见自己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寻觅儿时发现的山洞,找到之后迅速把她放进漆黑狭小的洞内,然后在洞口堆起大石块。我看见自己又握着方向盘,在漫长的回家之路上驱车前行……
我不知道自己在石头上坐了多久,应该有一会儿了,因为月亮比之前升得更高了。一只猫头鹰扑棱一声飞起来,嘎嘎鸣叫着,我这才回过神来。夜晚依然很热,而我却感到阵阵凉意,不由得一阵战栗。我快步返回家中。
我从不酗酒,可我走进厨房,从橱柜里取出那瓶占边威士忌,又拿出一个半透明玻璃杯,倒了半杯酒,连喝三口。喝完酒我不再颤抖,但依然没有觉得暖和。我想洗个热水澡,只要受得了,水越热越好。然而,我却不得不走向前厅的壁炉架。我不由自主朝前走,就像无法控制自己走向河岸一样。
壁炉架上有张镶在相框里的照片,立在玛丽·安妮的婚纱照旁。我拿起相框,捧在手心。这是小克莱顿的高中毕业照。他高大威武,跟我一样。照片里的他英俊潇洒,笑容满面,正值最美好的年华。
突然,他的容貌渐渐模糊起来,幻化出另外一副模样。上扬的嘴角开始向下撇,神色惊恐,满头大汗,面目扭曲。那天晚上,他就是这样惊慌失措地跑回家,冲我大喊,连声音都在颤抖。我又听到他在呼喊,支支吾吾,上气不接下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清清楚楚。
“爸爸,天哪,爸爸,我刚才勾搭上那个女孩,把她带到河边……我们发生关系之后,她说她只有17岁,如果我不给钱,她就叫警察把我抓起来……我动手打她,她又踢又抓,我就……我就急坏了,一把掐住她的喉咙……我不想弄死她,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抓住她的脑袋,啪的一声,她就不动了……她死了,爸爸,我杀了她,我把她的脖子拧断了……天哪,你快救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一不做二不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他是我的儿子,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只是我终究还是没能留住他。
六周后,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句话都没留下。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差不多一年后,伤亡通告处来人告知他在战场上营救受伤战友时,遭遇敌人炮火袭击,不幸牺牲。
悲痛之余,我真想开车到县里,向警长交代事情的始末。如果琳内·汉森有亲戚住在这里,我多半会去自首,但她在这里没有亲戚,只有一个叔叔住在偏僻的东部,而且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所以,我当时没有自首,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害怕我会怎么样,而是因为小克莱顿为国捐躯,是个大英雄,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他的名誉和形象受损。
他参军是爱国精神使然?还是因为羞愧?抑或是良心不安?他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是想将功赎罪?我不知道,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但我知道的是,他终究会受到惩罚。
我也一样。
过去18年,琳内·汉森并非独自躺在山洞里。那晚过后,我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就留在了她身旁。而终有一天,我的遗骸也将长守洞中。
(王闻: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4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