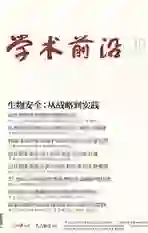论革命的人性
2020-12-28张志丹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流行已久、为患颇深。其中,“告别革命论”者打着似乎天经地义的“人性”幌子,试图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否定党史、国史和军史等历史本真,甚至否定革命。无论如何包装装潢、乔装打扮,都难以掩饰其唯心论、机械论、形式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虚假本质。总体上看,革命与人性主流是相互促进的,革命本身蕴含人性、革命过程彰显人性、革命之后可以提升和优化人性,人性有助于革命发生以及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对革命的评价应该敷设以客观标准为基础的价值标准和人性标准,因此,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革命問题上的合法性地位和正当性价值,在占领历史制高点的同时占领道义制高点,从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夯实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 人性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0.011
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高扬着“普世价值”——打着似乎天经地义的“人性”幌子,试图通过指摘历史上革命的非人道不人性而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进而占领历史的制高点。对此论调,人们的态度有三种:一种是持“割裂主义”的观点,认为决不要掉入“人性”的问题式来考量革命,因为人性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不要生拉硬拽、将两者联系起来;另一种是持“联系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的合法性标准就应该是人性,背离人性而革命是非法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持“辩证的联系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可以同作为社会实践的革命相联系,但是,不能简单地肯定抑或否定两者的关联,更不能本末倒置,而应该敷设言说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方能行稳致远。基于此,革命与人性虽有区别,本质上并不截然对立,革命总体上可以促进人性的提升与完满,革命本身有人性、革命过程有人性、革命后更有人性。革命的理念、本质、实践、制度等均总体上具有积极的人性内涵。人性及其进步同样有助于革命发生和进展,还有助于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不过,其中有不少理论关节需要仔细地窥测甄别,以求达到通达之效。
问题的提出
曾几何时,有些人把革命化约为“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等,并且认为革命是过去时,无需重启革命。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认为,革命只起颠覆性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因而需要“否定革命”“告别革命”。既然“激进主义”的革命之路不通,那么,推崇和颂扬“保守主义”的改良就是必然的选择。近几十年来的“告别革命论”,与历史上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想何其相似乃尔。伯恩施坦等人的理论失足在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他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用阶级矛盾可以调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驳斥上述思想”。[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用意识形态偏见和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油炸”“戏说”历史,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还说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伪命题,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否定革命存在的合法性,继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二人在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2]该书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3],“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4],“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5],“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6],近代中国百年的革命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7]。由此,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都在“告别”之列。在这种“告别革命论”思潮影响下,革命的“弊病”和“祸害”被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8]。“否定革命论”的鼓吹者还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9],“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10];如维新运动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是“早产儿”[11];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12];“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13]。由此,他们骑着历史唯心论的野马,进而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进步性,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统统被否定。显然,他们两位否定的是新陈代谢、变革国家政权社会性质的“暴力革命”“政治革命”。
革命本身蕴含人性
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人性不断丰富和展开的历史,由此,认识人和人性,乃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认识人性问题的革命性贡献在于,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指认了人性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具体历史性,即说到底,不是人性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人性。何谓“人性”?人性介乎兽性和神性之间,是人的本质(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的具体表现。关于革命的本质,革命化约为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不同形态 (尽管后者是革命的主要形态) ,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4],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美国著名哲学家阿伦特认为,革命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知的故事将要展开”。[15]可见,这里的“革命”是指表明着断裂、飞跃的政治革命。革故鼎新的革命承载着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对新制度的期待和对新秩序的憧憬,对于人类文明诸共同体的建构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革命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新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石,所以革命必然会引起平常时刻难以出现的激情,其背后就是对于新时代和新秩序的憧憬与期待。
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本身蕴含人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革命,尤其是实现社会质变的政治革命,体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中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16]没有革命,就没有历史的断裂,就没有应有的飞跃。革命的“发生学密码”在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由此,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或者集团揭竿而起,“替天行道”,发动革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从而以“铁血”“激情”的方式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人间大道和世间正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17]从此意义上,“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18],“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19]。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現在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20]
政治革命本身代表着以先进阶级为内核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性需求,极大地彰显了他们的历史主体地位和积极能动性。因而较之于剥削阶级的“虚情假意”的“人性统治”本身,革命要人性、人道许多倍,易言之,二者在人性的本质及含量与成色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革命阶级的诉求如同历史洪流,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具有不可战胜的意志力和决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1]在中国近代史上,社会革命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问题。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史,在一片“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声浪中,无数中华志士仁人纷纷把西方革命模式当作心目中的“救世福音”,于是乎,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等悉数粉墨登场,却落下事与愿违的“无言的结局”。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人民的未来在哪里?无声的呐喊在神州大地回荡。正当中国人民在救亡道路上四处碰壁、不得其法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谓的“链条最弱的一环”的俄国凿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闭链条,也惊醒了当时一批行愁坐叹、寝食难安,沉浸于资本主义幻梦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诞生了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社会革命就不再是对西方革命模式的机械模仿,必须另辟蹊径,寻求出路。为此,只有认清中国基本国情,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也只有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发展新中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坚持“主义”不改旗易帜,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徘徊动摇,顶住压力、抓住重点、守住底线、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从革命、建设、改革走向复兴大道,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朝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断进发。
毫无疑问,如果从“社会革命”意义上来理解“革命”的话,那么,革命本身体现出来的人性化的或者人本化的内涵就一目了然。习近平总书记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对我们党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光辉探索历程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就大大拓展了“社会革命”的内涵。从这样的概括来理解,社会革命就不仅仅局限于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的阶级易位,以及相应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新陈代谢,还应关涉生产关系改革与完善、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心有灵犀”“密切配合”的,也有“琴瑟失调”“脱节无序”的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即通过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治愈“肠梗阻”的旧的具体体制机制的“痼疾”,使社会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发展,促进生产力、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进步。换言之,这种社会革命,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破立并举的过程,破旧与立新的过程同样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无论是暴力革命的“破”,还是社会革命的“立”,或者社会革命中的“破”与“立”,总体上都体现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人性化、人道化、人本化的内涵。这就是说,社会革命本身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利益”的,是符合革命的人性论的,因此,我们必定反对以部分人的利益为据否定革命、拒斥革命的人性论。总而言之,无论是政治革命(含暴力形式),还是社会革命,二者历史前提、时代背景、主题任务、途径方法、目标理想等方面虽有区别,但是彼此处于统一体中,相互递进、不可割裂。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深化。无论如何“变”,唯一不变的是与革命相适应的实践优化和人性优化。
所以,革命是立足现实、通达理想社会的阶梯,而在落后制度框架中的改良无论如何摆弄折腾,都难以给自身“附魅”质性提升的人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价值判断:革命不仅具有人性,而且具有旧的制度及其改良中所不具有的更高的人性内涵,折射出具有符合历史大势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性反映了文明积淀不断丰富,人类社会不断进阶发展的“刻度”。
革命过程彰显人性
除了革命自身之外,革命过程也彰显人性。之所以有革命时期“一天相当于二十年”的提法,是因为革命时期社会发展狂飙猛进,人性的光辉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和彰显,这不是某些人,而是人民的整体。“人性的光辉”是指人性中的闪光点,即高尚的人格或品质的彰显。
一方面,革命过程中人性得以提升。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23]由此可见,革命不仅是推翻统治阶级的必要且主要的方式,也使革命者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实现自身的革命和人性大革命,锻造有利于革命的“革命的人性”。这种观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改造”的基本观点——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十九世纪中叶是革命与战争不断交替的时期,恩格斯认为,革命“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4],“革命是一种纯自然现象,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25],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26]。实际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情况,不是一种空洞的玄虚的口号,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生动的现实。“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对于生产落后的克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文化的普遍发展。诚然,在这样的飞跃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径情直遂,经常会遭遇阻碍、遭遇逆流,甚至有时采取的手段不一定合情合理,呈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巨大悖论,有时因为铸成大错而导致一时后退,但是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再也不同于往昔,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带着它们走上新方向了,这种新方向以及“沛然莫之能御”的新社会建设,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人性也由此得到很大的提升。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7]
另一方面,革命当中确实也有不可胜数的人性光辉的大释放、大彰显。这种人性的彰显集中体现为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革命过程中,许多中国优秀儿女背井离乡,舍生忘死,豪气冲天,气干云霄,为国赴难,九死未悔,这种精神是平常生活当中难以见到的。无论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还是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进步的人性都在革命时期火热的斗争中大放异彩。而和平时期,人们习惯于日常生活,卓越精神之花的大绽放往往难以实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敢于牺牲的精神是红色精神价值宝库中最为闪亮的部分。红色精神可以达到感召、凝聚和净化人心的目的。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革命者,不要忘记了革命精神”[28]的原因所在。然而,马克思笔下的那些用尺子和“报纸趣闻”来衡量历史的“小市民们”,拒斥宏大叙事、拥抱细小叙事,对于否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依托的生产方式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飞跃,他们如何能够接受?因此,他们不去推求革命产生的原因,只责怪革命本身,只能是嘲笑、嫉妒而后恨,因为革命打破了他们的白日梦、打破了他们的幻觉。由此可见,“立场决定观点”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是何其深刻。正如列宁说道:“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29]
革命之后提升人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结构系统中,社会意识的根源、内容和动力均来自于社会存在,但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和其他社会因素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映历史规律、顺乎时代潮流的社会意识威力之大、势头之猛,可谓“移山可也,填海可也”。近代以来真正的意识形态转型变革发生在国家制度的变革之前,前者对后者起着引领作用。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同样是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构成其政治制度和政治合法性、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的思想基础。革命之所以具有道义合法性,是因为它以先进的意识形态来反对和摧毁旧的没落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着先进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世界走势。所以,革命意识形态具有人性内涵和提升人性的意蕴。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旧制度下人的“非人性”不是源于自身原因,而是根源制度的“不人性”“非人道”,批判的锋芒直指制度的“人性失灵”,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新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从而通过制度自身的“人性含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大程度和范围地保障人性提升,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进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30]他还认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31]无独有偶,科斯洛夫斯基指出:“‘个人良心不能抵消体制失灵。只有在不会通过体制设置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才能期待道德行为。”[32]制度安排合理,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方有可能,否则,好人不敢做好事,而坏人坏事大行其道。这就是说,暴力革命的方式可以使得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的人性化体现不仅在于政治领域的人民民主,而且在于经济领域人民得到更多的权利,从而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彰显更高层次的,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人性含量。
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革命”是指推动社会“质变”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先进阶级发动革命,摧枯拉朽,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新旧更迭、社会制度新旧更替。由于反动阶级不愿自动走下历史舞台,所以政治革命是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形式,改良则是特殊方式。“广义的社会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还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彻底改造社会的进程;不仅包括社会形态更替的“质变”,也包括维护新生政权、巩固社会形态的持续“量变”。
在中国革命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分别表征了狭义的和广义的社会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朝着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奋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仍在进行当中。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3]这就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系列建设和发展历程科学地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谱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快速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最终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积蓄力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任务。在化解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34]
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我国在发展中产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总目标,必然要依靠各个阶段性的胜利来实现。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任务,就是要围绕主要矛盾开展重点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不是一般地否定“不断革命论”,而是特殊地否定“不断革命论”。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无论是哪种革命,都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性诉求。继续推进两种革命,一方面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性诉求,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抽离人性、伦理道德价值观来审视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建设实践,是一种抽象的孤立化的思维方式,无益于问题的理解把握。“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35]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36]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断,明确了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和崇高使命,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性观的人民性、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
人性如何合理地成为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即理论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形而上学、抽象人性论以及“伪价值中立论”,片面地、孤立地、主观任意地去看待历史。[37]从其实质来说,就是消解党史、国史和军史,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主张“改良”“和平”),诋毁和嘲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不难看出,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具有合法性,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就是不合法的,抽空人民革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基石、根据,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站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角度来否定革命,从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同时也根本背离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历史事实。中国人民没有选择“当牛做马”“奴颜婢膝”“屈从现实”,而是选择了一条“揭竿而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反映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哲学道理。同样,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绝不会充满朝气、蓬勃向前,现在我们也决不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即在革命时期,实现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建设初期,实现民族从衰落到扭转命运、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年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38]所以,决不能否定革命,张扬抽象人性,贬低革命是“兽性的疯狂”,应该维护历史本来面目,拒斥歪曲历史真相;更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9]
进言之,“革命”与“革命中的那些事儿”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革命是一个整体,诚然是由革命中一件件的“事件”构成的,但是它绝不等于“事件”的简单相加,更不能等同于事件自身。退一步说,即使革命过程中存在一些扭曲人性的情况,恐怕也并非普遍性的常态。因为有价值冲突,善与善、善与恶之间的矛盾,等等,所以需要价值排序。从方法论上看,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有所虚无、有所夸大”,“玩弄实例”。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40]因此,以革命中出现的某些人性扭曲的“那些事”来否定革命本身的历史合理性和道义性,恐怕有点儿类似于“瞄准了敌人却打中了自己”,由控诉革命中的“错误”变为否定革命本身,因噎废食。
能否以人性来评价革命,关乎革命有无价值、有无道德,革命有无相关价值哲学的内涵等重大问题。实际上,从本体论层面看,革命作为一种重大的实践活动,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物质,即使有着客观化的外壳,其中也充盈着精神、内涵着道德、彰显着人性。然而,以人性为根据忽略了一个最为一般的哲学原理,那就是名实不符的问题。就是说,在“人性”一词的下面,大家各说各话,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思和诉求。换言之,在同样的词语下面,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内容。正如恩格斯说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現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41]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基于共同的历史背景,某些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贯穿于人类社会的较长时段,但是这些道德规范依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和形式,比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切勿偷盗”,等等。如果从道德体系来说,绝对不存在“普世价值”“普世伦理”。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尽管文明时代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性”的价值和可爱,但是人性并非平均分配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性,同一阶级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人性。试图以人性作为永恒不变的唯一标准,本身就“不标准”,甚至无异于痴人说梦。毛泽东同志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42]资本主义道德优于封建主义道德,无产阶级道德优于资本主义道德,但是它们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因而也不是“普世伦理”。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革命与人性有何种密切关联,从人性视角来评价革命只具有有限的合法性,人性不是我们评价革命的主要标准,只是一个第二位(当然并非不重要的)标准。这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人性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人性,评价革命的主要标准是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等客观尺度,人性要以此为根据,在占领历史制高点的基础上占领人性的制高点。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所以不能以人性的主观标准来衡量革命“应该”与否。马克思还以一个社会的“两对矛盾”以及统治阶级不会轻易放弃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论述革命的必要性,即革命对于摧毁国家暴力及“唤起民众”和教育革命者自身的不可替代作用。他写道:“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43]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彰显“革命的人性”,我們需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坚定理想、脚踏实地,朝着理想目标继续前行。
事实上,多年来否定文化、理论、道德、价值,甚至“否定历史”“否定革命”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过,“后革命”的幽灵到处游荡,无论在真实空间还是网络虚拟空间都是如此。究其原因,与时代性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与改革开放时期以和平和建设为主题,与“拒斥形而上、回归形而下”的“后哲学”思潮的泛滥影响等宏观背景不无关系。说到底,打掉革命、否定革命的实质是企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或历史观,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别有用心。一言以蔽之,“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44]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ZDA016)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4卷附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00年,第38页。
[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267页。
[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262页。
[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60页。
[5]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144~145页。
[6]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62页。
[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67页。
[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63页。
[9] 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37、438页。
[10]转引自梁祝:《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11][12] [13]冯林:《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47、171、16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7页。
[15][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6]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2页。
[19]《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
[24]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28]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29]《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3页。
[32]陆晓禾:《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3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3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5~216页。
[3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37]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4~207页。
[3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23页。
[40]《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1页。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205页。
[44]沙健孙等主编:《走什么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