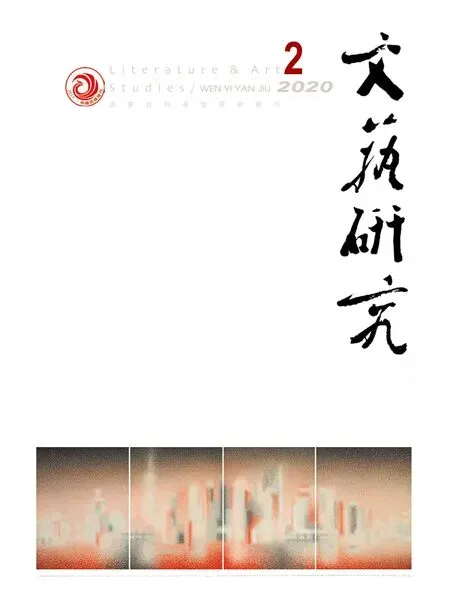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起源
——基于德国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系统论考察
2020-12-28范劲
范 劲
国别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孰先孰后,是争执不下的老问题,但如果“文学”概念自始就被设定为普遍的“世界文学”理念,文化自始就以比较为内在结构,那当然是世界文学/文化应先于国别文学/文化产生。对此问题,欧洲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能提供一个知识社会学佐证,因为如果把文学史书写视为“文学”知识系统的构建行为,那么从系统角度来看,欧洲的世界文学史书写才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母型:有了书写世界文学史的氛围,有了世界文学史的知识系统框架,才有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结构性需要。而从历史事实来说,早在顾路柏(Wilhelm Grub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人撰写专业的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者就已在世界文学史框架内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后来在德国学界的基本格局。
世界文学史书写盛行于19世纪的德国。随着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民族学等知识领域的兴起,赫尔德《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807)和弗·施勒格尔《古今文学史讲演录》(1815)中呈现的世界文学理想逐渐为公众接受,至1897年鲍姆伽特纳(Alexander Baumgartner)七卷《世界文学史》出版时,世界文学史书写已蔚为大观。英法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在19世纪的欧洲独占鳌头,德国汉学家处于绝对弱势,然而,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家很早就开始利用英法汉学家的成果,试图在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呈现出异于欧洲的中国文化精神。佛特拉格(Carl Fortlage)《诗史讲演录》(1839)、蒙特(Theodor Mundt)《文学通史》(1846)、谢来耳(Johannes Scherr)《文学通史》(1850)、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诗及其历史》(1855)、卡里耶(Moriz Carriere)《文化发展脉络中的艺术和人类理想》(1863)、斯特恩(Adolf Stern)《世界文学史》(1888)、哈特(Julius Hart)《所有时代和民族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历史》(1894—1896)、鲍姆伽特纳《世界文学史》(1897—1912)等都含有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共同塑造了19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意识。
一、浪漫派世界文学史:绝对批评的工具
欧洲的知识系统生产出中国文学史(而且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等于是从一个大脑中生出另一个大脑的记忆,这本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要让不可思议的事变成现实,需要整个系统的协同运作,从根本上说,汉学家不是从别处,而是从系统自身学会了书写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的中国文学史和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揭示这一点。不过,要理解世界文学史中的中国文学史,首先要理解浪漫派文学观,而后者几乎等同于文学史观。
首先,对于浪漫派来说,(世界)文学史是绝对物的自我显现,而非文学经验的归纳总结。弗·施勒格尔是浪漫派文学观的奠基人,也是世界文学史的开创者,以他为例,最能够显示这种内在关联。弗·施勒格尔和黑格尔一样代表了唯心主义的艺术形而上学,历史对他们来说都是精神的历史性展开,只是后者的历史以哲学为引导概念,历史的本质是哲学,而前者以诗为引导概念,历史的本质是诗。弗·施勒格尔和他的哥哥奥·威·施勒格尔——浪漫派文学和文学史书写的另一位开山大师——也有区别,后者更接近赫尔德的客观主义,重视经验性的语文学阐释,而前者在历史和哲学之间更倾向于哲学,其阐释方式是一种“在经验分析和绝对分析之间独特的、但倾向于精神一面的‘摇摆’”①。但施勒格尔兄弟都笃信:1.文学只能以历史的方式存在,因此文学科学即文学史;2.历史作为精神形而上学有其绝对目的;3.文学史包含历史、理论、批评三要素。这三个原则,构成了浪漫派文学史观的核心。
在当时的德国学者看来,文学史必定是世界文学史,因为文学即“诗的真正世界系统”②。卢曼认为,浪漫派开启了从客体艺术向世界艺术的转向,即是说,艺术不再取决于模仿对象,而是由整个世界关系规定的,故称之为“世界艺术”(Weltkunst)③。世界关系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因此浪漫诗必然是弗·施勒格尔所谓“演进中的宇宙诗”④。在此意义上,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在空间和时间维度都具有普遍性。
“绝对物”(das Absolute,或绝对目的)是精神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即先于反思规定、为主客观奠定基础的无条件之物。世界文学史作为绝对物的历史显现,是一种“绝对批评”(absolute Kritik)。绝对批评没有客观主义的标准,只能依靠绝对物自我传达。而人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是绝对物返回自身(即文学史实现自身)的帮助者。但是,如果呈现历史的整体脉络需要和绝对物合一,批评就不能依靠掌握美学原则或历史事实的学者,而只能借助天才。天才可在当下的瞬间回顾过去和预卜未来,从而实现历史的整体性。理论和历史各有局限,历史无法给出规定性和统一性,理论又会限制自然,唯有批评能够连接二者。批评将阐释方向从过去转向未来,和绝对物、无限性直接挂钩,文学史因此本身就是普遍诗:“它是二次幂的诗,完全浸润了哲学和语文学。”⑤
可见,在德国浪漫派心目中以批评为核心的文学史,绝非博学史或编年史之类的实录,而是帮助文学走向神圣和完善的阐释工具。德国浪漫派构想了一个自治的艺术系统,它自我分化、自主演化,以此展开自身的核心悖论(精神既是绝对又是个别,因为绝对物只能以个别的形式显现)。在具体操作中,批评代表了悖论的暂时统一,天才性的批评实现了瞬间中的无限、个别中的普遍。例如,歌德不是汉学家,在部分德国学者心目中却比一般人更懂得中国诗的精神,就因为他有批评的天才。
其次,在浪漫派理念性的世界结构中,“东方”具有专门功能。这也和绝对物的自我呈现有关。在弗·施勒格尔那里,绝对物的世界历史性的展开,需要一个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来表征原初统一的开端。他的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既是东方学的奠基性文献,也是其世界文学史构想的重要转折,从此东方成为重要的一极。一方面,东方是“原初启示”(Uroffenbarung)的源头。浪漫派重视整体,希腊古代和浪漫主义现代这对反题,必须得到综合。对于弗·施勒格尔来说,未来的、理想的综合是天主教的启示,而开端的综合就是东方思想,两者都能显示精神的整体性。印度作为基督教“最精神性的自我消灭”和希腊宗教“最恣肆狂野的物质主义”的“共同父国”,为两者提供“更高的原初形象”。东方代表统一,而欧洲代表分离,诗和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分离是“一种主观的纯粹欧洲的观点”⑥。另一方面,东方也在文化政治层面充当着欧洲的精神对照。弗·施勒格尔的东方学研究始于1802—1804年在巴黎逗留时期,对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以及“欧洲腐败”⑦的厌憎,促使他把理想投射到东方。他认为,欧洲的分离倾向在现代发展到了自我消灭的地步,预示着革命必然到来,然而真正的革命并不是法国革命那种躁动实验,欧洲人只能盼望来自东方的救赎。东方的永恒优势,在于它是“永不枯竭的热情之源”⑧。联系到“一战”后德国出现的“东方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欧洲陷入文明危机,德国知识分子的眼光就不由自主地转向东方,不管东方的象征是印度还是中国。弗·施勒格尔明确提出,北方(即德国)和东方作为“地球上善的原则之可见的两极”应当联合起来,以实现“真正的欧洲”⑨,即真正的世界。但除了理念性的东方,东方还包括和欧洲人有现实接触的现代蛮族,即阿拉伯世界。弗·施勒格尔意识到,世界文学最初的萌芽是民族大迁徙,蛮族入侵对于文化融合意义非凡。他说,南方(古代晚期-基督教文化)和北方(蛮族-日耳曼文化)是最初的两个世界文学元素,第三个元素则是阿拉伯文化乃至整个东方。然而,由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只是混合,而前者已完全吸纳了古代和基督教的因素,他们和东方才构成“现代历史的第一个二分”⑩。它们的综合促成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兴起,成为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
因此,东方具有三重意义,它是世界的起源,是腐败欧洲的精神对照,也是文明之外的蛮族。对于“真正的欧洲”来说,三个意义上的东方都很重要:起源保证了系统的同一性,对照可造成差异,蛮族的干扰则能够提供即时的刺激。
但谈及东方的功能,还必须考虑黑格尔的塑造作用,是他确定了东方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精神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弗·施勒格尔强调绝对物和同一性,而黑格尔更重视否定性。从否定性的角度来看,分裂对精神来说是必要的自我否定,没有分裂的统一是虚假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中华帝国最醒目的特征是法律、伦理、家庭、国家浑融不分,然而这恰恰是主客体无力分开的外在表现,之所以统一,是因为精神未能成为自为的主体。换言之,中国精神是不合乎黑格尔理解的精神概念的精神。反过来,欧洲的分离状态一旦和精神相结合,反而获得了超强的创造冲动,让贫乏的需求之乡最终成为真正的乐园。
黑格尔的历史讲演录建构了一个包括哲学、宗教、美学在内的世界历史系统,对于文学史领域的黑格尔拥趸来说,其功绩在于从精神哲学的角度给现有的世界文化认知以理论根据。对中国文学史叙述来说,其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弗·施勒格尔并未直接谈论中国,而黑格尔对于中国宗教、哲学和文化则有系统论述。黑格尔将东方文化精神的基本特性界定为自然性和实体性,即在东方,精神与自然直接统一,造成一种自然意识亦即感性意识,同时神不是精神,只是抽象的“绝对的威力或实体”⑪。中国文学是绝对的自然实体精神,毫无主观性、内在性可言,而印度文学的梵天看似摆脱了自然,实则抽象而空虚,中、印两国文学都只能将意识消泯,而非向上提升。在绝对实体面前,个人毫无反抗的可能,只能被动接受。而自然实体精神的最高阶段即佛教,“寂灭”最终会将否定性推入极致⑫。
二、世界文学史精神结构中的中国
由浪漫派文学史观出发,就能理解世界文学史的精神结构了。首先,19世纪德国的世界文学史书写基于普遍性的文学概念。蒙特的《文学通史》直译为“普遍文学史”,是19世纪德国诸多“普遍文学史”的代表。蒙特19世纪20年代在柏林听过黑格尔讲课,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蒙特断言,文学就是黑格尔追求的绝对精神本身,代表了创造性的主体精神和客观思想、个体意志和普遍命令真实而有机的同一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即最高级科学,能够塑造自由的世界秩序:
文学是一个为了理念的必然性的自由的领域,最新的哲学还努力要解决的,即将普遍理性的思想建立在和个体自由的同一性中,已经在文学中施行其权利,在文学中成了一种塑造性的世界秩序,一种自由的世界秩序。⑭
文学作为世界框架,需要一个世界的开端。蒙特使用了弗·施勒格尔的东方语义,认为东方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原初统一,在语言和理念上都构成了开端和终点,向欧洲人展示着“无对立的精神同一”和“直接的自然生活”⑮。蒙特称东方精神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认为东方主义是现代精神的重要塑造者,影响绵延至今,弗·施勒格尔对印度语言文学的关注就是明证⑯。考察东方文学其实是研究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原初诗”,寻找失去的地上乐园。在蒙特看来,西方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解决,因为所有问题都是精神和自身分裂、主客体相互限制所致。进一步,还可以解决文学史家的身份困惑。那个时代的德国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文学不过是消遣,哲学才是理性的唯一源泉、民族和历史的塑造力量,然而代表了原初统一的东方文学,不仅让文学作为“无限的表现和塑造”得以和作为“无限的科学”的哲学分庭抗礼⑰,还让那种文学和哲学的区分显得可笑。
其次,世界文学史给出了中国文学的人类历史定位。世界文学史家笔下的历时结构以古代/现代区分为基础,区分的方式大致有三种。1.形态。如弗·施勒格尔时常说的,古代的修养原则是自然宗教,而现代是神秘的爱;古代的素材是热情,而现代是机智;古代的基调是雕塑性的,而现代是音乐性的⑱。2.独立性。席勒早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里就指出,古代是和谐的统一体,而现代的特征则是各系统相互分离⑲。同样,蒙特在《文学通史》中强调,文学在现代是独立的生活领域,而古代社会只有一种统一的国家生活,不论诗、历史还是哲学都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⑳。3.能动性。文学自治意味着文学系统的自主发展,如蒙特所说,现代文学面向无限未来,从不餍足,充满渴望,具有躁动、紧张、无节制的特色㉑。
中国文学的历史位置,取决于它究竟属于古代还是现代。但古代和现代的区分又是依据编码性的形式原则,因此古代/现代的区分会再次输入到古代内部,从而在古代之内造成古代/现代的区分,进一步规定中国在古代之内的位置。浪漫派往往将古代划分为开端(东方)、高潮(希腊)、衰落(希伯来)三个阶段,同样在东方中,依据和欧洲精神的距离,又可以分为较现代的西亚民族和更远古的中国和印度。
罗森克兰茨和佛特拉格均为世界文学史先驱,前者在《诗及其历史》“前言”中,称自己的《诗的通史手册》(1832)为首部世界文学史,佛特拉格的《诗史讲演录》(1839)继之。罗森克兰茨属于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在《诗的通史手册》“前言”里称自己是“黑格尔的信徒”㉒。佛特拉格最初也是黑格尔主义者,深受其世界史观的影响。在这两位哲学界权威写成的世界文学史中,对中国文学的古代位置有明确界定,关键点首先是中国文学不自治。佛特拉格就强调,东方民族的诗和国家、宗教、风俗合一,生活是诗的,诗也是生活的,而西方人的诗和生活相互分离,诗只是装饰而非基础㉓。
其次,中国文学被动、保守。罗森克兰茨用被动性定义全部东亚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东亚文化不超出“止于己内的直观性的理论过程”(theoretischer Prozess in sich ruhender Beschaulichkeit)㉔,也就是冥想静观。佛特拉格概括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为“描写和描述”(Beschreibung und Schilderung)㉕,与罗森克兰茨的观点完全一致,没有精神的主动塑造能力,只能被动地摹写和描画。到了19世纪末,世界文学史家们仍持同样的看法。哈特就认为,东方民族文学反映了人类文化的第二或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无文字的“自然民族”)㉖,“保守主义”成为此阶段的普遍特征,因为刚刚脱离原始混沌状态的人们,不具备强大的进取能力。
再次,罗森克兰茨和佛特拉格等人也在横向比较中规定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罗森克兰茨《诗及其历史》将世界文学分为三个圈子:“人种学民族”(ethnische Völker)、有神教民族和基督教民族。宗教形式是区分圈子的根据,人种学民族从自然直观出发,逐渐提升到对于上帝的统一、善和智慧的表象;有神教民族从唯一全能神的表象出发,返回自然直观;基督教民族则从上帝道成肉身的直观出发,上升到作为绝对精神的上帝概念。三种宗教倾向分别对应于美、智慧和自由三种美学理想。第一圈的人种学民族,从诗的理想来说又分为:1.东亚组(感伤的理想),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支那;2.西亚组(英雄的理想);3.欧洲组(个体的理想)。为了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特征,罗森克兰茨使用了简明的操作程序。第一步,确定东亚文化的总体特征。他将中国、印度和印支民族归入“被动民族”,其文学亦清静无为,以抒情性和纯描述为特点;第二步,相互区分中、印两国文学。中国诗的精神原则是孝敬,由此引出理智(教化)和感伤两大特征,一方面儿童需要教训,另一方面孩子和父母之间又充满温情。印度诗的原则是性爱,游移于纵欲和厌倦享乐的两极之间。中国、印度又统一于无我的佛教精神,无论中国的父权专制还是印度的放纵都只有一个后果,即个体的消解㉗。
佛特拉格在古代民族中区分中国和印度、希腊、希伯来三种美的理想,分别对应于史诗、戏剧、抒情诗。用体裁来代表不同地域的文学,将世界文学呈现为一种“体裁诗学-地理学结构”,这也是19世纪的通行做法㉘。中国、印度代表诗的孩童时代,幻想多于情感。希伯来的诗歌情感深沉,如音乐般震撼灵魂。希腊居于印度和希伯来中间,遵循优美与和谐的规则,如雕塑般形态优雅。他认为,东方诗虽不乏优雅、崇高、感伤、哀诉及滑稽幽默,但缺乏最基本的两种要素,即希腊式的和谐和希伯来式的激情,中、印两国文学则只发展了“较小的美的要素”㉙。
最后,通过推演、区分和联想,世界文学史家构造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世界文学史的各式偏见中,最经常冒出的一个词是“中庸”,代表了世界文学史家对中国文化性质的普遍看法。罗森克兰茨认为,“中庸”意味着远离现象世界的扰攘,抑制感性欲求,让意识沉浸于“一切存在的本质性一体的思想”㉚。蒙特说,孔子在伏羲的基础上发明了“中庸”,这个概念强调力量的平衡、人世的和谐,它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人处在天地之间,既遵循宇宙法则,也是其维护者,从而成为天地间真正的“中”,这是中国独有的“三位一体”理论㉛。卡里耶认为,中国人处处求中庸,导致了普遍平庸,排斥独创和天才㉜。
不难看出,19世纪德国的世界文学史中,中国的“中庸”被悄然转化为世界的“中庸”,即价值等级刻度上的“世界之中”。中庸本为儒家至德,旨在与天地和谐,而到了世界文学史那里,中庸不仅意指平庸,且标明了中国在世界的中间位置:中国人和野蛮人相比是有教化的,但和真正的教化民族相比则是平庸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诋毁自孟德斯鸠、赫尔德以来已成传统,在世界文学的“中庸”图式下,中国人虽然也是理性民族,但只有乏味的实用理性,感伤和迷信就是这一准理性实现自我超越的方式。“中庸”概念的世界化,终于吞噬了浪漫派心目中东方作为原初统一的所有正面意义。对整个文化来说,上不能达到主观,下不能达到客观的中间状态,排除了作为主客观斗争的精神运动的可能。
三、世界文学史的形式与中国文学框架
对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家来说,文学史的功能是建构文学秩序,而真正的文学秩序即世界文学秩序。为何研究文学?为何研究东方文学?是世界文学史暗含的导引问题,分别代表世界系统的同一化和差异化冲动,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世界系统运作需要两种意识形态,一是普遍主义,二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种族和性别是个别性的象征)㉝。面对社会这个看不见的质询者,文学史家无数次提出类似的问题又自己给出答案,小心翼翼地试探系统反应,决定下一步行动,因为要证实自己在系统内的合法地位,就不得不参与问答游戏。反过来,汉学家的研究源于系统的何种需要,从世界文学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文学史家代替汉学家回答了几个关键问题:1.普遍文学概念意味着世界一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2.东西方是世界文学的基本结构;3.中国文学属于古代中的古代。在此意义上,世界文学史成了中国文学史的精神母体。不仅如此,世界文学史家还先于汉学家进行了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初步尝试,其主要贡献为:1.草拟中国文学史的体例;2.确认中国文学的主要符号;3.研究中西方文学理念的差异。19世纪初,“文学”和“世界文学”在知识系统内争取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在系统内为“中国文学”这个子系统预留了位置。换言之,早在中国文学译入欧洲之前,系统就已经知道中国文学是何等面目。
早在历史主义出现之前,16、17世纪就有了作为“博学”(Gelehrsamkeit)史的世界文学史。19世纪初的部分文学史仍属于博学传统,一方面以目录学的方式进行编撰,尽可能多地辑纳材料,另一方面则试图包含诗、哲学、历史、神学、自然科学等所有科学。瓦赫纳(Ludwig Wachler)《文学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1822)和格勒塞(J.G.T.Grässe)《文学通史手册》(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Literaturgeschichte,1844)是这类世界文学史的代表。《文学史手册》中,中国文学条目处在古代第二阶段即“从摩西到亚里山大大帝”时期,提及中文的特点、孔子生平、六经和《大学》《中庸》。《文学通史手册》则分割中国文学为中国诗、中国神学和中国史学三个条目,前两条位于第二阶段第一期即“从摩西到亚里山大大帝”时期,中国史学条目位于第二阶段第三期即从奥古斯都时期到公元476年。其中中国诗只提到《诗经》,中国神学提到孔子生平、四书五经及老子《道德经》,中国史学则提到司马迁、司马光等。
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中国文学述稿》(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出版于1854年,一些中国学者视其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㉞,德国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也认为它是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代表㉟,然而这一界定尚未获得普遍承认,原因是体裁认定有困难。硕特的文学史分13章,前12章分别为:国家宗教的经书;道士经书与其他哲学宗教典籍;佛教经书及宗教道德典籍;独立的儒家、经师、方士;朱熹的作用与中国文化的僵化;史书;地志;统计和法律;语文学典籍;博物志和医书;生产百工;汇编和百科全书。最后一章才是“美文学”,篇幅很小。形态上,《中国文学述稿》更像书目辑录,和一般文学史相去甚远。然而,联系到当时还在通行的博学史式的文学史,《中国文学述稿》作为缺乏历史线索的文学百科全书,其实属于博学传统的世界文学史类型,称它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是没有问题的。
弗·施勒格尔心目中的文学形态也是如此。《古今文学史讲演录》定义文学为“一个民族的智性生活的总和”㊱,“以生活和人自身为对象的”的所有“艺术和科学”㊲。但浪漫派文学史的形式从根本上被绝对物所决定,并非经验性的文学知识,世界文学史能够预演后来的专业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形式,结构性原因就在于此——德国汉学家同样出自精神史传统。绝对物显现的三种主要方式是语言、体裁和文学史本身。语言需要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斡旋。不同文学体裁作为绝对物的不同显现方式,地位并不平等,文学史因此具有“体裁诗学”维度㊳。文学史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形式,为了重构精神确定又不确定、主观又客观的特征,须交替使用概念和象征。文学史书写可使用对话形式(弗·施勒格尔《关于诗的对话》也是世界文学史㊴),也可以采取讲演录形式。讲演录严格遵循事件“生成法则”,但仍暗含了开端—历史描述—结局的三段分/合模式,且部分要与整体相似,每一时期以开端和衰败为两端,加上中间的高峰,又构成一个三段。在德国浪漫派眼中,只有三段才是有机结构,表示精神在交替中走出自身又返回自身。这在弗·施勒格尔那里就是“时期”(Periode)的基础和起源。为了调和历史判断和绝对的美学法则,他还引入了“理想”(Ideal)的先验概念,使形式和内容在“理想”中得到综合。
百科全书的条目安排已经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定位,但只有在理想的相互衡量和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欧洲的“文学万神殿”为中国文学准备的位置才能清楚呈现。世界文学史家和后来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学史的同构性,源自精神的规定作用。精神通过范畴塑造历史事实,导致早期中国文学史述中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带有象征的意味,以偏概全的修辞运用随处可见(这样也能将很有限的中国文学素材利用到最大限度),其主要手法为以下三点。
首先,呈现精神最方便的途径,是找到作为原型的符码。博学史中,它只是条目下的核心内容,而一旦进入精神史轨道,它就像一颗种子,可自行产生对立面,从而展开自身。以孔子代表中国的文学理想,是常见的处理方式。在19世纪任何一部世界文学史中,孔子都是中国文学的引导人物和代表作家。可想而知,有了孔子,就必然有和孔子相区分的符号:先是老子和道家,后来是佛家,最后是市民化的小说、戏曲。
其次,古代的命运是走向没落,为现代文明所取代,这注定了中国在文学史叙述中从古代高峰衰落的趋势。换言之,中国精神无法返回自身的开端。佛特拉格说,中国文学的荣光只存在于最古老时期,之所以充满感伤,是由于“帝国大概也意识到,不管经历多少次复苏,也无法达到它最古老的繁华时代神一样的纯粹和鲜活了”㊵。到19世纪末,斯特恩仍然认为,《诗经》是中国文学唯一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它多少保持了青年期的活力和新鲜,甚至勇武的战斗精神㊶。
再次,中国文学史分三期,经常是以《诗经》代表古代,李杜代表近代,小说、戏曲代表新时代。佛特拉格如此勾勒中国文学的三个阶段:1.古代诗围绕“国家和帝国历史”展开㊷,总是甜美、感伤地追忆古时;2.近代诗反映了日益文明化的自然,李杜是其代表;3.戏剧和小说反映了“人在国家中朝着科学和知识攀登”,科考沉浮的间歇也有对爱情和自然的憧憬㊸。罗森克兰茨眼中的三阶段是:1.由自然诗到艺术诗的发展,对应于国家由封建制过渡到君主制;2.“叙事性娱乐诗”(小说)阶段,这是君主制下官僚体系的全盛期;3.戏剧文学阶段,这一时期的君主制虽然形式上严守传统,内部却已开始瓦解㊹。
最后,由精神概念推导中国文学的特性,成为隐蔽的思维定式。19世纪是欧洲知识系统接纳中国的最初阶段,对中国文学的想象只能借助固有范畴来实现,例如中国人不是自然民族而是文明民族,有文学,但没有悲剧和史诗,低俗的戏曲代替了悲剧,才子佳人小说代替了史诗,科举及第的书生就是中国的英雄。这相当于说,中国文学是不符合文学概念的文学。德国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宗教缺失,宗教是绝对物最直接的体现,没有向神的超越,就没有摆脱经验限制获得自由的可能,个性就无从实现。但中国文学用局部技巧来弥补内在精神的不足,这就是卡里耶说的,“矫揉造作代替了艺术”㊺。佛特拉格也认为,中国、印度文学只拥有“较小的美的要素”。也许是中国工艺品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象牙雕刻成为形容中国文学最经典的比喻之一。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核心,卡里耶的世界文学史对中国诗的描述可谓集各类范畴之大全:
抒情诗是情感的直接倾诉,中国民间诗通过理性的感知方式,获得了教训的色彩,通过从自然图像出发,获得了描述性和直观性特征。启迪它的基本情感是孝敬;温柔的献身、细微的触动全然压倒了激烈和行动欲;明朗的愉悦和怨诉的感伤相交替。㊻
引文中并没有贬义词,但每一句都是无具体作品支持的范畴的自行展开。中国文学是“抒情诗”和“民间诗”,“理性”一词连接了“教训”,而“描述性”“直观性”代表了和自然相交融的面向。这就是罗森克兰茨讲的基于孝敬的中国诗的双重特征:感伤和理性。从固定图式出发,自然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并转化为对象本身的千篇一律,这就塑造了凝固而单调的中国文学。
四、交接时刻:世界文学史家和汉学家的相遇
世界文学史家遵循精神史逻辑制造的中国文学模式,对汉学家也产生了影响。所有认知性操作都需要规定其对象域的初始结构,这一结构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早期汉学家(如硕特、顾路柏)并无文学专业背景,更需要借鉴他人的研究。“中庸”经过世界文学史家的渲染,俨然成了中国文学的天然结构:一方面缺乏幻想力,偏好教训和史书;另一方面十分感性,时时陷入感伤。西方汉学界后来流行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和史传的叙事传统两大命题,在此都能看出端倪。汉学家的经典主题如中国无史诗、无神话、无个体英雄等,也源自世界文学史书写。
佛尔克(Alfred Forke)是德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率先在德国译介中国诗歌和戏曲,其基本观念却和世界文学史家无异。《汉六朝诗精华》(1899)“前言”中,他认为中国诗的情感生活出自“更简单文化”,无法和“我们的更高的文明”相比,只能和同一文化阶梯上的希腊、罗马、印度、波斯、阿拉伯人对照。希腊和罗马的诗歌在形式上更清晰、优美,但忽视爱情。印度诗写爱情,但不超出最粗鄙的感性。波斯和阿拉伯诗的情感被智慧和反思所窒息。中国诗的好处是“真切、深刻、诗意的情感,感觉的纯粹和温柔,对于自然的全心投入和热爱”,缺陷是缺少想象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主题单调㊼。同时他相信,所有的东方诗人都因袭陈套,喜欢描写外部和次要之物。世界文学史家把印度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参照,佛尔克亦如此。他断言,印度人有强烈的宗教性,因此富于幻想,能创造神话和史诗,中国人只有实用理性,长于历史编纂,但也不会陷入印度那种无节制的臆想,而以世俗生活和情感为导向。在历史线索上,佛尔克将中国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以《诗经》为代表的古典期;2.两汉到唐之前的近代;3.文人诗最完善的唐代;4.宋以后进入现代,现代诗人一味追摹唐诗,如同西方人崇拜拉丁文一样㊽。如果注意到两汉到唐的过渡期性质,这仍然是一个开端—高潮—结局的三阶段模式。
佛尔克的《中国元剧选》是德国汉学在中国戏剧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和世界文学史家遵循同样的阐释模式,辨析中国戏曲是否属于悲剧类型,是他们关心的头号问题。他说,《汉宫秋》虽被王国维称为悲剧,却并不符合西方的悲剧概念,因为其中既无强有力的性格,也无剧烈的灵魂冲突:“我们的悲剧要求伟大斗争——伴以心灵冲动——中的强有力性格,英雄是在和命运开战。”㊾类似观点直到今天还通行于德国汉学界,顾彬的《中国戏曲史》完全采纳佛尔克对《汉宫秋》的评论,和他的先辈一样,其阐释兴趣主要是批评中国戏剧不注重个体性格,只关心道的永恒秩序㊿。
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系统间传递,最清楚地显现在世界文学史家鲍姆伽特纳和汉学家顾路柏相遇的那一刻。鲍姆伽特纳《世界文学史》第二卷《印度和东亚文学》1897年出版,其中“中国文学及其分支”一章篇幅不小。鲍氏不通中文,完全依据欧洲二手文献完成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1902年,顾路柏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前言”中提到鲍姆伽特纳,称赞其中国文学史叙述为同类著述中“最好”的一种[51]。的确,鲍氏的作品不但内容充实,体例也较完备,共分五章:第一章“《诗经》”,第二章“中国文学的一般发展”,第三章“中国文人文学的主要分支”,第四章“中国小说”,第五章“中国戏剧”。对于习惯了把文学当作所有“艺术和科学”的世界文学史家来说,中国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完全不是问题。鲍氏将中国文学分为经、史、子、集和词曲五类:孔子代表经,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核心;司马迁代表史,史和经的关系最为紧密;老子代表哲学;集部被译成“美文学”,包括《楚辞》以及各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包括戏剧和小说。中国文学的平面框架就此设定。在鲍氏眼中,《诗经》、李杜和小说戏曲分别代表了历时的三个阶段,但在纵向描述上,存在着“活中国”和“死中国”的矛盾,这自然反映了欧洲人不断增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一方面,“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观念更错误,即认为中华帝国在逾四千年中都僵化不动,如同固化凝结在最初的制度设施中了”[52]。鲍氏长篇引用翟理斯译《佛国记》,介绍佛教在中国历代的传播,把佛教看成和本土宗教对峙的他者,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动能。另一方面,他把“皇家图书馆”的绵延不衰视为中国文学发达的标志,而图书馆显然代表了保守精神:保存、整理的热情压倒了个人创造。
对于中国文学的具体评价,鲍氏因袭前人见解。李杜是中国诗全盛期的代表,但李白这位“中国的俄尔甫斯(Orpheus)”,并没有超过《诗经》的水平。他认为中国诗永远是“现实主义的自然描写”,没有“真正的虚构、充满想象的塑造和热烈运动”,如同象牙、珠母上的精雕细琢,只是“小工艺品”(Kleinkunst)[53]。中国小说不过体现了中国人的劳动本能,因为他们特别善于收集;相应的,章回小说也只是历史故事、街头见闻的流水账。鲍氏对中国戏剧评价也很低,《赵氏孤儿》在他看来集中了中国戏剧的全部弱点:没有深刻的心理发展和性格刻画,没有更高的理想作为视角和动机,而只是以人的同情心作为救人的根据。全篇结论是,真正的“年轻理想”属于基督教民族,他们远远超越了“印度人的假理想主义”和“中国人童稚的现实主义”[54]。而中国文学因为没有宗教启示,无法超越现世,薄弱的想象力仅能完成细部雕琢。
《诗经》单列为第一章,无疑是以个别代表整体的修辞:一部《诗经》即全部中国文学。其他各章都未分节,而这一章特别分为五节:1.“《诗经》的历史”,2.“爱情诗”,3.“出自自然生活和人民生活的音调”,4.“宗教诗”,5.“政治时事诗”。叙述从国风进到雅、颂,从私人、家庭转入宗教和国家生活,自成一完整的小结构:
临近结尾时,个人性为更大更普遍的观点所取代,统驭思与诗的不再是个别的情爱悲欢,而是国家整体的哀与乐,在庄严的祭祀歌中,所有主题中的最高者——宗教——迎向我们,然而更多的是仪式、尊贵和豪华,而非内在的神圣和高尚。”[55]
这里暗示的,首先是精神从个人、自然向普遍性跃升,但上升之途止于国家,和国家融为一体成为精神超越的终端。其次是宗教在中国处于悖论性位置。《诗经》多少表达了中国人的宗教性,因此格外受西方人重视,然而这种宗教性绝非“内在的神圣和高尚”,而只是外在仪式。在鲍姆伽特纳看来,不仅哲学、科学、技艺,即便宗教在中国也低于经,它只是实用知识而非文人教养的核心。故凝聚于《诗经》的中国文学精神既非希腊式的个体意识,亦非希伯来式的宗教激情,政治批判和宗教崇拜不超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都限制在“中庸”框架之内。鲍氏总结说:
总之,吹拂《诗经》的不是那种创造了《伊利亚特》的战争英雄精神,也不是鼓舞《奥德赛》历险的浪漫冲动……处处都是现实之物和可理解之物……贯穿《圣经·诗篇》的为上帝所激励的热情,在这里无法想象。只有在深重苦难中,诗人才会偶然高尚奋发,成为天子和庶民的最高审判台。一般情况下宗教不超出市民和乡村的狭隘圈子。[56]
与鲍氏著作相比,顾路柏《中国文学史》有很大不同,其中《诗经》的比重大大降低,对孔子的描述则极为详尽。同时代西方汉学家引用这部文学史最多之处,就是其中对儒家思想的深入阐释,圣徒传般的孔子生平是这部文学史的核心。然而,描述孔子就是间接描述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顾路柏相信,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深刻意义是其在各方面都是最典型的中国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57]。他的文学史其实更像经学和思想史。鲍氏虽然也介绍经史子集的分类情形,然而文学是主要脉络,这尤其体现在对《诗经》的详细介绍上。顾路柏的文学史更忠实于中国“文”的历史发展,经史和哲学是其重点,文学主要体现在第八章唐诗和第十章戏剧小说。《诗经》是作为孔子的作品淹没在第一章的五经中的。第五章讲屈原和《楚辞》,但篇幅很小。在第六章汉代文学中,他认为只有历史书写取得成就。第七章涉及赋和散文,但重点是介绍佛教。第九章(宋代文学)同样没有为文学留出多少空间,因为“宋代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应该归功于哲学而非历史”[58]。他的文学史描述了一个三阶段的倒退过程:1.先秦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其代表是儒道经典;2.中国文学全盛期在唐代,但唐诗的成就只是形式的完善,即完成了民众诗到艺术诗的过渡,和通行做法一致,顾路柏以李杜代表全部唐诗:“关于李白和杜甫所说的,略加改变就适用于唐代其他诗人,不管他们在李杜之前还是之后。”[59]3.戏剧、小说在宋代以后兴起,它们作为古代文学语境中的“新文学”,并未带来文学的复兴。
顾路柏对中国的定义是:“一段还活着的古代。”[60]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是传统的延续,但对于民族的精神发展来说,连续性绝非福音,欧洲读者在读中国小说时会感到“不同面具下是同一个感知的心胸”[61]。他说,中国诗歌的母题、意象单调,想象力贫乏[62]。中国散文是一种象牙雕刻般的艺术形式,只有美的形式而无内容[63]。中国小说则只铺陈外部事件,不顾及性格刻画,人物的特征是缺乏“自由的自我规定”[64]。他还批评说,“要在中国戏剧中找到那种我们理解为性格发展的东西,纯属徒劳”[65]。停滞的中国精神同样可以归咎于宗教,顾路柏认为,中国人缺乏一种“实证宗教”,朱熹用“实证礼学”取而代之,填补了这一空白[66],却让中国文化精神跌入万劫不复之地。这些起到支撑作用的偏见,可以在各类世界文学史中找到,显示了汉学和一个更大的知识系统的关联。
顾路柏一向被尊为德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物,按照司马涛(Thomas Zimmer)的评价,他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研究有两大意义:一是从18、19世纪欧洲小说发展史的背景上来解释中国小说,二是对中国长篇小说进行了初步分类[67]。司马涛的看法表达了德国汉学家的某种认祖需要,而有意忽略顾路柏的“专业性”的系统根源。两个“意义”其实都是世界文学史的通行做法。鲍姆伽特纳在顾路柏之前就将中国长篇小说分为历史、世情、神魔等类别。不仅如此,鲍氏关注佛教,视其为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挑战,同样,顾路柏认为佛教是凝滞的中国精神经历过的唯一动荡。鲍氏称赞中国人勤于保存,故将《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字典,或《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当成中国文学的核心内容。同样,顾路柏震撼于中国人在文献编撰方面“蜜蜂般勤劳”[68],认为《永乐大典》这类“编辑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最核心的特点之一,这本身就暗含了对中国文学创造性的否定,即中国人更善于保存,是天生的语文学家而非诗人[69]。关于经学、哲学、宗教,顾路柏给出严谨的专业评论,然而在文学方面,相对于以往中国文学史叙述增加的新内容并不多,如宋诗和词完全被忽略,元曲则只字未提。在材料编排和阐释上,顾路柏也沿用既有框架,只是以专业汉学家的知识去填充和丰富它,却并未开发出新的意义。
五、世界文学史悖论和20世纪以来的变化
“世界文学”概念背后除了唯心主义哲学外,还有文化比较的需要。按照卢曼的观点,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文化”(Kultur)概念的语义结构即比较文化。与传统“文化”关联于农牧业的“培养”(Agrikultur或cultura animi)不同,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第二次登记造册,且要在世界范围进行比较,所牵涉的参照越多,越有异域色彩,也就越有趣。文学作为文化卓越代表,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事件”,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一普遍性事件却出自专门的欧洲地域和专门的历史时代,欧洲人在这个时代特别热衷于比较,试图建构一种比较视角[70]。故卢曼认为,“文化”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概念之一,因为这一概念将系统的自我描述误认为普遍描述。诸如个体、自由这类理念源于欧洲传统,却被不假思索地当作文化比较的前提[71]。
换言之,世界文学史书写的两大支撑性概念——精神和文化——都内含着悖论,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怪异地位:世界文学运作基于文学间的比较,故需要一个“中国文学”作为对照,但中国文学既然是欧洲文学的他者,则又是作为被排斥者纳入整体的。既纳入又排斥,这是孕育关于中国文学的一般偏见的基本悖论。德国的文学史书写在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精神哲学向实证主义的转变,然而这并未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因为结构改变以知识积累为前提,关于中国文学的实证知识超出了世界文学史家的能力范围,而汉学家的知识获取仍然依赖既有结构,这注定了观念转变的艰难。
为了将“后验”(a posteriori)移入“先验”(a priori),消除先验性文学结构的抽象性,佛特拉格曾提出一种“经验性方法”(empirische Methode),其内涵是既采纳“理想”概念,也引入比较文化结构,以实现理想的具体化——他相信理想可以按其“内在重量”来称量[72]。然而,理想造成了后验向先验转化,却不能返回后验,要么作品成为精神象征,要么将精神变为工具。能有效连接精神和现实、整体和个别的,只有“批评天才”——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抽象形象。但即便是了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也不见得有体验中国文学作品的能力,成为理想的批评天才。
实际上,整套浪漫派文学观念背后,藏有德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世界文学史的悖论在于,它是“德国的”世界文学。弗·施勒格尔用德语写作世界文学史,有着强烈的“述行”(performance)意味。文学史首先是缔造民族的工具:有教养的民族既要有文学,也要有历史记忆。同时,文学史要造就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将不同的民族精神联成一体,这种大同理想反过来要印证德国精神的优越性。浪漫派艺术自治论本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艺术的世界自己观察自己,主体只是观察媒介。然而,客体艺术向世界艺术的转变,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尚未彻底完成,它将本民族文学系统内的普遍性误认为超系统的普遍性,证明他们还彷徨于作为实体的世界和作为世界建构本身的世界之间。显而易见,在“德国的”世界文学史中,中国诗人不会成为英雄,中国文学也不会占据舞台中心。而先验的世界文学史概念,给它所孕育的中国文学史打上烙印,使中国文学史本身也成为某种脱离经验实证的结构,为各种幻想和偏见提供土壤。
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汉学学科的设立和对中国文学了解的深入,对中国文学的描述不仅分量增加,也日趋正面。实证知识在理念指导下产生,反过来也塑造理念,浪漫派熟知的这一先验和后验的解释学循环原理,同样可应用于欧洲的中国文学发生学。豪塞尔(Otto Hauser)在《文学的世界史》(1910)中毫不掩饰其种族偏见,称“浅色民族”为“天才民族”[73],但他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却颇佳,主要原因就是知识视野的扩大。在德国翻译出版了首部李白诗选的豪塞尔,具有一定汉学能力,能够吸收欧洲人新获得的汉学知识。
由于汉学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世界文学史家在丛书编写时逐渐将汉学家纳入。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是施密特(Erich Schmidt)编《东方各族文学述》(Die Litteraturen des Ostens in Einzeldarstellungen)的第8卷。施密特是著名文学史家谢拉(Wilhelm Scherer)的弟子,他还另编有一卷本《东方文学》,其中顾路柏撰写的中国文学部分实为其《中国文学史》的缩微版。出版过谢拉文学史的瓦尔泽尔(Oskar Walzel)主编了《文学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丛书,收入卫礼贤《中国文学》(1928),该书为德国汉学界公认的第二部中国文学史。这都很好地说明,(世界)文学史是一种纳入机制,这一机制产生了对中国文学史的需要。不过,在20世纪的德国文学研究界,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书写方法已让位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国别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热潮都已过去。
有意思的是,在史观反思上,世界文学史家又走在汉学家的前面。世界文学史在20世纪德国风光不再,拉特斯(Erwin Laaths)《世界文学史》(1953)是硕果仅存的代表,至1988年已出六版。拉特斯对世界文学史传统有继承也有革新,继承表现在,他接过了人本主义理想和精神史导向,将文学史理解为“一个精神-艺术集体的传记”[74],以人为中心和标准;革新是,他放弃了19世纪的普遍主义,意识到现有的历史概念和历史模式未必永恒不变,数百年后也许有“新的、绝对有效、被普遍相信的理念作为新的共相逐渐形成”[75]。19世纪世界文学史家相信有一个“俯瞰视角”,观察者由此“看见地上各国”[76]。拉特斯却坦承,他的目标只是“西方的世界文学”,而非“其他的世界文学”[77]。“其他的世界文学”因为和西方的关联才被纳入系统。拉特斯的基本任务首先是“世界文学交织关系和效果的统观”,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忽略对西方民族文学中那些尚未上升到跨民族层面的伟大作品的细读,即是说,世界文学加西方民族文学是他的基本结构,西方中心的意味非常明显[78]。但他能意识到西方的世界文学是诸多世界文学建构的一种,并不具备普遍性,也是认识上的重大进步。通过自行呈现自身的悖论来展开悖论,19世纪的理念普遍性被系统内自我规定的普遍性所取代。自身系统之外,别的世界文学系统(如中国)可以自行其是,按自身的方式进行自我观察。
拉特斯在中国文学史叙述上和前辈的区分,首先是根据新的汉学知识更新了经典库。《好逑传》这类才子佳人小说,是19世纪世界文学史家心目中中国文学的顶级瑰宝,而他特别指出,这类小说在中国是“不大受重视的产品”,对它们的选择是“不走运的”[79]。其次,他颠倒了以往的价值评判,认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不能由汉语的孤立语特征推导出感觉和思想的贫乏——单凭汉字的无比丰富就足以反驳这一点[80]。孔子绝非欧洲人常说的毫无乐感的冬烘,他非常重视音乐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且“像这样宏伟风格的改革者,世界上再没有见过”[81]。中国文学非但不低劣,且很早就达到了西方文学今日的水准。《关雎》一类抒情诗如耳语般直入灵魂,类似的“高明处理自我心灵和世界心灵的和谐同一”的西方诗要到歌德之后才会出现[82]。中国小说的特点是“现实主义描写的非凡能力”,这种能力西方人要到19世纪才掌握[83]。为证明此言不虚,他特地引用雷慕沙(Abel-Rémusat)19世纪初认为中国人在若干世纪前就有了今日欧洲人才有的风俗和历史小说的观点:“童年阶段的民族有寓言、传奇故事、史诗;真正的小说却只有在社会的时代才能产生,即当信仰减弱,社会将其注意力转向现世事物之时。”[84]拉特斯还认为,《金瓶梅》展现了中国人对女性特性的深入了解,却没有用到“附加的或独立的心理学”——“最近许多西方小说的一个艺术上如此可疑的特征”[85]。中国戏剧实为搬上舞台的叙事文学,比较冗长也是可以理解的。形式上,它把抒情诗唱段以史诗的方式串在一起,主要兴趣是以曲词和歌唱表达人物的灵魂状态,而非借戏剧冲突制造幻象。但相比于欧洲歌剧,中国戏剧又具有优势,因为它是“更纯粹的艺术品”,而欧洲歌剧依赖音乐,文本过于稀薄[86]。
中国文学在拉特斯的世界文学系统中发生了挪动,原因自然是世界文学结构本身的改变。系统的结构性需求体现于文学理念,它对域外文学知识生产的调节作用提醒人们,世界文学概念的先验结构不但决定了世界文学的普遍联系,也决定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国别文学的个别性。考察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书写,可以看出,作为精神的文学理念为了展开自身,需要分裂为众多民族文学,但首先要构造出一种精神上异于西方文学的东方文学,以演绎“东方”在世界精神演化中承担的特殊功能,于是,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就成为逻辑必需。中国文学自身的构造同样是精神自我展开的结果,由孔子表征的中国精神必然生成代表中国文学高峰的李杜和代表新时代的小说、戏曲,在此构架上添砖加瓦,中国文学大厦一步步建成。然而,因为中国文学代表了不合乎西方精神概念的精神,注定处于保守、中庸的凝滞状态。世界文学史家在书写中国文学史时,不需要具体的中国文学知识和体验,他们铸造的中国文学框架却对后来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和中国文学体验起到预先塑造的作用。这说明,西方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专门的知识结构,隶属一个更大的知识交流系统,文学史所包含的知识和错误、洞见和偏见、赞誉和诋毁,超出了史家的个体意志,只有联系系统需求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①⑩⑱㉘㊳ Hans Dierkes,Literaturgeschichte als Kritik,Tübingen: Max Niemeyer,1980,S.132,S.241,S.275-277,S.257,S.135.
②④ Friedrich Schlegel,“Athenäums-Fragmente”,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Bd.2,Ernst Behler,Hans Eichner(Hg.),Paderborn: Schöningh,1988,S.154,S.114.
③ Niklas Luhmann,Schriften zu Kunst und Literatur,Niels Werber (Hg.),Frankfurt a.M.: Suhrkamp,2008,S.189.
⑤ Friedrich Schlegel,“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620”,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Bd.5,S.91.
⑥⑦⑧⑨ Friedrich Schlegel,“Reise nach Frankreich”,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Bd.3,S.14-15,S.12,S.16,S.18.
⑪ 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⑫ 参见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第119—142页。
⑬⑭⑮⑯⑰㉛⑳㉑ 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Berlin: Simion,1848,S.1,S.6,S.32.36-37,S.36,S.160-166,S.2,S.4-5.
⑲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㉒ Karl Rosenkranz,Handbuch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der Poesie,Halle: Ednard Anton,1832,S.V.
㉓㉕㉙㊵㊷㊸[72][76] Carl Fortlage,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oesie,Stuttgart: Cotta,1839,S.23,S.42,S.10,S.30,S.24,S.42,XII,S.17.
㉔㉗㉚㊹ Karl Rosenkranz,Die Poesie und ihre Geschichte,Königsberg: Bornträger,1855,S.40,S.40-42,S.40,S.44.
㉖ Julius Hart,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und des Theaters aller Zeiten und Völker,Bd.1,Neudamm:Neumann,1894,S.23.
㉜㊺㊻ Moriz Carriere,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Bd.1,Leipzig:Brodhaus,1863,S.139,S.152,S.160.
㉝ 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P,2004,pp.38-41.
㉞ 詹春花《中国古代文学德译纲要与书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和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世界汉学》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版),都指出硕特中国文学史为世界上首次尝试。
㉟ Eduard Erkes,Chinesische Literatur,Breslau: Ferdinand Hirt,1922,S.82.
㊱㊲ Friedrich Schlegel,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Bd.4,S.3,S.6.
㊴ 参见Hans Dierkes,Literaturgeschichte als Kritik,该书第六章标题即《〈关于诗的对话〉——缩微的美学史》。
㊶ Adolf Stern,Geschichte der Weltlitteratur,Stuttgart: Rieger,1888,S.16.
㊼㊽ Alfred Forke,Blüten chinesischer Dichtung aus der Zeit der Han-und Sechs-Dynastie,Magdburg: Faber,1899,S.XIII,S.XV.
㊾ Martin Gimm (Hg.),Chinesische Dramen der Yüan-Dynastie:zehn nachgelassene Übersetzungen von Alfred Forke,Wiesbaden:Franz Steiner,1978,S.594.
㊿ Wolfgang Kubin,Das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Theater,München: Saur,2009,S.85-86.
[51][57][58][59][60][61][62][63][64][65][66][68] Wilhelm Grube,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Leipzig: Amelang,1909,S.VIII,S.27,S.333,S.291-292,S.1,S.4,S.251,S.252,S.424,S.386,S.342,S.360.
[52][53][54][55][56] Alexander Baumgartner,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Freiburg im Breisgau:Herder,1897,S.483,S.509-510,S.536,S.464,S.480-481.
[67] Thomas Zimmer,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München: Saur,2002,S.53-54.
[69] Erich Schmidt u.a.(Hrsg.),Die orientalischen Literaturen,Berlin: Teubner,1906,S.348-349.
[70][71] Niklas Luhmann,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Suhrkamp,1997,S.341,S.398.
[73] Otto Hauser,Wel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1910,S.VI.
[74][75][77][78][79][80][81][82][83][84][85][86] Erwin Laaths,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München: Droemer,1953,S.15,S.7,S.12,S.12,S.199,S.188,S.190,S.191,S.196,S.199,S.198,S.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