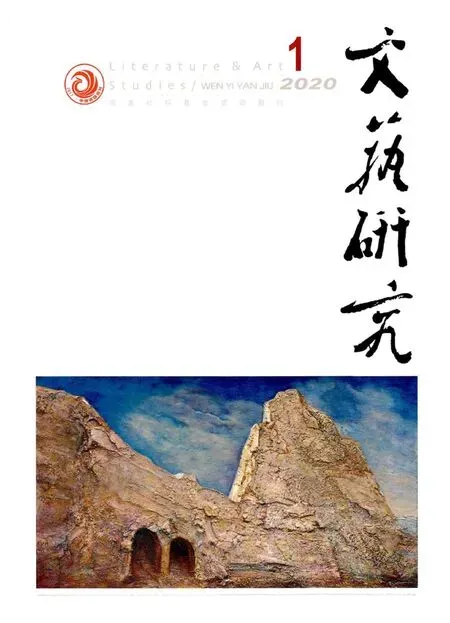“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
2020-12-28邱焕星
邱焕星
关于厦门鲁迅,既往研究普遍受其《〈自选集〉自序》里“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荒凉的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①的影响,偏于探究其精神的苦闷以及这两类创作,总体上将鲁迅定位为“孤岛过客”②,然后视厦门阶段为一个中转站或消沉期。但是,这种认知和鲁迅更早时的一些自述相矛盾,他在1927年曾多次表示“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③,“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④,“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⑤。显然,厦门阶段的面向远比既往认识复杂得多,它还发生了一些使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事件,最终让其摆脱了颓唐苦闷的状态。
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从厦门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对学院文化的疏离等抗争性角度给出新的解释⑥,但总的来看,这些事件都不足以提供鲁迅状态何以转变的合理解释。究其根源,是既往研究者没有重视鲁迅《两地书》原信中那些未删改的政治内容⑦,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原信,就会发现鲁迅在厦门这个“孤岛”虽然只待了135天,却因为此时北伐的进展,他的思想较之北京时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因此,本文试图以《两地书》的原信和一些新搜集的史料为基础,讨论厦门阶段在鲁迅思想道路发展上的重要意义。
一、党同国民党:欢迎北伐与倾向左派
鲁迅1926年南下厦门的目的,最初不但不是为了革命,甚至一度情绪消极,“很想休息休息”,“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⑧。虽然鲁迅此前曾和国民党一起对抗过北洋政府,呼应过国民革命,还出任过《国民新报》(国民党北方机关报)副刊的编辑,但随着奉系军阀杀入北京,鲁迅先是遭遇通缉传言四处避难,后因军阀枪杀知识分子,他开始意识到政治的可怕,“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于是选择南下,“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⑨。
对于广州政府正在展开的北伐行动,身在北京的鲁迅起初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国民革命在北京的失败,让他并不看好南方的革命形势,以致颇为悲观地表示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革命”⑩,实际上这也是北方社会的普遍看法,“直到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认为蒋介石的北伐也会像过去‘孙大炮’(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半途而折”⑪。但来到厦门后,鲁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各种北伐胜利的消息,他开始和许广平在通信中频繁交流,前后信件多达十几封。从“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⑫、“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⑬、“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⑭等内容来看,鲁迅显然深受震动和鼓舞,其心情随着战况而不断起伏,开始自觉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上,积极拥护广州政府的军事行动。
这里最值得分析的,是鲁迅对暴力革命和军事行动的态度。早在介入国民革命前,鲁迅就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⑮,这种对“火与剑”的认同,和其民元情结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鲁迅“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⑯,另一方面,辛亥后的复辟频现又让他非常失望,因而期待孙中山能够继续革命再造民国。而孙中山也在多次依靠军阀失败后以俄为师,提出以党治国、建构党军的措施,随即获得巨大成功,先是在1925年初的东征平叛中以少胜多,后又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胜利,以致舆论都认为“革命军之所以能达战无不利之效果,实原由该项制度之设立”⑰,“主义之昭示”“军队之政化”“民众之合作”是南方取胜的核心因素⑱。
鲁迅最初觉得“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⑲,但在厦门受北伐鼓舞后,他开始相信“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⑳,此时的他还意识不到“军队为政党掌控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由‘文斗’转入‘武斗’”㉑。与此相反,鲁迅因革命胜利表现出强烈的“党同伐异”倾向,他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㉒因此,他反对“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认为必须“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㉓。
不只是鲁迅,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对北伐持肯定态度,譬如周作人就认为“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㉔,而胡适更是宣称“南方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政府”,“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它不是红色政权”㉕。不难看出,北伐成功和国民党人展示出的力量,让这些本来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制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光明和希望,但也因此暂时性地丧失了反思批判的意识。
而相对于欢迎北伐,鲁迅与许广平厦门通信中关于国民党派系的讨论,其实也值得关注。它们最初若隐若现,后来又被有意删改,从中能看出二人当时的革命倾向。鲁迅最初是光复会成员,由于蒋介石刺死陶成章,他一直对同盟会心存芥蒂,后来他又加入过反对国民党的共和党。所以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复杂,他支持后者的革命行动,但又与其保持距离。不过鲁迅和不少国民党党员保持着密切的私人联系,譬如蔡元培一直是他在北京时的主要庇护人,后来他又在参与女师大风潮的过程中,和李石曾、易培基有过合作关系,而许广平更是国民党党员,回广州后出任省立女师训育主任,支持顾孟余等汪精卫派。
鲁迅南下虽然选择了厦门,但“也未尝不想起广州”㉖,许广平在听到他对厦门闭塞的抱怨后表示:“广州似乎还不至如此办学无状,你也有熟人,如顾某(顾孟余——引者注)等,如现时地位不好住,也愿意来此间尝试否?”㉗但鲁迅听许广平讲老同事陈启修就任中大法科主任后受到右派攻击,“在此似乎不得意,有向江西等地之说”㉘,“就暂时不作此想了”㉙。不过中山大学的改制,给了鲁迅进入广州的机会。1926年10月14日中大从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戴季陶、顾孟余为正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此举意在解散学校重新整理,来推行新的党化教育。10月16日,朱家骅致电自己之前的北大同事沈兼士、林语堂、鲁迅,想叫他们“去指示一切”“议定学制”,鲁迅收到信后觉得“应该帮点忙”㉚,而许广平也建议:“你如有意,来粤就事,现在设法也是机会,像顾孟余,于树德……你都可以设法。”㉛
鲁迅和顾孟余订交于女师大风潮,后者担任北大教务长多年,同时还是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主任,实际是北京学潮的幕后核心,“三一八”惨案后他因政府通缉南下,之后出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成为汪精卫派的核心人物。由于顾孟余当时主管中央宣传,为扩大宣传力度,1926年9月23日他电邀孙伏园赴粤办报,鲁迅对此非常支持,他说:“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后来为了给许寿裳找工作,鲁迅还曾“托伏园面托孟余”㉜。但许广平不久透露消息,“顾先生的态度听说和在北京时有点不同,向后转了”㉝。对此,鲁迅回信说:“孟余的肺病,近来颇重,人一有这种病,便容易灰心,颓唐,那状态也近于后转;但倘若重起来,则党中损失也不少,我们实在担心。”㉞由此可见,鲁迅对顾孟余和国民党的关切。
隔了几天许广平传来好消息:“这回改组,是绝对左倾,右派分子已在那里抱怨了,这回又决意多聘北大教授。”㉟收到信后,鲁迅随即表示:“如果中大很想我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便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㊱据顾颉刚日记记载,鲁迅为了私下疏通,“遣其旧徒孙伏园到广州……孙到校访各委员,具道鲁迅愿至粤意,彼等示欢迎”㊲。最终鲁迅被聘为唯一的正教授和文学系主任,鲁迅分析这是因为中大觉得自己“非研究系的,不至于开倒车的”㊳。事实也是如此,中大的长聘原则正是“择其努力的党员,与本校有很大的劳迹关系,而根据党的旨趣以进行者,为本校永任教授”㊴。
不难看出,鲁迅此时的思想已经颇为左倾,甚至为创造社成员离开中大而气馁,他很想联络对方在广州有所作为,许广平甚至建议他出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但是左派在广州的优势是暂时性的,实际上各派斗争非常激烈,随着1926年底汪精卫、顾孟余等人随政府迁往武汉,中大的权力逐渐掌握到国民党右派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却在中大与共产党接近,“他对代表共青团和他接近的青年特别热情”㊵,并拒绝国民党人的宴请和约稿,这无意在“清党”之前将自己放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位置。
二、伐异顾颉刚:“研究系”与“反民党”
鲁迅在厦门一步步“党同”国民党左派之时,政治思想的左倾也影响到了他和顾颉刚的关系,彻底激发了双方在北京被掩盖的矛盾,使其“伐异”也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顾颉刚和鲁迅本属同一阵营,他们在北大是师生关系,最初都是国学研究所和《语丝》的成员,顾颉刚“以鲁迅长我十二岁,尊为前辈”㊶,不过由于他也是胡适整理国故派的重要成员,同时和陈西滢是同乡好友,所以顾颉刚一直游走于浙派与皖派、英美派与法日派、《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这种情况最初没有影响,但随着女师大风潮和国民革命的发展,两大知识群体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顾颉刚开始体会到“在夹缝中度生活”的“可怜”㊷。由于顾颉刚内心更倾向于英美派,“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也”㊸,所以一方面“《语丝》宴会,予亦不去”,另一方面开始在《现代评论》上大量发表文章,甚至“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古温《支那文学讲话》”㊹,由此导致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更加激烈。
不过,两人在北京时期并没有公开的矛盾,在厦门初期关系也看似不错,“同室办公,同桌进食,惟卧室不在一处耳”㊺。但随着“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㊻,鲁迅对他的恶感越来越强烈,不仅如此,顾颉刚还不断援引自己人到厦大任职,因而被鲁迅视为“有意结成苏党,与彼暨孙、章(孙伏园、章廷谦——引者注)之绍兴帮相对,于是北京大学之皖、浙之争,移而为厦门大学之浙、苏之争”㊼。鲁迅开始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多次对顾颉刚加以抨击:“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㊽;“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㊾。在“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的情况下,让情况更恶化的是现代评论派的“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这让鲁迅觉得双方有合流的趋势,“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㊿。
而此时的北京政府正在合并女师大和女子大学,这让身在厦门的鲁迅知道消息后非常气愤,他和许广平觉得“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在他们心目中,现代评论派和梁启超臭名昭著的《晨报》研究系是一丘之貉,他们一贯“迎合卖国政府,而利己阴谋,可恶可杀”[51]。在这种背景下,鲁迅觉得厦门“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52],而顾颉刚之前在北京拒绝参加《语丝》聚会、积极参与《晨报》活动的事,就被鲁迅回忆起来了。如果查顾颉刚1926年的日记,会发现他上半年多次记录与江绍原、徐志摩、陈博生等研究系人宴游、通信和写稿,此外他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逆潮流的“反动”行为。所以,顾颉刚很快发现“鲁迅公开向学生斥我为‘研究系’,以其时正值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北伐,以研究系梁启超等为打倒之对象也”[53],显然,双方的矛盾从派系冲突上升为革命/反革命的对立了。
不过让鲁迅更加不满的,还不是“顾颉刚之流”和现代评论派这些“研究系”占据了厦大国学院,而是广州政府意识不到他们是反动派。先是许广平来信说“政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到(道)国家主义的周刊《醒狮》应禁,而不知变相的《醒狮》,随处皆是”[54],接着孙伏园从广州带回了顾颉刚被中大聘任的消息,让鲁迅觉得“似乎当局者于看人一端,很不了然”,因为“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55]。鲁迅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顾颉刚曾在北京参加“救国团”的事情。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被推举为出版股主任,负责《救国》特刊的编辑,并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连载。救国团是一个国家主义派占主导的组织,强调“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因而既反苏俄又反国共,由于不满于女师大风潮干扰了民众对“五卅”爱国运动的注意力,谭慕愚发表了批评性的公开信,“语侵李石曾、易培基等”[56]。李石曾、易培基随后策动救国团中国民党人反击,谭慕愚被迫退出了文书股。在顾颉刚看来,“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慕愚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57],为此他在《救国》特刊上发表文章声援谭慕愚,结果“邵飘萍(京报老板——引者注)以救国团攻击苏俄,不允将《特刊》继续出版”[58]。气愤难平的顾颉刚在最后一期登载谭慕愚的文章,将救国团内部“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冲突”公开化,以致“救国团中傅启学、梁渡、李凤举、钟书衡四人来信,责我在《救国特刊》中登谭女士《呐喊后的悲哀》一文,以为我放马后炮,破坏团中名誉”[59],自此双方彻底反目。
正是基于对顾颉刚这些言行的了解,鲁迅才会认为“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如今许广平说这些人又要在中大汇聚,而当局被其伪善所迷惑,所以他提出“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60]。而据顾颉刚日记记载:“鲁迅已到粤……即谓‘顾某与林文庆(厦大校长——引者注)交情好,他是不肯来的’,一面又使章廷谦在厦大内宣传:‘鲁迅是主张党同伐异的,看顾颉刚去得成去不成。’”[61]顾颉刚1927年4月到广州后,他发现鲁迅不但随即提出辞职,而且发现“鲁迅有匿名揭帖,说我为研究系,要人签名反对”[62]。不仅如此,鲁迅还给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去信,“云:‘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其徒谢玉生亦与函,同是对我破口大骂,而伏园加以按语,增其力量。此信于四月某日刊出,如我在武汉者(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63]。顾颉刚自然非常愤怒:“我诚不知我如何‘反对民党’?亦不知我如何使兼士为我愤愤?血口喷人,至此而极,览此大愤。”他接着自辩说:“我虽纯搞学术,不参加政治活动,而彼竟诬我为参加反动政治之一员,用心险恶,良可慨叹。”[64]顾颉刚说自己“纯搞学术,不参加政治活动”,显然经不起事实考辨,但他认为鲁迅“用心险恶”虽是揣测,但也确实是鲁迅此时对反动派的基本态度:“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65],因此办法只有一个——“研究系应该痛击”[66]。
不难看出,此时鲁迅和顾颉刚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表面看,这是“五四”后开始的新知识阶级分裂的延续,但与北京时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派系冲突不同,厦门国民革命形势和鲁迅政治思想的变化,将二人从同一阵营的内部矛盾激化成敌与我的政治对立:顾颉刚变成了反革命,而自居革命的鲁迅则“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三、学潮的悖论:党化教育与“火老鸦”
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除了表现在他和政党、知识分子的关系外,还涉及青年学生,但鲁迅对学潮的态度颇为复杂,他一方面支持许广平压制广州女师学潮,另一方面却又鼓动厦大学潮,使我们看到“青年叛徒的领袖”及“党同伐异”的悖论性一面。
1926年夏许广平毕业后,受广州教育局视导“陈向庭表叔”[67]的推荐(教育厅厅长许崇清是其堂兄),回到母校广州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教八班,每班每周一小时三民主义”[68]。这是一个新设岗位,1926年5月,广东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宗旨应注意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以完成国民革命”,要求各校“校训应定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增设政治训育部”[69]。许广平能被委此重任,是因其国民党秘密党员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的身份。而她也很想在这个位置上有所作为,她对鲁迅表示:“以人力移天工,不是革命人的责任吗?所以,在女师,有时我常常起灰心,但也高兴,希望能转移她们。”[70]
鲁迅对于党化教育虽然从未明确表态,但一直有所支持和参与,譬如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71],而他之前参与的女师大风潮,正是国民党在北京高校推行国民革命和党化教育的重要举措。至于邀请鲁迅去“议定学制”的中山大学,其改制的目的就是“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72],而鲁迅正符合中大“拒绝反革命分子,聘请良好教师”[73]的原则。鲁迅不但主动表达前来的意愿,还对中大聘请了“反民党”的顾颉刚非常不满,认为“当局者于看人一端,很不了然”,由此不难看出鲁迅是自觉基于“革命”的标准来进行的评判。
而许广平担任训育主任后虽然抱负极大,但最初“对于训育,甚无进展”[74],因为“学生会为右派把持”[75]。不过“忽然间一个机会来了”,由于学生会主席李秀梅私下选举自己的“树的派”成员参加广州学联会议,许广平以“违法召集会议,违反校规”[76]的名义,将李秀梅等人开除,她“得意”地告知鲁迅,一方面“现时背后有国民政府,自己是有权有势,处置一些反动学生,实在易如反掌”,另一方面“校长教职员,有力者都是左的,事甚好做”[77]。知道此事后鲁迅评论说,“中国学生学什么意大利,以趋奉北政府,还说什么‘树的党’,可笑可恨”;“校事也只能这么办。但不知近来如何?但如忙则无须详叙,因为我对于此事并不怎样放在心里,因为这一回的战斗,情形已和对杨荫榆不同也”[78]。
但是,许广平发现被开除的学生先是“以共产二字诬校长,教职员”[79],后又极力酝酿罢课,为此她成立了“革新学生会同盟会”进行对抗。但校方情况越来越差,经费拖欠、校长辞职,许广平为此抱怨不已。鲁迅回信安慰说:“事到如此,别的都可以不管了,以自己为主,觉得耐不住,便即离开。”[80]然而,许广平的处境越来越糟,随着形势的“右倾”,学生开始骂许广平是“(共党人)走狗”,于是她接受了鲁迅“躲起来”[81]的建议,请病假逃回家里,至此广州省立女师风潮告一段落。而鲁迅在接下来1927年1月7日爆发的厦大学潮中,却转而支持学生反抗学校,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厦大学潮的爆发,实际是国民革命和鲁迅的合力所致。厦大此前就风潮不断,1924年因校长林文庆要求学生“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82]而爆发学潮,随之被国民党利用,他们煽动一部分学生“出校创校”并提供经费[83],最终在上海成立了大夏大学。此次风潮虽让厦大遭受重创,但因为“厦门大学为私立学校,苟陈嘉庚氏始终袒护林文庆,则改革一层,颇为不易”[84]。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动,国共两党1925年重新派人回到厦门,“发展国民党左派,建立秘密组织”[85]。不过,“因厦地各界思想太落后,极难接受革命宣传”,到1926年4月厦大左派也只有“五十余人”[86]。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等北大新文化派的到来,使他们想借机再次发动起学潮。不过,鲁迅很快察觉了他们的意图,他对许广平说:“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87]“有几个学生很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88]对此,许广平建议说:“学生欢迎,自然增加你的兴趣,处处培植些好的禾苗,以喂养大众,救济大众吧。”[89]而鲁迅也尝试着“鼓动空气”[90]:首先,他支持俞念远、王方仁、魏兆淇等文学青年成立了泱泱社、创办《波艇》。其次,他参加了学生党员的会议,了解到“本校学生中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但他颇为担忧地对许广平说:“昨夜开会,我觉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徒令当局者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却在门外窃听。”[91]再次,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演讲,譬如在厦大周会上倡导“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在集美学校呼吁学生“应该留心世事”,以致校长叶渊后来抱怨的“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指鲁迅——引者注)不好”[92]。鲁迅的这些言论“很得学生的信仰”[93],他甚至抱怨“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94]。
而随着鲁迅在1926年11月私下接受中大的聘任,在厦大聘期未满的他为了脱身,故意将“要走已经宣传开去”[95],同时拒绝校长请客和拜访,“他由此知道我无留意”[96]。不仅如此,顾颉刚还发现“鲁迅既得粤校聘书,便急切欲离厦校,而苦于无名,乃专骂林文庆与顾颉刚,谓厦大中胡适派攻击鲁迅派,使鲁迅不安于位,又谓校长克扣经费,使沈兼士无法负研究院责任,逼使回京云云,于是我与林遂为鲁派(旧徒孙伏园、章廷谦,新生谢玉生等)攻击之对象,不徒流言蜚语时时传播,又贴出大字报,为全校及厦门人士所周知,我与林遂均成反革命分子矣”[97]。
1926年12月31日,鲁迅正式递交辞呈,校方“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因而反复挽留,但都被拒绝。1927年1月4日,鲁迅参加了全体学生送别会,“夜中文科生又开会作别,闻席中颇有鼓动风潮之言”[98],于是“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99]。以罗扬才为首的厦大国共两党党员迅速行动起来,以“把持校务”“排斥异己”为由,要求驱逐理科主任刘树杞[100]。得知学潮重生的陈嘉庚极为愤怒,停办国学院并开除罗扬才等19名学生(近一半出现于鲁迅日记),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国赓见“此十九人中大部为驱刘委员会执行委员,隶籍国民党者十一人”,“知关键在民党方面,乃找市党部筹备处共出调停”,最终以厦大实行党化教育、免去刘树杞职务、收回开除学生成命等为条件调解成功[101]。
在风潮越闹越大之际,鲁迅自言“此次风潮,根株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102],但实际上他“放火”之功并不少,以致被舆论称作“火老鸦,到一处烧一处”[103]。然而从鲁迅对广州女师学潮和厦大学潮的不同态度看,他这个“火老鸦”显然并非一切“青年叛徒”的“领袖”,而是视其位置和政治倾向而变化,对青年学生既有鼓动支持(党同)也有压制利用(伐异)。
四、“党同伐异”与知识分子革命伦理
鲁迅后来在回顾厦门这段经历时,自觉“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104],他本来因为奉系军阀入京而情绪低落,但随着国民革命北伐的节节胜利,其政治热情重新高涨,开始憧憬着进入广州这个革命的策源地。显然,厦门绝非一个中转站或消沉期,而是鲁迅从思想革命者转向国民革命同路人的最终完成阶段,因而在其思想道路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厦门鲁迅在日渐左倾之时,我们却只见其批判右派的反动,不见其反思自身的激进。如顾颉刚就发现,此时鲁迅在厦大公开宣传自己“是主张党同伐异的”,甚至还在离开厦门之际撰文反对“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在报刊上公开提倡“党同伐异”,主张“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章士钊——引者注)为是者章辈”[105]。可见,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引发了知识分子精神和伦理价值观的重大变化。
“党同伐异”语出《后汉书·党锢传序》:“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106]在提倡儒家“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07]的中国社会里,“党同伐异”一直被认为是小人的行径,是一个中国传统学术批评伦理中的负面概念。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近代,“五四”思想界在引入西方自由主义伦理时,积极倡导“建设的批评论”和“学者的态度”,强调“第一,不可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第二,不可有攻击人身的论调”[108]。周氏兄弟最初也认同这种态度,譬如周作人倡导“文艺上的宽容”,反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109]。而鲁迅更是受尼采超人观念的影响,强调“独异”和“个人的自大”,反对“党同伐异”和“合群的自大”,认为这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110],“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111]。不难看出,此时的“党同伐异”仍是一个文艺批评内部与“宽容”相对的词。
但随着鲁迅卷入女师大风潮,他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先是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强调:“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112]后来更是在女师大复校后,反对《语丝》同人提出的“费厄泼赖”,明确提出:“‘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113]此时的“党同伐异”已经从一个传统上被否定的对象,变成了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公理正义”和“费厄泼赖”相对的正面口号,从一个文艺批评态度变成了知识分子派系纷争时的伦理价值观。而真正将“党同伐异”进一步提升为政治斗争革命伦理,无疑是在厦门阶段:鲁迅一方面将“党同”的范围扩大到南方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从“朋党”转向了“政党”、从“文化”转向了“政治”;另一方面又将“伐异”指向了知识界阵营内部,将私人冲突政治化,把顾颉刚塑造成反革命的“研究系”,进而将这种知识分子派争伦理推至学生运动之中。
这种转变出现的根源是政治形势的变化,由此导致“公平”“宽容”与“党同伐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实际上,“宽容总是在强者对弱者,或者两个势均力敌的存在者之间才会呈现的美德”,它其实是“强势者认同自由正当性所作出的自我约束”,因而“只有在相互承认宽容交往规则的基础上,普遍宽容才有可能”[114]。但问题是,不但北洋时代缺乏公共理性、充满了怨恨和不宽容,而且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一方最初处于劣势,因而他只看到现代评论派依附政治权力压迫己方的伪善,“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11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同伐异”反而成了团结弱者(在野革命)对抗强者(在朝政治)的必然武器,甚至需要“犯而必校”“以牙还牙”[116],以革命的暴力来对抗反革命的暴力。而随着厦门时期国民革命的胜利,逐渐左倾并即将进入广州的鲁迅,开始从在野革命转往在朝革命、从弱者转为强者,鲁迅不但公开宣扬自己的“党同伐异”,还表现出从怨恨心理到报复冲动的明显变化[117],并有意借助革命势力来打击自己的“敌人”。
显然,正是革命大潮的推进逆转了双方的关系,最终“公理宽容”成了反动的“学者”态度,而“党同伐异”则从一种“道德之恶”变成了“革命之善”,因其反抗和解放的进步功能,具有了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成为一种与现代革命共生的现代性现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何者为同,何者为异?鲁迅对此的看法是:“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118]“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119]
可以看出,“党同伐异”反对“公理”“上帝”这些外在的绝对性、超越性标准,强调判断的个人性和主体性,但在“自我/他者”或“我们/他们”的建构中,会陷入主观性和易变性。这主要表现在鲁迅对广州女师学潮和厦大学潮的悖论态度上,从“因为这一回的战斗,情形已和对杨荫榆不同也”这句话来看,鲁迅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悖论,因为在他的革命“战斗”精神视野里,厦大学生是革命左派,而广州女师学生是反动右派。
由此我们就发现“党同伐异”的背后,实际是革命伦理中“惟己独革”“惟己真革”的专断心态,不仅如此,革命人“对于异己的,一概加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积极消灭”[120]。也就是说,“敌对者很容易转化成一种邪恶的、野蛮的‘非我’”[121],最终变成恶魔。这一点在顾颉刚的命运中看得很清楚,他在厦门明显遭遇了一个从私敌到公敌再到“足制死命”的阶段变化。由此,“党同伐异”就从“暴力的批判”转变成“批判的暴力”,其负面效应开始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容易忽视论敌的复杂性,譬如顾颉刚其实看不起研究系,曾要求胡适“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因为“他们确自有取咎之道”[122],还表示“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123],所以他觉得“我如此欢迎北伐军,而鲁迅乃谓予‘反对民党’,岂不可笑”[124]。其次是容易回避对自我阵营的反思,顾颉刚就曾讽刺“鲁迅先生诋杨(杨荫榆——引者注)不遗余力,顾于易(易培基——引者注)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125]。而陈西滢也批评鲁迅“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126]。实际上,“党同伐异”的背后有一种“以革命的名义”施加的自利性,厦大学潮中鲁迅为了脱身有意利用学潮,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严重后果。风潮过后,陈嘉庚怒停文科各系,闹事的学生“人心惶惑”[127],致电陈嘉庚请求妥协,自此厦大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然而鲁迅关心的却是“我到广州后,便又粘带了十来个学生,大约又将不胜其烦,即在这里,也已经应接不暇”[128]。
尾声:走向“横站”
总之,厦门时期对鲁迅来说是一个“党同伐异”的革命化阶段,其知识分子斗争伦理开始和国民党的革命伦理趋于同一,此时他尚未发现“党同伐异”的问题,更多看到敌人一方的压迫,对于己方阵营却充满乐观的期待,“预料着广州这地方已进入光明、解放和自由的建设时代,不晓得怀着怎样的梦想和多大的希望来到这里”[129]。然而鲁迅到广州后的最大发现,却是革命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在野革命”一转成为“在朝政治”,最终这种“革命的政治化”导致了清党。鲁迅则因为之前北京的问题和在广州亲共,反而从“党同”变成“伐异”的对象,报纸上的流言“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130]。因此,胡适当初劝和时的话,显示了他的前瞻性,“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31]。
不仅如此,鲁迅还从青年人的惨死中,反省自己之前的“党同伐异”实则是背了“战士”招牌的“奉旨革命”:“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132]由此,鲁迅发现了“革命”内部的“政治”压迫问题,意识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133],此后他就重回“在野革命”,不仅再也没有公开倡导“党同伐异”,反而在加入左联后严厉批评左联成员“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134]。此时的鲁迅开始强调建立革命“联合战线”[135]的必要,并且特别指出“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36]。
“横站”的出现,表明鲁迅和左翼政党在“党同伐异”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离,双方在对国民党等反动势力进行“伐异”方面仍有基本共识,但在“党同”问题上,鲁迅开始正视和批判革命阵营的政治压迫问题,因而在左翼内部选择了“横站”这个新的知识分子革命伦理。不过,“横站”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总结的那样,“‘横站’与‘过客精神’、‘反抗绝望’、‘历史中间物’等构成了鲁迅精神的核心”[137],将鲁迅塑造成“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形象,表面看抬高了他的地位,视之为非左非右的第三条路线,但严重背离了鲁迅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横站”是以“革命联合战线”和“革命同路人”为支撑的,因而它以“联合”为目的,试图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来对抗敌人,由此鲁迅联合的对象就不仅有中共,还有宋庆龄、蔡元培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可能联合的革命左派。此外,“同路人”不同于“党员”,后者无法放弃“党同伐异”的僵化路线,因为左翼政党是从阶级论出发看问题的,在此视野中个体虽然可变,但阶级性质不会变化,所以“党同伐异”的背后是阶级对立和阶级专政的问题,而革命同路人却具有“自由漂移”[138]性,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僵化的政治,表现出“横站”的优越性。
但是,“革命同路人”的定位也说明“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在革命时代的消失,他们放弃了充当主体阶级来领导社会变革的可能。实际上从晚清开始,梁启超就提出过“中等社会之革命”[139]的号召,而五四运动也暗示了“知识阶级”相对于政治集团的优先性,但知识阶级有着先天的结构性缺陷,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阶级”观念,不能有意识地构建客观阶级归属(经济结构)和主观阶级认同(文化政治)合一的“知识阶级”主体,总是习惯性地着眼于思想文化批判,不断因认同问题分裂,而非凝聚本阶级的力量。先是“五四”时新旧知识阶级分离,然后是国民革命时代英美派和法日派分裂,此后是鲁迅的《莽原》内部分裂,最终从一个“阶级”变为“阶层”再变为“分子”,正如曼海姆指出的,“知识阶层并非一个阶级,也无法组成一个政党”[140],因而批判知识分子在具有“自由漂移”优点的同时,要想对社会变革有所作为,就必然陷入某种“依附性”,追随革命做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点上,“横站”实际表征了“革命同路人”的困境,他们无力领导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只能依附革命政党和其他主体阶级起到某种从属性的作用,因而“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141],但是,“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144]。
①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②“孤岛过客”来自房向东的《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崇文书局2009年版)书名。
③⑨[132] 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第1卷第49、50期合刊,1927年10月1日。
④[128] 鲁迅:《270102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第599页。
⑤ 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⑥ 参见朱水涌:《厦门时期的鲁迅:温暖、无聊、寻路》,《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张全之:《鲁迅在厦门时期思想与生活态度的变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王富仁:《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⑦ 王得后:《校后记》,《两地书全编》,第655页。
⑧ 鲁迅:《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
⑩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362页。
⑪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⑫ 鲁迅:《260914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73页。
⑬[87] 鲁迅:《261010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96页,第496页。
⑭[78] 鲁迅:《261109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31页,第531、532页。
⑮⑲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11页。
⑯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6页。
⑰ 《日陆军中将南游后之革命军观察(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
⑱ 张嘉森(张君劢):《一党政治之评价:一党能独治耶?》,《晨报》1926年12月5日。
⑳ 鲁迅:《革命时代底文学》,《黄埔生活》第4期,1927年6月12日。
㉑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61页。
㉒㉚㉜[52][65][88] 鲁迅:《261020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08页,第506页,第508页,第507页,第508页,第507页。
㉓ 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第197页。
㉔ 岂明(周作人):《南北》,《语丝》第104期,1926年11月6日。
㉕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420页。
㉖㉙ 鲁迅:《261015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03页,第503页。
㉗㉘ 许广平:《261007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494页,第494页。
㉛㉝[74] 许广平:《261018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05页,第505页,第506页。
㉞[90] 鲁迅:《261023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14页,第515页。
㉟[54] 许广平:《261027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16页,第516页。
㊱[66] 鲁迅:《261101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21页,第522页。
㊲㊶㊷㊸㊺㊼[53][56][57][58][59][61][63][64][97][125] 《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32页,第832页,第673页,第710页,第832页,第798页,第778页,第657页,第659页,第662页,第669页,第833页,第834页,第836页,第832、833页,第659页。
㊳ 鲁迅:《261115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42页。
㊴ 《中大党部欢迎经代校长宣布革新计划纪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6日。
㊵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㊹[62][98][124] 《顾颉刚日记》第2卷(1927—1932),第15页,第39页,第39页,第29页。
㊻ 鲁迅:《26092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81页。
㊽ 鲁迅:《260920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76页。
㊾ 鲁迅:《260930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89页。
㊿ 鲁迅:《26101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04页。
[51][89] 许广平:《261014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00、501页,第501页。
[55] 鲁迅:《26110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28、529页。
[60] 鲁迅:《261107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30页。
[67] 许广平:《260908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468页。
[68] 许广平:《260912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469页。
[69] 《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
[70] 许广平:《261010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498页。
[71] 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3月12日。
[72]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8日。
[73] 《广东大学近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5日。
[75] 许广平:《261104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24页。
[76] 《女师学生纠纷彻底解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5日。
[77] 许广平:《261107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27、528页。
[79] 许广平:《261113致鲁迅》,《两地书全编》,第540页。
[80] 鲁迅:《26120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70页。
[81] 鲁迅:《26121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84页。
[82] 伐木:《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怪论》,(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4月14日。
[83] 《行将成立之大夏大学》,《申报》1924年7月4日。
[84] 《大夏大学成立经过及其现况》,《教育杂志》第17卷第2号,1925年2月20日。
[85] 连尹:《罗明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厦大党史资料》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86] 《夏特志关于三月份的综合情况报告(1926年4月16日)》,《厦大党史资料》第1辑,第21页。“夏特志”即中共党团混合的厦门市特别支部。
[91] 鲁迅:《261125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57、558页。
[92] 鲁迅:《海上通信》,《语丝》第118期,1927年2月12日。
[93][123]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3页,第426页。
[94][96] 鲁迅:《261224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91页,第591页。
[95] 鲁迅:《261215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83页。
[99] 鲁迅:《270106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603页。
[100] 蜀生:《厦门大学的驱刘运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3日。
[101] 蜀生:《厦大风潮尚未解决》,《申报》1927年3月8日。
[102] 鲁迅:《270111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606页。
[103] 卓治(魏兆淇):《鲁迅是这样走的》,《北新》第23期,1927年1月29日。
[104] 鲁迅:《通信》,《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105] 鲁迅:《新的世故》,《语丝》第114期,1927年1月15日。
[106]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107] 刘宝楠注:《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2页。
[108] 成仿吾:《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2月。
[109] 仲密(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晨报副镌》1922年2月5日。
[110] 迅(鲁迅):《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111] 风声(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7日。
[112] 鲁迅:《并非闲话(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133页。
[113][116]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莽原》第1期,1926年1月10日。
[114] 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273页。
[115]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117]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118] 鲁迅:《250503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430页。
[119] 鲁迅:《杂忆》,《莽原》第9期,1925年6月19日。
[120] 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121]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122] 顾颉刚:《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9页。
[126]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第171页。
[127] 《厦门大学风潮之余波·尾声》,《厦大校史资料》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129] 山上正义:《论鲁迅》,李芒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90页。
[130] 鲁迅:《略谈香港》,《语丝》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
[131] 胡适:《胡适致陈独秀(1925年12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7页。
[133][141]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5页,第121页。
[134]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4页。
[135]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
[136] 鲁迅:《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1页。
[137] 林春城:《横站与中国革命传统——王晓明的批判性、介入性文化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38][140] 卡尔·曼海姆:《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第130页。
[139]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05页。
[142]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5页。